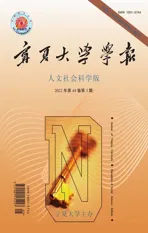庶民视域下东汉中晚期人才选评问题探论
——以王符《潜夫论·论荣篇》为考察中心
2022-11-23桂珍明夏保国
桂珍明,夏保国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自先秦以来,儒家非常重视“君子”“小人”之划分,及至东汉中后期,思想家王符对此亦有所措意。在继承先秦儒家学派“君子”“小人”分辨的思想基础上,王符还结合当时“浮华交会”“以结党助”的社会现实,批评在人才品评、选拔过程中,“世不识论,以士卒化;弗问志行,官爵是纪”[1]之弊端,因感伤风俗陵夷,远离圣人之道,遂作《潜夫论·论荣篇》。本篇以君子、小人之区分为始,引出身份、地位跟贤与不贤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进而指陈东汉中后期门阀政治兴起,豪门大族控制人才品评与选拔,品评士人“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不正常风气,并对此予以深刻批评。《论荣篇》结构明晰,正如彭铎先生所说,“此篇首明君子小人之辨,继论寡德高位之人不足以为荣,而终之以人惟其任”[2]。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韩复智《东汉大思想家王符之研究(一)》(《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8 年第5 期);王鑫义《王符的人才观》(《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2期);常校珍《王符的人才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1 期);周桂钿《国以贤兴——王符尊重人才思想述评》(《社会科学》,1988第1 期);赵英斌《王符用人思想的价值》(《社科纵横》,1994 年第6 期);杨春毅《谈王符量才授任明选考功的用人思想》(《社科纵横》,1995 年第1期);方军、荆琳《论王符的人才观与汉代儒学选贡制度化》,(《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1 期);徐玉金《略论王符的用人思想及其现实启示》及常东成《王符人才思想探析》(《王符治国安民思想与忧患意识研究。中国·镇原第二届王符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等论著对王符及《潜夫论》人才观的诸多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讨论,值得参考借鉴。然在王符的人才选评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故笔者不揣浅陋,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探讨该篇关于“人才”选评的说理层次和精神意旨。
一 贤人君子以品行志节高尚为荣
王符将此篇定名为“论荣”,顾名思义是要发表对“荣”的看法。当然,其思想意旨,又不局限于“荣辱”问题,此点稍后再论。在一般人看来,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大抵可以将“荣”的内涵概之。但是,通观《论荣篇》,王氏显然不是要论述大富大贵、高官厚禄者如何“荣”,而是针对当时社会对荣辱、穷达及对士人品评的现实,提出自己对于“荣辱”的看法。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辱厄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3]
君子、小人之辨是儒家学派众多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大焦点。如果自春秋上溯至西周时期,《尚书》《诗经》等经典多以“君子”为“本皆有位者之称”(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352 页),亦即“统治阶级”(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页),“小人”即“小民”“庶民”或“普通百姓”之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1 年版,第30 页),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襄公九年》),即此之谓也。从早期语义来看,以身份地位和财产占有的多寡来区分君子、小人,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君子、小人二者的身份更多地被赋予了道德、品行,乃至才干的意义。比如孔子强调,在德行和利益取舍方面,主张“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在道德品行修养方面,重视“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5],“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6],旨在把“君子”道德方面的内涵予以大幅度地扩充。此时,“君子”的上层身份这一义项已经淡化,在富贵与德义的选择方面,孔子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即便没有高官厚禄,君子仍有自己的坚守,与没有道德操守的“小人”自是不同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即为明证。此后,孟子、荀子更进一步地完善“君子”道德礼义方面的特性,遂成为后世士人的人格范型。还要指出的是,荀子已经将“士”与“君子”合称为“士君子”,此二者的身份或所指对象可能已经趋同。荀子所谓的“君子”,诚如周书灿先生所说,“似为战国时期士人的代名词。”[7]
王符在本段文字中,既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君子”“小人”的原始含义,同时又注意到此二者评判的复杂性。他指出,不能单凭“高位厚禄”“富贵荣华”和“贫贱冻馁”“辱厄困穷”与否的表面现象,就作出孰为“君子”,孰为“小人”的判断。其实,自孔、孟、荀以来的儒家,在给“君子”赋予道德含义的过程中,就蕴含着“士志于道”的价值追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了践行德义,追求心中的“道”,他们不会在意“食”与“贫”,也能忍受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当生命与仁义二者不可兼得之时,即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在所不惜,这昭示着他们将牺牲宝贵的生命去践行德义。
王符既然在《论荣篇》的开篇就把“君子”“小人”的问题揭示出来,自然有其深意在内。细读文本能够发现,这种安排正是为了引出东汉品评人才的标准。王氏在《潜夫论·考绩篇》中的论述正可与《论荣篇》相呼应:
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8]
在理想的状态下,君子爵禄显荣而身居高位,小人困厄而居于贫贱。但是,在实际中,荣辱显达与君子、小人的身份往往是倒置的。这个反常的现象,不能不引起王符的深入思考。此时东汉政权在社会品评和遴选人才的现实是,富贵的人凭借他们的财力,尊贵的人凭借他们的权势,社会上把财物丰厚者视为贤能,也把刚猛强横者视为上品。这种遴选人才的方式,貌似选出了才能俱佳的人,实则是颠倒黑白,与道德、学识、才干无甚关系,名不副实。比王符稍晚的汉末,人才品评、遴选不正常的风气更为严重。《抱朴子》一书中对这种非正常现象记录甚多,兹试举两例:
《抱朴子·外篇·审举》:
而汉之末叶,桓、灵之世,……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或卖要人之书,或父兄贵显,望门而辟命;或低头屈膝,积习而见收。[9]
《抱朴子·外篇·名实》:
闻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10]
通过葛洪的记载,我们对汉末人才选拔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其一,《名实》篇直接点出了汉末选士“名不准实”“品藻乖滥”这一社会现实。此时品评士人的标准严重乖乱,有才德之人得不到上升渠道。社会上品评人物以地位显达的人为贤才,出身贫寒的则为愚人,正是王符《论荣篇》君子、小人之辨的社会背景。其二,汉末选士崇尚权力、财力,政府和官员甚至卖官鬻爵。东汉自建立之初,世家大族的势力就很强,他们控制下的察举制,无可避免地会重视身份地位。道德高尚和坚持正道的人反而不如阿谀谄媚者能够受到朝廷的重用。与此同时,汉末公开卖官鬻爵,《后汉书》之《桓帝纪》《灵帝纪》《羊续传》《崔寔传》《宦者列传》等篇目对此现象皆有载录。这说明,此种导向是自上而下的,皇帝好钱财,“财力”因之成为皇帝及其利益团体选士任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时,学问德行要为金钱让路,仕途对于那些缺乏政治、经济实力的贤能守正之士来说基本上关闭了大门[11]。其三,世家大族控制人才选举的权力,攀附、请托、交接权贵之风盛行。葛洪指出,当时的人们为了仕进之道,不知羞耻、自贬身价,举凡献宝、攀附、仗势、门第都可得到提拔,等而下之,如向豪族低头屈膝者,也能得到任用。由此可见,王符在文中针对荣华富贵、穷达与否和君子、小人的区分所作的论断,正是基于此而发出的。
尽管如此,王符并没有随波逐流,屈从一般的士人评价标准。正是因为看透了身份、地位和富贵等不能代表贤能,故他仍坚持以儒家“德才兼备”的标准来判断君子,“反对贵族世袭权位和把富贵作为任贤的先决条件”[12], 故他在《潜夫论·本政篇》给出的答案是“苟得其人,不患贫贱;苟得其材,不嫌名迹”,亦即举贤不问出身、名气和经历。因为这些外在的方面固然重要,但却没有直指“君子”最核心的特质——道德修养、嘉言懿行。为了解答上面的疑惑,我们接着看王符的论述:
夫桀、纣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恶来,天子之三公也,而犹不免于小人者,以其心行恶也。伯夷、叔齐,饿夫也,傅说胥靡,而井伯虞虏也,然世犹以为君子者,以为志节美也。[13]
在引出君子、小人如何区分的基础上,王符还以具体事例进一步说明身份地位跟贤与不贤没有必然的联系。王符运用正反对比的方式,将身份地位较高的桀、纣、崇侯、恶来同生活困苦的伯夷、叔齐,出身低微的傅说、井伯(百里奚)进行对比。前者的身份地位高出后者不知凡几,然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却正好相反,足见地位高的不见得是君子,地位低下的也并非小人。桀、纣之劣迹,史不绝书,而以纣王及群臣更甚。《墨子·所染》曰:“殷纣染于崇侯、恶来,……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14]伯夷、叔齐因与周武王道不同而义不食周粟,纵饿死首阳山,然志得全。傅说和井伯,《孟子·告子下》记载说,“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百里奚举于市”[15],此二人虽出身卑微,然分别能辅佐殷高宗武丁、秦穆公建立不世功勋,其品行志节及才干当然值得肯定。
桀、纣及其臣属和武丁、秦穆公及其臣子,同样身居高位,前者臣属的出身虽强于后者,但功业却正好相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德行修养水平的不同。由此可知,“心行恶”的价值判断,表明了王符眼中的君子、小人,是与他们的道德修养及行事密切相关的。因此,本节所引的两段话,也可以看作是王氏对当时士人品评、遴选的黑暗状态有力的回击。比他稍晚的仲长统,直接把君子、小人荣辱贵贱倒置的情况视为“乱世”,“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16],此批评较之王符更为辛辣,可以视为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发展的顶峰。
二 品评士人:崇志行而轻遭命
王符在《论荣篇》的开头揭橥了君子、小人评价的问题,此部分则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即品评士人“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以志向和品行论定士人为正途。至于他们所遭逢的命运,穷达与否、宠荣与否、富贵与否,皆是外在的东西,不足以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故论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则虽有天下不足以为重,无所用不足以为轻,处隶圉不足以为耻,抚四海不足以为荣。况乎其未能相县若此者哉?故曰: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17]
本段中的“遭命”之“遭”当作“逢”或“遇”讲,诸如“有天下”“无所用”“处隶圉”“抚四海”都包括在此范畴之内。该词的含义略等同于后文的“二命”,所不同者“遭命”乃混言之,“二命”乃析言之,等同于《潜夫论·卜列篇》的“行有招召,命有遭随”之“遭随”。需要辨明的是,俞樾、彭铎认为,此处的“遭命”不同于《纬书》及《潜夫论》后文之“遭命”,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俞氏认为汪继培“不本上下文为说,而泛举《援神契》之遭命、随命以说此‘二命’,失之”[18]。(按:汪氏固然没有严格地以富贵、贫贱释“二命”,但俞氏也未注意后文于富贵、贫贱而外,尚有“潜龙未用”“亢龙在天”,难道“君子”的穷达,不在“二命”之中吗?)自此而言之,拥有天下的君王、未出仕的人才,身陷囹圄的奴隶杂役、抚有四海的统治者,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正是“遭命”的不同样态。
又,“遭命”亦见于《庄子·列御寇》篇,“达大命者随,达小命者遭”,历代注家皆以“遇”释“遭”。然核诸《庄子》文本,其中有“凶德”“中德”,最后分别以“达于生(性)”“达于智”“达于命”作结。倘若“随”为随顺,“遭”为“遇”,二者似无必然的对立成分在内,只作一“命”字即可,大小、遭随之区分似不必要。因之,我们再来看《论衡·命义篇》对它的说明,“随命者,勠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19]《春秋元命苞》也有与之相近的解说,其曰“有随命,随命者,随行为命也。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误,逢世残贼,君上逆乱,辜咎下流,灾谴并发,阴阳散忤,暴气雷至,灭日动地,天绝人命。”[20]从这里不难看出,“随命”是根据行为得到的命运,善恶施报非常明显;“遭命”是正道直行而意外遭到的祸患。可见,“遭命”“随命”的区分也是存在的,只是所指不同。综上所述,“遭命”既可作一般意义上的遇、逢讲,又可以作为偏向消极意义的“逢世残贼”来理解,其限定条件则是各自所依据的具体语境。
早在东汉前期,《论衡·逢遇篇》就将才能德行与身份贵贱无关的问题揭示了出来: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21]
在王充看来,士人能否得到任用而出仕、能否荣华富贵,与才能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此时,他更强调“遇不遇”之“时”的作用。当然,这也和国家取士的标准、制度以及士人阶层“德才并举”出仕任官的价值观之间的分离有关。士人能否“遇”,固然有偶然的因素在内,但时、逢、遭、遇与“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将士的才德修养同富贵显荣剥离开来,给士人一个看似可以接受的解释;另一方面,“命”“数”等必然因素与“时”“遇”互为依托、循环论证,最终也没能道出“不遇”的真谛。
王符处在东汉由盛而衰之交,相比王充来说,他对士人的品评和选拔制度所存在的问题,看得更为透彻。他深知察举制之弊端,提出了以“志行”为导向的选士标准。众所周知,汉代以察举制选官,同时还有征辟、恩荫等其他授官方式。这项制度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其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就已显现,据荀悦《汉纪·武帝纪》记载,“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22]。 说明西汉时期的察举已非其实,“游行”者结交朋党,名誉、喜怒、亲疏乃至舆论等,皆受利益团体的左右。《后汉书·韦彪传》记载了东汉前期汉章帝时选士重“阀阅”而轻“才行”的情况,韦彪谏言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23]及至东汉中后期,门阀世族的权势进一步加强,对官员选拔的控制更为严格。曲利丽先生认为,“王符不再像王充那样把个人仕宦的沉滞归之于命运而安然处之,他看到了选举制度本身存在的种种弊端。”[24]这个认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还要补充的是,作为庶族代表的王符,其本身也深受察举制流弊之害。《后汉书·王符传》记载说,王符“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25],“‘无外家’‘庶孽’的身份,决定了王符低人一等的命运”[26],又不事交游引荐,“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27]王符不但看出了选举制度存在的弊端,而且还以激切的言辞勇于抗争,符合儒士积极有为的作风。他主张“崇志行而轻遭命”,坚持以志向与德行的品评为选拔人才的基本观点,黜退以外在的身份、地位、财力作为遴选士人的条则,几乎是对整个上层社会选士标准的批判。这既是王符作为庶族对个人命运不公的呐喊,也是东汉庶族对豪门世家的一次挑战。
三 权位不足恃,求贤不责备
东汉中晚期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上文已略作了一点探讨,而王符在《论荣篇》中,更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评析当时的人才品评和选举制度,进而提出他所认可的人才观。以下,我们将循着作者的思路,从东汉中后期人才评鉴和选拔、王符的人才观两方面出发,探索《论荣篇》的核心意旨之所在。
(一)“以族举德,以位命贤”之不足
王符强调好的声誉由个人自我成就,而非由他人品评、称誉而来。世运的穷达、遭遇则是上天所决定的,具有一定偶然性。王符论理,喜引经据典,此处亦然。他引据《诗经·邶风·北门》之诗,不是空谈形而上的“天道”究竟如何左右命运,而是立足现实,化用《周易·乾卦》之《文言传》“潜龙”“亢龙”的事例,以此证明个人的升降沉浮,与他们的才能、德行的好坏关联度不高。“君子”可能在野,“小人”也能够居于高位,足见仅仅依靠单纯的“富贵”“贫贱”等表面现象是难以判定人们贤愚的。
夫令誉从我兴,而二命自天降之。《诗》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或潜龙未用,或亢龙在天,从古以然。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兹可谓得论之一体矣,而未获至论之淑真也。[28]
通过这段文字,王符向大家道出了当时的实情是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士人的品评、选用靠的是以家族出身定德行、用社会地位任命贤能。这样做的好处自不待言,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及其依附者,往往能够轻易地利用规则获得美名和高官厚禄。仲长统《昌言》直接将这种“选士而论族姓阀阅”的方式贬斥为天下“三俗”之首。[29]阎步克先生在其《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一书中将“选官的腐败”“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视为“汉末的选官危机。”[30]王符直接点出“今观俗士之论”所说的“俗士”,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掌控仕进之途的豪门大族。当然,他也没有完全否认世家大族、身居高位的人里没有贤能之士,这一点是非常公允的。因而,他所说的“得论之一体”,先承认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是非常有局限的,即“未获至论之淑真”,没有得到最本真的品评士人之法。王氏先肯定以家族出身、社会地位评选士人的方法有可取之处,而后又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欲抑先扬的手法运用得非常成熟,增强了说理的效果。
王符既然指出了“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不可取,那么,他又是如何论证这一命题的呢?王符非常善于引用古圣先贤的事例作为论据,使用正反对比的方法,引用尧、舜、禹、周公、叔向、季友、颜回、原宪及丹朱、瞽叟、鲧、叔鲋、庆父、管叔、蔡叔、周厉王、周幽王的史事,“通过他们虽同出一族,地位显赫,而人格品行却完全相反的对照,有力地反驳了俗士的谬论”[31],说明“论士以族”“论士以位”既不符合人才的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儒家先圣的经验教训。
尧,圣父也,而丹凶傲;舜,圣子也,而叟顽恶;叔向,贤兄也,而鲋贪暴;季友,贤弟也,而庆父淫乱。论若必以族,是丹宜禅而舜宜诛,鲋宜赏而友宜夷也。论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
昔祁奚有言:“鲧殛而禹兴,管、蔡为戮,周公佑王。”故《书》称“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厉之贵,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颜、原之贱,匹庶也,而又冻馁屡空。论若必以位,则是两王是为世士,而二处为愚鄙也。论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32]
其实,族姓与地位问题,我们还能以《孟子》中的史事为例,对此加以补充说明。先看族姓和出身问题。《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33]他们所处的地方一东一西,可能还与“中原”相距较远,族源上具有东夷或西部族群的血缘,但这都不妨碍他们是圣人,其德行历千古而永光。若以地位看,武王伐纣则是臣弑其君,《孟子·梁惠王下》评论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34]。倘若用东汉“以位论士”的标准来看,岂不是愚钝粗鄙之人讨伐圣贤吗?何来“安天下”“诛一夫”之说?《庄子·盗跖篇》引子张之语曰:“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35]正可为王氏以“志节”“心行”为中心的选士思想之注脚。不难看出,王符的选士、论士观是严格继承先秦儒家学派的人才思想而来的。
纵论古代先贤、奸凶之人后,王符再一次将东汉中后期品评遴选士人的准则提了出来,指出“以九族”“以所来”选士方式,越来越背离选才之实,距离获得真正的贤才则更加远了。
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今之论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来,则亦远于获真贤矣。[36]
我们认为,《论荣篇》的主旨即“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也就是说,仁德与权势相比,地位和道义相比,仁德、道义更为重要。权势和地位不足以涵盖贤才的优长,上文已经举例予以论证了。因而对于东汉中晚期品评士人的问题来说,那些固守家世和地望观念来选士的人,实则是放弃了真正的选士准则。东汉自立国之初,豪门大族的势力就非常强大,他们在政治上占据要职,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私徒属、宾客、庄园,学术上以经学传家,进而形成了累世公卿、累世地主和累世经学的三位一体的垄断,取士看门第、阀阅即由此而来。同时,作为官僚的世家大族之人,又影响和掌控着地方上的人才品评、遴选渠道,引导着社会上人才品评的舆论导向,门阀政治正在形成当中,成为了东汉社会的一大痼疾。
王符没有在《论荣篇》过多地描述“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现象,但其《潜夫论》的《务本》《贤难》《明暗》《考绩》《思贤》《本政》《潜叹》《实贡》《三式》《交际》诸篇对此则多有载录。《潜夫论·本政篇》指出选官之人畏惧贵族的风评、权贵之嘱托,致使“请谒阗门,礼贽辐辏”“请托”之风盛行,长此以往,所谓的察举,往往所选非人,名实不副、触目惊心者,如《考绩篇》所言:
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37]
豪门大族的子弟,凭借着垄断权力及其利益关系粉墨登场,一般的庶族士人则进仕无门,这正是“日益奏效的人际关系因素蚕食着官僚体制中所可能存在的政治理性”[38],世家大族和士大夫间的相互请托、“交游”的变质,使得本就不甚严密的察举制丧失了基本的效能。鲁惟一(Michael Loewe)先生指出,“吸收文职官吏主要是通过地方官员或朝廷高官的推荐。……但当时至少有一位作家(王符,约90—165 年)抱怨举荐制事实上更多地依靠循私而不是功绩。”[39]这种以“人际关系”为主导的人才品评遴选的情况,亦如王氏在《交际篇》所揭露的那样,“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至此,制度设计中的正式选举规则已然失灵。对于庶族士人来说,他们所倚重的“明君”和政府,在人才选拔方面,早已作出了选择,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减弱乃至阶级固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成了当时真实的写照。这样做的后果是下层民众由于对朝廷的失望,进而产生疏隔,相疏生怨,由怨而叛[40],历史遂陷入“一治一乱”的周期性循环中去了。
(二)举士选材不必求全责备
“国以贤兴,君以忠安”,人才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求贤任能是国家和君主的要务。一般而言,人们都希望拥有德行才能堪称完美的圣人,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完人”几乎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只有遵循德行道义的“君子”,才是选拔人才最可依凭的群体。王符在本节中延续出身、地望等话题,以古今对比的方式,再次托出他的人才主张——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选拔任用人才时,要“弃其所短而采其长”,不要以“完人”的标准去求全责备于他们。
昔自周公不求备于一人,况乎其德义既举,乃可以它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于五狄,越蒙产于八蛮,而功施齐、秦,德立诸夏,令名美誉,载于图书,至今不灭。张仪,中国之人也;卫鞅,康叔之孙也,而皆谗佞反复,交乱四海。由斯观之,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负苞,山野生兰芷。夫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产于蜃蛤。《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故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则虽细行小瑕曷足以为累乎?[41]
王氏于此所举之例,张仪乃中原之人,而卫鞅乃名门之后,他们的出身自然好过由余、越蒙,然核其功业,出身好的反而不如“夷狄”“蛮越”之人。如果说,由余、越蒙因出身不好而被视为瑕疵,这正与山野生长出来的兰花、白芷,璞石生长出来的和氏璧,蜃蛤生产的隋侯珠一样,低微卑贱的出身,并不能掩盖其本身的“大美”。回到现实中来,东汉朝廷和社会评骘士人、遴选人才,又怎能限于人才的出身门第,而将他们的大才掩盖呢?他还引《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为证。诗文中的“葑”为须,“菲”为“芴”,“下体”毛传曰“根茎”,郑玄笺云,“此二菜者,蔓菁与葍之类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时并弃其叶”[42],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篇》亦曰“取其一美,不尽其失”并引此句为释[43]。可见,王符于史实之外引经据典,仍然在为选任人才当取其长的方面作补充说明,以增强其说理的可靠性。在圣与贤的任用选择上,他还在《潜夫论·实贡篇》中申述道,“夫圣人纯,贤者驳,周公不求备,四友不相兼”,肯定除了圣人以外的其他人才群体不是“全知全能”的。更何况到了东汉衰微的时期,取士更应当从其志节、德行大的方面来考量,而非纠结于他们的出身族姓和世俗的毁誉。
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国士,而患其非忠;世非患无臣,而患其非贤。盖无羇縻。陈平、韩信,楚俘也,而高祖以为藩辅,实平四海,安汉室;卫青、霍去病,平阳之私人也,而武帝以为司马,实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远之有?然则所难于非此土之人,非将相之世者,为其无是能而处是位,无是德而居是贵,无以我尚而不秉我势也。[44]
国家到底应该重视士人的什么方面呢?王符回答说,忠与贤。忠出于德行,贤出于才能,此为任官选士的重要标准。他在《务本篇》强调臣下的道德与品行,“人臣者,以忠正为本”“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正是忠诚、忠信与贤能的合一。陈平、韩信早先都是项羽的人才,于汉而言,他们的身份是“楚俘”;卫青、霍去病起初也只是平阳侯的奴仆。汉高祖任用前者而平定四海、安定汉室;汉武帝启用卫青、霍去病为将军,征伐匈奴,置郡河西,开疆拓土。如果高帝、武帝皆拘泥于他们的身份,又何来的大汉天下和河西四郡呢?综上,只要人才有能力,又和卑贱、疏远有什么关系呢?故此,王符在《本政篇》中倡言,“是故贤愚在心,不在贵贱;信欺在性,不在亲疏。”[45]国君需要臣下的,不在于他们的出身是否高贵,而在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忠信和欺诈在于人的本性,而不在于他们同君主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本篇的末尾,以“非本国之人”“非将相世家出身”的人,他们在现实政治中,所需要担心的是,没有才干却身处高位,没有德行而据有富贵,不能辅佐君主反而利用主上的威势。换句话说,只要有能力、有德行,能够为国家、国君尽忠,这一切的担心也就不存在了。同时,王符在此处虽没点明世家大族出身的人没有能力、没有德行、不辅佐君主却窃据高位、享有厚禄,但是,反讽的意味确是非常浓烈的,值得人们深思。
结 语
王符以君子、小人的穷达荣辱问题,引出东汉中晚期朝廷与社会在品评、遴选士人方面的道德品质与身份地位相倒置的问题。他在《论荣篇》中,借“论荣”以指陈世家大族控制下的门阀政治,世家大族相互交游、互相攀援举荐的黑暗现实。东汉豪门大族对朝廷有极强的影响力,他们在地方上控制人才察举的制度和人才品评的舆论机制,将门第阀阅、政治权力、经济实力作为评价士人贤与不贤的重要标准,更甚者,朝臣卖官鬻爵、明码标价,这就从制度体系中将庶族排除掉了。这样一来,本就不严密的“察举制”在请托交游、人际关系因素的干扰下,极大地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怀抱真才实学、道德行为高尚的庶族士人进取无门,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作为庶族出身的王符,他的下层生活经历和正直耿介的秉性,让其对此时人才选评方面的弊端认识更加深刻。出于儒家士人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坚持“士志于道”的传统,故王符敢于将人才“不遇”的矛头直接指向豪族,重新提出以才能和德行作为考核士人的标准,旨在为国家遴选真正的人才,“反映了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参政要求”[46]。如果说王符以《赞学篇》作为全书之始,是为了给“贤才”的判断定下一个标准,本篇则旨在申述“势轻”“位蔑”的寒门庶族之人,其生活境遇与经历也并不影响其本身所具有的道德仁义和聪明才干。总之,王符意在呼吁朝廷应当把视线更多地放在社会下层,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