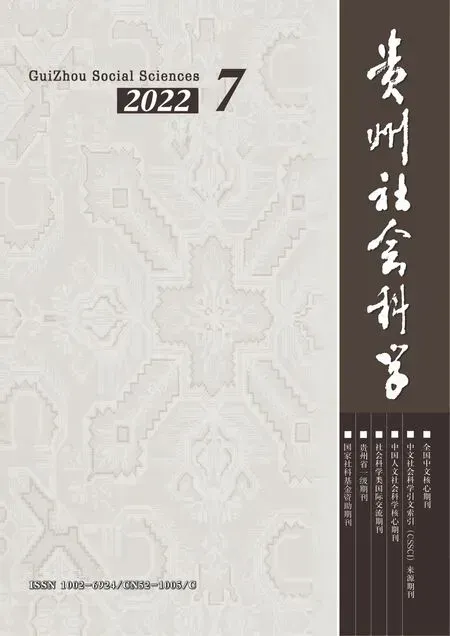工业口述史中家庭记忆的建构与传递
——以鞍钢为考察中心
2022-11-21刘凤文竹
刘凤文竹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中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方法的口述史学诞生以来,口述方法便迅速地摆脱了个体口述的单元选择,而开始探求其复杂的主体构成。以哈布瓦赫为代表的“集体记忆”学派着力强调通过家庭记忆找回社会记忆的隐秘链条,开辟了口述史研究的新局面。尤其是当我们运用工业口述史的方法,从家庭记忆建构与传递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展开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官方文献和正史所未加刊载的珍贵事实,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持。
(一)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与鞍钢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的凋敝境况,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成为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当时中国共产党恢复全国生产的策略是,先利用东北已有的残损工业基础建设工业基地,再以此为基础尽快恢复国内工业生产。1948年2月,鞍山解放后,东北局立即作出“逐步恢复鞍山钢铁生产”的指示,同年1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1]14。在这一背景下,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凭借强劲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组织与调动劳动者进行鞍钢建设。此后,伴随“一五”计划的实施,鞍钢进入大规模建设和发展的兴盛时期,除提前完成“三大工程”外,基本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生产基地[2]17。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恢复和建设起来的特大型国有钢铁企业,鞍钢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快速的工业发展给鞍钢带来的直接结果,不仅是生产出优质的钢铁,同时也塑造了共和国第一代社会主义“工业人”群体。在“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斗争”的理念之下,以革命年代“生产战斗”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理念,绝大多数工人被塑造成具有集体主义精神、敢于牺牲奉献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与此同时,国家强有力的整合与动员能力使其所在家庭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工业化建设运动之中,导致单位人呈现出明显的“复数性”[2],包括个体生命及其所属家庭的生命史变迁均被导引进工业化建设的历史洪流中,使得二者(工人阶级和工人家庭)与共和国工业化进程具有深刻的勾连性与内在一致性。遗憾的是,相比于对鞍钢工人其人其事的文字书写不胜枚举,从社会学学科视角对其生命历程及家史变迁的口述史研究并未充分展开,而学界现有关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研究也多局限于自上而下看历史的阶段。记忆是口述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在中国工业口述史研究中记忆同样是中心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要破解在国家宏大叙事之外,那些被视为对当今工业发展起重要奠基性作用的重要历史,探索具体个体的微观生活及其表述背后的内在纹理,对这一群体记忆的析出及对其历史叙事内容展开研究显得十分重要,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二)口述史中的“家庭记忆”
记忆是口述史研究的核心议题,自19世纪末以来,传统史学强调历史研究应框定在明确可考的官方档案及文献史料的范围内的观点受到激烈抨击,研究者开始提倡关注在官方历史档案等研究资料之外平民大众的非正式历史。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社会学开始进入口述史研究领域的。口述史一方面被赋予超越传统史学过于专注精英史研究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通过寻找普通百姓生活的记录,并以其特有的生动性与鲜活性被冠以“会说话的历史学研究”[3]。易言之,作为在既已存在和流传的事迹与传统之外的一块“白板”,口述史自诞生之日起就倾向于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回视与打捞“沉默”的历史,对既有历史进行补白成为其核心追求之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理论对“元叙事”的摒弃与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推崇,将叙事从科学的独断论中进一步解放了出来[4]。这表明,“正统共识”对日常生活的忽视被日渐打破,社会学口述史的补白功能越来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一意义上,家庭记忆由于具有一定的个人化与私密性特征,成为对正统历史补白的重要渠道。家庭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对其概念及内涵界定学界尚缺乏系统性讨论。但一种较为公认的观点认为,家庭记忆的形成与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5]。就其功能而言,德国学者阿斯曼提出,家庭记忆即为“世界历史的私人通道”[6]51,甚至认为“家庭史是世界史的对立史”[6]70。
口述史的另一核心追求则表现为对“时间极限”的追索,而这一点往往被学界所忽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运用口述方法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经常面临的一种困境,就是因事件发生的时间距我们较远,且被访者受年龄、身体状况等客观因素限制,我们可能很难或者无法找到事件的亲历者,导致对其社会记忆的挖掘面临瓶颈。而面对时间的逼迫,家庭记忆往往可以满足研究过程中对“时间极限”的追索。所谓“时间极限”,主要是指在通过口述方法回溯个人记忆及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将时间前溯,以发掘到时间更早、更为丰富的口述记忆,并由此建立起时间上的连续性及因果解释的体系。换言之,口述史对“时间极限”的追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早期时间最大限度地回视,二是建立记忆连续性的过程,并据此进行因果阐述。
就鞍钢工业口述史中的家庭记忆而言,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第一批工业建设者,尤其是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参与者,如今已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应当承认,在记忆随时间进程趋于弱化的背景下,通过与其拥有共同经历的其他社会成员接触沟通,周期性地对相关记忆进行强化与再巩固,集体记忆的内容就会被再编码与再储存[7]。在哈布瓦赫看来,依靠家庭找回深藏的记忆是最为直接可行的方法,最常见的记忆扩展场域便是家庭,以家庭为根基,包括代际互动、口述、书信、仪式等形式在内的记忆形成路径在不断地进行着口语、身体以及文字等社会记忆的实践,关系较为亲密的人(如子辈)往往不仅与当事人生前的交往互动最为密切,可能共同经历与见证了某一刻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现场情境,对某些细节也较为熟悉了解,这种不可替代的“在场性”使得其记忆往往具有权威性,且最具时间阶段上“极限意义”的向前探索性,以至那些无法窥见的历史细节,可以通过对其子辈的访谈得到一种延迟性的弥补。第二,如果说正史所注重的是事件发生的社会结构与意义,那么家庭记忆则更加注重延续性。阿斯曼认为,个体的生活早就已经被嵌入进“超越个体”之上的生活,而没有这一个体之上的生活,个体生活根本不会出现并获得发展[6]51。席勒也同样指出,个体具有一种“向未来世代缴纳它已无法向过去世代所缴纳的债务”[6]51-74的责任,此外,施瓦茨曾指出,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8],集体记忆具有确保文化连续性的功能。也就是说,家庭记忆通过个体的形塑与表达,成为世代得以延续的“链锁”。正如哈布瓦赫所言,“寻找他们所在时期流行的各种类似的情况、通行的观念,以及一整套观念。正是这样,历史才没有仅仅局限为再现一个由过去的事件同时代的人们讲述的故事,而是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地不断翻新它。”[9]129本文以计划经济时期鞍钢建设与生产的过程为背景,以鞍钢第一代建设者的子辈的口述记忆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家庭记忆何以建构与传递,尝试解释这种记忆具有怎样的特点与主题,以及父辈对生命历程的意义赋予对后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
二、工业口述史中家庭记忆的建构与传递机制
长期以来,对于记忆的形成过程和影响机制研究多以心理学视角下个体维度的单数记忆为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所具有的社会属性。自哈布瓦赫创造性地提出“集体记忆”这一研究概念起,便将学界对记忆何以产生之研究引向了社会建构的路向。哈氏认为,“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9]93
(一)寻根机制
家庭记忆的建构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的代际互动之中,包括交谈、共同参与某项事件等。在哈布瓦赫看来,社会上并不存在纯粹的个体记忆,人类记忆形成过程中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等均是在社会交往的群体情境中实现的,个体利用特定群体(如家庭、社区等)情境进行记忆或再现过去。[9]129这种家庭记忆在子辈讲述个人历史的过程中自觉转化为一种“寻根意识”。寻根不仅涉及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追索,同时也包含微观层面上对自身家庭家系史的自觉探寻。通过对被访者叙述文本的整理分析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不断被强调的与那个年代有关的述说主题,其叙事模式通常以时间序列为基准,以时间上的向前追寻为特征,从童年时代家庭境况或更为早期的事件开始其讲述,首先实现时间上的“寻根”。此外,在时间上向前追索的过程中,普遍涉及的主题有:家庭的苦难、解放与奋斗以及家风教育三个方面。这几个主题互相穿插于寻根叙事的整体过程当中,在时间的追索中互相交织。
1.家庭的“苦难记忆”。家庭记忆往往是以“苦”的记忆为开端,大多数被访者以祖辈、父辈苦难的童年经历开始,讲述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家庭磨难,具体内容既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家庭生活的贫苦,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工厂工作的辛苦及三年自然灾害等特殊时期生活上的艰苦等。个人及家庭的生活之“苦”、生产之“苦”的双重叠加,成为回溯家庭历史时挥之不去的一大主题。
“那时家里没有做饭的柴火,冬天都得去外头搂草、搂树叶,浑身就穿那么一个空心棉袄棉裤,这个集(市)特别远,得走四十里路……那年老父亲19岁,在私人开的小煤矿干活,吃的苞米面做的窝窝头,都发霉了……那蚊子、苍蝇和跳蚤呀,工房里到晚间跳蚤满腿都是……我们到家以后,就吃野菜,吃糠,最后实在没钱了,还有仅仅那么一点钱,就把棉花籽买回来磨成面,做成饼子,搓一团一团的,就像吃中药。”(1)本文主要访谈资料来源于笔者基于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2020年10月合作展开的“新中国工业口述史”调查。AG03口述,2020。
“我父亲10岁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家里边就是很困难了,我父亲还有两个妹妹,为了养家,他14岁进到昭和制钢所,实际上就去做苦工,就是童工……有一次他偷看一眼,当时就挨打了,他不能学技术的,就是干苦力、干苦活。”(2)AG04口述,2020。
通过叙述回视家庭过往,将这种逝去的“苦难”转换为一种记忆模式,同时由这种苦难而锻造出来的家庭成员坚毅的品格得到子辈很大程度上的认同和自豪。
2.解放与奋斗。在鞍钢访谈中,除了强调苦难外,“以厂为家”“为工业中国奋斗”的内容构成了家庭记忆的另一突出主题,其前提是充满了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
”就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从火坑里(被)救出来了,就是这种阶级感情。(工作的)力量就是报恩,就是要无私奉献、忘我工作……国家当时提倡全国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我爸得以身作则啊,就把这些劳模、先进生产者(组织起来),白天工作发现很多问题,干不完,晚上到咱家来继续研究怎么解决……咱家专门腾出来一个房间,我奶奶当时70多岁了,和我妈就给他们烧水,我们这几个孩子,就跑腿,接这个人来,或者引路,有时候冬天下雪了或者夏天下雨了,咱们这几个孩子就跑出去帮着看自行车,拿布单、雨具把自行车车座盖上,不让它水淋淋的……六十年代正赶上自然灾害,晚上人吃完饭马上就得睡觉,怕饿,但是这些人从不考虑这些,有站的、有坐的,大部分是站着听、站着说。有一次后半夜两三点钟,都饿得受不了了,我妈就把两个掺苞米面的菜团子拿出来,但谁都不忍去吃,有人想了个办法,把它搓碎了,多添点水,(放)大锅里边熬成糊,这一大锅大伙一人分一碗粥糊,还真就熬过去了。”(3)AG04口述,2020。
“我记得(19)53年2号高炉大修,当时炉里有瓦斯,这个炉子就爆炸了,非常危险,先一股红烟、最后黑烟,炉上的工人就像流水似的都往下跑,这时听上面有工人喊“救命”,我老父亲一听,放下东西就往那炉子上头跑,去救人。后期我说‘老爸呀,那时你怎么还上?上面有瓦斯。’他说听着有人喊救命,他就上去了……”。(4)AG03口述,2020。
从讲述中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民翻身做主人、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使得百姓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激之情,同时将这种情感转化为工作的动力,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目标,成功塑造了一代甘愿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青年形象,这代人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奉献意识、感恩意识,这种意识在工业建设的氛围下变得更加强烈。而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公与私、社会与家庭、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城市社会中“国家-单位-家庭-个人”的链条使得家庭生活与工厂生产唇齿相依,成为家庭记忆的重要部分。
3.家风教育。如果广泛阅读口述史文本就会发现,子辈对家庭教育的印象尤为深刻,在很多情况下,子辈的叙述中夹杂着对家庭教育的回忆。而父辈为新中国工业奉献的状态在子辈身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制和继承。
“老父亲是劳模,我也受熏陶,我描图那时候要求写仿宋体字,我哪会写?但我也认真,晚上8点多钟给孩子喂完奶,睡觉了,我就拿那个纸拓,描,一写写到半夜……组织给我的任务,我指定干好,能吃苦,能认真干。后来我做审核、校对,就像这个数字,上头描的啥样,我就得去校对。我校对那么长时间,没出一个事故,父亲是我的榜样,那要是底下是40,上头你写个41,就麻烦了,那车床又得重卸、重整,所以说我很仔细、慎重。”(5)AG03口述,2020。
“‘好孩子永远不能说谎’,我一直牢记我爸的话,好孩子不能撒谎,这个我坚持几十年……当时我下乡我爸就讲,‘你得过劳动关、过生活关,姜不吃蒜不吃的,这都不行。’那时候我刚入这个厂,他没有说给我讲个十分、二十分钟的,没有,就说‘那和战场没啥区别,都是钢铁。’”(6)ZAG04口述,2020。
借助家庭中那些直接卷入到外部世界集体生活中去的人作为媒介,一个社会的普遍信念能够影响到家庭成员。哈布瓦赫认为,家庭记忆并不只是由一系列关于过去的个体意象组成的,不仅再现了这个家庭的历史,还确定了它的特点、品性和嗜好[9]132。“一个家庭所唤起的记忆和它试图在已离去的成员之中保存的记忆,无疑都会从这些成员的长辈那里汲取力量。”[9]132在这样一个工业化运动极为活跃的特殊时刻,父辈的创造精神和工作积极性对于子女的生活价值观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家庭记忆事实上承载着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将家风、文化认知等在代际间绵延。
总之,家庭记忆的寻根机制事实上是在一种历时性地追索的基础上,实现情感上的共鸣。被访者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线展开寻根问祖式地回忆,在传达自身生命历程之源头、形成历史上的感知的同时,也本着寻找家庭历史与特定主题的自觉,通过描述家庭的来源、变迁的过程等,将碎片化的生活细节加以回顾与整合,生成故事性很强的叙事,也从而寻找构建当下的根据,找到一种光环和意义,体现为心理上的“寻根情结”,是构建自我认同的材料。
(二)联结机制
一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结。记忆的每一个瞬间都是连接时空的,认同的时间维度关注的基本问题是认同如何处理自身与某事某物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家庭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特殊表征,其构建与传递具有维持自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连续性和同一性的功能。
二是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联结。家庭记忆的形成与传递是子辈与所在家庭构建连接的关键。家庭成员间密切的人际互动为记忆在代际之间传递和延续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作为旁观者或边缘性的参与者,子辈部分地参与了父辈生命历程中某些事件的发生,留下了特定观察视角下的相关记忆(如以家庭聊天、子辈参与长辈间聚会等形式),这种家庭记忆一方面连接着个人生活经历,另一方面也连接着家庭变迁历程。应当承认,这种记忆在家庭成员记忆中具有一定重叠性,家庭记忆的叙述图式被多个成员所接受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就会成为稳定的跨越代际的家庭记忆,同时,在传统“家观念”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式记忆,这种传播和认知的机制生成构建起个体与家庭的紧密连接。哈布瓦赫曾提到,记忆的回溯给家庭提供了机会,让家庭重新确认它的关系纽带,重新确认家庭的统一感和连续感。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9]82。
三是个体与社会的联结。心理学通常强调记忆具有单数性,将其视为个体心理活动的特征之一,但如果超越这种视点,我们会发现,个体及其记忆无疑是嵌入于整个社会语境当中。在哈布瓦赫的解释体系中,记忆是一种由社会维持并存储的符号,这一符号可以被社会成员所获取,而当记忆在社会环境中传递扩散时,易演变成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的内容。正是在社会关系和互动中人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具体而言,集体记忆最初仅是孤立的记忆,而通过符号互动或叙述,孤立的记忆获得了独特的结构,并具关联性和连续性,且与其他记忆信息互相印证并最终嵌入整个社会运行体系[7]。家庭成员通过对家庭记忆的回视,能够将自身置于社会情境之中,从而完成更大范围的定位与追索。而根据记忆信息的社会属性。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基于集体记忆的符号性与可传递性,笔者以为,个人的家庭记忆一方面是存在于家庭共同体中的个体记忆,另一方面亦是可以被社会成员共享与索取的符号系统。
(三)细节再现与修复机制
哈布瓦赫曾经提出,家庭记忆对遗失内容的修复事实上是一个“重构的画面”,在叙事过程中一些细节被有意识地集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能够有效地唤起对其父母的特殊回忆,并且重构已经变得生疏的家庭夜晚的日常氛围[9]105-106。这实际上是强调口述方法在社会事实的细节再现和修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对遗失内容的修复。由于时间的限制以及时人对其经历事件价值认识的局限,再现历史事实变得异常困难,而子辈一代由于其特殊的在场性使其获得了家庭事件“参与者”或“边缘配合者”的身份。人对于某一特定时刻的记忆是关于许多个这样的回忆的集中在单独的一个场景里,他描述的是对一个时期生活的整体概括[9]104-105。作为那段逝去并被遗忘细节的见证人,承载着前一代的人生经历,并通过调取相关记忆(有些资料是具有保管记忆意识的子代主动收集而来,并有意识地进行长期保存),能够将有关家庭的记忆激活并口述出来,从而对缺失的历史细节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补。
二是对时空转换后关系的修复。哈布瓦赫认为,修复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重塑机制,每当我们回溯到这些事件和人物,并对它们加以反思的时候,它们就吸纳了更多的现实性,而不是变得简单化[9]107。人通过回忆过往不断进行反思,在家庭记忆中,一些呈现出矛盾冲突,并造成家庭成员间关系紧张的记忆,在时空转换后吸收了当下现实性以后,可能有所转变。
“当时不理解,他上北京,我住他的房没能住上半年呢,撵我走,说那个是给他的待遇,不是给我的,‘你住影响不好,老工人住铁床、睡上下铺,你给我造成多坏的影响,赶紧出去。’当时房产部门还不好意思找我,他就追着他们,‘赶紧让他走,影响不好。’这个不能恨,人家是正面的,可当时是没法理解。”(7)AG04口述,2020。
记忆对亲密关系具有一定能动作用,因环境变迁而处在不断转化的实践之中。通过对家庭记忆的析出,人们对其加以反思,某些思想得以修复。这表明,家庭记忆的建构过程之于人并不是一个被“场”所限制的客体,而是能够影响人及其与周遭的关系,能够影响其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中被重构。
三、工业口述史中家庭记忆的价值及限度
从一般意义上讲,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重要方法,口述方法业已为中外学界所广泛认同。而将此种方法置于新中国为实现工业化而斗争的具体进程之中,我们会发现口述方法与工业口述史研究之间高度的契合性,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单位体制下“复数单位人”介入到工业化进程及历史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工业口述史中家庭记忆价值及限度作出进一步界定。
(一)口述史中的“时间极限”追求
如前所述,口述史中最为突显的传统有二,其一在于对正史不予记录的边缘人物话语的描绘;其二在于对社会记忆的时间追索。就前者而言,自口述史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此种使命,学界对此已进行系统研究,无须赘述。但就后者而言,仍需进行进一步阐释。有学者提出时间是一种主观的选择,也是一种嵌入在叙事语言内部的“深描”[10],而口述史无疑需要对这种“深描”进行最大限度的探寻,家庭记忆恰恰满足了这一需要,这是因为:一是将过往相关事件在时间上进行最大限度地回视,表现为时间上的“寻根机制”;二是通过回溯家庭过往、建立连续性的过程,搭建起因果解释的体系,表现为“连接机制”及“修复机制”。 家庭记忆是实现历时性和时间延续的器官,通过储存和重建功能,回溯家庭过往、建立起连续性。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内部的代际沟通成为建构及传递的重要方式,宏观国家社会变迁为其构建与传递提供了具体情境和记忆框架。
(二)价值与限度
笔者在鞍钢访谈的过程中,深深地意识到,通过对被访者家庭记忆的析出,有助于我们挖掘与解释那段不被人知晓的历史,丰富现有工业口述研究资料。许多被访者是在国家“为工业中国而奋斗”的制度话语及工人家庭家教的影响下走进国营企业,参与这场工业建设运动,以个人生命历程的转向为代价或结果,其生命体验与记忆的建构在“为国”和“为家”的交织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此外,家庭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一种特殊表征,对于进一步理解集体记忆的不同面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因为它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之间,不仅能够关涉个体的生命历程,同时也能反映出宏观时代背景。此外,还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家庭关系的写照。叙事的心理因素不仅仅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其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是关系的结果。口述历史并非只是为“典范历史”增枝节之末,更为重要的是,透过人们的口述历史记忆,我们可以在各种边缘的、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中,了解我们所相信的“历史”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11],而从社会记忆的视点出发,一个人对“过去”的记忆同时能够反映出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的社会现实[11]。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反思性理解,记忆不必可避免地存在主观建构的倾向,对家庭记忆的回溯不仅具有验证性、补充性,同时也具有再造性。哈布瓦赫曾指出,“记忆并非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凭之就能重建包含它们的整体。”[9]82在人们对过往生活和当时场景进行回顾与再现描述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润饰、削减或隐讳完善,乃至赋予其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9]91由于时间推移及时空转换,某些当时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在当下会被再描绘与再理解,甚至将其“放大”,而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文化曾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主张尊者、贤者、亲者的耻辱或不足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真实情感,理应受到保护。循此逻辑切入家庭记忆内部,我们会发现,由于家庭记忆具有这种“放大机制”,需要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进行对接,使得“说出来的记忆”带有一定的选择性、趋利性,构成了一种“主观的真实”,且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一意义上,集体记忆不是在保存过去,而是借过去留下的仪式、物质遗迹、经文和传统,并借助晚近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资料重构着过去[9]92-93, 其稳定性和灵活性受到社会框架的影响。
(三)家国关系与家庭记忆的建构
一般而言,宏大历史时间节点与微观个体生命史混合造就了家庭记忆的生成。无论是在传统中国、集体主义中国还是改革开放时代,家庭始终是连接个人与国家的重要纽带。纵观中国社会家国关系,“国”始终处在“家国关系”的主导地位,“家”为“国”的无上性提供了基本和首要支持。对于中国人而言,公与私、国与家具有突出的“同构性”。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被访者在谈及家庭成员的个人命运及有关家庭的记忆时,首先提到的是当时国家与社会正处于哪一时期、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并通过此勾连出家庭与个人的相关故事,而这些故事多以服务国家、为国奉献为主线,“家国命运一体化”及“家国利益共享化”等观念使得人们普遍建立起一种“一切服从革命利益”的家庭制度和观念,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过程中设,家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合理化家庭位于国家之下的“舍小家,为大家”的价值秩序,塑造了一种家庭记忆的源基因。
此外,这一群体中工业生产者是其职业身份,而工人子女是其代际身份。由于国家在“公领域”建立起一种为工业化奋斗的氛围,家庭记忆受此“公领域”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家庭场域中的子辈还通过参与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工业化建设的浪潮之中,并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的途径被影响着,从而在家与国之间完成共生与契洽,使得个体“国家人”与“家庭人”的身份相互重叠,进而共同影响着其记忆的建构。可以看出,外部环境不可避免地具有嵌入性,被访者的记忆与特殊历史时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家庭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不仅影响个体生命轨迹,家庭生活还托举了社会史,表现出家庭故事与历史风云形影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