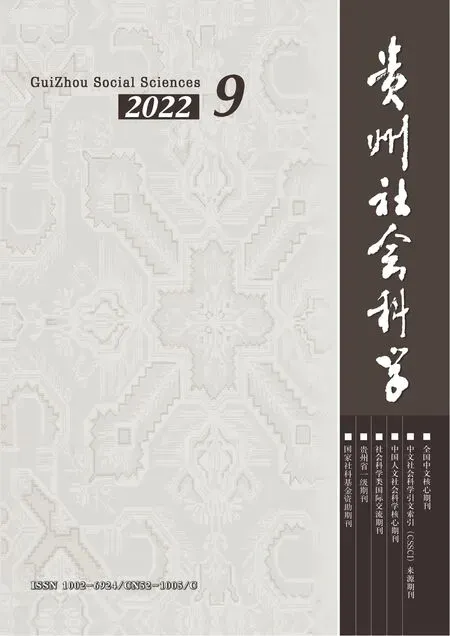黔东南苗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与融合
2022-11-21梅传强严雨桐
梅传强 严雨桐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治理,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相结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统筹推进乡镇和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村规民约等民间习惯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苗族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作为我国主要的苗族人民聚居区之一,众多苗族村寨(1)本文所称的“黔东南苗族村寨”,即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以苗族群众为核心的聚居村寨;本文所称的“苗族习惯法”,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范围内的苗族习惯法。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民族特色的村规民约等习惯法,在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维护民族稳定和规范生活秩序等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国家制定法的有效补充。村民自治规范的体系化建设需要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村规民约等习惯法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刑事领域,部分苗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依旧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治现代化在苗族地区的贯彻落实。因此,笔者于2021年7月前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棵树镇南花村和从江县岜沙村等地开展田野调查(2)下文中所涉村规民约,未标注出处的均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立足于苗族村寨村规民约的发展历程及适用现状,发掘国家制定法与苗族刑事习惯法在兼容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尝试在国家制定法与苗族刑事习惯法调适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上提出实现两法融合的合理举措,以期进一步推动黔东南苗族村寨的法治建设。
一、黔东南苗族刑事习惯法的历史渊源与适用现状
早在九黎蚩尤时期,古苗社会就有了自己的领土和刑罚,形成了牢固的阶级管理体制。(3)《尚书·吕刑》有言:“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意为苗民不遵守政令,就用刑罚来制服,制定了五种酷刑作为法律。参见顾迁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70页。明朝十分重视对苗族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并根据户籍、赋税以及与汉人的亲近程度分为“熟苗”和“生苗”进行差异化管理。(4)《贵州图经新志》有言:“曰苗人者,即古三苗遗种也。其类有二,曰生苗、曰熟苗。生苗者,自古不知王化……熟苗者,叛服不常。”参见(明)沈庠修正,(明)赵瓒编著,张光祥点校:《贵州图经新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清朝对苗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加强对苗族地区的管理,并出现了大量约束官吏权力、规范土地分配、调整苗汉关系、禁止兵器制造和劫杀抢掠等方面的立法(5)除《大清律例》外,清政府还制定了约束苗族官吏的《会典》《则例》,以刑事法律规范为主约束苗疆地区苗民行为的《戒苗条约八条》和调整苗汉关系的《苗汉杂居章程》《官员失察汉民进入苗地处分条例》《吏民擅入苗地惩处条例》《苗汉禁婚令》等。参见徐晓光、吴大华、李廷贵:《苗族习惯法》,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然而,尽管苗汉之间的封闭隔绝状态已逐步改善,但由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社会发展迟缓、宗族势力牢固等原因,加之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汉文语言障碍,苗民对“官法”了解极少。《清会典》有言:“苗夷犯死罪,按律定拟题结,不准以牛马银两抵偿。其自相争论之事,照苗例断结,不必绳之以官法。”(6)参见《清会典》卷五十三,中华书局影印,1991年版第499页。因此,在清律等成文“官法”之外,“苗例”作为处理苗人纠纷案件的不成文习惯法之一,发挥着“准据法”的重要变通作用。乾隆即位后,颁布《永除贵州、古州等处苗赋令》,免除黔东南“新设六厅”(7)指雍正开辟黔东南苗疆后建立的郡县,包括古州厅、八寨厅、都江厅、清江厅、台拱厅、丹江厅,其政区地域相当于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剑河县、榕江县、台江县、雷山县以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东部。的粮赋,并明谕:“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论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之以官法”(8)参见《大清律例》卷三十七《刑律·断狱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6页。,确认了苗族习惯法“苗例”在处理苗民之间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方面的法律效力。以苗民熟悉且信服的“苗例”处理案件,不仅有利于修复宗亲关系,促进苗疆社会稳定,也避免苗民因不懂“官法”、不通汉语而受到官吏欺诈。[1]
苗族早期历史中没有文字,古歌、诗词等口承文化(9)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有文字的民族习惯法多以文字记载,如藏族、傣族、蒙古族等。没有文字的民族习惯法则以不成文的形式,通过口承文化传承下来,苗族则属于口承习惯法中具有典型性的民族。是“苗例”传承至今的重要载体。在诸多苗族古词之中,贵州黔东南苗族口承习惯法极具代表性,其核心内容为“贾理”(10)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丹寨、麻江、凯里、雷山、黄平、施秉、台江、剑河、榕江、从江等地区,世代流传着口传经典“贾”,苗语音译为“Jax”,具有“讲、说、论、辩”之意。“贾理”即为“贾”所阐述之理,苗语为“Jaxlil”,又译为“理词”,涵盖了苗族的创世神话、族源传说、支系谱牒、知识技艺、宗教信俗、民俗仪礼、伦理道德、诉讼理辞和典型案例等方方面面,是民众解决纠纷的依据。,寓褒贬观点于其中,教导村民明辨是非,以维护村寨和谐稳定。除了起到实体法作用的寓言故事外,“贾理”也包含了较为完善的刑事诉讼程序。其中,《汤粑理词》和《油汤理词》(11)《汤粑理词》和《油汤理词》指分别通过“烧汤粑”和“捞油锅”两种神判形式作出最终判决的程序法。记录了处理刑事纠纷时的审判场所、起诉词与辩护词、诉讼代理人、举证质证、审理期限和判决结果等完整的刑事诉讼审判流程,体现了苗族人民在程序法运用方面的智慧。为了使“贾理”更好地传承和更新,苗族议榔制(12)议榔制组织可以由一个鼓社、一个寨或几个寨乃至整个地区组成,是苗族社会中议定、执行习惯法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盟组织。的榔头(13)榔头是议榔的首领,对内负责制定规约,对外负责联络交涉等各种事务。会定期组织“议榔会议”,以“贾理”为据开展立法活动,制定有关调解婚姻家庭纠纷、山林土地纠纷和偷盗、放火、斗殴纠纷的“榔规”(14)“榔规”是苗族社会中流行的一种习惯法,是苗族村寨公众制定、共同遵守的社会管理条款,主要记载了苗族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是苗族“议榔会议”的产物。。纠纷发生时,由熟悉“贾理”的理老(15)在苗族,寨老依据“贾理”主持和处理公共事务;鼓藏头依据“贾理”主持办理祭祖大典;巫师依据“贾理”主持祭祀和祈禳活动;理老根据“贾理”评判裁决纠纷案件。主持,依据“贾理”和“榔规”等苗族习惯法进行解决,体现了苗族人民高效灵活解决村寨内部纠纷的智慧,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逐步从“单一治理”转向“综合治理”,号召各村制定村规民约。黔东南苗族村寨根据其特色文化习俗制定的村规民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从中也可窥见从“祭祀神判”到法治现代化的发展。如,对于斗殴伤害行为,台江县大寨村2005年制定的村规民约第二条规定:“严禁酒后闹事,凡因各种原因发生打架、吵架的,责令双方各出120斤米、120斤肉、120斤酒,请全村聚餐,以示谢罪。”[2]345对于违反防火规定引起火灾的行为,雷山县西江村2007年制定的村规民约第三条规定:“在本村耕作区内发生山火的,过火面积每亩50-80元……在一个星期内交足罚款,拒交的请鼓藏头、寨老出面处理。”[3]对于偷盗行为,从江县岜沙村2017年制定的村规民约第四条规定:“非法进入他人住房、经销店、粮仓、果园、工棚、牛棚等地盗窃的,除退赃外,另罚120斤米、120斤酒、120斤猪肉。”对于传播淫秽物品和猥亵行为,岜沙村村规民约第十九条规定:“不准制作、出售、传播淫秽物品,不准调戏妇女,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违者罚款200元。”可见,涉及放火、盗窃、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行为,相比诉诸公力救济,黔东南苗族村寨的村规民约主要采取罚款、罚酒、罚肉、赔礼道歉、提交寨老调解、请全村吃饭等方式进行处理,将矛盾化解在村寨内部。
二、黔东南苗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衔接困境
(一)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倾向不同
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保护方面,苗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有着不同的侧重。相较于保障人权不受侵犯,维护个人自由平等的国家制定法而言,苗族“贾理”和村规民约等习惯法以调和民间公共秩序为目标,更加注重对社会集体关系的修复。苗族各村寨内成员的姓氏较为单一、集中,以村寨为单位的聚居生活使得生产生活中的主体彼此相互熟知。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依据社会团结方式的不同,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机械社会和有机社会两大类。[4]在机械社会中,社会群体之间受共同的宗教和信仰形成联系纽带,在情感、意愿、价值取向上高度趋同,也因其民族独特性和地域独立性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较为明晰的界限。而在有机社会中,各群体之间联系紧密,社会高度分化和精细分工使得社会各部分相互依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形成利益纽带而保持动态稳定。易言之,苗族地区形成的是机械而非有机的社会,村民内心真正惧怕的并非是肉体惩罚,而是被其他成员否定和抛弃。黔东南苗族村寨对自然意象(16)例如山崇拜、水崇拜、树崇拜、桥崇拜、牛崇拜、蝶崇拜、日月崇拜等。有着虔诚的崇拜信仰,坚信万物有灵。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村寨至今仍保留着“巫师”“祭师”的身份传承。同时,苗族人民对祖先十分崇敬,将祖先的智慧和遗言奉为古理古规代代相传。因此,通过“议榔”会议制定的规则一旦通过会餐、祭祀等方式被集体确定下来,便受到祖先和自然的庇佑,受全体村民监督。《贾理》有言:“千行百样入榔约,水不入榔淹田庄,风不入榔倒房屋,火不入榔烧山野,茅不入榔划手脚。”意指若不愿意入榔归约,不遵守行为准则,将会导致洪水泛滥、狂风大作、火烧山野、伤及自身,遭到祖先和自然的责罚,甚至在死后无法正常入葬。故而一旦发生刑事案件,相较于有机社会中普遍适用国家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情形,苗族人民内心由于敬畏自然、害怕被集体抛弃而产生的负罪心理远强于对其而言尚不熟悉的成文法规定。因此,当事人更加习惯于接受村内权威人士居中“裁判”达成的当事人之间的和解结果,求得祖先、神灵和同村邻里的原谅。国家制定法的适用优先级和适用频率并不乐观。
(二)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侧重不同
国家制定法普遍认为权利是法律关系的本位,在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以法律权利为核心地位。而苗族习惯法则是以和谐为目标的义务本位,无论是社会关系的调整还是司法纠纷的解决,都不以明辨是非为目的,而是以平息纠纷为根本追求,更加侧重村民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苗族习惯法的刑事纠纷调解范围与国家制定法不完全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版,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1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中明确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即主要适用于部分涉及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轻微刑事案件。而苗族地区在刑事和解的范围上并非仅限于轻罪案件,其偏向于广义上的和解,甚至可以涵盖强奸等部分严重的刑事案件。例如,在苗族“游方”(18)“游方”旧称“摇马郎”“串姑娘”“搭小屋”“住公房”“摇马郎”,是黔东南、黔南苗族青年男女公开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苗族青年男女往往通过“游方”的形式交结朋友,选择伴侣。中发生未成年人性行为时,普遍息事宁人,令双方结为夫妻。榕江县加宜村规定,青年男女在“坐姑娘”(19)“坐姑娘”指青年男女通过对歌的形式私定终身。的社交中发生性关系,男方致使姑娘怀孕,要赔偿女方一头牛。若双方未订婚,男子按正常习惯娶该女子为妻。[5]改革开放以来,苗族村寨在保留村规民约中对强奸行为的处罚时,已明确强奸属于犯罪行为,应由国家法律处理,但依旧存在因考虑到早婚早育的民族风俗和家庭和睦的社会效果而沿用习惯法予以免除刑事责任的案例。如“王某与未满14周岁的苗族幼女韦某发生性关系”的案件(20)被告人贵州丹寨县苗族农民王某于1980年与时年未满14周岁的苗族幼女韦某相识。后韦某对被告人产生好感,韦母也对王某表示满意,便私下将女儿许给王某。此后,被告人与韦某经常情书往来并约会见面,这期间两人曾多次发生性行为。1981年,两人又按照民族习惯举办了婚礼。后来,韦某父亲得知此事后便将女儿叫回家,否认婚姻的成立,并于此后的一年内,先后四次向公安机关报案称王某奸淫幼女。公安局也以奸淫幼女罪向检察院提请逮捕。经该县、州两级检察院审查后决定不予批捕,后州检察院又向省检察院进行汇报,省检察院亦认为“不应作犯罪处理”。参见周相卿,付媛:《雷公山地区苗族婚姻习惯法与刑法冲突现象分析》,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年第2期64页。中,因考虑到在贵州苗族聚居的地区有早婚早恋的习俗,“游方”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性行为的发生,为维护家庭稳定和民族团结,尊重苗族习惯法,从而做出了不起诉决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事实上,在经济科技快速发展、人与人利益界限明晰的团体关系中,以和谐为目标的义务本位将耗费更多的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来确认义务和责任的分配关系,导致社会运行效率降低,因此,私权界限明晰的权利本位更能适应高速运转的机械社会。但是,苗族地区以和谐理念为指引,人际关系在冷漠的契约规范和明晰的权利界限之外多了家庭、邻里、村寨的温情纽带。在遵从本人意愿,承担自身义务的同时,接受他人义务履行的“义务本位”更能有效地保障村寨的和谐稳定。
(三)主动干预与滞后干预效果不同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机关全程介入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而苗族地区有所不同,苗族人民十分看重个人和家族名誉,若发生刑事案件,一般不会主动报案和移送司法机关,而是采用习惯法自行解决。例如,2013年的岜沙村村规民约规定:“有下列行为者,按‘三个一百二(21)“三个一百二”指一百二十斤猪肉、一百二十斤大米、一百二十斤米酒。’承担违约责任:盗窃、毁坏他人财物500元以上;种植毒品原植物、吸食毒品;毁坏公益林;引发寨火;通奸、拐骗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可见,部分村规民约内容未能与国家制定法紧密衔接,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置均无“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规定,司法机关缺乏主动介入苗族地区刑事案件的渠道。滞后干预不仅会降低纠纷解决的效率,还会导致习惯法效力和基层自治组织权威性的动荡,掣肘苗族区域自治平稳发展。
随着法制教育的普及和乡村建设的完善,各村寨不断修改村规民约以保证其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施秉县马溪村2009年制定的村规民约便在兜底条款中规定:“凡是违反上述规定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报派出所或综治办进行处罚。”[6]248同时,苗族习惯法逐渐与国家制定法接轨,对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和村寨内无法解决的刑事案件应交予司法机关处理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岜沙村2017年新修订的村规民约第二十条便对严禁非法限制他人自由、非法侵犯他人住宅、隐匿、毁弃、私拆他人邮件的行为,规定了“处罚‘三个一百二’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变通方式。然而,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不享有执法权。因缺乏制定村规民约的规范流程和对法律条文的细致了解,部分村规民约中与法律相抵触的条款依旧能够正常执行,以至于出现“无执法权的基层自治组织先行处罚后,有执法权的司法机关滞后介入再次执法”的现象。例如,柳川镇巫堆村村规民约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三年内发生两次以上火警的,除加倍罚款外,并责令该户搬迁到离寨子150公尺外的地方居住,不肯自动搬迁的,由村委、支部及治安联防组织派人撤出,造成损失概不负责。”[2]266雷山县上郎德村村规民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加强本村治安管理,严禁在我村管辖范围内打架斗殴、侮辱妇女、扰乱公共秩序;对违反上述条款之一的,除承担相应刑事、行政、民事责任外,另行缴纳200-1000元的违约金,触犯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2)《村规民约》。参见黔东南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朗德村馆网站http://museum.zhaiu.com/default/pedigree/view/id/7/stockade_id/40/left_id/279/sitemap_id/265。访问时间2022年5月5日。可见,在苗族习惯法尚未与国家制定法顺畅衔接的情况下,缺乏执法权的苗族自治组织根据习惯法的惩罚措施于法无据。国家公权力的滞后介入不仅不能获得双方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普遍认可,还会带来“一事多罚”的不当后果,既可能激化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司法机关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矛盾,也给社会关系的平稳修复带来负面影响。
三、黔东南苗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基础
(一)理论基础
1.国家制定法与苗族习惯法刚柔并济
国家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着国家意志的规范系统,具有规范性、强制性、阶级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7]“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具有刚性尺度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然而,一方面,国家成文法的制定成本较大,制定周期较长,立法存在滞后性。我国立法步伐虽不断加快,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关系呈现多样性、复杂性特点,把握适应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变化方向和刚性法律的稳定性、安定性之间的平衡,依旧是立法需要面对的长远难题。另一方面,刚性的国家制定法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作为支持,具备了行之有效的强制力。但强制力的实施将面临着资源的大量消耗,且实施成本将随层级的下沉和地理的延伸而逐渐增加。具有柔性特点的习惯法则能够以其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特点消解国家法刚性的弱点。基层村规民约的强制力依赖于村内全体成员的认可,制定成本低、效率高,能够快速适应本地的民族特色和生产发展需要;由村民委员会监督实施,能够有效避免国家制定法因层级下沉而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执行力逐层递减的问题。在法治思想深入贯彻、法治进程稳步前行的部分苗族村寨中,已逐步达成了“情节较轻的非恶性事件由村内自治解决,严重的刑事犯罪交由司法机关处理”这一共识。如施秉县屯上村村规民约规定:“酗酒闹事、以酒盖面找人麻烦,造成民事纠纷的,罚款酗酒肇事者伍拾元(误工费除外),情节严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6]107可见,国家制定法与现代苗族习惯法一刚一柔、刚柔并济的默契配合能够较好地在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中形成有机多元的互动局面。
2.国家制定法与苗族习惯法张弛有度
国家制定法作为调整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强制力规定,旨在为所有人的行为提供一个模式、标准和方向,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绷紧“原则之尺”。“国家制定法作为社会结构存在弹性空间,法律规范存在着‘真空’区域,因而民间法的存在能弥补现行国家法的不足。”[8]习惯法来源于长期乡土生活中文化和习俗的传承,以生动、独特、具体的表达形式调整着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社会生活,维系着微小、个别的利益关系,弥补了国家制定法宏观、抽象原则下的空白,把握“法外之弦”。例如,黔东南凯里市南江村村规民约规定:“偷盗村民田间地头的庄稼(如药材、豆类、瓜果、蔬菜等作物),每人每次罚款20-100元;偷盗村民家禽家畜,每抓到一次罚款50-150元,家禽归于失主;禁止偷钓、偷砍村民养鱼塘或责任田的鱼,违者每次罚款130元,鱼归田主。”[6]98可见,各苗寨村规民约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偷盗对象的种类、价值进行细分,发挥着调整“细微之罪”时的补充与缓冲作用。国家制定法与苗族刑事习惯法宏观与微观结合,抽象和具体互补,“原则之尺”与“法外之弦”一张一弛,在调和群众纠纷、恢复社会关系、惩治和预防犯罪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二)现实基础
1.民族习惯法具有准法规范的法律效力
习惯法的法律地位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习惯法是国家认可的制定法的组成部分”(23)“习惯法,指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是法的渊源之一。”参见中国大百科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习惯法即渊源于习惯并由国家认可的法律。”参见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有观点认为“习惯法是传统的道德习惯”(24)“鄂伦春人在长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中,很自然地形成了一整套的传统习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参见秋浦:《鄂伦春社会的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也有观点认为“习惯法是民间有强制性的准法规范。”(25)“习惯法是依据一定的社会权威而存在,并被保证在违反时对强制执行或对违反者予以责罚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参见周勇:《习惯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历史地位》,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4期161页;“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根据事实和经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 参见田成有、阮风斌:《中国农村习惯法初探》,载《民俗研究》,1994年第4期22页。总体观之,第一种观点认为只存在正式法律渊源意义上的习惯法,混淆了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区别,缩小了习惯法的范围。第二种观点混淆了习惯法与习惯的区别,将未被固定下来的传统习俗也认定为习惯法,扩大了习惯法的范围。因此,第三种观点较为适当,习惯法应当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根据社会生产经验和民间习惯,并通过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固定下来、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2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也提到,在法律没有规定时,可以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适用习惯。可见,习惯法作为准法规范在实现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始终有着不可替代的一席之位。
作为“准法规范”的习惯法具有法律的某些特征。首先是具有规范性。习惯法是对习惯的筛选和凝练,孤立、零散、间断的风俗、现象、观念不能称之为习惯法。苗族在没有文字之时,苗例便通过“贾理”等古歌形式固定和传承,形成了长期流传的规范,受到苗族人民的普遍认可。其次是权威性。制定法的权威来源于国家政权,习惯法的权威来源于民间传统,这种社会权威是社会外在力量与守法者内在力量的结合,是与人们内心信念相一致的权威。[9]最后是强制性。国家制定法由公权力保障执行,而习惯法由权威人士或民间自治组织保障执行。苗族人民通过议榔立法、理老司法、鼓社执法(27)“鼓社”又称“吃牯藏”,即立鼓为社,源自苗族的氏族、部落联盟时的社会组织体制,小的十几户或百来户,大的几百户乃至上千户,首领为“鼓藏头”。至近现代,鼓社组织在其他地区已经消失或大部分消失,黔东南地区仍有保留。“鼓社”具有组织和发展生产,调整婚姻关系,促进人口增长,调整内外部关系等基本职能,并承担维护氏族的荣誉与复仇(执法)的职责。这一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使苗族习惯法获得了权威人士的监督背书,维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习惯法以“准法规范”的法律效力不断调整着特定范围的民间社会关系,对特定群体起到了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的积极影响。
2.民族刑事政策是两法衔接的主要桥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我国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少一宽”(28)中共中央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巩固发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的成果和准备第二战役的一些设想》(中发[1984]5号)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少一宽”政策,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对少数民族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处罚上一般要在法律规定的限度范围内从宽。民族刑事政策。基于这一刑事政策,我国民族地区一直都以尊重民族地区文化习俗和考量民族地区社会需要为立场,实行着有别于国家制定法的特殊立法、司法和执法政策。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版)第116条(2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版)第75条(30)《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第二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版)第19条(3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均承认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刑法》第90条(3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也与宪法性法律相对应,赋予了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刑事变通单行条例的权利。另一方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第十八条指出,研究、制定或修订有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政策法规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增加专条专款加以明确。(33)2009年7月5日,国务院以国发〔2009〕29号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因此,纷繁复杂、因地而异的少数民族犯罪治理,应当以“两少一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为指导,通过对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分析,结合民族特色文化风俗,建构与时俱进的民族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合理推进民族习惯法与刑事法律制度的融合。
3.恢复性司法作为纠纷和解的共同理念
相较诉诸刑罚的传统报应性司法理念而言,恢复性司法理念更加符合“息讼”“厌讼”的中国传统刑法观,注重对人际关系的修复,并通过对违法者的矫正和改造来愈合犯罪行为给被害人、社会以及犯罪人自身带来的伤害。犯罪人可以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生活帮助等积极行为弥补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解决犯罪人再社会化困难的问题,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同时,恢复性司法理念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中心,在司法上赋予了被害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追究犯罪的愿望和要求的权力,弥补了应对犯罪影响时的缺位。在民族地区,相较于对被告人实施剥夺政治权利、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和生命的刑事处罚,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更倾向于邻里及家庭关系的修复、家族地位的维持和经济利益的补偿。“无狱讼之烦”的处事原则与刑事和解制度中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相契合,为国家制定法与苗族刑事习惯法的衔接提供了可行性依据。
四、黔东南苗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变通
(一)加强刑事政策研究,确立纠纷和解原则
“民族刑事政策是民族刑事法律的灵魂与核心,民族刑事法律是民族刑事政策的条文化与定型化。因此,民族刑事政策对于民族地区刑事变通立法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10]在赋予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权利的同时,应当加强民族刑事政策的研究,从宏观上把握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政策导向,确立以下原则保障纠纷和解的顺利进行。其一,双方平等自愿原则。在解决民族纠纷时,应当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陈述理由、提供证据、相互辩斥的权利,确保判决的公正信服。其二,公序良俗原则。在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乡村治理体制下,由现代“理老”——村民委员会委员居中裁判的科学调解方式应当予以适当借鉴和保留,但苗寨中对“人类的一切行为,无论善恶,都必为鬼神所洞悉”[11]的信奉观念,以及“捞油锅”(34)“捞油锅”:将油倒入大锅内使油沸腾,再放入斧头等物件,让被告和原告分别伸手捞出后查看手臂是否被烫伤,被烫伤一方会被判为理亏,而受害者因受神灵庇佑则会安然无恙。“鸣神”(35)“鸣神”:宰杀牲畜由鸣神裁定,根据鸣神约定,在四十九日内,遭受报应的一方就被认为理亏,应将赔偿给予未受报应的一方。“杀鸡”(36)“杀鸡”:通过两棵分立的树桩代表纠纷当事人的双方,待祷告后将一只大公鸡宰杀,将其抛在原来竖立好的两棵树桩的正中间位置,通过鸡临死挣扎的位置离木桩的远近判断何为理亏的一方。等神明裁判的方式应当在新时代的法治普及和文化教育中淘汰,使得刑事案件的和解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科学进行。其三,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兼顾原则。“传统刑事司法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以纠纷的法律解决为圭臬,漠视当事人的情感诉求、关系修复等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这一制度设计的取向与人情社会的处世观念根本对立,无助于问题的实质性解决。”[12]在村寨这类范围有限的“熟人社会”中,机械性地要求犯罪人承担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往往难以使得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实质性修复,反而可能激化族内矛盾。因此,在司法机关介入的同时,不可忽视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补偿,应当将赔偿损失的态度与数量纳入刑事责任的考量因素之中。
(二)优化刑事诉权配置,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诉权
2012年3月,刑事和解制度被首次写入《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之所以限制为轻罪案件,其核心问题是刑事诉权的配置。诉权理论是合理配置当事人具体诉讼权利的依据,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诉权主张权利,同时承担己方义务,是诉讼平等化、对抗化的基础。因此,诉权的配置决定了被害人在何种程度上享有对案件的发言权。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自由处分的权利。而在公诉案件中,在刑事和解制度产生之前,因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和对公共秩序的维持,被害人不允许过多干预公诉权的行使,甚至不具备根据被告人赔偿态度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利。随着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落实,被害人能够通过正式的司法程序获得赔偿,亲身参与到案件的处理中,充分表达诉求,肯定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也使得被害人能在最大程度上挽回自己的物质损失。
中国古代有着较深厚的“德主刑辅”“以和为贵”的思想传统理念,有“厌讼”情结。民间一直存在多种“非官方”的犯罪处理方式,认可非正式程序的调解与和解,双方当事人对纠纷处理的结果导向有着绝对的主动权。若要平衡国家制定法与苗族习惯法之间的冲突,应当结合民族村寨的实际情况,从根本上优化刑事诉权的配置,即便在涉及严重刑事犯罪,公权力已经介入的情况下,依旧充分赋予纠纷中被害人参与案件、获取赔偿、提出量刑建议的权利。
(三)明确制定流程规范,推动村规民约备案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乡镇(街道)指导村(社区)依法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健全备案和履行机制,确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13]村规民约制定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与国家制定法的衔接程度和苗族地区法治思想的进步程度。《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第八条对黔东南地区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提出了要求:“民族文化村寨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依照本条例……组织订立民族文化村寨保护和发展的村规民约,并督促实施。”(37)《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参见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qdn.gov.cn/zwgk_5871642/zfxxgk_5871649/fdzdgknr_5871652/lzyj/dfxfg_5871654/202110/t20211020_70987037.html。访问时间2020年5月5日。因此,在制定主体上,现代苗寨村规民约的形成应当由村民委员会牵头组织进行,并召集村委干部、党员代表、知识分子、权威人士共同商议,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结合群众的意愿形成约束和规范全体村民的行为规范。
村规民约的制定应把握几项核心原则: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二是村规民约制定内容要因地制宜,在“制定规范日常行为、维护公共秩序、保障群众权益”的基础上,结合当地风俗民情进一步细化实用条款,进一步提高基层群众的自治水平;三是村规民约的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要做好苗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衔接工作,除了明确制定主体、把握制定原则外,还需要对各苗寨的村规民约进行梳理、总结。由村民委员会委员、党支部和少数民族骨干设常驻法律备案工作点,做好习惯法的更新和备案工作,并定时统一汇总上报至省级备案审查机构,便于省级人大能够动态了解苗族地区的法治进程,及时调整民族政策,指导立法和司法。如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凯里市三棵树镇南花村2020年制定的村规民约就实现了制定内容和制定流程的双重规范,(38)2020年南花村村规民约第十三条规定:“凡是在我村范围内拦路抢劫、聚众斗殴、拉帮结派、聚众闹事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第十五条规定:“凡是进入他人家里进行偷盗等不良行为,无论成功与否,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第五十三条规定:“本村规民约于2020年8月7日经全体村民讨论表决通过,报镇民政办、司法所、计生办、派出所备案。”确保了村规民约在动态变化和与时俱进的同时与国家制定法保持一致。
(四)加大民族骨干引进,纳入权威人士调解纠纷
对习惯法的认知和依赖实际上受限于对国家制定法认知的不足,而解决认知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汉语言文字、普通话和法治观念的普及。发展基层民主,提高对法治观念的认知,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教育是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的要求。[14]十余年来,在重视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指引和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顺利实施下,促进民族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有了稳定的前进方向和智力支撑。让了解民族地区习惯法的高学历骨干人才投身司法实践的相关工作,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改善刑事纠纷的和解效率,提升刑事案件的审理水平。因此,一方面,应加大对黔东南地区民族院校的扶持,通过研究生支教团、骨干计划等平台,挑选同时具备法律思维和习惯法认知的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应加强少数民族骨干在苗族地区扎根发展的经济支持与后勤保障,解决民族骨干长期留任、正常安家的基本需求,落实薪酬动态调整机制和乡镇工作补贴政策,减少民族骨干人才流失,树立高学历人才返乡建设乡村的信心,助力苗族地区法治进程蓬勃发展。
除提高教育水平和法律素养外,将同时了解地方特点与国家法律的民间权威人士直接纳入纠纷调解机制,则是获得双方当事人认可、平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为高效便捷的方式。2011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条赋予了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的权利,为民族权威人士参与纠纷调解提供了法律保障。在黔东南苗族村寨,“理老”依照习惯法说理、裁判的传统习俗使得民族内部人人皆信服,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因此,一方面,可将德高望重、能言善辩的苗族权威人士纳入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由司法机关委托的刑事和解案件,担任主持和引导工作,能够为苗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构建良好的制度基础,实现社会关系修复和司法持正不阿的双赢。另一方面,可赋予苗族中的权威人士以陪审员身份,参与司法机关主导的刑事和解案件,担任以案释法的说理工作,能够为苗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融合构建良好的制度基础,实现社会关系修复和司法执正不阿的双赢。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民事审判中将“德古”作为“特邀陪审员”的先行尝试为民间权威人士参与司法机关主导的刑事和解提供了宝贵经验。[15]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当前,乡村治理正在从“因俗而治”向“依法治理”转变,迫切需要把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而村规民约等习惯法,则是助力苗族人民实现法治路径和法治内容创新的有效举措,对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意识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并非对立关系。民族习惯法的留存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宏观指导和原则把控,国家制定法的发展离不开对基层治理现状的考察和人民意见的表达,两者相互影响、相互配合,形成静态认可与动态校正的多向互动关系,将在维护民族团结稳定、保障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共同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