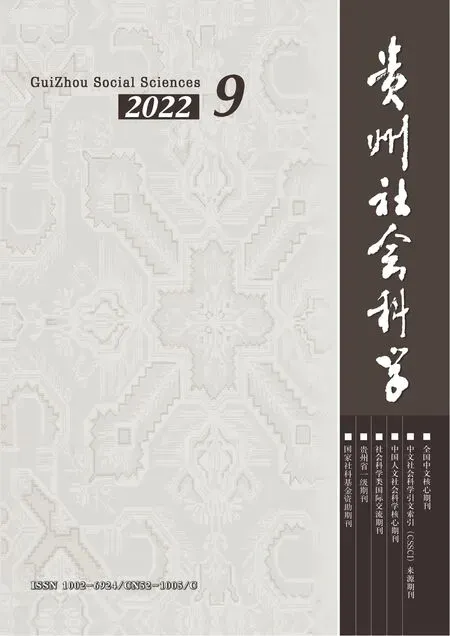新村主义在中国的流变及其路径
2022-11-21赵泓
赵 泓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广州 510614)
一、引入与扩散:选择性传播
新村主义是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或曰空想社会主义,它源自19世纪至20世纪在欧美流行一时的新生活社区运动。20世纪初传入日本后,日本现代文学的先驱武者小路实笃削弱了其中的集体主义成份,注入了东方式的田园意境,强调艺术与劳动的结合,主张通过建立新村,使全人类过上“人的生活”,实现平等、互助的理想社会。[1]由于个人动机尤其是社会土壤的差异,中国新村主义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所宣传推行的新村与日本的新村从一开始就有所区别,尤其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新村主义者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差异也越来越大。
周作人较早也最全面系统地介绍新村主义。他于1919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日本的新村》,内容大半译自武者小路实笃《新村的生活》一书,但介绍时有所选择。如在“利己”与“兼爱”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偏重于‘利己’,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则更偏重于‘兼爱’”。[2]武者小路原本十分推崇托尔斯泰,倡导利他精神,但接触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之后,思想发生了改变,宣称:“从此经常把‘为了自己’放在心头来行动”。他虽然主张利己与利他、自爱与他爱相一致,但认为应先立足于利己和自爱。[3]周作人介绍引进新村主义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国内正流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泛劳动主义崇尚体力劳动,强调每个人必须参加体力劳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阶级之间的对立和不平等。《日本的新村》一文开头即介绍新村,虽然宣扬了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但在重视体力劳动的同时,也肯定了脑力劳动的重要性;在主张担负人类义务的同时,也不忽略个人的义务,以促使个人与集体能够和谐发展。这种个人与集体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念主要见《关于新村之对话》的《第一之对话》。周作人选译的内容近半来自《第一之对话》,主要谈个人与集体如何共存并协调发展。一小部分译自《第二之对话》,主要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应当并重。专谈信仰问题的《第三之对话》则完全被忽略。显然,周作人接受武者小路的思想是有选择性的。[4]尤其是武者小路为了实现新村理想,同时也为了改造自己,把自己私人财产捐献给新村,以祛除自己作为资产阶级的愧疚之心。关于这一点,这三个对话中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而周作人也完全没有介绍。没有地主、资本家主动捐献财物或土地,是“五四”激进青年知识分子推行新村运动从一开始便遇到的难题,也是不久后新村运动改头换面以工读互助团的形式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传播者的不同立场与视角
在1919—1920年间,北京、上海等地《晨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介绍和讨论新村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不难看出,新村主义支持者是从各自的立场去接受、理解新村主义的。
(一)从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角度接受新村主义。最早在中国尝试创办新村的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新人社是“五四”时期新村主义团体,1920年4月成立于上海,社员多为上海和各地文教界人士,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或倾向无政府主义。社刊《新人》有些文章从无政府主义角度阐释新村的价值。如有人指出现在的社会组织乃“纵面的组织”“强大支配弱小”的组织,在这种组织里,“强大就好比监狱,这监狱里头的囚犯,就是弱小;强大做了监狱,弱小做了囚犯,其结果强大进化,弱小也跟着进化;强大如果退步,弱小也跟着退步”。而且即使有进化,“那进化的幸福,多数人却享受不着,只有极少数的人类,会得他的幸福”。[5]35-38这里使用的便是无政府主义的语言,旨在对国家统治机器进行揭露。新人社社员有些不过将新思潮当作谈资,且言行不一,如新人社的陈伯熙有次约见“多年研究无政府主义要立即组织新村的谢叔夜先生”,这位无政府主义者说起社会主义,“就拿出漳州送来自造的一盒烟膏,彼此一面吸鸦片烟,一面讲新思潮,一联想到现在所谓同志,大都如此”。[6]374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对于这都市的处罚,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激烈的,痛痛快快地将炸毁粉碎了;一是消极的,就是劝那觉悟的人们,都脱离都市,回到乡间去运动。前者是可替不可久的一种手段,遇有机会未尝不可有此快举,后者乃是我们底康庄大道。”[6]373他们是以“脱离都市,回到乡间去运动”为出发点来宣传新村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天津真学会出版《新生命》杂志,试图把这种小册子传到全国乡乡村村去,作为文化运动的利器。该刊物曾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为新村主义进行宣传,以求组成一个以自由、平等、互助为原则的新社会。”[6]372直至1923年,江苏无政府主义社团微明学社还在其简章中表明要“组织新村”,以“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5]35-38
(二)从乡村教育改革出发推行新村运动,以叶圣陶、陶行知等为代表。新村主义传入中国后,与其他思潮相互渗透并发生了转向,并导致了本土化实践。叶圣陶较早成为新村会员,1915年,他经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小学教国文。1917年,他在苏州甪直镇创办“生生农场”,实践生活与学校相结合的新式教育模式。“生生农场”占地不大,只有2亩多,本来是一块荒地,他与学生一起开垦,共同耕作,分享收获,目的是让孩子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生农场融入了叶圣陶对教育改革的思考,寄托了他的教育创新理想。这种教育改革理念与新村主义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容易引起共鸣。1920年1月,叶圣陶正式申请成为日本新村会员。[7]与此同时,叶圣陶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1917到1918年,杜威的忠实追随者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传入中国。克伯屈主张在教学实施中,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仅作为指导者而存在,特别是教学内容(教材)须根据具体活动场景需要而动态生成。这种新颖的教学令叶圣陶耳目一新。在杜威的教育实践中,尤其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学校中得到3条最广为人知的“经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在此基础上,又形成“教育除了生长,别无自己的目的”“学校是雏形的社会”“教育过程论”等一系列基于心理学、社会学而得出的判断。叶圣陶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这些主张并付诸实践。另外,匡互生的立达学园,陶行知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等,跟“生生农场”的主旨都很接近,都强调平等友爱、互助劳动。这是新村主义与乡建运动中的乡村生活改造派理念一致的地方。
(三)将新村作为改造社会的利器,未来新社会的雏形。1919年12月,毛泽东的《学生之工作》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这是一份详细的新村计划书,虽然并未付诸实施,但将新家庭、新学校以及附近的新社会连成一块构成新村的蓝图,有学校、医院、工厂、银行、图书馆、蒙养院等,俨然一个新社会的缩影,在规模上远大于日向新村。将新村作为乡村改造示范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是王拱璧和傅柏翠。王拱璧早年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到新村主义,他于1920年回国后根据中国国情,将新村嫁接到中国乡村,淡化了新村的乌托邦色彩,体现了本土务实的特点。从1920年至1927年,他将家乡河南西华县孝武营村改造成“青年村”,进行了长达7年的新村实验。他组织素社,以“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为宗旨,推行减租减息,建立青年自治会,创办以“农教合一”为教育管理体制的“青年公学”,以“劳动”“健康”教育为中心,培养适应乡村建设的各类人才,“开启探索新村教育和新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8]
和王拱璧一样,傅柏翠赴日留学期间也受到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的影响。1919年他返回闽西老家后,打算邀一二十人到梅花十八洞一带创办“新村”,因应者寥寥,无果而终。接着,他又在家乡蛟洋实验,把自己的土地送给佃农,共同耕作,共同消费。在他的“新村”里,成员按能力分工,各尽所能。参加这一试验的有十几个农户,主要是傅姓本家。后来因不能自给而无法维持。傅柏翠作为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率先在自己家庭实行二五减租。八七会议之后,“打土豪、分田地”被确定为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但是傅柏翠对于立即暴动并实施土地革命持反对意见,于是与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特委产生矛盾。1929年12月,傅柏翠自动脱党,回到蛟洋老家搞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实施“共家运动”和“公田主张”。1930 年12 月,中共闽粤赣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开除其党籍。此后,他拥兵自重,割据古蛟地区近20年(1931—1951年),实行“农村共产团”试验,旨在建立一个无赋税、无征兵征粮、自立自保的“新桃源”。古蛟乡由原来上杭的古田、蛟洋、文都三个乡合并而成。傅柏翠为了实现新村梦想,带头捐出自家1500多亩土地。他“推行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把区内所有的土地收归集体公有,实行‘共生产,共消费’,组织‘农村共产团’。”[9]10-13“以区乡农民联合会和代表会议,代替被取消的区乡苏维埃和代表会议,作为古蛟地区最高权力机关,农民联合会设立执委会,以代替区乡苏维埃的执行机关。”[9]10-13“创办了学校,如平民学校、农民夜校、识字班、私立古蛟初级中学,倡导成立农村教育社,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9]10-13
(四)从个性解放角度去接受新村主义。这些人主要是当时思想比较激进的作家和青年学生,如女作家庐隐认为旧制度下的旧生活“不能尽力发展自己的个性,而求得人生底乐趣;唯受环境底支配,而牺牲自己底天才……这新村的理想实现了,岂不是可恢复人生底价值么?”[5]35-38北大学生罗敦伟积极宣传新村主义,曾发表《艺术复活与新村》一文,认为人类都有艺术的天才、创造的能力,并引用尼采的话说:“艺术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即是一种艺术”。但由于物欲泛滥,艺术濒临死亡,“艺术已宣告死刑了!近来虽有人替他说了一些不平的话,替他想营救的方法。但是据我看,事半功倍,直截了当可以收效的,就莫过于‘新村’了”。[5]35-38
三、新村主义的变化轨迹
在乡村,王拱璧和傅柏翠等人将新村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他们借鉴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模式,淡化了原来的空想色彩,同时主张在旧村基础上进行改造,而不是另辟“新村”作为理想的桃花源。因此,他们创办的“青年村”和“农村共产团”实验,与武者小路实笃的日向新村,已经有了明显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村之路。匡互生的立达学园、黄质夫的栖霞新村、陶行知的山海工学团,以及张一麐、李根源的苏州善人桥新村等,则将新村思想吸纳到方兴未艾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0世纪30年代,移民新村受到政府和地方士绅的重视。1930 年上海出版的《新村建设》一书,主要讲述如何通过开垦荒地建设移民新村,内容包括担任机构、土地选择、农场布置、农场分配、移民选择、移民安插、经济设施、社会设施等,作者杨开道系著名社会学家,曾于1928年组织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北京以北18里的清河镇设立试验区,深化乡村建设运动。在《新村建设》一书中,杨开道希望垦殖机构和合作移民共同“创造新时代的农村,产生新时代的农民”,相信“垦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可以产生新的社会,可以产生新的文化;这许多新的思想,新的社会,新的文化,又可以引导旧的思想,旧的社会,旧的文化,向光明之路前进”。[10]1933年,段绳武和刘春霖、张清廉等人发起组织“河北移民协会”,向西北河套地区移民,建立河北移民新村。同年,广州出版《新村》半月刊,旨在宣传农村地方自治及土地规划。
在城市,新村主义的发展路径则要复杂得多。由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城市,新村主义与当时流行的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后,便以工读互助团或类似的小组织的面目呈现。在《新村之小问答》一文中,武者小路实笃针对有人提出新村“没有一定要到乡下去的必要”时回答说:“我们想跳出现社会的涡窝,脱出现社会所已经造成的不合理的秩序,愿生活在新而且合理的秩序下。总而言之,我们不愿做现在的资本家,做现在的劳动者,也不愿过现社会食客的生活,务必尽力求着较为像人的生活”。“像人的生活是先须将以人类一分子生活于世上所必要的劳动做完,其余的时间做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11]75武者小路实笃这种“跳出现社会的涡窝”,另创一种“人的生活”的想法,是逃避都市生活的一种乌托邦,但中国的新村主义者却主动将新村组织搬到城市,以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试验。
左舜生较早考虑如何让新村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足乃至事业发展的大本营。1919 年 7月2日,左舜生发表《小组织的提倡》一文,指出:“理想上的‘小组织’是由少数同志组织的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团员必须有独立工作能力,与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劳动所得完全归公共使用和分配,子女也归集体负责教养”。[12]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王光祈读到此文后,在给左舜生的信中详谈了自己的具体设想。这个菜园新村计划刊载在1919年12月的《少年中国》月刊第1卷第6期上,他把这种新生活组织设想为在离城四五里远的地方建一个“菜园”,大家劳动之余读书写作,每天种菜两个钟,读书3个钟,翻译书籍3个钟,其余为游戏、阅读时间。开设一个平民学校,让周围的农家子弟免费上学。这个菜园新村集结合了流行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1919年发生的李超事件导致新村很快移植到城市。这年夏天,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有位叫李超的学生因肺痨在一家法国医院去世,这桩看似平常不过的事在北京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年中国会员之间讨论的这种新村式小组织很快设计为工读互助团,发起者试图使这个乌托邦团体成为穷学生的庇护所,同时也成为新生活的试验场。因此,工读互助团可视作新村运动在中国发展的重要一环。王光祈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主要组织者,他的理论是各种带有社会主义标记的大杂烩,旨在通过新村式的组织培养互助意识,以适应未来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能力。
1919 年12月4日,北京《晨报》发表王光祈的《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在城市创办工读互助团,既能解决贫困学生的求学问题,又能试验新生活,为将来的理想社会做准备。工读互助团的主张杂糅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工读主义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时开始流行,本来只是一股教育救国思潮,“五四”前后糅合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之后,发展成为一股主张劳心与劳力相结合,通过半工半读改造个人和社会的工读互助思潮。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这一时期相互渗透和影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鼓吹过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
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激进青年通过工读互助团尝试新村式的乌托邦,而在上海,新村主义者最早开启了模范村镇的试验。对于新村主义的这种流变,周作人很早便有所察觉。1919年第10号的日本《新村》杂志发表了周作人写于9月16日一封信的前半部分,信中谈到:“上海附近出现了称作新村的组织,我了解了一下,发现其目的并非为培养模范的‘人’,而是为了培养模范的国民,建立社会上常见的模范村镇”。[13]这段话可与同年11月8日题为《新村的精神》的讲演中他对上海龙华新村等组织的批评互相印证。在这场演讲中,周作人对新村的概念作了详细说明,指出:“中国近来有少数觉悟的人,也发生几种运动,颇和‘新村’相像,这原是很可喜的事。但是实际还与‘新村’有几个异点”。他把当时国内出现的南京启新农工场有限公司、北京的平民新组织以及龙华的新村进行比较,认为这三种类型都不是新村,“一般人多误会‘新村’是模范村。近来有许多人,去做那‘理想村’的计划,也有要实行他的计划,去建设模范村的。但是他们的注意点,多从外表文明上着想:什么学校、公园、图书馆、工厂、住屋、街道,都要设置的整齐完备,至于对那实际上的生活问题,反没有什么主张”。“我们‘新村’的理想,是要人努力做一个模范的‘人’,他们‘模范村’的理想,是要人努力做一个模范的‘国民’。”“龙华的‘新村’这个组织,简直就是‘模范村’,请看他的简章上说的那些机关,什么行政、司法、警察……这全是‘新村’里所不应当有的。”[14]周作人提到的上海新村于1919年在上海西郊的龙华村建立,乃借用日本新村的概念规划设计,打造一个模范社区。蔡式之、顾念劬等人考虑到沪上风气堕落,便在龙华试办模范新村,倡导健康向上、互助关爱的新生活。龙华新村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尚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理想色彩。
此后,新村这一理念和模式逐渐在以上海为主的城市中推广开来,引起了一些社会人士尤其是知识精英的关注,认为它有利于培养市民参与政治的习惯,甚至有助于推动地方自治。因此,龙华新村开启了新村在上海的发展历史。在最初一段时间,新村还是稀见的新生事物,且集中在城市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城区地皮紧张,新村便向周边扩散,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这种小区的规划方式受到追捧。“这时,新村的建设与最初的新村运动有了实质性的区别:它们大多由企业和学校主导修建,作为员工宿舍。”[15]最初的乌托邦空间理想与新村的建设,更多地以救亡图存、社会改造为出发点。一些激进青年往往把新村与自治组织联系起来。龙华新村成立后不久,上海民治学会由于得到商界巨子包达三等人的支持,在江苏淮安创建新村:“包君达三为我等在淮安开了三百亩之地组织新村,请诸君研究民治学理,他日均到兄弟处先办一小小新村,亦可讲宗教及教育。诸君要造净土及黄金极乐世界请到敝处初步试验”。[15]在新村起始阶段,发起者有意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乌托邦信念仍然执着。但当新村这一模式纳入城市开发轨道之后,新村的乌托邦理想消退,逐渐沦为了地产商营销的手段。
1929年,曾参与杨开道主持的清河实验区项目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万树庸考察了上海沪东公社和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并视二者为“新村”的典范——“沪东公社着手募捐改建社址,并增设工人的储蓄银行及餐馆等等,这样的设施,虽没有新村的名目,谁能否认他是新村呢?……据我的观察,依照晓庄创设的目的说:‘要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不如把晓庄名为新村实验区,倒很干脆”。[16]沪东公社成立于1917年,由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人葛学溥在杨树浦路建立,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社区服务机构。沪东公社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教育,开办各类成人补习学校和短期扫盲班等,其他社区服务包括民众图书馆、民众茶园、民众同乐会、施诊所等。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由陶行知于1927年创办,有中小学、幼稚园,还有民众补习学校、茶园、剧社、商店等。陶行知通过教育实践总结出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其核心观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
20世纪30年代,国内一些城市有了以“新村”命名的新区。1937年,成都发布新村建设计划。1939年,西康省会康定确定在头道桥建设新村住宅区。这一时期,各地被命名为“某某新村”的住宅小区已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被提上日程,它成为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受条件限制,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家庭住房短缺严重,因此加快建设工人住宅小区提上日程。1952年5月,曹杨新村在上海建成,这是新中国首个工人住宅小区,并很快成为各地效法的样板。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工人新村”成为城市居民眼中最时髦的居住方式,一些大型工人新村相继建成,如20世纪50年代济南兴建的二七新村、工人新村等八大新村,沈阳铁西区工人村等。沈阳工人村位于沈阳铁西区西南部,占地面积0.6平方公里,由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投资1200万元兴建,1952年12月第一期工程完工。工人村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有景点绿化带,兴办了中小学校、幼儿园、饭店、副食商店、照相馆、粮站、卫生院、邮电支局、储蓄所等。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新村”命名的街区在全国各城镇随处可见。工人新村吸收了新村的理念并加以改造。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把为全村服务的商业文化、行政机构集中设置,其中设立各项公共建筑,包括合作社(商店)、邮局、银行和文化馆等,组成新村中心”。[17]工人的业余生活主要借助于公共空间,如阅览室、电影院、文体活动中心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城市布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 50 年代的新村建设,一方面通过紧凑的住宅设计以容纳更多的人口,达到缓解住房困难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体现出了强大的国家意志,唤醒了大家的集体主义意识,“工人新村”成为了互助的集体化的生活空间。“新村”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亦纷纷建立。1958年8 月 28 日应城率先建起了湖北省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红旗公社作为共产主义建设样板,社员除分配制度外,生活上也要体现出共产主义优越性,因此,新村建设很快纳入各级组织议事日程,并紧锣密鼓展开。应城县高度重视新村建设,成立了“共产主义新村基本建设委员会”。由于新村的规划立足样板建设,立足于大而全,银行、文化宫、电影院、工厂、食堂等应有尽有,大大超出了当时应城农村实际,最后被迫停工。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建设的特色小镇、特色村落也吸纳了新村的理念。以“新村”命名的城市住宅小区更是比比皆是,配套设施齐全的广州祈福新村便是一个典型样板。这说明“新村”不仅是人们眼里美好的想象家园,也是渴望实现新生活的共同理想。
四、结 语
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过程中,因为传播者视角的差异,或其他思潮的渗入,以及现实改造需要、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有复杂多变的特征。但不管怎样变化,新村主义始终与民族的救亡图存相结合,与时俱进。在这一根本点上,它与日本新村有很大差别。武者小路实笃表示他嫌恶社会改良家或革命家的称号,“宁可人家说我是思想家或是宗教家”,[11]78中国新村主义者则大多承载了改造社会的使命,这也就造成了二者不同的结局。
日本新村从完善个性出发,强调“自我”与“爱”,在共产的同时也允许一定程度的私有的存在。他们尽量不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不挑战现有的政治体制,故历经百年能够存活下来,只是影响有限,仅具样本价值。直至今天,仍不时有人参观访问日本日向新村。而中国的新村主义者多为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惜牺牲自我,以改造整个社会为己任。他们在新村和工读互助运动失败后转而选择暴力革命,并最终夺取了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没有放弃当年的理想,我们从遍布神州大地的工人新村和人民公社,不难找寻到新村的影子。
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大体沿着乡村和城市两条路径变化着。在乡村,王拱璧和傅柏翠直接从日本接触到了新村主义,并结合具体国情将新村主义嫁接到家乡进行实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受到新村思想的直接影响,但又有别于日本的新村,创造性地开发出了带有本土特色的新村发展模式。叶圣陶、匡互生、陶行知等人,则通过乡村教育实践,将新村与乡建运动结合起来,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独树一帜的派别。他们实验“生活与学校结合的新教育模式”,大家共同耕作,分享劳动的快乐,让学生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又联系和发动了周边群众。这一教育创新旨在促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日本新村思想是相契合的。但它的影响面更广,更具教育实践和社会改造的意义。在城市,新村主义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工读互助团这种乌托邦由于过于激进,成为无政府主义试验场所,很快昙花一现,归于失败,工读互助团成员何孟雄、施存统等人因此转而走向了激进的革命道路。而以模范町村为目标的上海龙华新村,则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却了原来高远的新村理想,一步步地蜕变成了商业资本家的工具,但这种新型的居住模式却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