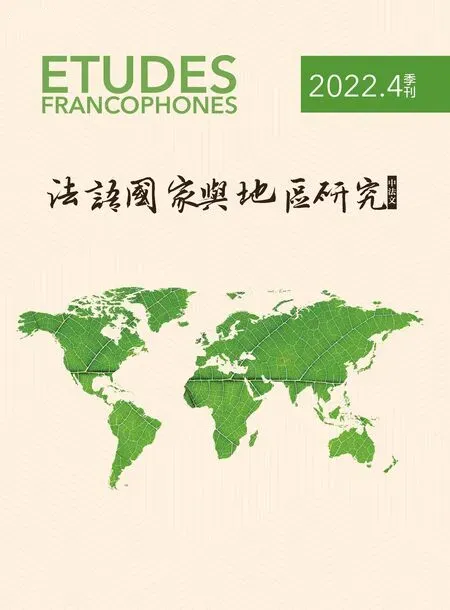莫里亚克《蛇结》中的叙事声音①
2022-11-20陈泽帆陈穗湘
陈泽帆 陈穗湘
内容提要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蛇结》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叙述者路易讲述了他对妻子和子女的仇恨以及想要剥夺他们继承权的计划。然而,在故事的结尾,他却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重新找回了爱和信仰。小说的力量不在于情节的发展,而在于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及其修正。通过对小说叙事声音的分析,我们将阐明小说的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关系,挖掘小说的不可靠叙述及其修正,发现作者通过叙事技巧表达的对叙述者的同情,最终揭示小说的意义以及莫里亚克关于家庭、爱、信仰的看法。
一、《蛇结》中的叙事交流
在叙事声音的研究中,叙事交流是最基本的问题。在《故事与话语》(Story and Discourse)中,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用以下图表为我们展示了叙事交流情境:

这个图表为我们厘清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之间以及真实读者、隐含读者、受述者之间的关系。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是处于现实生活中的,隐含作者是真实读者通过文本阅读推断出的一个人格,隐含读者则是能接受隐含作者全部价值判断的理想读者。查特曼认为叙述者和受述者可以不一定存在,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叙述是交流的关键:(叙述中)有一个叙述的给予者,也有一个叙述的接收者……不存在没有叙述者和听众的叙述。”②Roland Barthes.«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écits».Poétique du récit.Paris:Seuil,coll.«Points»,1977,p.38.在阅读《蛇结》(Le Nœud de Vipères)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辨认出一直在场叙述的叙述者,但他的受述者则有待辨析。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界定也是我们分析小说不可靠叙述的关键。
1.《蛇结》中的叙述者和受述者
根据查特曼的图表,作者和隐含作者在文本之外,叙述者则在文本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根据叙述者是否是文本中的一个人物区分了两种叙述者的类型:“在此要把两种类型的叙事区分开来,一类是叙述者不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另一类是叙述者作为人物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③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72.他将第一类叙事称为“异故事”(hétérodiégétique),将第二类叙事称为“同故事”(homodiégétique)。接着,热奈特根据叙述层次又区分了另外两种叙述者。向故事外的对象讲述故事的为故事外叙述者,向故事内的对象讲述故事的则为故事内叙述者。在《蛇结》中,叙述者路易同时也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向故事内的人物讲述,因此他是一位同故事、故事内叙述者。
罗伊特(Yves Reuter)认为:“受述者基本上通过一组语言符号(例如‘你’‘您’)被构建出来,这些符号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指示出谁是‘接收’故事的人。”④Yves Reuter.L’analyse du récit.Paris:Armand Colin,coll.«Lettres Sup.»,2016,p.55.据此,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蛇结》中只有主人公路易一个叙述者,然而他却有多个叙述的对象,一些如“你”或“您”的语言符号可以帮助我们区分这些不同的受述者。
小说第一部分,受述者是叙述者的妻子。开篇头两句话即揭示了受述者的身份,使得真实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是故事的受述者,而是像发现了一封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私密信件:“你在我的保险柜里一扎证券上面发现这封信,肯定会吃一惊。也许最好把信托付给公证人,让他在我过世后转交给你,或者把信放在我写字台的抽屉里。”(莫里亚克 2013:5)
小说第二部分则是叙述者为自己而写的,他通过一本日记宣泄自己的情感和想法,甚至在临终前作出忏悔,我们可以在这一部分看到大量的内心独白,例如他对自己的欲望进行的反思:“我一辈子都受制于一种欲念,其实它并没有支配我的力量。像一条对月狂吠的狗,我不过是受到一道反光的迷惑。到六十八岁上才醒悟过来!临死之际方始得到新生!但愿我还能多活几年、几个月、几个星期……”(莫里亚克 2013:237)
另一方面,叙述者想在他死后将这本册子留给他的子女们。他在第十五章写道:“我现在知道我这本笔记是为谁写的了,我必须完成我的自白;不过我应该剔除其中好几页,因为他们读到这些地方一定会受不了的。”(莫里亚克 2013:191)通过这些句子我们可以发现这本册子并不是没有别的叙述对象。叙述者希望将它留给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子女,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他。
2.《蛇结》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
“隐含作者”及“第二自我”的概念是由布斯(Wayne C.Booth)在他的著作《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提出的,他认为对于作者而言,“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作家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表明自己。”(布斯 1986:81)借助布斯的理论,我们认为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是不同的,他只对具体的某部作品负责,一部作品的价值标准是可以和真实作者本人的价值标准不同的,布斯的理论侧重于论述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一种选择。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关于隐含作者的看法则与布斯不同,他认为:“隐含的作者应该被看作是读者从文本的全部成分中综合推断出来的构想物。”⑤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黄虹伟,傅浩,于振邦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57.
在《蛇结》的引言中,作者表达了他对叙述者的态度:“此人与自家人为敌,这颗心被怨恨和贪吝败坏。”(莫里亚克 2013:3)显然,隐含作者的价值标准和叙述者的并不相同。此外,既然隐含作者也是真实作者的一个选择,我们还可以借助文本外的因素构建小说隐含作者的形象。
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加强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学生应全面准确掌握的理论知识、专业能力和技能水平,同时,积极探索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导的长期、稳定、制度化的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建立更加完善的学习实践和现代学徒制度。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等方面突出职业导向,不断推进应用型本科院校与行业企业的交流互动,深化校企合作,推动校企之间实施全方位、深层次、全过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小说叙述者是一位仇视家人、蔑视基督教的吝啬鬼,而隐含作者以及真实作者莫里亚克则很明显并不赞同叙述者的价值判断。首先,“家庭”是莫里亚克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家庭是一个同时充满爱和恨的场所,尽管家庭成员饱受家庭矛盾的折磨和伤害,但他的人物总是能在最后关头重新找回家庭的爱。塞阿耶(André Séailles)总结道:“关于家庭最终的定论是由《不为人爱的人们》(Les Mal aimés,莫里亚克1945年发表戏剧)中的一个角色给出的,在背叛、对抗和仇恨的呐喊之后,伊丽莎白·德·维雷拉德低声说:‘但我们彼此仍然相爱’。”⑥André Séailles.Mauriac.Paris:Bordas,1972,p.210.其次,莫里亚克是一位天主教作家,“从小就沉浸在深深的宗教家庭氛围中,这种氛围渗透在他的许多作品中”⑦Guillaume Gros.François Mauriac.Paris:Geste éditions,coll.«Portrait d’histoire»,2011,p.115.。从这些证据中我们得出结论:莫里亚克在他的作品中寻求家庭的爱和天主教的信仰,他的价值标准自然与小说叙述者路易不同。
在叙事交流中,接收隐含作者信息的主体为隐含读者。隐含读者是隐含作者理想的读者,因而我们不能将其同真实读者相混,因为并非所有的读者都能理解隐含作者的思想与价值判断。隐含读者应该是隐含作者的“同谋”,和他们相对立的则是小说的不可靠叙述者。通过小说引言以及有关莫里亚克及其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断出隐含作者非常重视家庭及天主教信仰,我们应该尝试成为隐含读者(隐含作者理想的读者)以理解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
二、《蛇结》中的不可靠叙述
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是我们研究小说叙事声音的第二个问题。布斯是如此定义“可靠”和“不可靠”两个术语的:“当叙述者的语言和行动同作品的价值标准(也就是隐含作者的价值标准)相同时,他就是可靠的(reliable),相反情况下他则为不可靠的(unreliable)”。 (Booth 1977:105)在《叙事学词典》(DictionaryofNarratology)中,普林斯(Gerald Prince)也做出了相近的定义:“其价值观(品味、判断、道德观)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相偏离的叙述者。”⑧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39.《蛇结》中叙述者路易同时也是小说的一个人物,他的叙述在事件上和价值观上都存在不可靠的地方,但随着小说的推进,他也逐渐修正了自己的不可靠。
1.叙述者路易的不可靠叙述
在《蛇结》中,叙述者既存在事件叙述上的不可靠,又存在价值观上的不可靠。首先,叙述者路易讲述的事实是让人怀疑的,尤其是关于他妻子的事情。在婚后他觉得妻子不再关心他,而且避免和他交谈或拥抱,在日记的开始,他就谴责妻子的冷漠:“我压根儿在你所关心的事物之外,你避开我,不是出于害怕,而是由于厌烦。”(莫里亚克 2013:9)在孩子们相继出生后,孩子成了她唯一关心的事情:“你的注意力从我身上移开了。你不再看我一眼;千真万确,你的心里只有孩子。我使你怀了胎,便完成了你期待于我的使命。”(莫里亚克 2013:65)读到这些描述,我们很自然地会猜想他妻子一点也不在乎他,但在他出发去巴黎前和妻子的对话中,妻子伊莎的行为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当初,从我们分开睡的那个时候起,好多年来,即便孩子们生病,不管我多么想照顾他们,我也不留一个在身边过夜,因为我老在等待,我总希望你会来的。”(莫里亚克 2013:177)这些话语不仅引起了路易的沉思,也引起了读者对路易的描述的怀疑。我们认为路易对事件的描述是不可靠的,他的妻子可能一直都尝试靠近他,是他自己拒绝了。
除了事实的不可靠外,叙述者路易在价值观上同样缺乏可靠性,例如,他将自己的财富视为一切,制定了不让他的子女获得继承权的详细计划。从引言中我们知道,路易对于金钱、子女、家庭的态度是极端的,这些态度肯定不是隐含作者持有的,读者自然也不能赞同这些价值观。布斯认为:“叙述者的价值观和读者的价值观之间可能会有或大或小的差距”。(Booth 1977:102)他在同一段落中也举了《蛇结》作为例子。在这种情况下,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可被视为“同谋”,而叙述者的语言和行为则变成具有讽刺意味的。叙述者的价值观和作品的,即隐含作者或真实作者的价值观是不相符的,路易是缺乏价值观可靠性的不可靠叙述者。
最后,在宗教问题上,叙述者的价值观也和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不同。正如我们提到的,莫里亚克是一位天主教作家,他的宗教信仰滋养了他的作品,而《蛇结》叙述者路易则对信仰持怀疑态度。他蔑视宗教仪式:他从不去做弥撒;他在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不吃肉的耶稣受难日吃羊排以表示自己对宗教的不在乎。总之,他并不是一个遵守宗教教义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宗教观念和隐含作者、或者说作家本人的宗教观念有很大的差距。
2.路易不可靠叙述的修正
不可靠叙述的修正的概念同样是由布斯提出的:“可靠叙述者或不可靠叙述者在没有其他叙述者的支持下都可以从始至终地坚持自己,或者,他们也可以被支持或被修正。”(Booth 1977:106—107)在《蛇结》中,叙述者路易通过他妻子的话语和日记修正了自己的部分叙述。他一直认为妻子长期冷落他,但当妻子向他解释其实她经常整晚上都在等他后,他第一次对自己对妻子的偏见进行了反思:“此时此际我不由发生疑问。对于那个与我们同床共寝的人,我们观察了将近半个世纪,难道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她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否养成习惯,对她的言行有所取舍,只留下其中足以滋长我们牢骚和怨恨的部分?”(莫里亚克 2013:178)
在宗教信仰方面,他觉得女儿玛丽是家里唯一真正的基督徒:“小玛丽却有一种感人肺腑的虔诚,一股对仆人、对佃农、对穷人的发自内心的热忱。”(莫里亚克 2013:94)在他眼里,玛丽是一个天使,如果不是因为夭折的话,也许玛丽能够指引他向上帝靠近。在生命的尽头,他终于明白唯有上帝能够拯救他的灵魂,使他能够爱人并且被人所爱:“是的,需要那个人,在他身边我们大家都能携起手来,他将对我家里人担保我内心斗争的胜利;需要那个人,他将为我作证,将从我肩上卸下那个不堪忍受的重负,把它背到自己身上。”(莫里亚克 2013:248)“那个人”指的就是上帝,在上帝的指引下,他终于发现了自己身上温柔的情感和模糊的信仰。他承认自己曾有好几次机会得到这种指引,但他都放弃了:“我不知疲倦地设法丢掉这把钥匙,而在我生活的每一个转折关头,总有一只神秘的手把钥匙递给我。”(莫里亚克 2013:267)对他来说,这把钥匙指的就是上帝的启示。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叙述者的宗教观念与作品的观念越来越契合,也就是说,通过纠正自己在宗教观念上的不可靠叙述,叙述者变得越来越可靠。
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的心理状态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发生了转变,布斯认为这是现代小说一个明显的特征:“现代小说中最流行的情节之一,是描绘一个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个人特性发生变化的叙述者。……人物向上或堕落的故事越来越受欢迎。”(Booth 1977:102)在《蛇结》中,叙述者是一个在道德上和价值观念上都发生深刻转变的主人公,叙述者内心的描述比情节的发展更为重要。正如巴特隆(Sylvie Patron)所说:“不可靠叙述的目的是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叙述者而不是被讲述的故事上,并激起他们对叙述者心理活动的兴趣。”⑨Sylvie Patron.Le narrateur.Paris:Lambert-Lucas,coll.«Rééditions/Réimpressions»,2016,p.130.这一转变正是小说的主题—蛇结的解开,《蛇结》的力量就在于叙述者可靠性的变化。一开始时叙述者将自己的内心禁闭,他的女儿玛丽本来有机会改变他,却早早夭折了。紧接着,在妻子死后,他对自己和家人都重新进行了反思,最终发现了爱和信仰。小说的主题正是建立在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主人公路易这一彻底转变之上的。正如小说名《蛇结》一样,小说讲述了叙述者内心的蛇结是如何解开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作者想展现的小说最主要的价值。
三、《蛇结》中对叙述者路易的同情
作者如何通过叙事声音激发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同时也表达自己的同情,是我们研究的最后一个问题。布斯认为,在作者沉默的小说中,“只要人物认为并感受到,什么可能直接作为他所面临情况的可靠线索,读者就可能有身临其境之感”(布斯 1986:305),这一效果在同故事叙述(第一人称叙述)中更加明显,因为读者只有通过叙述者的视角才能进入到小说中。作者借助对叙述者内心的描述、大量的内心独白引发读者的同情,使读者与叙述者同化。此外,通过小说的引言我们也能观察到,作者对叙述者同样也是怀有同情的,有时作者甚至还借叙述者之口表达他的一些观点。
1.读者对路易的同情
在《蛇结》中,同故事叙述者“我”总是无处不在。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为我们阐明了语言的主体性和语言中的陈述理论。他认为陈述(énonciation)是陈述主体(locuteur)通过说“我”来占用语言的过程,它同时基于特定的语言标志,例如时间(今天,现在)和空间(这里,那里)。他解释道:“一旦他成为一个陈述主体并对语言负责时,他就将他者置于他面前,无论他赋予这个他者的在场程度如何。任何陈述,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是一种话语(allocution),都会产生一个受话者(allocutaire)。”⑩Emile Benveniste.«L’appareil formel de l’énonciation».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I.Paris:Gallimard,1974,p.82.在小说中,叙述者路易正是通过贯穿小说的“我”占用了语言,然而,读者并不会将自己和受话者同化,因为我们并不是这本日记的对象,我们仿佛是在偷读一封私密的信件。在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倾向于和叙述者同化,布洛克(Béatrice Bloch)的观点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读者会立即和一个感知者‘我’(也就是说对他的身体有内在的感知,同时也有视觉、听觉等)同化,因为读者处于对书面符号的感知情境中,他很容易与在感知情境中的角色叙述者同化。”⑪Béatrice Bloch.«Voix du narrateur et identification du lecteur».Cahier de narratologie.2001(1):224.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描述叙述者身体内在感知的句子,例如:“我坐出租车回到勃雷阿街,躺到床上”“我切开一块嫩白色的兔肉”“我把电报揉成一团,继续吃饭”(莫里亚克 2013:200,213,214)。这些对于内部感知过于精细的叙述会使读者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叙述者同化。当我们读到这些句子时,我们觉得似乎自己也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品尝着兔子,手里拿着皱巴巴的电报。当路易留心偷听着家人的低声谈话与争辩,却没办法辨认出到底是谁在说话的时候,这种同化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由于缺少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读者只能透过叙述者的视角了解故事世界。这样的同化有利于激起读者对叙述者的同情。布斯认为:“也许,与一个在不起作用的作者陪伴下的叙述者打交道,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印象,就是感情上距离的渐渐缩小。”(布斯 1986:305)通过路易的描述,读者能够感知到他所看到和感觉到的事物。当叙述者感到孤立无援时,这种效果会更加明显。例如,当路易担心他的子女在谋划着夺走他的遗产的“阴谋”时,我们同样感受到令我们窒息的焦虑和威胁。我们甚至希望他能够成功地报复他的子女,不给他们留下任何遗产,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他的一边,因为我们只能了解他的想法和感受,我们无法再对他的叙述无动于衷。
心理描写同样强化了读者对叙述者的同情。通过对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爱玛》(Emma)的分析,布斯认为读者会随着爱玛的视角进入故事,而不是站在她的对立面。他认为对内视角的控制有助于激发读者的同情:“如果一位作者要使那些不具有强烈美德的人物获得强烈的同情,那么,长久和深入的内心观察提供的心理生动性将会有助于他。”(布斯 1986:422)在小说中,路易一边叙述一边借用内心独白展现自己的心理世界,读者几乎了解他所有的想法。我们可以了解到路易在爱情中的自卑情结、被爱时的喜悦、在妻子向他供认有过相爱的未婚夫时内心受到的伤害以及他对玛丽的感情。当路易想转移财产的计划被儿子发现后,他感到十分焦虑,觉得他所有的保险箱可能也会被发现,他一生积攒的财富可能在死后会被子女们挥霍殆尽。当读到这些内心独白时,读者很自然地会对可怜的路易怀有怜悯之心,并且不自觉地将他的子女们也视为敌对一方。读者被叙述者的内心视角所影响,忽略了他的自私与道德上的错误。布斯在谈到内心观察的作用时说:“我们已经看到,内心观察可以为甚至最邪恶的人物创造同情。在运用得当时,这一效果可以在迫使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物的人性价值方面发挥无限作用,即一个我们从客观上考察其行动会加以谴责的人物。……运用这一效果的作品时常导致道德混乱。”(布斯 1986:423)《蛇结》正好可以作为布斯所说的“道德混乱”的一个典型例子。对于那些不能意识到小说的不可靠叙述以及隐含作者的道德观念的读者来说,他们确实有可能赞同叙述者的道德观念,并同时把它当成小说的道德观念。
在小说结尾,我们发现叙述者路易的内心独白标志着他心理上的转变,他最终重新发现了爱与信仰。他心中的蛇结终于解开,也最终明白了自己的罪孽:对亲人的仇恨、对报复的渴望、对金钱的欲望、对救赎的拒绝。他最终成了一个可靠的叙述者,而也是在这个时候,读者对他的同情达到了顶点。附录中他儿子写给他女儿的信更加强化了我们对他的同情。在读完父亲的这本日记后,他的儿子始终无法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父亲最终留下了遗产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可怜的人自知大限将临,没有时间也没办法另想法子剥夺我们的继承权。”(莫里亚克 2013:272)他甚至声称他的父亲有间歇性谵妄,这一误会更加激发了读者对路易的同情,因为即使他在日记中作出了忏悔,依然无法得到子女们的理解。
2.作者对路易的同情
由于小说的同故事叙述,除了很简短的引言以外,作者几乎没有机会进行表达。在引言中,作者请求读者即使知道路易是卑鄙的,也要对他怀有怜悯,他还请求读者在读完小说后能够理解路易:“不对,这个吝啬鬼珍视的并不是金钱,这个发狂的人渴望的也不是报复。什么才是他真正热爱的对象,读者只要有毅力和勇气听完这个人被死亡打断的自白,自然便会了解……”(莫里亚克 2013:4)
读完小说后,我们发现尽管路易蔑视宗教,但在他心中深处其实一直都埋藏着信仰的微光,只不过那些平庸的基督徒—他的家人们—阻碍了他感受到上帝的爱。他们一方面严格遵守宗教礼仪,另一方面却没有虔诚的信徒所有的精神:大爱、慷慨、真诚、友爱等。他之所以欣赏玛丽身上的品质,正是因为他觉得她拥有这些精神。作者对路易在宗教上的困惑表示遗憾的同时,也对他表示同情,因为他也谴责平庸的基督徒那些与信仰脱节的行为。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莫里亚克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作品展现了上帝对人的爱,然而,我们有时却“可以感受到莫里亚克小说中的宗教世界令人窒息甚至可怕”⑫Jean-Pierre Jossua.«Mauriac romancier ou le religieux fluctuant.Essai de discernement théologique».Revu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et théologiques,3/2007 (Tome 91),p.514.。尽管他有虔诚的信仰,却也对一些宗教教义、无意义的仪式、教会的禁欲主义感到厌恶。1922年出版的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Le Baiser au lépreux)讲述了一段不幸的包办婚姻,成为一个基督教要求的真正的妻子的愿望以及生理上对丈夫的厌恶深深折磨着诺埃米,她对自己不能遵从上帝的要求爱她的丈夫感到非常懊悔,不断地祈求上帝原谅她的错误。诺埃米的苦难和牺牲在基督教看来是值得称赞的,而这正是莫里亚克所拒绝的。他指责宗教严格教义的枷锁,在他看来,信仰上帝并不是盲目的崇拜。
在《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普鲁斯特借叙述者马塞尔之口表达了他关于艺术、文学、爱情等许多方面的观点。在《蛇结》中,莫里亚克同样借叙述者路易之口表达了他关于宗教的一些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并不完全是不可靠的了,他同作者的观点有一些相同之处。在小说中,路易谴责了妻子的吝啬:“那个每天清早推着菜车沿街叫卖的穷老太婆,如果她向你伸手乞讨,你会慷慨解囊施舍,可她每次把生菜卖给你时,你不从她的薄利中克扣几个小钱就似乎有损你的面子似的。”(莫里亚克 2013:97)我们认为,路易对妻子吝啬的谴责恰恰对应于莫里亚克对一些人没有真正慈悲心的谴责。对于这些人来说,虽然他们信仰上帝,但他们宁愿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寻求财富和安逸的生活。如果他们转向宗教,那只是为了他们的良心能好受点,因此,对他们来说,慈善不是目标,而是良心的救赎。
在《蛇结》附录里路易外孙女的信中,她同样捍卫作者所倡导的那种宗教精神:“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生活是完全分开的。我们只是口头上皈依宗教,而我们的思想、愿望、行为与信仰完全脱节。我们浑身的力量都用在追求物质财富上,而外公他……”(莫里亚克 2013:281)这封信也是作者同情叙述者的证明,因为这封信不仅仅是路易的外孙女在为他辩护,实际上也是作者在为他的主人公辩护。路易儿女的思想、欲望和行为并不符合真正基督徒的要求,相反,路易虽然没有皈依基督教,但仍然保持着基督教精神,并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找到了信仰。作者的同情和叙述者的宗教信仰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只有上帝的爱与拯救才能解开隐藏在心底的毒蛇之结。
结语
叙事声音的分析对于第一人称小说《蛇结》的叙事学研究至关重要。首先,叙事交流理论帮助我们区分出文本内的各种主体(叙述者和受述者,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和文本之外的各种主体(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蛇结》中的叙述者是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同故事叙述者和一个向文本中的角色讲述故事的故事内叙述者。他的受述者包括他的妻子和子女,同时他也对自己作出忏悔。
接着,对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分析使我们关注到小说不可靠叙述的问题。在小说中,叙述者早就误解了妻子对他的爱,所以他所讲述的事实并不完全正确。此外,叙述者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与隐含作者或作品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然而,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并非贯穿始终。在他的妻子去世后,他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他的观念也渐渐接近小说或作者的观念。总之,小说的价值和力量就在于叙述者可靠性的变化。
最后,小说中对同情的控制减弱了读者对不可靠叙述的感知,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混乱。内在的视角有助于激发读者的同情,同时作者表达了他对叙述者的同情以及他在某些观点上对叙述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