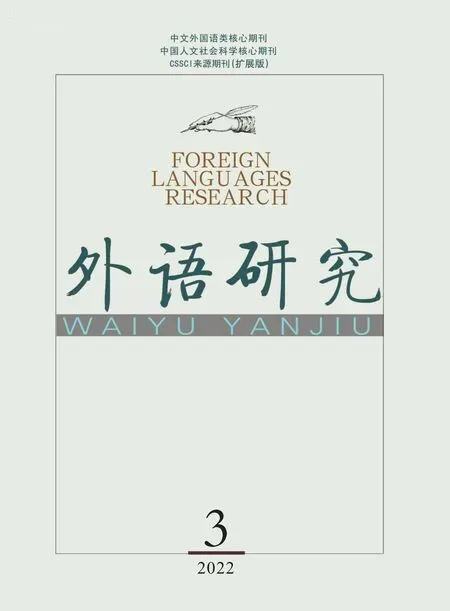《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阶级、冲突与婚姻*
2022-11-17胡鹏
胡 鹏
(四川外国语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重庆 400031)
0.引言
恩格斯在1873年12月1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说到“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1973:107),又在1859年5月18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福斯塔夫式背景”:“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这幅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马克思,恩格斯1972:585)显然恩格斯也和几个世纪以来的观众一样,对莎士比亚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以下简称《温》)的精心设计和舞台表演拍案叫绝,但更重要的是恩格斯认为《温》把置于社会矛盾和语言对比中的中产阶级戏剧化了,即真实地反映出莎士比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现实。的确,该剧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唯一一部精确设置在当时观众耳熟能详、真实英国城镇的作品。整体而言,其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在舞台上展现出一幅有关小乡镇里的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其中有店主、医生、法官、牧师、市民及其妻子儿女。(Evans 1997:320)此剧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充分反映出伊丽莎白时期人们所生活的经济世界,描述了当时中产阶级家庭贪财心态,正如亚瑟·肯尼指出该剧“最重要的……首先就是一种经济叙事”。(Kinney 1993:234)本文试图以《温》为例,结合该剧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分析剧中的阶级及其冲突,指出这一时期人们共同的金钱价值观,以及莎士比亚在对待阶级矛盾上的复杂心态和试图和解的理想视角。
1.阶级问题
戏剧甫一开场时上台的并非如剧名所指的主角培琪大娘和福德大娘,亦无福斯塔夫。在正式进入戏剧的主要情节——福斯塔夫和两位大娘的故事,以及次要情节——安的婚姻之前,非常突兀地以法官夏禄及其侄儿斯兰德、牧师爱文斯等三人的对话开场。其中夏禄蠢笨的侄儿斯兰德吹嘘着舅舅的社会地位,继而强调其家族纹章,而牧师爱文斯的误读也充满了讽刺意味。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该剧对夏禄个人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强调。初登场的法官怒气冲冲,扬言要到御前状告福斯塔夫,声称“就算他是二十个约翰-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s),他也不能欺侮夏禄老爷(Robert Shllow esquire)”,其侄儿斯兰德则立马补充说他的舅舅“是葛罗斯特郡的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 and Coram)”,而夏禄骄傲地介绍自己还是个“推事(Cust-a-lorum)”①。(莎士比亚1994:177;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夏禄老爷(Esquire)控诉福斯塔夫骑士(Knight),彰显出地位的差异,实际上骑士是不能欺辱老爷的,因为Esquire意为在战场上手持骑士盾牌的绅士,后来特指“一位绅士,地位略低于骑士,有资格佩戴纹章”,大部分绅士都是有佩戴纹章资格的人,拥有继承来自先代的财产与庄园(Melchiori 2000:124)的权利。斯兰德说夏禄是Coram,实际上是拉丁文quorum(源自法官就任时的准则,引申为仲裁官)的变体,暗示着对夏禄法官头衔的正式承认。(ibid.:124-125)而夏禄特意突出拉丁文custosrotulorum的缩写“推事”,意味着自己是掌管档案的法官,即记录审判的治安法官中的首席法官。(ibid.:125)另一方面,斯兰德和夏禄在对话中展现着他们家族三百年的悠久历史,强调高贵的出身和血脉谱系:“牧师先生,我告诉您吧,他出身就是个绅士(gentleman born),签起名来,总是要加上‘大人(Armigero)’两个字,无论什么公文、笔据、帐单、契约,写起来总是‘夏禄大人’。”(177)他吹捧绅士出身的舅舅在正式文件上签名都要加上Armigero,这也是对拉丁文Armiger的拼写错误,原拉丁文指中世纪对绅士的定义:“一个拥有高贵出生并在战斗中带着骑士盾牌的人”(同上),实际与上文中的“老爷”同义(同上)。斯兰德接着说,“他的子孙在他以前就是这样写了,他的祖宗在他以后也可以这样写”(同上),斯兰德是个低能儿,说话总是颠倒的,此句话应当理解为他前面的祖祖辈辈和他后面的子子孙孙,接着指明了引以为傲的家族纹章:“他们家里那件绣着十二条白梭子鱼的外套(the dozen white luces in their coat[-of-arms])可以作为证明”(同上)。在他看来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能够借光使用十二条梭子鱼的家族纹章。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梭子鱼在爱文斯的威尔士英语中变成了白虱子(louses),牧师还津津有味地评论“那真是相得益彰(well passant)”(同上),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passing well,而passant是一个纹章学术语,即纹章上的爬行动物或生物抬足呈步态状,但是这里却变成了步行的鱼或虱子,充满讽刺意味。(Edgecombe 2004:34-35)夏禄赶紧纠正他的话并强调了两点,其一这不是白虱子,其二这是“淡水河里的‘白梭子鱼’”,而不是爱文斯错误发音cod所指海水中的鲟鱼。斯兰德对舅舅说“这十二条鱼我都可以‘借光(quarter)’”,对方则肯定地回答:“你可以,你结了婚之后可以借你妻家的光。”(178)Quarter也是纹章学术语,即娶绅士家女子后可添加对方家族纹章到自己纹章上面,占盾形纹章四分之一的面积。无论如何,作为夏禄假定的继承人,他可以将夏禄家族的纹章图形放在自己的纹章之中,实际上就是把纹章一分为四,其中两部分包含原有家族的纹章,另外两个部分则是通过与一位绅士家庭联姻获得。(Melchiori 2000:126)反讽的是爱文斯接口说“家里的钱财都让人借个光,这可坏事了”(178),剧作家利用牧师的错误解释指出了通过婚姻获得四分之一的纹章实际上变成了“婚姻”本身。
进一步而言,剧中有关纹章的内容是莎士比亚年轻时斯特拉福德镇的真实写照。“十二条白梭子鱼”指向了斯特拉福德镇附近查莱克特的露西家族,他们的纹章中就包含三条银梭子鱼。早在18世纪就有这样的传闻(特别在很多传记中有记载),说莎士比亚不得不离开家乡是因为他在托马斯·露西爵士的林苑里偷猎麋鹿,因此有人认为莎士比亚在剧中对夏禄的嘲讽是为了向露西家族报复。(Crane 1997:4)而威尔士牧师爱文斯把coat念成了cod,这个词不仅有“鲟鱼”之意,更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指“阴囊”的俚语,从而丑化了露西家族的纹章。17世纪晚期的牧师理查德·戴维斯初次记录说莎士比亚“在偷猎鹿和野兔时陷入了极大的麻烦,尤其是因为偷了——露西爵士的鹿和野兔,这个爵士派人多次鞭打他,还将他关押了一段时间,最终迫使他逃离家乡,直奔大好前程而去”,这一说法被后来的传记作家采用,但其真实性存疑,一是露西爵士1600年就过世了,二是他没有林苑,三是鞭挞并非当时对盗猎行为的合法处罚。(转引自Greenblatt 2004:150-151)重要的人物通常会因为其重要性成为人们揶揄的对象,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莎士比亚对露西家族印象深刻。
更为重要的是莎士比亚及其家族在具备财力的基础上试图申请纹章寻求自身社会地位上升的努力。那时的社会在贵族和“普通人”“下等人”之间存在十分严格的等级划分,一般被神化为血统的区别,一种无法改变、与生俱来的特性。但此界限同时又是可以跨越的,“至于绅士”,托马斯·史密斯写道:“他们在英格兰变得廉价了。因为任何学习王国律法、上过大学、声称受过文科教育的人,简单地说,任何无所事事、不从事体力劳动、具有绅士的姿态、钱财和外表的人都会被称作老爷,因为这是人们对乡绅和其他绅士的称呼……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出钱向纹章局购买新造好、新设计的纹章,这个称号就会由上述纹章局伪称是通过读旧文献发现的。”(ibid.:77)早在约1576年,成为当地市镇官员之后的约翰·莎士比亚就曾提出过申请,但后来由于经济情况恶化而搁置。1596年10月20日,纹章官威廉·迪斯克同意了约翰·莎士比亚的第二次纹章申请,拟授予其纹章,但实际上莎士比亚和父亲足足等了三年,直到1599年这项梦寐以求的家族殊荣最终成功实现,过程之中约翰·莎士比亚也如愿以偿地将自己的纹章与妻子娘家阿登家族的纹章合并,他的男性后代也可以将母亲家族的纹章置于四分之一盾面上。(李2019:196-199)
因此正如莫里斯·亨特指出那样,这部喜剧的开场对话实际上强调了三点:首先这是一部关于绅士状态和地位的戏剧;其次,莎士比亚当时为自己的家族申请纹章(或许当时还在担心能否合法地获得纹章)也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何对这一主题感兴趣。最后矛盾的是,莎士比亚在戏剧的开始通过展示自大的角色讽刺了拥有纹章的人,但他们的社会状态正是作家个人及其家族所渴求的。(Hunt 2008:411)1577年,威廉·哈里森划分了四个阶层:“绅士、市民、约曼、工匠/劳工”。(Harrison 1968:54)史学家基思·赖特森将1600年的英国人划分为贵族、市民、约曼、工匠和农民工。(Wrightson 1982:21)两人的划分思路基本相同,约曼指拥有40先令每年收益价值土地的自耕农男性或农民乡绅。而社会最底层包括“零工、贫农、技工和仆人”,他们“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权力,却是被统治的对象且不能统治别人”。(ibid.:91)赖特森将贵族和绅士等同,隐晦地把某些市民也当作了绅士(显然不是所有的绅士都是贵族)。在莎士比亚的时代,gentry是gentlemen的一个更广义的同义词。绅士的顶层接近贵族的底层,即那些没有佩戴纹章资格的非贵族绅士,同时比他们地位低的是乡绅租户(gentlemen tenants)。(Hunt 2008:418;Theis 2001:48)培琪家族有产业无纹章却被视为绅士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莎士比亚的祖父理查德是农民、约曼,而他的儿子约翰和孙子威廉则通过努力成为了市民以及拥有纹章的乡绅。但演员属于社会底层,亨利·皮查姆在《绅士全集》(The Complete Gentleman 1622)中在讨论“舞台演员”时标注了16世纪的观念,即演员和那些“击剑手、杂耍人、舞者、江湖骗子、饲熊者类似的人”一样不可能成为绅士,因为“他们用身体进行辛苦工作”。(Peacham 1962:23)因此毫不奇怪剧作家不以自己职业身份为荣,在世时仅仅将之视为谋生手段,赚取钱财后则在家乡置地买房,并申请纹章以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与其说《温》剧是有关“绅士状态”的戏剧,倒不如说是有关类似作家本人这样的中产阶级的戏剧,而且该剧几乎反讽了每一个角色所宣称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斯兰德对自己高贵出身的自吹自擂从头到尾都受到无情的嘲笑,夏禄开场时的表现不是维持和平而是破坏和谐,相似的是威尔士籍的牧师爱文斯,他赞同去处理另一个外国人——法国籍医生卡厄斯,但剧中的大部分角色都是“从外部(如教会或宫廷)获得某种权威”(Greenblatt 2016:1463),侧面反映出伊丽莎白时代阶级问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正如格林布拉特指出那样,莎士比亚是具有双重意识的大师,他既为纹章花钱,又嘲弄这种权利要求的做作虚伪,在嘲笑为纹章自负的人时,也暗自忍受了同样的嘲笑。(Greenblatt 2004:155)
2.阶级冲突
当福斯塔夫出现在伦敦舞台上时,英国的封建主义全盛期已经过去,那些附庸于日益没落的大封建主的封建骑士,开始从他们本阶级中游离出来,有些流落在社会上成为不务正业的游民、浪人,福斯塔夫就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方平2014:205)进一步而言,这是一部有关冲突的戏剧,特别是地位稍低阶层与比其略高地位阶层之间的冲突。正如格拉夫指出的那样,在莎士比亚这部唯一的“英国”喜剧中,培琪和福德两家,斯兰德、夏禄、爱文斯及卡厄斯共同代表了16世纪后英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Grav 2006:218)剧中最主要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以福斯塔夫为代表的贵族和温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但冲突的核心却源于金钱和财产,该剧就是“一部关于财产的戏剧”(French 1981:106-110)。
剧中首先出现的例子是夏禄与福斯塔夫的冲突。斯兰德吹捧舅舅,指出其法官的身份和家族纹章以及对贵族的签名方式的使用。讽刺的是虽然夏禄开口闭口都在讲家世、阶级,指控福斯塔夫不该以上欺下,但实际最关心的却是物质财产,因为福斯塔夫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打了我的佣人,杀了我的鹿,闯进我的屋子里”,从而让他感觉受到了侮辱:“他侮辱了我;真的,他侮辱了我;一句话,他侮辱了我;你们听着,夏禄老爷说,他被人家侮辱了。”(180)尽管我们常会把莎士比亚的温莎作为一个类似于“绿色世界”或世外桃源的地方,但《温》中的鹿并非如阿登森林中的那样是公共资源,反而是私有财产。(Grav 2008:57)夏禄的私人小屋及周围的林地其实是他租赁王室的林地,因此在他眼中福斯塔夫就是强盗。可见福斯塔夫被构建为一个对温莎构成道德和经济威胁的人,正如斯兰德随后控告福斯塔夫及其跟班将他带到酒店里,“把我灌了个醉,偷了我的钱袋。”(181)文·纳迪兹分析了《温》中夏禄和斯兰德这类上流社会人士的社会和经济特权,指出市民的反应体现出“新兴都市中产阶级的自由个人主义”。(Nardizzi 2011:124)为了解决争执,爱文斯牧师提议组建一个由温莎本地代表成立的特别法庭,其中有教会代表爱文斯牧师、中产阶级代表培琪、企业家代表嘉德饭店店主。然而正当他们听取双方所谓“证词”时,被安·培琪、福德大娘和培琪大娘携带酒具的上场打断,培琪随即招呼大家去吃饭喝酒:“来,我们今天烧好一盘滚热的鹿肉馒头,要请诸位尝尝新。来,各位朋友,我希望大家一杯在手,旧怨全忘。”(183)显然这个所谓的“法庭”根本无法解决双方的矛盾,剧中的中产阶级代表培琪以热情好客打发、掩盖了双方的不合,“在此处并不是说他们无法处置约翰爵士,而是吃喝玩乐的享受财富才更吸引他们”。(Grav 2008:57)
剧中的主要情节是福斯塔夫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培琪大娘和福德大娘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冲突的实质和根源还是在于金钱,所谓的“浪漫”“爱情”不过是幌子而已。我们看到福斯塔夫的潦倒和困窘,他向店主哭穷:“尽是坐着吃饭,我一个星期也要花上十镑钱”(188),乃至于“快要穷得鞋子都没有后跟”,因此不得不辞掉自己的跟班(189)。可见其随后的举动都是由经济现实状况导致的,他对福德大娘和培琪大娘的追求完全是出于身无分文的窘境。他把富裕市民主妇视为容易上当的目标,因为在他眼中拥有爵位的自己会成为主妇追慕的对象,充满了阶级优越感。他觉得福德大娘对他“很有几分意思;她跟我讲话的那种口气,她向我卖弄风情的那种姿势,还有她那一瞟一瞟的脉脉含情的眼光,都好像在说,‘我的心是福斯塔夫爵士的’”(189-190),并认定培琪大娘也在向他“眉目传情”“用贪馋的神气把我从上身望到下身,她的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炙我”(190)。由此才写了两份一模一样的情书给两人,这才有了后续的故事。但实际上金钱才是此剧中心情节中的关键,因为温莎的主妇们掌管家庭的经济大权。伴随着英格兰日益增长的新世界贸易,他将主妇们视为可以掠夺的经济殖民地。16世纪90年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对圭亚那和委内瑞拉进行了考察。1596年他回到英国之后的一年,出版了《圭亚那采风》(The Discovery of Guiana)。书中对探险和未知财富的描述在民间激发了活跃的想象力。(MacGregor 2012:10)他把福德大娘比喻为雷利曾经描述过的伟大的金城:“她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并说“她们一个是东印度,一个是西印度,我就在这两地之间开辟我的生财大道。”(190)他化身为殖民者,将性掠夺比作经济掠夺,指派着仆童罗宾给两人分别送去几乎完全相同的情书,“你就像我的一艘快船一样,赶快开到这两座金山的脚下去吧。”(191)可见福斯塔夫勾引两位大娘完全没有任何浪漫因素,这突出了他唯利是图的本性,也让观众中止了道德判断,制造出滑稽的喜剧效果。(Wells 2010:110)
除此之外,剧中还存在着福斯塔夫与福德这位镇上两位中产阶级男性之一间的冲突,实际上两人在冲突之外还具备本质上的一致性,即金钱的绝对力量。为了测试其妻子是否忠贞,福德竟假扮成一位喜欢随便花钱的绅士白罗克,出钱邀请福斯塔夫去追求自己的妻子。他与福斯塔夫的初次见面展示出两个男人讲相同的语言、有相同的逻辑。正如怀特指出,“[福德的]观念与福斯塔夫完全一致,在福斯塔夫看来,女性的性是一种商品,能够用花言巧语买到,也能够转化为钱财。”(White 1991:25)他虚构白罗克对福德大娘的失败追求,吹捧福斯塔夫“是一位教养优良、谈吐风雅、交游广阔的绅士,无论在地位上人品上都是超人一等”(213),随后展示出自己的财力:“我这儿有的是钱,您尽管用吧,把我的钱全用完了都可以”(同上),只要求福斯塔夫将她征服。福斯塔夫如是评论福德:“哼,这个没造化的死乌龟!谁跟这种东西认识?可是我说他“没造化”,真是委屈了他,人家说这个爱吃醋的忘八倒很有钱呢”(215)。正如彼得·格拉夫指出那样,他的话不仅证实了福德的富有,也表达出福德的男性自我构建,即“他的富有建立在物质(他的钱箱是否装满)上而非无形、不可触摸之物(妻子的忠贞)上”。(Grav 2008:60)福德接着讲到:“娶了一个不贞的妻子,真是倒楣!我的床要给他们弄脏了,我的钱要给他们偷了……骂我……魔鬼夜叉……乌龟!忘八!(Cuckold!Wittol!)”(215)。此句的最后福德使用了两个有区别的词,前者为戴绿帽的人,后者指知道妻子不贞但予以容忍的丈夫,他宣称妻子的出轨威胁了其性控制、财富乃至最重要的名声,强调妻子是自己独有、无法假手他人的财产。(Kegl 1994:78)而且福德在最后要求福斯塔夫归还之前白罗克给的钱,认为这种经济伤害更能打击福斯塔夫,表现出经济上的优越感:“现在已经吃过不少苦了,要是再叫您把那笔钱还出来,我想您一定要万分心痛吧?”(278)同时在评论婚姻问题时,他指出:“在恋爱的事情上,都是上天亲自安排好的;金钱可以买田地,娶妻只能靠运气(sold by fate)。”(281)只有财产才可以被买卖,而他却将妻子也视为交易物品,始终将金钱视为至高存在,正如肯尼指出,“[……]动词卖(sold),而不是命运,透露出他的(乃至本剧的)基本价值感。”(Kinney 1993:214)虽然福德由于嫉妒而受到惩罚,但因结尾处中产阶级的团结而回归主流社会,这正说明了“贫穷和道德失范与温莎的集体价值恰好相反”。(Grav 2008:61)
在批评家看来,福斯塔夫的全面失败在于其是带来威胁的外来者,温莎人将他当做“来自其他社会和道德领域的不速之客……对已建立社群秩序的威胁。”(Evans 1997:322)同样,卡米拉·斯赖茨也指出其“所有自然的热情、其对鹿和温莎妇女的企图,凭藉文明的贪婪和骄傲对满足的田园乡村生活构成了一种攻击。”(Slights 1993:155)不管是夏禄控告福斯塔夫,还是福斯塔夫紧盯福德的财富,为钱去追求两位妇人,乃至福德愿意支付金钱成为带绿帽的男人,都表现出福斯塔夫对温莎中产阶级构成的实际威胁和冲击,让我们在矛盾冲突中看到了经济在情节中的主导地位。
3.安·培琪的婚事
剧中另一个冲突集中爆发于安·培琪的婚事这一次要情节上。我们能够发现安在剧中只是一个经济客体,她的婚姻也成为了一种交易,展现出“财富是如何取代等级/爵位在早期现代英格兰作为衡量社会阶层的工具和尺度”。(Grav 2008:62)剧中安·培琪的婚姻后备人选有三人:本地乡绅子弟斯兰德、法国籍医生卡厄斯以及贵族子弟范顿。
首先,第一位人选斯兰德只是一位唯舅舅是从的傻小子。剧中爱文斯、夏禄、斯兰德的对话无疑将安当作了婚姻市场中有利可图的商品。爱文斯提到安是一位“标致的姑娘(pretty virginity)”(178),暗示着她的处女之身,就像完好无损的货物。因为在当时女性的贞洁是无价之宝,贞洁确保了未来丈夫家族的纯洁、继承人的合法性及其家族的名声,因此守护贞洁是头等大事。“一个女人的性荣誉不只是她个人的,首先不是她的;它与一种更为复杂的荣誉计算紧密相连,其中既涉及家族荣誉,也涉及支配该家族的男人的荣誉……整个家族以及对家族负责的男人的荣誉都以保持女儿的童贞为核心”。(King 1991:30)更为重要的是她在年满十七岁后就能获得去世爷爷留下的“七百镑钱,还有金子银子”。当夏禄称赞安“人品倒不错(good gifts)”时,爱文斯则直白说道:“七百镑钱还有其他的妆奁,那还会错吗?”(179)一下就把安无形的美好品德降格为有形的物质财富。(Crane 1997:46)随后夏禄和侄儿在与安的对话中暴露了真实企图:
夏禄:安小姐,我的侄儿很爱您。
斯兰德:对了,正像我爱葛罗斯特郡的无论哪一个女人一样。
夏禄:他愿意像贵妇人一样地供养您。
斯兰德:这是一定的事,不管来的是什么人,尽管身分比我们乡绅人家要低。
夏禄:他愿意在他的财产里划出一百五十镑钱来归在您的名下。(237)
夏禄的遮掩和斯兰德的露白凸显出他们眼中的婚姻本质上就是经济利益,尽管夏禄为安提供了寡妇所得产(jointure),似乎暗示着法官有意愿为保证婚姻的成功担保,若如剧中所言斯兰德每年有300磅收入,则意味着其身家有6,000磅,而根据普通法寡妇有资格获得亡夫至少三分之一财产,由此类推斯兰德的遗孀会每年获得100镑,夏禄的开价显然慷慨。(Craik 2008:168)但这种承诺在《温》创作的时代显然值得怀疑,实际上对寡妇所得产的承认会极为限制其丈夫死后继承财产的多寡。正如西蒙·雷诺兹指出,夏禄“希望既能安全获得遗产和陪嫁,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花费越少越好。通过提供一笔出人意料的大数目,他希望诱使安在结婚前同意寡妇所得产的数额,从而断绝她之后可以放弃这笔收入换取自己嫁妆的机会。”(Reynolds 1996:323)显然夏禄想以一次性付出谋求更多的好处,可见斯兰德及其家族完全不是理想的联姻对象。
第二位候选人是法国医生卡厄斯。此角色笔墨不多,但大龄且脾气暴躁,自始至终专注于财产问题,正如他每次提及安名字时都使用相同的动词:“你不是对我说安-培琪一定会嫁给我的吗?(have Anne Page)”“我要是不娶(have)安-培琪为妻,我就不是个人”“要是我娶(have)不到安-培琪为妻……我就不是个人。”(196)在他眼中,妻子就是一件可以买回家的商品,从而将安物质化,以强化温莎整体的经济思维模式。
有趣的是斯兰德与卡厄斯两人背后各有一位支持者,分别是培琪与培琪大娘。培琪大娘的话充分说明了她和丈夫选婿的立场,斯兰德“虽然有家私,却是一个呆子”,而自己中意的医生“又有钱,他的朋友在宫廷又有势力”,因此只有医生“才配做她的丈夫(have her)”。(260)培琪大娘嫌弃斯兰德是傻瓜,而医生则既有钱财又有势力,是理想的结亲对象,乃至于和卡厄斯一样用了“have”这个动词将女儿和医生扭在一起,幻想着联姻带来的巨大回报。可见她既抵抗着福斯塔夫的贪得无厌,又自觉地遵从福斯塔夫的经济原则。(Grav 2008:64)而培琪的选择则是出于“门当户对”,斯兰德既有钱又听话,正如雷诺兹指出“如果培琪清楚斯兰德会继承鹿苑和夏禄其他所有的财产,这就证明了他看中的是钱。他的家族可以通过联姻成为士绅贵族,他的‘物品’会增加。”(Reynolds 1996:322)而安的话则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有了一年三百镑的收入,顶不上眼的伧夫也就变成俊汉了。”(237)实际上这对夫妇证明了温莎中产阶级的道德已经被金钱所腐蚀,他们对女儿婚事的安排正体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即“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63:40)
最后一位则是范顿。我们可以发现范顿虽出身高贵,但与前两位候选人相比在经济条件上却处于下风且有劣迹在身。在培琪看来,“这位绅士没有家产”,而且爱厮混且“地位太高”,会染指他的财产,如果安和范顿结婚只会是“空身娶了过去”(227)。随后范顿也向安转述了培琪的理由是“门第太高”“家产不够挥霍”“过去行为太放荡”“结交的都是一班胡闹的朋友”,只是把安当作“一注财产而已”(236)。在温莎的中产阶级看来,高贵出生和贵族头衔毫无意义,也就是比破落户多个头衔,让观众回忆起同时代那些败家子贵族。显然福斯塔夫乃至范顿都被视为入不敷出、财务紊乱的贵族。克里斯托弗·克雷就指出,当时的贵族们由于“……日益增长的挥霍消费再加上普遍的通货膨胀,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仅1602至1641年间,37家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中就有14家失去了家产中至少一半的庄园,22家失去了四分之一。(Clay 1984:150,157)所以近代英国贵族择偶观念的最大变化就是经济上的考虑成为第一因素,特别是16-17世纪盛行的嫁妆制,使英国贵族在婚姻中追求财富的倾向越来越强烈。1600年前后,一些贵族面对经济困境,被迫缔结能有效增长财富的婚姻,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许杰明,王云裳2019:256-257)可见培琪夫妇对范顿的提防并非毫无根据,他们担心最终人财两空。
但范顿深谙安才是关键,因此采用不同的策略以达到目标。首先,他极力劝说安“应当自己作主”(236),坦陈自己最初的动机不纯:“我最初来向你求婚的目的,的确是为了你父亲的财产。”(同上)为了消除负面影响,范顿对安甜言蜜语:“自从我认识了你以后,我就觉得你的价值远超过一切的金银财富(gold or sums in sealed bags);我现在除了你美好的本身(the very riches of thyself)以外,再没有别的希求。”(同上)尽管范顿想要强调安无形的价值和重要性,却使用了突出的经济术语来评价安,他并没有将安与“金银财宝”的意象分开,反而在过程中将安商品化,进一步巩固了物质财富观念。(Grav 2008:70)另一方面,范顿通过对快嘴贵嫂和店主进行金钱贿赂获得助力。他先是让桂嫂收下钱,拜托她“说句好话”,随后又赏钱给桂嫂帮忙送“一个戒指”(197,239),让她在安旁边多加美言。接着又许诺嘉德饭店店主“不但赔偿你的全部损失,而且还愿意送给你黄金百镑,作为酬谢”以破坏培琪大娘的阴谋(265),并承诺“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德,而且我马上就会报答你的”(266),正如格拉夫所言,这句话既挪用了传统的效忠宣誓,又将这一仪式降格为一笔交易。(Grav 2008:68)实际上,范顿、桂嫂和店主同样遵循着温莎流行的金钱道德观,他们二人其实也将安当做了货物,正如罗兰德·休伯特指出那样,“快嘴桂嫂对待安就像一件货物,而且是必须得到快速利益回报那种”。(Huebert 1977:147)而怀特也认为“对金钱的需要让他们掩盖或隐瞒了自己的想法……他们所关心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价高者得。”(White 1991:11)剧中只有范顿贿赂了店主,而夏禄和卡厄斯也仅仅口头委托桂嫂说好话。从剧情发展看来两人的助攻是有效的,从这点上讲范顿的策略是成功的。
反观最重要的当事人安,其实她十分清楚三位人选及自身的情况,正如她仿佛玩笑似地回应范顿对她父亲话语的转述,“他说的话也许是对的”(236)。斯蒂芬·厄科韦茨将四开本第三幕第四场中的安视为消极被动、不活跃的角色(Urkowiz 1988:298),但安愿意质疑范顿说明虽然她知道范顿追求也有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却并未因此气馁。露丝·内沃就认为这一含糊的回答表明安能“为自己代言,是独立和喜欢冒险的而不仅仅是装饰物或‘财产’”,从而“成为了喜剧情节的主体,而非客体。”(Nevo 1980:159)实际上剧中的安从未提及对范顿的爱,相比愚蠢的斯兰德和大龄暴躁的法国医生,范顿虽财力略弱,但门第不错且多才多艺,“眼睛里闪耀着青春”(226),是唯一吸引安的追求者。
戏剧的最后范顿财色双收,培琪夫妇骗女儿去教堂成婚的可耻诡计被他利用,他得以带走安并私定终身,他谴责两人并说安“所犯的过失是神圣的,我们虽然欺骗了你们,却不能说是不正当的诡计,更不能说是忤逆不孝,因为她要避免强迫婚姻所造成的无数不幸的日子,只有用这办法。”(280-281)正如彼得·艾瑞克森指出,“范顿最终对神圣爱情的宣告……并未排除经济考虑。他通过否认安的私奔是‘不正当的诡计’以避免安可能失去继承权。”(Erickson 1987:125)最终夫妇二人只有认下此事,显然已认识到在经济斗争中输给了头脑精明的范顿和女儿,而温莎的生活似乎又重新恢复正轨,年轻的夫妇也会继承他们在温莎的财富和地位,可见此剧潜在强调的社会价值就是经济价值。
4.结语
此剧“在某种程度上是莎士比亚最具现实性的喜剧”,而且这是莎士比亚唯一一部确凿的英国场景设置喜剧,我们有理由认为剧中对金钱的态度反映出作者乃至当时社会的财富观念(Evans&Tobin 1997:323;Felheim&Phillip 1981:57)。此剧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潜在的阶级对抗性,特别是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间斗争的三种方式:“第一是中产阶级团结一致战胜了贵族,第二是中产阶级和贵族世界的完美和解,第三是贵族权力藉由平民主义路径得以增强。”(Erickson 1987:124)第一种表述体现在第五幕温莎中产阶级团结起来惩罚和侮辱了徒有贵族头衔的福斯塔夫上,表明中产阶级价值打败了腐朽的宫廷贵族价值。而第二、三种方式都在范顿与安成功的结合上有所展现,我们既可以说两人的婚姻相当于一种妥协,也可以说范顿的成功翻转了中产阶级的胜利。剧中福斯塔夫和范顿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两人在本质上可以说是平行、相似的:(1)贵族出生;(2)需要金钱;(3)因经济因素追求女性;(4)过往经历不堪;(5)通过贿赂的方式达到目的。就像艾瑞克森所说,“这部喜剧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将范顿和福斯塔夫比较和对比。”(ibid.)相似的是乔治·亨特指出本剧“高贵者/诱骗者的角色是双重的,范顿接管了高贵的一面,而福斯塔夫保留了黑暗的一面”。(Hunter 1986:4-5)可见莎士比亚虽在剧中凸显阶级问题与阶级冲突,但范顿与安的婚姻以及惩罚福斯塔夫和治愈福德的结局,让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矛盾得以缓和。一方面是贵族阶级的修正和向下看,另一方面则是中产阶级的改变及向上流动,两者相互吸纳交融,共同构成了新的群体和阶层,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解。此外,本剧也从侧面突出同时代阶级间的经济纠缠和婚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范顿愿意付出真情实感、摒弃过去恶习,他和安的婚姻象征着贵族地位和中产阶级财富的结合,两人的爱情同时也展示出爱情调和阶级及巩固国族的理想视角。
注释:
①《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引文括弧里的英文均出自G.Melchiori编辑的W.Shakespeare.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2000).London&New York:Bloomsb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