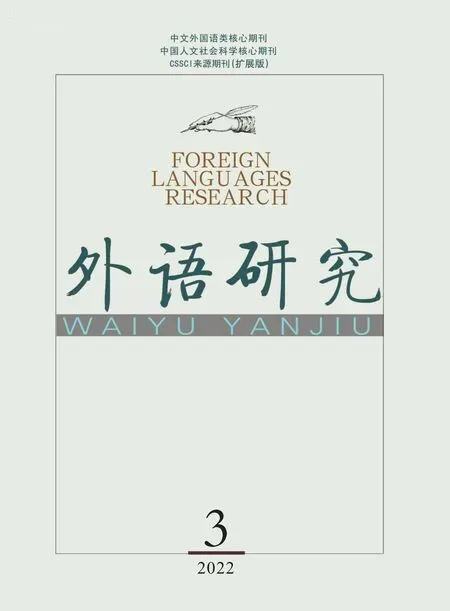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翻译”模式与铭文概念及其对社会翻译学研究的意义*
2022-11-17骆雯雁
骆雯雁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香港特别行政区 999077)
0.引言
目前,在翻译研究领域,国内外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国外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了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介绍,如Buzelin(2005)讨论了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布迪厄社会实践论相结合,用以研究翻译生产的可能性;又如,Chesterman(2006)指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可能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路径。另外,也有不少学者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具体的翻译案例,包括Buzelin(2006,2007),Bogic(2010),Haddadian-Moghaddam(2012)等;近期的案例研究还包括:Munday(2016)聚焦英国诗人Jon Silkin,分析其作为人类学家、编辑以及译者的多重身份如何影响他的诗歌翻译活动;Boll(2016)围绕翻译项目参与者的多种角色,以企鹅出版社在1952-1979年间的西班牙与拉美诗歌英译项目为例,开展叙事轨迹研究;骆雯雁和郑冰寒(Luo&Zheng 2017)则探讨了亚瑟·韦利(Arthur D.Waley)版《西游记》英译本翻译过程中涉及的非人类行动者及其能动作用。同样,在国内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的理论探索与引介,如黄德先(2006)、王岫庐(2019)、邢杰,黎壹平,张其凡(2019);另一类则是理论或概念在具体翻译案例中的应用,如汪宝荣(2014)、张莹(2019)、骆雯雁(2020)、彭诚(2020)等。
总的来说,国内外研究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引介与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翻译的生产过程研究逐渐兴起,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参与者以及他们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孤立的、一成不变的。翻译研究开始将翻译活动放回到具体的、实际的、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中,探索翻译在“自然”的状态下如何进行与发展。然而,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集中于对Bruno Latour思想的讨论,忽视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其他非常重要的学者(如Michel Callon和John Law等),忽略了他们对理论的发展与见解;对一些关键概念(如行动者和翻译ANT等)的理解不够全面抑或不够深入;理论的应用与案例分析常常以描述或是叙事为主,不够严谨、系统,且容易与理论脱节;另外,行动者网络理论属于微观社会学范畴,一般运用于研究个体行为,但在翻译研究中却常被用以分析中观或宏观层面的翻译现象。值得一提的是,骆雯雁的博士论文(Luo 2018)以及专著(Luo 2020)已经开始尝试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弥补以上不足。此外,骆雯雁(2022)对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行动者网络、翻译ANT和黑箱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并分析了它们对于翻译研究的启示。本文中所讨论的“利益翻译ANT模式”与“翻译ANT”的第二个要素“利益赋予”紧密相连,可视为其中一部分,为狭义的“翻译ANT”(Luo 2020;骆雯雁2022);此外,“铭文”的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涉及不多,相关的讨论难免不够透彻。本文会对这两个概念展开较为详尽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概念会为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带来哪些新问题和新视角。
1.Latour的利益翻译ANT模式
在现有的翻译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用“转译”来指代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translation”概念(如王岫庐2019;邢杰等2019)。但是,本文沿用骆雯雁(Luo2018,2020;骆雯雁2022)的命名方式,用“翻译ANT”来指代这个概念。因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翻译ANT”本身包含语言学层面的含义,与翻译学中的“translation”有着天然的联系(骆雯雁2022)。因此,同样的名称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突出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此外,“翻译ANT”名称的上标(ANT)也能提醒研究者这个概念的特殊性。这样,从名称上就能非常直观地既展现两个概念的关联,又标注出了它们的区别。更关键的是,笔者认为,“翻译ANT”概念将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的语言与文化范畴内,翻译研究中对于“翻译”的定义。翻译研究的“翻译”将会借助“翻译ANT”所蕴含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含义,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拓展,翻译研究的内涵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变,翻译的边界也将极大扩张,“翻译”与“翻译ANT”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仅仅强调二者的区别并不利于应用“翻译ANT”推进翻译学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发展。目前国内对于“翻译ANT”(即转译)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行动者为了统一利益与目标而进行的语言转述,二是Callon提出的四个“翻译ANT”要素(如王岫庐2019,邢杰等2019),极少有人提及Latour提出的五个利益翻译ANT模式,这导致目前对于“翻译ANT”的讨论尚不够系统和连贯。骆雯雁(Luo 2018,2020)提出的狭义的和广义的翻译ANT概念很好地梳理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学者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赋予翻译ANT的含义。
Latour(1987,2005)认为,行动者网络的发展,离不开招募(enroll)行动者并对其进行控制(control)。然而,招募与控制之间存在着矛盾:招募的行动者越多,控制起来就越难(Callon 1986;Latour 1987)。要解决这一矛盾,首先需要将散落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行动者们聚集起来;接着,需要调和或转化行动者各自不同的利益,促使行动者能够协同合作,朝同一方向前进,进而实现共同的目标(Latour 1987;Luo 2018,2020)。骆雯雁(Luo 2018,2020)认为,广义的翻译ANT概念包含Callon的“翻译ANT四要素”(“four moments of translation”)(Callon 1986)和Latour的“翻译ANT中心”(“translation centre”/“centre of calculation”)(Latour 1987),它可以用以描述散布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的行动者如何聚集到一起;而狭义的翻译ANT概念,主要指“翻译ANT四要素”中的“利益赋予”(“interessement”)(Callon 1986)以及Latour提出的五个“利益翻译ANT模式”(“modes of translation”)(Latour 1987),它是理解行动者之间利益协调方式的关键(ibid.)。本文聚焦狭义的翻译ANT概念,又因“利益赋予”已被多次引介(详见黄德先2006;王岫庐2019;邢杰等2019;骆雯雁2022),所以,笔者在此主要介绍Latour(1987)提出的五个利益翻译ANT模式。
简单来说,利益翻译ANT就是某些行动者使用策略,将其他行动者的各自利益与大家的共同利益挂钩,从而吸引其他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在利益翻译ANT过程中,各个行动者商议、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达到各方协同维持和发展行动者网络的目的。利益翻译ANT模式是Latour用以概括行动者之间翻译ANT利益的方式,即行动者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引发、阐释或转化各自利益,以便在调整和整合利益关系后,共同协作完成目标。
若以资源调配能力的大小作比较,行动者大致可以分为较弱势行动者(下文简称“弱势者”)和较强势行动者(下文简称“强势者”)(Luo 2020;参见Latour 1987)。利益翻译ANT模式的第一个模式(模式1)中,弱势者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与强势者朝共同方向与目标前进,以获取利益;模式2与模式1正好相反,强势者调整自己原有方向与目标,与弱势者一起,顺着弱势者的目标前进,达成共同目标,获取利益。这两种模式一般出现在行动者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如果有其他办法,行动者有可能会做短暂的调整,即采用迂回(“detour”)(Latour 1987:111-113)的方式,将其他行动者带到自己原来的行动方向上来,继续朝原定的目标前进,这就是模式3展示的利益翻译ANT方式。前三个模式中,行动者皆有明确和固定的目标和利益,模式4则显示了行动者在目标和利益不明确或者仍待商榷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利益翻译ANT方式。模式4中,行动者采取各种策略,包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interpret)其他行动者的目标与利益、创建新的群体或目标等等,达到共同前进、实现共同利益的目的。模式5中,行动者变得不可或缺(“indispensable”)(ibid.:120),所有其他行动者如果想要达到各自的目的,就必须通过他/它(们)这一关。这样,这个/些不可或缺的行动者就构成了行动者网络中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passagepoints”,OPP)。(ibid.:108-121)
2.铭文(inscription)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参与社会活动的要素(此处主要指实体)散布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Latour 1987,2005)。因此,开展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行动者能够对其他实体进行远程控制,或者,这些实体能够在相同的时空中集合起来(Luo 2018,2020)。Law(1986a,1986b)分析了行动者对实体进行远距离操作(long distance control)的问题;而Latour(1986,1987,2005)提出“不变的移动物(immutable mobiles)”的概念,旨在探讨处于不同时空的实体能否、以及如何在某个(同一的)时空内集合。顾名思义,“不可变(immutable)”和“可移动(mobile)”是“不变的移动物”最根本的两个特性。“可移动”是指实体能够从不同的时空中移动到同一时空框架下,为它们聚集、互动、编织社会网络提供可能;“不可变”指的是实体在时空移动的过程中不会被歪曲或不易产生实质性的变化(Latour 1986)。“铭文”具备这两个特性①,属于典型的“不变的移动物”。
铭文通常以文本的形式存在,包括文字文本和图像文本,例如书籍、文件、档案、表格、照片等等(Latour 1986,1987;Latour&Woolgar 1986;Cooren et al.2007);铭文也可以以其他形态存在,标本(“specimen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Latour 1987:70)。铭文通过“铭写机器(inscriptiondevices)”产生。铭写机器是指“能将实质性物质转化为图形或图表的任何器具或特殊的设备,其所产出的图形与图表可供在(实验室)办公室区域的工作人员直接使用”②(Latour&Woolgar 1986:51)。铭写机器“将物质转化为书面文件”(ibid.)。根据以上对铭写机器的定义,Latour&Woolgar紧接着指出“铭文与转化成铭文的物质有着直接相关的联系”(ibid.)。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铭文”带有强烈的社会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涵,与传统文学理论中“文本”的含义有本质上的差别——生产铭文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运用铭写机器,将不同的物质集合、转化,使不同的物质能以二维平面的方式呈现在大众眼前(参见Latour 1987)。
3.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启示:以利益翻译ANT模式和铭文两个概念为例
3.1 狭义的“翻译ANT”与翻译研究
Latour的利益翻译ANT模式运转的前提就是行动者之间的力量不均衡。Latour认为行动者可支配和可利用的资源多少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力量大小(Latour 1987);不仅如此,行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各有不同的目标或利益诉求(Callon 1986;Latour 1987)。因此,在行动者不能独立完成目标、获取利益时,他们会建立新的社会联系(Callon 1986),在这个过程中,协调、整合各自的目标与利益(Callon 1986;Latour 1987);而他们之间力量的差距以及目标和利益的分歧使得组建同盟的过程变得复杂。在(科技)社会学研究领域,Latour(1987)通过对科技生产(包括论文等科研成果产出)的研究,总结了五个利益翻译ANT模式,用以分析科学生产活动中,社会关系的建立。那么,在翻译研究领域,我们是否能运用Latour提出的利益翻译ANT模式,来分析和总结翻译活动中和译本生产时,各个翻译行动者在调节利益、整合目标、达成目的的过程中构建的翻译生产行为模式?这些翻译活动中的翻译ANT模式与科技生产中的翻译ANT模式有什么相同或差异?这些异同对翻译研究会有什么样的意义与启示?
目前为止,利益翻译ANT模式极少被应用于翻译研究。骆雯雁将利益翻译ANT模式作为分析翻译行动者关系变化的模型,以亚瑟·韦利版英译《西游记》为例,讨论了其中各色参与者在译本出版的过程中,在各自利益与目的不一致、力量差异与身份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联系、建立了何种联系,这些联系又如何推进了翻译项目的发展(Luo 2018,2020)。在此基础上,骆雯雁总结了韦利版《西游记》英译出版过程中产生的利益翻译ANT模式,将它们与Latour的五个模式进行对比,并做了扩充(ibid.)。根据骆雯雁的研究来看,Latour的利益翻译ANT模式能用以揭示翻译行动者之间,如何以利益或目标为导向发起行动,进而触发各自身份、角色与关系的变化。换句话说,这五个模式有助于分析翻译网络发展中,由利益或目标的冲突、和解与合并引发的权力关系的构建。讨论这些关系的构建过程能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导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带来新视角与新突破。然而,目前为止,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利益翻译ANT模式为指导的实证性案例研究屈指可数,因此,判断这一模式对翻译研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抑或在何种条件下或作何调整后适用,都需要更多的案例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另外,骆雯雁(ibid.)在Latour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并提出的翻译生产中的利益翻译ANT模式是否具有典型性(即是否在韦利版英译《西游记》以外的翻译活动中也有类似的模式存在)、是否有其他模式的存在、它们与Latour提出的利益翻译ANT模式之异同等研究议题,也需要大量的新的案例研究来支撑。
利益与目标是社会活动产生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社会学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与研究。翻译行动者也无一例外主动或被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翻译活动实现某些利益与目标。这些翻译行动者各自拥有什么样的利益与目的、通过何种方式与途径在翻译生产过程中实现各自的利益与目的、这一过程又对翻译行动者自身、最终的翻译产品(包括译本),乃至翻译作为社会现象本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通过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翻译的各个参与者怎样通过调节各自的、共同的利益与目标,促成翻译这种特殊社会活动的发展。理解翻译行动者复杂交错的利益与目的,是将翻译作为一项实际的、现实的、复杂的、受各种翻译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社会活动加以考量,是将翻译研究在根本上从传统的文本框架中③解放出来的突破口之一。此外,在分析翻译行动者各自的利益与目标如何影响翻译(译者翻译过程、译本生产过程、翻译产品)的基础上,总结翻译中的利益翻译ANT模式,有助于从众多的个案研究中找到普遍模式,总结在利益与目标驱动下,翻译活动发展的共性与规律,这也将为对比翻译生产与其他社会生产模式的异同提供可能性。将翻译与其他社会活动作对比(不仅限于利益翻译ANT模式的对比),能够加深对翻译活动作为一类社会活动的理解,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翻译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比,存在哪些共性与特殊性,最终将翻译确立为一类独特的、重要的社会活动,从而大大扩展翻译的内涵与边界,巩固并提高翻译与翻译研究的地位。另一方面,虽然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与社会活动中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却较少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翻译学领域运用社会学理论开展研究,并将翻译学的研究发现与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进行对比与补充,也将有助于两个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各自的发展。
3.2 翻译中的“文本”
在讨论“黑箱”概念以及“黑箱”对研究翻译文本网络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时,笔者曾指出,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中的文本网络不仅包含以往研究中最常见的、传统翻译学意义上的、两相对应的源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还涉及大量在翻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间文本”和“外围文本”(Luo 2018,2020;骆雯雁2022)。中间文本主要指在译本生产过程中,在源文成为最后的译文成品④前,译文所呈现的不同状态;它们与源文和译文成品直接相关,介于源文与译文成品之间,在不同的翻译生产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态与功能(Luo 2018,2020)。外围文本主要指行动者在翻译生产过程中,为了交流信息、保证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而生产或借助的文本;它们与源文和译文不直接相关,在不同的翻译生产阶段可能以同样的形态存在或发挥相似的功能(ibid.)。⑤
“黑箱”概念表明,行动者之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联结,但这种复杂的网络关系在行动者作为“黑箱”之时(即不被检查或不受质疑之时),是隐于行动者之后、藏于黑箱之中的(Latour 1987;骆雯雁2022)。研究译本的生产过程,分析构成译本(翻译生产)的行动者网络,就是打开译本这个“黑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铭文”这一概念对研究翻译网络中的文本这类既关键又特殊的行动者大有助益。以下,笔者主要围绕与“铭文”概念紧密相关的三个问题,讨论如何运用“铭文”来研究翻译网络中的文本,以及此类研究能给翻译研究带来怎样的研究思路和启示。
第一个问题:铭文指什么?对应到翻译研究中,这个问题就成了:翻译中有可能出现哪些铭文?简单来说,铭文主要是指集中在文本中、以文本形式存在的物质或资源。这些物质或资源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各种事实与实验结果。骆雯雁(Luo 2020)以韦利版英译《西游记》的生产为个案,对翻译中的铭文种类进行了梳理。在她看来,韦利版《西游记》翻译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铭文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译文文本网络、源文文本网络、翻译参与者之间的书信等等(ibid.)。在梳理译本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与译本有直接联系的文本后,骆雯雁发现翻译中存在着复杂的译文文本网络,大致由译稿、译本样稿、译本校对稿、初版译本、不同版本的译本和基于初版译本的再译本组成;它们环环相扣、在翻译生产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功能(ibid.:142-147)。同理,亦能推导出翻译中的源文文本网络(ibid.:147-149)。
第二个问题:铭文是如何产生的?对应到翻译研究中,这个问题就成了:翻译中复杂的、互为关联、结成网络的源文文本⑥、译文文本、翻译参与者之间的书信等等是如何产生的?既然铭文由铭写机器产生,那么翻译中的铭写机器是什么、构成如何,又是怎样运作的呢?需要注意的是,铭文是翻译生产的最主要产品之一,译文生产也是翻译的目的,研究翻译的铭写机器,就是研究翻译中的文本生产机制,属于对翻译生产的运行机制的探索。要回答这第二个问题,需要回到行动者和翻译ANT这两个基本概念上——找出翻译行动者(行动者概念),分析他们用什么方法、借助什么工具、通过什么渠道与其他行动者建立联系,并调动处于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各种资源,最终产出包括译本在内的哪些翻译产品(广义的翻译ANT概念)。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方能总结出翻译生产的机制,找出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铭文,描述、探讨并归纳翻译的铭写机器。
第三,铭文有什么特点?对应到翻译研究中,这个问题就成了:翻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铭文有什么特点?前文已述,铭文最基本的两个特点就是“可移动”和“不可变”;铭文的其他特点(Latour称为“优势”)包括“可合并”(“combinable”)以及“可展示”(“presentable”)等等(Latour 1986:18-20)。那么,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铭文,如信件、源文与译文文本、合同等等,它们身上是如何呈现这些特点的?它们的这些特点为翻译生产提供了什么帮助?如何促进翻译活动的进行?又能为我们认识翻译中的铭文、翻译生产,以及翻译本身带来什么启发?翻译研究在目前为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同样稀缺。骆雯雁曾经以翻译项目参与者的书信为例,以铭文“可移动”和“不可变”的两个基本特性为切入点,从书信铭文推导出韦利英译项目的特点(Luo 2020:154-158)。翻译中种类繁多的铭文及其特点(“优势”)、它们对翻译(产品、过程等)和翻译研究能产生什么样的助力和启发——这些问题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深入讨论。
4.结语
鉴于目前翻译研究领域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利益翻译ANT模式和铭文两个概念的关注较少,本文着重对它们进行了介绍,并分析它们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方法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运用利益翻译ANT模式(属于Luo 2018,2020所指狭义的翻译ANT概念),研究者能够分析和总结翻译活动和译本生产中,各个翻译行动者在调节利益、整合目标的过程中构建的翻译生产行为模式,这有助于我们探索在利益驱动下,翻译活动发展的共性与规律,有利于丰富翻译的内涵、扩展翻译研究的边界。铭文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文本网络,以及各个文本在不同的翻译生产阶段呈现的不同形态、发挥的不同功能及其在翻译行动者网络中的角色与位置;利用翻译铭文的特点,研究者能更好地探讨具体翻译案例的特点及其发展状况。研究者在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索翻译的社会性内涵时,需要根据具体案例的需求,选择适当的概念与观点,构建合理的理论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自洽、方法齐备、自成系统且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翻译研究若想通过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得到发展,必须首先充分、正确且系统地理解理论;其次,根据具体研究案例,选择适合的观点、概念和方法,并在必要时对它们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进行足够数量和富有深度的案例研究。尤其重要的是,在理解与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任何一个概念或研究方法时,研究者都需要牢记整个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知识观(认识论)及其在社会学中的位置,将它们看作是一个有机的、密切联系的整体,不能孤立、片面、静止地看待和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任何一个概念与方法;同时需注意理论的适用范围,避免随意跳脱或穿梭于不同的理论的应用或数据分析层面(例如微观与宏观层面);在尝试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概念与方法与其他理论中的概念与方法相结合以前,应该首先考虑这种结合是否必要,并对两者的兼容性作出合理的判断。笔者希望通过本文与Luo(2018,2020)、骆雯雁(2022),为翻译研究搭建起一个较为系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框架,并提出新的研究问题、研究构想和研究方向,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做好铺垫、抛砖引玉。
注释:
①Latour(1986:18-20)总结并分析了铭文的九个“优势”。其中,前两个优势分别是“可移动”和“不可变”。
②原文:“an inscription device is any item of apparatus or particular configuration of such itemswhich can transformamaterial substance into a figure or diagram which is directly usable by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office space”(Latour&Woolgar 1986:51)。
③笔者认为,在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出现以前,绝大多数翻译研究都是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以传统意义上两相对应的源文和译文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对于翻译中的其他要素的研究(例如译者研究)也几乎没有例外。
④此处,“译文成品”指最终呈现在读者大众面前的译文文本,与“翻译产品/产出”的含义不同(详见Luo 2020)。
⑤笔者在论述“中间文本”与“外围文本”这两类文本时,皆以翻译研究中通常所指的源文文本和译文文本为参照。
⑥此处所指的翻译过程中的源文文本网络不仅仅包括翻译研究中通常所指的源文本。此处源文本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翻译生产阶段呈现不同的形态并发挥不同的功能(Luo 2020:147-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