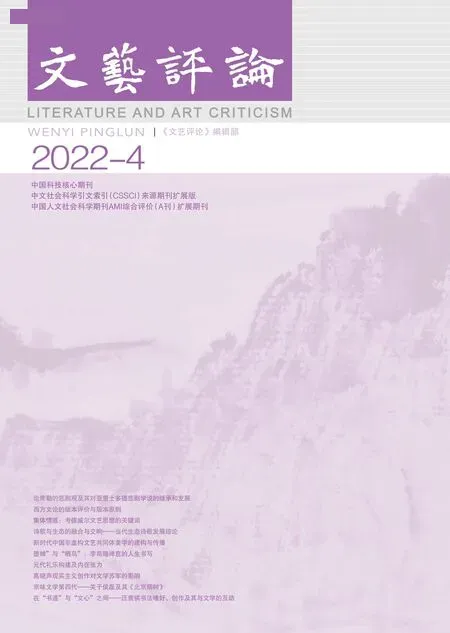李东阳《麓堂诗话》及其诗学理论的建构
2022-11-15耿三琳
○耿三琳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以戍籍居京师。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卒谥文正。所著有《怀麓堂稿》《怀麓堂续稿》《燕对录》《麓堂诗话》等。
诗话是中国传统诗学著作的重要形式之一,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以来的作品来看,其所叙内容及所担当之功能都在不断地发展。以宋人诗话及元人诗法资源的借鉴为基础,明代诗话由单一功能向复杂形态演变,不仅于诗话之质性、功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且已完全突破其成立之初“资闲谈”的狭义边界,涵盖诗歌批评实践和诗学建构的众多方面。就诗话的叙述策略、结撰形式及刊刻传播而言,亦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异,显示出复杂的形态与格局。李东阳《麓堂诗话》是这一变革的引导者。一方面,正是借助李东阳《麓堂诗话》的推介,在宋元至明初较长的时间内都未能成为诗学的主流的严羽诗学,才得以摆脱被肢解、被误读的窘境,被奉为诗歌理论指导的典范[1];另一方面,《麓堂诗话》在撰著宗旨、文本构成、理论体系及诗学范畴等方面,都显示出严羽《沧浪诗话》影响的痕迹,具有明确的理论自觉及较高的理论修养,是明代诗话由记人叙事、探究诗法向综合性理论阐释转变的代表作品。
一、《麓堂诗话》的文本结构
关于《麓堂诗话》的撰著及刊刻时间,钱振民《李东阳年谱》认为:
此卷所收为李东阳谈诗论文的随笔,非一时之作。正德间,辽阳王铎得之,在扬州刊刻行世……王序中称“今少师”,而李东阳于正德元年底升少师,正德七年底致政,因知诗话初刻于正德间。王序自署“辽阳王铎”,陈跋称“辽阳王公始刻于维扬”,知初刻本刊刻于扬州。[2]
其后学者多依钱先生此说。马云骎更考证认为,《麓堂诗话》“初由辽东籍弟子王铎于正德四五年间在扬州刊行”[3]。陈大晓嘉靖刻本跋云“辽阳王公始刻于维扬”[4],无论(万历)《扬州府志》,还是马云骎所引(康熙)《扬州府志》,均载王铎于正德四—五年间任扬州知府,此说似无疑问。然南京图书馆藏梅纯所纂《艺海汇函》抄本一种,其中卷五“说诗类”即收《麓堂诗话》,首有王铎序,梅氏所抄当据王氏刻本。《艺海汇函》梅氏自序末署“正德二年岁次丁卯春二月朔旦,赐同进士出身中都留守司署副留守夏邑梅纯序”,据此可以判断王铎刊刻《麓堂诗话》应在正德元年底至正德二年二月之前,这与王序中“今少师”之说相合,当无可疑。王铎之序,并无刊刻之地的信息,陈大晓所说或因王氏曾为扬州知府而致误。[5]
就生平经历及所具有的政治、文学地位而言,李东阳与欧阳修极为相似。二书均作于晚年,稍不同者是著书时欧阳修已归隐而李东阳尚在位。但细细考察即会发现,与《六一诗话》追求“资闲谈”不同,《麓堂诗话》无论诗学观点还是诗话的文本构成,都受到严羽《沧浪诗话》的影响。
《麓堂诗话》的文本结构,一般认为仍沿用传统诗话独立条目组合的形式,各条目间缺乏显然的联系。[6]但细察文本,《麓堂诗话》在结构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1至第7条:“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古诗与律不同体”“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柳子厚‘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这些条目涉及诗与文、古与律、宋与唐之别及诗歌声律等,属于宏观视角上的诗歌体性阐释。许学夷称:“李宾之《怀麓堂诗话》,首正古、律之体,次贬宋人诗法,而独宗严氏,可谓卓识。”[7]大致是指此7条而言。这里的首、次与正体、贬宋、宗严,揭明了《麓堂诗话》第一部分的逻辑构成,如果将其次序打乱,所表达的观点就会有所变化。尤其“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不仅是辨诗文之别,更意在抬高诗歌在社会教化中的地位,处于李东阳诗学的逻辑顶点,将其置于首条,应该是有着自觉意识的结构安排。另一方面,就此部分每一条的叙述结构来看,除“柳子厚‘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一条为先提出例子,再归结到中晚唐之别,最后引其子兆先之言以证外,其余各条均是先提出核心观点,然后分述论证,是相当严谨的理论阐发之作。
第8条“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属于诗人评论,第9条“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以下至第40条“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所讨论集中在辞意、句法、声韵、诗病等,基本属于诗法一类的内容。
第41条“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以下基本是以人立目(部分以诗类如集句、雪诗等),属于诗人诗作评论。
这样来看,《麓堂诗话》的文本结构包括诗论、诗法、诗评三个部分,将之与《沧浪诗话》相比较,基本与《诗辨》《诗法》《诗评》的性质与地位类似,显示出《沧浪诗话》文本构成对《麓堂诗话》的影响[8]。
二、《麓堂诗话》的撰著旨趣
《麓堂诗话》共137则,以叙事为主的约有二十则,其余均是辨别诗文、古律之体,探讨诗歌风格及评论历代诗人创作得失。即使以叙事为主的条目,也多是对作者及时人诗学交流的记录,与欧阳修《六一诗话》基本是以事见人、以诗见人不同。这些纪事条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在叙事中表达自己的诗学观,如下面一条:
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费殊不信。一日与乔编修维翰观新颁中秘书,予适至,费即掩卷问曰:“请问此何代诗也?”予取读一篇,辄曰:“唐诗也。”又问何人,予曰:“须看两首。”看毕曰:“非白乐天乎?”于是二人大笑,启卷视之,盖《长庆集》,印本不传久矣。(第24-25页)
“诗必有具眼”显然是源自严羽:“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具耳”则是李东阳在此基础上的发挥。与费誾、乔维翰辨诗之事,可以视作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所云“自谓有一日之长,於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的现实实践;或者未必真有其事,仅是李东阳为陈述自己诗学观的一种虚构叙事策略,这在其他诗话中是颇为常见的。
一类所叙为作者及同人、其子兆先关于诗歌创作的讨论。其时习诗、谈诗之风甚盛,如下面一条所叙:
曩时诸翰林斋居,闭户作诗。有僮仆窥之,见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韵嘲之,几致反目。予为解之,有曰“拟向麻池争白战,瘦来鸡肋岂胜拳”,闻者皆笑。(第292页)
又如“夏正夫、刘钦谟同在南曹”条叙二人作诗争胜:“夏每见卷中有刘钦谟诗,则累月不下笔,必求所以胜之者。”他如“兆先尝见予《祀陵》诗”“予尝作《渐台水》诗”“吴文定善苏书,予尝作简戏效其体”等条,均是记作者及友人作诗往还、推敲利病之事。
一类是叙述时人对自己诗作的认同与赞赏,如“方石自视才不过人”条,以叙谢铎“不待辞毕,已跃然而起矣”来表达对自己古乐府的赞赏。又如“彭民望始见予诗”条,彭泽称:“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潘南屏时用深于诗”条,潘辰与谢铎评李东阳古乐府《明妃怨》《新丰行》,二人所见各有不同,或以为“无一字不合作”,或“寻常视之”。此类叙述颇受后人非议,如俞弁《逸老堂诗话》云:
《麓堂诗话》载同官献谀之辞,如西涯专在虚字上用力,如何得到?又云西涯最有功于联句。又云西涯所造,一至此乎?又云莫太泄漏天机。至若与吴文定公和般斑韵,西涯公诗警联,俱载于内,文定和章,不录一句。文定未第时,有赠西涯诗,全篇俱载。古人诗话未必如此。噫!涯翁天下士也,何必亦著此语?虽非自矜,亦未免起后人议论。[9]
《麓堂诗话》自载己诗的条目共15则,引时人之诗14则。以李东阳之地位,确实不必借诗话来获取声誉;其诗文流行,刊刻便利[10],亦不需要借诗话以传。推究原因,除了自宋诗话以来,自载己诗成为一种风气,即使李东阳也不能免俗外,主要还是与李东阳亟欲廓清凡庸、有所树立的心态有关。当时的文学创作处于低潮时期,要想振作诗学,便不能不广布声气。除树立严羽诗学为典范外,以自身或同人诗歌创作的得失作为向他人号召的证据,对于倡导一种新的风气应该是较为有效的策略。
还有一类是在叙事中强调自己诗学主张与时人观念形成对立紧张,且常常强调自己的观点难获知音的孤独,如:
尝有一同官见予辈留心体制,动相可否,辄为反唇曰:“莫太著意。人所见亦不能同,汝谓这般好,渠更说那般好耳。”谢方石闻之,谓予曰:“是恶可与口舌争耶?”(第236页)
又如“宋诗深,却去唐远”条云:“与予论合者,惟张沧洲亨父、谢方石鸣治。”又如“柳子厚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条云:“予谓若止用前四句,则与晚唐何异?然未敢以语人。”又如“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云:“予初欲求声于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成化、弘治间是明代文学思潮转换的关键,李东阳本人在诗学及创作上受到严羽《沧浪诗话》影响,经历了出入宋元向独宗唐诗的转变,李东阳虽然政治与文坛地位崇高,然而要改变一时风气,亦非易事。胡应麟《诗薮》叙此一转变时云:“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俱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故不易也。”[11]因此,《麓堂诗话》中关于诗学活动的叙述多是其本人及同志者开辟文学新域的艰难及自信的记录。李东阳在戮力实践其诗学主张时深感难获知音的孤独,本着这一独任其事的志力,在叙事及论评时的心态、辞气自然就与欧阳修优游林下的境遇及《六一诗话》和缓平易的风格不同。
三、《麓堂诗话》的理论范畴
“范畴”一词译自英文category,是指反映认识对象性质、范围和种类的思维形式,揭示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中合乎规律的联系,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和形态上的稳定性,它的出现并丰富,表明主体认识的深入和成熟,[12]是考察文学理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麓堂诗话》与宋诗话、元人诗法及明初诗话相比,在范畴的使用上更为丰富,也更具有理论体系的层次,尤其“格调”这一范畴的提出及界定,是明诗话乃至明代诗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将《麓堂诗话》所使用的范畴作一区分后,我们发现,李东阳虽然也偶然论及“理”“道”“感兴”一类本体论范畴,如云“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又如“感兴之作,盖以经史事理,播之吟咏,岂可以後世诗家者流例论哉”“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但这并未成为李东阳理论展开的核心。《麓堂诗话》中居于第一层级的是“体制”“格调”“意”“才力”等创作论范畴。李东阳论诗、评诗的核心即为辨体,所谓“予辈留心体制”“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都是这一诗学思想的体现,而其诗学思想的基础亦是源自严羽《沧浪诗话》而有所生发与开拓。
《麓堂诗话》中“体”这一范畴共出现了21次,其涵义除“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指称时代风格,“张式之为都御史,在福建督叔军务,作诗曰:‘除夜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为言者所劾而罢,诗体不可不慎也”一则,指称诗意得体与否外,基本都是作为“体制”、“体裁”来使用的,如:
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第6页)
顾其所自为作,徒得唐人体面。(第27页)
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第55页)
岂惟杨体易识,亦高差难学故耶?(第94页)
国初,人有作九言诗曰:“昨夜西风摆落千林梢,渡头小舟卷入寒塘坳。”贵在浑成劲健,亦备一体。(第158页)
罗明仲尝谓三言亦可为体。(第160页)[13]
一般认为,从明代开始,“格调”这一范畴才被人反复提及,并被抬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而占据古代文学批评核心位置。李东阳是明代较早将“格调”作为核心范畴来使用,并且以其地位使得这一范畴成为“足以标别时代的核心范畴”[14]。严羽诗学的核心之一是辨别体制,自谓“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又云“辩家数如辩苍白,方可言诗”[15]。严羽虽也将音节作为诗歌五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但“苍素”“苍白”云云,都是指称诗歌外在形式而论,李东阳则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从体制、声韵方面对“格调”加以阐释:
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16]
相比严羽的家数、体制的提法,李东阳“格调”的范畴显然具有更高的理论综合性。《麓堂诗话》中论诗、评诗时也大量使用“格”和“调”的范畴,如“格”的范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而其为格,亦渐粗矣”“视格调为深”“格力便别”“韩、苏诗虽俱出入规格”;“调”的范畴:“古涉律调”“尝按古人声调”“学者不先得唐调”“殊乏兴调”“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其为调则有巧存”“譬之琴有商调”“音殊调别”“绰有古调”“其音调起伏顿挫”“视格调为深”“概之唐调”“不失唐诗声调”“略有唐调”。
“意”也是《麓堂诗话》中一个重要范畴,其涵涉主要有作者所欲表达之思想情志、借助客观事物所表现出来的情态意境,以及所体现的总体风貌三个层面。如思想情志层面的范畴:“感发志意”“作诗不可以意徇辞,而须以辞达意”“言意之表”“言有尽而意无穷”“语短而意益长”“语 简 意 切”“真 情 实 意”“命 意 托 兴”“句意皆非时人所到”“见意义之无穷”“更出新意”“时出新意”“以律意相称为善”“诗亦有新意”;情态意境层面的范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意象具足”“圆活生动之意”“恨其意象太著耳”“意 识 超 诣”“殊 乏 意 致”“意 象 超 脱”“无可奈何有馀不尽之意”;总体风貌层面的范畴:“间出古意”“绰有古意”“无复有古意”“少委曲沉著之意”“最得古意”。
李东阳虽然推崇严羽诗学,称“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但亦指出“拘于才力”是其创作之不足。[17]才力是《麓堂诗话》重要的创作论范畴,如“高季迪才力声调”“联句诗,昔人谓才力相当者乃能作”“其辞虽夸,然论其才气,实未有过之者也”“廉夫深于乐府,当所得意,若有神助,但恃才纵笔,多率易而作,不能一一合度”“非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太白天才绝出”等。
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气”常作为本原性范畴来使用,一般指称“基于创作主体生命活力之上的气质个性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18],“气”作为《麓堂诗话》中一个重要的范畴,李东阳则主要用来指称诗人、作品及时代的风格特征,如“不能脱元诗气习”“不脱宋人习气头巾气”“馂馅气”“脂粉气”“台阁气”“山林气”等。此外,也用来指称对诗歌创作有所影响的自然、社会形势因素,如“文章固关气运”“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人囿于气化之中”“气运亦随之而升降”等。
处于《麓堂诗话》范畴体系第二层级的,主要是有关创作技巧及诗歌风格的范畴。有关创作技巧的,如“入妙”“纤巧”“简当精密”“圆活生 动”“卑 陋”“稳”“精 刻”“拙”“巧”“生 硬”“支离”“快直”“委曲”“精炼”“神妙”“老辣”等。有关诗歌风格的范畴,如“浓淡”“深浅”“悠远”“深厚”“古淡”“华靡”“清浊”“黏带”“浅俗”“涩僻”“质”“俚”“简 远”“感 激 悲 壮”“纤 巧”“高 下缓急”“清”“婉”“长”“激”“跌 宕 奇古”“轻 重 清浊高下 缓 急”“质 厚”“平 易”“凄 婉清 切”“和 平富丽”“和 平 温厚”“警 拔”“浑 成 劲 健”“雄 健”“粗率”“深厚”“臃肿”“本色”“豪纵”“捷健”“萎弱”“奇崛”“深”“直 率”“浑 雅 正 大”“野”“俗”“幽寂雅淡”“潇洒超脱”“奇”“怪”“清激悲壮”“劲 健”“警策”“清 丽”“清 绝 高 古”“华 丽”“斩绝”“奇怪”“浏亮”“俊逸”“温润”“激烈”“萧散”“沉著”“惨凄”“忠厚”“雄壮”等。
就概念范畴的使用而言,《麓堂诗话》的诗学体系基本是由诗歌体性阐发为核心,以创作技巧及美学风格体认为辅翼构成,这对于此后明人有关诗学理论阐发的进一步深入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麓堂诗话》的诗歌辨体理论
关于李东阳《麓堂诗话》的理论体系,研究者已有了较多的论述,如李庆立认为《麓堂诗话》“诸条目之宗旨大都指向诗文辨体、诗歌音律、诗歌真情诗歌基本问题,而这几个基本问题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于是一个潜在的诗学体系便依稀浮现在我们面前”[19],并以此为基础对李东阳的诗学体系作了细致的辨析。这一构架的概括与考察的细致,无疑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在具体的操作上,也存在着分类不够周密及部分条目性质的判断上不甚恰切的问题。如李东阳辨体理论的两个核心乃是体制、声律,即所谓“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麓堂诗话》亦称其“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而李教授将李东阳诗歌辨体理论从大的方面分为“诗歌与其他文体和艺术之别”与“诗歌内部诸样式之别”,虽然又以“诗歌音律是其贯串的主线”为题予以专门讨论,似是置于更高的理论层面,但就揭示李东阳诗学辨体理论的架构而言,不免有所缺失。如诗话第1则,分别归入了两个大类“诗与文之别”和“古诗与近体诗之别”,虽然此则诗话所述内容复杂,但仍应该根据其主要的方面加以归类,综合来看,将之归入第一类即可。
在仔细甄别《麓堂诗话》各条所述内容之后,我们认为,李东阳诗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辨别诗歌体制与诗歌声律论两个核心部分,体制论包含本体特征论、诗体论及风格论,声律论包含诗韵、时代及个人风格、诗歌品格。
李东阳对诗歌本体特征的认知首先是通过辨别诗文之别体现出来的。对于诗文之体的不同,李东阳认为在于乐律和真情两个既相独立又密切相关的方面:“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关于乐律,除了如陈文新教授所提出的李东阳“将音乐性视为诗的原生属性和根本属性”[20],其中亦值得注意的是其对真情的重视:“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对于真情的表达,李东阳认为应“善用其情”“不失其正”。以对书写真情的追求为基础,李东阳又能够认识到民间诗歌的价值:“彼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李东阳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杜甫、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倾向,如《麓堂诗话》第14则云:“诗与文不同体,昔人谓杜子美以诗为文,韩退之以文为诗,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长独到之处。近见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为诗,则毫厘千里,终其身而不悟。然则诗果易言哉?”
传统诗学对诗歌体制的区别主要是从形式及内容两个方面展开,如严羽《沧浪诗话》从语言、时代、个体、内容等方面专论诗体,吴讷强调“文辞以体制为先”,将古诗分为四言、五言、七言、歌行四类,近体分为律诗、排律、绝句、联句、杂体五类。《麓堂诗话》区别古诗与律诗的不同,认为:“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这事实上是在有意识地抬高古诗的地位。
李东阳较为推崇的诗歌风格为简远古淡,如:“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又云:“古歌辞贵简远,《大风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弹铗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后世穷技极力,愈多而愈不及。”所谓简远古淡,其实也是对中唐白居易以来俚俗倾向及宋诗议论化的不满:“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乐府歌辞所载《木兰辞》,前首最近古。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刘梦得《竹枝》亦入妙。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涩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以这一诗歌风格认知为基础,李东阳对唐宋元等历代诗歌的时代风格加以辨析,认为历代诗歌各有其风格特征:“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强调时代风气对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因此,在评价金诗时,李东阳认为:“《中州集》所载金诗,皆小家数,不过以片语只字为奇。求其浑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见。元诗大都胜之。外邦僻处固难以深考。意者土宇有广狭,气运亦随之而升降邪?”李东阳又以柳宗元《渔翁》一诗末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的删存来辨别中晚唐风格的不同,以深、浅来概括宋元诗:“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
李东阳辨体理论的另一核心是诗歌声律。陈文新教授认为:“李东阳对风格的辨析,主要依据声调。一方面,他认为诗文之别主要在声,在于诗歌有声律可资讽咏,另一方面,诗歌风格的区别也经由声律表现出来。”[21]自齐梁沈约、周顒以来,关于近体诗的声律研究主要集中在平仄、押韵、偶对等形式技巧因素方面,《麓堂诗话》虽然也对诗韵、对偶等技巧有所讨论,如云:“诗韵贵稳,韵不稳则不成句。和韵尤难,类失牵强,强之不如勿和。善用韵者,虽和犹其自作;不善用者,虽所自作犹和也。”但李东阳更重视诗歌内在声律韵调的辨析,综合来看,主要体现在音节、声调节奏、品格等方面。
首先,李东阳认为诗歌音节不仅是“平侧短长”,更是自然之声的体现,对前代诗歌的习学,应以讽咏体悟为主,才能千变万化而合于法度。如果“泥古诗之成声,平侧长短,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则不仅“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
其次,李东阳认为诗歌的声调节奏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从而构成不同的风格特征:
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汉以上古诗弗论,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此何故邪?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苟非心领神会,自有所得,虽日提耳而教之,无益也。(第134页)
这里,李东阳将作为规矩的“律”,与规矩运用形成的“调”加以区别,认为诗歌之律法相同,而运用之方不同,反对机械模仿从而丧失个性特征的做法。
第三,李东阳强调音律节奏所体现的诗歌品格。如云:
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祯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第64页)
《宋书·律历志上》引扬雄云:“宫、商、角、徵、羽,谓之五声……声和音谐,是谓五乐。”[22]
五声本是五种不同的音调,无所谓品格高下,但《吕氏春秋》又以角、徵、商、羽分配春、夏、秋、冬,而以宫总四时,潘祯所谓“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当即出自此说。又《礼记·乐记》云:“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则五声实际上被比附以品格之高下。《麓堂诗话》又将诗歌声调分别雅俗,云:“古雅乐不传,俗乐又不足听。今所闻者,惟一派中和乐耳。因忆诗家声韵,纵不能仿佛赓歌之美,亦安得庶几一代之乐也哉!”所谓宫声、雅乐,实即李东阳所认为“必有其一”的“台阁气”这一平和雅正的诗歌风格体派。倡导宫声雅乐,表明就诗学观念的根本而言,李东阳仍是台阁文学的代表,其对于复古的理解与后来李梦阳、何景明所倡导的诗学盛唐应是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