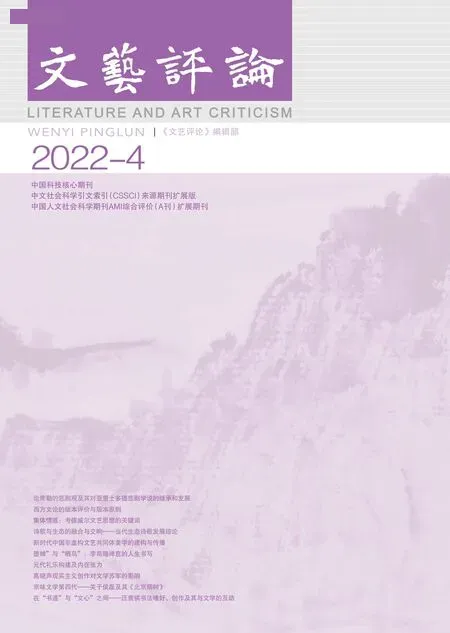高晓声现实主义创作对文学苏军的影响
2022-11-15魏宏瑞蒋恬恬
○魏宏瑞 蒋恬恬
一、引言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中各路流派异彩纷呈,各种写作手法标新立异,域外新的写作技巧和方式也大量涌入,各种新颖独特的文学类别出现并抢占了文化市场,积极参与着对大时代的言说。这对作为传统文学体裁的小说在时代大背景下如何获得对大时代的总体言说的主动权提出了新的考验。作为中国文坛不可忽视的强大一脉的“文学苏军”自然不可拒绝认领这一时代课题的破题任务。如何处理好小说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成为“文学苏军”亟待解决的问题。创造出具有经典气质和存史意义的小说,是破题之道。而对于如何创造这种小说,恩格斯给出他的答案,“一部作品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存就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1]。
江苏文脉源远流长,在各种文脉中,现实主义始终作为主脉为江苏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坚守。“文学苏军”在“探求者”文学社群影响下成长起来,“探求者”社团成员之一的高晓声,其特殊性在于他不仅是“探求者”文学社群的重要成员,而且也是第一代“文学苏军”的领军人物。他极高的文学史地位和伟大的文学成就必然而又应然地影响了“文学苏军”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范小青、赵本夫、叶兆言等人,到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苏童、毕飞宇、韩东等,再到更加年轻的鲁敏、黄孝阳、叶弥等人,高晓声的现实主义创作对他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意义。
二、高晓声与“文学苏军”
1957年,“探求者”文学社团成立于南京。如果按照社团流派的定义来关照这个群体,可以发现这个文学社团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所以我们称之为“文学社群”。仅仅刊发了社团的宣言,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让还未出发的文学“探求”之旅匆匆结束,也让社群成员们陷入了人生低谷,高晓声就是其中的一员。“探求者”们短时间的昙花一现却带来了灿烂绚丽的文坛地位。王尧认为“探求者”事件是“文学苏军”成型的标志。[2]高晓声等人笔耕不辍的20世纪80年代,组成中国当代文学年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所留下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深深地启迪了之后出现的几代作家,为后辈“文学苏军”的勃起蕴蓄了充足的能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文学创作也勃发生机。大量域外文学写作经验的涌入对江苏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创作形式的更新方面,而不涉及精神内核。沈杏培在谈到本土资源与江苏文学关系时提出,除却对国外写作方式技巧的借鉴之外,“50后”的江苏作家更为积极主动地探索本土前辈作家的写作精神内核,“探求者”社团成为他们主要的学习对象。[3]以1984年由梅汝恺、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范小青、赵本夫等作家组成的江苏作协青年创作组为例,这批“50后”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成就至今未衰。作为50年代中期的“探求者”文学社群重要成员的高晓声秉持着纵深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他扎根现实主义所创造的“陈奂生系列”影响深远,他对“人”的关怀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随时代变迁历久弥新,不仅表达了新时期文坛的“现实”诉求,也启示新世纪文学的“写实”追求,并且给予“文学苏军”以积极的影响。
三、典型人物
被文坛放逐了二十多年后,重返的高晓声以“陈奂生”系列作品重获众彩,重申了“典型人物”作为现实主义创作的经典形塑意义,并启发“文学苏军”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大胆开拓创新,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明、有血有肉的具有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闪现着现实主义光彩,读来真实可信,尽管时代变迁,但他们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和陈奂生相呼应,与现代人相暗合。
(一)典型人物的精神困境
说自然,高晓声“陈奂生系列”之所以给读者俯贴于“地”的真实观照的印象,主要原因便是高晓声对人物陈奂生的塑造。而陈奂生之所以成为文学史屹立不倒的典型,就在于其拥有十分典型的性格。丁帆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作家描写的人物要成为文学史长廊中最为突出的“典型人物”形象,不仅要具备鲜活生命力,还要上升到“典型性格”的高度,这样才能进入到对“国民性”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的人物雕塑的艺术殿堂之中。[4]而陈奂生作为人物典型不仅完成了对当时的社会的深刻揭露,而且仍然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之中,同时还会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存在方式。陈奂生所产生的超越时代的审美魅力和精神价值,自然而又应然地源于高晓声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
《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重感冒后被吴书记送进高档宾馆,他的从一开始毫不知情下的胆战心惊到后来得知花了五块钱后认为“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的急剧转变的心态,以及将“五元钱”与“凌驾于乡村世界独一无二的经历”进行等价交换的精神胜利法,让我们看到了新时期农民的精神局限。
高晓声通过塑造陈奂生这一典型人物重树了江苏文脉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大纛,对后来的文学苏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文学苏军重要成员的苏童虽然没有直接提及高晓声对于他的影响,但是2002年他提及“现实”时谈到:“时间上离现在越来越近,目光上也越来越不漂浮,越来越务实。到了我这个年龄,势必会越加脚踏实地直面惨淡的人生。”[5]2003年,他再次谈到:“我可以做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作家,但我要做一个对现实生活有所超越的作家。”[6]由此可见,高晓声创作所坚守的江苏文学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为苏童所承继是不争的事实。
苏童也着力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体现现实主义追求,而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尤为精彩,这早在《米》中就有所体现,主人公五龙是出生于饥荒年代的孤儿,早年吃不饱的阴影,来到瓦匠街后受到“地头蛇”六爷及其下属阿保的欺凌,在冯家米店受尽的白眼与打压,这些长时间的精神世界的压抑,促使五龙形成一个十分难以启齿的癖好:将米塞进女人的下体。这种近乎变态的表现,源于其精神世界的困局,饥荒的阴影促成五龙对米独特的恋物癖,将米等同于一切美好事物,米在他眼里是饱足、安全和幸福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总相信米能够解决:饥饿时随便拿一把米放在嘴里嚼,他就感觉无与伦比的幸福、拿着米去兄弟会“创业”、得了梅毒,他相信米能够拯救他、濒临死亡时,他想到的也是载满一火车皮的米衣锦还乡,这些是其病态精神的体现,五龙对于米的痴狂使他难以突破自身所造的精神牢笼。
苏童的新世纪新作《河岸》在《米》的基础上加深了对典型人物刻画的深度。小说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下展开,库文轩因为一次神秘的调查一下子从革命烈士后代变为阶级异己分子,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场所从岸上转变为船上,从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崇高转变为节衣缩食、社会地位低下。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高度紧张的精神压迫使库文轩变得精神异常,他干出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库文轩精神世界的扭曲和变异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对于烈士后代身份认证近乎疯狂的偏执,二是对于男女关系近乎病态的提防。库文轩执着于自证是革命烈士邓少香的后代,因为这不仅是一种荣誉,背后还暗藏着数不清的特权和地位,而一旦失掉这一层身份后,他的物质世界的虚无便转变为精神世界的变异。在革命烈士后代的身份光环下,库文轩乱搞男女关系不仅无伤大雅,其他女人还争着抢着送上门来,连妻子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一旦这层身份被卸载,之前所有的丑事成了压垮他的巨大雪球,妻子的背叛、人民的仇视、儿子的轻视纷纷涌来。因此他对于坚守自己的烈士后代身份十分执着:十几年来坚持向高层寄信要求重新调查自己的烈士后代身份;因为儿子库东亮看不清邓少香的祠堂而大发雷霆,并怒扇儿子巴掌和罚跪;漫长时间里的每年两次虔诚的对邓少香的水上凭吊;守着屁股上象征着“荣耀”的鱼形胎记,因为胎记的消退而近乎疯狂的歇斯底里,待最后唯一证明自己身份的胎记也黯然褪去,他内心崩溃的洪流冲破堤坝,一发不可收拾,便只能将那象征邓少香英魂的烈士纪念碑绑在身上,与之共沉河底,以此决绝的方式作为最后的倔强坚守。
因为生活作风问题遭到阶级打压的库文轩,对男女关系的严防死守不仅表现为剪掉自己的阴茎,并且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监视着儿子库东亮对异性的一言一行。就连七岁的女孤暂宿船上过夜都成为他臆想中的隐患,儿子库东亮对于异性的正常渴求遭到了他的强烈打压,精神世界也在近乎崩溃的边缘徘徊。
从五龙到库文轩,人物的精神困境是逐渐加深的,所造成的后果也更为震撼人心,如果说五龙处于精神异变的初期,那库文轩持久的精神世界的虚无与压抑则使他病入膏肓,苏童对于人物精神世界的描摹在高晓声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和加深。
同为文学苏军的毕飞宇似乎也更偏爱于现实主义创作,他所创作的《平原》《玉米》《推拿》等无不是现实主义经典。而在这条创作道路上,高晓声对他的影响可谓明晰而又深远,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高晓声对自己的影响,在南京大学演讲时提出“别忘了,中国还有一个高晓声”。在“第二届扬子江作家周”上,他描述自己眼中的高晓声时认为:高晓声坚守了一个作家的尊严。[7]可见在毕飞宇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高晓声无疑是一盏指路明灯般的存在。
在长篇《平原》中,他继承了高晓声现实主义创作的特色,刻画了一群具有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比如同样是有着精神局限的三丫母亲孔素贞。发现三丫与端方在一起后将解救三丫的希望寄托在“佛”这个虚无的形象之上,遭到三丫的拒绝和反抗后,对三丫进行着更为严酷的精神禁锢,当三丫听从她的建议信了佛,她心中才变得清爽,装满了别样的满足。然而信了佛的三丫,并没有像母亲孔素贞所说的那样去往极乐世界,而是以喝农药误死惨淡收场,空留孔素贞自己的虚妄于无物之阵。孔素贞可否谐音为“控诉着”?毕飞宇以这一人物来控诉时代的弊病。孔素贞对佛的崇拜反衬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境遇,她无法摆脱现实的沉重负担,从而麻痹自我感知现实世界苦痛的神经,企图徜徉在虚幻的精神世界获得永恒的解脱,这种承继于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换了模式而继续存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毕飞宇在《平原》中对此类人物精神方面的病态的刻画比比皆是,下乡知青吴蔓玲与狗的交媾、养猪户“老骆驼”与母猪的交媾,都是人物精神困境的体现。人物内心的空虚通过“性”得以释放。老骆驼缺少与人的沟通,在长期与猪的交往中将自己也同化成了猪。与之类似的是吴蔓玲与狗的交媾,但是吴蔓玲与老骆驼又是不同的,吴蔓玲作为下乡知青又身兼着书记官职,其地位的特殊性使她始终压抑着对端方的性渴望,长久的压抑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喷涌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更为年轻的一代文学苏军以不同于前辈作家的视点体现了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积极关照,比如鲁敏,她的小说《六人晚餐》以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为背景,从晓白一家的生活琐事切入,描写晓白的精神困境。小说中在写到姐姐晓蓝有一次夜晚被性侵时,对于晓白失语的描写很细致。这里晓白短暂的失语症状的出现是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所造成的,这好似陈奂生当年失语症状的现代性回光返照,分析陈奂生的性格可知,长久于陈奂生生存状况中的失语症状,是由特定时代环境造就的,并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气质,相反,他是极为渴望话语权的。但缺粮的尴尬处境和“漏斗户主”的低下社会地位使得他压抑个体深层的自我言说能力,从而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失去话语权,最终导致精神的“沉沦”。晓白的失语是由于他亲眼看到姐姐被一个陌生人侵犯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加深了他的精神顽疾。失语反映了晓白的精神变异的加深,鲁敏将这一过程进行了放大,使读者透过人物的语言变异这一外在探究到人物精神异化这一内在。
(二)典型人物的价值与意义
人物精神世界的疯魔化变异是一种丑的内容。但是这些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精神世界变异的典型人物形象却给文本带来美的效果,这暗合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丑纳入审美领域的思考。
精神异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环境对人的压抑。社会促成人的精神方面的局限性,反之,人的精神面貌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作家们从人物的精神方面切入,对人物精神弊端的刻画能更深刻地揭露社会的顽疾。同理,从精神方面对人物进行研究也就更能掌握社会的现实本质。
对人物精神困境描写颇有成就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通过作品中杰符什金、卡捷琳娜、戈利亚德金等人物的精神变态的描写揭示了俄国的社会现实。大约半个世纪后,在遥远的中国大地上,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一角粉墨登场,其人物精神困境所显现的极大普泛性,使得其后几代人读的时候不免窥见自身的倒影,尽管高晓声已经故去,但是陈奂生的幽灵却一直飘荡在人类社会的上空!其作为典型性格的魅力随时间的流逝更加提升。高晓声对陈奂生精神局限入木三分的刻画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深深影响了文学苏军,使得文学苏军继续在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昂首阔步。文学苏军在描写人物精神困境的过程中,对现实的不合理现象做出及时并深刻的反思、否定和批判,进而肯定和宣扬人的本性。在人物的多变异常中寻求其存在常理与社会的正理是这类作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四、特色方言
语言是人们在对现实世界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人类特有的交流工具,它反映客观世界,是再现现实的符号。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要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类认知及思维的特征,特定的语言常常代表它所对应的特殊现实情境,这体现在地域性写作中最为鲜明的就是方言的书写。新时期文学之初,在现代化的大目标下,普通话成为国家推广的标准语言,方言处于潜在的压抑状态,更不用说方言的自觉运用问题。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高晓声的语言实践依然在不经意间涉及到方言问题。高晓声小说创作对方言的积极实践给“文学苏军”留下了可供无限回味的资源。江苏可分为三个方言区,即江淮方言区、吴方言区和北方方言区。从吴方言区的高晓声、范小青、苏童等,到江淮方言区的叶兆言、毕飞宇等,再到北方方言区的赵本夫,方言入小说成为“文学苏军”现实主义写作的独特思维方式。
(一)方言书写的具体实践
王彬彬提出:欣赏小说有欣赏故事的层次、欣赏思想的层次和欣赏语言的层次这三个由低到高的层次。而一个作家最值得称道的贡献,是语言上的贡献。[8]高晓声方言创作可以作为例证。其小说在语言运用上带有苏南方言特色,“肉痛(心痛)、困觉(睡觉)、适意(舒服)、活络(灵活)”等等。
如《陈奂生上城》中提到陈奂生欲将卖油绳的行当向人们炫耀时,害怕遭到刻薄的人吊他的背筋于是选择不开口。
“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嗳!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9]
“吊背筋”是吴地方言,指讪笑、揭人短、拿别人开涮。陈奂生就是这样一个似乎背上的一根筋被别人吊着的、脚不着地的人。他不但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而且又是处于农民的最底层,身无一技之长,处处被别人低看一等,缺失话语权。从“吊背筋”这短短一个词语我们似乎可以揣测出陈奂生的真实神色面容,甚至推导出其生活处境,机动灵敏的方言将他的困境淋漓尽致地向读者传达了出来,这是方言入小说的成功案例。正如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提出:“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10]如同绘画时的一种写意技巧,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整个画面的意境,只取灵动之意,方言之于小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又如写到陈奂生花了五元钱住招待所后感到肉痛。“肉痛”是吴语词,指心疼。在这里用“肉疼”表达陈奂生花掉五元钱住了一晚高级房间的无比后悔与自责。找不到精神负担排解之处的陈奂生只好重拾阿Q的精神胜利法,将住招待所的钱等同于买药钱的时候,似乎找到破解之法的陈奂生感到无比欣慰和解脱,但是精神、良心的不安反复折磨他,使得他又纠结起来。陈奂生这一心理变化过程被作者灵敏地捕捉并无尽地放大。作者有意通过这一事件揭示城乡价值对立的深刻矛盾,这一矛盾是历史的产物,深刻的社会现实未免太过沉重而不易言说,作者将千斤重转化为绕指柔,通过陈奂生这一小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巧妙地展现出来,而在速写这一小人物时也尽力以最能展现其思维方式的方言轻松出之,使其亲切可观,也使得整个文本行云流水,生动形象。
苏童的吴方言写作与高晓声一脉相承。《河岸》当中吴地方言词语的应用也真实地体现了其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写到库文轩因为个人作风问题及历史问题被打成阶级敌人后主人公库东亮的遭遇时有这段描写:
库文轩是阶级敌人了,他现在算个屁,你是屁的儿子,连屁也不如,你就是个空屁![11]
“空屁”是吴地方言,根据作者在小说中的描写,“空屁”有空的意思,也有屁的意思,两个意思叠加起来,其实比空更虚无,比屁更臭,它成为伴随库东亮一生的绰号,出现在他所出现的小说中的每一处,这个方言词总结出主人公库东亮悲惨而又虚无的一生,其内蕴价值已经超越单纯方言词层面而上升到对小说主旨的披露。从这一方言词中我们细细品味,可以咀嚼出瞬息万变并且无法掌控的生命大背景下的渺小个人失去身份归属后的恍惚,存在与虚无的边界逐渐消解的困顿。
范小青的吴方言实践在《裤裆巷风流记》中最为明显,例如“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这是苏州特有的表述日常生活的方言,意思是“上午茶馆喝茶,下午进浴室洗澡”。又如:张师母气哼哼地说:“现在的小年青,全精刮的不得了,比老娘家还要狗皮倒灶。”“狗皮倒灶”是指人吝啬小气。[12]凡此种种,吴地方言给小说增添了更为活泼灵动的特质。范小青对于苏州方言的书写不仅局限于日常生活用语,同样涉及在人称上。如《身份》中以“老隔年”指老不死的;《瑞云》中出现的“瑞云好婆”,“好婆”在苏州话中指年老妇女。
赵本夫所创造的“地母三部曲”中较多地涉及了方言的写作实践,如《天地月亮地》中“小城人把月亮叫做天地,月亮出来了叫做天地出来了。”用“逢集”表达“赶集”的意思。《黑蚂蚁蓝眼睛》中“一期里”指七日内,“一期外”指多于七日以上。
(二)方言书写的重大价值
文学苏军承继于高晓声的方言写作体现了对江苏地域文化的强调与凸显。他们以方言写作打捞被掩埋的珍贵江苏记忆,编码被同构的独特江苏文脉。何平提出江苏青年一代作家缺乏群体性的审美共同性,这对聚合出有着一致文学精神性的、青年性的“江苏文学”带来挑战。王尧也认为如何在“文学苏军”的视角中,将“散装”的“苏军”聚拢在一起,形成“苏军”论述的历史与逻辑脉络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文学苏军”才有可能成为文学史表述。就解决这一困局的办法而言,“文学苏军”或许可以参考高晓声体现现实主义特色的方言写作实践。方言的运用可带来文本的可分析的地域性、感性与日常性以及某种不可分析只能感受的审美特性。一方面,方言明显的“口语化”特征能满足意识形态直接、通俗的展示要求;另一方面,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被定位在展示地域特色与塑造人物时能够使人物形象活泼、亲切,方言运用有利于典型人物的塑造,而典型人物塑造的目的也是为了宣传、为了向其看齐的整合需要。
五、总结
高晓声立足时代背景,以陈奂生这一典型环境中具有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形象鞭辟入里地阐明了特定时代下人的精神困境。文学苏军承继高晓声,借助现实主义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创作方式,以真诚的写作态度紧跟时代的步伐,为文坛奉献出一批具有典型性格和时代意义的人物形象,努力营造属于“文学苏军”独特的辨识度,这是高晓声的现实主义跨越近乎半世纪的强大余震。
伟大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不仅对当时现实的描摹产生意义,并将仍然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之中,甚至还会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所以陈奂生至今读来魅力不减的原因就在于此处,高晓声的热度到今天仍然高涨的原因也在于此。
而方言运用也有利于典型人物的塑造,早在寻根文学出现时,方言便作为表现地域文化特色的副产品而出现,江苏的新写实小说家以对先锋作家的反拨而步入文坛,他们标榜不加修饰原生态地展现出生活,因而对小说语言也力求回归它的原生态——方言。方言带有真诚的现实正视与严肃的精神审视的特点,方言的真实性在于我们进入小说文本时透过它可以窥探到真实的现实世界。高晓声富有前瞻性的方言实践为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并且影响着文学苏军的方言写作。
当前的大时代背景下,如何创作出具有恒久价值的存史意义的文本从而掌握时代言说的主动权,如何通过写作实践将“散装”的“文学苏军”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一条可供研究的明晰脉络是“文学苏军”所面临的两大时代难题。面对时代的发问,“文学苏军”只能以勇于探索的姿态继续“探求”,而高晓声所展示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在未来的道路上,“文学苏军”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种具有深远传统而又历久弥新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对中国现实生活的披露始终切中要害,这源于其与时俱进性。作为一汪永不枯竭的“泉水”,现实主义是“文学苏军”文学创作自始至终都必须坚定高树的大纛!正如高晓声所言:“有的年轻人说,中国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够用了,要创新。这句话口气好大,如果对我国现实主义传统并不摸底,就轻率地说不够用是不正确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