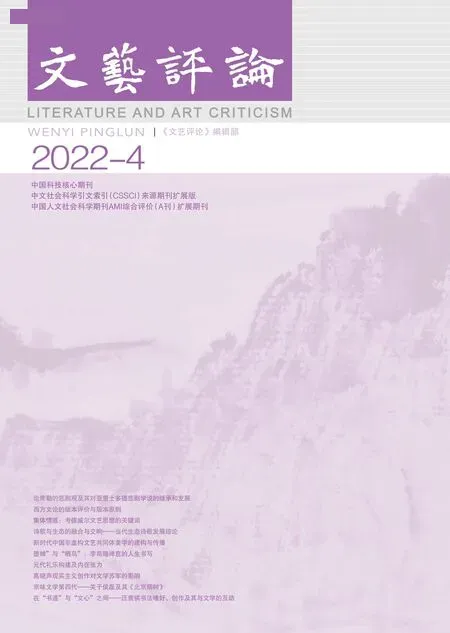在“书道”与“文心”之间
——汪曾祺书法嗜好、创作及其与文学的互动
2022-11-15史婷婷
○史婷婷
当代作家的书法嗜好与创作构成作家研究的重要内容,亦是解读为人为文的独特角度。具体内容方面,包括匾额、题签、条幅、对联、日记、作品手稿、往来书札、篆刻等,含有书学与文学史料的双重价值。在当代文坛,热衷书法收藏或创作的作家不少,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孙犁等。这之中汪曾祺作为个案是特别的:他自小便受到祖父汪嘉勋与父亲汪菊生的言传身教,在书法修养与读帖方面有着较为浓厚的家学渊源,曾从祖父临《圭峰碑》《闲邪公家传》,尤擅绘画、篆刻的父亲则建议汪曾祺临写《张猛龙》;其次,在受教育经历方面,汪曾祺少时曾从乡中名儒韦子廉学,临习《多宝塔》。作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和得意门生,汪曾祺也受到恩师书法创作及书学思想的陶染。散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专门提到沈氏论书法之文,尤其是关于宋四家的认识,是颇有见地的。此外,汪曾祺的书法实践直接对短篇小说、散文、旧体诗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使其作品带有气韵生动、“素朴亲切”(沈从文语)特点;文学理念与创作风格亦促进了书法作品的文学性。研究二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不单具有书学与文学的补缺价值,亦可拓展、深化汪氏史料研究。
一、书法嗜好、创作与交游
与一部分“自学成才”的书家有别,汪曾祺于书法上的嗜好及修养具有浓厚的家学渊源,亦与受教经历密切相关。汪氏曾自述十几岁时即跟随祖父读《论语》,一段时期内每日“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一个暑期,从韦鹤琴学习桐城派古文、写字,临的是《多宝塔》。在父亲的建议下,一个暑假临写《张猛龙》,皆因父亲主张应临习魏碑,方可“掌握好字的骨力和间架”。汪曾祺认为,三部字帖给自己的书法打下底子,“尤其是《张猛龙》”,以至于后期字中尚可看出其余韵。[1]除却临帖,祖父、父亲的书法嗜好与创作,也对汪曾祺书法兴趣的形成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譬如位于高邮的两家祖产万全堂及保全堂,药房过年贴的春联即由祖父自撰,分别书曰“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和“保我黎民,全登寿域”。[2]祖父还曾经奖励给汪曾祺颇为珍贵的“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字《麻姑仙坛》”之初拓本。据汪曾祺回忆,祖父收藏有两件心爱的宝物,“一块蕉叶白大端砚”和海内无二的旧拓《云麾将军碑》。[3]依父亲之说,前者“是夏之蓉的旧物”;擅长绘画的父亲也会刻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4]以上无疑均为汪曾祺书法嗜好的形成和书法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家学基础。
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汪曾祺也受到来自老师的正面影响,《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提及,除了看电影,沈先生还喜欢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5]西南联大时期,汪曾祺还曾陪沈从文一同遛街、欣赏字画,其时昆明市政府对面的大照壁上“写满了一壁字(内容已不记得,大概不外是总理遗训),字有七八寸见方大,用二爨掺一点北魏造像题记笔意,白墙蓝字,是一位无名书家写的,写得实在好”,以至于师徒二人每每路过,都会前去观摩品鉴一番。[6]战时西南后方,大部分师生皆生活困窘,有的不得不变卖衣饰、书籍以改善伙食。或许在跑警报、泡茶馆之余,欣赏字画亦不失为一种文人独有的苦中作乐之法。
在临帖与书法创作方面,除却祖父、父亲、韦鹤琴建议临习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张猛龙》《多宝塔》外,汪曾祺还自述学习书法自描红始,其内容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底子是欧字”[7];年龄尚小之时初学图章,“第一块刻的是长方形的阳文:‘珠湖人’”[8];曾写过《乐毅论》[9]《张迁碑》[10];一度“小楷效法倪云林、石涛”[11];1947-1948年间“用结体微扁的晋人小楷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稿、写信”[12];1948年11月30日曾致信黄裳,“昨睡过晚,今天摹了一天的漆器铭文,颇困顿,遂不复书。颇思得佳字笔为阁下书王维与裴迪秀才书一过也”[13]。对于自己的书法风格,汪氏亦有较明确的认识:“我没有临过瘦金体,偶尔写对联,舒张处忽有瘦金书味道。一个人写过多种碑贴,下笔乃成大杂烩,中年书体较丰腴,晚年渐归枯硬。”[14]事实上,汪曾祺还特别提到当年若未考取西南联大,自己打算考国立艺专,[15]从中亦可见汪曾祺对于书画的嗜好。即便在艰苦的“下放”沙岭子岁月,汪曾祺仍坚持用毛笔写字,且在家书中写明“要‘鸡狼毫’”,因而妻子施松卿经常带着孩子去文具店询问是否有货。如有,则购买若干放置家中以备用。据汪曾祺子女回忆,当年父亲的信件“全是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很黑”。[16]
汪氏的书法嗜好与品位还体现在对于古人及同时代文人书法作品的独特见解上。例如《自得其乐》一文述及自己不喜《曹全碑》,“盖汉碑好处全在筋骨开张,意态从容,《曹全碑》则过于整饬了”[17];《韭菜花》提到“五代杨凝式是由唐代的颜柳欧褚到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我很喜欢他的字。尤其是‘韭花帖’。不但字写得好,文章也极有风致”[18];宋人书法之中“当以蔡京为第一”[19];对于郑板桥《城隍庙碑记》拓本的评价是,“写得很好,虽仍有‘六分半书’笔意,但是是楷书,很工整,不似‘乱石铺阶’那样狂气十足”[20];“《张黑女》北书而有南意”[21]。今人方面,汪曾祺认为赵树理的钢笔字“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毛笔字“极潇洒,而有功力”[22];张充和的书法“结体用笔似晋朝人”[23];端木蕻良“字很清秀,宗法二王”[24];陶光所书小条幅“字较寸楷稍大,写在冷金笺上,气韵流转,无一败笔”[25];等等。若无相当的书法修养与读帖积累,是很难与古为邻,对古今书法作出个性化见解的。
汪曾祺不但有数量颇丰的书法作品存世,参考《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其与黄裳、巫宁坤、宗璞、胡絜青、朱德熙、李政道、邓友梅、聂华苓、安格尔、李欧梵、邵燕祥、张抗抗、王安忆、韩少功、蒋勋、陈若曦、王浩、何立伟、范用、孙郁、李辉、徐城北、黑孩、田原、贺平、麦风、苏北等人皆有翰墨情谊。如曾作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用一张毛边纸写成一个斗方”赠挚友朱德熙,后者很是喜欢这幅字,装裱后挂于书房内[26];1982年“以《成都竹枝词》中《成都小吃》《宜宾流杯池》《离堆》《宿万县》四首抄示朱德熙”[27];1982年出版的朱德熙《语法讲义》,即由汪题签[28];赠昔日老师张道仁、王文英夫妇《敬呈道仁夫子》《敬呈文英老师》二诗;1987年9月与古华一道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赠聂华苓画有秋海棠、草虫的条幅,并自题朱自清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29];给蒋勋手书“春风拂拂灞桥柳,落照依依淡水河”[30];在聂华苓先生安格尔79岁生日之际,赋诗一首以赠之[31];赠宗璞一幅牡丹,题诗“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32],等等。汪曾祺也得赠静融所刻篆字田黄图章一方,是三十多年的唯一名章,“签收邮件汇款全用它”[33]。以上均见证了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同时也是作家、学者等文化交游的重要史料。
概而言之,与家学渊源、后续受教育经历有关,汪曾祺在临帖、读帖、书法鉴赏方面颇有兴趣与心得,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亦留下数量可观的书法材料,其中不仅包括狭义的题签、条幅、对联,还有往来书信、手稿等。此外,与个人性情有涉,汪曾祺亦颇喜以书画作品馈赠友人,在表明文人间翰墨情谊的同时,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承续。或许目前这批材料尚处于文学史边缘地位,但正如有学者所论,其至少存在书法艺术、文学及文献的三重价值,[34]故不可轻易忽视。
二、书法与文学实践的交汇
在文学、戏曲、书法、绘画等方面均颇有见地的汪曾祺认为,“中国各项艺术都与书法相通”[35],狭义的文学创作亦然。更何况,“基于体道的共同目的,诗文书画看起来形态各异,实际上却一定是声气相通、此呼彼应的”[36]。翻阅汪曾祺书法与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书道”与“文心”的互融互构:一方面,书法元素常化于短篇小说、散文中,成为笔下人物、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手书条幅、对联、诗作中亦融涵汪氏对于人道主义、人性、人情的独有见解,从中也可见汪曾祺作为“杂家”所具有的艺术修养与文化底蕴。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创作虽常带有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影子,但无论是早期作品,还是较后期的成熟之作,个人生活经验与经历的化用是一以贯之的。汪曾祺强调“真实”,反对材料堆积,主张写熟悉的人事,[37]体现之一就在于短篇小说的诸多本事与原型:譬如《徙》中汪厚基身上有汪曾祺本人的身影,谈甓渔的原型即祖母的父亲谈人格,[38]高北溟是汪曾祺五年级时的国文老师[39];《受戒》里的菩提庵即祖父、父亲早年在乡下避乱时住过的小庙,[40]赵大娘会剪花样化用了祖母的事例,[41]大英子的原型是曾带过弟弟的保姆,[42]石桥原型是父亲的画友铁桥[43];《珠子灯》孙小姐的原型是二伯母[44];《岁寒三友》靳彝甫的三块田黄即为父亲所有的三块图章[45];《大淖记事》小锡匠差点被保安队打死,后用尿碱救回确有其事[46];《仁慧》里祖母吃的香蕈饺子亦与汪曾祺记忆中的祖母饮食习惯相符;《皮凤三楦房子》中特别提到的对“‘该人’如何如何”[47]的不满即源自汪曾祺本人不愉快的政审经历;《虐猫》故事的部分细节来自汪朝所述之事[48];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美食与同学轶事、个人烟酒爱好常成为笔下内容或情节;等等。
与《红楼梦》中薛宝钗替贾惜春开繁复周到的画器清单类似,由于汪氏的书法嗜好、创作积累,书法元素也常见于其短篇小说、散文之中。孙晓涛、李继凯《论汪曾祺的书法修养对其小说、散文创作的影响》一文就特别论及《鲍团长》《子孙万代》《名士和狐仙》《金冬心》《落魄》《王四海的黄昏》等小说,《读廉价书·旧书摊》《读廉价书·鸡蛋书》《泰山片石·泰山石刻》《泰山拾零·经石峪》等散文受到的书法影响。[49]除却孙、李文所提及的片段,尚至少有以下内容具有明确的书法元素:《受戒》中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50],善因寺走廊砖额上刻着方丈石桥写的大字;《故里杂记》土地祠“灯对子”上书有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51];《徙》中高北溟代谈先生写碑文墓志、寿序挽联;《故乡人》中的大红对子“登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52];《晚饭花》中大福子“请一个擅长书法的医生汪厚基浓墨写了一副对子: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53];《鉴赏家》季匋民“写字写的是章草”[54];《八千岁》里的八舅太爷“请人刻了两方押角图章,一方是阴文:‘戎马书生’,一方是阳文:‘富贵英雄美丈夫’”[55];《戴车匠》里戴车匠店里的对联“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56];《收字纸的老人》老白代印《阴骘文》;《詹大胖子》里的校长张蕴之爱写挽联;《八月骄阳》中顾止庵“字写得不错,欧底赵面”[57];《尴尬》里的洪思迈“会对‘颜柳欧苏’发表一通宏论”[58];《礼俗大全》吕虎臣“用一张白宣纸,裁成四指宽、一尺多长,写了三个扁宋体的字:‘盥洗处’”[59];等等。短篇小说中擅书的石桥、季匋民、汪厚基等人物并非是为会书法而会书法,皆与文学原型本就具有的书法修养或与人物行止相契合;小说里的对联、图章等亦非可有可无的摆设或闲笔,在篇幅短小精悍的短篇里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汪曾祺短篇中的书法元素体现作家本人的书法嗜好与修养,也使得小说呈现鲜明的汪氏风格与趣味,透出今人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古意。
汪家子女提到,大抵由于心境较前开朗,父亲汪曾祺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正经写字画画”[60]。与老师沈从文转行从事文物研究不同,同样是由“现代”进入“当代”的作家,汪曾祺文学创作延续时间较长,对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等文类皆有所涉猎。虽作为“摘帽右派”在政治运动初期受到一定冲击,但与江青对其的“知遇之恩”有关,在历史受难者这一身份方面并不如巴金、王西彦等作家一般充分,以至于新时期初期,汪氏不得不频繁地检讨、“自证清白”。与当时绝大多数获得“平反”的作家相比,心情自然是颇为苦闷且无奈的。在其时文学刊物编辑的支持下,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陆续有短篇小说问世,且获得不俗反响,作家本人也因此得到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的青睐。可以说,外部环境的改变为汪曾祺书画作品的批量问世奠定了基础。作为作家,汪曾祺的书法作品也如文学作品一般具有风俗画、平常心色彩。比如汪曾祺本人十分钟意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不单常引用,“还多次写成大字条幅,送人,留着自己看”[61]。与长于表现宏大历史、社会变革的作家不同,汪曾祺常于小处着眼,在文学创作与书法实践中所透露出的也往往是对普通人事的关注,“须知世上苦人多”一句就颇有人道主义色彩;再如“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62]不唯道出兴之所至,书画自娱,亦体现书者对人间草木的喜爱、在“俗可耐”“故为新”方面的美学追求。在汪曾祺看来,着意描绘草花鱼鸟,恰恰是忠于内心艺术追求的具体表现,不随大流之作方能经受时间的冲刷而愈加耐人寻味——此种艺术坚持本身也是一种“耐烦”(沈从文语)吧;《岁交春一首》“不觉七旬过二矣,何期幸遇岁交春。鸡豚早办须兼味,生菜偏宜簇五辛。薄禄那如饼在手,浮名得似酒盈樽?寻常一饱增惭愧,待看沿河柳色新”[63]道尽汪曾祺价值取向的同时,颇有幸遇岁交春的轻快自得意味;所书“长乐未央”[64]、题画自寿诗《六十七岁自寿》(“尚有三年方七十,看花犹喜眼双明。劳生且读闲居赋,少小曾谙陋室铭。弄笔偶成书四卷,浪游默数路千程。至今仍作儿时梦,自在飞腾遍体轻”[65])亦延续了汪曾祺所具有的自得其乐心态,以及汪氏文学所内蕴的乡土风格。“至今仍作儿时梦”不禁令人联想到《受戒》结尾“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的书法与文学创作正是对记忆中故土世界的理想化构筑,更是对自我内心的感性回归。汪曾祺在手书条幅、题画诗中所透露出的自得其乐心态,亦与笔下明海、小英子、黄巧云、“岁寒三友”、陈四、仁慧等形象贴合,或许这便也是一种“人间送小温”的形式吧。
对于汪曾祺而言,书法实践与文学创作均是表达独特生命体验的渠道和窗口。得益于良好的书法素养,其书法作品与文学作品常常呈现互融互构之态:一方面,书法元素以自然生动、不落斧凿之痕的方式成为文学创作的资源与有机组成,如笔下虚构人物的书法嗜好、修养、创作与交游,场景中常见的对联、条幅、图章等,皆令作品浸润了浓厚的文人气息,兼有与古为邻特点;另一方面,汪氏文风也同样进入书法创作,对自然万物的观照、对人事的温情理解、对草花鱼鸟的钟情,使其书法作品具有一定书学价值,更是可堪细品的文学文本。
三、书学思想与文论的互见
除却书法与文学实践的交汇,书法方面的家学渊源,个人书法嗜好、创作与交游也对汪曾祺书学思想与文论的互动、互见产生直接影响。在涉及文论之先,有必要对汪曾祺性情作一概括。中国自古便有“文人相轻”一说,在汪家子女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中,可见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定位与“傲气”,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汪曾祺并无某种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姿态,或是以看似平等实则带有自上而下教育意味的方式看待普罗大众。早期作品中虽不无嘲讽之意,但总体而言,汪曾祺更关注普遍人性,超脱了传统的认知定势与偏见,对社会风气、人情有着自然主义倾向的理解与体察,其笔下人物陈小手、陈四、陈泥鳅、戴车匠、詹大胖子、保姆小芳、黄开榜、王宝应、辜家女儿、薛大娘、小陈三、侯银匠等皆内蕴人性之美。汪曾祺本人亦崇尚自然及淡然之态,曾自述是一平常、平和之人,“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66]。平日“很爱逛菜市场”,皆因可以切实感受“生之乐趣”[67]。对于“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的偏爱也直接反映于日常笔墨之中,水萝卜、葡萄、野菜等都是汪曾祺笔下可见之物。
上述价值取向也对汪曾祺书学思想与文论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汪曾祺一直认为以笔、墨、颜色抒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68]。比起繁复、曲折、隐晦的表达,汪氏更为崇尚自然、不做作的写字与作文方式。譬如关于当时外界存在的书写篆隶之风,汪氏认为应“首先把楷书、行书写好”。针对鼓励小孩子习篆隶的做法,汪曾祺以为“还是先写楷书为好”[69]。书写不同字体虽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选择有涉,但仍有一个打基础与先后次序的问题。汪曾祺提倡先习楷书、行书,再写篆隶,亦彰显书学思想中的“诚”,这也与其文学创作主张相契合。汪氏曾论及小说思想与技巧的关系问题,认为小说最关键的是思想——即“对生活的看法、感受和对生活的思索”[70]。技巧固然紧要,但“修辞立其诚”[71]。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现代小说通过译介的方式被一批大陆作家所了解、模仿,继而在文学编辑的策划、助力下出现“先锋”等浪潮。小说家过分看重技巧,却削弱了对于思想的关注。当文本更多地服务于炫技目的,反而会对审美形成负面作用。当然,这并非指向技巧无足轻重,而是技巧应服务于思想、与思想有机结合。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自然也有所谓的技巧——如忆及沈从文曾教授“要贴到人物来写”[72],但在他看来,对生活的独有看法、见解、感受、思索才是关键所在;否则,如其所言,“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73]。对于《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岁寒三友》《仁慧》《黄油烙饼》等作,读者之所以被感动,其核心即是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人道主义、普遍人性的善意理解与美好向往,这也是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文学价值所在,使得汪曾祺成为难以被简单归类的当代作家,与其他同时代作家有别。
此外,汪曾祺还特别论及对“字品即人品”观点的看法。汪氏认为,该观点虽不无道理,却存简单化之嫌。譬如蔡京、赵子昂、董其昌就因人品欠佳而被书界贬低书法成就,与其书法作品的真正价值存在出入。可见,“用道德标准、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是古已有之的”。汪曾祺进一步认为,应用新观点与新方法研究“书法美学、书法艺术心理学”,倘若以简单化的方式评判,“是有害的”[74]。体现了汪曾祺对于艺术标准的见解——即不应以机械、简单的方式,用道德或政治尺度取代艺术尺度。这一点也可作文学角度的延伸。毕竟,在用政治伦理取代艺术标准的方式生产、塑造文学经典这一点上,汪曾祺是深有感触的。曾作为样板戏创作团队的一员,在特殊时期受到一定保护,但汪曾祺对于会泳所提出、概括的“三突出”“主题先行”原则是有保留意见的,认为其并不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实践证明当时政治统摄下的剧本写作带有形式主义的痼疾。在《“样板戏”谈往》一文中,尽管部分肯定唱腔、音乐等方面的经验,汪曾祺认为样板戏是“中国文艺史上一场噩梦”[75]。由是观之,拔苗助长式的组织化生产弊大于利,书法、文学、戏曲等艺术形式皆有其独立的评判标准。而这,也是特定书法、文学作品得以成为经典或传世之作的要义所在。
在书学思想与文论互见方面,汪曾祺还常以书法论文学,主张作家应懂书法、多看书法作品,特别是行草,有益于“行文的内在气韵”[76]。关于“内在气韵”或曰小说语言的流动性,汪曾祺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一文中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好的书法家写字,不是一个一个的写出来的……他是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一篇一篇地写出来的。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气就是内在的运动。”[77]可见,高明的书法家写字讲究行气、一气贯穿,而非拆字地“写”出来;文学创作亦是如此,高明的小说家作文也应同高明的书法家写字一般,讲究一气呵成,语言具有自成一体的流动性,而非干涩无味的文字拼贴游戏或材料组装工程。在这一点上,汪家子女特别述及,父亲的手稿颇为工整,他通常于构思完整后再动笔写文章,一般没有打草稿的习惯,“一篇东西往往一气呵成”[78],在实例角度体现读帖、写字对汪曾祺文学实践的积极影响。事实上,汪曾祺本人的文学创作亦在整体风格方面呈现气韵生动的特点,读来自有韵律,而无明显的艰涩凝滞之感。或许对于“一气呵成”的偏好与坚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汪曾祺对鲁迅、孙犁等作家的作品评价甚高,以及缘何以短篇小说、散文创作为主,而对长篇小说的兴趣则并不大。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特别的,不唯其延续了京派文学传统,在短篇小说、学者散文创作上皆卓有建树,其书法实践亦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承续。与家学渊源、后续受教育经历有关,汪曾祺形成了独有的书法嗜好,对古今书家具有独到见解,于书法创作与交流方面亦留下一批材料。这批史料对于接近汪曾祺的内心世界,研究其人其文有着重要意义。毕竟,文学或文学史维度的汪曾祺仅为一面,作为书家、画家、美食家、杂家的汪曾祺,同样与之一道构成了立体多维的形象。与此同时,书法嗜好及创作、书学思想亦与其文学实践、文论形成互动关系:书法元素——如对联、图章、书法爱好与收藏等,成为小说中的有机组成,手书对联、自寿诗等亦兼具书法与文学的双重价值。除此之外,汪氏还常以书法论文学,提倡以“诚”写字、作文,推崇一气呵成、气韵生动的书法及文法。以上种种,均体现“书道”与“文心”在汪曾祺这一个案上的互融与互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