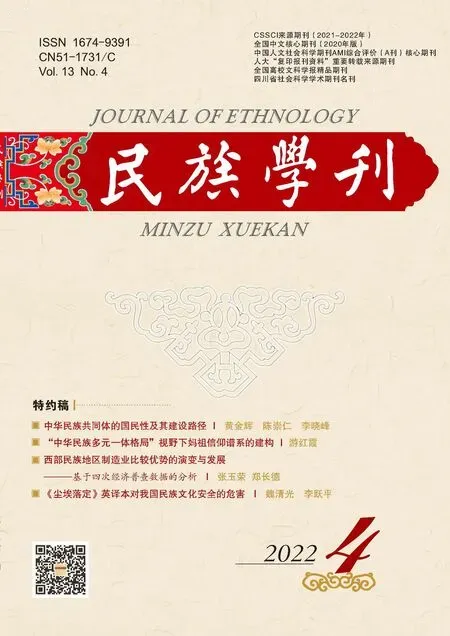《尘埃落定》英译本对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危害
2022-11-12魏清光李跃平
魏清光 李跃平
在当今世界,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翻译,特别是中译外,关乎国家安全,尤其是民族文化安全。翻译所涉及的民族文化安全问题,具有隐蔽性,容易为人所忽视。但国家安全无小事,我们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本文拟以《尘埃落定》英译本为研判个案,剖析译者通过翻译从外部对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危害,并提出针对性的思考和建议。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以其故乡马尔康为地理空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8年。“《尘埃落定》这部小说借独特、新鲜的藏族社会生活题材,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主题。”[1]2000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尘埃落定》又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给出的推荐入选评语是:“《尘埃落定》探索出了在同一种空间演绎多种故事的可能,以优美的文字、丰富的情节表现了康巴藏族的历史。小说具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神秘、神奇的魔幻色彩,在达成了历史与人性的探求后,展示出作家阿来高超的写作能力和烛照历史的卓越才华。它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语言,充满灵动的诗意,对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历史、自然、人性所进行的完美呈现,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尘埃落定》不但是藏族作家的巅峰之作,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之一。”[2]可以说,《尘埃落定》是一部中国文学经典。“于是,否定‘经典’和摧毁‘经典’,肯定‘经典’和捍卫‘经典’也就成为维护和捍卫民族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3]72
《尘埃落定》由美国译者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及其夫人Sylvia Li-chun Lin(林丽君)(以下简称葛、林)翻译为英文。2002年,《尘埃落定》英文版以RedPoppies(《红罂粟》)为书名由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发行,次年又以RedPoppies:ANovelofTibet(《红罂粟——西藏故事》)为书名由Mariner Books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发行。虽然这两个英文版的书名略有不同,但书中内容并无二致。葛、林翻译的《尘埃落定》英文本,是对这部经典小说的摧毁,是对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侵犯。但已有对《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研究,均对此有所忽视。
目前对《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司”“罂粟”等文化意象的处理、叙事视角、书名、题材、语言使用、政治叙写、章节标题的翻译等方面。黄丹青认为葛、林将“土司”译为chieftain“既能削减异质文化间的隔阂又不至于造成文化误读,正是一种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翻译方式。”[4]55王琼、谭源星对比了原文本与译文中的“罂粟”意象,认为“《尘埃落定》中‘罂粟’的文学意象承载着多种永恒的文学主题。英文目标文本在重构文本疆域的时候,做到了很好的对等效果。”[5]106顾毅、李丽从叙事视角的角度研究了《尘埃落定》英译本,认为:“译者葛浩文和林丽君的译本在叙事视角方面成功地再现了原著的叙述特色,将原本冲突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第一人称全知视角恰如其分地再现,实现了与原著在文学和审美价值层面的对等,让英语读者拥有相同的阅读体验。”[6]126蒋霞从题材、叙事角度、语言使用、文化意象等四个方面研究了《尘埃落定》英译文,认为“葛浩文夫妇在翻译小说《尘埃落定》时,最大化地再现了其中的陌生化成分,保留了小说在题材、叙事视角、语言使用、文化意象诸方面的陌生化特征,将神秘的藏族文化意蕴呈现出来,使译文的读者得到与源语读者相近的审美体验。”[7]139黄立通过研究葛浩文对书名的翻译、政治叙写、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处理,认为英译本“传递出葛浩文在翻译中淡化原作历史叙事、模糊原作政治话语、强化原作娱乐功能的翻译思想。”[8]73
综上,已有对《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研究,未涉及翻译有危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内容,即便认为有文化意象的误译,“但瑕不掩瑜,译本总体上很好地翻译出了川西高原土司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文化韵味,让英语读者享受了藏族文化的饕餮大餐,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民族文化。”[9]65然而,事实上,经过葛、林的翻译,《尘埃落定》英译本中的藏族文化已变得面目全非。葛、林肆意歪曲、颠覆《尘埃落定》文本中的藏族文化,破坏中国文学的经典性,危害了我国的民族文化安全。接下来,我们拟通过文本对比予以揭示。《尘埃落定》中文版,我们选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次印刷的版本[10]。该版本也是《尘埃落定》英文版版权页上注明的版本。《尘埃落定》英文版,我们选用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的版本[11]。我们共发现了90余处翻译问题,现选取部分主要问题进行评述。余下问题将在以后进一步讨论。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虽是虚构,但文本中呈现的民族文化是真实的。民族文化是独具特色与标识的传统文化,是人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的最深厚文化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2]民族文化安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在文化交往、交流中,民族文化中固有的信仰、精神、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个性特征、存在样式等应得到尊重、保护、认同,民族文化利益不受损害,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完整的文化主权。否则,则危害到了民族文化安全。加强文明互鉴、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翻译是重要的媒介。但另一方面,又要警惕翻译从外部给我国文化安全、尤其是民族文化安全可能带来的危害。“必须密切关注译者渗透在微观字里行间的文化、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倾向,警惕可能存在的伤及软实力效能的译文。”[13]20通过文本对比,我们发现《尘埃落定》英译本对我国民族文化安全的危害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严重歪曲小说主题
《尘埃落定》以诗意的笔调书写了马尔康藏区土司家族经战争、现代文明的冲击,由兴盛到崩溃毁灭的历程。小说以“尘埃落定”作为标题,既突出了故事主题的深刻内涵和分量,又具有象征意义。“‘尘埃落定’确是一个富于寓意的书名。土司制的寿终正寝,看似由于外力的冲击,恍若‘尘埃落定’般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但细究‘尘埃’如何‘落定’,又似乎不至于这般简单。当社会从一种形态朝另一种形态过渡,当一种文明转化为另一种文明,一些曾经喧嚣与张扬的‘尘埃’随着必然的毁灭与遗忘而迅速‘落定’。而另一些看似细小的‘尘埃’又是那样顽固地漂浮在空中乃至长存于人们的心灵世界。……《尘埃落定》很容易令人想起‘史诗’二字,它毕竟记录了土司制终结的历史,但这样的‘史’更是一种被充分人性化了的心灵史。”[14]49“尘埃落定”这么严肃、厚重、寓意深刻的小说标题,在英译本中被葛、林改译为Red Poppies(《红罂粟》)。红色(red)在英语文化中的联想意义为暴力、血腥、革命、狂欢。罂粟(poppies)本就是制造毒品大麻的原料,其花色为红色。葛、林以red(红色)对poppies(罂粟)加以强化,更是有意凸显血腥、杀戮、毒品、情色、贪欲、犯罪等低俗的文化联想。葛、林对《尘埃落定》小说标题的这种改写,大概是为了迎合西方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不过,“标题通常表明小说的主题。”[15]44标题的改变,自然引导读者对小说主题做出不同的解读。由red poppies(红罂粟)来解读小说主题,自然关联毒品与犯罪、财富与暴力、情色与肉欲、欺诈与谎言等,这与作家阿来的创作主题是天壤之别。针对葛浩文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所做的改写,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作如是评价:“他[葛浩文]根本不是从作家原来的意思和意义来考虑,他只考虑到美国和西方的市场。”[16]73葛、林对《尘埃落定》小说标题的改写,使得小说主题被丑化、矮化,这消解了中国民族文学的经典性。
《尘埃落定》是一部中国文学经典,具备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潜质,但葛、林拙劣的翻译消解了《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经典性,使得英译本已无文学经典的特质。我国有学者将《尘埃落定》英译为The Dust Settles(Tang Li,2016)或Dust Settles Down(谭瑶,2013)或Dust Settled Down(宁芳,2016)①,这些英译,虽然有细微差异,但核心(词)是相同的,我们认为这是不错的英译,基本上做到了“信、达、雅”。为了加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根据《中国国家标准英文版翻译指南》和国标《公共服务领域英文写译规范》的相关内容要求,使用汉语拼音,即:Chen Ai Luo Ding也比英译为Red Poppies恰当。
二、误识民族乐器
《尘埃落定》叙事中书写到的藏族本土乐器有蟒筒和牛角琴。蟒筒为藏族寺院宗教乐队中重要的吹奏乐器。牛角琴是藏族拉弦乐器,音色柔和、悦耳,利于表露情感,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这两种藏族特色乐器均被葛、林误读,失去了民族文化特性。
例1
原文:背上插满了三角形的、圆形的令旗。他从背上抽出一支来,晃动一下,山岗上所有的响器:蟒筒、鼓、唢呐、响铃都响了。[10]134
译文:He was carrying all sorts of triangular and round ritual flags,from which he picked out one to wave,summoning all manner of noisemakers: snakeskin tubes,drums,suonas,and bells.[11](P.143)
葛、林不是以尊重原文和原语文化的态度对待中国民族文学,在原文中遇到不懂的或理解不准确的表达,不去查证或咨询他人,而是靠连蒙带猜,敷衍了事。“蟒筒”(Tibetan tuba)本是藏族传统乐器,结果被葛、林译为snakeskin tubes(蛇皮筒)。蟒筒为藏族本土乐器“筒钦”的俗称,藏语“筒钦”为大号的意思(参见图1、2、3)。虽叫蟒筒,其材质与蛇皮无关。蟒筒一般用白铜、黄铜或红铜制作,号嘴和喇叭口用银子镶边。筒身由上、中、下三节号管衔接而成。上节最细,下节最粗,长度在1米左右至3米左右之间。演奏时,喇叭口着地,或置于架子上,双手扶持蟒筒上节,双唇紧贴号嘴送气发音。蟒筒音色低浑、厚实,是藏传佛教寺院的一种重要乐器,带有“召唤、传播”的意味。藏区每个寺院都有专门吹奏蟒筒的乐手。

图1 蟒筒(藏品)

图2 长短蟒筒

图3 喇嘛吹奏蟒筒
此外,原文是描写门巴喇嘛运用各种响器做法的场景。响器(wind and percussion instruments)是各种吹打乐器的总称。葛、林不懂何为“响器”,又无视原文的上下文语境,仅凭猜测“响器”的字面意思,将之误读为noisemaker(噪音制造者)。经过葛、林的翻译,noisemaker(噪音制造者)和乐器完全无关了。“蟒筒”是一个重要的民族音乐文化符号,但经过葛、林的翻译,该文化符号被破坏,在英语译文中变成一个“制造噪音”的物件。
例2
原文:我和她的缘分,我对她的牵挂,在这一天,就像牛角琴上的丝弦一样,嘣一声,断了。[10]204
译文:Our relationship and my concern for her snapped like the strings of a lute on that day.[11]216
在此例中,葛、林将“牛角琴”误读为lute(鲁特琴)。“牛角琴”(Tibetan fiddle;ox-horn fiddle)为藏族本土乐器“毕旺”的俗称,又称“牛角胡”(参见图4)。琴筒用野牛角或牦牛角粗端绷牛肚子皮或大鱼皮做成,上钻小孔,插入长约2尺许的木琴杆,弓以弯曲藤条和马尾制成,弦用牛脊筋或牛尾搓绞而成。演奏时,将琴放于双膝之上,琴杆贴于左肩,音色婉约,柔而动听。牛角琴为藏族传统拉弦乐器。“鲁特琴”则为欧洲拨弦乐器,琴体由木材制成,琴弦一般采用羊肠线。藏族传统乐器“牛角琴”被译为欧洲传统乐器“鲁特琴”,而不是译为Tibetan fiddle或ox-horn fiddle(牛角琴),藏族乐器符号被“他者化”,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性。

图4 牛角琴
三、窜改民俗文化符号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习俗。这些习俗已成为藏族人民约定俗成的生活模式,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尘埃落定》原文中对藏族民俗的书写,都被葛、林无端窜改,变得谬妄不经。
例3
原文:他燃了柏枝和一些草药,用呛人的烟子熏我,叫人觉得他是在替那些画眉报仇。[10]11
译文:Kindling a spruce branch and some herbs,he smothered my eyes with pungent smoke,as if avenging the thrushes.[11]13
柏树(cypress)的枝叶含有油脂,并有特殊的芳香气味。“点燃柏枝和一些草药,用烟子熏”,是藏族地区的一种传统习俗,称为“煨桑”。“煨桑”起初是藏族祭祀仪式。“煨桑”必不可少的一种材料就是柏枝。“藏族先民的煨桑活动都是在部落外的山头或河岸上举行,煨桑时把扁柏、艾蒿、小叶杜鹃的枝叶堆起来,中间放上五谷杂粮,然后由仪式主持者撒上一点水,点燃后祀神。”[17]72史诗《格萨尔王》中也有关于“煨桑”的记载,如:“二十一骑兵向岭国驰去,丹玛则不慌不忙地从阳山采来冬青,从阴山采来柏枝,从山谷采来香茅草,煨起桑来。随着香烟如白云般袅袅升上天空的时候,丹玛唱起了赞颂战神的歌,准备只身挡住霍尔的兵马。”[18]245后来,“煨桑”逐渐由藏族宗教仪式演变为藏区民间习俗。“煨桑习俗渗透到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医院的病房里,病人亲属一早一晚都用桑烟依次熏床下、被窝、衣服和整个病房。熏过之后,病房里顿时空气清新,病人也要清爽许多,精神也能为之一振。”[17]74原文中,“他”用点燃的柏枝和草药熏“我”,蕴含着藏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和藏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智慧。葛、林将“柏枝”译为spruce branch(云杉枝),而不是译为cypress branch(柏树枝),藏族民俗文化在译文中被随意窜改,藏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在译文中不复存在。
例4
原文:我呶呶嘴,小尔依就苍白着脸爬上了梯子。梯子高的一头就搭在那间阁楼的门口。门口上有着请喇嘛来写下的封门的咒语。[10]84
英文:I gestured with my mouth,and Aryi,his face ashen,climbed a ladder that ended at the attic door,which was protected by an amulet inscribed by a lama.[11]89
“咒语”(incantation)是指“信奉某些宗教之人所念的、认为可以除灾或降灾的语句。”[19]351咒语可以是口头的,也有以符、画充当文字,代替语言,描画、张贴于一些场所,用于辟邪镇妖。葛、林将“咒语”译为amulet(护身符),而不是译为incantation(咒语)。尽管护身符和咒语在功能上有类似,但护身符是佩戴在人身上的。在英语译文中,本来应该佩戴在人身上的护身符竟然贴在阁楼门上,这不符合生活常识,破坏了原文的叙事逻辑。英语读者读到这样的行文,是读不懂的。原文中的正常风俗、生活经验,被葛、林窜改,变得不符合常识、怪诞,这也必然会消解文本的经典性。
四、错用动植物名称
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不同的动植物物种。《尘埃落定》这部小说设定的空间地理背景是阿来的家乡马尔康。小说中书写的动植物都是马尔康地区常见的物种。这是文学真实性的表现。但在《尘埃落定》英译文中,这些动植物名称被译者进行了乾坤大挪移,变得与文本中的生态地理环境完全不相符。
例5
原文:往常,打马经过此地,我每次都看见路边的杉树下有几团漂亮的艳红花朵,今天,它们显得格外漂亮,我才把花指给管家看。[10]129
译文:Every time I’d ridden past here before,I’d seen bright,beautiful flowers beneath roadside pines,but today they looked especially pretty,so I pointed them out to the steward.[11]138
“杉树”(China fir)是马尔康地区主要树种之一,也是中国特有树种,有植物中的“活化石”之称,用途广泛。葛、林可能想让译文靠近英语读者,选择英语读者熟悉的树木名称pines(松树)来取代“杉树”。通过检索“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基本可以证实我们的判断。检索发现,在收词量达十亿的“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中,pine(pines)有11408频次,而China fir(firs)只有3频次。这说明,在英语文化中,China fir(杉树)是一个极为陌生的词语。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以pine(松树)来代替“杉树”固然可以减轻英语读者的陌生感,但却颠覆了原文本书写的真实生态地理环境。
例6
原文:我听到了画眉的叫声,还听到了百灵和绿嘴小山雀的叫声。[10]397
译文:I could hear thrushes,robins,and tiny green-beaked mountain sparrows.[11]423
“百灵”(lark)也叫百灵鸟或沙百灵,为小型鸣禽,叫声响亮,音色委婉动听,主要分布于我国一些草原地区。robin(知更鸟)也是一种小型鸣禽,分布于欧洲、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知更鸟(robin)是一些英美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尘埃落定》英译本中,葛、林用robin(知更鸟)来取代原文本中的“百灵(lark)”,大概是为了迎合西方的文学景观。不过,这种译文会让英语读者产生知更鸟(robin)也分布在中国藏区的错误认知。经过葛、林的翻译,《尘埃落定》文本向外传播的是完全错误的藏区生态地理知识。
五、遗漏礼仪文化
藏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仪的民族。藏族民风纯朴,礼让谦恭、尊老爱幼、诚信无欺是自古传下来的纯良礼俗。应大力向外传播这些优秀的礼仪文化,向外说明,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礼仪之邦,与人为善、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尘埃落定》原文中书写的藏族礼仪,在葛、林译文中都不见了踪影。
例7
原文:下人们上酒上茶时,管家开口了:“都到我们门口了,你们还要在外面住一晚上,少爷很不高兴。”[10]198
译文:As soon as the wine was served,the steward spoke up: “The young master was unhappy that you decided to spend the night outside after reaching our territory.”[11]210
在译文中,“上茶”(serving tea)被省去不译,属于漏译,不仅藏族的茶礼文化被过滤掉,而且阻碍了藏族茶礼文化的向外传播。“藏族是一个极讲究礼仪的民族,有关茶之礼更是不胜枚举。……藏族婚丧嫁娶都用茶,宴请待客更离不了茶和酒。藏族谚语有‘以茶饱肚子,以知识饱脑子’之说。可见藏族嗜茶之普遍,饮茶量之多。一般情况下,藏族不论贫富,一日三餐不离茶,诵经闲谈也饮茶,接待来宾必用茶。”[20]232翻译时,对于原文中的“上茶”,不但不应省去,还应采取补充文化背景信息的方法向外传播藏族的茶礼文化和藏族人民的待客之道。
例8
原文:土司和太太坐上首,哥哥和我分坐两边。[10]111
译文:The chieftain and his wife sat at either side of the room,my brother and I sat on opposite sides...[11]120
“坐上首”(to take the seat of honor)的意思是长辈在家中坐在尊贵的位置上,这表现了藏族人民孝老爱亲的美德。葛、林凭主观猜测,将“坐上首”译为sit at either side of the room(坐在房间的两边),属于错译。藏族人民孝老爱亲的美德在译文中不复存在。
六、扭曲服饰文化
千百年来,藏族人民根据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服饰艺术,展现了独特的审美观。对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已提出重要要求:“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12]但葛、林在翻译藏族服饰时,完全无视中华美学精神,用靠近英语文化的词语来翻译藏族服饰名称,破坏了审美效果。
例9
原文:金子的黄色是属于宗教的。比如佛像脸上的金粉,再比如,喇嘛们在紫红袈裟里面穿着的丝绸衬衫。[10]94
译文:The yellow of gold is associated with religion,like the glittery powder on the Buddha’s face,or the silk chemises the lamas wear under their purple cassocks.[11]99
“袈裟”(Kasāya)原意为“不正色”“杂色”。佛教戒律规定,僧人不许着青、黄、红、黑、白“五正色”。故从色而言,称僧人所着法衣为“袈裟”。葛、林将“袈裟”译为cassock。在英语文化中,cassock是指“a long,usually black,piece of clothing worn by priests(基督教教士穿的黑色长袍)”[21]370。在英语文化中,cassock(长袍)的颜色为黑色,穿着者为基督教教士。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cassock为喇嘛(高僧、僧人)所穿,而且是“紫色的”(purple),这是严重的文化扭曲。
此外,依原文的上下文语境,“丝绸衬衫”这个细节意在说明衬衫的颜色——金黄色。葛、林将“衬衫”(shirt)译为chemise,更是荒谬。因为,在英语文化中,chemise是指“a piece of women’s underwear for the top half of the body;a simple dress that hangs straight from a woman’s shoulders(女性上半身穿的内衣;吊带衫)”[21]410。我们把chemise键入美国购物网站“亚马逊”,点击搜索按钮,该网站页面呈现的是五颜六色的各种女性内衣图片。葛、林将喇嘛穿的衬衫译为女性穿的内衣,是不尊重中国民族文化,又无视原文上下文语境的乱译。
例10
原文:我撩起一件有獭皮镶边的,准备好了在里面看见一张干瘪的面孔,却只看到衣服的缎里子闪着幽暗的光芒。[10]85
译文:Holding up a robe edged with sealskin,I expected to see a gaunt face,but I found nothing but a satin lining that gave off a dark glint.[11]90
以饰物镶边是藏族服装的传统。“精美漂亮的镶边是藏族服饰很诱人的特色。不论冬装夏装,还是男袍女服,在襟、摆、领、袖的边缘,用名贵的水獭皮、虎豹皮,以及用手工在颜色不同的约二寸宽的氆氇或长布条上,以各色丝线精心绣制各种花边,即使在最简朴的牧区光板羊皮袍上也要用五种色彩不同的布条嵌镶成各种花边。”[22]300《尘埃落定》原文中的“獭皮镶边”,体现的是其在藏族服饰文化中的美学价值。葛、林将“獭皮”译为sealskin(海豹皮),而不是译为otter fur。在西方服饰文化中,“海豹皮”用于制作御寒保暖的外套、帽子、靴子,但不用于服装的配饰镶边。换言之,“海豹皮”服装在英语文化中体现的是其功能性价值。加上“海豹皮”不用于配饰镶边,英语读者在英语文本中读到“a robe edged with sealskin”(海豹皮镶边的长袍),会感觉怪异。葛、林的英译不但没有把藏族服饰的独特审美传播出去,反而是对我国民族服饰文化的扭曲。
七、曲解饮食文化
藏族人民生活在高寒地区,特殊的自然、气候条件决定了藏族人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藏族人民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为糌粑和酥油。葛、林对藏族饮食文化不了解,又不认真查证、咨询,在英译文中完全歪曲了这两种藏族食物。
例11
原文:这时,那些在院子里用手磨推糌粑的,用清水淘洗麦子的,给母牛挤二遍奶的,正在擦洗银器的家奴突然曼声歌唱起来。[10]65-66
译文:Singing suddenly erupted among the servants who were pounding glutinous rice into paste,washing grain,milking the cows for the second time,and polishing silver-ware.[11]69
糌粑(tsampas)是藏族特有的一种主食,主要原材料为青稞。用手磨推糌粑,就是把青稞洗干净、晾晒干、炒熟之后磨成粉。食用糌粑时,一般是先将糌粑放在木碗里,然后加入酥油茶,慢慢转动木碗,用手指不断搅匀,直到可以捏成团为止,即可食用。糌粑里亦可放入茶水、奶渣、白糖或青稞酒。还可在糌粑里加入肉、萝卜及其他蔬菜,煮成粥喝。糌粑具有营养丰富、携带方便等特点,是藏族人民最方便的一种食品。葛、林把“用手磨推糌粑”翻译为pounding glutinous rice into paste(把糯米打成糊状),意思是“打糍粑”。打糍粑是中国南方地区传统小吃的做法。打糍粑是以糯米为主要原料,把蒸熟的糯米饭放入石头槽里用木槌用力反复捶打或舂成泥状,并趁热捏成团状或饼状。葛、林对待翻译中国民族文学的态度不端正,对文本中的民族文化不做深入地了解,肆意歪曲藏族饮食文化。这种歪曲的译文还会导致真正了解藏族饮食文化的英语读者对原作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毁损原作者或原作在目的语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例12
原文:先上来的是酥油拌洋芋泥……[10]148
译文:The first course was larded mashed potatoes ...[11]159
酥油(Tibetan butter)是从牛乳或羊乳中提制的奶油制品,是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酥油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不仅有滋补作用,而且能产生很高的热量。喝后既可御寒,又可防止唇裂,是高寒地区的最佳奶制品。在藏族地区,酥油的吃法很多,主要用来打酥油茶,也有放入糌粑、大米、面粉及奶渣中,制成各种美味食品。葛、林将“酥油”译为lard(猪油),而不是译为Tibetan butter(酥油),是不尊重藏族人民生活习惯的错译,向外传播的是错误的藏族饮食文化知识。
八、屏蔽传统技艺
藏族传统技艺是藏族人民历代传承的工艺。这些技艺既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也表现了藏族人民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和创造意识。《尘埃落定》原文中这些烙着民族印记的传统技艺,在葛、林的译文中都被屏蔽了。
例13
原文:下面的科巴寨子上,人们在自家的屋顶上擀毡或鞣制皮子。[10]51
译文:At the Kaba fortresses below,people were weaving wool blankets or tanning leather on their rooftops.[11]54-55
“擀毡”(rolling and making felts;felting)是纯手工作业的藏族传统技艺。“毡”的原料为牛绒或羊毛,制作过程要通过弹毛、铺毛、喷水、喷油、撒豆面、铺毛、卷毡、捆毡连、擀连子、解连子压边、洗毡、整形、晒毡等13道工序。“擀毡”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葛、林将“擀毡”译为weave wool blankets(织毛毯),藏族传统技艺在译文中被屏蔽。“擀毡”与“织毛毯”的工艺完全不同。“擀毡”不需要借助针线但工序复杂;“织毛毯”则是借助针线把部分连接为整体。葛、林这种无视藏族传统技艺的做法阻碍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族传统技艺的传播和传承。
例14
原文:土司还招来许多裁缝,为兵丁赶制统一眼装:黑色的直贡呢长袍,红黄蓝三色的十字花氆氇镶边,红色绸腰带,上佩可以装到枪上的刺刀。[10]102
译文:The chieftain summoned tailors to make uniforms for them: black Venetian robes decorated with red,yellow,and blue cross-stitched edges,and red silk belts on which bayonets could be sheathed.[11]111
“氆氇”(pulu,Tibetan tweed strap)是以羊毛为原材料手工织造的彩条呢,宽20至30厘米不等,是藏族人民制作服装和鞋帽的主要材料。织氆氇时,经纱用本色毛线,纬纱用枣红、深黄、墨绿、黑色毛线,可织出各种图案或花纹。氆氇色彩丰富、鲜亮,立体感强,结实耐用,保暖性好,深受藏族人民喜爱。氆氇不仅仅是藏族人民的传统手工艺制品和技艺,更是汉藏民族团结的象征。“唐代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西藏时,传去先进的纺织工具和生产技术,并以西藏出产的羊毛织成毛织物,称氆氇。”[23]444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葛、林把“氆氇”省去不译,阻碍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向外传播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4]313在译文中,不仅应该把“氆氇”译出来,还应该把有关“氆氇”的背景信息在译本中加以增补,向外讲好中国的民族团结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此外,葛、林将“直贡呢长袍”译为Venetian robes,是错译。Venetian为专名,意为“威尼斯的”。“直贡呢长袍”对应的译名为venetian robes。Venetian与venetian的首字母大小写不同,意思不同。这说明葛、林翻译中国民族文学的态度不认真,敷衍了事。
九、以圣经文化向藏传佛教文化渗透
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全民族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在藏族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葛、林以圣经文化向藏传佛教文化渗透,颠倒是非,这既颠覆了中国文化,又破坏了文本的语义连贯。
例15
原文:我叫了她一声,可她睁开的眼睛里,只有一片眼白,像佛经里说到的事物本质一样空泛。[10]67
译文:I called out to her,but only whiteness showed in her eyes,which were as empty as the essence of things,as described in the Scriptures.[11]70
葛、林将“佛经”(Buddhist sutras)译为the Scriptures。在英语中,the Scriptures就是the Bible(圣经)[21]2300。葛、林企图把西方的圣经文化渗透到《尘埃落定》英译本之中,但这种操作又是在制造破绽百出的译文。因为,“空”是佛教中表示根本立场的概念,在原文中,“佛经”与“事物本质一样空泛”存在语义关联性;将“佛经”改译为the Scriptures(圣经)之后,在译文中“圣经”与as empty as the essence of things(事物本质一样空泛)则不存在语义关联。也就是说,英语读者对as empty as the essence of things,as described in the Scriptures(像圣经里说到的事物本质一样空泛)是读不通的。“中国故事能不能讲好,中国声音能不能传播好,关键要看受众是否愿意听、听得懂。”[25]译文读者“听不懂”,自然就不愿意“听”。
例16
原文:巫师们在行刑人一家居住的小山岗上筑起坛城。[10]133
译文:Our shamans built an altar on a small hill near the executioner’s house.[11]142-143
“坛城”(Mandala)是藏传佛教做法的工具,用以呼唤神灵。“坛城亦称‘曼荼罗’‘道场’,意为本尊佛、菩萨和周围环绕的眷属等聚集的场所。坛城用形象表现佛智与道果功德。形象化的方法是绘图,或用彩色绘于布上、墙壁上,或用彩色细沙堆成,还有用木或金属等制成的立体坛城。”[26]1101葛、林将“坛城”改译为altar。altar是基督教堂里摆放祭品用来祭祀神的祭坛、圣坛。葛、林以基督教文化符号altar(祭坛、圣坛)取代藏传佛教文化符号“坛城”,是对中国藏传佛教文化的颠覆,也破坏了文本的上下文语境。因为在原文中,“筑起坛城”的目的是“做法”,但到了英语译文中,“祭坛、圣坛”(altar)与下文的“做法”场景相冲突。葛、林这种漏洞百出的翻译,不是在助推中国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而是在帮倒忙、消解中国民族文化,摧毁文本的经典性。
十、颠覆制度文化
藏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藏族人民自古就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并与汉族、土族、蒙古族、羌族等兄弟民族进行着密切的交往。在唐朝时期,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分别迎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一步加强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自元朝统一西藏之后,藏区在政治上都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元、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对西部、西南部、南部民族地区管辖的深入,建立起了土司制度。封建王朝对中国西部、西南部、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授予世袭的官职。少数民族首领作为“朝廷命吏”,守土有责。土司制度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民族地区秩序、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土司”一词在《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中共出现1728次,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文化符号,表明藏区土司与当时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葛、林将“土司”译为chieftain。在英语文化中,chieftain是指“the leader of a tribe(部落酋长)”[21]413。葛、林将“土司”译为“部落酋长”(chieftain),是对中国历史上“土司制度”的解构。也就是说,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chieftain只是藏区部落的头领,不体现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已成功举办了10届。从2015年第5届起,研讨会开幕式主席台上的幕布文字为汉英双语,主办方将“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翻译为Tusi system and culture。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翻译,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同时,对单个制度文化符号的解构,还导致顾此失彼,影响整个译文的逻辑连贯性,使得目标语读者读不通译文。如下例:
例17
原文:我的父亲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土司。[10]4
译文:My father was a chieftain ordained by the Chinese emperor to govern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11]6
葛、林将“册封”(confer)译为ordain,妄图以西方的宗教制度解构原文本中的封建集权制度。在英语中,ordain的意思是“to officially make someone a priest or religious leader(正式任命某人为牧师或任圣职)”[21]1816。也就是说,ordain是一个具有基督教文化意蕴的词汇。从文本的可读性角度来看,译者的这种文化置换是失败的。英语读者读到这种译文,获得的感受是:“我父亲”获得了一个圣职,这个圣职的头衔叫chieftain(酋长),是由中国皇帝任命的。这种逻辑荒谬的译文,为英语读者所不能理解和接受。葛浩文在接受访谈时曾说,“我的目标是让目标语读者与市场能够更好地接受译本。”[27]128但是,从《尘埃落定》的英译来看,事实上他不是这么做的,他既没有尊重中国的民族文学和中国民族文化,也没有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感受。
《尘埃落定》原文中多次提到“汉人”“汉地”,指的是汉族人、汉族人聚居地,与藏族人仅是民族身份的不同。按照国家标准,汉族的罗马字母写法为Han。汉族、汉族人翻译为英语时则为the Han ethnic group、the Han people。但是,在《尘埃落定》英译本中,葛、林将“汉人”译为the Han Chinese(汉中国人)、将“汉地”译为the land of the Chinese(中国人的土地)。葛、林在译文中添加Chinese(中国人)这一标示国别身份的词汇,显然是在做国别区隔。加之英语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特点,标示有Chinese的人、物或地方与未标示有Chinese的人、物或地方自然就形成了对立关系。经过葛、林的翻译处理,藏族人在英语译文中被排除在了Chinese(中国人)之外。这种翻译显然是在歪曲事实,人为制造民族分裂,侵犯中国主权。仅举一例:
例18
原文:“你已经背上不好的名声了,你请了汉人来帮你打仗,已经坏了规矩,还想有好的名声吗?”来使说,“现在家里人打架请来了外人帮忙,比较起来,杀一个来使有什么关系呢。”[10]32
译文:“You’ve already tainted your reputation by seeking help from the Han Chinese. You have violated the rules,so how can you expect to preserve your name? Compared to asking an outsider’s help in a family feud,killing a messenger means nothing.”[11]34
此例中的“你”指的是“麦其土司”,“汉人”指的是“汉族人”(the Han people)。但是,经过葛、林的翻译,“汉族人”变成了“汉中国人”(the Han Chinese),语义中心落在了Chinese(中国人)上。加上后文outsider(外人)的语义叠加,会导致英语读者认为文中的“麦其土司”不属于the Chinese(中国人)。这是译者在人为地制造民族分裂、主权分裂。这与原文事实不符,更是危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
思考与结语
建议成立外译中国图书译稿审察委员会,对译稿从国家安全和翻译质量方面进行严格审察,把好海外出版关,铸牢国家文化安全底线,加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尘埃落定》文本中的民族文化特性被美国译者葛浩文及其夫人林丽君肆意歪曲、遮蔽、置换,变得面目全非,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丧失,文本的经典性被摧毁。这种不尊重原著的翻译,表面上表现为译者毫无职业道德,深层次上则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心态在作祟,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度不尊重。这种心态加持下的翻译,不是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是在颠覆中国文化,破坏中国形象,危害了中国的文化安全。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出发,笔者提出以下思考建议:
(一)对有危国家民族文化安全的翻译行为,应及时干预、做出纠正
维护国家民族文化安全,就需要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保持特定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使其在体系上不被解构,在风格上不被篡改,在价值上不被消解。”[28]114如果有外国译者不尊重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随心所欲地改写,严重歪曲中国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生态地理、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我们须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应对译者的错误行径进行干预和纠正,不能任其肆意妄为。我们的干预和纠正,就是对外国译者的回应,就是表明我们的主权。
(二)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能盲目仰仗外国译者
《尘埃落定》是一个好的中国故事,讲述了马尔康地区藏族土司制度的兴衰过程和相关的历史、宗教、文化知识以及人文、自然景观。“小说让人惊叹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它那十分逼真的、具有震撼力的真实感。”[1]但是好的中国故事因为译者葛浩文、林丽君的文化霸权主义心态作祟,中国民族文化被歪曲、故事的真实感被破坏,危害了中国的民族文化安全。阿来本人也坦言:“今天,在这个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世界上,一方面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走向世界,但也要警惕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文学可能造成的伤害。”[29]我们不能贸然下定论,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了,就认为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能盲目仰仗外国译者。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要靠自塑,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借船出海”,更要“造船出海”。中国本土译者应肩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任,向外展示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弘扬民族文化,更好地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维护中国的民族文化安全。
(三)建议建立外译中国图书译稿审察机制
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国从2004年起陆续推出国家资助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等中国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工程。这些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对选题有评审、评估机制,有的还重点支持由海外汉学家、翻译家、作家翻译出版的项目,但目前对译稿缺乏审察机制,翻译质量可能难以得到保证,甚至会从外部危害到我国的民族文化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已做出指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30]为了维护国家的民族文化安全及国家主权安全,保障翻译质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对国家资助的中国图书对外翻译出版工程,建议建立译稿审察机制。建议国家宣传部成立专门的外译中国图书译稿审察委员会,对国家资助的外译图书,在国外出版前,由审察委员会对译稿从国家的民族文化安全、国家主权安全和翻译质量方面进行严格审察,把好海外出版关,铸牢国家的安全底线。
注释:
① 这几位中国学者的《尘埃落定》英译使用的核心词都是“Dust Settle”,寓意深刻且具有“乡土气息”和“中国特色”,译词达意。参见:Tang Li. Alai[C]. Contemporary Chinese Minority Writer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Edited by Wei Qingguang,Salt Lake City: American Academic Press,2016: 140-141;谭瑶. 从边缘文化看福克纳影响下的《尘埃落定》[J]. 外国语文,2013(S1):1-4;宁芳. 《狂人日记》和《尘埃落定》中的狂人和傻子的意象对比[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9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