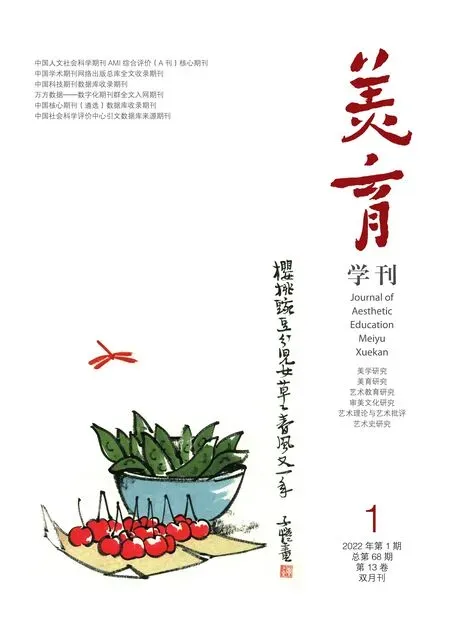张光“闺阁绘画”之近代际遇
2022-11-11丁海涵
丁海涵
(温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女性作者历来占据了中国画史历史叙述的部分篇幅,且向被视为一个特殊群体,对女性画家之记载,往往另辟章节、另造别册,亦可算吾国之特殊国情。《玉台画史》等相关典籍之记载,构成了我们对这一群体的基本历史认知。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风气逐步开化,女性逐渐摆脱家庭限制,走向更开阔的社会舞台,获得了较之以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女性画家在这过程中的身份转变,是其中引人兴味的一个话题。她们往往借助时代变更之利,超越以往“闺阁画家”的性别局限,投身新兴的美术教育、美展、社团甚或艺术运动之中,因之获得全新的人生经验与艺术历练,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介入、影响了绘画史的发展。这其中,永嘉张光堪称典型与优异者,其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共和,先后侨寓粤、京、沪、杭、渝等地,以女性画家的特殊身份参与、见证了近世画史之流变,美术教育之滥觞变迁。本文拟以其生平、艺术活动与从教经历的史实梳理为基础,考察张光此期的绘画创作与画学思想,进而讨论“闺阁绘画”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特殊境遇与独特意义。
一
张光(1879—1970),字德怡,晚号红薇居士、红薇老人,永嘉城区(今温州市)人。其先祖南宋时自福建莆田迁居永嘉,六世祖为明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张璁。阁老后嗣,家族中历来文风颇盛,父兄辈中多有能诗擅文者。张光早慧,幼年时“从兄朗西学诗,同邑汪如渊习缋事,年十二,辄能诗画,及长,学日进”。民国初年曾入当时永嘉卓有影响的诗社慎社,留存至今数册社集中尚可读到她早年几首诗,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女作者之一。早期诗歌以讽咏田园、描写草木为主,诗中有画,如“连朝不雨花如渴,晓汲流泉为灌柯。忽觉满庭春泽足,盈阶细草际阳和”,工丽清新,钱名山直叹为“元气淋漓,造化在手”。终其一生吟咏不辍,书斋因之名为“红薇唫馆”“诗选楼”,辑有《红薇诗草》,蔡元培评价为“淳澹婉美”,可见旨趣与造诣。亦善书,笔下一手褚河南的簪花小楷,劲秀婀娜,与雍容整饬的工笔没骨画风相得益彰。
张光生于晚清,幼时缠足,淹留诗文、娴习书画为旧时书香门第禀赋出众女子之普遍教养,假如早出生百年,终其一生不过成就旧式的闺阁画家。改变其人生际遇首要来自时代风气的转变。晚清时期的温州为沿海开埠较早城市(1876),社会风气开明,以孙诒让、刘绍宽等为代表的开明士绅,倡导新式教育,兴办各类学校。“温州学界开新,始于戊戌以前”;“吾郡学堂之开,始于壬寅。诸邑次第兴举,瑞安先成,而平阳、乐清续之”,近代办新学,温州得风气之先。兴新学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重视女性教育,“妇女无识,则一切教育皆失根源”,女学的兴办亦纳入新教育蓝图。初由设立女子蒙塾始,续设女子学堂。瑞安一邑,晚清已有宣文、毅武、德象等女学的兴办,1907年《浙江教育官报》所载全省普通学堂学生统计表所示,当时“瑞安女学生之数至达九十五人之多,为全省女学之冠”,一时称盛。正是出于这一女子接受新式教育风气之推动,张光的图画教师汪如渊(1867—1923),门下女弟子众多,除张光外,还有鲁文(1868—1940)、蔡笑秋(1885—1974)、鲁藻(1903—1979),皆享画名。而在士绅襄助之下,优异者还可以进一步获得教育机会,蔡笑秋及胞妹蔡墨笑1904年于平阳毓秀女学毕业后,就由孙诒让推荐至天津北洋女子师范深造。鲁文则在孙诒让举荐下任教上海大同女学,且鬻画海上。民国之后,汪门弟子多有在本乡倡办女学的,如马孟容、马公愚昆仲1912年创办“永嘉启明女校”,蔡笑秋创办“平阳县立女子高小”,受聘于“温州女子学馆”。推波助澜下,女子接受美术教育蔚成风气,1934年成立于海上的中国女子书画会,两年后会员发展至140名,永嘉籍人士占15人之多,其中与汪门一系多存或亲或疏的关系。“廿年湖海声名满,争识东瓯女画师”,在温州这一因女学兴盛造就的女画家群体之中,张光堪称先行者,也最为杰出,显然得自这一地方风气之熏陶,对后之来者而言,无疑又具备了典范意义。
更直接改变张光人生轨迹的是她的婚姻。其丈夫章献猷(1867—1944),字味三,号士荃,瑞安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与蔡元培、张元济同年,是陈黻宸的门生弟子。1898年章氏参加会试,偕同乡陈虬等至京师,一度参加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戊戌之后宦居广东十余年,其间张光与章味三结缡。章味三与蔡元培私交甚密,张光很可能因之结识秋瑾。《红薇诗草》存有《秋瑾函促东渡,不果往,诗以答之》:“东国三千里,春风剑笈寒。他山希借镜,怀宝莫轻干。阮子今绳法,祖生独挽澜。月明珠海阔,双泪沁红栏。”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吸收西学方面成为国人“借镜”的重要对象,秋瑾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宣扬女学与女权,兼有考察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的目的,张光在秋瑾“函促东渡”之际曾计划同往,应该出于考察女学之意图,或也为留学东瀛。如随之东渡,个人命运必将重写,然终“不果往”,见得其思想中矛盾与保守的一面。
瑞安办新学、兴女学风气特盛,章氏夫妇浸淫其中,深受影响。章味三戊戌之后追随老师陈黻宸南下,于广东两广方言学堂任教职,张光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广州洁芳女子师范任职监督,均是这些学校滥觞时期的教员与管理者。在广东,章味三还做过嘉应县等地的地方官,张氏随行,得以“遍游琼崖、潮州、嘉应诸州名胜”,心胸眼界得以扩展,画技也得到长足提高。其间张光以岭南花木入画,作《百花图卷》长卷,为平生得意之作,历次展会均予展出,观者往往驻足流连,叹为观止,张大千描述为:“卷长二丈余,写杂花百神,用笔轻倩,布局闲雅,繁枝密叶,冷蕊疏花,各具神态。用水特妙,挹之如清露未干,殆欲袭人襟袂。”章味三持之在友好间遍征题咏,陈师曾、黄节、马叙伦、黄群、刘景晨等人均有赠诗,陈师曾诗赞云:
闺中小试天机手,组织南方草木香。
比翼壮游伴妆镜,鸥波无此好风光。
提携一代丹青价,要使千秋书卷香。
解识筌鱼两无碍,牛背明明生眼光。
四时蜂蝶不到处,分艺南田一瓣香。
婀娜徐滕传骨法,蔡方犹得借晖光。
对张光花卉画作倍加赞誉,而“比翼壮游”确成为后来章味三、张光的生活常态。广东回乡,章氏夫妇暂居永嘉城区虞师里,随行箧带回一批魏源的旧藏典籍,夫妇二人丹黄在手,昕夕弗倦,甚为相得。章味三雅好书画与鉴赏,加之前半生一直陪侍身边的姨甥郑曼青(1902—1975),大致可以构想出张光家庭生活里终日手不释卷、寄情翰墨的风雅情形。
二
回乡暂居时日非常短暂,辛亥后章味三再次北上,一度任初建时的北京大学学监。张光随夫流寓北京,赁居宣南下斜街。宣南在清代为外省士人在京聚居地,光绪十二年(1886)瑞安黄体芳与温籍同乡京官曾在宣武门外教场五条胡同建有温州会馆,这里也成为在京温州士人的聚集地。鼎革之后,文人燕聚酬酢遗风尚存,张光得以与樊樊山、方菊人等名士唱酬,同乡书画家王荣年、刘景晨等亦时相过从。下斜街一带旧设花市,近有崇效寺牡丹、法源寺丁香最闻名,是旧京宫阙重重、花团锦簇之地,花鸟画家寓所近此,不啻如鱼得水。“廿四番风莺燕慵,宣南春老碧重重。一江楚雨欹愁冷,万里嵩云入眼浓。”“春深花气到吾庐,花好何嫌近市居。三径毶毶新树柳,五车杂杂旧藏书。”均可见当时兴味与境况。
张光在京先后任教于私立郁文大学、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北京艺专第一位女教授是1920年始执教于西画科的邵碧芳,才华横溢,可惜两年后早逝,蔡元培曾撰《事略》追悼,之后数年女教员付之阙如。续之,张光1926年始任教艺专,是最早任职北京艺专国画科的女教授之一。至1927年,随着国民政府南迁,北京易名北平,时局巨变,在京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北平艺专国画科一时群贤毕至也成星云散。郑曼青此年离开北平艺专南下,任上海美专教授,并很快接任国画科主任,以其长袖善舞,整顿教务扩充师资,引进一批有声望的国画家任教员,使得上海美专续北平艺专之后,成为中国画教学的新高地。次年张光随之落户上海,执教美专。而在1930年至1932年期间,因郑曼青、马孟容、章味三牵头组建中国文艺学院(后更名为中国艺术专科学校),张光又腾挪至此,任花鸟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33年张光入国立杭州艺专,与潘天寿、李苦禅同时任教国画系,直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内迁,时已年近花甲,遂离开杭州艺专,随章味三迁徙南京、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张光重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为新成立的上海国画院画师、上海文史馆馆员,终老海上。
在上述这一漫长的个人经历变迁过程中,张光最重要的身份是各校中国画科滥觞时期的重要教员,对国立杭州艺专而言,更是学校创办后第一任工笔花鸟画教授,开创之功自不待言。检阅近代美术教育史,最开始执教于美术院校的女性画家多为西画家,著名者如前述国立北京艺专的邵碧芳,上海美专的潘玉良、唐蕴玉,国立杭州艺专的蔡威廉,以女性身份摆脱封建礼教之束缚,接纳新思想新艺术,正是当时各校张扬、标榜新的教育理想所亟需。在民初学校由男女分校逐步实现为合校过程中,这批“女先生”率先登上讲坛,对普及教育,消泯性别歧视,无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张光较上述者年长,值其任教各艺校国画科,已届中年,不同于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激进者,是以旧式闺阁知识女性的气质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舆论甚至评价为“吾国妇女艺术界之宗匠”。后之续者,如执教上海美专的“女先生”余静芝、金启静、李秋君,活跃海上的周炼霞、陆小曼、陈小翠、顾飞、顾青瑶等,擅水墨丹青,兼能赋诗填词,均可称新时期深具古典文化修养的“闺阁淑女”。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风尚的微妙转变。而价值取向中与西、古典与现代的二元并存,其丰富与张力,构成了近代海上画坛充满魅惑色彩的“生态”之一角,正是“海纳百川”景观的生动展现。
1928年至1933年期间,执教上海美专、中国文艺学院,活跃于海上画坛的张光,已达至个人事业与声誉的巅峰。其间张光的社会身份与参与重要艺术活动甚夥,重要基本信息可胪列如下:1928年5月于沪上宁波同乡会举办张光、郑曼青联合画展,盛誉如潮(详见下文所引);6月1日大夏大学校庆举办书画展览会,会聚海上书画名流,《申报》8日刊出评论,称“张红薇花鸟草虫,不泥于古,不趋于时,女界作品,此为仅见”;6月参与大学院(后改称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被推举为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审查委员,同列为委员的女画家仅蔡威廉;6月,参加天马会第九届美术展览会,俞剑华撰《天马会观画记》称“花卉秀逸,则仍推红薇女士居首,豪放则推曾农髯先生为最”,柯定盦《今年之天马会》说“(红薇居士)画法工整,色泽艳丽,可称名作”;11月,参加秋英会第一次展览会,沧波《秋英会读画记》称许“花卉工笔,首推红薇老人”;1929年1月,参加寒之友画会第一次展览,常州诗人谢玉岑特为作品赋诗(见下文所引);6月,上海美专师弟书画金石展览会,展示郑曼青执掌改组国画系后的教学成绩,俞剑华《志美专师弟画展》称“学红薇工笔花卉之孙孟昭、丁月瑞、刑德慧等,均能亦步亦趋,虎贲中郎,逢离莫辨真赝”;9月,参赴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召集之海上书画同人海庐雅集,与何香凝等合作;11月,参与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同时出品展览画集,履历称许张光“自古擅三绝者几人?闺壸尤罕,如夫人者诚足为吾国妇女艺术界之宗匠也”;1930年3月,参加蜜蜂画社画展;同年参与比利时国际博览会,获金牌奖;1932年10月6日,《申报》刊出张红薇参观楼辛壶画展后评论文章《湖社观画记》;1933年4月,巴黎堡姆美术馆举办中国画展,现代名家七十一人参展,张光列席;11月,参加刘海粟组织的中国画家赴柏林举办的中德美展。此外,报章所见参与赈灾、慈善各种书画展览活动不胜枚举。检阅张光此期海上之艺术活动,涉及沪上传统画会雅集、新兴政府行为的全国美展与重要国际美术交流,而如天马会、寒之友社、蜜蜂画社,张光均是较早参与者,当时女会员寥寥无几,称张光为此期海上最活跃最具影响的女画家之一,不算言过其实。
以章味三、张光夫妇的年资与威望,两人居所“薇雪庐”成为沪上温籍书画家荟聚与海上书画家雅集交流的中心。1928年8月20日《申报》刊出“薇雪庐诗文书画篆刻合例”,章味三诗文序跋、张光与郑曼青花鸟画、方介堪篆刻同时刊布润例,“薇雪庐”所在附近“法租界斜桥安临里十号”成为集体鬻画取件的地点,这一集体协作的方式,在同期海上书画家中间堪称鲜见特出,毋宁说,张光在上海美专与海上画界的诸多活动,是在海上永嘉书画家这一群体的背景之下展开。
1932年淞沪战争之后上海局势的改变,与此年中国文艺学院宣告解散,最终促使张氏移居杭州,执教国立杭州艺专。张光曾在林风眠执掌北京艺专时任花鸟画教授,向有交往,转为蔡元培支持下新设立的国立杭州艺专出力,自在情理之中。“料峭春寒梅讯迟,桃花争发上林枝。白公堤畔闲经过,旖旎难逢雪后姿。”流连湖上胜境,课徒作画赋诗,是乱世中一段从容静谧的时光。同乡友人刘景晨寻访过孤山畔杭州艺专任教的张光,为我们留下一幅当时写照:“白傅堤边访画师,壁间悬我送行诗。没劳报问灯初上,稍佐谈谐酒不辞。他日琼贻添绘本,临流盥诵待新词。传衣自续南田起,弟子尤尊老壸仪。”在其时年青一代学生眼中,年近花甲的女教授举手投足之间,隐现的已是旧时闺秀端庄内敛之“壸仪”,与其教学作画笃守传统、整饬谨严的工笔画风一起,汇成在“为艺术战”激情鼓动中一泓可供濯洗躁动的清冽水源。当张光1936年携带湖上画作于南京青年会开展会时,有评论道:“那样幽娴庄静的前朝大家风度,这样的人,这样的画,可以说静到一点烟火气息都没有。”“红薇女士久居西湖,她的画,多半是在杭州画成的,她的诗,又多半是在杭州所作的,读她的画,吟她的诗,至少要和时代的动乱的世界,隔离一世纪以上。”言志载道,为正义与光明呐喊,自是构成这一时期绘画的主流声音,但是在混乱与变动的人事之中,以一种沉潜与定力,描绘天地自然间不变的水流花开,指明“变”之中的“常”,何尝不能振奋精神、安顿人心?评论者感受到的或许就是这么一种带有女性特征的温暖力量。
三
以师承来看,张光画风基本承袭自永嘉画家汪如渊,汪氏在清末民初曾于诸多新式学堂任图画教员,画风综合中西,张光沿袭发展了其师秀雅正统一面,是向传统笔墨图式的回归。再深一步探究,汪如渊绘画得之家学,温州博物馆所藏汪氏生父杨得霖(生年不详,约1881年卒)的一组花鸟册页,形象谨严生动,设色明丽,技巧上以没骨为主,有近于岭南“二居”画风的撞粉、撞水法运用,从中可以感受到张光画风更深远的传承脉络。汪门弟子如郑曼青、施公敏、徐堇侯,皆擅意笔,而女弟子中除却鲁藻擅写逸笔兰竹,鲁文、张光、蔡笑秋等基本恪守师法,皆以工笔没骨花鸟画风、褚遂良体的小楷题跋,形成富于闺阁趣味的“簪花格”。张光留存至今的画作,即以工笔为主,偶作小写意;没骨设色为主,偶涉水墨逸笔。画风在寓居广东时大体已发展成型,终其漫长一生,尽管不断磨砺完善,但画风稳定,鲜有变化,堪称笃守典型,这既是“闺阁画家”的一般特点,也是近代传统派画家的通常选择。
近代花鸟画的发展,延续明清以来的文人写意画风,吸收了乾嘉以来金石学的成就,兼取西画形式趣味,以阔笔湿墨的大写意画风为主流,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可代表其发展的几个阶段与最高成就。相较而言,工笔画风趋向式微,除却岭南“二居”与少数地方画家,工笔没骨一路,承袭者不多。但在明清以来闺秀淑媛笔下,却向以此为正宗,如文俶、恽冰、李因、陈书、顾蕙、缪瑞英等皆为个中翘楚。张光画风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闺阁绘画”传统在民初的一种延续,下引当时诸家评议,皆指明了这一点:
南楼去遂远,清于亦不作。近来常州派,细甚气已涂。画史信手写,几辈矜磅礴。人间花鸟春,丹青久冷落。红薇乃法宗,神明无所缚。临轩调露脂,精心写风蕊。潜伏昭渊鱼,高举来云鹤。勤飞与歧行,随意显活泼。眼前万姿态,胸中一丘壑。动植无遁形,出手姿抄掠。(沈尹默)
南楼人远清于逝,没骨谁祧正始音。欲为谢迟求书法,闺中应有绣丝人。(谢玉岑)
花卉工笔,首推红薇老人,设色用笔,直追宋元,世谓其抗手南沙、南田,当非虚语,《珠江香韵》之古艳,《三清图》之清丽,风神绝世。近百年来,没骨钩勒之妙,已成广陵散绝,天生老人庶绍坠绪。(沧波)
红薇夫人所作工笔花鸟,宛然恽南田手,自饶清丽高逸之致。(周瘦鹃)
张红薇女士以咏絮之才,禀簪花之格,远法崇嗣,近挹恽蒋,手植名花,妙传真态,博观妙迹,自翮径畦。其设色之清丽闲雅,如天仙化人,不食人间烟火。画虽没骨,而骨法用笔,显然纤素之上。(杨清磬)
评价者皆将张光置于肇始自北宋徐崇嗣,清初恽寿平(南田)、蒋廷锡(南沙)发展成熟的工笔没骨花鸟画的传承脉络之中,更视为清代早期闺阁淑媛之中擅此道的陈书(南楼)、恽冰(清于)之后劲。
工笔花鸟画滥觞于唐、五代以来的宫廷,历来依附了院体特征,较之文人画具备更多职业色彩,在绘画史的历史叙述中,大致归属于“匠体”。近世以来,康有为等将中国画“衰败”原因部分归结为“元明后高谈写神弃形,攻宋院为匠笔”的文人画之泛滥,而在康南海看来,“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唯恽蒋二南,妙丽有古人意,其余则一丘之貉,无可取焉”,对承袭北宋院画传统的恽南田、蒋廷锡的工笔没骨画风青眼有加。在对文人画的批评声之中,院体与写实画风重新获得正视,是民初画坛的一股重要潮流。张光之所以在近代美术教育滥觞期获得极高出镜率与参与度,正是因为其工笔画风暗合了时代的需要,而对于以写意为尚但常流于放诞失范境地的海派末流而言,往往还具备了针砭弊端与矫正之意义:
张氏作品多工笔,赋色深得南田、南沙之神髓,清丽雅静,似不食人间烟火者,与庸史之涂朱抹粉不可同日而语矣。(辰伯)
近数十年来,海上画史大抵浓墨破笔,狼藉满纸,自以为天池、雪个矣。不知古人作画,首重气韵,岂任意涂抹耶。(张大千)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论及杨逸《海上墨林》一著时,曾痛斥海派末流,“夫自海通以来,上海所号为画家者,以迎合富商巨贾之故,笔墨日趋狂怪,靡然成风,雅道陵夷甚矣”,新兴都会之商业氛围与市民趣味对绘画传统的改造与侵蚀,势必与传统文人的画学理念形成冲突。而上引所述“涂朱抹粉”“狼藉满纸”之海派末流,确切来说更多指的是“吴派末流”,早在吴昌硕尚在世时,已有批评的声音:
吴缶翁现在有许多高足令徒,惟妙惟肖崇拜而模仿之,造成所谓吴派花卉。渐至用笔粗野,赋色丑俗,只取吴缶翁之面貌而遗其精神。终至东涂西抹,一塌糊涂,而吴派方大盛。……今吴派花卉可谓盛矣,满坑满谷,红绿纵横,观者亦多厌苦之矣。有奋起而作新画派者乎?余拭目俟之。(俞剑华)
“吴派花卉”大盛导致的审美疲劳,亟需“新画派”予以反拨与调节,拯衰救弊。至1928年,永嘉书画家已渐次落户沪上,以群体姿态执教于上海美专,时人显然对这一新生异质力量充满期待,杨清磬在观“张、郑画展”后撰写评论文章,标举“永嘉画派”,寄予厚望:“将见永嘉画派,独张南宗,岂独让水心论学,四灵言诗,焜耀于艺术已哉。”这一预见,时过二十年施翀鹏在观郑曼青画展后,做出了更深入的阐释与总结:
与粉红骇绿之海派画搏斗者,推永嘉诸子,而以郑曼青实执其牛耳。永嘉花卉,以熟练之技巧为其艺术形式之基础,以深邃之精神修养,为其艺术内容之重心,忠于形似表现而不为形式所拘束,长于内容修养而不至虚空,所谓脱略行迹神韵弥漫者庶几矣。
海上“永嘉花卉”画家,以张光、马孟容、郑曼青为代表,余如刘景晨、马公愚、方介堪等,实为兼擅绘事。其中张光画风最工丽典雅,马孟容融合中西,擅小写意,郑曼青佳作“挥洒自得”(陈定山),笔墨最放逸。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郑曼青任上海美专国画系主任,参与筹建中国文艺学院(1930—1932),活跃于海上画界,风头正健,但郑氏自幼追随姨母,深受熏陶,画学修养实部分承继自张光。郑曼青画学执“气韵”说,至后期,亦趋向以近徐渭、朱耷的文人墨戏为能事,虽绝非“粉红骇绿”之辈,往往也以“任意涂抹”的简逸画风招致同道批评,即施文所谓“脱略行迹神韵弥漫”者。相较而言,执守“忠于形似表现”“长于内容修养”,实指张光、马孟容,尤以张光最为典型,这在她留存至今的画作与画论中有集中体现与阐述。
张光《论画家之美化与文化相错综》一文,回答的是关于画之“内容修养”的问题。于张光个人而言,画境之所以远离尘嚣,关乎笔墨技巧,更是因为画者内心远离现实羁绊,悠远高旷,始终与天地精神相往还:
月落参横,晓烟初日,各有寥廓苍莽之景象,予吾人以流连惆怅之怀。而画家遐观远眺,随其兴之所至,即有无数之奇形变态,以荡吾心胸。一旦挥毫落纸,而烟云之气环绕笔端,此其境有超出乎尘埃之外,而不食人间烟火者也。
凡花之一瓣一蕊一萼,叶之一筋一刺,枝之或斜或直,无一不曲肖其形。于风光澹淡之中,更得摇曳旖旎之致。观其画如见其人也。即如鸟兽之羽毛,与飞翔跂蹻之姿势,虫鱼之灵活,与跳跃游泳之嬉聚,亦能栩栩欲活。传神在阿堵中,岂可以笔墨求之哉。
“忠于形似表现”,落实到技巧层面,则体现为“工”“写”之辩。张光任教国立杭州艺专期间,发表在校刊《亚波罗》的《绘事偶设》一文,深入思考讨论了工笔、写意之关系问题:
尝读朱景玄及黄休复画论,以逸为先,神妙次之,自宋以后,皆宗其说。故后之推崇,倪云林之山水,陈白阳之花鸟,皆曰逸品,莫与之京。虽然倪陈之画固高,简之又简,剥肤存翼,可谓不食人间烟火。究所由来,则云林师北苑,白阳师衡山,北苑衡山皆神品也,皆谨严工稳,非简笔也,是则倪陈之作,有以异乎其师欤?曰,非也,白阳工写生,云林尝作十万图,曰万松、万壑、万流之类,夫岂简笔也哉?是以知云林白阳亦神品也,简笔者乃其晚年脱化之作也,名之曰逸,未始不可。而世之学倪陈者,类皆忘其本,而不究其源,几一学步,便求捷径,牵(率)而涂抹,辄自拟于云林白阳,薄俗可鄙。板桥云,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此言极当。倪陈之作,诚如是也。余又观雪个之花鸟,虽如大笔狂草,然皆左规右矩,骨法神理,丝毫不爽,是寓工笔于写意之中,所以妙也。石涛之山水,往往写丈幅,以数笔了之,不失其为工,写尺幅千崖万壑,咫尺千里,不失为写意也,或偶以工写精粗之笔,杂出于一幅之间,亦无所不可,以其有根柢也,由工笔而后达于写意,方能臻此。然以石涛雪个之狂,犹不能离于学力,以板桥之怪,犹恐欺人瞒己,且必曰,极工而后写意,况世之才思不如石涛雪个板桥者,自欺欺人,更何如也?
置于当时语境,仔细体味,这一番将工笔归为写意之“本源”,“由工笔达于写意”的论证实是针对写意画发声的。国立杭州艺专国画科建立伊始,以潘天寿、李苦禅、吴茀之等为代表,是吴昌硕影响之下海上大写意金石画风的延续发展,写实、谨严,穷究物理的工笔画所天然具备的“科学性”与西来的素描意义相当,转而在学院的国画教学系统中获得了一种基础训练的意义,也是作为课目被赋予的重要教学任务。这在杭州艺专早期学生后来的记忆叙述中,可以得到印证,“先由张红薇老人教工笔,这位前清翰林(案:应为举人)夫人教画一丝不苟,从白描勾线到设色,十分严谨。……以后潘天寿先生又来教我们国画写意,他的教学是结合讲授中国美术史,分析画理,然后示范,有时还看图片和各家原作,山水、花鸟、人物都要涉猎”。由工笔写生达致写意抒情,结合画史、画论、鉴赏、书法、题跋的系统学习,正是从那时候开始,逐步形成杭州艺专中国画系的教学传统。二十来年后,潘天寿在关于中国画基础训练问题的讨论中,针对“西洋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论,提出“白描、白画就是中国画捉形的基本训练”,呼吁承续传统的白描、双勾教学,未始不曾记忆起当年红薇老人的工笔画课堂。国立杭州艺专的工笔花鸟画甚或工笔画教学传统,实应追溯至红薇老人张光。
张光的画学理想,自然不局限于时代赋予的“基础训练”的意义,原本还有一番宣扬人文精神的构想:
诚以美为天下之大公,而非一人所能私。他人处之,淡然而若忘,画家得之,穆然有深思。凡有一境,即有一景,有一物,即有一情,触景生情,而画家之画理参焉。惟其画理之精深,是以不为境限,不为物囿,而能超乎境与物之外者,仍不离乎景与情之中也。画之藉景与情而得其真者,亦犹文之有境与物臻其妙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为义当富矣哉。吾故曰:美术者,由于文化与美化,相错综而成者也。
这是基于那个时代“美育”之宏大理想所建构的绘画创作与功用的理想境界。这一“藉景与情而得其真”的超逸画境,于一生孜孜矻矻于诗、书、画修养与融通的张光而言,或已曾一探其津梁,而对于普遍缺乏诗书教养、视工笔画为纯粹精细视觉制作的诸多当代画者来说,终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幻梦,吾辈可不警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