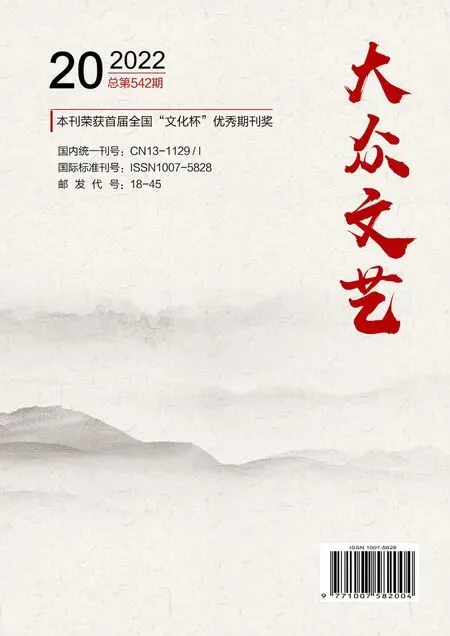镜花水月中的沉思:京派诗歌意象的互文现象*
2022-11-04李艳敏
李艳敏
(衡水学院中文系,河北衡水 053000)
京派诗人采取了以实写虚的手法,使心境和意象珠光交映。“人生如梦”的感慨又让他们体悟到了生命与自我的可贵。他们寄意于所写的实象——镜、花、水、月、星、灯都是实物,而镜中像、花下影、水中月、灯里梦则是恍惚的迷离的景象。类似的诗歌意象在京派诗人彼此的诗歌文本中虚实相映,构成了意象互文现象,各类诗歌文本间互文见义,达到了无限与有限统一。“镜花水月”是佛经中常用的对世间万象的比喻,也是传统禅境诗歌常见的意象。这类意象造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审美距离,虚幻的影像呈现出缥缈的朦胧美。意象的虚实结合构成摇曳多姿的美感效应。朦胧迷离和虚静空灵的意象组合是京派诗歌最为突出的艺术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派诗歌文本互文性。
“临水照花”的京派诗人把“镜”和“水”作为主要的诗歌意象,又以光影的象征体“灯”和“月”为其诗着色。庄禅之道、意识流动,丰富联想、大胆想象构成了废名的诗。众多的京派诗人中有一位为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所迷醉,他“蛊惑于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部分法兰西诗人的篇什里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诗人表示他“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
一、镜和水的互文
镜和水都能成像,是自我观照的载体,二者在京派诗歌中构成一对互文参照,隐匿着历史的迹象却付之于缄默。它能照见自己的影像,象征着人对于自我的思考认知。镜照物时,物来则来,物去自去,不将不迎,物过不留。人心也应是一个镜子,而一般人却偏不肯安心,处处驰求,时时攀缘。诗人的心如果和禅者一样重视内心发掘,不假外求,不缘境转,则诗的境界将更趋于圆融和谐。“镜”和“水”就是京派诗人转回内心世界、观照自我本性的潜意识意象映现。废名曾自负地说他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故又较卞之琳、林庚、冯至的任何诗为完全”。而“镜子”意象的出现绝非偶然为之,试看以下的诗句:“时间如明镜,/微笑死生”(《无题》);“如今我是一个镜里偷生”(《自惜》);“自从我梦中拾得一面好明镜/如今我晓得我真是有一副大无畏精神”(《镜》);废名对镜子的偏爱几乎到了把自己和镜子化为一体的程度。“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沉在海里它将也是个镜子”(《妆台》);“余有身而有影,/亦如莲花亦如镜”(《莲花》);出于对镜子的珍爱,他“不愿我的镜子沉埋,/于是我想我自己沉埋”(《沉埋》);“我惕于我有垢尘”(《镜铭》);“病中我起来点灯,/仿佛起来挂镜子”(《点灯》);“黄昏街头的杨柳,是空中的镜子”(《天上的星》)。“海是夜的镜子”。卞之琳的“镜子”多用来表现对爱情的期待,“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鱼化石》)“镜子”一样的爱蕴含着这样的内涵:镜子里有我的形象,我天天照镜子为了使自己在爱人的面前更完美。“昨夜付一片轻喟,/今朝收两朵微笑,/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我为你记下流水账”《无题四》朦胧的爱情让人回味无穷,为了记住爱人的一颦一笑,诗人不惜用“流水帐”来记录交往的细节。窗玻璃是镜子的变相,卞之琳写镜子的同时也常写道窗,如:“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穿衣镜也怅望,何以安慰?”(《无题二》),又如:“灯前的窗玻璃是一面镜子,/莫掀帷望远吧,如不想自鉴。/可是远窗是更深的镜子:/一星灯火里看是谁的愁眼?”(《旧元夜遐思》)废名曾经引波德莱尔《窗》做《竹林的故事》集的序言,这也应是京派诗人的共识,“从开着的窗看进去的人,决不比看那合着的窗的人所见之多。世上再没有东西更深奥,或更眩目,过于烛光所照的窗了。你在日光所能见的,常不及在窗玻璃后所演了的更有趣。”镜子中的虚像和镜子外的世界都是相对的,这正合佛教的“相对论”。废名说,“世人不知道佛教的真实,佛教的真实是示人的‘相对论’,不过这个相对论是说世界的真实都可以作其他世界真实的比喻,因为都是因果法则”(《说梦》)。《坛经.咐嘱品》“吾叫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种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既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皆取对法,来区相因,究竟二法尽处,更无去处”。“三十六对”对立又相因,对立物之间还有相互交织,彼此沟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面。要求人们在对立因素中不断往返流动,在对立的空间中体悟关系中的特殊意味。这一原则的在诗歌情感表达中的运用,使诗语有极大的包孕性和含混性。卞之琳的《断章》中两组相对的“看”与“被看”的风景在读者眼里又是一道新的风景。“要知道,绝对呢,自然不可能;绝对的相对把一切都搅乱了:何妨平均一下,取一个中庸之道?何妨来一个立场,定一个标准?何妨来一个相对的绝对?”《雨同我》《距离的组织》都是这一原则在诗歌上的应用。何其芳在《梦中道路》表示,他追求的是诗歌的感觉方式和传达方式之美,而《古镜》是他身世之感的形象表达:“我前身底华年/岂亦消逝在叹泣底风雨里/夜夜在褪色的窗帏下/挑灯自画自媚的长眉”,其前世和今生之思在古镜中交相辉映,如同轮回观念的再现。
二、灯和月的互文
灯和月是光明的象征,然而此“光明”非“太阳”和“火把”那样熊熊灼人的“光明”,而是温暖柔和的心灵之光,呈现出和谐圆融之美。佛教有“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灯”是佛教文化的一个中心意象,照耀“此在”的人生,是光明佛国的象征,是现实人生的一种安慰和希望。诗人把“灯”引入诗中,也许并没有想到佛教的“传灯”,但灯能唤起人们关于人间温情的绝美想象。“共剪西窗烛”是一种温馨的美,“江湖夜雨十年灯”是一种沧桑的美。灯象征着光明和温暖,具有家的意味。正是因为佛教把握了人的光明崇拜心理,以“灯”为传宗的媒介,所以才有《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文字记载。月光的清朗柔和,使人产生安静宁谧之感,和灯光一样给人慰藉,为心的皈依提供了方向。在京派诗歌中,二者同样存在着显著的意象互文现象。
卞之琳的《第一盏灯》写道:“鸟吞小石子可以磨食品。/兽畏火。人养火,乃有文明。/与太阳同起同睡的有福了,/可是我赞美人间第一盏灯。”鸟吞小石子磨食品是鸟的生存本能,“兽畏火”一样是生物本能,“人养火”是为了取得光明温暖和自身安全,归根还是为了生存,但因为有了智慧的思考而不同于纯粹的生物本能。太阳只能给人白昼的光和热,而“灯”则可以驱散野兽和寒冷和黑暗,让没有阳光的黑夜不再可怕,作者“赞美人间第一盏灯”也即赞美人类的智慧之美。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和《灯》都把“灯”作为诗歌的主要意象,采用了博喻形成恍惚迷离的诗境。废名《和鹤西》写深夜的灯——“糊糊涂涂的睡了一觉,/把电灯忘了拧,/醒了难得的大醒,/冷清清的屋子里夜深的灯。”诗人形象写出了自己在灯光下梦醒后的感受,交织着庄禅的朦胧和空灵。林徽因的《莲灯》把“灯”和梦交融于一体:“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作者把人比作宇宙中的过客,将无法确定的人生旅途当作一个梦,内含着她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对理想的不屈信念。辛笛《垂死的城》“在沉沉睡了的茫茫夜/无月无星/独醒者与他的灯无语无言”,把“无语无言”的“独醒者与他的灯”扩大到了所有不甘沉沦的知识分子身上,寄托了对光明未来的希望。
三、梦和花的互文
京派诗人是写梦的高手。废名写梦,俞平伯写梦,何其芳画梦,卞之琳也把梦当作诗歌的一部分。他们在梦里回忆过去的童年、关注当下的人生和憧憬美好的未来,暗示着他们对生存本身的思考和追问。梦有虚实之分,京派中写实梦的以俞平伯最典型,何其芳、卞之琳、林徽因等则以写虚梦为主,所谓的虚梦是指理想、情绪或瞬间恍惚的感受。废名的梦既有实也有虚,他喜欢李商隐的“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认为这是中国绝无仅有的一个诗品。常人眼里梦是假的,可在他眼里却是真的。在其散文《说梦》里他说,“作者当他动笔的时候,是不能料想到他将成功一个什么。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然而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所以虽然是无心,而是有因。结果,我们面着他,不免是梦梦。但依然是真实。”他为好友梁遇春作“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花招魂”的挽联,他为不自己不会画花儿而惋惜——“不然我可以将这一册小小的遗著为我的朋友画一幅美丽的封面,那画题却好象是潦草的坟这一个意思而已”,他“喜欢具体的思想,不喜欢‘神秘’,神秘而要是写实,正如做梦一样,我们做梦都是写实,你不会做我的梦,我不会做你的梦”。故而他的诗歌多是自己幻想的梦境,和卞之琳《旧元夜遐思》的“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独醒者放下屠刀来为你们祝福”存在鲜明的互文。废名评卞之琳诗歌道,“卞之琳的诗又是观念跳得厉害,无题诗又真是悲哀得很美丽得很。”其实这也是废名的夫子自道。卞之琳的《车站》形象写出了在车站等车时的感受——“抽出来,抽出来,从我的梦深处/又一列夜行车”,另一首《入梦》把古典的诗歌境界化得不落痕迹,作者于“梦中的烟水”中幻想着自己在秋天的下午卧病在床,“望着玻璃窗片上/灰灰的天与疏疏的树影”,诗人看着“枕上依稀认得清的”的湖山,“仿佛旧主的旧梦的遗痕,/仿佛风流云散的/旧友的渺茫的行踪,/仿佛往事在褪色的素笺上/正如历史的陈迹在灯下/老人面前昏黄的古书中”,忧伤和缱绻之情跃然纸上。而他的《倦》则用“蟪蛄不知春秋,/可怜虫亦可以休矣!/华梦的开始吗?烟蒂头/在绿苔地上冒一下蓝烟吧?”诉说着人生的无聊与厌倦的心态。
何其芳的《预言》集有诗34首,其中18首写到了梦,而梦在诗中出现达29处之多。诗人自己也说“我是一个喜欢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的人。” 他的“梦”里常有歌声响起。“我要歌象梦一样沉默,/免得惊醒昔日的悲咽;/我要梦象歌一样有声,/声声跳着期待的欢欣。”(《我要》)他的梦就是希望“我也曾有过并不狂妄的希望,/往梦里去索现实生活的赔偿,/但梦里仍然是充满沉郁和烦忙……”(《我也曾》),然而梦是虚幻的,“对于梦里的一枝花/或者一角衣裳的爱恋是无希望的”(《赠人》)他把爱人比作燕子问道,“翩跹在这寒冷的地带,/你这不知愁的燕子,/你愿意飞入我的梦里吗”,当终于成熟时,却又“始感到成人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柏林》)。诗人以黄粱一梦的典故作比,感叹“一个幽暗的短梦/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古城》),暗示着人生如梦般短暂而空无。而“朦胧间觉我是只蜗牛/爬行在砖隙,迷失了路,/一叶绿荫和着露凉/使我睡去,做着长长的朝梦”(《墙》)则形象表达了诗人人生失路的迷惘和无奈。
在废名和林徽因的诗里“梦”和“花”互为映衬。废名诗中的花以想象居多,随处随时有花,以坟上的花最为独特,前面已经论及。同样把“花环”“放在一个小坟上”的是何其芳,这两位诗人显然把死亡美化成了生命的另一种转换形式:人死后的墓正可以成为新生命的生长地,用来养育新生命——那美丽的花。废名想象“鱼乃水之花”,想象“满天的星,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东墙上海棠花影,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沉在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林徽因的花则在恍惚的幻境中,象征着飘忽不定的情绪。她感叹“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她的昼梦似乎“垂着纱”,而那无从追踪的情绪竟然可以“开了花”,倏忽而至的灵感则“是花,是梦,打这儿过”(《灵感》),当意中人到来时,“花开到深深的深红/绿萍遮住池塘上一层晓梦”(《你来了》),花和梦的意象构成恍惚朦胧的另一种互文。
整体上看,京派诗歌在本质上继承了传统诗歌的禅思美学,其丰富的意象展现了京派诗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构成了奇特的互文现象,代表了初期现代汉诗在融化传统诗歌精髓上所作的努力,而京派诗人生存与救世的现代焦虑也在镜花水月的意象互文中得到了如实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