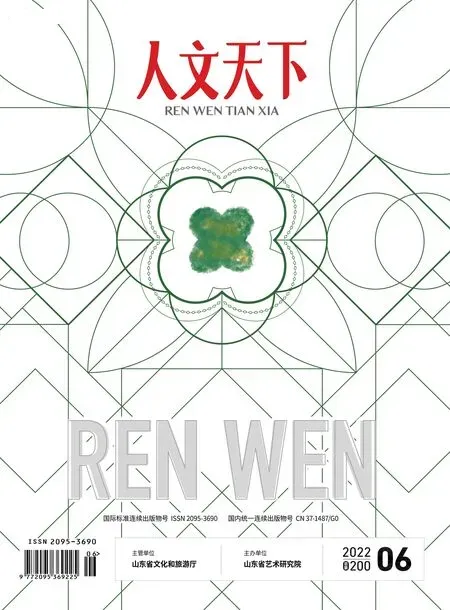吕剧《板桥县令》的艺术特色
2022-11-02■张强
■ 张 强
新编历史吕剧《板桥县令》根据清代著名文人郑板桥的故事改编而成,该剧曾入选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并于2018 年1 月在潍州剧场成功首演。该剧自首演以来,便因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表演方式的开掘、悲剧意蕴的营造、思想内涵的开拓等方面所具备的鲜明艺术特色而广受好评。
一、矛盾的人物塑造
吕剧《板桥县令》中郑板桥的人物形象是丰满的,这种丰满的人物是通过矛盾的手段与方法塑造出来的,主要体现在人物处境与人生追求之间的矛盾,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表面行动与实际作为不协调导致的矛盾,以及人物品性与周围人物格格不入造成的矛盾。
(一)身在庙堂,心在远方
吕剧《板桥县令》中郑板桥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郑板桥辞官退隐才得以终结。起初,郑板桥的人生理想是“造福百姓保乾坤”,他为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为了正义能够得到伸张,兢兢业业从无倦怠,深得百姓信任。但他除了潍县县令的身份外,还有另一重身份——文人,而且是生性落拓的文人。因此,当他受到官场中条条框框的限制而身不由己之时,当自己“焚香”“烹茗”“开酿”的闲情逸致被积压的案牍文书袭扰之时,当自己的政治雄心被官场的黑暗现实逐渐击垮之时,他那身处庙堂、为民伸冤、造福百姓的壮志雄心便逐渐隐退,潜藏在心中的退隐之意、逍遥之情逐渐萌发。第三场中“十年盖破黄绸被……多少雄心退”的唱段,便是他人生理想逐步转变的直接表达。此时,他虽身处庙堂之中,心却已飞向远方,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再次发生,他没有选择为追寻理想立即辞官退隐,而是选择替百姓主持公道之后潇洒离去。如此这般,既让郑板桥实现了为民分忧的理想,又实现了逍遥江湖的理想,使其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最终得以解决,郑板桥的人物形象也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二)表面糊涂,实则聪明
剧中处理郑板桥对于案件的态度时采用的方式亦是矛盾的。他表面上装作对案件并不在意、糊里糊涂的样子,“草率行事”,实际上则仔细谋划,在办案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与智慧。公堂之上,郑板桥在得到当年修筑白浪河大堤的账本后,并没有直接提审黄四,而是假装糊涂,对账目充耳不闻,转而欣赏起账本上的字,并对此赞不绝口。这一行为,从潜意识的角度出发,可以解释为身为文人、书画家的郑板桥内心不自觉流露出的对书法的赏识;从审案的逻辑出发,则充分展现出他对账本真伪的毫不重视,以及他为官极其“糊涂”的一面。这就使得黄四的管家看到郑板桥的举动之后,对账本一事、对贪污公款一案放松了警惕,这也间接保护了知道当年事件真相、藏有真账本的张王氏一家,同时也为进一步探听事件的虚实争取了时间。
剧中郑板桥所表现出来的糊涂,是他自己在是非混淆的官场之中的伪装,真正的大智慧隐藏其后,他的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罔顾公平正义,亦不会将假糊涂变为真糊涂。因此,当马知府以黄府说客的身份前来劝说郑板桥装糊涂,将账本一事遮掩过去之时,他并没有被蒙骗;当马知府要挟郑板桥之时,他也没有选择妥协;当巡抚的重重命令传来之际,他也没有选择放弃。可以说,郑板桥正是通过这种表面糊涂、实则聪明的为官方式,才能在浑浊的官场之中屡屡为民伸冤,深受百姓爱戴。也正是通过这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处事方式,才使得郑板桥的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饱满,使得他的智慧得以彰显。
(三)官场腐败,独善其身
前两种郑板桥形象的塑造利用的是其自身的矛盾,另有一种则是通过与外界、与他人的对比展示出来的。在郑板桥所处的封建官场,官员贪污腐败的事件屡见不鲜,官官相护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在大多数官员心中,“步步高升”“光宗耀祖”“荫护妻儿安宁”成了大事,伸张正义、为民做主反倒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当年的县令、如今的巡抚才收受黄四的贿赂,将民脂民膏收归己有,致使花费重金修建而成的白浪河大堤被一场洪水冲垮,引得潍县哀声四起;导致马知府当年出任县令之时,贴出“新官不理旧事”的告示以求自保;这也是促使马知府登门劝说、巡抚远来问罪、黄四不知悔改等事件出现的诱因。郑板桥虽在如此浑浊的官场之中生存,却依然能够做到独善其身,他能够在有事之时勤勤恳恳,操劳政务;亦能够在无事之时来到市井,走到大集,与百姓交心谈话,去体察民间疾苦;更能够不惧自身的前途,不顾个人的安危,将与巡抚、与马知府皆有关联的黄四绳之以法。马知府、黄四等人愈是猖狂,愈是腐败,愈能反衬出郑板桥的清廉与正义。
二、新奇的表演方式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板桥县令》采用的是矛盾的手段,从表演方式来看,《板桥县令》亦有其独特、新颖之处。
(一)打破行当界限,增加喜剧效果
在以往的戏曲作品中,清官多由老生(如昆曲《十五贯》中的况钟)或是花脸(如京剧《铡美案》中的包拯)扮演,用丑角来扮演的戏曲作品虽有(如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徐九经),但数量并不多。而用老生演清官,又在其基础上融入丑行表演风格、打破行当界限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吕剧《板桥县令》中郑板桥的饰演者董家岭便是主攻小生和老生。但在实际排演过程中,考虑到郑板桥的人物身份与人物性格,以及该剧诙谐幽默轻松的艺术风格,董家岭便“大量地借鉴了丑行的动作和念白,着重表现郑板桥的‘怪’,滑稽幽默、寓庄于谐,充满了轻喜剧风格”。因此,郑板桥初上场时并非如同况钟或者包拯一般正襟危坐,一本正经,而是匆匆忙忙,踉踉跄跄,不时地环顾四周,使得本就严肃的公堂变得轻松了许多,而后又借用丑行的语言风格说了一句“嘿!这就奇了怪了”,使得郑板桥的形象脱离了普通文人的刻板形象,平添了一分机趣。此外,剧中还多次运用方言与现代词汇,增加了很多喜剧效果,使原本一桩严肃的公案戏,变为一桩轻松诙谐的传奇剧。
(二)丑行跳入跳出,增加审美意趣
除主角的表演形式有其独特之处外,剧中两名衙役的设置也有其亮点。作为该剧导演之一的芦珊便在其创作随感中谈及两名衙役的作用:“类似曲艺中的说书人那样自由地跳进跳出,创造性地扮演剧中各种各样的角色形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剧中,这两名衙役灵活地跳入跳出,不受舞台时空的限制,既是这个故事的参与者,又是整个事件的旁观者。他们既可以在戏曲开场之时,向观众介绍郑板桥的人物形象与所作所为,又可以利用自身行当特点插科打诨,营造轻松幽默的氛围。他们既可以跳入剧情承担衙役的任务,帮助郑板桥审理案件,捉拿凶手;又可以跳出情节担任理想的观众,对郑板桥的一举一动加以评判;也可以在剧中充当叙事人物,推动戏剧的发展。剧中郑板桥被革职离去用的是暗场处理,但被革职的原因,观众并不甚清晰,可经过衙役的一番交代后,大家便知晓其中缘由。该剧对衙役这一角色的设置,与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有异曲同工之妙,该剧的审美内涵也因此更加丰富。
三、深厚的悲剧意蕴
吕剧《板桥县令》整体艺术风格是诙谐幽默的,但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诙谐幽默只是该剧的华丽外衣,隐藏其后的深刻的悲剧性才是其真正内涵。
(一)政治黑暗,为官者生存艰难
中国古代文人在真正接触官场之前,大都胸怀大志,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但官场中的勾心斗角、政治上的你争我夺往往让他们难以适从。而郑板桥所处的清代,政治更是黑暗,这就导致大批传统士大夫要么背弃自己当初的理想谄媚求存,要么选择继续坚守理想清贫度日。前者在黑暗政治环境之下逐步走向沉沦,成为当初自己最厌恶的人,但他们大多能够平步青云、衣食无忧,《板桥县令》中的马知府与巡抚便是例证。马知府在担任潍县县令期间便得知黄四贪污钱款一事,但因此事牵涉自己的顶头上司,也就是后来的巡抚,他为保全自己的官职,便下令不审理前任官员留下的案件,他也因此得以升任知府,得到好处的他便继续与恶绅、贪官同流合污,并帮助他们劝说郑板桥放弃审理此案。反观郑板桥,苦读圣贤书,虽才华盖世,却终难得志,数十年寒窗发奋,最终只获得个七品芝麻官的职位。想要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却因官卑职小难以施展,多少辛酸、多少悲苦涌上心头,只得独自吟咏“多少雄心退”的悲歌;想要伸张正义,却因得罪上级而被罢职归乡,只得归隐田园,不问政事,虽是逍遥,却隐藏着无尽的酸楚与无奈。在《板桥县令》中,马知府与郑板桥同为文人、同为传统士大夫,改变初心者,飞黄腾达,但人已变傀儡;未改初心者,仕途坎坷,最终落得个罢职丢官的下场。人生理想终究败给社会现实,黑暗现实终究摧毁人生美梦,空寂感与幻灭感油然而生,怎能不令观者为之扼腕?
(二)官官相护,老百姓苦不堪言
文人混迹官场中展现出的空寂感与幻灭感远远抵不上底层民众遭受官员压榨,遭受土豪欺凌,拥有无数冤屈却难以昭雪,掌握事件真相却难以言明,持有公平正义却难以伸张所带来的无力与悲伤。《板桥县令》中有两个人物从未出现在舞台之上,却不断被人提及。一个是巡抚,他是当年主持修筑白浪河大堤的官员,也是贪污案的第一受益者;另一个是张师爷,他是当年与巡抚共事之人,是贪污案的直接见证者。但巡抚从此扶摇直上,官位不断上升,师爷却因得知当年真相,被迫自尽而亡。此后,巡抚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潍县官员与百姓的身上,致使马知府有案不审,张王氏有苦难申,还准备对郑板桥审案一事横加阻拦,将正义扼杀。若不是张王氏遇到了正直、不惧权贵的郑板桥,张师爷的死永远得不到公平的审理,百姓对官府的信任也会逐渐消失。但是,即便黄四被打入监牢,潍县仍然在巡抚的魔爪控制之下,潍县的底层百姓仍然生活在无尽的苦难之中,这就使得全剧增添了一份生存的苦难与平民的悲剧。
四、丰富的思想内涵
诚如编剧李英明、王汝凯所言:“回想当初创作《板桥县令》的动因,并非命题作文,更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就是想写一个可以呈现于舞台的、关于郑板桥的故事。”吕剧《板桥县令》虽然在其思想上也展现出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和对主持正义的郑板桥的歌颂,但它与当今大部分主旋律戏曲作品并不相同,它没有类型化的人物,没有说教式的台词,最后一场中体现出的乐观逍遥的人生态度、高远豁达的人生境界,更是大部分主旋律戏曲所没有的。
(一)反对腐败,弘扬正义
吕剧《板桥县令》蕴含的最为明显的思想内涵便是对正义的赞颂、对清官的赞扬、对邪恶的抵制和对贪官的批判。郑板桥到任之前的潍县百姓,可谓是苦正义不来许久,前两任知县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对黄四欺霸百姓的行为不闻不问,尽情搜刮百姓的血汗钱,将平民的性命视如草芥,将大众的冤屈抛掷脑后,自己则享受美食美酒,四处阿谀奉承,官职步步攀升。幸亏郑板桥走马上任,当即下令“在县衙院墙上开了七八个大洞”,“不光出了晦气,还开了方便之门”,使受到冤屈的百姓有屈能伸,有官可依。与这类通过演员之口讲述出来的话语相比,在舞台之上直接搬演的审理贪污白浪河大堤修筑公款一案,更为直观地展现出百姓对正义的渴望、对清官的渴望。也正是因为郑板桥在审案过程中实事求是,面对威逼利诱永不妥协,面对敌人陷阱巧妙脱困,坚决为民做主,伸张正义,才深得百姓爱戴,在其罢职归乡之时,才会得到百姓惋惜又无奈的叹息。
(二)诗意人生,乐观逍遥
郑板桥虽心怀天下,然官场的险恶、仕途的坎坷、放荡不羁的性格、浪漫的文人情怀最终让他归隐田园,自由自在地过活。最后一场中的郑板桥,一支钓竿,一顶草帽,一身蓑笠,在河边钓鱼为乐,没有政务的袭扰,没有官场之间的勾心斗角,虽然生活贫寒,仅有几只小鱼、几根鲜笋果腹,但他逍遥快活,无拘无束,心灵得到极大的解放,不会为了钱财去巴结权贵,不会为了功名劳累奔波。此时的他,正如同庄子所讲的“曳尾于涂中”,宁愿在贫寒中清静无为地度日,也不愿靠阿谀奉承谄媚求存,“这种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生存理念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也正如本剧编剧所言:“最后一场戏把郑板桥的散淡、那种文人的东西表现出来了,有诗的意趣,使整部戏的美学品味上升了。”正因如此,整部戏的思想内涵也得以更加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