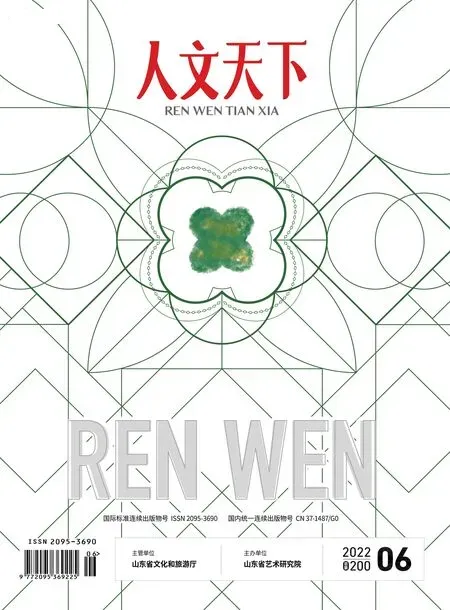复原古意与拓展新解
——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注解方式
2022-11-02何室鼎
■ 何室鼎
《老子道德经》在古代有汉代河上公本和曹魏王弼本,当代注译本比较著名的有陈鼓应的《老子今注今译》、任继愈的《老子绎读》等。其中,《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下文简称“河上公注”)尤其值得关注。
在现存“河上公注”中,多处注文与对应的《老子》原文有看似矛盾之处:“河上公注”会以与原文完全不同的含义使用原文中出现的字词,如原文中的“自然”“万物”“身”等词,在原文中,读者可根据上下文大致判断其词性与大致含义,在对应注文中出现时其词性、句中角色完全不同,或被解释为一个西汉之后才出现的、不太可能是原文含义的词义,或作出与原文文句结构完全相反的解读,如解“道法自然”作“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这样直接背离原文字词语句的释义,不仅看起来有违“注不破经”的古代治学原则,也与当代学界的规范有明显冲突。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现象存在就简单地斥“河上公注”为“任意阐发”,而有必要在评价古人工作前考察以下问题:在对原文注释解读中“河上公注”作者是否自知同词异义现象,是否有意区分了忠实于原文思路的“解读”和基于原文思路加以补充发展的“阐发”两种活动。据此,今人才能判断,“河上公注”作者是无意混淆词义,还是有意借新义释旧词。笔者发现,“河上公注”作者实际上是与《老子》原文身处不同时代、关心不同问题的“后人”解读者,他在解读前代文本时较为成功地规避了词义差异、语境变迁所带来的误读,并就“古为今用”、借助古代文本得出自身所期待的结论的阐释活动做出了自己的尝试,这值得同为“后人”的当代学者反思借鉴。
一、忠实于原文的解读:以“道法自然”为例
“道法自然”语出“河上公注”第25 章。对该章的解读必然面对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自然”仅在全章末句中出现。此前原文先论“道”,再言与“道”共享“大”这一特征的“域中四大”(即“道”“天”“地”“人”或“王”),完全没有提到“自然”,而末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除“自然”外,“人”“地”“天”“道”等所“法”者或被“法”者均为前文提到的“域中四大”之一。原文除末句外,并未说明“自然”与“域中四大”的关系,对原文的解读不应在缺乏文本支撑的情况下增加对“自然”与“域中四大”关系的解读。
二是纵观《老子》全文,“自然”仅出现5 次,其余4 次“自然”均有所属:为“XX 之自然”或“X自然”(主谓结构),而“道法自然”中并未点出“自然”所属,而是以排比句式从“人法地”讲到“道法自然”。原文中“自然”与“道”等“域中四大”并立,而不能支持“道法道自身之自然”的解读。因此,此处“自然”是“谁的自然”需要得到回答。
面对上述问题,历代注家各有处理,其路径主要有两种。
其一,以“王弼注”为代表,保留原文排比句式的连贯性,认为四句中的“法”有相同的含义。王弼注将“法”统一解释为“不违”,将“自然”解释为“道”外之物,即“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自然”是“形魄”“有仪”“智”所不能及的“无知”“无形”“无仪”,而“道”“天”“地”“人”依次更为“不及”,因此需要依次相“法”“不违”才能保全自身。
其二,以“河上公注”为代表,认为前三个“法”和后一个“法”有别。前三者有明确的“所法”,即区别于人的地、区别于地的天、区别于天的道,对于“道”而言,并不存在一个这样的“所法”,“道”“法自然”的方式是“性自然”,即不“法”于他物而“法”自己。现存各主要版本的《老子》原文均全篇没有“性”字,看似是一处“随意”解释。然而实际上,这一看似“随意”的解释却真正契合了原文。
首先,“无所法”并不等同于“不法”,而仅仅是因为“无物可法”故“不法外物”。这里“道”的确“法”着“道之自然”,只不过没有在“道”之外“另有所法”。这样一种“我法我自己”的关系被作为《老子》之“后人”的注者依照后代语言习惯在注文中解释为“性”,这是在不篡改原文前提下作出的解释。
其次,将“道法自然”释为“(道)无所法”并没有直接违背原文,因为《老子》原文中“法”字只在本章出现。“法”在《老子》文本中的具体含义没有其他限制,故根据语境作出对“法”的具体解释,从而保持四个“法”字形式上的连贯及四个分句结构上的统一。因此,作此释义并没有直接违背原文,同时解决了上文提到的挑战。
最后,将此处“自然”释作“道之自然”,为“自然”找到了其“所属”,使此处“自然”用法与《老子》原文其他“自然”统一,不会带来类似上文所述的困难。因此,这种解释完美解决了前述两个潜在问题,不仅保持了本句的连贯,还保持了整个第25 章的连贯(使整个第25 章的论域未超出“域中四大”),甚至保持了《老子》全文“自然”一词用法的一致。尽管从掌握多个早期出土文献版本《老子》的当代人角度看,《老子》是否应当被看作一整部著作,是否在同一时期成书而保持一贯的用词习惯和主旨,第25 章是否原本就是相对独立的一整个章节,这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但不能否认,“河上公注”作者作为还没有看到更多早期版本、与我们同为《老子》之“后人”又没有掌握我们所见丰富材料与大量研究成果的早期研究者,在对此处文本的注释上做到了对其所见《老子》文本的足够尊重。
反观上文所述“其一”路径,则完全无法在不超出原文的情况下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首先,无论将“法”作何解释,只要坚持四个“法”字同义,便不得不在“道法自然”句引入一个区别于“道”而高于“道”的“自然”以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保持一致,从而使末句论域超出了第25 章“域中四大”之限,故无法在不引入超出原文范围的“自然—道”关系论述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一。其次,四“法”同义意味着“自然”之于“道”的关系等同于“地”之于“人”、“天”之于“地”及“道”之于“天”,而“道”是“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的,“道”独立于“天”,因此“自然”也必须独立于“道”,故“自然”不能是“道之自然”。同时,由于“道”是“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的,所以“道”不可能反过来去法“天/地/人之自然”;而若这个“自然”是无所属的、独立于道天地人乃至天下事物的另一种东西,则不仅“自然”一词的用法与《老子》中其余4 处“自然”不符(带来了上述“二”中的困难),而且即便着眼全篇,一个高于“道”的“自然”也不符合《老子》对“道”的论述——在《老子》原文中,“道”字出现于38 个章节,所有这些“道”均与理想状态或最佳行为(最高价值)、发生力来源(物或天地的原初状态、“起点”、归宿)相关,而《老子》原文从未提到还有在时间、逻辑或价值上更先于“道”的任何东西。所以,上述第一种路径的四“法”同义解读方式虽然符合读者习惯且看似忠实于原句,实则不仅超出本章论域,还与全书的用词情况冲突。
二、古今同形异义词的区分:以“身”为例
“贵大患若身”语出“河上公注”第13 章。在本章注文中,“河上公注”对“身”字的解读与原文明显不同。“身”在《老子》原文中共出现于9 个章节,本章之外的8 个“身”均在与“他人”或“众人”对比之下的语句中使用,故只能被看作“某人自己”“某人自身”,可见《老子》原文并不支持“身”意为“身体(躯体、肉体)”的解读。然而,在并未引入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河上公注”却写下了“有身则忧其勤劳,念其饥寒,触情纵欲,则遇祸患也”的注文,似乎是将《老子》原文中的“身”无根据地解释为有饥寒、有情欲的“身体”或是“躯体”“肉体”。
纵观“河上公注”注文中对“身”的使用,我们发现,“河上公注”对原文“身”的解读与其对“自然”的解读一样严格且前后一贯:除此处外,《老子》原文中的“身”均被对应的注文解读为“我自己”或“某人自己”,并未被解释为“身体”。而在对应的《老子》原文无“身”字的情况下,“河上公注”的注文中也多次使用“身”字,而注文中的“身”字既指“自己”(如第13 章“宠辱若惊”注文“身宠亦惊,身辱亦惊”,而宠辱显然并非对肉体情欲所作的修饰),也指“身体”(如第10 章“爱民治国,能无为”注文“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也;治国者布施惠德,无令下知也”,此处“呼吸精气”说明“身”指“身体”)。可见,“河上公注”作者应该清楚《老子》原文中“身”的含义(仅可指“自身”,不可指“身体”),因此,区别使用了原文的“身”与“河上公注”作者自己习用的、“后代”语言中的“身”。
这种区别使用同一个字的“古义”(此处指《老子》文本中的字义)和“今义”(此处指“河上公注”作者所处时代的字义)的现象并非孤例,本文第一部分讨论的“自然”一词在注文中的使用也是如此。在《老子》原文出现“自然”时,“河上公注”注文同样出现了“自然”(或近义词“自当然”),而包含“自然”一词的注文语句仅仅是对原文含义的直接解释(以后代熟悉的说法“翻译”原文,并没有出现类似“身”与“养生”的阐发)。而在《老子》原文未出现“自然”时,“河上公注”对“自然”的使用便并不拘于《老子》原文对“自然”必有所属、限于名词和形容词的使用范围,出现了无所属的、独立出现的“任自然”及作副词修饰动作的“自然远离”等独特用法。这种对古今词语同形而异义的警觉值得当代学者参考:古今词语同形异义现象在经历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及现代汉语的快速演变后,在当代成为可能导致今人对古代文本严重误解的隐患。如刘笑敢(2022)指出,近代作为“nature”中译的“自然”与《老子》等古代文本中的“自然”相去甚远,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代研究者混淆。
三、阐发文本以得到文本外新问题的答案:以“养生”问题为例
《老子》原文也有“修身”的说法,如第54 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实际上是在说“修德于身”。但从第54 章全章来看,《老子》并未解释“修德于身”的具体方式,而是将“修德于身”与“修德于家”“修德于乡”“修德于国”“修德于天下”并列,得出“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的结论。可见,“修德于身”的“身”依旧是“自己”“自身”,这种“修德于身”并不一定是“河上公注”所说的“爱气养神,益寿延年”的“养生”或“治身”。同时,即便第10 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这样看似完全可以被解读为“养生”方法的段落,但这一章节上下文并未明确将这一句归于个体之身体,而后文在谈“爱民治国”“天门开阖”时的具体做法,又与这一句形成了类似54 章“身-国-天下”并列的结构;同时本章末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讲的是生万物、长于天下、流行于全天下之德,因而本章前半部分对“身-国-天下”应当采取的行动更可能是《老子》原文给出的顺天下之德的方式,而非于一己之内修一身之道德、行一体之气运的“养生”行为。
如上文所述,“河上公注”对原文用词和论证思路有清晰的认知和充分的尊重。至于为何“河上公注”要在原文并未谈及“身体”问题的情况下在注文中讨论“养生”,这应该不是由于注者误解了《老子》原文,而是注者有意识地将原文思想用于解决注者所关心的问题而留下的阐发性论述。因此,在《老子》原文既没有出现“身”字,也没有谈及身体健康问题的情况下,注者依旧会大谈养生,如第26 章“重为轻根”被注作“治身不重则失神”。尽管这些阐发性论述与对《老子》原文的释义没有被分开标注,但应该是被注者明确区分开的,绝非随意篡改原文,这一点可以从“河上公注”在三种不同情况下的注释方式中看到。
情况一:《老子》原文明确地在谈论非“治身”的其他问题,如“治国”。这样的段落共有6 处,均将“治身”与“治国”的论述并列。“治国”部分为对《老子》原文的具体解释,“治身”部分则并不参与对原文的解释与佐证,也没有预设“治身”与“治国”的关系(如治身当为治国之前提,或两者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应当被看作由“治国”引出的阐发,即对于治身者而言,也可以采取治国者的类似策略来达到治身的目的。
情况二:《老子》原文在谈论“道”“德”“天下”等问题时,这些内容会被用于支撑关于身、家、乡、国、天下的具体结论。这些讨论虽然并没有被明确说明“适用于修身”,但据《老子》原文对于“道”“德”的其他论述可知,从遍及天下、生万物育天下的“道”“德”引出“修身”甚至“养生”的结论是可行的,尽管《老子》原文并未讨论“养生”,但也并不排斥从“道”“德”之学中得出关于“养生”的教益。这样的段落共有8 处。
情况三:《老子》原文提到了“修之(德)于身”(个体、自我),但未说明其具体含义。“河上公注”用“养生”来解读“修德于身”的过程,即前文提到的第54 章,“河上公注”将“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注作:“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德如是,乃为真人。”此处原文指可修于身、家、乡、国、天下的“德”要在个体身上修,尽管没有提到必须是以“养生”的方式来修,但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注文讲“修道于身”,并非在天下通行之“德”外另求一“德”,而是将天下之“德”作用在“自己”之处。此处注文的“身”完全可以被解读为与原文相同的“自己”“自身”,只不过可能在“河上公注”看来,“爱气养神”就是在“自身”上修德所要做的。
由此可见,“河上公注”并不是在任意地谈“养生”,而是在原文文本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论述。无论是从原文“治国”类比到“治身”,从原文“道”“德”具体化到身体问题,还是对“修道于身”作具体化解释,都没有与《老子》原文产生直接冲突。《老子》原文没有提及,并不代表《老子》原文一定可以被排除在“养生”之外。当然,“河上公注”也的确关心着“养生”等一些《老子》原文没有着墨的问题,并试图借助《老子》对其他问题的讨论获得对注者所关心的新问题的解答。“河上公注”作者做到了在尊重文本的同时,借助文本去探索“后人”所关心的问题,既避免了任意阐释的篡改,又拓展了既有思想,这样的治学方式值得今人借鉴。
结语
“河上公注”中有注者并未采用明确标识区分的“复原古意”与“增补”两部分内容,但注者对于两部分的工作是自觉的,对原文原意复原和回应原文所提问题的进一步阐发使用了不同的方式,进行了独到的探索。有鉴于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河上公注”作者视作与《老子》作者共享语言使用习惯和思想关怀的“同时代人”,而应当将“河上公注”作者视作《老子》原文的“后人”,这种处境与当代学者面对《老子》原文时的处境是相似的。作为“后人”所注的“河上公注”需要兼顾复原古意与拓展新解,有所作为,这在我们解读“河上公注”时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