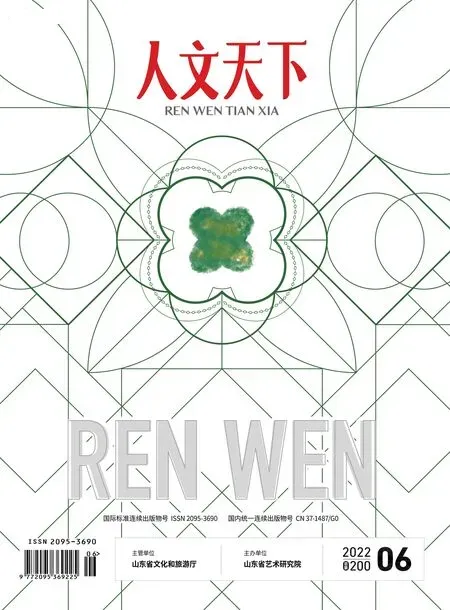美国生态戏剧批评的起源与发展
2022-11-02杨慧芹
■ 杨慧芹
20 世纪90 年代,“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作为一种新的批评理论在美国被正式提出。1999年,我国学者司空草在《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中引入“生态批评”这一新词汇,与国外生态批评思潮的兴起大抵同步。2002 年,王诺先生发表了《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一文,标志着生态批评真正传入国内,引发了研究热潮,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然而,我国生态批评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生态批评试图涵盖所有艺术类型,却又唯独对戏剧艺术不置一词,而戏剧艺术又是通过舞台剧这一不同于其他艺术类型的特质,反过来推进生态批评、生态艺术乃至整个生态文明进程的新生力量。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发展动态缺乏及时的了解与跟进,使得戏剧与生态问题在我国成为被忽视抑或被遮蔽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美国生态戏剧批评作为生态戏剧批评的肇事者与中坚力量,在生态批评、戏剧批评与戏剧创作活动中交叉演进。目前,无论从研究规模还是从研究成果来看,美国代表了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最高水平,并作为风向标引导着全球生态戏剧批评的发展趋势,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紧随其后。近年来,生态戏剧批评研究陆续在西欧、东亚等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呈现出较强的学术生长性。
一、生态戏剧批评的渊源
随着地球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以及人类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生态学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基础,其理念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发生了新变化,形成了从自然学科领域向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也催生出文化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文学生态批评、生态艺术研究、艺术生态批评等新兴学术领域,不断开辟出新的学术空间,拓展出新的学术维度,并激发出强大的生态智慧和永续的生态价值。20世纪70 年代,在生态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思潮在美国发轫,倡导用荒野描写和自然书写的手段恢复人类对大自然和生命万物的体验能力,以期形成推己及人的换位反思意识。
在这一背景下,戏剧学者温蒂.阿伦森认为:“艺术(包括戏剧和表演)也不能免俗,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任何从事批判性和知识性研究的人,包括戏剧艺术家和学者都可以而且应该解决这个问题。”20 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翼正式兴起,又逐渐影响到绘画、音乐、戏剧、电影、建筑等其他艺术门类及批评,相继产生了生态绘画批评、生态音乐批评、生态戏剧批评、生态电影批评、生态建筑批评等生态艺术批评范式。它们都与最早产生且最为成熟的生态批评保持着一定联系,同时又依据艺术生存与发展的特殊规律,提出了相对独特的批评话语。
作为生态批评的新分支与戏剧研究的新领域,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戏剧研究的全新理论视界与新的研究方法,其理论框架建构及学术研究活动与生态批评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相关。早在1978 年,美国生态学家威廉.鲁克尔特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批评”这个术语,强调批评家与文艺理论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建构出一个生态诗学的体系”,打开了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打破了“文学即是人学”的传统观念。此后十余年,生态批评逐渐升温,20 世纪90 年代出现了生态批评史上两大里程碑式的事件:一件是1992 年美国“西部文学学会”成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另一件是1996 年,彻瑞尔.格罗特费尔蒂主编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出版,明确提出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旨在强调文学是人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反映,而现实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因而,文学批评应具有关注人类生存问题责任,关注人类生态体统的意识,这也是生态批评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由此,生态批评是“借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从生态视野观察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是探讨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社会及人的精神状态的关系的批评”。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和视角。然而,当生态批评蓬勃发展之时,戏剧研究与创作中的生态学观点姗姗来迟。直至1994 年春,耶鲁大学《戏剧》期刊主编艾丽卡.蒙克与客座编辑尤娜.乔杜睿,以共同主持的《戏剧与生态学》专刊为阵地,敦促剧作家与戏剧评论家关注“环境”“生态”问题对戏剧艺术产生的影响。蒙克指出:“我们的剧作家将环境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从而保持沉默,而我们的戏剧评论家选择忽视戏剧产生的生态影响。”乔杜睿则直言道:“(西方戏剧自身)先天的、反生态的人文主义范式……与工业文明同流合污,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完全社会化的描述。”拘泥于这一范式的戏剧形式,充其量只能反映与自然分离的人类文化,这一论断也正式拉开了“传统戏剧与生态戏剧研究的范式之争”序幕。
生态批评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种戏剧批评立场,倡导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出发,衡量与指导戏剧艺术的文学创作实践,注重生态文学批评的介入性与戏剧表演艺术的实践性相结合,形成“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理念,进而以协作对话的方式表现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关系。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批评与戏剧研究两个学术领域。一方面,生态批评将戏剧作为一个新的批评对象,延伸与拓展其批评主体与范畴;另一方面,戏剧研究同样需要将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打造具有独特生态审美和生态情感的戏剧艺术。
迄今为止,西方学界采用生态学视角的生态批评戏剧研究,生成三篇重要的纲领性文章,共同指出戏剧研究是文学研究和表演研究话语之间的有力桥梁,倡导文本创作与文化表演回归“物本体”或是“物转向”,抵制自身将“生态学”作为一种修饰手法。笔者依据发表时间依次评介三篇重要文献,具体如下:1994 年,乔杜睿在《那个湖里必多鱼:走向生态戏剧》一文中指出,生态戏剧批评的理论源头蕴藏在戏剧自身中,继而提出“生态戏剧物质文化批评”的实践轮廓;2005 年,特蕾莎.梅在《绿化戏剧:生态批评由案头转向剧场》一文中探讨生态文学批评转向剧场生态批评的绿色策略;基于进一步研究,2007年,她在《超越班比:走向危险生态批评的戏剧研究》一文中正式提出“生态戏剧构作”手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戏剧作为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的独特地位,正所谓戏剧使得“人类想象力参与方式具体化,是我们生态学‘物质化’不可或缺的方式”,可以并且应该响应21 世纪生态问题的紧急召唤。总之,这些重要的文章和书籍奠定了从生态文学批评到生态戏剧批评的理论基础,其相关阐述最终融合成一种称之为“生态戏剧构作”的新兴生态戏剧实践,并形成了一个公认的、不断增长的戏剧批评话语。
生态批评有效地从各种研究方法论中汲取灵感,成为一种参与地球物种生态福祉的研究范式,其中包括环境史、性别与后殖民研究、现象学、文化地理学、唯物主义史学和表演研究等。乔杜睿与梅作为生态戏剧批评研究的先驱者与领军人物,也为生态戏剧研究勾勒出几个引人注目的研究方向,设计出一系列具有驱动性的研究问题,下文逐一进行总结。
二、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戏剧批评研究
人文地理学与戏剧批评研究各有各的发展路径且互动较少,但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两者的结合都显得颇为重要。舞蹈、戏剧、音乐等现场表演艺术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者研究人类如何体验和理解他们的日常世界的手段,进而审视空间是如何通过我们的身体被实践与体验的,对传统空间观念的极大挑战。同时,戏剧理论家和实践者越来越多地运用文化地理学的原理与方法,探讨戏剧文本与舞台上的地点、空间与景观之间的关系及其内涵,探寻景观戏剧研究成为戏剧研究新方向的可能性。
人文地理学与戏剧研究拥有各自的发展路径且互动较少,直到1997 年,乔杜睿在《舞台:现代戏剧地理学》一著中首次提出“地质病理学”(Geopathology)这一术语,以邻里、家乡、社区、城市、国家等空间概念为媒介,探讨地方问题以及作为问题的地方深刻地影响着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既涵盖女性剧作家、有色人种剧作家的新作,也涵盖易卜生、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尤金.奥尼尔、哈罗德.品特和山姆.谢泼德等创作的现当代经典剧作,力图阐明剧作中的“自然环境”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但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公正制度”存在着相似之处,形成“人与地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为戏剧研究开辟一个全新的方向。1999 年,加勒特.沙利文在《景观戏剧》一书中使用“乡土景观”(Vernacular Landscape,也称为风土景观)这一术语,借助人类学、现象学、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和城市研究的方法,从地点、空间、荒野、城市、社会、自然以及意识形态等多重角度,强调土地和人类之间各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揭示戏剧中蕴含的阶级不平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
乔杜睿与伊莲娜.法奇共同编辑的论文集《地方/景观/戏剧》(2002),提出“景观”是现代剧场空间美学思考的必要范式,“旨在朝着恢复自然和建筑环境以及非人类秩序的方向迈出一步,并使其在考虑戏剧形式和意义时适当地存在”。这一戏剧研究的新方向融入了剧场、地方和空间的文化意义,也为生态戏剧批评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维度。2006 年,皮尔森在《来了我:表演、记忆和景观》中围绕村庄、邻里和地区等地理标识展开书写,贯穿全书的一系列特定场地表演,如歌曲比赛或土著表演等,将自传、记忆、地点与当地人日常言行或事件交织在一起,从农业劳动到民俗传统全方位地界定在北林肯郡。2013 年,考特尼.瑞安在《戏剧期刊》上发表《与植物一起表演》,详细介绍了当代装置艺术表演家沃恩.贝尔将城市植物从商店、花园、温室、窗台等预期存在的地方挪移,重新构思它们的活动轨迹,以期通过贝尔的作品阐明乔杜睿倡导的“移植理论”,即一种跨越了私人与公共、自然与文化、动植物和人类空间界限的创新关系,一种人与植物相互融合的交替式生态过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米歇尔.沙佛在其博士论文《地形变化:景观、生态与环境戏剧》(2015)中,借用“生态病理学”(Ecopathology)这一术语,再次阐释乔杜睿“地质病理学”的批评理念。沙佛围绕“生态病理学”这一议题,提出从“景观戏剧”和“生态剧场”的批评视角来组织推进生态戏剧批评工作。一方面,“景观戏剧”议题是对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断裂的传统人文主义戏剧(即生态问题的病症所在)的生态反思;另一方面,“生态戏剧”则遵循“万物相连”生态第一定律,探索戏剧和生态圈之间的联系性,探寻戏剧进入长期与之隔离的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
三、动物批评视角下的戏剧批评研究
几个世纪以来,以人类为中心的单维度动物研究普遍认为,动物是没有思想甚至是没有意识的。直到20 世纪70 年代,随着文学生态批评和动物生态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开始频繁寻求与动物平等对话的契机,阐发出让文学生态批评研究与当代动物研究领域充满活力的诸多话题、问题和论述,凸显出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跨物种转向”趋势。其后,音乐、电影、绘画、摄影等众多艺术形式,也在塑造、深化、调整人类与动物关系上发挥出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强大的影响力。然而遗憾的是,戏剧和表演学科因其强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在应对动物问题时反应相对较慢:一方面,动物批评研究领域中的表演研究几乎无迹可寻;另一方面,表演研究领域中关于动物批评研究的论述与实践也相对缺乏。
乔杜睿是最早涉足“动物研究”的戏剧学者之一,围绕这一迅速拓展的跨学科领域,创造性地采用“动物文化实践”(Zooesis)这一重要术语,标记在文学艺术、戏剧表演、社会实践等领域的动物话语。对于乔杜睿来说,“动物文化实践”是人类思维、写作和说话方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涉及在文学作品中和舞台上所表现的动物意象等。应当说,其“动物文化实践”理念对戏剧创作以及戏剧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了我们久已熟知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戏剧流派和美学。2013 年,《戏剧期刊》邀约里克.诺尔斯编辑《跨物种表演》专刊,研究人员在人类文化学、文化生态学研究和跨物种实践的视野下,提出将动物、植物、昆虫和其他物种视为文化,跨物种表演是跨文化的理念,继而独辟蹊径从跨文化主义的角度探讨“跨物种表演”的可能性与重要性,以期读者重新认识到“在跨物种表演中没有一方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西方学界还辑有三本集大成的论文集,试图在表演中将动物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人类之外的动物行为能给戏剧和表演研究带来何种启示,分别是罗尔德.奥罗斯科主编的《表演动物性——表演实践中的动物们》(2013),乔杜睿与修斯.霍利合编的《动物行为——表演今天的物种》(2014),乔杜睿主编的论文集《动物的舞台生活——动物文化实践与表演》(2016)。
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反思与批评生态危机中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真实动物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动物参与表演”路径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并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路径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展现生态系统“万物一体”的生存现实、树立人类生命共同体意识等意义重大。
四、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戏剧批评研究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及其对自然的剥削类似于对女性的压迫,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以各种方式将环境正义问题与性别、性取向、种族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生态女性主义涵盖了各种政治、哲学和文学干预措施,将生态、女性主义、环境正义和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分析资本主义积累对女性和环境的影响;审查性别主义、阶级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的重要联系。梅在其撰写的《当代女性剧作家的生态戏剧构作》(2013)一文中指出:葛丽塔.加德和帕特里克.墨菲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8)中将生态批评的网撒得很广,不仅涵盖男权社会中对自然的剥削和对妇女的压迫之间联系的认识,也涵盖对这两种统治形式与阶级剥削、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紧密相连的认识。梅认为:“当生态批评的观点可以扩展到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白人特权等问题的范围时,戏剧——一直是行动主义和传播霸权神话的力量——似乎已经成熟,可以对之进行分析与批评了。”可见,后殖民生态学、批判种族理论、酷儿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等相互勾连重叠,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着生态戏剧批评实践活动。
贝丝.奥斯内斯的《女性参与可持续性发展戏剧的研究》(2013)是第一部涉及生态学、性别研究和文学批评等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奥斯内斯从理论思考、学术实践两个维度深入考察戏剧创作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探讨来自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危地马拉的三个跨文化实践案例,揭示了“应用戏剧”中的各项策略对促进女性参与可持续发展戏剧、实现人类可持续生活的作用。
梅与苏珊.伯塞尔等共同主编的《鲑鱼即万物:克拉马斯流域的社区戏剧》(2014),通过关注与社会正义运动相关的“社区戏剧”,将环境问题、种族问题、性别歧视和生态帝国主义问题连接在一起,阐明了在创作和表演的过程中涉及土著和环境问题。鱼类杀戮对整个克拉马斯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同时,鲑鱼作为当地人文化信仰的载体与图腾,也标志着传统文化习俗的不断丧失。由此,梅的戏剧创作团队与部落成员合作的《鲑鱼即万物》也收录在该著中。史蒂夫.博顿斯与马修.古雷斯合著的《修复行动——表演、生态与<山羊岛>》(2007)是早期尝试在环境关注与社区戏剧创作、表演之间建立起重要联系的论著。
伦.琼斯在其《扮演自然:土著表演的生态批评》(2013)一书中研究人类身体的物质性与自然世界,探寻表演与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2014 年,比尔吉特.道斯与莫福德.马克编撰的论文集《自然的生成: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土著表演》出版,研究来自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著名土著剧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如汤姆森.海威、德鲁.海顿.泰勒、玛丽.克莱门茨、伊薇特.诺兰、凯文.洛林、卫斯理.伊诺克、布莱尔.格雷斯.史密斯和威蒂.希米埃拉等,由此,土著戏剧研究、表演研究成为生态戏剧批评中的一部分。
文化生态学逐步成为生态批评和环境人文思潮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方向。南希.伊斯特林在《文学理论和解释的文化生物方法》(2012)一书中,将认知和进化研究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方法相结合,展示了理论和批评中的“生物文化”视角如何为文学(包括戏剧文学)阐释开辟新的可能性。盖伊.库尔斯与帕斯卡.吉伦在《艺术伦理:表演艺术的生态转向》(2014)中探讨了艺术界日益增长的生态伦理意识,阐释艺术团体如何在关注“身体”潜能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社会对话。该著在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生态哲学”关注生态艺术实践并作为研究对象,表明人类对环境更大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以当代舞蹈场景为例清楚地阐释了艺术伦理对“身体”的关注,其目标是在“个人身体”层面上乃至更大的“身体政治”层面上的合作与协作,而不是违背它。艺术家与批评家为艺术伦理发出的独特声音,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结语
如今,生态戏剧批评作为生态批评对象的延伸与拓展,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深入考察生态批评中的戏剧批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开辟出新的学术维度与学术空间,推动中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推进戏剧批评与研究范式的绿色化进程,从而提供较为全面、系统、明晰的生态戏剧批评研究图谱,反思戏剧与表演的性质及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全球性生态危机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明确提出亟待解决的生态问题与环境议题。可以说,生态戏剧作为建构生态文化的重要力量,让生态保护成为全球共识,让生态文明成为全民共识,这对于我国坚持绿色发展之路、推进生态文明理念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