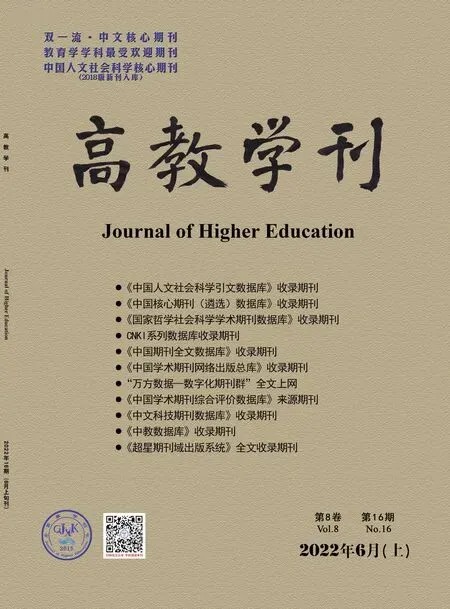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国家认同建构研究
2022-11-01胡倩一
胡倩一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随着高等教育由最初知识和学术的自发流动转变到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的自觉行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由知识和学术的国际化逻辑转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竞争的逻辑。”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都必然面临着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和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国家间竞争发展的博弈。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要通过教育流动保证其优势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则意味着身份认同和文化殖民的风险。简·奈特等在谈到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时指出,国际化的事实之一就是以本土环境为基础,尊重本土环境。如果忽视本土环境,缺乏身份认同,国际化将失去真正的价值。
一、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
国家认同一词最早由勒文森在1953 年论梁启超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提出,这里的国家认同是个政治概念,是一国的公民对自己身份归属的自我认知。安德森认为国家身份是想象和构建的。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HONTINGTON也提出类似的看法: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特性/身份,……人们认同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在当今世界,几乎不存在单一族群的国家,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处理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马来西亚的国家认同在历史上并不强烈,赵海立指出,“如果不是从殖民统治者到独立后新政府一脉相承的种族、民族政策的偏向,也许不会产生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马来西亚是典型的多元族群国家,有着较长的英国殖民统治历史,独立后面临国家整合的迫切问题。
(一)族群认同
据统计,马来西亚人口共计3 270 万。其中马来人69.1%,华人23%,印度人6.9%,其他种族1.0%,三大主要族群在文化特点、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及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各有不同。英国殖民者对三大族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该政策被视为马来西亚一切族群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独立时期马来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推动力就是来自于一种对其他族群特别是华人族群的“被威胁感”。这种“被威胁感”最终触发了1969 年的“五一三事件”,这一种族冲突极端事件导致上百华人死亡。“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在政治上修改宪法,通过《煽动法令》,在经济上提出“新经济政策”,旨在“消除贫困”和“重组社会”。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大力推动伊斯兰教在全国的普及,希望借此主导国家意识形态。虽然这些政策带着浓厚的扶马抑华色彩,却使族群之间获得了磨合和共进的可能。
(二)宗教认同
马来西亚三大族群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印度人信奉印度教;华人宗教信仰比较多元,包括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等。根据《马来西亚联邦宪法》,马来人必须信仰伊斯兰教,习惯于说马来语,奉行马来传统习俗,宪法中对于伊斯兰教的规定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事实上马来西亚各族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非马来人为了获得政治和社会地位而改信伊斯兰教,也可以信仰自己民族的宗教。按照1991和2000 年的马来西亚人口普查数字,全马华人穆斯林占华人总数的比例已由1980 年的0.2%提高到0.4%和1%。这种理性且务实的宗教政策,以及对宗教信仰宽厚和包容的心态,有效地减少了族群间的矛盾,既保持宗教多元化,又能使得各族群和谐共生,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文化认同
马来人的认同是以文化定义的,马来西亚的宪法将马来人界定为信伊斯兰教、说马来语以及遵守马来人习俗。这一文化认同促成原本的非马来人转化并进而形成马来人的共同意识。70 年代的《国家文化政策》有三条指导性原则:国家文化以马来土著文化为基础;其他文化可以适当方式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文化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元素。以马来人为核心的国家政策其实就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这种文化同化政策带着强烈的文化偏见。90 年代后,以宗教认同强制达到国家认同的做法正在转变为以文化认同潜移默化地建立国家认同。随着教育上的“固打制”被“绩效制”取代,马来西亚的文化政策也开始变得较为宽松,虽然“马来人优先”的原则并未消失,但政府更倾向于倡导各民族的共同发展,马哈蒂尔总理甚至提出要让马来人扔掉“马来人优先”的“拐杖”。马来西亚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同化到融合,单一到多元的流变过程。在非马来人看来,文化认同和其他身份认同是不矛盾的,他们始终把自身传统文化作为誓死捍卫的底线。
(四)政治认同
无论是印度人还是华人,都有着身份焦虑感。如一些华人学者拒绝使用“移民”来称呼华人先民,他们更强调华人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或先驱者。华人在马来西亚三大族群中的经济地位最高,成为马来人眼里最大的威胁。华人和印度人都是“他者”和“想象中的敌人”。王庚武用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变来形容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转变。他指出陈嘉庚代表的是“落叶归根”,在南洋赚钱后最终要回到祖国,马华公会创党人陈祯禄则代表的是“落地生根”,华人应该参与到“马来西亚建国”中去。马来西亚华人的确是区别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的特殊群体“,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族群并不仅仅是华人而是带有马来西亚认同意识的华人。”华人和印度人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参政权力和话语权,他们都有自己的政党,这为他们解决自身诉求提供了合法途径。以协商和妥协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避免了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由移民身份到公民身份的转变,这一政治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华人和印度人获得了国家身份认同。
二、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国家认同建构的路径
(一)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国家权威
马来西亚被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HE)称为“新兴竞争者”,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在东南亚地区具有绝对优势,同时也极具特色。在发展中国家,教育历来被视为重要的国家资产,有着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责任。在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家角色始终处于最核心的位置。LEE 指出,“马来西亚通过其国家政策倡议表明,它不是一个日益萎缩的福利国家,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干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商业化的背景下,外国高等教育中国家角色逐渐淡化,马来西亚却通过资金支持继续扮演着高等教育提供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上世纪90 年代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时期。1991 年政府提出的“2020 宏愿”,旨在推动马来西亚到2020 年成为完全发达的国家。政府关于私立高等教育的限制开始松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大规模地和外国高校建立合作机制,公立高等教育也开始市场化。松动不表示放任自流,马来西亚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台了《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等系列法案,同时设立了国家认证委员会等相关机构,2004 年还单独成立了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很显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国家权威一直贯穿始终。
(二)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共生互补理念
早期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对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影响深远。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从事不同的职业,进入不同的学校接受教育,族群之间缺乏交流,并未形成共有的民族意识。许宪隆、沈再新在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提出“共生互补”理念: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要确保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优势互补、协同进步和发展。马来西亚在缓和族群关系和建立国家认同意识方面,族群之间共生互补理念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新经济政策到新发展政策再到国家宏愿政策,这些强有力的人为干预政策在缩短族群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1969年“五一三”种族暴乱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府发布了第一个长期发展计划,该计划以消除社会贫困与纠正种族间经济差距为目的的“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特别是对贫困阶层人数居多的马来人采取了优惠措施,该政策在教育上施行“固打制”,规定公立大学必须按照马来西亚人口的种族构成进行招生,这一规定成功提高了马来西亚土著学生进入公立高等教育的比例,大量求学无门的非土著学生选择赴海外留学,经济条件较差的非土著学生,则选择进入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以获得接受外国高等教育的机会,由于私立学院不允许授予学位,直接刺激了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海外高校的合作。上世纪90 年代后,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公布了“新国家发展政策”和国家宏愿政策,这些政策延续了此前新经济政策消除贫困、重组社会和族群团结的目标。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马来西亚开始鼓励私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并对公立高等教育进行企业化改制。
(三)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语言策略
东南亚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身份认同的转变,这些国家独立后面临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复杂问题。“如果有任何文化层面可以超越种族和宗教差异,并建立跨越种族界限的纽带,为民族认同提供一种手段,那就是语言。”共享语言是国家团结和身份形成的最重要因素,语言问题一直都是马来西亚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在马来西亚,语言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马来西亚一方面得益于英国殖民时期的语言环境,塑造了以英语为核心的国民语言体系,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语言优势;另一方面,独立后保留了马来语(Bahasa Malaysia)在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中的主流教学媒介地位,以建构国家身份认同意识。在殖民时期和民族主义时期,马来西亚有将近140 种不同的语言,城市的主要教学语言是英语,住在村庄贫穷的马来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英语,被排除在马来西亚精英和上层社会之外。在独立和民族融合时期,国家教育发展计划的重点是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教育和教学语言被用作实现这个目的的工具。在全球化和马来西亚国家发展时期,知识经济和科技发展推翻了语言政策上对政治和民族主义的传统考虑。马来语促进国家统一和融合,英语促进全球交流,看似矛盾的做法却透露出政府在试图平衡英语国际作用和马来语国家地位上的努力。
三、结束语
作为后殖民国家,马来西亚有着复杂的族群关系,却没有发生过频繁的族群冲突,国家经济处于东南亚国家的前列。仔细检视会发现,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一直践行着国家中心主义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国家认同是最重要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随国家发展形势而不断修改和调整,甚至有矛盾和摇摆不定,却并不妨碍其高等教育历经殖民到独立、公立到私立、精英化到大众化、单一类型到多样化的发展历程,成为东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领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