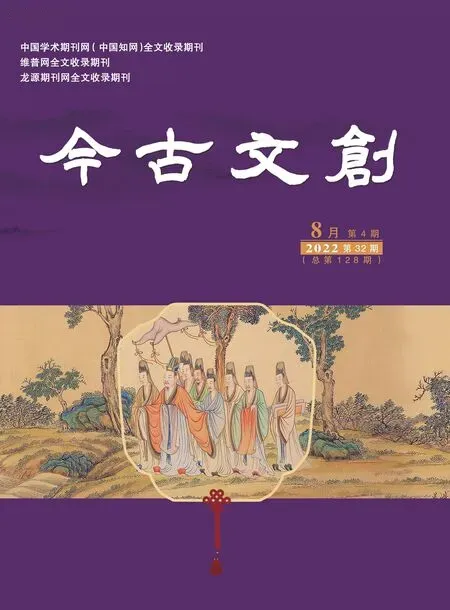数字时代的人造“ 灵韵 ”
——“ 人设 ” 的产生及其异化
2022-11-01◎刘雪
◎刘 雪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灵韵(Aura)是本雅明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本雅明多部作品中出现并且内涵有所差异。本雅明用“灵韵”描绘机械复制时代之前的艺术特征:一定距离之外的独一无二的现象,以及人与物的距离感。在资本主义文明时期,灵韵艺术被机械艺术取代,随着商品成为主题,灵韵的独一无二性也随之消逝。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也提到了“人工制造灵韵”。比如戏剧舞台上,演员面对观众诠释角色时有依附在演员身上的灵韵。电影演员在机械前会诧异,当他意识到观众席上是摄影机器,他的形象展示就要以放弃灵韵为条件。但电影在摄影棚之外对“名人”的人工制造来补偿光韵的消失。明星的“名流的魅力”实际上是由电影资本支撑的,但这种魅力存在于其商品特质的虚假之中。
在资本经济的发展下,文化工业成为趋势,商品成为时代的主题,人在这一浪潮中也开始异化为商品,“人设”即为人异化为商品的一种典型表现。为迎合市场消费需求,大众将自己的形象特质碎片化、符号化,用打造“人设”的手段来营造与受众或远或近的距离,制造、凸显人的“灵韵”。
“人设”是“人物设定”的简称,是指对漫画、小说、游戏人物等文化娱乐产品中角色的性别、年龄、外貌、性格、爱好等方面的设定。目前对“人设”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文娱活动上,或者分析“人设”如何利渐用传播媒介产生商业价值。“人设”在发展中也逐渐偏离本义,表现为“人设”的主体由动漫、游戏等角色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到现实的世界,成为符号资本,并借助媒体传播到大众消费端,实现从符号资本到资本的转化。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来说明大众如何通过“人设”的制造在数字时代的异化劳动中,逐丧失主体性,最终澄清文化工业中的“人设”不是彰显个性的工具而是人丧失主体性的体现。
一、从专业术语到流行话语
“人设”原本是文艺创作上的专业术语,用以对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角色特征进行概括。但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个体往往以网络为媒介,在各种虚拟平台上展示自我,每个人都渴望以一种理想的形象、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以实现自己或大或小的目的,对自我形象的维护慢慢发展成为对特定形象的追求,以使自己更加具有辨识度和吸引力,“人设”便应运而生。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都不例外。“人设”逐渐以网络热词的形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时,接受和使用范围也不断扩大。
明星的人设特征由活动、广告、媒体宣传、粉丝吹捧等多种途径持续地呈现并得到强化。他们以“人设”为手段,根据粉丝或受众喜好强化其某一特质,尽管这些特征可能并不是他们真实的自我,而是为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而装扮的。比如,为了拉近与大众的距离,营造“亲民”“草根”的人设,获得认同感;相貌、才艺优越的艺人以“吃货”“蠢萌”“铁憨憨”等人设降低自己形象带来的距离感从而让群众感到“真实感”,给予大众心理愿望和情感满足,最终实现吸引粉丝维护、吹捧和消费,达到兑现商业价值的目的。
在互联网时代,“人设”早已不是明星的专利。大众在互联网的隐蔽性、虚拟性特质下也可以自由地展现自我。只是这个自我是需要获得社会认同的,是渴望在他人的镜像中去重塑自我。人人都可以与公司或者平台合作打造个人形象,取得粉丝流量并在粉丝的追捧与互动中实现符号资本到资本的转化。以小红书、微博APP为例,各类博主通过分享生活来展示自我,积累一定数量的粉丝后就开创个人品牌或者与商家合作进行产品推广,从而获得经济收入。
可见,明星的“人设”是渴望拉近与大众的距离,而普通人则更想展现出优越感来逃离自己原有的生活状态。这种刻意制造与他人的距离感以及凸显矫揉造作的个性,可以理解为数字时代人为地制造“人的灵韵”。由此,“人设”经过资本的运作、各类媒体的宣传,明星带来的效应,将“人设”从文娱创作领域扩大到日常生活中,大众利用人设这种符号资本实现资本的转化。
二、人设中消失的“人”
在本雅明的阐述中,电影资本为补偿演员在机械面前因震惊和受观众控制而丧失的灵韵,去刻意地人工制造“人的灵韵”,支撑明星的魅力。“人设”的作用是彰显“自我”,以特性吸引大众目光,让大众去崇拜差异,但这却是在差别丧失的基础上去建立独特。当人设以工业品的形式用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大批量的生产和复制时,差异早已被大众约束,主体的独特性在标准化的文化模式塑造下异化成一种“伪个性”。
一方面,“人设”在制造的过程中,会像工业制作一样形成一套自己的表现形式。比如,确定接受人设的受众为哪一类人群,利用何种媒介传播,是展示个人照片还是在真人秀节目中刻意表现等等,不同的人设好像模板一样是可以人为选择组合的。明星在熟悉流程后可以在任何场合流畅地使用这种模板。打造人设的主体和背后资本的运作必须很“自然”地表现鲜明的、奇特的个人风格,即特定的“人设”,并使人们适应并接受。但是这种个人风格不是个人秉性的自然流露而是为了讨好大众强行表演出来的,甚至严重违背个人的性格特征,在大众前的表演只是一种“伪个性”的刻意展示。
另一方面,人本身是复杂多面的,而当人被抽象为 “人设”符号,原本完整的“人格特质”就碎片化了,人本身的主体性也就不完整了。人设的打造具有不可逆性,一旦个人在受众心中形成特有的印象,当受众看到某种特质或性格就快速联系到个人,或者当想到个人就联系上某种特质时,个人在公众面前就丧失了主体的完整性,行为方式也必然受到限制,按照公众认定的人设特质去表现自我。所以在文化工业中,“人设”所展示的“个性”不过是一种假象,是由资本打造的垄断商品,并被外界社会所支配。它们总是力图用自然的方式呈现非自然的特征,这本身就是扭曲的。对人设的经营维护不是对人的特质的确证而是在资本控制和劳动异化下不得已的被动行为。个体一旦表现出与人设不符的特征就会造成个人公众形象的坍塌、号召力的失败、商业价值的流失,最后被社会所抛弃。这个过程中,人就失去了自由发展的权利。
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是指人的劳动作为与人相对立、异己的独立力量,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相应地,异化是指主体派生出来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主体的力量,与主体相对立,甚至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的“劳动形式”在今天已发生变化,劳动场所不再是固定的工厂,而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连接虚拟世界,形成一种“非物质劳动”状态。在传统劳动下,劳动这种生产生活是类生活,而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成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然而在异化劳动中,工人同他所生产的劳动产品是异己的、敌对的关系;劳动中的生产行为也不属于他,而是成为反对他自身的活动。当代异化对人造成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心灵的折磨、精神的痛苦。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被马克思认为是人类的特性。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是人的类特性的首要内容。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人在利用“人设”凸显特性,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数字劳动以达到盈利目的时,劳动不再是确证自我,而是沦为生存手段;人设不再是人本质力量的实现,而是人的主体性的逐渐消失,人不由自主地为“人设”这个客体所奴役,成为符号资本,变得片面和被动,失去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权利。
三、沉迷人设的原因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到了大众对技术的依赖及其原因。电影演员的表演以电影的形式展现出来,演员在机械面前进行表演,在摄影棚、灯光、收音设备等器械中展现个性,人格魅力等人性特质。普通人实际上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临机械化的检测。现代社会精细的分工范围使得整个社会生活碎片化了。面对整日的机械检测,被忽略的人渴望像演员那样在机械前尽情展示人性特质。
科技带来的娱乐给现代人提供表现自我、释放自我欲望的渠道。人设就是大众渴望表现自我的一种体现,它的传播与互联网技术和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数字时代的社交平台使人人有展示自我的欲望,而各类平台简单易操作,对个人技术、素质要求不高,门槛低,吸引了广大的用户群体。目前的视频软件用各种极大地吸引、满足大众的自我表现欲,如抖音、直播平台可以多方位的创作和表现自我。
此外,社会对亚文化、新兴文化现象也更具包容性,从网络热词引发大众关注人设,网络现象在社会中传播时受到年轻群体或欢迎或调侃或模仿,社会也对新鲜事物具有包容性,可以接纳多元的、有活力的文化现象。
“人设”能够为大家熟知甚至模仿名人去“立人设”,除了社会环境的多元和包容外,经济效益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当小众文化、亚文化不再是特定群体的文化活动,而是逐渐变成流行的现象时,也就催生了许多的新兴行业和产业链。这种环境下资本运作将“人设”变得商品化,迎合大众喜好不断追求经济效益。无论是个体还是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扭曲自己的个性和初衷,甘心受文化产业的控制。原本自由展现个性的行为被量化为数据,如浏览量、转发量等,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异化。每个人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是受到文化工业的全面控制。文化产业带给大众是娱乐,缓解生活中的压力,然而工业制造的虚假的世界同样是苦役。
大众对“人设”的迷恋根本原因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分依赖。工具理性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速了科技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对事物认知。科学技术给大众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人们相信技术理性与个人自由可以同步发展,技术越进步,个人越自由。但是,在实际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对人的压迫由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借由工具理性转为隐蔽的心理和文化控制,因此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偏狭,导致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分裂,理性畸变为工具理性,人本精神被严重的遮蔽了。
工具理性没有让大众从繁重的劳动中彻底解放,也没有让个体更自由、更全面的发展,反而使大众在科技进步中愈发迷失自我,在文化产业中不是休闲娱乐,而是被文化产业所控制。资本控制文化创作,以追求商业价值、经济效益为目的吸引广大群体参与,投入创作的个体没有实现所谓的个性、自由,却在新时代的数字劳动中逐渐被异化,丧失主体性,不仅不去反抗,反而沉迷其中并甘心地维护异化。
四、走出虚假“灵韵”,回归人的本质
无论是本雅明认为资本保护的人格,还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对于今天的数字时代的劳动仍具有解释力。虚假的“灵韵”无论如何掩饰都不会具有“真”的独一无二的美,在劳动异化和文化工业中的展现的个性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社会新闻中明星“人设崩塌”的现象屡见不鲜,印证了看似新奇的个性恰恰是对人本质的遮蔽。对于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和工具理性的过度使用需要及时察觉和警惕。
工具理性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影响。要想减少工具理性对人的支配,避免在数时代劳动异化,个人、社会资本和政府都要做出努力去抵抗这些负面影响。
大众对明星、名人的了解和认知多数来源于网络中,但社会公民面对数字时代海量的信息时容易眼花缭乱,人的形象在网络世界中的展示也具有单一性、片面性甚至是虚假的。一旦对刻意营销的“人设”认可,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愿意为“人设”消费,这种行为刺激部分人去模仿这个行为从而产生恶性循环。所以,个人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要加强学习,提升个人修养和认知,要有分辨力,不去随意模仿,不沉迷于网络世界中的虚构自我,不能无理智地追逐流行,要学会分辨低俗、媚俗文化和现象,立足实际,保持本真。同时,社会公众人物要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大众视野前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向社会展示积极阳光的一面。
随着工具理性的统治性地位的确立,文化创作遵循的自身的规律逐渐消失。
目前文化产业对经济效益过度追求,贩卖“人设”获取利益正是文化产业负面作用的一隅。社会资本在发展文化产业时,不仅要丰富大众的休闲生活,满足人的审美娱乐的需求,还要承担社会效益。不以经济效益、时间为准则去干预文艺创作者,要精心打磨文艺作品贴合实际生活,增强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艺术特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破除唯经济效益论,拒绝快餐文化和低俗、媚俗文化,文艺作品要有精神性。
政府对文艺创作有引导作用,面对网络中的负面信息对大众的误导和精神腐蚀,相关管理部门有义务去规劝和惩戒。政府发挥其文化职能,制定方针政策依法对文化事业实施管理。比如,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制定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节目出镜人员不选用有不良社会影响的艺人;针对短视频中的“吃播”造成粮食浪费现象,“炫富”视频带来的拜金主义、奢靡之风进行及时引导和批评。政府和文化部门要对社会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予以引导,弘扬正向的价值观,大力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民众思想道德素质。
五、结语
“人设”从文艺创作的小范围使用的术语,逐渐地在资本的和数字平台的推动下,向大众的生活渗透。由明星到大众,将自我符号化,在媒介的传播下精准满足人的各类心理需求,达到人的镜像化表演,不自觉地异化自我,维护人设,失去本真和自我的全面发展。面对在文化工业中对工具理性过度依赖的现象,无论是个人、社会资本还是政府都应该保持警惕,有清醒的认知,努力减少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用科技进步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