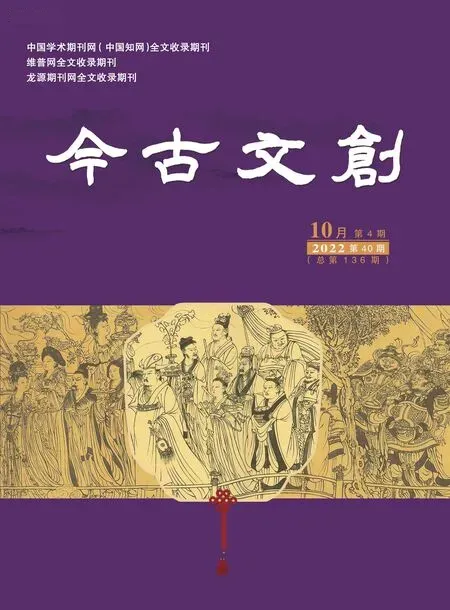《楚辞》服饰中的审美意境和文化内核
2022-11-01汪春晖
◎杨 丹 汪春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一、《楚辞》服饰的概述
屈原和《楚辞》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经常出现的热点话题,从古至今,对屈原和《楚辞》的深入研究一直存在,也是研究人员关注的主要问题。其中,通过《楚辞》深入研究楚文化一直是学界的中心,《楚辞》也为深入研究楚文化提供了研究依据。作为当时社会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楚人的服饰在《楚辞》中也有所表现,而这种服饰的记载也为研究当时的楚人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史料佐证,楚服饰现象在《楚辞》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而这些服饰现象为人们研究当时的楚地楚人都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楚辞》中对服饰的描述有很多,虽然有一定的虚构元素,但都是以实际情况为基础的。《楚辞》服饰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对于考证楚地风貌与习俗有着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对揭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楚人形成的独特审美意识以及精神内涵有着重要的作用。
《楚辞》中关于服饰的记载,除了展现了《楚辞》中服饰的特点以外,还展示了楚辞服饰独特的审美意识,以及楚服深刻的文化内涵,而这些又指向了楚人独具一格的浪漫特性。
二、《楚辞》服饰的特点
(一)追求灵动飘逸
偏爱飘逸美感南楚文化的传统理念,通过对于《楚辞》的研究,可以从多处细节理解楚辞服饰独特的飘逸之美。首先是描绘歌舞场景中美人翩翩起舞时,美丽的服饰轻柔飘逸。曼妙的舞姿展现出服饰的灵动飘逸,如同在眼前展开一幅幅画卷。还有可以从仪式活动看出楚人想要表达展现的飘逸之美。如《九歌·大司命》中的“灵衣兮被被”,描绘了古人在祭天、巫术等活动中优雅灵动的姿态。
(二)崇尚华丽精美
屈原在《楚辞》多处运用了服饰这一元素,而且关于服饰的描写大多为华丽辞藻,写尽了衣服的精美,如“华采衣兮若英”“荷衣兮蕙带”“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用花朵做衣应该十分繁复绚丽,并且根据现有的考古研究,楚国出土绣品的纹样多数都是以珍禽异兽、奇花佳草和自然物象为主题,一般为各种各样的凤鸟、龙和花草,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九章·涉江》的首句描写了屈原腰间挂着长长的宝剑,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冠。精美的服饰不仅彰显了独特的审美意识,也是屈原个人精神与独特品质的外化表现。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对于“奇服”的解释做了两种可能性的分析,一种可能“奇”是奇特之意,“奇服”指比较奇特的衣服;二种可将“奇”理解为稀有之意,“奇服”便是稀有珍贵的衣服。从上文提及的《人物御龙帛画》中“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可看出基本符合时代特征,所以这里的“奇服”翻译为稀有珍贵的衣服,华服之意比较妥帖。由此看来,楚辞服饰崇尚华丽精美也是没有疑问的了。
(三)重视佩饰,比德美
古人向来喜欢佩饰,分为事佩和德佩。事佩是指佩戴在腰间的日常生活所需的小工具,包括纷悦、刀、砺、小觽、大觽、木燧等。而德佩是用来彰显德行的象征,有比德之用。《楚辞》中多次提到佩饰:如“纫秋兰以为佩”“谓蕙若其不可佩”,这些佩饰除了有装饰美化的作用,更是外显佩饰主人的性格特征和道德内涵,所谓“德佩”,这是古代佩饰被人们关注的真实根源。
其实古代文学中“香草美人”的意象传统也和“德佩”有着非常精密的关系,上文提到的“纫秋兰以为佩”“谓蕙若其不可佩”,都是用香花类比喻美德,也属于一种“德佩”。正是香花的佩戴,让“香草美人”成为一种叙事可能。事实上,这种传统在楚文化中早已存在,由于楚地肥沃,物产丰富,河岸花草繁茂,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地人常常用香草来形容美好的事物,但屈原却赋予了它们更深刻的意蕴。
即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人高洁的品德与人格。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三、《楚辞》服饰审美意识的成因
(一)地理原因
提及服饰,就不得不提及地理方面的因素。楚国起源于“江汉之地”,在今天也就是湖北湖南一带,即使后来楚国版图不断扩大,但是“湿热”还是整个楚国不变的气候特点。我国南方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楚国也是如此,故而夏季往往多云多雨,气候温暖潮湿。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需要保证衣物穿着的凉爽和适宜,所以楚人的服装往往是轻薄罗纱之类的单薄服装,材料也是以轻薄为主。
(二)巫风盛行和礼乐制
楚人尚巫,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经常举行宗教祭祀与巫祝。在这些活动中,楚人表达了对神明的渴慕、崇拜都是以跳舞和歌声的形式,屈原创作的《九歌》正是这些礼仪的配曲。《招魂》也展现了楚人喜欢音乐的特质,而且巫舞场景宏大,为了与盛大的歌舞会相称,故可推断,当时的服饰也达到了比较高的审美水平。
“在人与物不分的远古时代,人们还不可能将自然界和人类区分开来。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神秘的关系,人类可以通过诸种手段作用于它们,以求得人类生存的需要。这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从史料记载中,可知楚怀王试图通过祭祀来使秦国军队退却,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行为是不科学的,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楚人崇尚巫风,对神灵的极度尊崇。其实不仅是楚地,在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都比较匮乏的古代,自我创造力微弱的人类会不自觉地将希望寄寓到神灵巫术上。屈原的《九歌》《招魂》等作品便是当时巫风盛行的产物,在服饰方面,则体现在纹样上,图案中的龙、虎等都蕴含着祥瑞的含义,还有凤鸟这一动物,其实它是人们臆想出的一种神鸟,并非真实存在。
(三)浪漫主义精神的熏陶
在《楚辞》中,屈原等人巧妙地将赋、比、兴融合,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在虚实中穿梭变换,描绘了神奇瑰丽的画卷,这些不仅展现出作者高超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充分彰显了他们浪漫的美学特质与精神。《楚辞》中所蕴含的情感是多样的,除了楚人对于自己民族国家的一腔热血,还有作者自己高尚品格与节操的自我抒发。从楚文化沃土中孕育起来的高尚的人格精神,不但体现在诗人的情感激荡中,而且在服饰上也有所体现。
四、《楚辞》服饰的文化内涵
研究服饰文化,其折射出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气质是尤为需要大家重视并深入的,其蕴有的文化内涵对于当今研究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强烈的生命意识
楚国的衣着强调优雅华丽,贵族的服饰更是如此。屈原作为楚国的王族,对于自己的衣着更是有极高的要求。但是往往其他楚国贵族选取衣服的标准仅仅是奢华华美,希望彰显自己的身份高贵和地位尊崇。但是屈原并非如此,屈原选择以“花草”作为衣服,这体现了他选取衣服的标准是为了彰显自己高尚的情操和纯洁的心灵。
当然,那个年代的屈原不可能真正做到直接用花草做成衣服,这样不雅观也不现实。所以合理推测,这里的“花草”有两种可能:一是带有“花草”图案的衣服,二是用当时一些稀有的材料制作而来的衣服。因为当时的衣服几乎都是植物制成,所以某些高档的衣料自然可以看作是名贵的“花草”。《九歌·大司命》有言:“灵衣兮被被。”能够产生“被被”,即柔滑顺爽效果的材料,说明这种衣料材质应该十分柔顺,按照年代来推测,应该是丝罗等织物。在那个衣料以麻为主的年代,丝罗是非常珍贵的材料。
据考究,楚人信奉“生富养,死富葬”这句话。这一点也通过考古研究得到了印证。从目前发掘的一些楚墓来看,在楚国的墓葬中往往有大量的陪葬品,甚至在有些王族或者大贵族的坟墓中有奢侈至极的丝质棺罩。从这种墓葬风俗中,就可以感受到楚人十分看重自己的生活品质与质量,由此可以感知到其背后强烈的生命意识。
从楚国的“发国史”一窥究竟,自然就能看到为什么楚人对生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一种有些过于重视、甚至有些畏惧的生命意识。
在楚国建立初期,由于处于偏僻荒芜的地界,没有很好的自然资源与生存环境,导致国力微弱且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即使楚武王、楚文王励精图治,加强国力,仍然没能让楚国走向鼎盛。
《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记载到了楚武王、楚文王时期,即使楚国此时已经是相较为强大的时期了,但也仅仅只拥有几百里的土地。春秋结束,步入战国时期后,楚国就今非昔比了,楚国经历一代代的努力奋斗以及兼并作战,楚国就已经成为一个国土达到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了。其间的艰难可想而知,眼看着自己的国家由微弱发展到强盛,身处这个时代的楚人自然会产生对国家的强烈信心和骄傲。在这样的成果下,楚国人把自己的成功归结在了自己民族的优越性上,认为是上天更加眷顾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自然而然,楚人也相信自己比其他任何的民族更易于与大自然联系、与上天的关系也更亲密。所以,楚人在生活中越来越爱自己的祖国,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更多的权利去享受世界上的美好事物。这其中,也就包括了香草、奇花、美玉等等稀有的物品。
故而,追求高雅精致的服饰,是楚人生命意识的一种体现。这种生命意识来源于楚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和对大自然的亲昵之感。
(二)“巫”文化催生的浪漫气质
无论是在《九章》中,还是《天问》中,那些在天空中无拘无束,恣意飞翔的巨龙和神秘莫测,变化多端的神灵,都映射出了屈原那发自本源的独特想象力和浪漫主义风格。
除了屈原本人的因素,这些还来源于楚地独特的巫术文化。“当时徜徉在原始社会中的楚人,惯于用超凡的想象来弥补知识的缺陷。正是在想象中,他们成了火神的子孙,有了顶天立地的勇气和信心。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又熟悉又陌生,又亲近又疏远。”
在楚地,“巫”文化的盛行是有起源的。“巫”文化随着楚人的身份认知和实践活动自然而然进入了他们的生活。楚人自认为自己的民族起源于火神祝融,所以楚人对于来自南方“凤”的崇拜,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民族,这或许出自他们对于祝融“爱屋及乌”的崇拜心理。在这样的环境下,“巫术”逐渐变成了他们对于知识缺陷的补充,他们往往用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知识,用“巫术”作为自己了解世界的钥匙。与此同时,在楚人用巫术寻求知识的过程中,诞生了“祭祀”和“巫祝”这两种仪式。无论是“祭祀”还是“巫祝”,其实都是远古时期楚人表达对“未知”的神明,也就是自然规律的一种敬畏和崇拜,同时也包含了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这些仪式往往也伴随着原始的舞蹈和吟唱等活动。
屈原的《九歌》正是作为配乐为了这两种仪式服务的。故而,巫术文化中饱含的特有的浪漫主义元素和天马行空的瑰丽想象,自然而然地倾注到了《九歌》之中,也倾注到了屈原其他的作品当中。而这种浪漫主义的气息,不仅仅体现在文本语句上,更体现在精神内核上。
前面说到,楚人把“凤”作为自己的图腾,表现在楚服上,就在于楚人非常偏好“龙凤”的元素。从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一些丝绣品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许多“龙凤”的元素,如“舞龙飞凤丝绣品”,多以花草枝蔓来进行连接,龙凤形象在花草的点缀下,更加生动,更加形象。这种尊崇“龙凤”的思想也能反映,楚人希望自己如“龙凤”一般,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美好愿景,深刻表现了他们对于自由和摆脱束缚,飞升上天,脱离尘世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恰恰就是浪漫主义思想的雏形和起源。
另外,前文还提到楚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对礼制进行了突破,主要集中在色彩和款式两个方面。这源于楚人自由自在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叛逆心理。
《后汉书·礼仪志》有:“初,缁布进贤,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礼制对冠高是有所规定的。但是屈原却突破了礼制,他的“高冠”,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对规矩和礼法的突破。
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楚人的叛逆心理和向往自由的生活态度,同时也展现了他们生命中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浪漫气质。
(三)“香草玉饰”的高尚情操
是什么促使楚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这来源于他们本身带有高尚的情操。众所周知,屈原是一个爱国诗人的同时,也常常在作品里抒发自己对“高尚情操”的向往和追求,“纫秋兰以为佩”的道德要求,一直刻在屈原的作品里,即使他的作品,例如《离骚》《九章》表达了郁郁不得志的悲愤和无奈,但仍然不忘记表现自己对于世俗的厌恶和对“高尚情操”的不懈追求。
“纫秋兰以为佩”正是一种集中表现。楚地盛产香花和异草,楚服上的“花草”元素也十分常见,这是因为楚人一直有“香花为佩”的传统,所以佩戴花草也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在屈原这里,这个习惯产生了新的含义,屈原将自己对“高尚情操”的追求分配到了两个方面:诗歌的感情和香草的佩饰。
屈原通过“香花”和“恶草”的对比,成功做到了将自己和一些奸邪臣子对比起来,以对奸臣的厌恶表现自己对朝堂局面的不满,同时也反衬了自己高尚的情操。那么“玉饰”呢?《说文》云:“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才也;其声舒杨,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古人也经常以佩戴“玉饰”作为表示自己品德高尚,“玉”也逐渐以其温润通透的特质,成了君子的象征。而其实古人爱玉的传统,恰恰起源于楚人,楚人对玉饰的喜爱,体现了他们对内外兼美的要求。
总而言之,屈原《楚辞》中的服饰,不仅仅展现了他个人的文学创作风格和对高尚品德的追求,还展现了楚人筚路蓝缕的生存历程和生存处境,同时彰显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楚国文化。人们从楚国服饰的特点,进而感受到了楚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楚文化的深刻内涵,其中包括独特的生命意识、特有的浪漫气质、“香草玉饰”的高尚情操。《楚辞》反映楚文化,与此同时,楚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涵也浸入了《楚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本文以服饰作为一个切入点,从另一个方面感受《楚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浪漫主义起源特有的审美意境和文化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