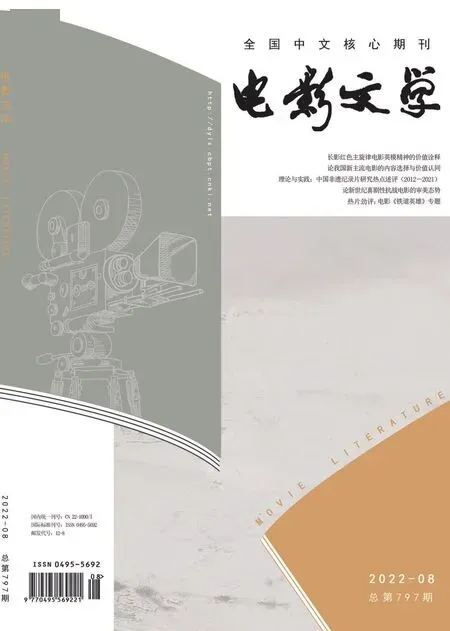《日光之下》的情感叙事机制研究
2022-11-01王雪徐桃
王 雪 徐 桃
(1.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海南 海口 571126;2.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一、后大片时代的地域空间与多元类型片创作
中国电影市场已步入后大片时代,产业化改革推动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多元化发展,雄踞票房榜首的不仅限于大制作影片,中小成本的类型片在近几年持续爆发惊人能量,一再改写中国影史票房纪录。在多元化发散创作思维作用下,诸多导演将创作焦点落在地缘电影上,地缘电影自带的视觉符号和文化景观从根本上给予影片以艺术个性和银幕辨识度,具有先在的受众优势。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和类型化创作逐步深化的当下,电影创作越来越朝向多元化发展,电影产量逐年增加(即便是在中国电影市场遭受疫情重创的近两年,国内依旧保持六百余部年产量),而风格化的美学表征成为作品突出重围的关键。东北电影凭借其自带的景观“光环”,具有强烈的视觉辨识度和银幕吸引力,审美风格优势的先在性使其成为诸多导演的创作热点,如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张艺谋的《悬崖之上》、刁亦男的《白日焰火》等,都是新世纪近十年出现的东北电影中的银幕佳作。《日光之下》是梁鸣的首部导演作品,是近年鲜少出现的东北文艺片,该片以犯罪悬疑片为“壳”,内部裹挟的是彻头彻尾的剧情片和文艺片内核。影片集中展现了少女谷溪无果的爱情和残酷的成长,细腻描摹了她的情感世界,谷溪身份的迷失和焦虑是推动叙事发展的动力源,也是她撕裂式成长的催化剂。
二、情感底色:东北原乡情结与个体精神还乡之旅
电影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通常是一次经验主义创作,会进行一次“向内”的自我审视,即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经验文本创作剧本,审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私有化的精神世界,用真实的个人经验最大限度地与观众靠近,寻找共鸣,实现共情,打动观众,打造一部真诚的作品。而《日光之下》所呈现的并非导演梁鸣的个体经验审视,梁鸣将故事背景定位到自己的家乡黑龙江省伊春市,将自己的浓厚乡愁蕴藏在极具代表性的东北地域空间当中,冬日冰冻的乡野小路,白雪覆盖的原野,黑黢黢的砖房,凌乱而随意切割着天空的输电线,等等。这些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景观组成了记忆中的故乡,导演借电影叙事空间(视觉空间)的塑造完成了一次个体意识下的精神还乡,同时,这些叠加了导演梁鸣个人情绪和记忆的视觉空间也同时赋予影片以强烈的作者性。
视觉空间的建构目标是为叙事服务。导演梁鸣对故乡视觉景观的选择、组合到最终呈现,是自视觉到知觉的还原和建构,视觉景观唤起的情绪、感受和记忆被带入故事情节的设计当中,什么样的故事段落设计安排什么样的视觉景观,都受导演的个人经验主义影响和控制。
人物形象设计同样如此,导演梁鸣记忆中的东北人是坚强的、乐观的,即便在东北发展远落后于国内多数经济发达省市的情况下,收入普遍偏低,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东北人依旧能够苦中作乐,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快乐,寻找积极生活的支撑点。谷亮兄妹只是小城镇上最普通的居民,每天都为了温饱、为了最基本的生活奔波,谷亮作为一家之长,四处寻找能够赚钱的机会,每天的生活丝毫不敢懈怠。而谷溪、谷亮和庆长三人第一次见面充满了误会和尴尬,第二次见面的三人又相见甚欢,个性洒脱的庆长被个性腼腆的谷亮戏称潇洒姐,谷亮和庆长酒后的忘我舞蹈,展现了东北人乐观和热情的一面,无论生活再不尽如人意,一醉解千愁。
除此之外,石油泄漏导致的海洋污染的议题作为《日光之下》的叙事副线,展现了导演梁鸣对东北故乡的人文关怀意识,石油泄漏导致的海洋污染问题不仅是一个环保议题,对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严重依赖自然环境生存的东北小城镇和农村居民来说,环境污染也直接影响了生存问题,人们会因此而失业,会因为没有收入来源而坠入底层生活的更深处,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像电影中出现的犯罪事件。即使影片《日光之下》没能更进一步地展开这个议题,但也反映了导演梁鸣先在性的乡愁情结对影片故事设计的导向作用,在以故乡为叙事空间时,其记忆中关切的问题都会慢慢浮现出来,最终汇聚成影片叙事的情感底色。
三、情感结构:亲情、爱情与友情交织的情感旋涡
《日光之下》是一部东北地域风格鲜明的艺术片,也是一部情感细腻的女性电影,影片既从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了谷溪的个人成长,也从少女谷溪的个人视角观察了成人世界。相对于海洋污染的环保主义的叙事主旨,以及由此引发的犯罪案件,情感才是电影《日光之下》描摹的核心和主旨,也是影片叙事的主要工具。
在《日光之下》悬疑片的表层之下是多重情感交织涌动的叙事结构。只有谷溪和谷亮兄妹二人的简单家庭单位中,亲情、爱情和友情多重情感交织,兄妹、父女、朋友、爱人多重身份组合,令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家庭变得复杂又特殊,少女谷溪在看似单纯的生活环境当中,经历的却是非同寻常的情感经历。对于谷溪来说,谷亮如父、如兄,在没有父亲和母亲角色出现的家庭成长环境中,谷亮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是照顾她生活、教育她成熟、辅助她成长的唯一的亲人,谷亮撑起了谷溪的天空,在少女思春的青春期微妙情绪心理变化中,谷亮又是她潜意识里的亲密爱人,是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谷亮兄妹残缺的家庭造成了情感结构的特殊性,谷溪始终生活在一个扭曲的情感旋涡当中,父母角色的缺失使她只能从哥哥谷亮身上寻找父爱和母爱的替代品,从她懂事开始,哥哥在哪儿,哪里就是家。片中家庭残缺的女性不止谷溪一人,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女庆长同样家庭不幸福,她的房间只有她跟母亲的合影,母亲角色的缺失,父女关系的冷漠,都让她十分羡慕谷溪能有谷亮那样的哥哥,庆长同样渴望亲密关系。
再单纯的少女终究要成长、要成熟蜕变为真正的女人。于是,影片将这场走向成熟的成长蜕变选在了这个多事的冬天,海洋被石油泄漏污染了,富家女庆长误打误撞地闯入了兄妹二人的生活,为了赚钱养家的谷亮参与了一场意外杀人案,谷溪的智齿也越来越频繁地疼痛,所有事情叠加起来激荡着少女谷溪的生活。《日光之下》架构了复杂的情感结构,谷亮、谷溪、庆长组成了三角关系,冬子作为谷亮的朋友,更像是一个入侵者,正是冬子给谷亮介绍的“工作”,才让谷亮卷入了犯罪事件,加速了谷亮和谷溪兄妹二人的分离,也让谷溪彻底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少女变成女人,这场成长几乎是撕裂式的。
四、情感旨归:自我意识觉醒、身份焦虑与分裂式成长
女性主义电影是21世纪电影的主流类型片之一,对于女性生存的人文关切深入叙事的方方面面,女性身体和心灵的成熟、两性关系、女性职场、女性权利等诸多方面成为大银幕主流话语,此外还有对女性精神世界、情感生活的深切关注。电影《日光之下》的叙事旨归是多维度的,不仅有对环境保护的潜在叙述,更为突出的是将少女谷溪置于镜头中央,将她对哥哥谷亮畸变的“兄妹情”以及她从少女快速长大的撕裂式成长过程完整呈现。《日光之下》中少女谷溪的成长与蜕变是被动的过程,虽然她在成长焦虑中想要通过寻求信仰的方式获得精神寄托和依靠,但最终发现哥哥谷亮已经是自己生命中的唯一信仰,她需要做出家庭关系与情感关系的两难选择。
(一)谷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谷溪从小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里,家里只有哥哥谷亮和自己两个人,哥哥就是她的全部。谷溪从未想过要长大,她在哥哥的眼里始终是那个小姑娘,她也不需要长大,她想要的哥哥都能给予。于是,谷溪的身体发育和心智成长呈现分裂状态。《日光之下》在叙事的推进过程中,不断用细节交代谷溪的身体已经成熟的迹象,她早已不再是少女了。一次,谷亮想拜托李哥给谷溪上户口,见面后对方惊讶道“还以为小女孩儿呢,都这么大了”,从旁观者的视角塑造了谷溪的成年女性形象;也有来自谷溪身体发出的信号——来月经肚子疼,表明了她的性成熟;还有谷溪那颗越来越疼的智齿,都表明谷溪的身体早已告别青春期,发育成熟,已经长大成人。可谷溪的心智没有和身体同步成熟,始终停留在小女孩的阶段,她在谷亮面前甚至是去性别化的,两人可以同睡一张床,现实正如二人中间的那块将床一分为二的纱帘,它就悬在那儿,但谁都不去扯掉,不说破现实。
可以说,谷溪过去的生活并不具备促使她成长、成熟的环境因素和条件,如果不是庆长闯入了他们兄妹二人的生活,她可以一直幼稚下去、偏执下去。然而,《日光之下》并没有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体成长完全归因于男性的启蒙,而是通过另一名更加成熟妩媚的女性庆长激发少女谷溪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促使她成长,向成熟女性蜕变。谷溪在庆长身上看到了自己不具备的成熟女性特征,庆长会戴着非常女性化的耳环,举手投足妩媚俏皮,甚至酒后可以不顾旁人的目光当众热情舞蹈,她比谷溪稳重洒脱,举手投足间透露着女人的妩媚。当谷溪觉察到谷亮被庆长深深吸引时,庆长身上的所有细节都被放大,并与自己比对,当谷溪潜意识下开始尝试模仿庆长,表明了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二)谷溪家庭到社会的身份焦虑
《日光之下》对谷溪的身份背景设定为没有户口的“黑户”,一方面她与谷亮缺乏基本的法律关系证明,成为“形式上”的兄妹关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谷溪在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上的缺失,是没有身份的个体,即她无法脱离哥哥谷亮独立生活,变相强制了谷溪对谷亮的依附关系。因此,影片一开始就交代了谷溪的社会身份危机——工作的地方对户口一事做出了最后表态,如果再没有户口就无法继续工作,这也意味着谷溪面临着失业危机,好不容易获得的社会身份岌岌可危,于是谷亮四处奔走为谷溪想办法上户口。随着谷溪的社会身份危机,她的身体也相应地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信号,隐隐作痛的牙齿潜在地隐喻着谷溪从精神到身体的焦虑和蜕变。
伴随传统家庭单位解体的是新家庭单位的建立,父母角色的完全缺失造成谷亮谷溪兄妹二人组建了新的家庭单位,对谷溪来说谷亮既是父亲,又是兄长,也是朋友。兄妹二人经历了漫长的共处时光以后,虽然谷溪始终是个不想长大的妹妹,但她也始终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家庭单位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梳理着两个人的关系。谷溪始终没有正视过自己的情感,在不断的模糊处理中,她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庆长的出现打破了原有关系的平衡,她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谷亮,另一名女性即将剥夺自己曾经专属的权利,甚至取代她的位置,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发生在谷溪社会身份危机的当下,这也意味着她可能同时失去全部身份,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于是,谷溪一方面与自己的老板建立联系,寻找保留社会身份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在想办法稳固自己的家庭身份。在原有家庭结构和情感关系被打破以后,谷溪急切地想要恢复原来的平衡。谷亮和庆长的关系日渐升温,谷溪内心的焦虑也在不断增加,她开始暗示庆长自己和谷亮的家庭关系的特殊和情感的和谐,“其实我俩长得也没那么像,他说他是我哥,谁知道呢?有时候他像个爸,不过有时候我也像个妈”“庆长姐,你还回韩国吗?”此时的庆长明白了谷溪的意思,沉默不语。
于是,谷溪的身份焦虑不断加剧,她亟须确定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身份、位置和权利,但她心里也很清楚她再也无法满足于妹妹身份。同时,没有户口又意味着社会身份的缺失,也代表着她无法脱离家庭身份,无论从生存角度还是情感角度,谷溪都对谷亮极度依赖。谷溪渴望获得谷亮爱人的身份,因此她假想过自己和谷亮不是亲兄妹,但这层身份幻想在加速崩塌。因此,谷溪的社会身份与家庭身份的危机使她的生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是她精神焦虑、扭曲和失常的根本原因。当她在被动中激发自我主体意识的同时,在认定自我生存价值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自我证明的过程被不断否定,这也直接激发了矛盾和危机的进一步深化。
(三)“爱与成长的智齿”:从肉体到精神的分裂式成长
《日光之下》在叙事动力的积累与加速推动上是十分成功的,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谷溪在成长蜕变过程中的内心挣扎和心理变化。谷溪的身份焦虑和情感焦虑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主要动力。当谷溪暂时保全了社会身份后,她急切地想要保住自己的家庭身份,而在她的思想认知里,家就是自己和哥哥组成的,他们既是兄妹,更是爱人。
谷溪越发觉得无法阻止谷亮和庆长关系的发展,谷溪的梦境正是她压力和焦虑增加的表现,谷溪在梦中参加了谷亮和庆长的婚礼,而所有人都看不见她,她成了透明人。睡梦中哭着醒来的谷溪扯出了作为证据的磁带,本想与现实妥协的谷溪却无意间撞见谷亮和庆长做爱的场景,彻底剪断了谷溪最后绷着的神经,摧毁了她仅存的与现实妥协的念头,也残酷地粉碎了她的所有幻想。因为,在谷溪的潜意识里她和谷亮是兄妹也是爱人,只是在道德枷锁下二人无法实现肉体结合,但精神早已融为一体,从她的角度来看,谷亮和庆长的性爱是对她纯洁爱情的彻底背叛。
始终拒绝长大的谷溪在性的刺激下实现了分裂式成长,甚至是迫切地想要成熟起来。于是,在谷亮的生日会上,谷溪疯狂地与身边的男性贴身舞蹈,当众朗读起黄碧云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中描述欲望和情爱的露骨段落,甚至对谷亮的朋友寻求慰藉。可以说,谷溪的情感变化完全控制了影片的叙事走向,伴随着她情感爆发和精神崩溃,叙事也被推向了高潮。
故事最终以谷亮被捕、庆长离开、谷溪落户结束。谷溪真正地失去了哥哥,失去了唯一的“爱人”,周围人如潮水一样退去,只剩下了她自己。至此,谷溪完成了精神层面的分裂式成长,而影片结尾谷溪用水果刀亲手挖出了智齿,也象征着她掌控自己身体、成长和蜕变的欲望和决心,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长大成人。谷溪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的焦虑,到精神层面的分裂式成长,呈现出女性成长的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谷溪细腻而丰沛的情感书写了爱情命题的复杂性。
对于东北独特的地域景观空间,不同导演都想通过构建景观符号,并赋予其一定的审美意义,从而借助这样一个具有银幕视觉辨识度的景观进行影像表述。梁鸣在导演处女作中利用东北地域景观空间,描摹了少女谷溪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情感成为影片叙事的全部。浅表层面以戏中人物的情感进行叙事,导演自身的情感也参与到了叙事当中,对故乡的情感,对故乡的眷恋,满怀东北原乡情结,尽情倾入影片叙事当中,汇聚成为影片的情感底色。
犯罪悬疑只是导演商业包装与多重叙事语境中的一环,推动叙事的并非推理式破案,情节的发展完全依靠少女谷溪的心理变化来推动,最终故事走向失控也全因少女谷溪的精神世界崩塌、精神失控使然。因此,案件最终的走向更加折射出谷溪毁灭性的爱情以及割裂式的野蛮成长,她的成长蜕变深受外力作用,影片结尾谷亮被捕,留下她独自一人,她只能与现实妥协,用刀自己挖出了智齿,用肉体的疼痛覆盖心灵的疼痛。
很难对影片《日光之下》做一个明确的类型划分,影片更像是国产文艺片惯用的融合类型创作与商业化设计,既有犯罪悬疑片的类型特征(犯罪剧情线),也有三角恋的爱情片特征,甚至贯穿影片始终的石油泄漏、海洋污染事件代表了影片的环保主义叙事立场,对多类型片特征的沾染使《日光之下》也表现出杂糅的艺术片特征。而影片以成熟的情感叙事体系塑造了谷溪的女性形象,架构了一场有着独特地域韵味的情感故事,有着别样的情感审美趣味。同时,《日光之下》作为导演梁鸣的处女作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青年导演在剧本创作上的集体问题,在商业意识渗透下,既想寻求商业利益,又想兼顾艺术理想化表达,结果往往会制造一部风格杂糅、内容混乱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商业与艺术夹缝中的集体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