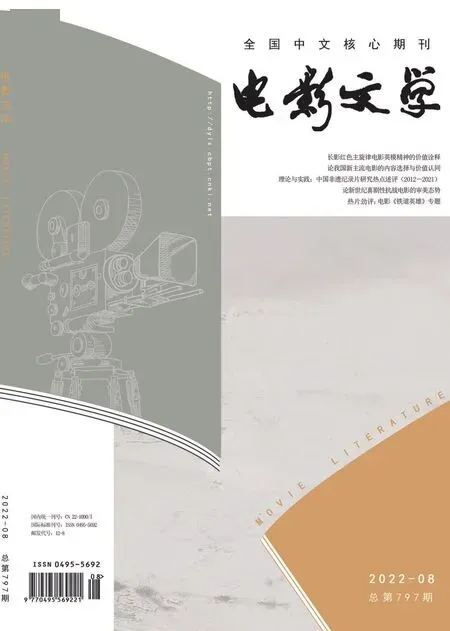论新世纪喜剧性抗战电影的审美态势
2022-11-01黄娟
黄 娟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艰苦抗战了14年,民族的心理创伤极深,所以,但凡涉及抗战的艺术作品,基本上离不开惨不忍睹的杀戮和大义凛然的牺牲。对电影作品来说,悲剧显然是抗战类题材的主流取向。但是,仍然有少数的抗战电影会运用喜剧性片段,或者直接就拍成抗战喜剧片。此类抗战电影大概滥觞于1992年张建亚导演的《三毛从军记》。这部影片没有完整统一的故事情节,仅以三毛的片断化经历为主要内容,讽刺非常时期“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的国民党政要,其间穿插了很多喜剧性片段。这些喜剧性片段和充满讽刺的黑色幽默都对后来的此类抗战影片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毛从军记》上映后,三四年间出现了好几部出色的抗战喜剧片,典型代表是1992年郭少雄、刘健魁导演,陈佩斯等主演的《迷途英雄》,1994年张建亚导演,潘长江、魏宗万等主演的《绝境逢生》(又名《老少爷们打鬼子》),1995年孙敏导演,黄宏、魏宗万等主演的《巧奔妙逃》。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类似的抗战电影并没有沿着它们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难简单地用“抗战喜剧片”来加以称谓了,而只能说是运用了喜剧性片段的抗战电影,即喜剧性抗战电影。下面就针对这种变化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对未来的展望。
一、审美上的两极趣味:严肃与戏谑
进入新世纪以后,不少抗战电影运用了喜剧性片段,但是,有的影片选择了早期抗战喜剧片中的讽刺方法构筑全片,虽然也运用了喜剧性片段,但那只是外在的工具,影片的内在意义是严肃、深刻而耐人寻味的,结局也并不美好,很难定义为喜剧片。有的影片则选择了早期抗战喜剧片中的娱乐方式构筑全片,大量使用喜剧性片段,却建立在丑化日军的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种漫画式的恶搞。因此,在审美趣味上,这两类影片大异其趣,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严肃与戏谑。
(一)严肃:深刻讽刺型
这种类型的抗战电影虽然运用了喜剧性片段,但其实是非常严肃的,它们并不以搞笑为目的;相反,喜剧性片段只是深化思想表达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有效手段,所以,风格上呈现为幽默与讽刺,充满了讽刺意味的调侃,令人深思。也就是说,它们主要通过将喜剧性片段形式化、工具化的方式解决抗战题材的严肃性与喜剧性片段之间的矛盾。代表作品是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2000)和管虎导演的《斗牛》(2009)。比如《鬼子来了》中马大三去找八婶子借白面那一段,八婶子猛一回头说道:“啥?白面?你看你八婶子像白面不?你吃我得了!”接着不理会马大三的赔笑,继续说:“这年头在家里私藏白面,那不是死罪吗?你不是要你八婶子的命吗?”针对马大三抱怨二脖子嘴不严实,她抢白道:“他把那话烂肚子里,那还是我儿子不?那不成了你儿子了吗?”这些语言配合演员的动作和表情,令人捧腹,却极为鲜明地表现了八婶子泼辣、犀利的个性。同时,这一段也间接表现了二脖子嘴不严实的毛病,并且从二人的抱怨中激发出搞笑成分,十分幽默。又如野野村队长天天带着队伍大张旗鼓地奏乐巡村、发糖,墙上贴着“东亚新秩序”,队伍后面却跟着一头不伦不类的驴,非常滑稽,前面的排场都是假的,后面来拉东西的驴才是真的。这显然是在讽刺日本人装腔作势、粉饰侵略的行为。还有突然发情冲上去与日本马交配的驴,几个村民慌神了,一边解释没有教过它,一边急忙拉开,场面滑稽,这与几个村民居然在日军炮楼底下把花屋小三郎禁闭长达半年的事实一样令酒冢队长十分难堪,这个插曲其实就是调侃,显然有影射事实、渲染效果的作用,很有表现力,堪称神来之笔。《斗牛》也是如此,或是从人物本身的个性中挖掘出笑点,或是借喜剧性片段深化思想,风格轻松却又不失沉重,耐人寻味。比如牛二偷喂自己的小黄牛吃奶牛的精料时说道:“你八路牛要有八路牛的样子吧?人家八路讲的什么,讲人人平等,牛跟牛就不用平等啦,到庄户人家了,就跟着吃点粗粮,吃点庄家饭,小黄啊,抓紧多吃点,不敢倒多了,别让人家看出来了。”然后,又偷偷地摸牛奶子说:“我摸不着九儿的,我还摸不着你的了。”这一段非常搞笑,却准确地表现了牛二自私、贪便宜还要讲歪理,粗鄙而又下流的特点。又如影片末尾牛二把祖传的银镯子戴在了奶牛鼻子上,解放军帮牛二写的“牛二之墓”被风一搅和,不认字的牛二把它们错拼成了“二牛之墓”,场面滑稽,却无比悲凉:爱人已逝,与牛为伍,人活得不像个人,虽生犹死,这就是侵略战争的反人类本质。所以,于此类影片而言,喜剧性片段只是一个外在的面具,真正的灵魂却是严肃而深刻的。
(二)戏谑:恶搞娱乐型
这种类型的抗战电影常常被人诟病,因为它们爱用巧合,主要通过丑化日军,恶搞日军来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风格夸张而又轻松。也就是说,它们主要通过让日军倒霉、丑化日军的方式消解题材的严肃性,从而解决抗战题材的严肃性与喜剧性片段之间的矛盾。代表作品是冯小宁导演的《举起手来》(2005)、《向我开炮》(2007)和《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2010)。比如《举起手来》之一中日军吃猪食的片段,郭大叔先后煮好了给日军吃的和给猪吃的食物,结果“我姥姥”弄错了,把做给日军吃的面条倒给了猪吃,而把给猪吃的食物分给了日军。虽然吃的是猪食,但是日军却只是觉得这味道有点难闻,仍然埋头大嚼了起来。日本人当然没有这么蠢,这显然是刻意地恶搞和丑化,包含了憎恶和唾骂日军的民族义愤在里面。与此类情景相对应,我方百姓在与日军斗争之中,或者机智过人、占尽上风,或者机缘巧合、化险为夷。前者如两个小男孩设置的各种门上机关,后者如日军打算炸毁出村的唯一通道——石桥之时,郭大叔阴错阳差地坐在箱子里跟着驴车上了桥,就在导火线即将烧尽的关键时刻,这头驴撒了一大泡尿,刚好把导火线给灭了。这些例子在整部影片中随处可见,观众除了轻松地爆笑之外,无须担心什么。在《举起手来(之二)追击阿多丸》中,虽然不再把日军刻画得非常愚蠢,剧情上甚至更多地体现了日军的狡诈,但是,仍然不乏各种恶搞和丑化,不乏我方机智而日方倒霉的情节设计。比如正当日本军官大佐炫耀自己的计谋,为了混过盟军的海上和空中封锁而伪装了这一艘伤兵船并一刀劈开自己的假石膏腿之时,那个身披三角形帐篷的罗圈腿日兵恰好从空中落下,挂在了桅杆上,这时候因为桅杆承受不住重量而摔了下来,刚好狠狠地砸中并压断了大佐的双腿,于是他不得不真正绑上了石膏。又如正当几十个日兵正在甲板上操练之时,郭大叔的孙女妞妞把电讯房的两极电线拉出来丢到满是水的甲板上,然后把电信房的开关推了上去,于是,这些日兵一个个被电得手舞足蹈。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所以,于此类抗战影片而言,重要的不是重揭伤疤,还原当年的真相,而是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爱憎和立场,通过恶搞娱乐大众之余,努力在14年抗战的痛苦废墟上重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未必是自欺欺人或自我麻痹,而可以是一种安慰与治疗,希望与期待。
二、审美上的两极姿态:进取与退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新锐导演并不满足于走前人的老路,他们有自己的思考与探索,虽然在抗战影片中运用了不少紧贴剧情的喜剧性片段,但从整体上又不妨碍抗战片的严肃意义,其特点是变奏,处理起来难度不小,很考验导演的整体把控力,然而,它们在风格的调和上却做得非常好,这很不容易。然而,也有些影片停留在机械地仿效前人,但又处理不好,只是简单地将喜剧性片段刻意地点缀在沉重的抗日题材之中,生硬而不和谐。因此,在审美姿态上,这两类影片截然相反,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进取与退化。
(一)进取:翻转变奏型
这种类型的抗战电影重在变奏,也难在变奏,它们主要通过翻转的方式达到喜剧效果与严肃的对接,构成格局上的变奏,风格既诙谐,又深沉。也就是说,它们主要通过变奏、翻转的方式将喜剧性片段处理为阶段性呈现,从而解决抗战题材的严肃性与喜剧性片段之间的矛盾。代表作品是宁浩导演的《黄金大劫案》(2012)和管虎导演的《厨子戏子痞子》(2013)。比如《黄金大劫案》的前半段主要是喜剧性的,以诙谐的方式展现了“街溜子党”小东北偷摸拐骗、吊儿郎当、油嘴滑舌,惯于抖机灵的生活,因为偶然获得了大和银行黄金车的消息而与救国会发生了联系,但他的目的只是捞一笔横财。这一部分喜剧性片段的运用并不浮夸,而是贴近生活真相的调侃。如小东北在敲诈了神父的钱财之后被五哥逮住进了警察局,他上交了一包钱,五哥说:“一块钱拘留,你这老些够判的了。”小东北赔笑着说:“不是,克星,你这不对呀。这一块是我的,其他不都是你的吗?上回出狱前我找你借的。”五哥回答说:“哦,对了,我把这事给忘了。”然后就把钱心安理得地揣兜里了。这显然是在调侃警匪一家、互通款曲的现实。还有对神父的刻画,着重展现他平凡而世俗的一面,消解了神父严肃而高高在上的意义,有很强的喜剧效果。同时,这些搞笑都不涉及日本人。虽然日本军官鸟山幸之助言谈举止颇有几分幽默,但那是笑里藏刀。影片的后半段,小东北经历了丧父之痛,又目睹了革命党在婚宴上惨遭日军杀戮,自己也九死一生,在茜茜的帮助下才逃过一劫。所以,后半段的风格大变,已经不是喜剧的格调了,而是一种悲壮、深沉的风格,背景音乐也揭示了这一变化。最后,叉子玫瑰变成了真玫瑰,“街溜子党”变成了革命党,无价值走向了有价值。这种翻转型处理喜剧性片段的方式,完全不影响抗日斗争的严肃性。与《黄金大劫案》的前后翻转型变奏不同,《厨子戏子痞子》是内外翻转型变奏。这个影片是讲几个燕京大学的学生如何智取虎烈拉病菌疫苗,拯救北平百姓的故事,包含了内外两种风格:一种是向外做给日本人看的戏谑而夸张的风格,一种是向内和自己人相处时的严肃而认真的风格。显然,影片里的搞笑片段只是这几个学生为了欺骗日本专家,诱使他说出疫苗配方而刻意演出来的戏。既然这些笑料被导演处理为智取的手段,那么与这几个学生所从事的抗日救国的严肃行为也就完全不冲突。所以,于此类影片而言,喜剧性片段本来只是任何时代凡俗生活里的必然片段,但是一旦有了抗日之心,那么它们要么成为过去,要么成为手段。它们事实上是严肃的抗日片。
(二)退化:简单点缀型
这种类型的抗战电影本意是想效仿20世纪的经典抗战喜剧片,但是又深受新世纪恶搞娱乐型抗战喜剧片的影响,结果是既没有达到恶搞娱乐型抗战喜剧片的漫画效果,又没有达到经典抗战喜剧片的高度,形成了一种在剧中点缀笑料的僵硬的风格,喜剧效果较弱,剧情假而空。也就是说,它们无法将严肃的抗日题材中的喜剧片段合理化,尽力消除可能给观众带来的违和感。所以,影片既不真实,又深度撕裂。代表作品是丁晟导演的《铁道飞虎》(2016)和崔志敏导演的《毒中毒》(2016)。比如《铁道飞虎》,演员阵容挺强大,但是主要人员满口的港台腔就已经不太符合普通的搬运工人设而容易让人跳戏了。在喜剧性片段的运用方面,较多与剧情无关而刻意织入的片段。比如搞炸药那一节,几个搬运工人叠罗汉,好不容易把同伴送上了墙,却发现不远处就有一个直达墙上的梯子;还有炸大桥那一节,当火车开到枣庄站日军例行检查山口队长已经发现有异样时,坂本翻译还有闲心在那里逗佐佐木站长笑。这些脱离剧情,纯属为了制造笑点而生的片段建立在将人物弱智化的基础之上,所以显得很生硬和突兀,最终影响了喜剧效果。比《铁道飞虎》运用喜剧性片段更僵硬的是《毒中毒》。其中笑点的主要承担者是日军队长,他的特点是随时没头没脑地、非常夸张地张大嘴巴狂笑,又疯又傻,比如在李老六带领下来到塔可世大院后发现桌上摆满了刚做好的菜团子,他就夸张地笑了很久,一边举起两个大拇指表扬李老六是“良民大大的”,一边又用手捧住李老六的脸挤压,同时拼命握住李老六的手摇来摇去,差点把李老六手里的枪摇走火。这个影片其实是一个悲剧,这样刻意地把日军队长处理为又疯又傻不正常的形象不仅很不合常理,而且也与剧情不匹配,喜剧效果很弱,呈现出一种在悲剧里点缀若干僵硬笑点的状态。虽然这些利用丑化日军的夸张表情和动作来搞笑的方式在恶搞娱乐型里早就用过,但后者是符合艺术逻辑的,在影片范围内的总体格调和人物设定方面是合理的、一致的。然而,《毒中毒》却把悲剧和喜剧生硬地拼接在一起,既影响了悲剧的严肃性,又影响了喜剧的效果,变得不伦不类。所以,于此类影片而言,喜剧性片段只是刻意为之的调料,用来点缀过于沉重的抗日斗争,其结果是走向虚假而让人哭笑不得。
三、展望未来:新世纪喜剧性抗战电影的三大方向
根据上述新世纪喜剧性抗战电影的审美态势,展望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顺应时代和艺术发展的需要,遵循“合适”的原则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人们对娱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娱乐、放松、无目的的玩耍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心理学和生理学上说,是保证旺盛的精力、刺激和强化活动能力所必需的。”恶搞娱乐型抗战影片正是基于这一需要应运而生,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舒缓压力、安抚创伤的作用。但是,一旦这种恶搞型片段被无限度地滥用,无底线地编造,那就很容易招致反感。所以,学术界曾一致对所谓的“抗日神剧”口诛笔伐,深恶痛绝。其实,早期的恶搞娱乐型抗战影片并没有那么不堪,也没有那么严重的负面影响。即使是“抗日神剧”,日本人看到也不以为然。“在日本民间,‘抗日神剧’通常仅被视为一种提供新奇场景与笑料的滑稽戏,或者是一种可归入‘特摄片’的军事题材喜剧。”这说明观众还是分得清历史与滑稽戏的界限的,更何况对历史的表述并非只有一个途径,也非只有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历史课堂就肩负了主要的教育责任,但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中国新生代,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还是有基本正确的认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让喜剧片来完成传播严肃历史的任务确实有些苛求了。正如冯小宁谈到电影《举起手来》时说的:“我觉得电影就是个大图书馆,而我这次选择的喜剧风格只是一本与以前不同的书。这就像人穿衣服经常换,但‘好看感人’的基本内容是不变的。这次我想让观众笑着知道,中国人民不可辱,你要是来劲,我们就收拾你!”可见,换一种艺术形式是艺术家们追求风格多样化或者说追求艺术挑战的必然选择。既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当然就遵循不同的艺术规律,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与评价。因此,那些以是否真实地反映历史来评价或质疑抗战题材喜剧片的意见,其实是失之偏颇了。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显然,文艺是提倡多样化的。抗战题材并非不能拍喜剧片,而是太难拍了,要注意把握好分寸。冯小宁就明确说过:“看看《黄河绝恋》和《紫日》,就会知道我的战争观是什么。拍《举起手来》对我是个学习。战争喜剧要把握分寸,参照对象就是《虎口脱险》,那部电影里德国法西斯就是傻瓜啊,《举起手来》这里日本侵略者也可以变成傻瓜,但不是说在历史上他们就是傻瓜,如果非要叫板,《虎口脱险》一无是处。”所以,顺应时代和艺术发展的需要,喜剧性片段在新世纪抗战电影中还是可以运用的,但是,要掌握分寸,遵循“合适”的原则。
(二)平衡喜剧与非喜剧的发展方向,丰富艺术形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运用喜剧性片段的抗战电影不少,但是,真正属于喜剧的其实很少。什么是喜剧?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正如前文所总结的,除了恶搞娱乐型属于真正的喜剧之外,其他的诸如深刻讽刺型、翻转变奏型和僵硬点缀型影片都并非喜剧,而是悲喜兼备的正剧。这种喜剧与非喜剧比例失衡的发展现状也并不奇怪,一方面因为抗战题材确实自带悲剧属性,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抗战题材就不应该拍喜剧;另一方面因为喜剧难拍,抗战题材的喜剧尤甚。冯小宁就曾经这样说过:“我从1990年就开始构思这部片子(《举起手来》),10多年了,我现在才动,是因为我觉得喜剧片最难拍,我必须有相当一段时间来积累我的艺术经验。喜剧就像一个在刀刃上的乒乓球,滚到左边是它的包袱没抖到位,滚到右边又过了,就成了胳肢人家,这个度很难把握,所以说,喜剧创作者拼的——是智慧。”他还认定:“战争题材的影片其实只要抓住‘正义感不可否定’这一点,就能站住。所以不必担心会不会不严肃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上的通达和艺术上的勇气,冯小宁肆意地拍了恶搞型抗战喜剧片。虽然剧情方面比新世纪之前的那几部抗战喜剧片逊色了一些(夸大日军的无能),但是喜剧效果十分显著,老百姓喜闻乐见,这种尝试也不失为对艺术形式的一种丰富,还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样的尝试并不多,这是不正常的。所以,郝建说:“也许是由于工具论的文艺观和实用的文艺目的论,也许是叙事上和哲学信念上所需要的权威性,革命叙事中的喜剧作品几乎见不到成功之作,经过时间检验能流传下来的一部都没有。在苏联和中国内地,革命文艺经常召开各种专家、领导参加的高级和认真严肃的研讨会来讨论为什么革命文艺中没有喜剧作品。专家、领导每次都要大声疾呼人民需要笑,革命需要喜剧,可至今革命叙事中还没有成功的喜剧作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文艺现象。”且不说成功与否,至少要给艺术家们创作的空间,鼓励艺术探索,那么抗战题材出精品,喜剧片才有希望。其实,新世纪之前的那几部抗战喜剧片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剧情曲折、合理,喜剧效果突出,只不过这样的抗战喜剧片在新世纪断档了,同一题材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艺术性呈现出不进反退的现象。所以,未来在抗战电影中运用笑料,要注意平衡喜剧与非喜剧的发展方向,丰富艺术形式。
(三)重视喜剧性与剧情的结合及多义性呈现,深化艺术效果
无论是喜剧还是非喜剧,抗战电影对喜剧性片段的运用都需要尽量避免走向肤浅和刻意的杂耍,这涉及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如果重视喜剧性与剧情的结合,让喜剧性在剧情的生发中符合逻辑地涌现,那么艺术效果会比简单、粗暴地刻意添加与剧情无关的笑点好得多。比如《巧奔妙逃》中著名的“弹棉花”的情节。剧中日本军官在国内的职业是小学音乐教员,所以热衷于收集中国乐器,误将老幺弹棉花的工具当作乐器收藏,在老幺他们被捕之后,精通日语的秦贵为了救大家将错就错,接住军官的话茬儿将弹棉花的工具指认为中国的单弦竖琴。在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痴迷于音乐的日本军官、耿直而操练老本行的老幺,灵活机变的翻译秦贵虽阵营对立,却个性鲜明、符合逻辑地上演了一场让人捧腹大笑的“弹棉花”演奏会。这种不违背性格逻辑、情境逻辑而自然衍生的喜剧性就是与剧情紧密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如果重视喜剧性片段的多义性呈现,让喜剧性片段不止步于笑,而是耐人寻味,那么艺术效果会比纯粹而单一的搞笑好得多。比如前面提到的深刻讽刺型和翻转变奏型当中的许多喜剧性片段,就不是单一的搞笑,而是既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又饱含影射的丰富内涵,呈现出多义性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单一的搞笑就毫无价值。朱光潜在《笑与喜剧》中说:“在大多数情境中笑都是一种游戏的活动,功用在使心境的紧张变为弛懈。笑有时是偏于情感的,仇意的诙谐和淫猥的诙谐都是要满足自然倾向。有时它偏于理智,情境的乖讹和文字的巧合都属于理智类的喜剧。笑是一种社会的活动,讽刺讥嘲的用意大半都是以游戏的口吻进行的警告。喜剧家大半在无意识中都明白这些笑的来源,把它利用在舞台上面,所以懂得日常生活中的笑,对于艺术上的喜剧也就能明白大要了。”前面提到的恶搞娱乐型影片中的喜剧性片段虽然主要是单一性的搞笑,但它们与剧情结合紧密,而且,显然就属于朱先生所说的情感类的笑,目的是“满足”“自然倾向”,其实就是一种慰藉了,那就还是有意义的。不过,饱含讥讽的理智类的笑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正如朱先生所说,“以游戏的口吻进行的警告”,那么艺术价值和艺术效果会更加显著。因此,喜剧性与剧情的结合及多义性呈现是喜剧性片段在未来抗战电影中运用时必须重视的创作要求,这于艺术效果的提升大有裨益。至于寻找这种喜剧性片段的难度,其实朱先生也给出了方向——“懂得日常生活中的笑”。这说明让创作回到现实生活中汲取养料,才是艺术创作制胜的法宝,喜剧性片段在未来抗战电影中的运用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