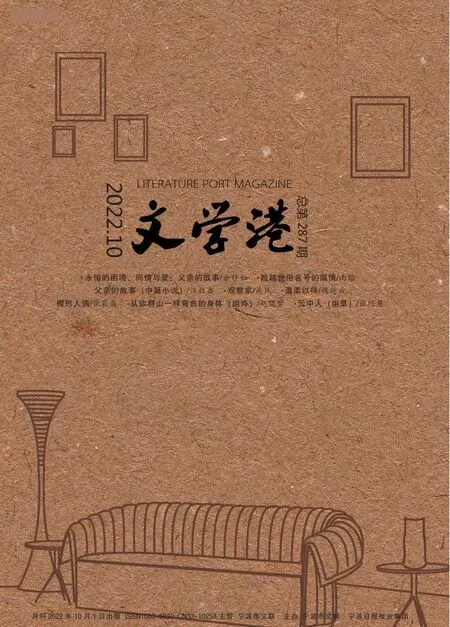白色,白色鸟
2022-10-27□安庆
□安 庆
我认识白色好像是从鸟开始。母亲拉着我,站在河边,河水流着,有几只鸟在河上飞,母亲指着鸟对我说着,那是白色、是白色的鸟。我和母亲一起看鸟,母亲一次次重复着,说着白和白色的鸟。我盯着鸟,那些鸟来来回回飞,像在配合母亲,让我认识它们是白色的。我在河边背着母亲的话,白——白色——白色的鸟……
整个下午我都在盯着鸟,它们让我入迷,有鸟儿飞走了,又有鸟儿飞回来,竟然都是白色的。母亲走向地里时,回过头叮咛,记住了,白、白色!母亲是去玉米地薅草,玉米棵打到了母亲的腰部,玉米叶在微风中轻摇。母亲让我守在河边,认识白色和那些白色的鸟。白色的鸟一直没有离开河道,或有几只飞走了,又有几只飞回来。河水一波波流着,水清清的,在水浅处我看见了卵石,从卵石的缝隙里钻出水草,水静处有鸟的影子。
后来,我发现了很多的白色,河水是白色的,河里的泡沫是白色的,喇叭花是白色的,芝麻花是白色的,梅豆花是白色的,云彩是白色的,羊是白色的,包括阳光都是白色的……多年后,我读到何立伟的 《白色鸟》,想起母亲教我认识白色,想起河滩上那白色的鸟儿。
在颜色里,白色首先长进了我的记忆。
我看见了很多的白,很多的白布。那时候我已经懂得了白布的意义,懂得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白色和白色的布。那些白成了村庄的气息,在村庄里弥漫,村庄里每年都会覆盖着更多的白色,出现很多的白布,白色的纸幡,穿着一身白衣的人在街上行走,集聚在一个院子里,从村庄走向村外的土地,白色浩浩荡荡,把一条街道,一条村路染成了白色。天空也是白的,白布一样的白。我不懂,一个人的死亡为什么一定要和白布有关,和白色有关?那意味着一个人的清白吗?怎么可能每个人都会清白?也许白色意味着空白,一切要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或许是说得通的,每个人在死亡的一刻要归于白色,归于空。我想起佛教里的“空”,白和空也许是相通的。从我懂事起,几乎每年我都会经历一次白事,甚至几次,都会看到很多的白色,很多白色的布。白,让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院子,一个村庄都凝重起来,都显得庄重。乃至现在,我匆匆忙忙回到老家,有时候也和白事有关,和家族里一个人的死亡,一个人的葬礼有关。白事,没有特殊的情况我是一定要回去、要参加的。这是和一个人最后的告别,和一个人一生的告别,是对死者对死者家人的尊重。尊重往往是要有仪式感的。
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家族,要做很多次的孝子。一个家族里有那么多长辈,祖爷爷、祖奶奶,爷爷、奶奶、叔伯,一辈压着一辈,总会陆续地有人离开,最后的仪式就是一场葬礼。我在白色里一次次感受着丧事的隆重,一次次为一个人,为一个成为亡灵的人穿上孝衣,一次次在白色里陷入回忆,关于逝者的生平,和逝者的交集。白布,往往是一个丧事上重要的开销。在奶奶的丧事上,我看见那个卖白布的人一趟趟地往我们家跑,三轮车上装着白布,车停在门口,他把白布一匹又一匹往我们家里扛,这个贩卖白布的人说他曾经在一家纺织厂上班,可以批到质优价廉的白布,所以他生意的范围主要就是白事。奶奶活了90 岁,单我父亲这一辈弟兄四个的家庭就有很多的孝子,还要加上我们整个的家族,管事的人说,奶奶的丧葬是近几年来用白布最多的一次。葬礼的前天晚上是路祭,在十字路口祭奠时,穿白色孝衣的人白花花跪满了半条街道。
几十年来我穿过很多次的孝衣,单是最近最亲的人里,就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奶奶,我的大伯,我的大娘,我的父亲……那些白色的记忆,让我无数次地落泪。母亲的殡葬遇到一个雨雪天,春寒料峭,雨雪交加,走在殡葬母亲的路上,我们的孝衣被雨雪淋湿,裹贴在身上,雨雪里带着寒风。我记得我的哭声在殡葬的路上回荡,一直从殡葬的墓地回荡到家,看到雨雪中狼狈的院子,空落落的家,母亲卧床的房间,我和妹妹的哭声再一次泛起。我的哭声那样痛,我捂着胸口,突然觉得没有了母亲的家失去了意义。我在哭声里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我不愿每次回来看到一个没有了母亲的家。可是我没有走得那么畅快,我的妹妹刚去镇里上学,母亲不在的那天早晨,是一个本家哥哥骑摩托车将妹妹从学校带回来的。还有父亲,我放心不下,不能如此自私仓促地离开,我在等待离开的机会。我不断地走向村外,自母亲殡葬的那个雨雪天后,天气渐渐转暖,我站在路边,远远地看着母亲的墓地,观察着母亲坟前那棵柳树的生长。在春天的阳光雨露中,柳树活了起来,伸出细小的嫩芽,柳枝上长出了嫩叶,嫩叶先是微黄的,慢慢地变成青色……就是那一年,在看着坟树长活,在对母亲思念的日子,萌生了写作的冲动,写出了我人生中第一首长诗 《母亲的坟树》 ……至于离开村庄,是在一年以后。
我想起一地的白,那是棉花,像一地白雪,大片的棉花地,白色的棉朵,无边的棉花棵,像一片森林。我孤独地站在一方棉花地头,不想再走,而后我扒拉着棉花棵,走向棉花地的深处,我要在棉花地里找到拾花的母亲。
母亲那天晚上对我说,我怎么可能在那样的棉花地里,还没有收过的棉花地是不能进不敢进的。可是,我就是想走向棉花地的深处,要往棉花地深处走,我想在那样的棉花地里找到母亲,凌晨就起床的母亲、出去捡花的母亲。我在那一方雪白的棉花地里走着,一地的雪白让我迷恋让我迷惑。说不清我走了多远,我最后钻出了棉花地,钻出了一地的雪白,我看到另一片棉花地,棉花都摘过了,棉花棵上偶尔闪动着残余的白色,像白色的孤独的蝴蝶。我没有找到母亲,回到家已是黄昏。我疲惫地坐在村口——北村口,母亲和那些大娘大婶一定会从那里回来,种棉花的县在我们村的北部。在夜幕里,我听见了疲沓的脚步声,我迎过去,母亲的肩上背着一个袋子,手里挽着一个小篮,这样的场景一直刻在我记忆的深处。母亲把捡了一天的棉花倒在了屋地,我看不到多少的绒白,更多的是棉花壳,壳里藏着残留的棉绒,我和母亲把那些棉绒从棉壳里掏出来,像掏着一个个贝壳。母亲还在一天天出去,在天晴的时候我们房顶上晒着母亲捡来的棉花,棉花在阳光中扑棱开身子,蝴蝶样在房顶上扇动翅膀。
有几年,我们家织布,相当多的棉花都是母亲捡来的。家里现在还放着很多年前的纺车,在我少年时代的很多夜晚,一双瘦弱的筋脉暴露的手在摇动纺车,母亲还偶尔哼唱着几句地方戏,纺车声和母亲的哼唱在深夜里交织,我在纺车和母亲的戏词里进入睡眠。一天夜晚,母亲给父亲讲着一个棉花地的故事,那个故事其实私下里已在流传,母亲的语气变得沉重:那是一个邻村女人的经历,她们在一起拾过棉花,那一天在一块棉花地那个女人落在后边,她走迷了路,误进了一块没有收完的棉花地,被一个男人抓住,那个男人扯住了女人的衣裳……她们听到了凄厉的嘶喊声,棉花地摇荡起来,十几个女人向着那块传来喊声的棉花地奔跑,她们找到地方时,那个女人还在精疲力尽地挣扎。一群女人冲向了那个男人,母亲和一个婶子搀起那个女人,帮她把衣裳穿好。那个女人挺起身,哭喊着,把篮子和篮子里的棉花朝男人摔去……我听见了母亲的讲述,那一刻我冒出的心愿,就是决不让母亲再去拾花。
一年春天,在一个村庄的庙会上,母亲突然在一个墙角站住,定定地看着人群里的一个女人,女人身旁还有一个女孩儿,她们在庙会上买什么东西。我们没有过去,母亲拉着我向另一个方向走。我隐隐猜到,那就是母亲讲过的那个女人。
时光过去,早已不是捡花的年代,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母亲离开我们都几十年了。
距离我在河滩上认识白色,认识白色鸟,三十年、四十年后,我的父亲又开始去苍凉的河滩上掘沙。说河苍凉,是近些年来河越来越旱,越来越浅,渐渐地断流成了干河,河沙早已被掘过几次。父亲不再像年轻时风风火火,他在河滩上悠闲地找着沙窝,打发着日子。有时候会挖出几担沙子来,也有一天一无所获。我不知道父亲要干什么,到底出于什么想法,他一天天在河滩上劳作,不强迫自己,干累了就坐在河滩上,坐在一片沙砾上歇息。他挖出的沙子找到买家是没有问题的,村里人要用沙子的很多,不断有正在建筑的房屋,如果谁家用几筐沙,父亲也会任他们拉走。父亲在河滩上日复一日地掘着沙子,他后来不再到处跑,从某一个地方连着掘,他掘出的坑越来越长,慢慢地连成一条水沟,河滩上形成一个狭长的水潭。那一年的秋天我回家,父亲告诉我,他看到了鸟——白色的水鸟。父亲继续说,好像是白色的水鸭,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父亲说,一天早晨他去河滩,突然在他掘出的水潭里看见了水鸟,那几只水鸟像是从河缝里钻出来,让父亲惊喜。父亲说,有水,就会有鸟。那天傍晚,父亲让我和他再回到河滩,我骑着父亲平常骑的三轮车,带着父亲。村外是大片的青纱帐,我们走到了河滩上,看到了父亲掘出的沙坑,沙坑边是他掘出的沙砾,沙坑里泛着浅水。整个河滩更多的是苍凉,野蒿在沙砾上生长。我和父亲坐在河滩上,等待父亲说的那种白色水鸟出现。天沉入了暮色,没有见到水鸟飞临水潭,父亲看看我说,的确是有过水鸟的,就是你最早看到的白色的水鸟,你妈教你认识白色的那种鸟儿。我看见父亲满脸的失落,我拉起父亲,我们回家吧,鸟有翅膀,今天它们可能飞到了其他地方。第二天,父亲又去了河滩,我知道他在等待什么。秋天的风刮着,河滩上旋出细沙,父亲望着他掘出的水潭,水潭的水其实是很浅的,望得见潭底;整个河床都是干涸的,不再是我当初看到水鸟的河流。也许有鸟偶尔落过父亲掘出的沙坑,也或许那是父亲的幻觉。
我知道父亲不能再掘沙了,那之后,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腰更加佝偻,他拄上了拐杖,一个人说老就更加老了。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单独过着,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0 多年。父亲开的荒地,交给别人家种了,至于他掘出的沙坑,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慢慢被风沙填平了。他偶尔还拄着拐杖去河边,去看他开的荒地,朝河滩上望,白色的水鸟终归也没有再飞回他的视线。
我看到更多的白色,我成为俯首灵堂的一个孝子,一身白色的重孝。这是我和父亲最后的交集,父亲在一天夜晚驾鹤西去。在他弥留之际,我听见一种低低的音乐声,妹妹一直在他的身边放着佛乐,为父亲超度。几天后,父亲殡葬,我在送葬的路上看到一路的白色,飘在空中的纸幡。白色鸟——我带着泪,朝天上望,鸟,白色的鸟在天空里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