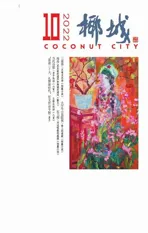生命追问与心灵治愈(评论)
2022-10-24辛泊平
◎辛泊平
这个假期,我重读了一些书,看了近百部老电影,虽然没有那种期待的获得感,但时间就这样静静地过去了。我喜欢这种近乎无事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看似松散无序的状态恰恰是生命最可靠、也最安逸的日常时刻。也是在这种状态下,我读到了阮敏哲的短篇小说《东南亚冰场》,读到了一种和此在并不同频的故事。似乎也是一种机缘,读这篇小说,我竟然想到了刚刚看过的电影《生之欲》。《生之欲》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作品,它通过一个身患绝症的小职员最终的人生选择阐释了生命的意志和价值,虽然是老电影,但很有现实的启示。
而阮敏哲的《东南亚冰场》也是关于生命意义追问和心灵治愈的小说,它的主旨和《生之欲》有太多的相似点。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名警察,只是,“我”不是我们期待的英雄式的人物,“我”没有感人的事迹,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我”的生命状态并不完整,更不饱满,因为女儿意外死亡,妻子离开了“我”;也因为女儿的意外死亡,“我”和母亲的关系近乎决裂。为了逃避,“我”选择了远离城市,而是自我流放到家乡的小镇。可以这样说,作为警察,“我”虽然也在履行警察的职责,但却没有热情,更没有激情。“我”的生命是残缺的,意志是消沉的,心灵是病态的。按照正常的人生逻辑,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没有热情、没有激情的“我”,即将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缺乏质量,更没有意义。
人生充满偶然,小说需要偶然。是偶然,让生命突破了惯性的方向和速度,有了流动的可能;同样,也是偶然,让小说的叙事走出了平淡,变得摇曳多姿、丰富多彩。在《东南亚冰场》里,也是偶然,让“我”走出了生活的阴影,和另外的人生遭遇,和另外的世界相逢,并在这种相遇中,扮演了心理医生的角色,从另一个维度上逼近了生命的意义与心灵的碰撞。没有铺垫,没有渲染,“我”就那样偶然地收到了奕铭的信,并通过这信进入了两个女孩儿的故事。和自己的女儿死于意外一样,奕铭的瘫痪也是源自儿时的疫苗事故,含之的无法参加舞蹈比赛也是源自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可以说,这三个“不幸”的人,正是因为这偶然的变故有了生命交集,也有了共情的条件。
奕铭之所以会选择“我”而不是其他人作为倾诉的对象,是因为她看到了“我”微笑的照片,而那微笑,让奕铭产生了信任感,让她有了倾诉的愿望。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们可以不相信身边的亲人,却因为一个微笑或者眼神,便可以向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当然,我们知道,这并非玄学,而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和情感寄托。不管怎样,这都是人生的积极意愿,它以可能让自己惊讶的方式打开自我,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信中,奕铭是敏感的,也是真诚的,她回顾了自己由健康到残疾的心理过程,回顾了因为自己的身体而引起的家庭变故,回顾了和含之交往并成为真正朋友的过往,在记忆中,往事虽然不堪,但也充满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坦然,充满了对亲情的理解和感恩。这是一个孩子对生命与人世的理解,却没有孩子的偏执和任性,而是多了成人的体悟与感受。正因如此,近乎自闭的“我”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干枯的心灵才再一次慢慢湿润起来。在奕铭看来,残缺的生命也有心灵的丰盈,带泪的人生也有动人的光泽。这种信念支撑着她,让她走过了短暂的人生暗夜,让她执着地坚守着人生的求索。
相对于奕铭的人生困境,含之的遭遇只能是一种挫折,它不构建人生的终极走向。然而,对于一个少年来说,这种挫折却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一种错位的认知,但却有可信的理由。孩子们缺少应对困境的心理准备,所以,一个小小的挫折便可以让他们对人生产生怀疑,对世界产生抵触。也正因如此,她需要一种共情的生命安慰,正如奕铭对她的影响和激励。健康的生命无法体验残缺的生命,因而也就难以进入那个残缺的世界。相反,残缺能够理解残缺,不幸能够包容不幸,痛苦可以消解痛苦。这是一种人生的悖论,我们无法超越,只能接受。
可以这样说,奕铭不仅仅让含之重新找回了自我,也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生命。这是一种相互的成就与慰藉。在这个过程中,力量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的、立体的。它让心灵治愈和生命意义的求索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和说教,而是有了现实关怀的温度和纹理。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除了含之,奕铭和“我”其实还在自我治愈的路上,他们必须继续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的生命现状,在心灵世界里与现实和自我达成最后的和解。这是日常问题,也是终极思考。正如小说的题目“东南亚冰场”所隐喻的记忆与未来——“明天的太阳总会升起,又是新的一天。”在我看来,作者这样处理是合理的,也是可信的,它有效地避免了那种理性主义的生命预设,让人物始终与大地平行,始终在困境中思考困境的本质与生命的出口。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相互关怀、相互惦念、相互激励的暖意中,所有人都会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发现自我,并确立自己在尘世与伦理中的存在与意义。
读这篇小说,我总是时不时想起史铁生,想起他笔下的人们。同样是残缺的世界和残缺的人生,同样是在残缺中寻找完整的自我,同样是让人心疼的坚守与希望,然而,却并不绝望,而是充满了生命的善意与期许。这是一种人生姿态,它可以残缺,可以隐秘,但因为那种守候和善意,让生命的力量与尊严得以彰显。在这篇小说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奕铭的父亲,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普通的男人,但他却以不平凡的付出和超出普通人的坚强,让这两个世俗角色都超越了自身的属性,拥有了神圣的光芒。他不是天生的强者,更不是自然的主宰,他说“脆弱,坚强,再脆弱,坚强,反复呗,谁的人生不是这么修炼的呢。以前她不怎么爱出来,敏感,觉得人家欲言又止,看她的眼神像看怪物,好像觉得她活不长。后来,那些眼神就更复杂了,觉得她是不是不会生育,不只同情她,还同情我们整个家庭。可去你的吧!我们过得好着呢!没有她,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坚强。”可以这样说,在陪伴奕铭成长的同时,父亲也在成长,在关照奕铭的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关照自我。在刻画父亲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作者内心的柔软,她用点点滴滴的细节,让这个背景人物有了清晰的刻度和可感可触的质地。
生命追问与心灵慰藉,这是一种哲学命题,但作者在叙事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而选择形而上的抽象议论,而是始终围绕人物的命运而展开,这是小说成功的前提。让人略感遗憾的是这篇小说的结构——书信与现实的转换还不够自然,两者的比重还有些失衡。所以,有些地方会出现一种“隔”,读起来不那么顺畅,毕竟,这不是纯粹的意识流写法,它的叙事脉络应该明晰,它的情节转换应该自然,这应该是作者的一种自觉意识。在人物塑造方面,作为叙事者的“我”还显得单薄,“我”对女儿意外事故的态度、对母亲的态度,都有点刻意和用力,不符合东方美学的语境和表达。让人物可信,让结构平衡,让叙事自然,这些,都是作者应该努力做到的,因为,它既是写作的起点要求,也应该是终点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