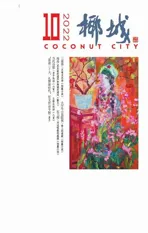冰火两极中的自我认定(评论)
2022-10-24◎阿探
◎阿 探
作为普通社会个体,或许精神会被不期而至的意外所击溃,然而作为人又不是那么容易被击溃的。正如《老人与海》所道“一个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于是从冰点到沸点,就是人之自我找寻与认定的过程。阮敏哲的短篇小说《东南亚冰场》,记录了三个被生活重创者的心路历程,曾经的“东南亚冰场”,现在的文化礼堂体育馆,既是“我”、奕铭与含之最终的精神交汇点,亦是世事变迁中情感缘起之地,生命所有感慨与重生亦在此一刻。
“东南亚冰场”是文本核心意象,它首先是一种变体的存在,承载着对过往美好时刻的不灭记忆,亦承载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它是起点,亦是终结点;它就是一个圆,是终点更是新的起点。它有着不同时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与内涵,它是人生起伏与沉淀的某种节点,它是小说主体叙事者生命过往与未来的链接点,是更是叙事弹性前后延伸的触发点,勾连起三个悲催的人生渐变。“枇杷树”则是小说的另一种见证性意象的存在,它标识着“我”的精神状态变化。
小说有着富于个性的内质构建,开篇第一句便勾连起了三个被生活重创者,即以他者故事的虚影钩沉起叙事者自身的故事。阮敏哲简单交代了不期而至的来信及写信者,以倒插叙事捧出最后的结果,并触及了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女儿。来信对于叙事者来说,是生命的一种转机昭示,甚至本身就是麻木生命的一种转机。叙事是套盒式故事结构,即“我”作为叙事者的故事中套着奕铭的故事,奕铭的故事中套着含之的故事。三个人原本并无交集的故事,通过奕铭写给片警的并非求助只为陈述的信件,有了自然而来的比对与共振,有着向阳光迈进的越来越清晰的路径。
奕铭作为因注射麻腮风疫苗而导致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人,是一个被社会漠视者,她写信投入片警便民点投口,是寂寥内心渴望被关注的行为语言。她是敏感的,从便民卡上片警的笑脸,感知到可以托付的信任。“我”因着女儿的意外坠亡,离婚,选择了离开伤神之地,从城关调到家乡东南派出所做片警亦有五六年,这是一种人生失神状态,亦即将所有的精力投入无边的警情零碎常态中,以期忘记深痛隐痛。X(奕铭)的来信只是在陈述,陈述了一个残疾的女孩去看另一位因车祸而受重创的女孩,陈述自己因打麻腮风疫苗致残的过程,亲人与父亲的关爱,以及认识含之。她的来信让“我”记起了曾经与她父亲的交集,她的父亲因她承受了难以承受的人生。奕铭让“我”想起不忍心去想的女儿,“我”看到了坐着轮椅的女孩奕铭和含之,去帮助她们报以微笑,并写信鼓励她。奕铭回信谈到了她与含之的交往,她们在彼此平等、尊重中成就了彼此精神。含之给予的帮助及其理想,奕铭鼓励了含之,含之也重燃了奕铭生活的信心而变得开朗起来。
“我”尽管可以在无尽的接警工作中冰释与遗忘伤痛,可以鼓励残疾的奕铭勇敢生活,却依旧无法面对丧女之痛,甚至对母亲的无心之过依旧无法释怀。“如果没有遇见你,多好”是妻子告别的最后一句话,她否决了两人的缘分。母亲电话告知前妻生小孩的消息,“我”电话祝贺,前妻指出因该向前看放下过往。奕铭再次来信说了含之通过了预赛、复赛进入了艺术节的总决赛的好消息,含之的进步又何尝不是奕铭的精神伸展呢?历经了文化礼堂体育馆(东南亚冰场)与奕铭及其父亲观看含之舞蹈的炫灿,“我”亦开始重新梳理自己的过往,东南亚冰场初始的恋情无疑是甜蜜铭心的。再次在医院里见到奕铭的父亲,“我”终于明白从奕铭坐在轮椅上时,她的父亲开始蜕变成一个精神强大者,在他精心的呵护中奕铭也成长为精神强者。含之的成功与离开,对奕铭心灵不可不谓一次重击,因为含之一直是她的精神同盟,是一种身边的精神鼓励者。即便如此,经历多年精神自疗的奕铭,在含之寄来的礼物中,在自己考试的优异成绩中找到了生命自信,以放远的眼光及拥抱未来的姿态,跨越了这短暂的精神幽暗,柔软的肉身承载起胜利者的胸怀。
奕铭与含之两个小女孩的惨淡人生中的精神逸出,奕铭父亲精神的蜕变,如同《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所体现出来的重度压力下的风度,无疑不舒化着“我”凝结与板结的心灵,在他人的故事里,“我”也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成熟过程。家中枇杷果落地,甚至滚到外面大道上,无疑是一种成熟的昭示。叙事者最后于女儿遗物——滑冰比赛第一名奖杯上“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一百零一次地站起来”的名言里,完成了与过往的最后释怀,并打算把奖杯与枇杷一起带给奕铭。文本在美丽的蝴蝶梦里终结,曾经远去的惊梦,醒来后依旧是太阳与新生。
小说以“我”,奕铭及含之精神嬗变的若即若离及相互作用,完成了冰火两重天下精神从羸弱到强大,从无以面对到坦然接受心灵动影的凝铸。奕铭的精神潜流,是由叙事者的精神流变带起的,它不仅伴随着叙事者的精神起伏,甚至说是它主导、促成了叙事者片警从悲痛的过往里完成了跨越。这大约就是阮敏哲文本构建的逆势而动吧,叙事者作为一个派出所的片警,他是一个成人,按说他的心理更为成熟,然而他依旧无法直面女儿意外坠亡的残酷事实。女儿没了,妻子选择了离婚,他选择了调离,其实无疑是一种主动规避事实的精神逃离,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无休止警情处理中,就是为了麻痹自己,为了遗忘痛苦。然而隐痛在不经意间会被触痛,最终在残疾女孩奕铭不知道给谁述说的来信阅读中,在与奕铭及父亲现场感受含之梦想成真的惊艳中,完成了对过往人生的梳理,完成了精神对过往的跨越与放下,终于找到了那个在长痛中迷失已久的自我。阮敏哲这种颇具个性的构建,无疑是成功的,既是丧女之痛入骨入髓的心灵阴影如黑洞无边际,更是精神隐痛难以跨越的心坎千万重。小说的构建目标完成度不错,叙事展开及推进如能更凝练一些则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