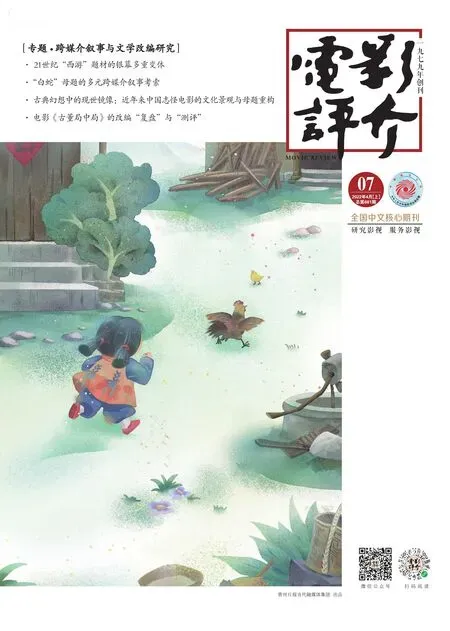《玩具总动员4》:一维特性、身份确证与主题诠释
2022-10-23龙星源
龙星源
《玩具总动员4》于2019年6月在北美和国内同步上映,它延续了前三部的成绩,继《玩具总动员3》之后再度获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奖。作为一部延续20余年的系列电影,其既保持了系列电影的风格,又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该片保持了“一维性特征”的单向隔阂规则,用相似的人物关系、故事框架稳定故事风格,塑造新角色、开展新冒险成就了系列故事的新生命力。与前三部影片形成了“差异性重复”,使观众在不割裂旧故事的前提下获得了新的观影体验,突破性的主题更引发了观众新的思考。
《玩具总动员》系列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 Animation Studios)出品的优秀的动画作品,自1995年《玩具总动员》第一部动画电影上映以来,就风靡全球。其人物形象独特立体,深入人心。接连四部情感充沛、情节刺激的冒险故事,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20多年的时光,主人公胡迪陪伴了无数的小观众长大成人,其深层次的情感内涵用童趣的文本模式输出更容易使观众获得精神上的独立成长。尤其是到《玩具总动员4》,“追寻内心声音”的哲学内涵更具有指路明灯般的深层次精神意义,不仅让主人公胡迪找到了未来的路,更使观众获得心灵上的触动。
在叙事风格上,《玩具总动员4》与同一系列保持了整体上的一致性,基本延续了“离家——人为障碍——解除障碍——巧合障碍——解除障碍——回家”的成长过程。不同的是,在第四部中,“回家”的结果变成了胡迪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也正是这一小小的变化,深刻地升华了成长主题,感动之余更引发观众无限的思考,将个体成长上升到了哲学命题,在变与不变中,深化了系列电影的内涵层次。
一、“一维性特征”
《玩具总动员4》延续了《玩具总动员》系列动画电影的叙事通则,即营造了一个“一维性特征”的叙事空间。所谓“一维性特征”即在幻想故事的世界中具有的“主人公对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感知并无差异,他不会对彼岸世界感到惊异”的特征。依据这一特征,《玩具总动员4》中所设定的动画人物活动世界的奇特性就合乎了叙事逻辑,给影片所营造的动画世界提供了特殊的叙事空间。
(一)单向隔阂的限域空间
依据“一维性特征”,《玩具总动员4》营造了一个具有单向隔阂的限域空间。其创造出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世界,即人类世界和玩具世界。人类世界是玩具世界的背景,玩具世界存在于人类世界之中又自成体系。玩具对人类世界了如指掌,而人类对玩具世界却一无所知。并且其所设定的玩具的任何行为、动作的变化对人类而言都处于无法发觉或忽略的状态之中,使得玩具世界对人类形成了一个无形中的单向隔阂。人类无法窥探到玩具的任何行为,而玩具却能够在人类世界中来去自如。这一特殊的设定给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提供了逻辑空间,使玩具的任何行为都具备了合理性。比如胡迪跟着小主人去幼儿园,从垃圾桶里捡拾材料给小主人;叉叉一次又一次地跳进垃圾桶,胡迪一次又一次地把它抓回小主人的床上;在游乐场里房车开走了而胡迪还没有回来,玩具们冒充导航把房车又带回了游乐场等场景,都是在“一维性特征”的作用下发生的。玩具能够改变人类世界的事物,而人类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二)童趣的拟人世界
影片中的玩具具备“人”的所有特征,按照人的行为逻辑表征方式生活,却又不失玩具本身的特征。在其所营造出的单向限域空间中,玩具不仅具备了生命,而且具备了人的思想、情感、行为、逻辑思考等能力,但这个拟人世界又很特殊,这是一个纯真、善良世界。玩具们看似具有逻辑性,却又不失童言童语,他们从小朋友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做出各种各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行,比如爱摆造型的潇洒公爵,为听从内心的声音不断乱按身上按钮的巴斯光年,一直把自己当成垃圾钻进垃圾堆的叉叉等,他们更像是一个个调皮捣蛋的小朋友。
热奈特将叙事视角用“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表述。“内聚焦”主要指“叙述者=人物”,即观众跟随某个人物的视角来观察、感知,叙述者只了解自己已知的事情,受主观意识的限制。皮克斯动画电影最常用的叙事手法即是“内聚焦”,影片将玩具们作为叙述者,通过他们的心理变化引起观众的共鸣。比如胡迪一次又一次地找回叉叉,不惜以身犯险也要从“二手玩具店”救出叉叉,正是出于他维护小主人的心理,而牧羊女宝贝则选择放弃舒适区,以冒险的方式生活,对于她而言更具有挑战性。正因为影片用了内聚焦的方式让玩具们不但以人的形态出现,也具有了“人”的心理状态,并且他们用真诚善良的方式去接纳朋友,包容他人的美好品格更容易被儿童所接受,比如即便盖比娃娃做了很多错事,但胡迪和牧羊女依旧选择接纳她、帮助她。影片正是抛却了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用儿童的方式,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童真的拟人世界。
(三)“人类”的叙事功能
人类世界在影片中处于背景地位,但又起到推动与促进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人类对于玩具而言,如同神话中的神,在单向限域空间的作用之下,玩具在人类面前只能被动接受,被人类的行为所影响,当玩具活动时一旦有人类出现,必须立刻进入休眠状态,成为一个“物”。玩具无法与人类沟通,不能与人类交流,却要在人类活动的限定下发生命运的改变。牧羊女宝贝被抛弃,胡迪被忽略,叉叉被偏爱,盖比娃娃被扔在纸箱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类的行为而发生的变化,“人类”不仅是背景板,更是情节的推动器。人类除了行为会影响玩具外,还会制造出种种限定,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戏剧冲突,形成紧张感,比如房车离开游乐园的时间即是对胡迪找到叉叉并返回的时间限定。
玩具们的命运受到人类的决定和态度的影响,虽然人类和玩具总体上延续了前三部的关系设定,但在第四部中,胡迪的小主人从安迪变成了邦妮,由于主人的变化,也导致了胡迪地位的下降,邦妮对胡迪需要性的下降正是胡迪追求新生活的先决条件。《玩具总动员4》在变与不变中使人物的成长产生了螺旋式上升,即保持了系列故事的延续性,人物关系的改变又产生了新的人物命运,甚至改变了胡迪作为玩具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在他的带领下,观众的内心也随之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二、童趣式身份认知:群体形象塑造
内聚焦的优势是观众能够跟着主人公一点点地去探索未知事物,并随着主人公的成长而发生心理上的变化,劣势则是观众不具备上帝视角,不能像零聚焦叙述者那样全知全能。影片以胡迪为主角,塑造了一群生动、可爱的玩具群体形象。作为一个玩具,自我身份认同直接决定了其行为、思考的方向,这也是影片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基础和前提。
(一)归属感身份认定
作为一个玩具,其社会属性即是陪伴小主人,拥有主人,给主人带来快乐是社会对“玩具”所赋予的社会价值,只有完成这一使命,于玩具而言,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人生”目标。《玩具总动员》系列影片中,胡迪等人不断对自己和别人强调这一点,并奉为圭臬,深入骨髓。在影片设定中,归属感的来源是玩具的鞋底上会写上主人的名字,通过鞋底的主人名字来确定是有主人的玩具还是没有主人的玩具,并且有主人的玩具显然对此十分自豪和骄傲,而那个名字,是他的归属,同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画地为牢”。
主人的身边是玩具们的“舒适区”,这里没有危险,需要做的就是让主人快乐,被主人需要、喜爱是玩具们的荣耀。长期处于“舒适区”的玩具们有一种被需要的认同感,他们将自己对主人的需要理解为主人对他们的需要,并觉得自己对于主人而言无比重要,不可或缺。当牧羊女宝贝被抛弃的时候,曾经邀请胡迪一起走,可是胡迪觉得主人更需要自己,不能抛下主人,只能和牧羊女分别,即使他万般不舍,也不得不忍受永远不能见面的分离。但是“舒适区”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有过一些冒险经历的胡迪和巴斯光年也并不能理解,他们对自己的认同是有主人的玩具,是被主人需要的玩具,这也是所有有主人的玩具伙伴的自我认知,至于是否“画地为牢”则不在他们的意识范围之内。
(二)弱势群体自我认知
《玩具总动员4》塑造了一个有趣的玩具群体,每一个玩具都有各自的特点,形象鲜明立体,饱满生动。与复杂的人类世界不同,他们的性格特点建立在明确的自我认知上,且没有复杂的心理变化,直来直去,就算是反面人物盖比娃娃也是坏得明明白白,自我认知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目标。
在玩具世界里,所谓的弱势群体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人类,玩具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自我定位就是陪伴主人,给主人带来快乐;相对于有主人的玩具,没有主人的玩具则是弱势群体,他们渴望获得有主人的生活,进入“舒适区”,过上安稳、快乐、温暖的日子;相对于胡迪而言,叉叉是弱势群体,他懵懵懂懂,面对陌生的一切以及强势价值观输出的胡迪他彷徨不安,只能以逃跑的方式来对抗。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叉叉,他是胡迪用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材料制作出来的,是一个“跨界”的存在。他不明白胡迪等玩具对主人的忠诚,更不认可因为邦妮的需要他就必须要留下的价值观,垃圾桶是他的“舒适区”,正如主人身边是玩具的“舒适区”一样,没有区别。当他意识到两者一致之后,就乖乖地回到了邦妮身边。叉叉的自我定位看似从垃圾变为了有主人的玩具,实则说明了他自我认知的是“舒适区”的一员,至于是垃圾还是玩具并不重要。
处于主流价值标准之外的边缘群体也有各自的自我认知,或清晰或模糊,游乐场里的兔哥和达鸭,作为投掷游戏的奖品而存在,两人相依为命,虽然向往有主人的生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游乐场里的自由;潇洒公爵曾经有过主人,被主人抛弃后,虽然有点神经兮兮,甚至陷入了自我怀疑,但在胡迪等人的鼓励之下,做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帮助大家摆脱了危机,于他而言,个人价值的体现是帮助朋友而不是取悦主人。
(三)对旧价值观的叛逆
如果说“玩具的使命是给主人带来快乐”是玩具世界的价值观的话,那牧羊女宝贝无疑是个叛逆者。《玩具总动员4》一开始,被遗弃的牧羊女宝贝就对来救她的胡迪说:“我不是安迪的玩具。”在牧羊女宝贝的心里,对胡迪所认可并遵循维护的价值观并不认同,她坦然接受被抛弃的事实。
牧羊女宝贝的经历丰富,有主人时她安心地做好台灯上的装饰品,被抛弃后坦然接受,被闲置在古董店失去自我最令她难以忍受,逃离古董店,冒险的生存方式让牧羊女宝贝更显得英姿飒爽。做自己才是牧羊女宝贝的自我认知,她不是别人的玩具,不是柜台上的商品,她有自己的世界,虽然充满了冒险和挑战,但作为一个战士,她无所畏惧。当牧羊女宝贝和胡迪吵架时,胡迪站在旧价值观的角度说牧羊女宝贝是lost toy,指她是被主人抛弃的玩具时,牧羊女宝贝则让胡迪好好想想,他是不是lost了,这是一个做自己还是别人所有物的问题,是是否遵守权威话语权的问题。
牧羊女宝贝是叛逆者,挑战者,却不是干涉者,她独立自主,选择野性冒险的生活,却并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当兔哥和达鸭想要一个主人而胡迪许诺让他们成为邦妮的玩具时,牧羊女宝贝没有干涉,当盖比娃娃想要得到一个主人时,她甚至还帮助了盖比。牧羊女宝贝尊重玩具们的想法和做法,她的包容和尊重给了玩具们自我选择的空间,也给了观众关于成长的思考空间。
三、追寻内心的声音:成长主题的打造
(一)对个体的尊重
《玩具总动员4》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玩具群体,影片给予了每一个角色充分的尊重,即便是配角,也拥有完整的成长轨迹。在《玩具总动员4》中,成长不是主角的专利,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小人物,小配角的转变描绘了一个整体成长的故事。兔哥和达鸭是影片中的小配角,他们本来渴望拥有主人,在古董店的冒险过程中,看见被猫掏出内胆的毛绒玩具他们恐惧了,害怕了,但是没有退缩,最终他们还是选择回到了游乐场,坦然面对甚至享受自己自由的生活。懵懵懂懂的叉叉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也从自我认同的垃圾成长为能够帮助伙伴的工具,当他完成伙伴交代的任务后,获得了新的价值体现。即便是反派盖比娃娃,影片也给予了她完整的故事线,最终放弃恶行,主动寻找自己的幸福,得到了美好的结局。在影片中,每一个小角色的丰富和完善都饱含着主创团队的心血,影片没有对玩具们的行为有褒或贬,如同牧羊女宝贝一样,充分尊重每一个玩具的选择,无所谓赞扬或批判,他们只是做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二)对人生的追寻
归属感是玩具们行为的出发点,或成为主人的专属玩具;或归属“垃圾桶”,寻求自我的“舒适区”;或成为自己的主人。无论是哪种归属,都是玩具在自身认识范围内所能做出的最利于自己的选择,玩具们在对归属的追求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这种归属的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玩具总动员4》中恰恰就体现了这种“变”。牧羊女宝贝遵循自己的意愿,成为自己的主人;盖比娃娃从无主人的娃娃变为主动寻找主人;潇洒公爵从被抛弃的不安变得自信;叉叉从自我认知模糊到对玩具身份的认同;当然变化最大的是主人公胡迪,从旧有价值观的维护者变为叛逆者,而这一切的变都是尊重了自己内心选择才完成的。
“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是《玩具总动员4》提出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命题。影片通过个体的自我实现过程完成了整体意义的提升,通过巴斯光年的误解不断按动身上按钮的幼稚行为使这一主题更带上了轻松幽默的童趣色彩。人生之路有很多种,变与不变全在于个人选择,聆听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声音,忠于自己才是自我实现的正确道路。
结语
《玩具总动员4》是一个冒险故事,也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影片全方位地呈现了一个弱势群体中每个独立个体的心理特征以及他们的追求目标。影片传递了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价值,牧羊女宝贝的出现,是对旧有价值观的挑战和反叛,她勇于追求自我、独立和自由,寻求自身的价值所在,在她的带领下,胡迪终于领悟到“追寻自己内心声音”的重要性,并最终获得了全新的人生价值。必须指出的是《玩具总动员4》没有从上帝视角批判或赞同任何一种价值取向,而是提出“遵从内心、忠于自己”这一简单又富有哲理的道理,用看似稚嫩的童言童语触动观众心灵,引发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