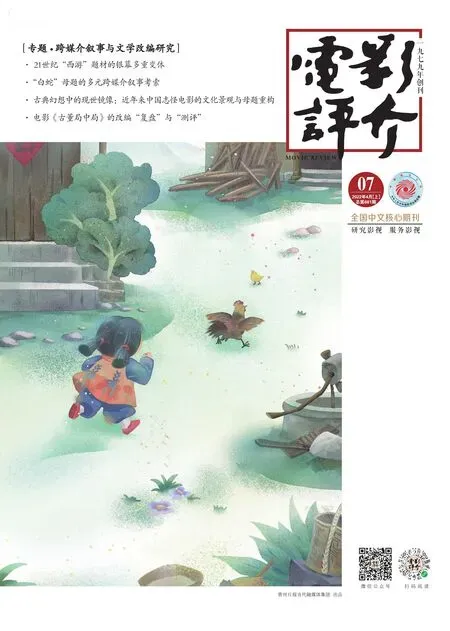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改编“复盘”与“测评”
2022-10-23任晟姝杨晓薇
任晟姝 杨晓薇
马伯庸擅长将史料文献与悬疑推理以及各类奇思妙想相融合,凭借独树一帜的“考据型悬疑文学”风格成为当下最为炙手可热的“头部作家”,其系列作品涉猎广泛,涵盖历史、推理、奇幻、灵异等多个领域,在跨媒介改编已然成风的市场语境下,成为被竞相追逐、当之无愧的“大IP”。截至2021年底,根据马伯庸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共有6部,包括:游达志、郑伟文联合执导的电视剧《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2018,改编自同名小说)、五百导演的电视剧《古董局中局》(2018,改编自同名小说)、曹盾导演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2019,改编自同名小说)、由爱奇艺出品,每日视界和霍尔果斯火天大有联合制作的动画作品《四海鲸骑》(2018,2019共两季,改编自同名小说)、谢泽导演的电视剧《风起洛阳》(2021,改编自同名小说)、郭子健导演的电影《古董局中局》(2021,改编自同名小说)。这些影视创作均选择了马伯庸在史料改写中“脑洞大开”并且叠加悬疑推理元素的原著进行改编,在延续文学内核的基础上,运用特定的媒介语言进行视听化的综合呈现。
电影版《古董局中局》作为马伯庸作品改编的第一部大银幕作品,首次将马伯庸文学“IP”在电影银幕之上进行了视听重构与创意表达,在电影改编的取舍与得失之间开启了“马伯庸电影宇宙”的布局和构建。
一、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改编策略“复盘”
《古董局中局》系列是马伯庸连载4册的“鉴宝悬疑”小说,被称为“古董界的百科全书”,该系列堪称马伯庸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之作”,自2012年出版以来广受追捧。2021年12月同名影片在全国公映,由曾经执导过《打擂台》《救火英雄》《悟空传》等影片的香港青年导演郭子健执导,演员雷佳音、李现、辛芷蕾、葛优等联袂主演。2018年《古董局中局》曾被改编为“网剧”在“腾讯视频”上映,累计播放量超过10亿,成为年度“爆款”作品之一,已有一定量的观众基础,该小说之所以能被二度影像化创作,足见其大“IP”价值和受众影响力。但电影版改编如何突破原作和“剧版”所形成的“既有印象”,成为一部既能保持“马伯庸底色”,又能打破视听定式、带给观众沉浸体验的电影,却仍旧面临很多的难题和挑战,电影主创团队在改编的取与舍之间,完成了第一次对“马伯庸电影宇宙”的创建。
电影版《古董局中局》仅截取了原著的一部分故事内容,主要围绕“武则天明堂玉佛头奇案”展开,从小古董店老板许愿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一场迷雾重重的古董江湖秘局故事。近几年电影市场中“盗墓题材”的影片屡见不鲜,但以古董、考古为题材的电影却寥寥无几。电影《古董局中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题材空缺,而郭子健导演在国内无甚同类题材作品可考的情况下进行改编,面临的挑战也不言自明。为此他特地邀请到亚洲最重要的古董经纪人之一、香港“永宝斋”的翟健民先生为古董顾问,深挖古董行业鉴宝细节。与此同时,剧组在拍摄中动用了30件真品文物以及数以万计的古董道具,还聘请了古董专家现场指导古董鉴定的相关台词、全程保证表演真实;全片的关键道具——武则天名堂佛头,更是采用3D打印方式,耗时7个月时间才制作完成,足见制作团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郭子健导演此番改编创作延续了其在《悟空传》等前作中所展露过的商业类型追求和超级英雄式的人物架构策略,将《古董局中局》定位为夺宝悬疑类型片,以“爽感”体验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灵活的改编,剧作上的大刀阔斧和视听语言的写意风格成为电影版《古董局中局》的改编实施路径。
在剧作构思层面,试图将如此大体量的小说容纳在两个小时的影像之内,必须对原著文本进行大量的取舍。若按照小说原本的叙事逻辑来编排情节,会存在诸多支线冗余,因而导演及编剧团队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开篇即围绕故事的“麦格芬”——“明堂佛头”展开,保留了主线情节,以“夺宝”驱动叙事,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在人物塑造方面,为了更好地带动观众进入角色理解和产生共情,导演及编剧团队重新定义了原著的角色内涵,强化或隐去一些人物细节甚至直接将多个人物特性合并在一人身上。例如,原著中的两位女主——木户加奈和黄烟烟(辛芷蕾饰演)本是平分秋色的笔墨描写,但在影片中木户加奈几乎成了背景,改编删去了许多关于她的情节,并将她身上的一些性格特质设定在了电影中唯一女主人公黄烟烟身上;影片改编对男主角之一的许愿(雷佳音饰演)也做出了一些调整,电影时长有限、不像小说可以用更多的文字细节去渐显许愿的性格特征和变化,电影必须在浓缩的有效时间里给予其更加鲜明的“人设”。因而,电影开场便将许愿呈现为一个穷困潦倒、吊儿郎当的颓废“酒鬼”形象,与古董界元老第一次会面就大出洋相,而这和原著的出场方式天差地别。随着剧情的推进,许愿逐渐明了自己身负着洗清家族冤屈的重任,不惜为揭开谜团、将生死置之度外,最终在饱满情感的积蓄中爆发出热血逆袭的英雄人格,而这种首尾颠覆的反差设计,也戏剧化地勾勒出了明显的人物“弧线”,人物性格反转的效果得到了强化;另一位男主人公药不然(李现饰演)在原著小说的第一部中着墨较少,导演借助香港类型电影中常见的“双雄对峙”模式,将药不然设定为与许愿势均力敌的对手,还将小说中药不然的哥哥药不是的性格元素附着在其身上,药不然表面上人畜无害、实际却野心勃勃,其亦正亦邪的身份属性,使得两位男主人公亦敌亦友,擦出许多对抗火花。此外,在人物关系的编织上,电影改编思路还刻意营造了付贵(葛优饰演)与卷入纷争的许愿、药不然、黄烟烟在代际关系上形成了“限定祖孙情”;四人各怀心事、分属不同阵营,却又在特定条件下组成了毫无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在嬉笑怒骂中形成了某种家庭温情。因而,最后付贵的舍命救人之举,对普通观众而言,或许成为全片最大的泪点。
在视听语言应用层面,全片最大的亮点体现在导演对动作戏的设计和视觉特效的构建。郭子健导演在采访中曾表达了他对原著小说的理解,他认为原著中存在着一股江湖气、很有武侠片的风味,这也是他最感兴趣的改编内容。在电影版《古董局中局》的视听语言实践中,郭子健导演创新性地开发出一套“文戏武拍”的视听手法,借用悬疑、谍战、动作、武侠等类型影片中常见的视听元素,将原本枯燥、术语晦涩的鉴宝场景转化为“擂台比武”似的视听桥段,将口灿莲花的古董鉴赏台词信息,视听化为观众更为熟悉、可观可感的动作场面,将语速语调置换为易于观影接受的节奏,从而形成了视听“通感”,使得乏味艰涩的鉴宝过程瞬间生动、刺激起来,令对古董知识知之甚少的普通观众也能充分地感受到鉴宝过程的紧张与兴奋。此外,影片中有许多特效设计也十分精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呈现是许愿和药不然二人十分钟比赛鉴宝的桥段。当鉴定乾隆青花云龙纹卷缸和赤壁图时,影片运用了视听特效手段营造出奇观氛围,将古器和古画的工艺手法化无形为有形,穿透表面、沁入结构,缸的釉色表现、盘龙的花色晕染、卷轴的绢纸构造、画面的立体山石都鲜活地浮现在观众眼前,影像大开大合、利落有致,带给观众极强的沉浸感。可见,电影版《古董局中局》的视听语言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马伯庸“脑洞”构建的古董奇幻世界,透过更为直观、通俗的视听手段,向普通观众展现了以历史文物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神韵与气象。
二、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改编效果“测评”
复盘以上改编思路可以发现,电影《古董局中局》正是通过“平民英雄”的人物设定、紧张刺激的视听节奏、不断加码的悬念冲突以及喜剧元素的杂糅拼贴等策略,来不断迎合观众对于“夺宝悬疑”类型电影的观影期待。然而,从后续口碑评价中却不难发现,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改编效果差强人意,据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进行的对2021年初冬档中国电影的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古董局中局》是调查对象中普通观众、专业观众的评分差值最大的影片(83.9/73.3)。如此两极化的观影反馈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引发对于该片改编效果的重新“测评”与创作反思。
首先,相较于《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题材影片刻意营造出的阴森诡异的“异世界”,考古题材电影《古董局中局》的优势在于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力图打造一个真实可信的古董世界,但这种尝试在改编过程中显然还是有些生硬的。贾樟柯导演在谈到电影中的“真实性”时曾说过:“电影中的真实性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一句,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古董局中局》为了“求真”虽然引入了诸多“货真价实”的古董,更聘请了鉴宝专家团队联合助阵,片中提到的“武则天明堂佛头”也的确有存在过的史实根据,但这些却依然没有为全片注入真实的质感。一部电影能否成立,最根本的依据应该是最底层的情感逻辑,这往往是电影创作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尤其是对于“悬疑解谜”类型电影而言,这类作品要求在有限时空内将纷繁的人物和复杂的事件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但在实际创作中常常会出现“人物服务于事件”的纰漏。电影《古董局中局》在改编中也浮现出同样的问题,错综复杂的解密情节并没有支撑起人物的复杂性,相反,一些人物仿佛“纸片人”,显得单薄又虚假,沦落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道具。例如,原著中黄烟烟与许愿的关系是有情感递进过程的,但在电影中,黄烟烟从一出场就被设定为许愿寻宝小分队中的一个得力助手,她对陌生人许愿给予笃定的信任和不离不弃的陪伴,即使家人大力反对,依然义无反顾地寻找佛头,黄烟烟的行为动机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违反亲情伦理的,很难令观众认同;葛优饰演的付贵就更加诡异,他在影片前半部分都被塑造为一个狡猾世故、见风使舵的小人形象,而最后的“舍身取义”就显得非常突然,与叙事主线割裂,主要原因就在于改编过程中对付贵与许家的“关系前史”交代不清,大多数观众只能感受到“煽情”,而无法真的“共情”。
其次,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改编失误还体现在它彻底动摇了原著故事的叙事立意和价值内涵。马伯庸曾在采访中表示:“民国是中国古董行当的一个大转折期。从反面来讲,乱世掠宝的行为愈加猖獗,达到高潮,出土了不少东西,但损毁湮灭的更多,实在是一大灾难;从正面来讲,这也是引入西方学术成果和科技的高潮时期,加上国人学者自身的努力,形成了现代意识的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建立起了现代考古的雏形框架,后世获益良多。我选择的这个故事背景,正是从大乱到大治的一个关键节点。希望让读者知道,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建立并非几纸政府公告那么简单,它是在混乱时世中顽强地生根、发芽,经过多少人的不懈努力,才成为保护文物的参天大树。”那些呕心沥血保护文物的先辈们,仅仅是出于对古老文化的热爱,便可以用生命去守护,只为问心无愧地说一句:“文物自前世遗下,经我而传,可至后世”。小说中,佛头虽回归了祖国的怀抱,但却有不计其数的文物在峥嵘的历史岁月里流失损毁,这也是国人心头一直以来一个沉重的话题。马伯庸期望通过“佛头一案”让观众窥见古董界前辈为了保护中国文物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中国考古百年来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原著中的许一城为了保全文物、精心策划了一场“局”,却被指控为“出卖国宝”,他便是这些先辈们的集合体和代言人,为了守护佛头、不惜背负“汉奸”的骂名,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而,许愿为爷爷洗清冤屈、踏上的寻找真相之旅应该是全片叙事的主线情节和价值归属,但在电影结局中却只揭晓了佛头是“假头包真头”的真相,对于许一城的其他计策却没有清晰的交代。这使得许一城这条全片最重要的故事主线被刻意模糊,严重削弱了原著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和价值内核。许多未读过小说的观众对许一城的设局动机依旧“一头雾水”,更无法体会到马伯庸作品的高深立意。此外,马伯庸还曾表示自己在书中最想表达的是六个字:“鉴古易,鉴人难”,古董江湖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各方势力的涌动纠缠本是作者在文本中所隐喻的重点。但改编过程中明显把动作戏作为全片的主要卖点,为了营造爽感、刻意制造笑料和煽情,尽管的确可以增加影片的商业噱头,却也削弱了原著中对于“人心博弈”的呈现,与原著叙事基调形成反差,将一场阴险狡诈、晦暗不明的古董连环局变成了一场夺宝、鉴宝的通关游戏。
最后,对于鉴宝过程的改编呈现也存在诸多遗憾。近年来,涌现了多档识宝、鉴宝以及与文物相关的电视节目,唤起了许多普通观众对于古董文物领域的兴趣。作为电影市场上少见的古董题材影片,《古董局中局》中的古董展现和鉴宝环节也自然应该成为影片的“重头戏”,原著中对于鉴宝环节有诸多精彩的描写。例如,姬云浮用指头在半空中比划出一个“元”字:“明代之前,本无‘原来’,都是写做‘元来’,比如唐诗《焚书坑》诗后两句为‘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再比如耶律楚材《万松老人琴谱》诗:‘元来底许真消息,不在弦边与指边’。后来朱元璋灭掉元朝,坐了天下,不喜欢这个字,这才把‘元来’换成了‘原来’。换句话说,这块石碑,最早也是明代的东西”,诸如此类的引经据典随处可见,诗词考据、金属灌注方法、古董的锻造技法、纹饰工艺以及有关佛教的概念和知识都在原著中有详细的记述,堪称是一本古董科普小说,其中知识“浓度”极高的新奇鉴宝手法,让书迷大开眼界。但在电影改编中却弱化了大量的鉴宝桥段,仅选取了几处鉴宝细节进行展现,其他全都靠演员“看”与“说”来进行叙事推进,而更失策的改编在于,影片高潮的解密环节被简化成了一场综合运用摩斯密码、铜金拼音密码、墓穴探险技巧的密室逃脱游戏,原著的风韵和文雅荡然无存。
三、“马伯庸电影宇宙”搭建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改编“测评”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客观而言,马伯庸的作品极具电影改编潜力和市场转化价值,“马伯庸电影宇宙”搭建的可行性依旧极高、值得期待。
马伯庸一系列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对于“历史可能性”的书写和自成一派的“考据型悬疑文学”。基于对历史进程的宏观把控,其作品在保持历史真实要素的同时,利用历史中的小人物重构历史细节、展现时代变迁。马伯庸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把故事镶嵌进历史的缝隙中,跟各路如雷贯耳的名人都发生那么一点联系。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感觉,俗称‘戴着镣铐跳舞’。情节是虚构的,但大环境却是真实存在的。而情节往往又对真实的历史产生了推动力,重新解释了一下历史”。大时代、小人物、深切口是马伯庸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这种基于史实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阶段方寸间的截取与深挖使得他的作品有着稳固的支撑、呈现出浓烈的历史质感,而他“恶搞”、戏谑的语言风格和扑朔迷离的悬疑营造又使得故事扣人心弦且独具解构色彩。悬疑考证和阴谋造势可以说是马伯庸小说的标识性元素,他擅长将读者引入其设下的一个又一个圈套之中,令读者在风声鹤唳的情绪之中感受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因而,从剧本开发的层面考虑,这种情节编排方式比较适合进行悬疑类型电影改编,惊心动魄的间谍行动、诡诈权术的营造和拆解都是制造剧作“爽感”的利器,也很符合当下受众的心理接受度和市场需求,再依托坚实的历史支撑和深厚的文化内核,使得马伯庸的作品在进行影视化改编方面有着天然的故事优势和“IP”含金量。
马伯庸的作品极具改编可行性还得益于他的写作风格有着明显的影视化思维。首先,他的作品在文本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影视化趋向,情节环环相扣、矛盾逐渐激化、危机不断升级、故事脉络清晰有序并接连不断地为观众提供惯性思维之外的新鲜感和意外感。马伯庸的代表作《长安十二时辰》与美剧《24小时》的剧作手法和布局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将纷纭复杂的历史信息浓缩在极短的时空内,讲述了发生于唐代上元节这一天24小时内的长安城中暗流涌动的故事。时间的限制、空间的封闭和“党争”“追凶”的双线推进,使得整体叙事一直具有一种“箭在弦上”的危机感。这种刻意压缩时空、设置极端情境的方式,在类型电影中比比皆是,可以有效地增加剧中人物的困境压迫感,令观众激发强烈的剧情参与动力。其次,马伯庸在创作时常常将蒙太奇思维应用在文字编织中,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会无意识地在脑海中转化为相应的视觉画面。例如,《长安十二时辰》中《巳正》一章对大唐国家安全机关靖安司的出场这样描写到:“曹破延并不知道,他和崔六郎的这一番小动作,被不远处望楼上的武侯尽收眼底……看到崔六郎的手势,一名武侯直起身子,拿起一面纯色黑旗,朝东方挥动三下,并重复了三次。两个弹指之后,望楼东侧三百步开外的另外一座望楼,也挥舞起了同样的黑旗;紧接着,更东方的望楼也迅速做出了响应。”这一段文字描写从两个反派的小动作特写镜头,切换到远景的望楼,继而又到达更多的群楼。一连串景别的切换镜头,将望楼系统的全貌完整地延伸了出来,也把靖安司的神秘面纱逐步揭开,如同电影的分镜头剧本一样为读者勾勒出生动的视觉画面。
结语
马伯庸凭借其独特的文风促成了其“作家IP”的巨大影响力,他的影视作品改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更为严苛的观众检验。第一部电影改编作品《古董局中局》虽有瑕疵,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凸显了“马伯庸电影宇宙”搭建的可行性以及风险性,为之后系列作品的改编创作提供了重要的“靶向”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