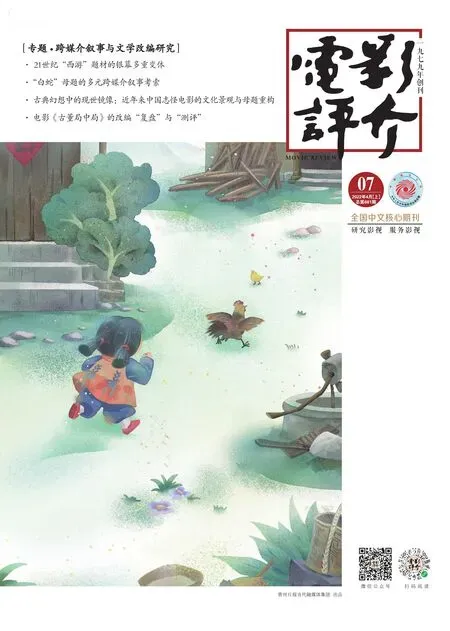古典幻想中的现世镜像:近年来中国志怪电影的文化景观与母题重构
2022-10-23李延睿
徐 爽 李延睿
志怪电影可以溯源至封建社会民间广为流传的志怪小说,基于作者的主观意志与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神话、寓言与史传进行细节处理和戏剧化加工。从口耳相传到案头之作,志怪文化始于世俗兴于世俗,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再生于世俗。从早年间《聊斋》系列的影视化改编到近年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影片的爆火,志怪电影逐渐发展成型,成为了一个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极具民族特色的类型电影。2020年的动画电影《姜子牙》累计票房超过了16亿元;2021年春节档《侍神令》上映首日收获约8212万元票房,单日票房排名第4。由此可见,志怪电影在依靠视觉奇观加持的同时,必然要经历向内的自我探寻与重构。
一、内涵与外延:志怪电影的概念廓清
志怪作为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其出现要远先于志怪小说,但小说摒弃了“志怪”作为一种记录活动的细大不捐,凝练怪异之志核心的戏剧冲突于文本。
(一)从小说文本到银幕再现:志怪电影的滥觞
“志怪”与“小说”二词最早均出现在《庄子》中。《逍遥游》提到:“齐谐者,志怪者也。”从“齐谐”的概述来看,志怪多为怪力乱神之事,风格奇崛罕见。《物外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彼时的“志怪”作为一种自发的记录活动,其动名词属性使之并不能与六朝时期的志怪文学相提并论,汉代桓谭在自己的著作《新论》中提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知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由此可见,小说的“近取譬论”与志怪在行文上的特性几乎如出一辙。《庄子》将“小说”和“大达”对举,等同于默认了“志怪”与“小说”的世俗血脉。受奴隶社会祭祀习俗的影响,先秦典籍中也不乏关于巫蛊神怪之事的载录,史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书写原则使鬼神之事并不为当时世人所疑,也为后世志怪小说的“考先志于载籍”提供了原始的素材。
脱胎于志怪小说的志怪电影诉诸人类社会现世的道德批判于虚构的志怪图景中,因此其社会背景大多为粉饰太平或是政权更替的封建王朝。“正统”的失落给了江湖之崛起以可乘之机,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清明盛世会有巫妖祸乱、派别割据的局面。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从而让志怪小说以本身的情节之惊险离奇加上巷说闾谈的世俗言说,使其无论是静态的文本呈现亦或是动态的银幕表达都无法摆脱想象与视觉上的奇观,正因如此,志怪电影的叙事“在极端的状况下有可能成为奇观的附庸”。“奇、险、急、满”的情节借助悬疑、惊悚的类型为外衣,为鬼市,易容术、蛊毒等志怪元素提供了合理的出场空间,小说中所志之“怪”在CG技术和特效镜头的加持下以现代审美复现,刺激着观众的审美体验,也使志怪可以以电影为载体逐渐摆脱“旁统”的标签。
(二)“怪”之异同:志怪电影的地缘特性与基因谱系
志怪电影之“怪”是典型的东方地缘文化的产物,多取材于神话、寓言或史传等。如《捉妖记》中妖王胡巴的原型是《山海经》所录传说中的六足怪;作为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的《白蛇传》在2021年成为跨媒介改编的热门题材;而《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姜子牙》则是将史料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或故事对其进行了夸张化的处理。这些具有东方面孔的“怪”同样也在诉说着东方秩序——首先是儒家思想中亘古不变的“忠孝仁义”。以2019年创下多项票房纪录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李靖豁出性命镇守陈塘关为臣子之忠;哪吒舍己救父为孝,为龙族留生路为仁;敖丙为压制哪吒魔性,拯救李靖夫妇从申公豹手中拿走乾坤圈为义。而“义”字当头的江湖精神在早期武侠片中特为尤甚,以中国文化的传奇故事为蓝本加入传统武术技巧“天外飞仙、剑光斗法、隐形遁迹、口吐剑、掌心发雷”等元素的武侠电影可以说初具志怪电影的样态。时至今日,激烈的打斗场面和江湖文化仍然宰制着志怪电影的视觉奇观,从《火烧红莲寺》到《倩女幽魂》再到《侍神令》,志怪的崛起并没有迫使武侠退位,反之在新的东方话语体系中共生共荣。
志怪电影的形骸之下是儒、释、道三教的耦合,作为近年来中国志怪电影的“对照”,西方魔幻电影中的多神论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魔幻电影源于“两希文化”语境下的欧洲文学,汇聚了西方传说和骑士文化中的魔法、巫术等元素。不同于儒家的“忠孝仁义”,希伯来-基督文化更主张“自我救赎”——《指环王》中的弗多罗抵抗咕噜的诱惑,护送魔戒到末日火山的过程是对欲望原罪的克服;《霍比特人》比尔博在索林命悬一线时的挺身而出是一次对价值判断中刻板印象的完胜。但希腊文明的多神论使得魔幻电影几乎很难看到诸神中有“一家独大”的现象,“漫威宇宙”和“DC宇宙”就是最好的证明:人人都是超级英雄,却很难在绝对实力上一争高下。而2010年路易斯·莱特里尔则直接将以希腊神话为原型的《诸神之战》搬上银幕,人类与国王、国王与诸神、人类与诸神的战争近乎是一场浩劫,冥王神哈迪斯即将获得宙斯的力量,而征服冥界禁地的帕尔修斯兼具神性与人性,如此一来究竟哪一方拥有绝对的统治力量又显得扑朔迷离。由此可见,魔幻电影集古希腊宣扬的“和谐”与希伯来追求的“超越”于一体,神神狂欢作乐,人人向往天国。
尽管在地缘文化上的差异客观存在,但志怪电影和魔幻电影多神的背景有着相同的触媒——即对“人”的投射。“志怪”与“志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孪生关系,鲁迅在划分六朝志怪时提到:“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提及《西游记》时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以《聊斋志异》为例,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异类皆具人性,《婴宁》一篇是典型的明清所盛行的才子佳人故事,但明眸善睐、顾盼生辉的狐妖婴宁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更视庠序之教和孝悌之义如无物,这与当时主流价值观中的“佳人”形象大相径庭。而《画皮》“披人皮的厉鬼”的设定更为直白,一切厉鬼作乱或狐妖魅人都是人世的恩怨嗔痴、因果轮回的隐喻。进行了多次影视化改编的《西游记》尤为明显,《西游·降魔篇》在师徒四人的祛魅上再接再厉,直接新增了玄奘和段小姐的爱情线,通篇强调“去除心魔”;《大话西游》对于孙悟空的改编是颠覆性的,“斗战胜佛”为了爱情不断在人性与佛性之间游走。而古希腊神话区别于其他神话最关键的特性是其“神人同形性”。宙斯泛爱,赫拉善妒,在以血缘为纽带组建的父权制家族中,诸神皆有人性最原始的爱欲与性欲。“DC超级英雄”中的神奇女侠被直接设定为天神宙斯和亚马逊女王希波吕忒的女儿戴安娜,取得了奥林匹斯众神赐予的武器与装备来到人间拯救世界,并和史蒂夫·特雷弗相爱,影片中的战神阿瑞斯也以帕特里克爵士的身份出现,一战人间浩劫的背后实质上是神界的角逐。
由此可见,无论是东方美学体系下的志怪电影还是“两希文化”映射下的魔幻电影,对人的批判并非是对于怪力乱神表征的“祛魅”,反之人即是怪,怪即是人,怪的种类特性之纷繁无异于人性的群体差异。同华夏民族有着黑头发黄皮肤讲汉语的特性一样,志怪电影也是民族价值传统的产物,因地缘特性而独具东方面孔,因文化亲缘与“人”的隐喻相伴相生。
二、国族神话与现代寓言——志怪文化的影像解码
志怪电影借鉴了小说的情节与想象,传统神话、寓言的猎奇狂想为电影提供了奇观的素材,但志怪文化从小说走向电影并不能在纯粹的叙事场域中完成,必须加以类型化的辅助和价值体系的升华。
(一)志怪图景:国族神话的类型化表达
文学层面上的志怪小说最大的特点便是“奇崛”,妖异之事或恐怖或离奇,或凄惨或惊险,表现在电影中都是视觉上的“奇观”。奇观在拉丁文中意为非同寻常的或与习惯相悖的视觉经验特征,以好莱坞为首的西方魔幻电影率先利用得天独厚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将想象力转化成视觉文化经济的重要来源,制造出视觉上的狂欢刺激着观众的审美体验。志怪电影作为“吸引力电影”的当代重要类型也在影像美学上不断追求异质化、极致化——猎奇狂想成为“眼球经济”的重要元素,挑战着观众的视觉神经和审美传统始终占据着影片的画面,譬如妖猫杀人、李太吃婴胎饺子、饕餮大军围攻长城等等。志怪电影运用大量奇观化的镜头打破了“静观的美学”,同时制造出宏大的场面“让电影回归视觉艺术本体论的层面去”。玄幻情境在宏大场面的加持下拥有了视觉上吸引观众的卖点,观众很难不为《妖猫传》的唐宫夜宴所震撼,也很难不对《寻龙诀》鬼门关的遍地骷髅和萨满僵尸产生恐惧。但观众喜爱、震撼与恐惧的感觉,“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上看,对‘奇观’的渴求与人的破坏本能、嗜血、野蛮本性紧密相联,是人性里‘变态’一面的反映。”诡谲审美下的叙事范式是志怪电影向类型化的迎合,但这个过程也容易矫枉过正。以2018年上映的《阿修罗》为例,“阿修罗界”的设定是欲望之境,影片在西方魔幻的模子里添加了志怪小说中六界轮回和中式神怪的原料,导致影片本身成为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四不像”。皇宫是炫目的金黄色,高山堆满金子,异次元空间是歌舞厅风格的斑斓光影的堆砌,夸张粗暴的色彩和胡乱拼贴的文化符号使整个画面严重失调,毫无审美秩序。为“奇”而“丑”的现象并非个例,归根到底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审美与志怪电影类型化的进程相脱节。创作者想当然地将刻板印象中的“怪”与“恶”进行了等量代换,理所当然地认为怪应该是大同社会亟待降伏的异符号,于是罔顾审美的协调性,在画面上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夸张,直至隐喻成为宣告,符号吞并主体。
实际上,志怪电影的类型化绝不等同于将“怪”与“丑”或“恶”相提并论。近年来志怪电影对于国族神话的重述反而包含着东西方话语体系交融糅合之下共同的美学追求,使之在“高概念”化的叙事模式下逐渐成为中式审美对于“克己复礼”的追求与西方“因信称义”理念融合的产物。“高概念”意为“针对全目标观众市场所采用的一种倚重技术特效生成的奇观化视觉效果、以极具吸引力的超级明星为卖点、以商业诉求为驱动力的电影拍摄模式,此类电影的核心故事极易被概括与传播,通过各种元素的组合来突出故事的透明性与说教主义。”而神话本身就具有篇幅短小、妇孺皆知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其看起来具备天然的“高概念”,因此这样的叙事更容易放大神话类型化的影像书写。东西方审美在“怪”身上的融合首先体现在对异文明符号的挪用,《画壁》的煤炭人和《西游·伏妖篇》的机械人偶红孩儿与传统的中式志怪符号大相径庭,在好莱坞魔幻电影或科幻巨作的影响下此类形象在志怪电影中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次,东方志怪元素也并非拥有着志怪小说中的原貌,而是以混血面孔重新呈现。以“龙”为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蕴含着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主天地、社稷和风雨的神灵,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但东方图腾在《新约全书》的启示录中被描绘为邪恶的“古蛇”,与魔鬼和撒旦划上等号。《哪吒之魔童降世》将龙这一古老的图腾拖下了神坛,龙族不再是呼风唤雨,呵气成云的神灵,而是西方魔物图谱中面目可怖,在终日见不得天光的深渊中低吼的复仇者。无论是直接挪用还是交互杂糅,“怪”的变迁都不再受制于某种单一的话语体系,且不可避免地走向“施夷长技”的类型化之路。
(二)现实互文:传统寓言的现代重塑
美国学者艾伯拉姆在《简明外国文学词典》中说:“寓言也是一种可以用于任何文学形式和流派的艺术技巧。”寓言对于志怪小说的影响不容小觑,在志怪电影中亦然。如前文所述,志怪电影中的“怪”是“克己复礼”与“因信称义”两种文化根基嫁接后的产物,因此在传统寓言的叙事框架下,志怪文化在科技社会被赋予了新的自由意志。多年之后观众未必会记得《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细节,但大概率会在某个不经意间讲出“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台词的“出圈”绝非偶然,“观众在对于电影镜像的迷恋关系中,也完成了一次舒畅的精神分析自我治愈。”可见,既然“志怪”与“志人”有着相伴相生的孪生关系,那么志怪电影必然要围绕当下社会“人”的心理诉求建立其叙事场域。《封神演义》中向姜子牙请辞最终肉身成圣、位列仙班的哪吒在当代的动画版本中不断追寻自我身份的认同源于志怪电影对于当代主流精神气质的迎合。
当礼义教化与自由主义的相互制约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志怪电影对于传统寓言的“新仪式”塑造必然与现实互文呈现。2008年乌尔善版本的《画皮》相较于1966年的第一次影视化改编,女妖的形象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无推己及人的内部道德约束。小唯热烈地渴望成为王生的“唯一”,却无法理解蜥蜴精的爱慕,希望蜥蜴精彻底消失在她的生活中。这种利己与利他不能平衡的爱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试想现实生活中一件件破坏家庭、背叛婚姻的案例,“破坏者与闯入者往往太过自我,渴望爱的热度,却无法承担爱的重量。”现实不可能尽如电影最终有“爱的觉醒”机械降神化解一切矛盾,从价值源头来看,将肯定自我价值与抑制个人主义的无限扩张相平衡是东西方文明发展永恒的挑战。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提出了“因信称义”,并认为人生而有罪,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孤独的,赎罪只能依靠对上帝最真诚的信仰,但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是平等且自由的。这样一来哪吒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便有了对舶来价值观的借鉴,但人同时还有着群体价值。“克己复礼”的主体虽然是“己”,但“礼”却是“争则乱,乱则离”之后的“制礼义以分之”。哪吒掌控了自己的命运,挽救陈塘关百姓的性命于危亡,一场新的“封神仪式”完美落幕,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也画上了一个新的句号。个人主义需要在礼仪教化的规范中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平衡,礼制也要在自我意识的帮扶下避免沦为禁锢人性的枷锁,因而在忠孝两难的境地下敖丙选择从申公豹手中夺走乾坤圈协助哪吒,申公豹放下执念,龙族泯去世仇。
与《画皮》和《哪吒》中的“人—怪”思辨同理,鬼、仙、妖、魔等等传统寓言的主角在志怪文化中都有着自身的话语机制与哲学内涵,清代刘璋的《斩鬼传》将鬼分为了“谄、假、奸、捣、诓骗、轻薄……”等40余种鬼魅以讽世劝世;《因循岛》的狼妖官吏皆为“外来移民”,“专爱食人脂膏”寓指晚清官吏的吃人本质;影视化频率最高的《西游记》无论是在文学层面还是影视改编层面都展现了一个空前庞大且等级森严的神魔宇宙。“对传说情节偶然性的建构,渗透着作者对社会强势权力话语的反叛与解构。”寓言的吸引力在于与“实事”相对举,将源于现实的素材褪去现实的外部形态,虚构的部分才有可能高于生活。于是,传统寓言蕴含着丰富的反压制、反权力中心的诉求,与当下社会对于个体精神狂欢的追求再次交汇,依托着志怪电影这一视觉媒介完成了现代重塑。
三、文化寻遗与精神重建——志怪母题的银幕升格
加里宁有言:“人民好比淘金者,他们所选择的,保存的,相传的,并且在几百年中加以琢磨的,只是最宝贵、最有天才的东西。”志怪文学对于崇高的追唤基于中华民族千年来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情感意向,历经革故鼎新仍然屹立不倒。
(一)文化寻遗:崇高垂范的踵事增华
审美与精神的“崇高”在东西方的文化土壤上有着不同的外部形态,英国的博克在《关于我们崇高美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将崇高的感情来源认定为“自我保全的冲动”,认为能够引起由于痛苦和危险的消除而产生不同于积极的快感的东西就是崇高的。康德将其引申为“一种只能间接产生的愉快”,生命力在受到阻滞之后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形态爆发,因此可以把人的精神力量提高到超越以往的尺度的东西就是崇高的。中国美学将崇高的形式定义为“壮美”,且“宏壮之形式常以不可抵抗外力之势力唤起人的钦仰之情。”可见,西方“伟大心灵的回声”的崇高和东方“焕乎,其有文章”的壮美虽有明显的外部差异,但所涉及的对象世界中都包含着对于苦难的感受,对苦难的感受和超越成为了每一个社会动荡或精神失序的社会共同的话语诉求。
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繁荣来源于民间玄学巫风的兴盛,但无论是志怪文化还是玄学巫风都只是一种现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艺术家必须要适应社会环境,满足社会的需求。”因而现象的本质还是社会环境使然。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于是封建正统独尊的儒学式微,玄学兴起。魏晋南北朝则更为动荡,数百年在短暂的统一与分裂中来回转场,士大夫对于儒学在狂澜既倒面前的无力失望至极,为求保命选择纵情山水,流连于山河百川,超然物外,谈玄说理,不问政事。政权高度集中的大一统社会可以依靠皇权专制统一思想,归化异族,但在更迭频繁、割据混战的六朝,封建主们无力实现思想的集中,又恰逢三教合流,巫鬼之风盛行,寻常百姓流离失所,民心惶惶却无权过问政治,便只能揣摩士大夫阶层的行为将现世的危机认作是巫鬼作乱。如此一来,“大楚兴,陈胜王”等鬼神迷信之事就有了天然的传播土壤。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下,人们开始重视向内的自我探寻,追求平和安宁的内心世界,摆脱混杂的世俗羁绊,文人志士“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放下笔杆就服药喝酒,对羽化登仙心驰神往。“魏晋风度”应运而生,中原士人天地悠游,钦慕老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恰似一场末世狂欢。
外部的祸乱使志怪小说在魏晋六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当代志怪电影的文化“再繁荣”却是来自于内部的危机,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本意义上的人成为被资本、科技理性规训与异化之后的“非人”。近几年来的中国志怪电影不乏对于人、科技的异化危机的审视。《晴雅集》中的发妖被自己所爱的画师杀害,于是成妖之后冤冤相报害死了当年画师的画中人——公主;《捉妖记》人吃妖,妖吃人,葛千户披上一身俊朗的人皮,掌握了人界对妖的生杀大权之后迷失了身份,将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同类。技术宰制下的西方文明难以再实现肉体上对于苦难的超越,由此将这种超越寓于对自然的征服。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物欲的猛增和“利益至上”的观念驱使着危机之下的人们失去忌惮与敬畏,对现代科技的过度依赖淡化了伦理道德对于人类的约束,因此“非理性”行为使得大多数人很难再遵循某种秩序,不反思、不怀疑地滥用技术以谋求现世的物欲与享乐。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志怪文化中的道德追求在今世对于礼义教化的匡扶中仍然有着大规模的施展空间,中国传统哲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内容,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门径,去构建人类生活的精神坐标和确认人类社会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传统天人关系赋予了中华民族寻唤崇高的使命。西方社会已有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试验的先例——全盘抛弃伊斯兰历史遗产,否认本土文化与现代化的兼容并蓄,导致了土耳其民族精神与政治统治的错位,使之成为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传统崇高垂范的坚守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助力于文化认同的建构。《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员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日自强不息矣。”中国传统志怪文化中的崇高垂范在志怪电影中完成了艺术崇高与现实崇高的有机统一,在对于文化自信的寻唤中继往圣之绝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守正创新,踵事增华。
(二)英雄解构:精神重建之审美嬗变
在信仰与理性双重失落的危机之下,任何一个社会匡扶礼崩乐坏之象都需要一种能够消弭崇高缺位的力量,或者说一个崇高垂范的符号化载体——英雄。传统志怪文化中的英雄是“集体无意识”下的“客我”,“客我”即“有机体自己采取的有机组织的一组他人态度。他人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为一个‘主我’对之作出反应”。《搜神记》记载了一则“谅辅求雨”的故事:大旱之年,“辅以五官掾,出祷山川,自誓曰:‘万物枯焦,百姓喁喁,无所控诉,咎尽在辅。今郡太守内省责己,自曝中庭,使辅谢罪,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誓,若至日中无雨,请以身塞无状。’乃积薪柴,将自焚焉。至日中时,山气转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至诚。”“集体本位”高于“个体本位”的谅辅式“客我”英雄形象是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体系下“集体无意识”遗传得来的思想和观念的倾向。这种在忠恕之道浸润下的“高、大、全”英雄在“十七年”电影中尤为普遍,《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勇于牺牲自我利益甚至个体生命的“革命悲剧”英雄与西哲柏格森所言的“封闭道德”相通缀,在“有意为小说”的使命烛照下笼罩了“神性”的光辉。
“柏格森将道德区分为‘封闭道德’与‘开放道德’,前者指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式道德,后者指个别榜样式人物践行的高于社会责任的抱负式道德,前者是公德,后者是美德。”就今时的志怪电影而言无论是《大圣归来》还是《捉妖记》,抑或是前文提到的《哪吒》,其主人公的体貌特征都不再如“十七年”时期(1949-1966)电影中英雄人物的“进、大、亮”,而是更接近于普通人甚至具有某些普通人尚且不存在的明显缺陷,这样的形象更贴近于生活中的平凡个体,使解救与被解救不再有清晰的边界。在“开放道德”的话语机制下不完美的“主我”不影响英雄成为英雄,哪吒依旧可以挽救父母族人,悟空照样可以战胜妖王,看似体胖笨拙的胡巴仍然是平衡妖界的密码,英雄解构并不代表“反英雄”,而是赞扬英雄的另一种形式——一个“小人”成为救世主是人本精神之下“神性—人性”的当代共生,是莱辛所言恪守崇高使命的“有人气的英雄”。英雄形象的下沉是对社会权力话语体系的挑战,激起了集体无意识这一社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的转变:超越“客我”的“主我”崇高也能惩恶扬善,英雄的候选皆可众生平等。
结语
时至今日,市场上的志怪电影作品仍然良莠不齐,但志怪文化的长盛不衰、历久弥新,标志着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顺应时代,因利乘便。志怪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绮丽炫目的一笔,文人们的大胆隐喻与狂想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疆域,影像科技的进步为古人宏大的猎奇想象与神话构想提供了画卷,使之探寻出了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仍然逻辑自洽的叙事范式。但志怪电影的影像书写只是一种隐喻与寻唤的载体,其母题终究还是要回归到人在面对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时的心理突围,突破本土与异域的限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圆心,在“主我”与“客我”的和解中构建“东方魔幻主义”话语机制下的价值观与志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