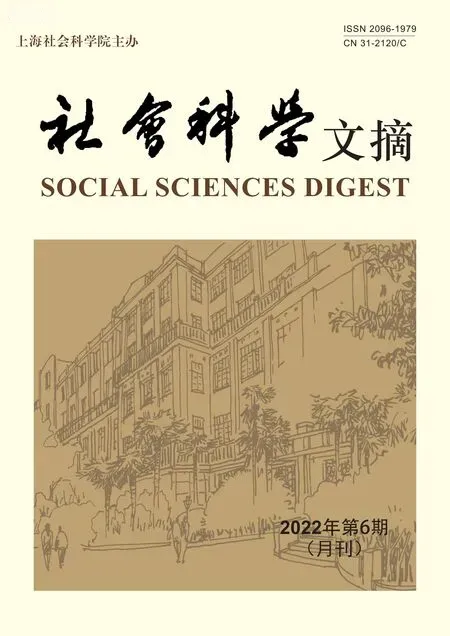论买卖人口犯罪的立法修正
2022-10-22罗翔
文/罗翔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否应当提高法定刑在法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基本上形成“提高派”和“维持派”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现行刑法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规定是否出现了无法弥补的漏洞,而有修订之必要。
买卖人口犯罪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反思
通过对买卖人口犯罪立法演进脉络的梳理,发现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收买型犯罪的立法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导向。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严惩拐卖决定》)首次增加了收买型犯罪,这是为了应对当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突增的现象。因此,法律的重心是打击卖方,而对买方则网开一面,所以《严惩拐卖决定》规定了免责条款。第二,拐卖犯罪的立法比较仓促,存在明显缺陷。这体现在:(1)绑架条款顾此失彼。现行刑法取消了绑架妇女、儿童罪,以出卖为目的绑架妇女、儿童成为《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的一种加重情节。但是,《刑法》第416条依然规定了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2)渎职条款缺乏协调。现行刑法中玩忽职守罪的法定刑从以前的一档变成了两档,《刑法》第416条并未体现对妇女、儿童的特殊保护,按照普通罪玩忽职守罪处理,刑罚反而还可能更重。(3)拐卖人口罪废除不当,存在大量法律漏洞。
买卖人口犯罪的法益衡量与侵犯客体
正是因为立法相对仓促,没有通盘考虑法条之间的逻辑关系,以至于刑法出现大量的体系性漏洞,其中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人的保护力度还不如物。与动物相比,同样是收买行为,《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买卖同罪同刑。与植物相比,刑法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力度也偏低。《刑法》第344条规定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无论是出售,还是购买重点保护植物或植物制品,买卖同罪同刑;同样是犯罪所得,如果收买赃物,构成《刑法》第312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基本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犯罪所得不是物,而是被拐的妇女、儿童,收买者的刑罚最高仅有3年有期徒刑。虽然《刑法》第241条第2款到第4款有数罪并罚的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实施非法拘禁、强奸等罪的,应当数罪并罚。但是,实施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罪后又实施其他犯罪,比如收购大熊猫后走私的,购买赃物后诈骗的,同样可以数罪并罚。因此,从表面的观感来看,法律很难摆脱人不如物的指责。
有学者认为人和动物保护的法益属性不同,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这种观点并不恰当,在刑法中对不同性质法益进行比较是必须的。
法益衡量背后的哲学观念冲突也与功利主义自身有关量与质的快乐的争论有关。在边沁看来,快乐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不同。但是穆勒认为,快乐有质的区别,功利主义应当区别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越能体现人的尊严的快乐就越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按照穆勒的修正,快乐是有质的区别,越体现人性尊严的快乐越是一种高级快乐。那么,越与人性尊严有关的利益就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之尊严就高于一切物权。我国刑法曾经规定盗窃罪可以判处死刑,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也有死刑条款。刑法修正案取消了这些死刑条款,背后的精神就是人高于物,熊猫是国宝,但人是无价之宝,无论多么卑微的人都高于一切财与物。
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犯罪,既然立法者已经明示本章罪名所侵犯的是人身权利,那就没有理由在人身权利中添加其他模糊的利益内容,否则必将导致定罪量刑的混乱。
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保护的客体,学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1)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2)被害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与身体安全;(3)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被收买者家庭的稳定。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另外两种观点都不具有客体(法益)的区分功能。第二种观点无法和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进行区分;至于第三种观点则无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的卖儿鬻女现象。
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相似,学界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保护的客体也有大致相同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学者在描述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所保护的客体时都使用了相同的表述。或许有人认为拐卖妇女、儿童行为除了侵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以外,还可能危及身体活动自由,因为拐卖犯罪会包容非法拘禁行为,因此较之收买犯罪更为恶劣。但是一方面,在收买犯罪中同样会高度伴随非法拘禁行为;另一方面,拐卖并不必然包容非法拘禁,比如将妇女骗卖至工厂做苦力,或者骗卖到色情场所卖淫,这都并不一定存在非法拘禁的现象,但这并不影响拐卖妇女罪的成立。总之,无论是收买,还是拐卖妇女、儿童罪,它保护的都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人不是商品,不能被买卖。买卖人口是对人的彻底物化,行为本身就从根本上亵渎了人性的尊严。无论拐卖还是收买,两者所侵犯的法益(权利)没有任何区别,在立法上,保持相同的刑罚是合理的。
权利是一种类型化的法益,它剔除了各种模糊的利益内容,可以让定罪量刑的尺度变得更为客观。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律人士对追究买主刑事责任存在一定的同情态度,认为买主也是弱者,大多出于结婚或者收养目的收买妇女、儿童,让其人财两空,甚至对其追责判刑,会影响社会稳定。无论这种观点是否合理,都是在权利以外考虑了其他模糊的政策利益,这些利益与权利没有关系,没有必要在定罪中进行考量。如果法益不被权利类型化,权利以外的大量利益内容,会让法益的权衡成为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有学者担心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会导致大量的衍生问题,比如解救困难、被拐妇女没人照顾、所生的孩子缺乏关爱等。这些问题当然需要解决,但它并非刑法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在权利之外进行利益考量是没有边界的,我们必须接受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任何基于结果的功利考虑都是不稳定的,总是存在源源不断的变量可以修正之前的计算。
当民众朴素的法感认为刑法存在体系性的漏洞,我们不能以法律理性之名拒绝聆听,法感本身就具有批判实证法的宝贵功能。法律绝非精英的智力游戏,它必须接受道德观念的约束。总之,刑法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存在着体系性的不匹配,人不如物的立法缺陷伤害了民众朴素的法感情。
买卖人口犯罪惩罚失衡:对向犯理论的审视
无论是拐卖还是收买妇女、儿童,都侵犯了人之不可被买卖的权利,本应被同等评价。但是仓促立法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买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失衡,与共同对向犯理论不兼容。
有学者认为,不能以孤立的视角看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因为《刑法》第241条的6款条文整体构成了重罪。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较之卖方,买方所受的刑罚评价要轻得多。从逻辑上来看,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刑罚偏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一般不会伴随非法拘禁、虐待、强奸等重罪。从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刑罚整体偏低。在笔者统计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案例中,数罪并罚的案件极少,绝大部分案件仅判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大部分被告人都被适用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
刑法中的对向犯有两种:一是共同对向犯,二是片面对向犯。我国刑法中的共同对向犯大致可以分为同罪同刑和异罪异刑两种类型,同罪同刑由于所对向的双方适用相同罪名相同刑罚,没有讨论必要。只有异罪异刑的现象才值得关注。异罪异刑的对向犯,我国刑法中主要有三类:一是贿赂犯罪中受贿与行贿的对向关系;二是渎职犯罪中的对向关系;三是其他犯罪中的对向关系。
在异罪异刑的对向犯中,所对向的双方很少像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这样,基本刑相差过于悬殊。其中原因,令人费解。在1979年刑法中,拐卖妇女、儿童属于拐卖人口罪的特殊类型,它原本属于片面对向犯,收买方不构成犯罪。1991年《严惩拐卖决定》将其修改为共同对向犯,但是基于当时的打拐背景,为了加大对卖方的打击力度,避免在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时遭遇太大阻力,所以买方的刑罚明显偏低。同时,由于免责条款的存在,拐卖犯罪成为事实上的片面对向犯。虽然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免责条款修改为从宽条款,此罪变为了真正的共同对向犯。但是,和其他的共同对向犯相比,对向双方刑罚明显失衡,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作为共同对向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严重失衡,与共同对向犯的理论很难兼容,实有调整之必要。
买卖人口犯罪的域外立法经验借鉴
梳理国际公约和其他国家、地区关于买卖人口犯罪的刑事立法,发现对拐卖与收买两种行为适用不同的刑罚幅度的现象在域外比较少见。
联合国大会于2000年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贩运人口议定书》),我国于2010年成为缔约国。《贩运人口议定书》规定:“贩运人口,系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按照该规定,贩运人口既包括“拐卖”常见的招募、运送、转移、窝藏行为,也包括接收行为。因此,贩运人口既包括卖,也包括买。《贩运人口议定书》强调贩运人口必须具有剥削目的。剥削应至少包括利用他人卖淫进行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迫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做法、劳役或切除器官。
在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国际公约的做法,以剥削为目的的买卖人口都构成贩运人口罪,买方与卖方的刑罚并无明显区别。在历史上,旧中国的法律也曾对买卖采取同罪同刑的立法进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世界性的眼光可以让我们走出地域性的偏见,而历史性的思考则让我们走出时代性的洞穴。
提高买卖人口犯罪中买方的法定刑
贩运人口犯罪现象不容乐观。虽然当前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在历史上,也曾出现下降之后数次反弹的现象。同时,传统的以出卖为目的的拐卖犯罪虽然逐渐得到控制,但是以劳动剥削和性服务为目的的拐卖人口犯罪呈上升趋势。因此,一方面,必须用足用好现有法律规定,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另一方面,则应适时进行立法修订,审慎提高买方的法定刑。
具体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将侵犯人身不受买卖权利的犯罪合并为一个罪名。无论何种性别、年龄,买卖行为都是对人的物化,亵渎了人性尊严,都侵犯了人之不可买卖的权利。因此,可以将《刑法》第240条、241条、244条、262条进行整合,将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买的妇女、儿童罪,强迫劳动罪,拐骗儿童罪统一为买卖人口罪,形式上实现同罪同刑,也与国际公约接轨。
买卖人口罪可以限定为剥削目的,无论是基于性剥削、强迫劳动还是营利等目的都可以解释为剥削,对于剥削目的的帮助和促进也可以解释为具有这种目的,具有剥削目的买卖人口均构成此罪。剥削目的是一种主观超过要素,并不需要实际实现,因此以让妇女卖淫为目的收买被拐妇女,同样构成买卖人口罪。如果又实施了强迫卖淫、组织卖淫等行为,则应数罪并罚。买卖人口罪的基本刑依然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设有加重情节,根据不同情节规定不同的刑罚。另外,取消《刑法》第416条的规定,相关行为直接论以玩忽职守罪或滥用职权罪。
第二种方案则无需变动刑法的基本结构,仅修改《刑法》第241条第1款,增设第二档加重法定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与第244条强迫劳动罪的刑罚基本保持一致。相较于第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变动较小,修法成本较低。
1991年《严惩拐卖决定》将收买人口规定为犯罪,至今不过30年的历史。我国现行刑法在保护妇女、儿童权利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任何法律一经制定,就已经滞后,当法律的漏洞无法通过解释学予以弥补,修改法律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刑法中的法益是一种类型化的利益,不能过度飘逸。法益具有解释论功能,也应具备立法批判的机能,立法从未绝对正确,不宜对其偶像崇拜。买卖人口侵犯了人之不可被买卖的权利,不能在权利以外考虑其他利益,买卖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刑法有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规定存在着人不如物、买卖人口刑罚失衡的漏洞,不符合共同对向犯的基本理论,背离了民众朴素的法感情,对于人身权的保护并不充分。综合考虑历史经验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状况,有必要慎重考虑修改法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