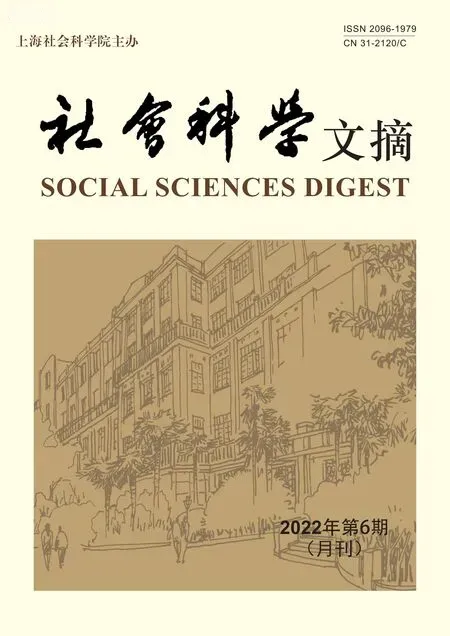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原理与路径
2022-10-22纵博
文/纵博
为什么要专门研究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问题
法律的适用离不开解释,刑事证据规则也是如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解释学研究刚刚起步,相对于刑法、民法解释学来说发展较为滞后,司法实践中解释技术匮乏。刑事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部分,而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必要专门研究其解释问题。
1.证据规则调整的对象与一般程序性规则有所不同。证据规则借由对证据采纳、采信、证明负担等方面的调整,最终实现对裁判者的心证进行约束,针对的是裁判者的主观判断过程;而程序规则通过对各项程序性事项的条件、范围、效力等方面的调整,针对的是诉讼主体的各类诉讼行为。因此,对证据规则的解释需要在尊重裁判者心证与必要的外在限制、准确认定事实与保障其他价值、及时解决纠纷与合理分配风险等复杂因素之间进行更多元化的考量。
2.证据规则的特征与程序规则也有所不同。正是因为证据规则要对裁判者的主观心证进行规制,所以一般而言证据规则在文字用语上应当具有较大的裁量和解释空间,并应当具有广泛的例外性规定,才能在证据的自由判断与法律的合理规制之间取得平衡,这与程序性规则应当越细越好的要求截然不同。证据规则这种文义结构上普遍的原则性、模糊性为法律解释提供了较大空间。
3.即便在证据规则体系内部,不同类型证据规则的解释界限也有所差异。在刑事证据规则中,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几类主要证据规则所调整的对象及规范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证据规则与程序规则关系极其密切(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且与公民权利保障息息相关,而有的则较为疏远(如证明力规则),且与公民权利保障并无直接关联,所以各类证据规则的解释界限、解释方法也有所不同。
刑事证据规则解释的特殊原则
刑事程序规则解释有其相对具体的、与程序规则解释有所不同的特殊原则。
(一)以准确认定事实为核心原则
在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中,准确认定事实作为刑事证据制度的整体目的,也是在解释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规范目的,不仅在目的解释中要综合考虑个别目的和准确认定事实之间的择取关系,对其他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通常也要以是否有利于准确认定事实进行检验。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中,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证明力规则、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都以促进准确认定事实为唯一目的,证明标准的主要目的也是促进准确认定事实。在这几类证据规则的解释中,如果按文义、体系、历史解释得出的结论不利于准确认定事实,就应以目的解释方法寻求合理结论;如果以目的解释方法探索条文的“可能的文义”仍无法得出合理结论,可以采取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或类推方法填补漏洞。
并非所有证据规则都以准确认定事实作为规范目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以维护司法公正并保障人权为目的;证明责任以分配证明风险为规范目的,但准确认定事实是刑事证据制度整体的、核心的规范目的,因此这两类证据规则均受制于准确认定事实这一整体目的。
(二)“非必要,不限制”原则
所谓“非必要,不限制”原则,是指在对证据规则的解释中,应当注意: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解释结论不应对法官判断证据的自由造成限制。“非必要,不限制”是准确认定事实的内在要求,其理由在于,准确认定事实主要依靠裁判者的理性判断能力,而非法律规则,所以除非必要,否则证据法就不应对人类这种理性判断能力进行限制。因此,在证据规则的解释中,裁判者不应进行作茧自缚的解释,将按照规范目的本不应施加的限制加于自身,尤其是在证明力规则、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的解释方面,通常应作平义解释,当规则的适用结果不利于准确认定事实时,应运用限缩解释、目的性限缩来缩小规则的效力范围,平衡规则的强制性与自由判断证据之间的关系。
(三)妥当性优先原则
在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规则旨在限制刑事司法权力,所以应当重视安定性,使刑事司法权力不得随意行使,也使公民对刑事司法权力的行使有所预期;而证据规则的主要规范目的是准确认定事实,则更应当重视妥当性。因为证据立法是对理性认知能力的外在人为限制,所以不仅要遵循“非必要,不限制”原则,即便要对证据判断作出限制,也应是一种灵活性的规则。若规则的文义过于绝对、僵化,直接按文义进行适用会得出不合理结论时,就应灵活采取其他解释方法或漏洞填补方法而取得合理结论,而不应限于文义导致实体不公正。
刑事证据规则解释的立场
与刑法解释主要处理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不同,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置于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之中,要面对更加多元化的目的、原则之间的权衡。
(一)刑事证据规则解释与不枉不纵
准确认定事实包含两个方面,即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所概括的“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准确认定事实”并不仅是“惩罚犯罪”,还包括“开释无辜”。虽然通常认为“开释无辜”更为重要,但绝非忽视“惩罚犯罪”,准确认定事实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整体规范目的,要消极与积极兼顾。对于刑事证据规则的法律解释来说,以准确认定事实为核心规范目的就要求在解释中不能单纯以结论有利于惩罚犯罪或有利于防止冤枉无辜为目标,而应以促进认识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为目标。
(二)刑事证据规则解释与无罪推定
从无罪推定的基本内涵来看,它与证明责任密切相关,是对证明责任解释的限制。但另一个问题是,当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中出现疑问时,是否适用无罪推定所内涵的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而选择解释结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多数观点,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只针对事实认定,而不适用于法律疑问,因此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当然也无需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但法律领域的事实与法律难以截然区分的难题在证据规则的适用中同样存在,此时能否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对于事实与法律问题难以区分的难题进行拟制,即“事实认定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难以区分的,视为事实认定问题”。这对于解决证据规则解释中事实与法律问题区分难题也是一种借鉴,即可以把难以区分的情形视为事实问题,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三)刑事证据规则解释与人权保障
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之一,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正式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因此人权保障也应当作为刑事证据规则解释中目的解释的法定依据。按照通常理解,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对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代表的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进行保护,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是重心,尤其是要防止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各项权利的非法侵害。
但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解释中要以人权保障为规范目的,不等于解释结果要有利于被告人。其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指的是法律规范应以直接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为目的,但刑事诉讼规范并不保障诉讼结果有利于被告人;其二,如果按照赫菲尔德的权利分类理论,刑事证据规则的权利义务对应关系对法官和当事人来说并不相同:对于法官来说属于“权力—责任”类型,对于当事人来说则属于“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刑事证据规则是对法官采纳、采信证据和分配证明风险的规范,适用证据规则是法官的职责,但其对应物并非当事人的权利;对于当事人来说其权利类型为请求权,即申请法官适用某一证据规则,但不意味着该规则必然会适用,更不意味着只有结果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则才可以适用;其三,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也难以预测最终的结果是否会不利于被告人,所以以有利于被告人作为解释标准也难以实施;其四,如前所述,有利于被告人是指在事实认定的结果上如果存疑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但在法律有疑问时并不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四)刑事证据规则解释与程序法定
程序法定原则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以法律限制国家刑事司法权力而保障人权,所以程序法定中的“程序”指的是规范权力行使的程序,不得通过解释而规避法律对权力行使所设置的限制,也不能通过解释而随意创设、增加权力,因为规避程序或增加权力就意味着会侵害当事人权利。但“程序法定”中的“程序”不包括非权力行使的具体操作程序(如勘验、鉴定的程序),因为后者主要与证据的可靠性、真实性问题相关,是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或证明力判断领域的问题。因此,程序法定原则对刑事证据规则解释的限制仅在于不得通过解释而扩充国家刑事司法权力并侵害公民权利,只要遵循这一界限,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就不必拘泥于文义的最大范围,遇有漏洞时当然也可进行填补。
各类刑事证据规则的具体解释路径
(一)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
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在于保障证明力,从而促进准确认定事实,与规范程序性权力、人权保障并无关联,所以如果存在影响证据可靠性的情形且裁判者最终无法确定证据证明力大小,可以直接适用规则而排除证据,但在裁判者能够确定证据的证明力较大的情形下,如果按照规则的一般文义仍要排除证据,可以采取目的解释方法解决规则过于机械或缺乏例外的问题;如果以目的解释探索文义的最大边界仍不能得出合理结论,则属于漏洞,需采取相应方法进行漏洞填补。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解释应当坚持文义的优先性,遇有疑义时,一方面要依据控制刑事司法权力、保障人权的主要规范目的对规则进行相对严格的解释,但同时要考虑准确认定事实的需要,因为准确认定事实不仅是证据制度的核心的、整体的目的,也同样是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的。二者在多数情况下并无冲突,对于某些非法证据的排除来说,准确认定事实本身甚至就可以解释为排除标准,如威胁、引诱、欺骗获取口供的排除标准。但在少数情况下仍会有冲突。准确认定事实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如果非法证据排除与准确认定事实的消极方面——开释无辜有所冲突,则必须优先考虑开释无辜的需要,因为任何目的都不应以无辜者被处罚为代价。如果非法证据排除与准确认定事实的积极方面——惩罚犯罪有所冲突,则需具体判断。
(三)证明力规则
在证明力规则中,多数规则仅是纯粹出于对证明力评价进行规范的考虑,个别规则还兼及其他政策性考虑。对于前者,在解释中应有较大的自由容许度,因为作为对自由判断证据的外在限制,基于经验的不完全归纳而创设的证明力规则或多或少会产生不合理结果,所以有必要通过宽松的解释而化解其刚性。对于后者,则应当持相对严格的解释,因为这类证明力规则承担着其他政策性因素,如果解释过于宽松,会抵消其政策性功能,但同时对这类规则的解释又不能过于严格而影响对证据的自由判断,所以要在保障政策的实施与自由判断证据之间寻得平衡。
(四)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对裁判者主观心证的尺度要求,是在案件事实无法重现的前提下对诉讼中认定事实程度的一种妥协式设定,也是对证明风险的权衡与分配,尽管如此,其主要目的仍是促进准确认定事实。如何在法律中设置一种能够发挥有效规范作用的证明标准一直是一个难题,因为抽象的、依赖裁判者主观认识的证明标准难以满足“标准”应有的客观化、具体化。但一般来说,证明标准在各种法律制度中还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如何解释和运用证明标准仍是难题。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紧密相连,其解释需要遵守无罪推定原则,因此不得通过解释而任意降低证明标准。但另一方面,证明标准又是对裁判者的主观判断的限制,所以又要在法律规制与自由判断证据之间取得平衡,不能过于机械而扼制裁判者的主观判断。
(五)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是一种风险分配规则,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大陆法理论上的“客观证明责任”,即在待证事实未能被证明至相应的证明标准时,由何方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决定了一般来说控方要承担被告人构成犯罪并应予以处罚的证明责任,因此对于证明责任应当进行严格的解释,不得通过解释而随意转移风险,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人必须有坚实的解释论依据。证明责任贯穿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特质决定了要从更广阔的法律体系中去搜寻分配规则并作出解释,而不限于刑事诉讼法本身。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发现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人的规则,要根据准确认定事实的整体目的,以文义、体系等解释方法确定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未达到何种证明标准时方可按证明责任作出判决。
结语
从证据规则的发展趋势来看“非必要,不限制”作为一种证据立法的理念已成主流,而我国目前的证据法学研究却多数还是以追求增加、完善、细化证据规则为己任,多少有一些不合时宜。作为对裁判者心证的限制,证据规则中的绝大多数在文义上都应当尽可能宽松,赋予裁判者更广泛的解释权力,这样才能在规范与裁量、真相与政策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因此,对证据规则的解释应当是司法人员的必备技能,也是刑事证据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的意图主要在于引起学界对刑事证据法解释学研究的关注,共同提高刑事证据法学的方法论水平,使其尽快成长为一门成熟的诉讼法学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