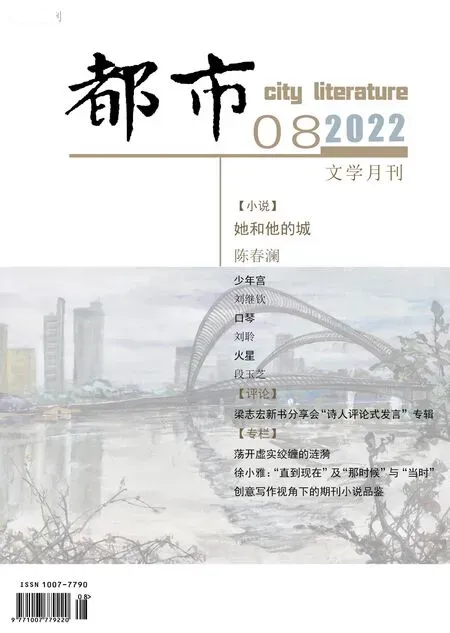口琴
2022-10-22刘聆
文 刘聆
1
铃声在想象的远方响起的那一刻,我依旧不愿意喊她一声妈。那时我正被困意从逼仄的出租屋拖出来,独自站在一张橙红色老式沙发前。我走进右边卧室,靠里一张单人床,上面铺着蓝色碎花床单,门边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只口琴、一朵枯萎的花。我拿起那支枯萎的花,一个尖利的声音像刀片划破我的耳朵,不许拿!那孩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到门边,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背心,他的牙齿又长又尖,闪着匕首一般的寒光。这时手机铃声从天而降,你……在睡觉?我一听就知道是她,这十几年我们从没联系过,就像她忘了我一样我也忘了她,但她的声音我记得,细弱、消瘦,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总是吞吞吐吐,生怕打扰了对方。我说,刚睡着,我挂了。她说,别……有事找你。我停了一会儿,说,说吧。她就在电话里说,我……你能回来看看你太婆吗?晚了就来不及了。我说,太婆身体挺硬朗的,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她说,大不如以前了,前几天又摔了跤,老人经不起一摔。我说,我看看吧,就把电话挂了。
到南歌已是晚上六点。家里没人,桌子上放着小半碟榨菜、半碗小米南瓜粥。我没有看到她那双散发着铜质金光的高跟鞋,是那个男人买给她的,她一直藏着,只过年才穿,男人不在,那双鞋也许扔了。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在铺着蓝色碎花床单的床上坐了一会儿。我拉开书桌抽屉,铅笔、钢笔,初中时买的改正贴,抽屉里面还有我小时候的日记本,最里面是一只口琴。
门响,她回来了。我关上抽屉从房间走出来,她正在脱鞋,她穿了双软底黑色布鞋。我没有说话。她的头发白了一片,脸色发黑,有了眼袋,瘦了很多。她抬头看着我说,天黑了,晚饭吃了吗?我说,太婆怎么样了?她说,没的几天了,前几天还喝点我给她熬的稀粥,昨天什么也没吃……她轻轻摇头。我觉得难过,说,怎么不去医院?她说,死活不肯,现在这样子去也没多大意义。
窗外还是灰蒙蒙的,她的房门没开,我站起来听了一会儿,她应该是起来了,没有咳嗽声,也没有电视和收音机的声音,那个男人死了以后,家里安静下来。我敲了敲门,说,我过去了。传来拖鞋的声音,她打开门,似乎比昨晚更瘦了,眼袋也大了一圈,脸色更黑了,带几根香蕉给你太婆,她昨天就嚷着吃,别的她也吃不下。我点点头,穿上外套走出门,把香蕉揣在怀里。
一切都没变,穿过十字街从巷子进去,最里面的小屋,那扇木门半开着,我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又敲了敲门,还是没有声音。我说,太婆?依然没有声音。我又喊,太婆!角落里传来轻微的咳嗽声,一缕声音传出来,哪个?我说,是我!江妹!太婆说,江妹,你是江妹?你回来了?你快过来,让太婆好好看看你。我走进屋里,放下香蕉,屋里阴暗,透着潮。我坐到她的床边,说,太婆,我给你带了香蕉。太婆卧在床上,头发像白麻一样飘荡着,两腮塌下去,牙齿几乎掉光了。太婆说,美凤要你带给我的吧?造孽哎。我说,太婆不要想太多,好好休息。太婆伸出枯枝似的手在我的脸上摩挲着,说,你不要骗我,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说,太婆你不要乱想。聊了一会儿,除了安慰,我找不出更多的话,门外的天光似乎更灰暗了。我说,太婆,这天空灰蒙蒙的,怕是要下雨。太婆说,你又不是头一遭看到这灰雾,雨下不来。我说,太婆,等下中午我给你送粥。太婆摆了摆手,说,江妹,太婆有几句话要跟你讲。我说,你讲。太婆将头缩进被子里,露出干瘪的嘴,眼睛突然发出明亮的光,用低沉又尖细的声音说,你还在吹口琴?我说,太婆,我早就不吹口琴了。初中时候,我爸给我买了一只口琴,吹了几年,离家以后我就再没吹过口琴。太婆说,不要吹口琴。我说,太婆,我现在一天到晚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吹口琴,就是有,也没这个心气儿了。太婆摇摇头,一脸悲戚地说,扔掉口琴。我没再说话,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直往下掉,像这间破破烂烂的小屋一样空荡荡的。
从太婆家回来,她正在熬粥,白米粥。我才记起还没吃早餐,这会儿却什么都吃不下。我说,中午我送粥给太婆吃吧。她说,你先喝粥,太婆怎么样?我摇摇头,情况不太好,总要我不要吹口琴。她突然惊惶地转过身,冲我喊,口琴还在?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头发披散着,脸色变得很难看。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她将碗一扔,跑到我的房间,打开抽屉,翻出铅笔、改正贴,还有我的日记本,没有口琴,她将东西都倒出来,没有口琴。你的口琴呢?她惊慌地看着我,眼里发出咄咄的光。昨天还看到呢,我指着抽屉说。你的口琴呢?她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头狮子吼起来,到哪去了?我倒抽一口凉气。她猛然抬头盯着我,你扔掉了?一定是的。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她安静下来,继续回到厨房熬粥,似乎那粥永远也熬不熟。我走进自己的房间,看见窗外的树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烟雾中,像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样子。
2
窗外的天光总是灰蒙蒙的,好像一直是晚上,又好像无边无际的大雾。从我有记忆起,这雾就没散过。跟着他到镇上天快黑了,我坐在地上哭,我要回去!我妈该着急了!他转过身,快到了,前面就是大剧院,大伙都在等你吹口琴!越往前走,山变得更灰白,石头一块块凸出来,像白骨,反射出惨白的光。爬过两座山,隐约听见机器轰鸣的声音,一些人像蚂蚁在山上爬。他指着山下一间犹如坟墓般低矮的房屋,说,到了。那天真黑啊,黑得透亮,像是从来没有亮过。我被关在小黑屋里,哭得嗓子哑了,沉沉睡去,醒来又哭,哭了醒,醒了哭,不知过了多久,我在一个半夜醒来,终于想到我应该要吃些东西。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我爸和我妈。
算来总有三十来年了。美凤跟着她娘来那天,傍着昏黑,天热得怪,闷劲直往骨子里钻,让人坐立不安。我正在厨房做饭,他猛吼,快弄几个菜!我妹来了!我慌慌张张走出来,美凤一蹦一跳地冲我笑,说,舅妈忙呢!我擦了擦围裙,说,还好,你们坐!他又吼,还不快去,磨磨蹭蹭的!美凤拉着我的手,说舅妈的手艺我早听舅舅说过,今天没什么事你教我两手吧!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美凤她娘说,这死孩子贱呢!美凤说,我偏要!钻进了厨房,挨着我说,舅妈,这厨房里跟蒸笼似的,十几年了你也忍得住。我说,习惯了,你出去吧,等会儿菜就好。厨房的蒸汽好像茫茫白雾,四处蔓延。美凤说,我看你做菜。她圆润的脸庞透过湿乎乎的蒸汽,汗津津的,身体微微摇晃着,轻纱快湿透了。一条黄鳝从盆里跳出来,使劲扭曲着,它的肚子胀鼓鼓的,尾巴显得单薄了,每次挣扎都费尽了力气。美凤看见了,捧起黄鳝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我将盆里的黄鳝摇了摇,倒进锅里,盖上锅盖,一阵噼里啪啦犹如炮仗般的声音响起来。爆炒鳝鱼,我说,油烟呛得很,你出去吧。美凤说,舅妈,他们说你爱吹口琴,现在还吹不?我摇摇头说,口琴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了。美凤看了我一眼,说,舅妈,你说女人是不是生下来就是受苦的?我说,你还小,不想这些。美凤喝了口水,说,不小了,楼上楼下好几个像我这么大的,都嫁人了。我看了她一眼,说,她们不读书吗?美凤说,我妈讲,女孩子反正是要嫁人的,读再多的书也没用。我将炒好的黄鳝倒进碗里,说,你不要听你妈瞎讲,你好好读书。美凤摇摇头,说,舅妈,我不想读书了。她转过身,拿背对着我说,我要走了。我将打好的鸡蛋倒进锅里,叹息一声说,你爹娘总是为你好的。美凤说,他们追我,争着对我好,比我爸妈对我强多了,我想早点离开那个家。我说,他们是谁?美凤说,徐缘和肖州明。我说,他们俩?美凤低下头,说,是徐缘。我说,你不要走我的老路。美凤说,我怀孕了。我问,你爸妈知道吗?美凤说,舅妈,我只有离开这里了。我说,你不要做傻事。她摸了摸肚皮,我只想和他在一起,苦些累些不在乎。他的声音雷一样炸进来,怎么还没炒出来!我将黄鳝和鸡蛋端出来,美凤跟着我出来。饭桌上,她跟我一样端着碗没有上桌吃饭,她的眼帘垂下来,始终没有看我一眼。我一晚没睡,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美凤挺着亮堂的肚皮走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月亮沉到山后面,夜色犹如矿渣落下来,像灰雾抹进我的眼睛。
过了些日子,美凤果然像扬进黑夜的灰烟消失了。美凤爹娘找他商量了好几次,美凤爹吼了几句,她娘默哭,这死女娃贱呢。几个人扯绊一阵,到末聊了一会儿其他事,不知是谁笑出声来,接着几个人大笑起来,美凤的事再没有提及。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美凤踩着自己的回声,如一只肥胖鸭子挺着肚子回来了。她娘隔着街骂,小婊子,你还好意思回来!你怎么不给我死在外头!她爹吼,有种就别进我这个门!她笑着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要?我跟徐缘结婚了。她娘问,哪个徐缘?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个人起哄说,就是那个成天写诗的疯子!大伙又是一阵哄笑。徐缘我也认识,头发老长,比潲水还脏,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是要去外面打工,找写诗灵感,但最后还是没有出去。过了两个月,美凤生下了江妹,美凤她爹哼了一声,又是女娃,她娘成天挂着脸嘟囔着他们好吃懒做;过了小半年,那天晚上,冷得厉害,美凤他爹来我家吃酒,醉醺醺地回家,倒在半道冻死了。美凤她娘从那以后就开始发癫,对着空气骂个不停,说江妹是丧门鬼,把美凤她爹害死了,指着江妹骂,有一次差点把江妹摔死。美凤和徐缘就搬了出来,在城边的棚户区租了房子,六十多平方米,日子过得紧巴。美凤搬出来没多久,肖州明也回来了,带着一个孩子,小尚,比江妹小。小尚十三岁那年跌到河里淹死了,那是肖州明和美凤在一起没多久的事。
后来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怎样谁也说不清,只晓得徐缘和肖州明大吵一架,断了来往。江妹一天天长大,这孩子真像我,爱吹口琴。江妹十五岁那年,徐缘生了病,说不出话,瘦得像片枯叶,只有肖州明去看了他。徐缘没多久就去世了,美凤就和肖州明在一起。刚开始还有人说,时间长了,说的人也没有了。有天傍晚,我在路边碰到了江妹,她在割草,一起一伏,肩膀的弧形和脊背的隆起晃着微光,胸脯鼓鼓的,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见到我,江妹擦了把汗,说,太婆,吃了没?我站在路边说,吃过了,这么早来割草?江妹笑了起来,这时候正好,晚了就看不清了。大厂建起来后,采矿规矩起来,山上山下渐渐长出草来,软得很,怎么也扯不断,有人说叫石草,可以编席,后来有人开始收购。江妹将石草搁进筐里说,太婆,你干脆跟我们一起住算了。我说,太婆年纪大了,反应慢,又爱啰唆,招人烦。江妹割了一把草,说,哪能呢,没有的事。我说,江妹,我问你一句话,你和小尚上学放学都是一起走的吧?江妹说,太婆,你问这个干吗?我说,听说小尚从河里捞起来的时候,肚子涨得像皮球,脸都紫了。江妹没有说话,很久才说,他调皮得很,你不晓得,拖拉机他都敢爬。我说,这也是他的命。江妹又低头割草,一边割草一边说,他哪是来读书的。她的口袋里露出半截口琴,我说,上学放学你都带着口琴?她说,是啊,难过的时候吹一吹。我说,你该多想想你娘。她低下头,眼泪掉下来,说,太婆,你不知道,我真想早点离开那个家。我说,你不要瞎想,好好读书,你爹走了,你娘总是为你好的。江妹抹了一把眼泪,将镰刀插进筐里说,太婆我知道了,先走了。说罢,背起筐回去了。
厂里庆祝建厂二十周年文艺会演那年,有几个女学生在路上唱歌吹口琴,后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她们。文艺会演以后,女学生们安静下来,歌声消失了,江妹却吹起了口琴,
我还记得江妹第一次吹口琴的样子。我送了碗鸡汤过去,美凤正吃着饭,江妹站在阳台上吹口琴,琴声飘出窗外。还有一次,我看到江妹在山上吹口琴,微风扬起她的头发,血一样的夕阳映照在她的身后,像她的琴声一样流出说不出的哀伤。肖州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像喝醉的人一样坐在她的身后,听她吹完,才摇摇晃晃站起来说,江妹口琴吹得蛮好。我说,现在小尚没了,她就是你的女儿。肖州明说,舅妈这还用你讲,我跟她爸本来就是过命的兄弟,有我一口,就有她娘俩一口。明天我帮她找个口琴老师,让她好好学口琴。江妹吹口琴吹出了名气,一到傍晚,就有心急的扒几口饭坐在路边听她吹口琴。年底,学校要办一场文艺演出,他们找到江妹说,江妹,你来我们学校表演吹口琴吧,你不去,我们这演出算什么演出呢?
那年夏天,江妹的口琴吹了没多久,大伙突然哄闹起来,美凤慌慌张张从家里跑出来,四处敲门。我收拾完灵堂,靠在椅子上,眯着眼睛,啥事都记不得,只看见一只碧绿的口琴转呐转呐。他死了,半夜起来屙尿,摔一跤就没了。这些年跟着他不知是啥个滋味,喜欢自然谈不上,恨也没有,我们无儿无女,我现在是个空空的肉篓子,不知道哪天就跟着他走了。有人跑过来喊我说,出事了,出事了,美凤老公死了!我说,美凤老公不是早就死了吗?不是那个,是现在这个,肖州明,就死在她屋里。我看到肖州明时,他躺在屋里门板上,换了衣服。美凤跪着,低下头,没有哭。江妹站在她的身后,也没有哭。美凤看到我说,脑溢血。又说,我让他不要喝酒他偏喝,徐缘死在酒里头,我爸也是。我说,这是他的命。美凤说,是我的命。肖州明埋在山上,跟他儿子小尚埋在一块,没有立碑。他的不远处,就是徐缘。办完了肖州明的丧事,美凤牵着江妹到我屋里坐了好久,舅妈,你一个人,跟我们娘俩一起过吧。我摇摇头,我在这儿自在些。美凤说,我们娘俩不硌人,你是知道的。我说,跟着他这么多年,我没觉着他走了。美凤说,舅妈,你说我们娘俩怎么办?我说,肖州明走了也好,我看他就不像好人。江妹大了,长得又好看,难免让人生出歪心思。美凤哭起来说,舅妈我晓得你的意思,不是你想的,再怎样也是我男人。我说,你们回去吧,带好江妹。
门外的黑越来越浓,像我刚来那天傍晚。是谁在外面吹口琴?这声音让我怎么也安生不了。江妹还没有走?这会儿我说不出话,我的声音先我一步走了,快轮到我了。我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握着口琴走进来,冲我温暖地笑,向我伸出手。我张了张嘴,想问去哪里。她只是笑,转身消失在门外的夜色里。口琴声又响了起来,江妹的哭声跳出来。我拼命想爬起来,身体像一截枯木不听使唤,门外的夜色犹如滚滚浓烟涌进来。
3
上中学后,我就没怎么上课。反正我妈讲女孩子读再多的书都是要嫁人的,当初留下我只是为了让我带弟弟,现在弟弟一直没有生下来,我迟早会被他们像垃圾一样扔出的,不如去耍。有天,打完游戏,我像以前一样跟徐缘和肖州明出来,肖州明停了下来,转过身望着我,又望着徐缘,说,我们就这样打游戏打到死?徐缘说,去上课?肖州明说,你上课干什么?写诗?鬼才看你的诗!我们不如去打工。我说,我不想去学校也不想回家,你们在哪里我就去哪。说完,我快步走上前,拉起他们的手。肖州明的大拇指在我的手背上力度不大不小地摁了摁,我抬起头看他正冲我笑,眼里有光在流动,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低下头,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乱窜,我的手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任由他捏着。那天晚上,徐缘要了我,他哭着说我是他的女人,我不许任何人碰你。之前的事,原来他都看到了。
我们最后还是没有跟着肖州明去。不久,徐缘带着我去了深圳。快要生江妹的时候,肖州明也来了。肖州明找到徐缘的那天傍晚,徐缘就订了回家的车票,我们甚至来不及收拾,就踏上了回家的路。后来,肖州明也回来了,带着个孩子,小尚。他像是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肖州明跑到家里,要跟徐缘一起做生意,徐缘一直对他耿耿于怀,话说得很坏,肖州明变了脸色,两个人大吵一架。我劝他说你这是何苦,他说,带好江妹,没你什么事!我觉得有些对不住肖州明,可肖州明一点也不在乎,一有空就到我们家来,徐缘不让他进门,他就守在楼梯口,等我出门。我说,你想做什么?他说,不想做什么,想看你。我的脸烧起来,你以后别来了,我连江妹都有了。他说,你有你的江妹,我来看我的。我说,你的心思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天渐渐黑下来,我看了看灰蒙蒙的天说,要看不清路了,你赶紧回去,我从头上解下一根发带塞到他手里说,以后别来了,给小尚找个新妈妈。我转身快步走回家里。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十多年,肖州明没来我家,可我感觉到他就在我的身边,像灰蒙蒙的雾无处不在。
直到徐缘病了,他又来了,有时候也不说话,只是陪我坐着。有天,大清早,他像往常一样到我家里来,递给我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钱。我把公文包递给他,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也不容易。他没有接,说,给我兄弟治病的。我说,我们不知哪年哪月才还得起你这个钱了。他说,不用还。江妹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说,我们不要你的钱!我喊她回房间去,她大声说了句,妈,我不想看到这个人!他放下公文包,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发带,说,我还记着呢。快出门的时候,我叫住他,说,你明天早点来,我煮了鸡蛋面。他看着我,用力点点头。我看见他眼里那道熟悉的光,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徐缘去世那天,我看到了他,办完丧事,我们就在一起了,好像我们一直在一起。我跟肖州明住进了江妹的卧室,小尚住进了我和徐缘原来的卧室,客厅的橙红色老式沙发成了江妹的床。从那以后江妹看我的眼神就变了,眼里长出刀子,漫不经心,但能划出血,我心里难受得很。我想找机会跟她说话,又不敢多说,她一听到我的声音转身就走。直到她喜欢上口琴,每天晚上都会拿着她爸买给她的口琴吹一阵子,吹完口琴后她才愿意跟我搭两句话。肖州明死的那天,我看见他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坐在江妹身后,看她吹口琴。江妹的口琴还没吹完,他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走过去,伸出手,说,来,叔教你吹。走了两步,他的身体剧烈地晃动起来,喉咙发出撕裂的声音,两只手捧着头摔在地上,把酒都呕了出来,身体像僵死的蚕一样蜷缩成一团。等我扶起来,他已经没了呼吸。肖州明的骨灰是江妹拿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娘俩坐在一起说了一晚上的话,现在都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说了一句,妈对不起你。江妹低下头,抹了把脸,偏过头看着窗外。我知道她哭了。不知过了多久,江妹说,妈,我想出去打工,我不想读书了。我看着她,说,不行!你得读!妈做的一切全是为了你。江妹扬起头看着我说,妈,你说女人是不是生下来就是受苦的?我说,你还小,好好读书,不要瞎想。江妹说,女孩子反正是要嫁人的,读再多的书也没用。我气得扇了她一巴掌,说,你个不争气的,那你去打工啊!江妹捂住脸,猛地站起来,盯着我,眼神像锥子一样又尖又利,泡在眼泪里,模模糊糊的。她跺跺脚,转身打开门走了。我看看窗外,也许亮了,也许没亮,灰蒙蒙的雾一样看不清楚。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不吃不喝,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感到自己也像一块死肉被薄薄的灰纱包裹着。等到下午,舅妈来了,问我,江妹去哪了?我摇摇头,眼泪从眼眶里像枯草一样落下来。舅妈问,你们吵架了?我说,她去打工了。舅妈说,她不读书了?打什么工!跟你当年一样?我捂着脸哭了起来,说,你以为我想要她去打工!
没想到半个月后,她回到家里,一个人躲进之前我和她爸住过的卧室。我去敲她的门,敲了一会儿,她的声音传了出来,隐隐约约,什么事?江妹,妈做了些糕点,你出来尝尝?不吃,我要睡觉了。你开门。有话明天再说,我要睡了。你开门,这几句话妈一定要说。我不听!算妈求你了!里面什么东西响了一下,门开了。江妹穿得整整齐齐,像要出门的样子。我问,这几天心情不好?江妹说,你有话赶紧说,不早了。你是不是不想见我?你以为我想回来?这个房间,我住进去都感觉恶心!江妹突然坐在床边,一只手捂住眼睛哭起来。我说,你有什么心事就跟妈说。江妹哭了一会儿,抹了一把眼泪,把眼光移开说,没什么跟你说的。我说,那把口琴扔了吧?江妹偏着头说,不要你管。我说,妈也是不得已。江妹哭着说,你当年生下我也是不得已吧!我抓住她的手说,去读书吧,妈不想要你走我的老路。江妹甩开我的手,我不去!说完,把我往外推,你走,我要睡觉了,我不想和你说话。从江妹房间出来,我高兴起来,她肯跟我说话了。那天下午,舅妈端来一碗鸡汤,江妹喝了好几口,我把着她的脸色说,不去上学了?她突然站起来,将鸡汤重重往桌上一放,跑进卧室,狠狠甩了门。我看了看舅妈,站起来,去敲她的门,说,不想上学就不上呗,妈妈说错话了。江妹断断续续的哭声传了出来,舅妈说,江妹,出来喝点鸡汤吧,你最喜欢喝太婆做的鸡汤了,有什么话就跟太婆讲。我又敲了敲门,门终于打开了,她看着舅妈,又盯着我,眼泪一滴一滴无声地落下,我怀孕了。
从医院出来后,江妹再不肯一个人睡。我将她抱在怀里,轻拍她的肩,哼着曲,就像刚生出她那会儿。江妹会在半夜突然醒来,流着冷泪。我打开灯,抹去她的眼泪,说,都过去了。江妹说,我还是想出去。我说,你出去,妈不放心。江妹说,在这儿我害怕。我说,妈跟你在一块,咱娘俩说啥也不分开。江妹说,你抱着我,跟没抱我是一样的,我感觉后背冷飕飕的。我说,是妈伤了你。江妹说,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他们在我眼前晃,要是没有肖州明和小尚打扰我们的生活该多好。夜深了,我听见她颤抖的呼吸,紧咬嘴唇的声音。天快亮了,江妹拉了拉我的手说,你看,天亮了,真好看。我坐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看着窗外,灰暗不明的烟雾不见了,天空就像被水洗过一样亮堂。我说,妈生你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早上。你的哭声好大,几条街都听得见,灰黑的夜好像被扯碎了,那天空亮得真白。江妹笑了笑,说,我有这么大威力咧,我怎么不知道?我也笑了,说,你的威力大着呢。江妹说,妈,我要走了。我说,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江妹点点头,笑了笑,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一闪。江妹打开门,一股清气扑了过来,你回去吧,早上冷。我冲她挥手。她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消失在小巷口、消失在路口,镇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天光亮得刺眼,几片枯叶被风吹起又落下。我听到嘶哑的声音,江妹,慢慢走!是舅妈,她的身影在巷子里慢慢映出来,她来送江妹。一只乌鸦从枯枝上飞起来,它回旋着,尖利地叫着,跟着江妹飞了出去,变成一粒黑色斑点。江妹就要离开这个小镇,这也许是她第一次离开也许不是,但我知道,她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她越走越快,清亮的白光被她的身影遮蔽,又很快闪现出来。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亮的清晨,像心里裂开的罅隙里穿过的一束光芒,我能看见。
4
天灰蒙蒙的,像黑纱在天上飘,却一直黑不下来。我回来对她说,我走了。她有些着急,说,就走了?饭都没吃一口。我说,看了太婆,就行了。她夹了两粒饭,慢慢送进嘴里,说,我等下要送粥给你太婆,你也一起去看看,跟她告个别吧。我坐下来,想了想,说,行吧。她又夹了一坨饭,放进嘴里,说,你太婆不管跟你说什么,你一定不要搁在心上。我说,我知道。
不知走了多久,转进小巷,看到一扇铁门,她敲了敲门,说,舅妈,是我!还有江妹。我说,这是太婆家吗?我上午来的时候,没有装铁门。我妈说,你太婆家这铁门还是你太公装的,跟我们家铁门一样,你上午不是走错了吧?我说,我小时候去过好多次,怎么会走错。门没有锁。我妈轻轻推开门,沉默寡言的昏暗从门口向后退了一步,微微向屋的深处退去,和里面的黑暗混在一起,四周的光线突然变得越发灰暗了。我听我妈轻声呼唤,舅妈,我送粥给你吃了。我喊了一声,太婆,我过来看你,我要走了。隐约听到一声轻微的哼声,我又喊,太婆,我是江妹。一缕生铁的冷硬罩在我的身上,整个房间突然晃动起来,发出沉闷的噼啪声,黑暗犹如沉重的铁铅在房间里滚来滚去,空气猛烈地振动起来。我冲她的方向喊,你去哪了!没有回音,空气中弥漫着一片荒废的陈腐气息。我走到太婆的床边,大片的黑暗犹如烧尽的纸钱飘进来,太婆你醒醒!太婆的床铺安静得犹如一座坟墓,她的枕边放着香蕉,已经发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太婆,你一定要看我最后一眼!我轻轻掀开被子,一只青筋毕露、瘦骨嶙峋的大手抓住了我,是她,她喘着细弱的气息躺在床上,眼睛覆上一层黑雾般的眼翳,透出惶恐的神情,口琴扔了吧?扔了。口琴一定要扔掉。她将身体蜷缩成一团,闭上眼睛,像死了过去。我大声哭了起来,妈,你怎么了?她身上的被子瘪了下去,身体仿佛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瘦小干瘪的头颅,张开嘴说,口琴一定要扔掉。太婆提着饭菜从一堆巨大的黑暗中慢慢移过来,像核桃一样干瘪的脸上挤出笑,我把口琴扔了。我说,太婆,你怎么起来了?大片的黑暗流入室内,像水一样泼进来,房间里的物件像落叶一样凋零,太婆在我面前慢慢地枯萎。我大声哭,太婆,妈,你们去哪里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跑进来,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背心,他的牙齿又长又尖,闪着匕首一般的寒光,你怎么不吹口琴?我最喜欢听你的口琴声了。他抓住我的手,往房间深处拉。屋里那送葬般的灰暗再次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我像被厚重的纠缠不清的黑色的茧卡紧了,透不过气。我不吹!我甩掉他的手,转身跑了出去。
我被自己的喊声惊醒,窗外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枕头全湿了,是我的眼泪。我看了看手机,六点,没有显示日期。一个未接电话,我妈的,打过去,没有人接。我站在出租屋里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是要出去,还是刚回来。汽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闪烁的街灯驱赶着像雾一样的黑暗,夜色变得稀薄,我不知道这是晚上六点,还是早上六点。我倒在床上,像死了一样睡过去,我想等我醒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