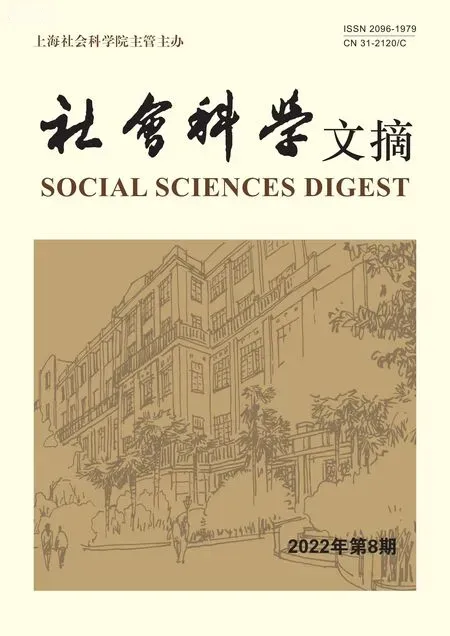中国制造业比重“内外差”现象及其“去工业化”涵义
2022-10-22黄群慧杨虎涛
文/黄群慧 杨虎涛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引发了广泛关注。从政策导向看,尽管并未淡化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但党的十九大以来,制造业作为“底层”和“基础”的作用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强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强调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同时,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重”相比,政策基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是,理论界对此仍有较大争议,这使得全面分析中国制造业比重问题以及对中国制造业比重变化趋势进行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制造业比重的“内外差”及其国际比较
对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事实,基于不同数据库得出的结论往往有所差异。而不同的数据来源均有各自的优缺点。为了更为全面刻画中国制造业比重的变化,本文基于不同数据库进行分析。在不同数据库中,中国制造业峰值和谷底年份出现的时间略有差异。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按当年美元计价的计算方式中,中国制造业GDP占比的降幅最大。对比同期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在5个国家均具有可比性的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数据库中,截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GDP占比降幅都是最大的。
全面理解制造业变化,还须考察制造业的全球份额。考虑到各主要工业国长期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联合国数据库作为资料来源。在比较对象上,选取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这5个主要工业国家进行比较,因为这5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制造业一半以上,且在联合国发布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中长期处于前五名。
从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看,以2015年不变价计算,1990—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4.0%增加到2020年的31.3%,成为份额增长最快的国家。以当年美元计算,联合国仅提供了截至2019年的数据。1990—2019年,中国的制造业世界份额从1990年的2.5%增加到2019年的28.7%,同期日德美的制造业世界份额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少,日本从18.0%下降到7.5%,德国从9.6%下降到5.3%,美国从22.1%下降到16.8%。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占比分析,2010年之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份额和占GDP比重基本保持变动方向一致,但占世界制造业份额增长更快。201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下降,但占世界制造业份额反而加速增长。按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12—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从峰值的30%下降到27.8%,下降2.2个百分点。但同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世界份额却从24.2%增加到31.3%,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内外差”变化趋势。
一国制造业世界份额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如相对他国制造业的增速、制造业规模、GDP增速等。199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国际占比的迅速上升,无疑得益于中国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GDP增速和制造业增速,其中,制造业增速远超GDP增速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0年之前,中国制造业远超其他国家的增速,是中国制造业国际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但201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与其他国家的增速差距明显缩小,中国制造业国际占比的快速上升显然不能完全通过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增速趋缓得到解释。201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两个占比之所以出现一高一低的“内外差”,一个可能被忽视的原因是统计方法的差异,即在不同的制造业增加值统计方法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相对被低估,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被高估。而在国内“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鼓励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占比的产业政策驱动下,中国制造业GDP占比又持续下降,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国内国际“内外差”变化。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被高估的情况下,仍出现了制造业国内占比持续下降,说明中国制造业衰退不仅来得过早,而且过快。对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而言,“内外差”反而折射出中国制造业在“大而不强”的现阶段已存在“未强先降”的整体衰退风险。
中国制造业的“内外差”现象,折射出在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发达工业化国家在“挤出”生产性服务业比中国更多的情况下,制造业国内GDP占比的下降并不十分明显,而中国却出现制造业国内GDP占比大幅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真实的“去工业化”程度要远远大于这些发达国家。绝不能因为制造业国际占比大幅提升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尚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而言,制造业国内GDP占比持续下降,这种“去工业化”趋势无疑是更值得警惕和担忧的。
中国制造业GDP占比保持基本稳定的必要性
对中国存在过早去工业化或者过快去工业化问题的判断,还并不能自然引申出中国制造业国内GDP占比保持稳定的政策导向。这里面有三方面问题需要回答。一是随着通信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日益融合,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特征正在出现新的变化,现代服务业在吸纳就业和促进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等方面正发挥着不同于传统服务业的作用,在“两业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中,保持制造业基本比重对于中国是否还十分必要?二是诸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同时仍然能有较好的经济增长绩效,这可以表明,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服务业将自然“接替”制造业成为新引擎,而中国为什么不能让服务业接替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三是诸如印度、哥斯达黎加、菲律宾等国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跨越制造业“引擎”阶段,直接以服务业作为“新船”来实现经济赶超。因而,中国是否一定要坚持以制造业作为自己发展的“扶梯”?围绕这三方面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说明中国在“十四五”时期保持制造业占GDP比例相对稳定十分必要、且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在“两业融合”过程中,制造业的引擎功能并不是“消失”,而是“下沉”,制造业的重要作用并不能被服务业所替代。第二,制造业对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引擎功能体现在技术创新,中国需要保持相当规模的制造业作为创新基础。第三,直接以服务业作为经济赶超“新船”的发展中国家,其本质上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制造业门槛提升、发展中国家产业选择集合“收缩”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引擎”功能的转换或者消失。第四,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也是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需要。第五,保持制造业基本比重稳定也是实现产业基础绿色化改造、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需要。
“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GDP占比的基本判断
2011年之后,全球价值链缩短态势十分明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形成了挤压。麦肯锡的相关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缩短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有关: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使中国能够消费更多的本国制造业产品而不需要出口;中国国内供应链的完善使许多中间投入品实现了在国内生产,减少了中间产品进口。
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发展趋势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价值链“缩短”趋势仍将继续。在制度因素上,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主义的抬头会继续导致制度“去能”,从而收缩全球价值链。在技术因素上,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一代数字技术促进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正在迎来的以机器人、物联网为代表的新的数字技术浪潮则可能会抑制全球商品贸易,但继续推动服务贸易。
按照难易程度的不同,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升级战略可分为四类:工艺升级或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升级。中国制造业过去的升级主要集中在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上,功能升级和链升级较弱。从技术发展趋势看,先进数字化制造将是数字时代工业化的核心所在,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集中表现。从中国现有的制造业结构和规模看,无疑具有这种基础条件。依托这种基础,实现从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和链升级的转换,将是稳定中国制造业基本规模的决定性因素。
从2020年制造业GDP占比27.8%这一基准点出发,在一定的GDP增速范围内,未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区间,主要取决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和GDP增速的相对差距。如果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始终低于GDP增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占GDP比重就会不断下降,反之,则占比会上升。
1991—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比GDP平均增速高1.06个百分点,2011年之前,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速一直高于GDP年增速,但2011年之后,制造业增速开始接近于GDP增速,2013年之后,则一直低于GDP增速。
202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8%。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2021—2025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速将保持在5%以上水平,到2035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速将下行至4.33%。按照该研究预测的GDP增速平均值计算,如果制造业增速沿袭2016—2020年的情况,低于GDP增速1.09个百分点,则2025年比重将下降到26.4%,2035年下降到23.77%;如果制造业增速沿袭1991—2020年的情况,高出GDP增速1.06个百分点,则2025年制造业比重将达到29.2%,2035年将上升为32.3%。但无论在短期内和长期内,制造业增速和GDP增速不可能保持一个较为恒定的值,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未来五年(2021—2025年)内,制造业增速将至少保持与GDP同步增长甚至略超出的趋势,截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最低比重仍可维持在27.8%左右甚至更高。其原因在于:
第一,从国内因素看,党的十九大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党中央一直在致力于扭转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第二,从国际因素看,尽管全球价值链缩短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止,而是出现了全球化快速发展后的“慢球化”。因此,综合国内、国际因素看,2021—2025年,在强化制造业的有效产业政策导向下,中国制造业将稳定增长甚至增速超过GDP同期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最低比重仍可维持在2020年的27.8%左右甚至更高。但随着各国制造业发展计划的实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国际占比将难以像2011—2020年那样快速增长。
从更为长期的发展看,随着制造业强化政策措施的效能逐步释放,中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将逐步低于同期GDP增速。从国际比较看,随着一国国民收入的不断提升,消费不断升级,对多样化的服务需求随之上升,制造业GDP占比将进入缓慢下降通道。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预测的GDP增速平均值计算,如果2025—2035年沿袭2011—2020年制造业平均增速低于GDP平均增速0.68个百分点的情况,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GDP占比将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按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约为26%。
政策建议
在“十四五”时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个重要目标的实现必须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政策供给支撑。必须认识到,制造业的“质”(包括竞争力、产业链现代化程度等)比制造业的“量”(包括规模、门类等)更为重要;但是,没有一定的制造业规模即“量”作为基础,创新的知识来源、作用对象就会受到限制,制造业“质”的提升就会成为无本之源,尤其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更是如此。“十四五”时期,围绕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政策供给上应集中于“三个基础”,政策导向上突出“四个强化”,从而在保障制造业基本规模即“量”的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动制造业“质”的提升。
所谓“三个基础”,一是有形的基础设施,统筹推进包括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数据基础设施;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等交通基础设施;干线油气管道、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等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全面、稳定的工业基础。二是无形的制度基础,包括适应现代产业体系特征、能准确把握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变化的基本统计制度、能准确把握产业短板、弱项变化的产业基础能力动态评估制度,旨在推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品质提升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如标准、计量、专利等体系,尤其是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产业质量、安全、卫生和环保节能标准等。三是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拓展和深化“工业强基”工程。通过“三个基础”的建设,实现“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所谓“四个强化”:一是总体导向上要强化构筑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二是强化新一轮工业革命背景下通用技术创新和应用的统筹部署,重在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应用所涉及的通用技术和使能技术的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三是强化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品质革命,在强基、提质、保规模的过程中,促进制造业附加值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四是强化政策转型,以适应现代制造业创新体系的需要。通过“四个强化”的推进,为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