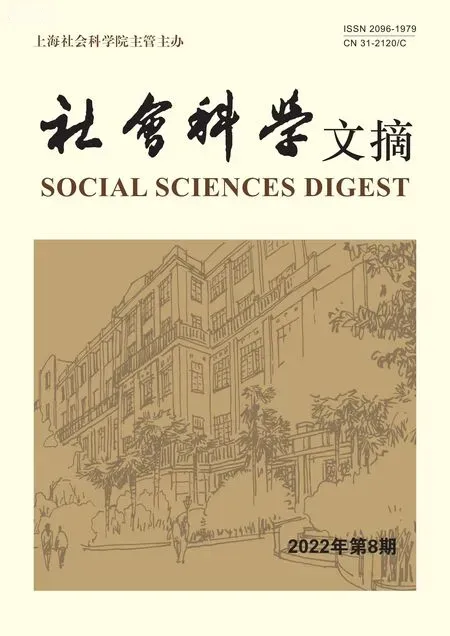文学共同体观念视野中的“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会通
2022-10-22韩高年
文/韩高年
从历史经验来看,构建文学共同体观念是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诗骚传统”发端于上古三代,形成于春秋战国,是一个融合南北、兼收并蓄的动态开放系统。因其文学层面、思想观念层面和人格层面的丰富内涵,而成为推动秦汉以后凝聚整合南北各族文学而不断建构中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基因。“三大史诗”《江格尔》《格萨尔王传》《玛纳斯》,以及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数百部史诗,与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学,形成形态上的相互补充与映衬,并在语言形式、情节母题、人物形象、价值观念等层面,与“诗骚传统”存在着诸多可以会通之处。
“史诗”形态的互补与会通
会通首先表现在藏、蒙、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对“中国史诗”形态的重要补充和对重新探讨“《诗经》史诗”问题的参照作用。以“三大史诗”为参照讨论“《诗经》史诗”的“合法性”及相关问题,需要从梳理西方学者对史诗范畴的界定和对活态史诗的最新研究入手。
史诗的概念出自古希腊,最早由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提出。至公元前6世纪末,《荷马史诗》已是希腊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黑格尔《美学》继承亚里士多德,以《荷马史诗》为蓝本界定史诗,将史诗分为原始史诗与正式的史诗两类,但他认为“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黑格尔因未见到中国的“三大史诗”而认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的观点是片面的。俄罗斯学者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史诗分期的观点,指出,经典史诗(成熟的)脱胎于原始史诗,而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组建成国家对英雄史诗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建立是原始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原始史诗”和“正式的史诗”(“经典史诗”)概念,对我们重新认识“《诗经》史诗”问题和“三大史诗”在中华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学界关于“《诗经》史诗”问题迄今尚无定论。笔者曾讨论认为“《诗经》史诗”的概念是成立的,《诗经》中《生民》等诗叙述周人立国的历史,颇具史诗的特征。除此之外,《诗经》中以祖先“世系”为叙事梗概的诗篇和甲骨卜辞中的“家谱刻辞”、载录于《国语》《左传》《大戴礼记》等文献中的“世系”类文本,在形态上也与西方学者所谓的“原始史诗”极其相近,可视为《生民》一类史诗的“蓝本”。
《生民》是周族史诗中最有名的一篇,属于追忆周人族群所自来的“创世史诗”。《生民》中言“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显然已经表现出明确的历史意识。《公刘》歌颂公刘迁豳之举为周人兴起的奠基之功,属于“迁徙史诗”。《绵》以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为中心,叙述他率领族人迁居于岐、营建家园、设“五官有司”之智慧,兼有道德颂歌和迁徙史诗的性质。《皇矣》与上面几首诗相似。《文王》《大明》《文王有声》则是对周文王姬昌开国功业的追忆,具有“英雄史诗”的性质。也就是说,《生民》等诗已经具备了“史诗”的条件,应当属于黑格尔和梅列金斯基所说的“正式的史诗”。
尽管《江格尔》《格萨尔王传》《玛纳斯》这三大长篇史诗产生的时代较“《诗经》史诗”要晚,但它们属于“中华文学”的重要部分,是与“诗骚传统”影响下的同时代(大约在唐宋以后)汉语讲史、说唱和历史叙事互通互融,具有蒙古族、藏族和柯尔克孜族等民族文化特征的活态长篇史诗。可以说,伴随着汉民族的“胡化”与“胡姓”的“汉化”的“三大史诗”的“演述史”,就是其对“诗骚传统”的会通与认同史。
按照黑格尔等西方学者所界定的史诗的篇幅标准,“三大史诗”完全可称之为“经典史诗”或“正式的史诗”。“三大史诗”均为活态史诗,其文本的建构,伴随着汉唐以来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北方边疆地区民族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过程。
可以说,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为我们重构中华文学的时空维度,重新认识诸如“荷马问题”“《诗经》史诗”和构建中国的史诗学范畴体系,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全面的视角和重要的动力源泉。
“史诗演述”认同功能的会通
“史诗”文本建构和不断演述的进程,对演述者和倾听者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功能。这一点,无论是就“非经典型”的“《诗经》史诗”而言,还是就活态的“三大史诗”而言,都是相同的。
笔者曾在《论“诗骚传统”》一文中指出:“诗骚传统”是指《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凝聚而成的文学精神。在周代以来的“礼乐文化”系统中,“诗教”“史鉴”相互融合,互为表里,是中华文学“诗骚传统”形成和流布的要关键。以保持族群记忆为核心功能的“《诗经》史诗”(包括《帝系》《世》等原始史诗)是周代礼乐仪式传承的主内容,而屈原的《离骚》《天问》则从个体认同角度创造性地升华和转化了这一制度化的族群记忆传承方式。这是“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认同功能指向会通的前提。
上古讲史制度与礼乐仪式中的《帝系》《世》等“原始史诗”的仪式性“散体叙事”与《生民》等“非经典史诗”的演述,以及盛行于唐宋以后的“讲史”“说唱”等口头程式传统,则是“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功能会通的主要呈现形式。
早在秦汉时代,“诗骚传统”就以不同的方式向四方传播。汉武帝朝,细君公主和之后的解忧公主及其随行者数百人,不仅将汉朝先进的农耕技术传至乌孙,而且将“诗骚传统”传播到伊犁河流域。此外,受中原文化影响,唐初突厥碑铭如《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暾欲谷碑》等,叙述历代突厥可汗和时任可汗的功业,均以突厥鲁尼文与汉文共同书写,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中原文化与突厥民族文化会通的结果。被称为“脱卜赤颜”的《蒙古秘史》最初也是于明洪武年间由翰林院侍讲火原洁(蒙古人)、编修马懿赤黑“以华言译其语”,即用汉语逐句记音的方式留存的。中原文学的“胡化”和胡族文学的“汉化” 在各个层面全面展开。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用蒙语演唱,其诗行都是韵语。蒙古族学者贺希格·陶克陶指出:《江格尔》中押韵方式有头韵、腰韵、脚韵和对仗性全韵等形式。其中押头韵是最古老的形式,脚韵为主、头韵为辅的形式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这里所说的“影响”,既有11世纪随同伊斯兰教传入今新疆地区的阿拉伯、波斯文学的影响,也有随中原文化西渐的《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学的影响。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雏形产生的时代大约在唐初或稍后。唐初文成公主入藏远嫁松赞干布,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吐蕃文化的交流融合。被称为“八大藏戏”之一的《文成公主》很明显地反映了汉藏两族当时的亲密友好关系。《格萨尔王传》中的谚语说:
*对汉人讲情会欢喜,对藏民造福得安乐。
*汉地货物运至卫地,并非藏地不产什么东西,而是为把汉藏关系连络起。
这些谚语反映了在这部史诗产生的时代藏汉人民友好往来、商旅互通、文化交流的状况。缘于上述认知,《格萨尔王传》难免受“诗骚传统”的影响。如其述格萨尔王出生之细节,实为《生民》《玄鸟》之始祖卵生神话之流衍;其叙事歌咏多取“对唱”,状物抒情则多用比兴手法等,尤与《诗》《骚》相表里。《格萨尔王传》中的唱词可分为“多段体”(又称“多段回环体”“鲁体”)和“自由体”两种。“自由体”不分段,不押韵,不受句数限制,意尽而止。从句法层面看,其中最占优势的是“六音节自由体”,即每句六音节。这种诗律结构与以《离骚》为代表的“六言体”十分相似。另据王沂暖先生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分章体”本采用标题双行等形式,则是受到讲史和话本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三国演义》等章回体的影响。章回小说的标题采用诗联的形式。这表明“诗骚传统”与《格萨尔王传》之间在标题形式和韵律等方面也存在着某种关联。
“三大史诗”产生后,经历了历代史诗歌手的演述创编,其间或直接或间接地认同吸收“诗骚传统”或在其影响下的讲史、说唱的因素。虽然“三大史诗” 在不同时期也形成了各自不同、丰富多样的书面史诗文本,但其“活态史诗”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其文本的构建和创编仍在进行之中,其以“仪式叙述”为呈现方式的“诗教”功能和文化认同功能同样也在进行之中。
“史诗”精神的会通
“史诗精神”是史诗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史诗主人公的伟大人格力量。具体到“中华文学”,史诗精神表现为慎终追远的历史意识、献身为民的集体主义、团结一心的爱国主义、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
首先,史诗精神中的历史意识,具体体现在“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对于族群来源乃至人类起源、宇宙起源等终极问题的探寻和认同。《诗经》的《雅》《颂》“史诗”全面体现了敬天尊祖、以史为鉴的文化精神。屈原的《离骚》开篇即“自述家世”,《九歌》《九章》等作也表现出屈子的家国情怀。《天问》是诗人“寻根意识”的集中体现。这种情况在《格萨尔王传》中体现为对格萨尔下界降生带有神话色彩的叙述,隐含着有关藏族族源的特殊记忆。《江格尔》中的“宝木巴”,是蒙古族先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是他们“精神的故土”。从史诗中可以看出,“宝木巴”是蒙古族的“根”,《江格尔》是“根谱”。
历代中原王朝与柯尔克孜族之关系均相当亲密,这在柯尔克孜族史诗中也有体现。《玛纳斯》第一部《柯尔克孜族的由来》中的一个异文大概内容是汉王宫中的40名宫女因不堪宫中的寂寞而出逃,在饥饿、寒冷又遇猛兽侵袭的困境之中,偶遇40位乌斯勇士相救,结为夫妻。他们的后代即称柯尔克孜。此“异文”体现了特定时代里《玛纳斯》演唱者和听众对中原汉族文化的认同心理,反映了历史上两族之间相互通婚、亲如一家的事实。
其次,史诗精神中的集体主义,体现为史诗的主人公生而具有为民请命、除暴安良、安邦定国的使命,以及牺牲自我、追求大我的家国情怀。史诗中的格萨尔,一出生就带着除暴安良、拯救百姓的使命。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大明》等周族史诗一样,也是一部充满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的颂歌。
再次,史诗精神中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史诗主人公对本族群和邦国的忠诚,以及对恶势力的英勇斗争。因为时代的原因,他们观念中的“国”,更多地体现为部族共同体和族群层面。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却都是中华文学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源头和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史诗中的英雄主义,表现为史诗主人公疾恶如仇、不畏强暴、敢于向恶势力宣战的勇气和决心。柯尔克孜族从公元10世纪始屡遭异族侵略,保家卫国的战斗从未间歇。人们渴望和平,渴望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他们的史诗《玛纳斯》以英雄玛纳斯的事迹为核心,刻画了英雄的群像。与格萨尔王和江格尔不同的是,玛纳斯是一个悲剧英雄,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有为了大多数百姓利益而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诗》《骚》“非经典史诗”或“诗史”中的家国情怀、英雄主义与《江格尔》《格萨尔》《玛纳斯》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形成会通。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和“三大史诗”之间存在着多个层面的会通关系。这充分证明,中华文学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其精髓是人民至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这既是“中华文学观念共同体”建构的基础,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源泉,以及从文学层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小结
综上所述,借助“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的会通,我们可以从“中华文学观念共同体”层面达成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诗骚传统”不仅是贯穿古今汉民族文学的优秀文化基因,同时也以“文化中国”的形象被汉唐以来边疆各民族文学所认同和接受。正是其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推动和实现了一个历久弥新、活力充盈的多元一体“中华文学观念共同体”的建构。
第二,作为一种理念和方法,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活态史诗的文本建构和不断展演,对重新认识“《诗经》史诗”、建构有中国气派的史诗学格局和范畴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本文所谓“会通”,可视为一种超越“中心—边缘”思维定式而寻绎“源流”、实现“互通”和吁求“融合”的理论与实践诉求。这既是一个事关文学共同体观念构建和中华文学史话语体系重构的重大学术命题,也是一个涉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求。
第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在“中华文学观念共同体”层面上,开展以人民性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基调的“诗骚传统”与少数民族活态史诗会通的研究,推动实施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活态史诗传承展演和经典史诗文本汉译,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方式。
第五,借助数字人文和网络平台等新技术,实现跨文化传播,是新时代推动“诗骚传统”与“三大史诗”中的“优秀中华文化基因”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