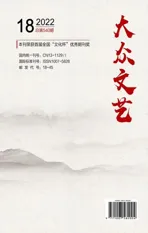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狩猎生活*
——以德利维斯的《水鼬》为例
2022-10-21刘雅虹
刘雅虹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 710128)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奉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断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使自然环境的持续性遭到破坏。20世纪后期,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应运而生并逐渐推向全球,成为一种新的跨学科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米格尔·德利维斯(1920-2010)是西班牙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杰出的散文家,塞万提斯奖获得者。作家密切观察西班牙内陆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广袤的农村世界在工业文明的侵蚀下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对大自然的捍卫贯穿了他的作品。德利维斯的作品独特之处在于:笔下的人物大多为爱好狩猎的人、以狩猎为生的人或优美自然景观的爱好者。德利维斯本人是狩猎爱好者,经常在河里钓鱼、在田野里猎鸟,因此有的评论家称德利维斯为“猎人—作家”。在狩猎的过程中,作家察觉到了物种濒危、自然环境受破坏、传统生活方式消失。他的狩猎观点是不能在自然保护区内狩猎,并且必须遵循自然界规律,给予动物繁衍生存的权利。换句话说,他认为只有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狩猎这种传统生活方式才会持续下去。
一、《水鼬》通过描写主人公外貌和性格的粗野,表达主人公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
作者没有给出《水鼬》主人公的名字,而以独特的绰号“拉特罗”(Ratero,即“捕鼬人”)来称呼他,这个绰号体现了人物的身份。随着故事的进展,一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漫画般的人物形象浮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发生在一个虚构地方的故事,丑陋荒唐的人物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效果,却恰如其分地象征了客观存在于卡斯蒂利亚——莱昂一带农村的某一类人。拉特罗外貌丑陋,眼神粗鲁,目光游移,龟裂的双唇露出一丝愚蠢而狡猾的笑容,有时候像野兽,使人恐惧。他头戴遮到双耳的贝雷帽,用一根细绳将帽子绑在脖颈上。一双有力的臂膀稳住了身体。双手及膝,五个指头齐刷刷一样长,就像断头台上的铡刀一样。他的样子像类人猿,肌肉发达,身体强壮,个头矮小。他说话不多于四个字,他不会组织句子。他的儿子尼尼给他的狗起名叫“法儿”,目的是避免名字太长使他厌烦。这是一个古怪的人物,就像一种卡斯蒂利亚古怪类型的合成体,未开化的野蛮人。他的行为出于本能而非理性,他像捕食动物一样在自己的打猎范围内做标记。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很丰富,突发事件会迫使他动脑筋。如果某一时期难以捕捉到水鼬,他就会推断水鼬数量减少的各种原因:枯水期提前,或者偷猎者侵入了他的领地。当受到周围环境逼迫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外界交流。他的头脑会出现难以揣测的恶念,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可能是毁灭性的。在田野里,拉特罗大叔无论对动物还是对大自然都没有感情,他从不走出山洞看看周围。自然界最美的景象也触动不了他的知觉。他对外来压力唯一的反应是扣动扳机:“保管打中”,与其说在说话,不如说在咕哝。他对人类的看法很消极,他确信水鼬比人类好得多。他懒于思考,不动脑子,只听从身边人的建议。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拉特罗大叔是一个古怪的人,外貌和性格与人类格格不入,然而,从自然的角度看,他恰恰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作者以象征的方式勾勒出一个大自然的捍卫者形象,实则表达了作者抚今追昔,对古西班牙植被茂密、生物多样、天人合一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怀念。
二、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弃的乡村在作者笔下呈现出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
故事始终未说明拉特罗的具体住址,但读者稍微留心一下,就能看出作家将故事安排在自己的家乡,即西班牙内陆高原的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某个小村子。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1950-1960年之间。村子里的居民不超过30个。这里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欠发达。在第11章作者勾画了这个村子的轮廓。教堂的钟塔在村子里占主导地位,和卡斯蒂利亚的所有村庄一样,教堂主宰着一切。村子坐落在河边,省级公路从这里经过。有一个集体草料店,还有一个畜栏,其主人是占有辖区内四分之三土地的富翁——绰号为“权势者”的堂安东。从一个给马钉掌的旧木架可以看出,村子里曾经驻扎过骑兵团,而现在只能经常看到有几头毛驴从草料店往家家户户运送烧锅用的稻草。四盏昏黄的灯光照着村子漆黑的夜晚。河对岸是山,拉特罗就居住在那边的山洞里。
在城市长大的村长太太高鲁姆芭非常厌倦村里的生活。她认为这里偏僻落后,尘土飞扬,环境肮脏。她抱怨没有自来水,街道没有铺沥青,没有舞会,没电影可看。她闭目塞听,眼里只有荒漠,却看不到燕子和石鸡飞来时的美妙景象,听不见蟋蟀在播过种的土地上鸣叫的协奏曲,感受不到其他诸如此类的自然美景,如鲜花之美丽、果实之丰硕。她看不起村里聪慧而淳朴的珍宝——小男孩尼尼,尽管她经常使唤他为她跑腿办事。她对村子的看法明显带着某种偏见,完全是以城市非持续发展式的所谓“进步”来评判农村世界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与高鲁姆芭的看法相反,作者在字里行间通过不胜枚举的例证,描写了这片土地上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及这里居民的乡村生活。德利维斯不时以抒情的笔调炫耀他的农村知识以及他对乡野的喜爱。在作者笔下,拉特罗十岁的儿子尼尼对大自然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幻想,他完全陶醉在亲近大自然的愉悦中。
大自然也是村庄的一分子,主宰着后者,掌控着其生活节奏。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从秋天到来年夏天,四季流转中的田野景象。作者对田野的描绘具体到方方面面:从5月9日的圣格利高里奥纪念日开始,蟋蟀的鸣叫“从四面八方的缝隙里渗出,像水面上的波纹一样,不断增长,向周边一圈一圈蔓延开去……,伴随着蟋蟀的鸣叫声,农民们在田里干着各种各样的活计”。作者的笔触经常走走停停,列举村子周围的地理景象、农业及自然环境元素。作者以与整个故事的冷峻风格截然相反的同情心,不吝笔墨、认真而仔细地描写动物世界,对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一视同仁。作者通过文中的人物阿文迪奥爷爷和罗曼爷爷的言行,汇集了世代相传的有关农村的一切智慧学问。拉特罗的儿子师承了他们:“男孩在罗曼爷爷身边也学会了感知身边的生命。”作者笔下的农村人愚钝而粗俗,不懂得欣赏其周围环境,不明白其价值。乡下人咒骂暴风雨、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这鬼地方太荒凉了,根本不是人呆的”。人们所谓的“荒凉之地”,对于拉特罗大叔的儿子却并非如此:“小男孩尼尼现在知道了村子并非荒漠,在每一寸播种过的土地里、杂草丛生的荒地里,活跃着各种各样的生命。”
三、城市的“进步”对农村和捕鼬人的逼迫反映了文明与自然的对立
拉特罗以出售在河里捕捉的水鼬为生。然而城市世界终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在他的天地。政府为了解决“居住山洞之耻”,要求他离开山洞去住房屋。解决村子另外三个山洞不难:给住户们换一所偏远老村子的房屋,将其分成三部分,每个月租金为20个杜罗。这事儿是部长以“规划”的名义强迫镇长,镇长逼着村长,村长下令民警何塞·路易斯,层层压力之下不得不进行的。根据报子弗鲁托斯反复宣读的“离开山洞协会”的决议,以一个工作日30个比塞塔为条件离开山洞,这笔交易没有确定的价格,毫无商量的余地。他们给拉特罗提供了几种解决办法,只要他答应离开当地仅存的最后一个山洞。拉特罗拒绝了,他固执己见:“我不走”“山洞是我的”,他与体制对抗,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搬迁。
文明的工业化世界、现有的体制认识不到那个作为自然之窗的山洞的价值,然而从那里可以享用独特的自然空间:山谷、河流、山峰、荒野、小山包、灯塔、丘陵……;观察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动物:小鸫、负鼠、石鸡、野兔、燕隼、鸽子、朱顶雀、赤胸朱顶雀、黄足豉虫、欧夜莺、凤头麦鸡、喜鹊、鸫、云雀、戴胜、长尾灰喜鹊、蜂虎、灰林鸮、雕鸮、蚊子……;欣赏品种丰富、各有价值、外观美丽的植物:麦子、马铃薯、蔬菜、细茎芦苇、宽叶菖蒲、灯芯草、疯长的薄荷、各种各样的毛茛、白色欧石楠、三芒山羊草、驴蹄草、长寿草、蒿草……;与壮观的天然气象共存:冻雨、寒风、暴雨、霜冻、冰雹、雪花、烈日……。
四、大自然的“屠夫”偷猎者和业余猎人在禁猎期狩猎破坏了生态平衡
在《水鼬》中,拉特罗大叔是捕鼬天才,他技艺精湛,无可挑剔。“他耳朵紧贴地面,倾听地下的动静”,动物般的本能使他行动干净利落,迅速准确。小男孩尼尼带着母狗法儿第一次陪他打猎的情景是这样描写的:“拉特罗将探棒准确地刺入土中,不料水鼬逃掉了”。他们仨紧追不舍,过了不久法儿嘴里叼着猎物回来了。拉特罗大叔有时候独自一人打猎,他将右手伸进河底的淤泥中摸索,用左手刺入,很快就看见他右手举起钳住的猎物炫耀战利品。然而,当禁猎期到来时,拉特罗立即停止狩猎,他尊重动物的繁殖期,直到来年秋季才开始狩猎。他是一个拥有高尚职业操守的猎人。与拉特罗相反,马蒂亚斯·塞莱珉则是偷猎者,他和拉特罗一样动物化了,但是方式不同,他狡猾、居心不良,令尼尼反感。他晚上活动,白天睡觉,整年都在狩猎,不给动物片刻喘息之机。他的狩猎原则是:对待野兔“连窝端”,用霰弹打烂动物头颅,不给它们别的选择机会。在马蒂亚斯身上,没有猎人的浪漫主义性格,他不是真正的猎人,而是屠夫。
拉特罗将水鼬卖给马尔维诺,后者在村子里有一家小酒馆。马尔维诺给一只鼬的开价是两个比塞塔。他买下拉特罗用背袋送来的水鼬,从中取出两只,给拉特罗用醋煎了吃。拉特罗的这餐盛宴还包含两杯葡萄酒和半块圆面包。
拉特罗的另外一位竞争对手是邻村的捕鼬人路易斯。他是业余猎人,打猎是为了消遣,然而,就像马尔维诺在他的酒馆里提醒拉特罗的话,路易斯是来跟拉特罗抢饭碗的。在路易斯还没出娘胎时,拉特罗早已经是打猎的行家里手了。路易斯是个公子哥儿,眼神聪明,脑子灵活,工于心计,言谈利索。他穿着深色毛料西装,漂亮的袜子,脚蹬用亮钉点缀的靴子。拉特罗叫不上他的名字,他和村里人都叫路易斯“那个家伙”。在水鼬数量锐减的时节,他没有停止捕鼬,拉特罗大叔因此杀死了他,彻底解决了缺鼬的问题。
五、文明与自然冲突的激化——拉特罗杀死竞争对手,失去捕鼬人身份
狩猎季结束了。饥饿的阴影降临到捕鼬人身上。告别狩猎的聚会上,人人都无水鼬可吃,拉特罗气得暴跳如雷。好在捉螃蟹似乎可以暂时缓解捕鼬人的境况,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螃蟹也很快就捉不到了。在村子里,当天际隐隐约约出现一丝薄雾的时候,庄稼收割在望。外号“精明人”的村民布鲁登听从尼尼的建议,收割了自家的小麦。但是村子里其他人不理会尼尼的劝说。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在五个小时之内摧毁了所有庄稼,颗粒无收。在这个悲惨绝望的气氛中,尼尼和路易斯在杨树旁的沟渠边不期而遇。他俩正在交谈的时候,拉特罗大叔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狂怒地攻击邻村竞争对手,一边叫喊着“水鼬是我的”,路易斯反抗他的攻击,企图制止他。拉特罗大叔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发起冲击,大喊大叫,用尖棒刺他,最终将对手置于死地。他拖着公子哥儿的尸体,“连续3次捅邻村小伙子的心脏,毫无怜悯之心”。由于誓死保卫山洞,他将失去山洞;为了保护水鼬的繁殖,他杀人犯法,再也不能捕捉水鼬了。城市世界的政府部门,国家机器不会理解他,尼尼说“他们不会理解他的”。政府趁机捣毁了这个粗野而自生自灭的空间。一方面由于拉特罗的无知、缺乏智慧,另一方面由于文明社会的组织体系遗忘了他们,政府部门也没有认真地追查导致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拉特罗的农村世界未能保护他的领地、他理性的一面及他身上的善良忠厚部分。
小说是这样结尾的:“在山岗的后面可以望见教堂的钟塔一如既往地耸立着,教堂周围,村庄里灰暗的房屋一栋一栋逐渐地在晨曦中出现……”,这就是乌纳穆诺笔下的“宁静而持续的生活”。具体到这个故事,就是乡村世界永恒的传统偶尔出现的波折——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班牙内陆卡斯蒂利亚乡村的意外事件:文明与自然的冲突。
结语
德利维斯的《水鼬》自1962年发表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阅读,已然成为经典,具有普适性。作家通过“捕鼬人”这个具体人物和其所处的环境,以象征性的方式再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在拉特罗身上,乡村世界、城市世界及社会体制碰撞了,然而他的遭遇揭穿了政府的谎言、法律的刻板及环境的恶劣。
“生态文学发出的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心灵诉求,是从文学文本中空前地凸显人类的重大困境,并对这种危及人类整体未来的困境加以审美解答,进而超越对具体问题的思考而直接深入到对智慧的深层关注中去,激发起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联系的内在情感,寻找人类与自然重归于好的和谐世界的新途径,探索人与自然发展的互惠型人类自然新伦理”。在尼尼身上,陷入无知和不幸的乡村世界和正在“进步”却对事物和人失去了真实感觉的文明世界得以协调,大自然没有使他窒息,“进步”也没有掏空他。作者赞扬他纯真而聪慧的心灵,给乡村世界的拯救留下了一束希望之光。《水鼬》表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坚决捍卫,赞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部作品仿佛是发自卡斯蒂利亚荒漠中的呼喊,那里的人们不得不咽下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破坏自然的苦果。那里的农业受损害,森林被滥伐,然而卡斯蒂利亚农村的淳朴生活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将活在德利维斯的作品中,成为历史的见证。《水鼬》表现了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密切联系。
①刘青汉.生态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②沈石岩.西班牙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
③MiguelDelibes,Las ratas,Destino,2000,P11.文中引文皆出自该书。
④Miguel Unamuno,En torno al casticismo,Biblioteca Nueva,1996,p63.
⑤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文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