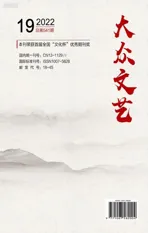《民谣》叙事伦理与叙事技巧初探
2022-10-21邓全明
邓全明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400)
一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民间歌谣汉乐府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民谣者,民间之歌谣也——个人情感、大众生活、民间立场是其重要表征,著名评论家、学者王尧教授的新作《民谣》虽为小说,但不乏民间歌谣表征,这应是名之为《民谣》的原因之一。
《民谣》首先是一曲个人色彩较强的青春小夜曲:追忆一段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青春往事,表现一个乡村少年梦想、迷茫、伤感。虽然生活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偏远贫穷的乡村,但并不妨碍“我”做种种青春的梦想。“我”梦想的直接资源来自勇子和表姐——那个时代的乡村范儿。那时的“我”——王厚平——虽然只有十来岁,但字写得不错,作文也不赖,后来又成为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被生产队视为小才子、小能人。不过,“我”的青春梦不久就受到沉重打击:先是石油勘探队离开了莫庄——勇子依托石油的美好设想随之落空;后是他的偶像勇子因为与秋兰结婚,调离岗位,离开莫庄。“我”虽然理解勇子的选择,但他认为自己应该比勇子更勇敢,故他并未因此丧失对未来的期许。尽管“我”没有放弃梦想,但现实却令人沮丧。“王二队长,外公,胡鹤义,勇子,他们都想改变生活。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但他们都失败了。我十四岁了,我看到了无法改变的生活”,“我”虽以王二队长、勇子自许,希望干一番事业,但并知道路在何方,苦闷、迷茫萦绕心头。很多年前,作者就为《民谣》写了开头:“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接着写道1972年的那次洪水以及洪水过后麦秸秆霉烂的场景,其后多次写道“我”对这场洪水引发的腐败气息难以忘怀的记忆。显然,像薄纸一样缺少热力的太阳、挥之不去腐败气息,是“我”对段青春岁月最深刻的记忆。
爱情也是《民谣》这曲青春小夜曲的重要旋律。《民谣》讲述了多对恋人的爱情故事:秋兰与勇子、巧兰与阮叔叔、独膀子与小云、“我”与方小朵和许玲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方小朵的情感故事。方小朵是一个情窦初开的漂亮女孩,她显然有意于“我”,“我”虽对青春男女的爱恋并非一窍不通,但在大方、美丽的方小朵前略显笨拙。方小朵离开前特意来“我”家一趟,吃完午饭后,一对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划着小船,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游玩,如诗如画,方小朵淳朴、真诚的挑逗更是增加了诗情画意。丘田说:“《民谣》里有不少生动的女性形象,一些女性刻画让人联想到沈从文笔下天真未凿的少女”,方小朵确实与沈从文笔下的少女类似,也不失汪曾祺笔下的少女的神韵,她与“我”青涩但天真无邪的情感可谓那个时代爱情的天籁之音。这段情感虽没有结局,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和许玲的一段爱情则让“我”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在“我”看来,许玲才是“我”的第一个初恋情人,因为我们可以将它与可设想未来——“我”能考上大学、她能回城——联系在一起。但命运弄人的是“我”高考失败,而她如愿成为工人,两人的爱情戛然而止,留给“我”沉痛的人生教训是爱情脆弱如薄纸。
生离死别虽说是人之大道,但对于人生刚起步的青春少年来说,死亡,特别是那些意外的死亡,总让人无法释怀。《民谣》写道许多人的死亡:胡鹤义、胡鹤义的大儿媳;小云、四爹、“西头老太”、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烂猫屎、根叔一个个离开了人世,让“我”嘘唏不已,而三小和根叔的死,更让“我”感慨万分。三小是“我”非常要好的小伙伴,他和父亲一样患上肺结核。多次咯血后,三小预感到自己离死神不远了,约我一同去打麻雀吃。那天晚上虽然嘴里嚼着平常很难吃到的肉,但无论是“我”,还是三小,心里都在流泪,都涌动着无尽的悲伤。三小的死,显然是“我”生命中的一件重大事件,以至多年“我”会将黄灿灿的油菜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在蓬勃的生命里闻到死亡的气息。“我”之所以对死于鼻癌的根叔印象深刻,不仅是他家离“我”家近、曾教我唱儿歌,还因为在他死前“我”的另外一个伙伴梅儿因为家里穷被迫去了远方,使“我”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命运的无常。
对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我们不难发现《民谣》中的乡村少年与作者王尧的人生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我”的“哀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刻骨的人生体验,作者正是因为这份“哀乐”创作了《民谣》。当然,虽说《民谣》中的“哀乐”具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
二
班固以为汉乐府的成功不仅在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还在于能让读者“观风俗,知厚薄”。班固所说“观风俗,知厚薄”即朱熹所谓“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民谣》之为“民谣”,亦该有此中之义。
叙述人的外公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使家族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建立了关联,也建立了“观风俗,知厚薄”的通道。胡鹤义作为镇上最富有的人,并非罪大恶极的恶霸,而是得到不少民众尊敬的士绅,他自杀身亡后不少人为他烧纸便是最好的证明。不仅如此,胡鹤义还和当地革命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王二队长曾经在他避过难,他和他的部下十几人牺牲后,是胡鹤义为他们收尸。这样一位开明绅士,在“文革”时期也不得不以自杀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胡鹤义的命运与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相似,但《民谣》没有赋予其形而上的意义——对正义的否定,也没有完全丧失对正义的信心。对于胡鹤义,外公在自己的审查结束后,转述了县委领导的评价,这一评价代表组织,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叙述人、隐含作者的看法。“革命的合法性和崇高性是毫无疑问的,但革命成功以后的问题也是需要反思的……不能以后来的悲剧否定之前的崇高,也不能以之前的崇高遮蔽之后的悲剧”,王尧在《访谈录》的这段话与组织对胡鹤义评价一脉相承,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理性、务实精神。不仅是革命与反革命者的关系,不像一段时期的革命小说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而且,对于个人来说,革命与反革命的选择,也具有某种随意性、偶然性——独膀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王尧像新历史小说那样,将类似历史事件的意义做过度、极端的阐释——否定整体性、本质等,而是旨在展示历史的复杂性、人在历史潮流前的渺小、无奈,表达对人物命运的同情。
作为“‘文革’时期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王尧对于那段历史和那段历史时期的文学了然于胸,而作为小说作家书写那段历史,他能为读者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什么新的视野呢?关于“‘文革’时期的文学”,王尧倡导“关联性研究”:“要在‘断裂’中发现‘联系’,在‘联系’中发现‘断裂’”。“关联性研究”的实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联系的、发展的、全面辩证的观点看待“‘文革’时期的文学”。文学如此,历史也是如此,《民谣》所呈现的“文革”时期的乡村生活也体现了同样的历史观。最能代表那个时代风气的人物是勇子和表姐。作为社会组织的基层干部,勇子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前途、理想和那个时代紧密相连,希望顺着时代“大势”实现个人理想。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他的个人情感与时代要求很快出现了龃龉。勇子喜欢秋兰,而秋兰是富农。如果勇子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和秋兰结婚,他的政治前途就结束了。何去何从,勇子曾经犹豫过、痛苦过,经过一番思想和情感的斗争后,他选择了秋兰,放弃了政治前途。表姐是妇女队长,那个时代的铁姑娘,她本能地感应到那个时代的脉搏,并不假思索地按照那个时代的要求塑造自己。表姐原来喜好文学,从北京串联回来后,面貌大变,决定成为一个在农村一线建功立业的新女性。作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勇子和表姐无法摆脱那个时代偏执与简单以及来自意识形态的挤压,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基本的人性。抑或《民谣》的故事发生在历史一隅的乡村,并采用了民谣的叙述方式与立场,因而与那些过度演绎历史对个人的挤压的作品之间画了一条线。可以说,无论写革命史还是“文革”史,作者始终保持比较清醒的理性精神,从而呈现了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也为读者观风俗、见得失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三
虽然具有较强个人性和民间性,但《民谣》并不是民间文学,而是学院派作家的小说创作,这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体现在形式上。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王尧就提及“小说革命”一说,在2020年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他再次推出“新‘小说革命’”,可见其对小说艺术革新的重视,《民谣》在艺术上确实有不少“革命”性的探索。
《民谣》的艺术探索首先表现在文体上。《民谣》由三部分构成:卷一到卷四为第一部分,外篇和杂篇分别为第二、三部分。读过《庄子》的人很容易由其内、外、杂篇之分将第一部分视为“内篇”。《庄子》之所以有内、外、杂篇之分是其中作品有地位、性质的区别,《民谣》也是如此。第一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差异首先是文体上。虽然第一部分故事性也不强,但无疑仍属于小说。第二部分为“我”中学时的作文、替人代写的各种应用文以及“我”对上述材料做的注释,这些内容并不直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是独立存在,因此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小说。外篇篇幅最短,为“我”中学时期杨老师创作的一篇几千字的小说残稿,虽是小说,与通常见到的“小说中的小说”不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外篇、杂篇的性质及与第一部分的关系。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称为“叙述转向”的思潮,“叙述转向”波及新闻学、心理学、医学多个学科领域,其中也包括社会学。放弃实证研究,通过“田野调查”、个体叙述等手段凸显个体的意义,是社会学“叙述转向”的重要特征。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掀起一股“非虚构写作”热潮。中国的这波“非虚构写作”浪潮可以说是“叙述转向”在小说领域的体现,或者说小说借鉴了社会学叙述方法。众所周知,叙事学首先诞生小说,赖恩将叙述定义为:“再现包括一个设定在时间中的世界(背景),居住着参与行动或发生(事件,情节)的个体(人物),从而发生变化。”,通过赋予特定时间中个体行为意义是叙述的突出特征。因为其具有个别性、特殊性,故而被科学排除,而叙述转向最大的意义正是凸显个别性和特殊性。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也在于此:恢复被典型化遮蔽的个体性和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民谣》的外篇、杂篇具有非虚构写作的某些表征,但它并不属于“非虚构写作”。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外篇和杂篇类似采用叙述学研究方法的文献,将社会学之“文”与文学之“文”融于一体,拓展文学的表现手法,是《民谣》的一个艺术创新。
第一部分和第二、三部分关系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我”和作者的关系——小说中的“王厚平”与现实中的王厚平的关系。作者王尧原名为王厚平,阅读《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后,我们会发现小说《民谣》和真实的王尧的生活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有意将小说人物与作者及其生活混淆,并不是《民谣》首创。众所周知,莫言现代派小说代表之作《酒国》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莫言、王尧对话录》中王尧特别提到这部作品,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据此我们有理由猜测《民谣》的这一构思多少受到莫言的影响。当然,《民谣》的这一手法具有自己的意义。我们知道《酒国》让“莫言”在文本内外穿行,目的是混淆真实与虚妄的界限,以否定现实的真实性。《民谣》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让王厚平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穿越,意在展示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洪治纲谈道“非虚构”写作时说:“‘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民谣》中叙述人与王尧的关系也是如此,而《民谣》中的仿“非虚构”写作,不过是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提供一种新的形式可能性。
《民谣》的结构也颇有新意,这不仅体现在内篇、外篇、杂篇的设置上,也体现在内篇之中。时间性是叙事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与之相应的是叙事作品通常将时间作为结构的重要依据。小说作为叙事文体,时间也是作者谋篇布局考虑的重要因素。在人类早期的叙述作品中,通常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讲述故事;在比较成熟的叙事作品中,虽然事件出现的顺序不再完全按照时间先后出现,而是通过倒叙、插叙方式,重新组织故事事件,但事故本身的时间顺序清晰可辨。意识流手法是对小说叙述的一次重大颠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时间的中断——时间被分割成许多没有时间性的片段。《民谣》内篇分为四卷,在时间上并不存在先后关系,那是否存在其他的内在关联呢?如空间的,逻辑的?小说卷一从1972年5月的一场大雨开始叙述,其后介绍莫庄的风水、地理,讲述外公的人生故事;卷二一开头这样写道:“外公和奶奶的故事不同,他们分别筑起一条田埂和一条砖头铺成的街道,我沿着奶奶的街道摸到了以前镇上的老屋,沿着外公的田埂回到了我现在的村庄”,似乎卷一、卷二分别讲述“我”母亲和父亲家族的历史。细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各卷或有所侧重,但其时间和空间交织、重叠,并不存在明显的时空界限或逻辑关系。笔者以为“内篇”之所以比较随意安排小说事件,意在以散文的结构模式来处理小说,其目的不是让小说诗意化,而是非传奇化。中国古代小说有两种不同的传统:传奇体和笔记体。魏晋的志人和志怪小说,传奇与笔记平分秋色。唐人重传奇,将小说称为传奇可见一斑。宋元明清小说,虽以传奇为主流,但笔记小说亦不绝如缕,并不乏佳作。生活固然有传奇,但传奇不是生活的常态,因此别林斯基特别强调“按照生活原来的样子”描写人物、反映生活。《民谣》有意于笔记,应是平实的现实主义审美追求的体现,也在作者作为学者型作家注重理性的体现。
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评论家,王尧先生的学术著作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不喜搬弄西方述语自重。之所以如此,抑或与王尧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有关。《民谣》对“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散文的笔法和结构、“非传奇”的叙述追求,依稀可见传统的影子。由此而言,《民谣》既是一次“新的‘小说革命’”,也是一次传统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