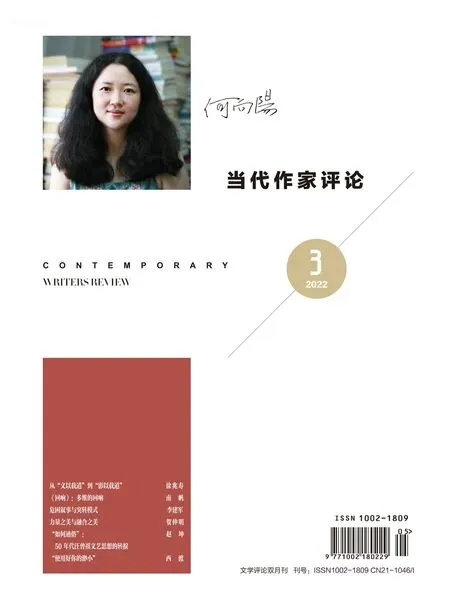目光、生命与记忆
——王威廉与未来诗学
2022-10-21刘大先
刘大先
基于这种现实感,王威廉从2018年开始将科幻元素纳入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确实,科技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它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从科幻文学史的进路所牵涉的亚文化。因此,他晚近的小说很难说是作为文学史边缘文类的“科幻小说”,这些小说既非技术流的“硬科幻”,也没有过多的政治与哲学角度的“软科幻”色彩,或可说他是在写一种从现实问题生发想象而产生的微型思辨文本。那些文本从文学性上来说也许并不很讲究,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它们的侧重点所在;或许也谈不上太多的思想性,因为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议题,而主要着眼于技术垄断及其带来的人的情感与精神方面的变化。他念兹在兹的话题是:如何面对野蛮现实,如何想象人文的未来。
摄像头就是目光、眼睛和观看本身,它将实在世界转化成了影像。表象取代实在成为超真实,一旦遭到反向的挑战(因为表象无法进行深度反思,只有即时反应),它就显示出自身的脆弱和无力。小樱男友的自杀或许由此可以得到解释。2017年,曾经有一则社会新闻,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2014级研究生葛宇路开展了一次行为艺术:搭建脚手架爬到和监控摄像头很近的位置,然后和监控摄像头对视。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有没有启发王威廉的创造,无疑《不见你目光》也体现出类似的反向凝视。但它似乎也并非意在体现被凝视主体对作为权力体系的目光的反抗,而更多表现为类似双缝干涉实验展示出来的量子纠缠状况。关于这一点,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有更为详细的叙述:在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物质与对象处于量子叠加态,或者说处于一个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的概率云中。当观察者出现时,物质与对象就向某个确定态塌缩。观察者的在场在这种情形中变得极为重要,被观察对象的不确定性在目光出现的时候就发生了转化,它的薛定谔式状态被目光确定了下来。从换喻的意义上来说,即某种世界观决定了所看到世界的面目,如同美杜莎的眼睛将看到的一切都固化下来。进而言之,透视未来的眼光是一种确定性,会改变未来,未来可能从未到来,它取决于现在本身,我们想象到的未来即是现在的投影,只是这个投影反过来作用于现在。
目光的普泛化是当代景观社会喜忧参半的现实,人们对此的态度暧昧错杂。《地图里的祖父》就有一种对“元宇宙”的犹疑。虚拟技术造成的影像让祖父的形象得以在死后存在(甚至永存),让孙辈的情感得到寄托,虽然是虚构的,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无限真实的。不过,就总体倾向而言,王威廉依然秉持了对影像现实的批判立场。《退化日》中的“我”因为喜欢安静和发呆而没有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偶然的机会被做了警察的老同学招募为联防员,工作就是盯着监控摄像头。在警察看来,他的发呆凝视与盯视摄像头差不多,殊不知两者并不相同,因为发呆其实更多是“向内(时间之内和记忆之内)注视”,而不是成为机器的辅助,即外向式的凝视影像。正是这种区别造成了“我”最终无法适应已经全面景观化的世界的最终逃离,向原生态的环境退去。“我”是基于虚拟真实已经侵占了生理真实的现实而做出的抉择——返归身体的实感经验和内心的记忆,这必然关乎如何认识生命存在本身。
《城市海蜇》便可以解读为关于一个人的身体与身份之间关系的讨论。在深圳广告公司做摄影的孔楠远离家乡,与旧时好友张锋渐行渐远,张锋死后关于张锋的记忆也正在淡去。某天孔楠收到一张自称张锋女友的人寄来的明信片,画面是深圳的海蜇,这让他备感好奇。他在深圳只找到一片看上去遍布海蜇实际上却是塑料垃圾的海滩。当女人来访时告知其就是变性后的张锋时,更是让孔楠莫名所以。当他俩来到那片遍布海蜇(塑料垃圾)的海滩时,孔楠注视着女人近乎完美的身体,关于她是否是张锋已变得不重要了。身体所表征的生命实体,让海蜇与塑料的对立融化在对于实感的经验之中。《幽蓝》讲述的是一架飞机被意识觉醒的人工智能劫持的故事,叙事视角由一个出生于北方小城到南方做推销员的男子展开。如果我们硬要给这篇小说寻找现实的影迹,它似乎是从2014年3月震惊世界的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事件的猜想而来,但它更多着眼于对生命的思考。被劫持飞机上的推销员看到机窗外美得令人心醉的幽蓝,回想起少年时代从家中窗外看到的远山深谷中的幽蓝,那是一种莫测与神秘,就像生命的秘密。在这里,生命被理解为超越了肉体束缚的自主意识,是一种万物有灵式的自由。
《潜居》中主人公的女友早年身亡,他用一个机器人作为替代,但芯片存储的记忆只是让机器人永远停留在她去世前的状态,这让他感到遗憾。同样作为怀旧的人,他与朋友敬亭打造了一个水下的故乡,“通过未来回到过去”,在那个微型的乌托邦里,一切都回到了少年时的模样,但这又让他有种自欺欺人的感觉,他还是期待有真实的身体接触和充满可能性的未来。记忆固然重要,但“我们会根据现在的需要去重新阐释记忆”,在《分离》中,王威廉将这种矛盾以冲突的形式展现出来。《分离》中,女主人公栗子在商场体验了一种能让回忆昔日重来的机器,而这个机器正是她的前男友孙坚发明的,当初他们因为理念的差异而分手,回忆让她重新燃起对他的情感。但孙坚只是爱着记忆中的栗子,那个过去已经是一个确定性的过去,而栗子则对世界的奇异性保持着敞开的心胸,也即未来的不可测才是其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居》与《分离》都指向了生命的体验性和发展论,拒绝某种确定性和本质化的存在,这种观念同他前述那些关于“目光”的小说一脉相承。
所谓古典主义的回归,并不是回到某种刻板的律令之中,在王威廉那里,它是聚焦于以人的感受力为中心——恰恰是人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要拒斥那种单维度的消灭奇异性的本质化想象。在我看来,这就是“野未来”的意义所在,这个词语是王威廉独特的创造,最初出现于《野未来》。《野未来》是王威廉此类作品中为数不多涉及较为广泛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城中村里具有科学天赋的边缘青年赵栋并没有融入主流社会的欲望,甚至拒绝了走普通人的谋生之路,拒绝被规训的未来,这不是wild future,而是future at large,即在逃的、未被规约的、不受束缚而充满多样性可能的未来。
中国科幻的起点便是以未来为旨归——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勾勒的是宏伟蓝图,一种基于现代性视野的远景目标。这一切经过整个20世纪的革命、建国、改革的历程,尽管与梁启超所设想的政治目标在具体形式上存在着参差,却毫无疑问在结构上实现了那个总体性未来的到来。而到了王威廉这里,那种关于未来的乌托邦变得不再那么不证自明。对确定性未来的放逐,固然有着缘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实践转型的原因,从思想上来说,根本性的原因在于,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理论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相应技术变革对生活世界和人们世界观的改变,用一个快要被遗忘的词语来说,这就是“后现代”,而之所以“后现代”不再成为显赫的话题,可能正因为它已经成为习焉不察的现实日常。
这篇小文主要以王威廉的小说集《野未来》中收集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你的目光》为讨论对象。这些作品跟科幻文学的小传统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它们在尝试接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的思辨小说。之所以采取了科幻的形式,是因为科学与技术已经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日常的组成部分,就如同农耕文化中的田园牧歌、工业文化中的写实小说,它是我们这个文化融合时代的主流文学,而不是像此前一样,作为亚文化或者类型文学、通俗文学、儿童文学或者科普读物的面目出现。所以,这些作品具有范例的意味,是一种文本形态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