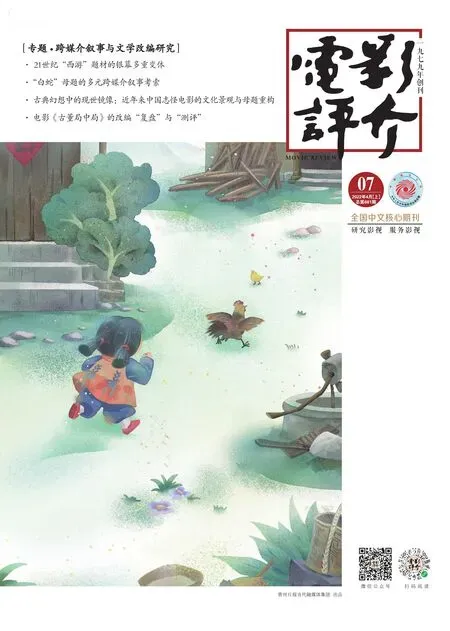超越在场:论纪录片“场”的深度表达
2022-10-09余洪源么加利
余洪源 么加利
自弗拉哈迪(Robert Joseph Flaherty)以声像方式将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真实而清晰地呈现出来,其对真实性的推崇被后续纪录片奉为经典。纪录片也成为人们关注事物、发现世界、表述世界的新方式。随着拍摄工具的迭代、视听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纪录片对清晰度的要求不断攀升,镜头也囊括了越来越多有用的信息。有关纪录片的研究与探索也多聚焦于影像表达、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等。毫无疑问,上述探讨推动着纪录片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显而易见,这类研究范式存在着研究视角的偏颇,即只关注了纪录片作为媒介所具有的功能和特性,忽视了其场域的重要影响。这种工具理性研究只关注了纪录片的在场性(presence)(即真实性的传达成效、效率),忽视了其不在场性(absence)(即隐蔽于信息后的事物完整性)。而纪录片表达的最终目的,正是让受众超越自身的文化背景,从现象体验到规则理解,最终获得德性层面的改变。要把握纪录片的深度表达,需从“心物场”理论出发,讨论纪录片场的深刻意涵,从“在场&不在场”的分野与内在整体性讨论纪录片丰富的场效应,从对思维理性的突破阐释跨越之道。
一、纪录片场的概念释义
场域是个多义性概念,物理学称物理时空,心理学称心理构成,社会学称社会网络,信息学称信息中介。虽然每个学科都赋予了场域以不同的内涵,但是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即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存在着不可见但可感的力,这种力对场域内事物均会造成影响。本文运用勒温(Kurt Lewin)的心物场理论对纪录片场及其对观众群体的心理行为影响进行观照,认为纪录片场包括了两大系统,一为客观存在的外界环境,这里称为纪录片的物理场;一为主观认识中的现象,这里称为纪录片引起的心理场。
(一)纪录片的物理场
从物理角度看待场的解释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其一,狭义的物理场源自物理学的场论。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在电磁场理论的研究中最先提出并确立了物理场的存在。他们认为带电或磁的物体周围弥漫着一种电子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实体)能传递电的相互作用。而后曾华霖认为将场仅定义为“空间仍有不足”,之后根据物理学《场论》原理澄清其定义为“空间中存在的物理作用”,强调了场的研究重点是“作用或效应”。这一视角下纪录片的物理场是纪录片作为视听媒介的物理特性产生的,对其探讨的重点应为光电效应。其二,广义的物理场实是物理学场论在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衍生,属于一种概念隐喻。这些学科认为事物都具备产生场并影响人的能力。这一视角下纪录片的物理场是由其客观存在本身产生的,是纪录片对人的作用力。
基于以上理解,纪录片中物理场的书写一定离不开纪录片的光电特性及其对人的影响。这两点共同构建了纪录片物理场的空间,并形成了场效应。媒介环境学旗帜人物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于《理解媒介》中讨论电视和电影时也曾提及这种由物理场所产生的影响。他使用“through”(透射)来描述电视的自发光特性,认为其以观众为屏幕,以每秒钟发出300万个光点的强度轰击着观众;使用“on”(照射)来描述电影的反射光特性,认为其屏蔽环境光线、营造唯一光源的播放手段,足以形成让观众沉浸其中的氛围。所以纪录片的物理场是“以非语言的完形(gestalt)或姿态(gesture)”营造出充盈着光电流动的传播情境,在此情境中观众可以获得多层次、多感官的沉浸式体验。
(二)纪录片所引起的心理场
纪录片的心理场其实是由纪录片的物理场所引起的观众的心理场。勒温继承了考夫卡(Kurt Koffka)对“心物场”的心理学解释并将其明确为“任何一种行为,都产生于各种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以及这些相互依存的事实具有一种动力场的特征”。他提出公式来揭示人的心理或行为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自我的相互作用。每个(自我)都将客观外在的(环境)解释为不同的,又反作用于导致其变为,最终得到完全不同的。借用傅统先先生在译著《格式心理学原理》序言中的有趣案例来解释尤为贴切:“标识语‘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我们可以作为‘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也可作为‘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此等客观环境可能导致三种心理结果:一为忽略,个体自身状态(不想小便)与环境没有交集;二为由于个体自身状态导致对标识语进行上述第一种解读;三为个体进行第二种解读。而造成不同解读的能量来源正是心理场。
纪录片物理场不断改变着客观情境,导致观众的心理空间不断产生和释放着紧力(tension),力的紧与放的变化为观众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提供动力和能量,催生其心理改变和行为表现。但是纪录片心物二场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纪录片“场”对于纪录片的深度表达又具备怎样的意义,我们还需借用“在场与不在场”的哲学思考来界定。
二、在场意义下的纪录片:召唤真实
“在场(presence)和不在场(absence)”是西方形而上学体现存在论基本意义的一对概念。萨特提及“不能把存在定义为在场,因为不在场也解释存在,因为不在那里依然是存在”,即在场与不在场是存在的显态与隐态。
纪录片因“记录真实”而被命名,《北方的纳努克》()甚至成为了照亮影视人类学前期发展道路的明灯。纪录片的在场意味着可见的存在,是当下的、真实的,分为物理在场和内容在场。纪录片的物理在场是客观外在的、可知可感的,是其作为视听媒介被众人所熟知的形态,是与其他媒介诸如书籍、录音等相区别的特征。纪录片的内容在场意味着纪录片表达各要素直接的、当下的展示,其主线必须遵循人类理性逻辑。比如饮食类纪录片必须循着食材采集——炊具准备——烹制加工——品尝这一逻辑进行拍摄,且必须兼顾到食材挑选、调料搭配等各个细节。如果逻辑与细节丧失,其真实性也就降低了。纪录片的在场构建起稳固的客观外在,召唤观众的心理场产生同调的在场感。这种在场感不仅是传播学意义上由感官或交互所产生的“临场感”,也包括具有哲学意蕴的认识论层面的、知性的、通过纪录片内容获取的信息。纪录片在此时的角色与教学场中的教师类似,具有权威性和引导性,其传播内容能被观众较好的接受和认同。
如果纪录片只强调在场、过于追求细节,必会给观众感官带来更大的负担,在不经意间提升观看压力。为避免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有必要放下在场,探求纪录片不在场的意涵与作用。
三、不在场意义下的纪录片:艺术表达
不在场是指“存在的缺失状态,即在空间上的隐蔽,时间上的非现在时刻(在过去或未来)”,是存在论硬币的另一面。纪录片的不在场也分为物理不在场和内容不在场。纪录片的物理不在场源自视听媒介的时空断续性,如平面对空间的遮蔽,视频帧在时间线上的缺失。纪录片的内容不在场即为运用镜头语言所创造的时空上的空缺,意同绘画的“留白”。创作者将题材进行艺术加工,造成时空上的省略,促发观众用完整的生活经验进行自主补充,将其改造为自我期许的事物完形。纪录片的物理和内容不在场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形成了“心理场的非平衡状态”,观众心理场产生紧力使其自主填补了纪录片的时空不连续、内容不完整,并通过延续情感的方式释放紧力,达到心理场新的平衡。
用国画“写意”的意境来阐释这种心理场的动态效果再合适不过。相传宋徽宗为挑选画师曾出题“深山藏古寺”:既要让人明白画中有寺,又必须藏而不显。画师一般采用半露半掩的手法在密林深处、山腰画出寺庙的一角或残垣断壁,唯有“老僧林间舀水”的画获得肯定。用心理场来揭示的话,前面看似委婉实则直白的画毫无变化可言,无法激起心理场的动力,而老僧舀水不见寺的画面让观众的心理场为“寻找寺庙”这一目的产生紧力,并在获得“有僧就有寺”的结果后释放紧力,一紧一释之间形成动力,留下意蕴。这种笔、意俱佳的境界不仅看重画面的留白,更看重值得反复咀嚼的回味。这不仅是国画境界的追求,也是不在场所表达的意义。
同样,纪录片作为艺术表达形式较之国画更甚的是,它在时间和空间的表现上都能留下想象余地。纪录片通过事物表面力透纸背般发出的超越主题内容的情感呼号,让它具备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引起观众的移情和共鸣。这些痛苦的、快乐的情感让纪录片所表现的内在意涵,犹如绕梁之音萦绕不去。比如《最后的棒棒》用自述式的画外音配合朴实的镜头语言描述了老黄、老杭、大石、老甘几位平均年龄60岁的重庆“山城棒棒军”的日常生活,没有高清画面和饱和色彩,也没有煽情语句和后期修饰,“却迸发出摄人心魄的强大力量,如同一个问号无数次叩问着关于‘活着’与‘幸福’的定义”,让观众 发出“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的感慨。
从上述看出,纪录片的不在场追寻的是艺术表达。其实诸多纪录片在拍摄期间都或多或少地掺杂了导演的个人意图,学界也明确了纪录片的真实性不同于客观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一种以美学风格和审美为出发点,对真实事物做创意的处理后的结果。早在1979年出版的《电影术语汇编》中也曾提及“纪录片首先是在艺术领域和虚构的故事片相对应的,他们都是艺术但又有不同(一个是真实的纪录,一个是虚构的)”。可见,纪录片的在场和不在场是共在的两面,在场召唤真实,不在场追寻艺术。但是由于不在场内容无法将意图直接展示于人前,往往被创作者忽视或放弃。当创作者堆砌在场的当下表达,不在场的艺术表达空间愈被压缩,遮蔽便产生了。当这种遮蔽趋于极致,表达最终变为了平铺直叙,观众的心理空间的平衡无法被打破,紧力无法产生,纪录片场和场效亦被瓦解,纪录片便沦为了在场的附庸。要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就必须突破在场,达成超越。
四、纪录片的超越之道
超越在场就是超越思维的、抽象的,就是超越对真实的刻板认知,达成对有限意义的突破;就是超越理性对知性的固守,达成思维的跳跃;就是超越工具理性,达成对功利性表达的消解。超越让人取得与万物共在的联系,达成人对自己的无限认识,不再把自己禁锢于对象性认知中。超越在场的纪录片不再以效率论成败,而是以诗性的表达,让传播变为信息和情感相交织的“感染”,通过激发心理场让观众获得不同的知性和德性,通过有限的知性通达无限的德性,最终让观众在不同的自我经历的基础上与传播主旨共在。
(一)以多样超越真实同一性
现实生活中,真实性意味着客观存在的不可否定,是客观存在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表现;在传播中,同一性意味着知性信息的准确性和抽象性,是在理性层面被约定好的规则,有助于知性信息的理解。但是在心理场中,每个人的“真实”都是通过自己与环境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处于同一客观环境下的两人,通过不同的感知、忽视和想象形成了不同的“心中的真实世界”。故真实的同一性只存在于知性信息内,不存在于心理场内。所以只重视各种在场,单从认识论层面追求知性信息的真实同一性远不能解释个体理解真实的多样性。要解释这种多样性,必须首先承认心理场在客观存在基础上建立的“真实”的相异性,然后从知性层面讨论同一性,再超越同一达到相通。就纪录片的传播而言,其在场的真实性可以让不同观众对同一对象形成知性层面的同一,其不在场的艺术性会激发观众的心理场形成不同的“真实”,同与不同的“真实”既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又认可了人的无限可能,是谓超越。
(二)以无限超越真实有限性
自人类首次意识到“我”的存在,即刻通过自知意识到“非我”的存在,并逐渐以对象化思维面对自己以外的事物。哲学认识论的“主客二分”观点扩大了这种主客间的差异,“在主客体分立甚至对立中思考人和世界的关系,强调天人相分,个体独立于整体”。这一观点让主客关系变为狭义的二元论,以理性分析方式将知性从整体感知中抽离,将人的认识局限于事物的形态、结构,将世界限制于个体的认识能力之内,自此人所知的真实成为有限的真实。但人是自然的造物,“我”与“非我”原本应是一个紧密相关的整体,“我”应以知性德性一统的完形来获知整体的无限,而不是以人类理性画地为牢。在纪录片的传播中,在场的知性构建于人类理性之上,其背后隐蔽着无法用外部语言表达的真实和联系。但是其不在场为观众心理场带来的紧力,其艺术表达带来的无限遐想和情感共鸣,让“我”暂时抛却对“非我”的在意并融入传播情境,用开放的感知与想象突破对在场的固守,获得与知性相连的无限德性,是谓超越。
(三)以想象超越理性的固守
认识论是一种影响至深的哲学观点,人们在不经意间都在践行着这种理性思维。比如生活中最常用的博弈论、统筹学,让大家习惯于在行事前做好分析并形成方案。这些理性思考毫无疑问推动着人类社会滚滚向前且势不可挡,甚至可以说居功至伟。但是可以用理性这台巨擘回答诸多规律性问题,却无法用它来应对意想不到的情境。如果用“知性之圆”来比喻个体的已知,理性就是在圆内反复横跳的兔子,它的能力极限是从圆的一个极点跳到另一个极点,却无法企及圆外的世界。但是变化始终是宇宙不变的主题,偶然间圆里出现了一个洞,于是兔子通过洞第一次到了圆外。这个洞让兔子忙得不可开交,它慢慢把洞变成了四通八达的隧道最终越过了原本的圆。这个洞就是想象:想象建立于知性却超越了知性的桎梏,让人与无限共在发生了联系,是人类自有限通达无限的途径;它回应了人类对于未来和未知的期许,激励着人类思维的跳跃发展。
在纪录片中,将文化或生活作为一种对象性的知性来把握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个人的知性之圆都浸泡在其中,这些圆就像水池的涟漪一般发生着碰撞,每个圆随时都在坍塌或重建,每次坍塌与重建都意味着一次思想的跳跃。所以文化与生活情景所召唤的其实是想象。纪录片的不在场响应了这种召唤,以心理场多感官共振的丰富层次对接着文化情境中知性水塘的复杂性,为观众打造了沉浸于其中的完整体验,催生了想象,迸发了融通,是谓超越。
(四)以主体性超越媒介工具性
认识论层面将媒介用作主体与客体交互的桥梁,创作主体使用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并经由媒介将意图传达给客体。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具有工具性质,必须是准确的、规范的,就像是装水的碗,水被装进去和拿出来时必须无限接近。主客体只在意碗是否漏水或吸水,并不关注碗的形状与颜色。但是麦克卢汉以“媒介即讯息”意指媒介不仅作为信息的载体发挥作用,其存在本身也传达着自己的意蕴。比如书籍将信息凝固于创作者的时空,其存在形式也要求读者必须以与之契合的外部语言解锁内容。麦氏理论赋予了媒介生命力,以主体视角关照其不断进化演变的过程。媒介召唤着人们的理解,需要被人们不断解读赋予新的含义。对媒介的两种理解表明了其两种表达特性:工具性要求的精确表达和演变性呈现的诗性表达。有的媒介二者皆可,如语言或文字可以表达理性推导也可以呈现韵律或笔画优美;有的媒介更偏向其中一边,如图片与绘画容易让人产生审美意趣。纪录片正是用这种诗性的表达形成具象可感和想象空间,产生雾里看花“是花非花”的朦胧,使附属在表达中的意义发挥整体性作用。据此,观众用自己的方式解答着纪录片所带来的整体意义,构建起自己的理解和精神世界。此过程依靠于媒介又凌驾于媒介存在本身,是谓超越。
(五)以自我表达超越功利传播
现代人类社会构筑于理性之上,我们竭尽全力地推动着科技、社会的发展。我们用割裂又高效的方式教育下一代,急不可耐地扩张着知性之圆,期望自己知道得更多,掌握得更多,这些形形色色的内在目的和外在形态都是功利的。功利毫无疑问具有强大的动力,但是没有边界的功利就好似没有休息站和终点的马拉松,从目的明确的起步到被迫你追我赶,这时心中涌起的不再是澎湃的豪情而是迷茫孤独。因为生而为人追寻的不仅是得到,还有放下。纪录片用“他者”视野,不直接与观众对话,以自述的方式在观众想象中建立起的一个可供观察的“他”。“观众以旁观者的身份考量‘他’与‘我’的不同,却构成了‘我’的先在经验,形塑了作为此在的‘我’”。在这个过程中,纪录片好似舞台上自顾表演的演员,只专注于自己的表达,慢慢将真实与艺术娓娓展现。它是功利的,又不是功利的,它期冀着观众的观察,却不强制观众接纳,不限制观众的思考。观众可以获得也可以放下,是谓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