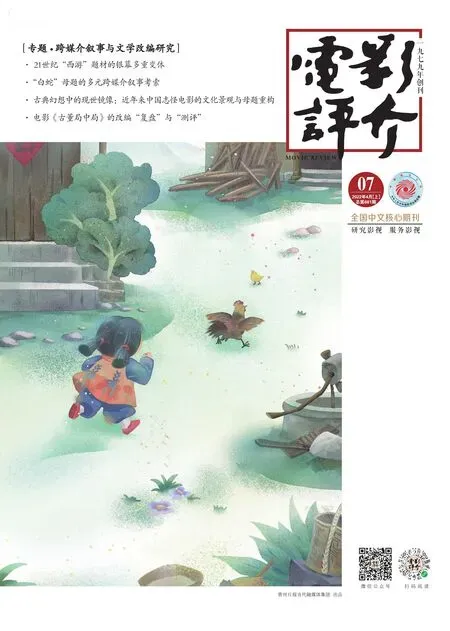“白蛇”母题的多元跨媒介叙事考索
2022-10-09黄钟军翟嘉璇
黄钟军 翟嘉璇
从图腾符号到神话传说,从文学作品到影视艺术,链接集体情感的白蛇母题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形式及文化内涵的艺术表达。影视艺术虽为一种年轻的艺术形式,但其对于白蛇故事的改编创作却不断涌现,其或是在经典内容的基础上对传统故事进行再表达,或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现代意识的注入,亦或是通过形式的转换开拓经典故事的表达空间、增加受众……近年的《白蛇传·情》《白蛇:缘起》和《白蛇2:青蛇劫起》亦是在不同层面上对白蛇故事进行的再度创作。其在承续集体共享的传统故事的基础上,从形式或内容层面皆注入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意识,使白蛇母题成为链接传统与当下的双重改编。
一、白蛇母题的改编概述
(一)白蛇母题的出现与成型
《白蛇传》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其主要围绕修炼成人型的蛇妖白娘子爱上了凡人许仙后的一系列事件展开。事实上,作为民间文艺的白蛇故事,其形成经历了诸多发展阶段。蛇妖虽作为白蛇故事的主角一直存在,但故事主题并非一直围绕爱情展开。在民间艺术中,“白蛇传”的雏形可以追溯至唐代传奇小说《李黄》,而《李黄》阐述的正是与现今“白蛇”故事完全背道而驰的主题:切忌贪恋美色。李黄与一白衣女寡妇共处三天后,回家精神恍惚、卧床不起,最后身子化作一滩水,而白衣女的住处却空无一人,仅有条白蛇常年盘踞树下。千字的唐代传奇小说放大了人们对白蛇的恐惧,并将异类的蛇妖设置为女性,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美色与罪愆关联。同时,人类与异类的对立也从集体无意识的神话传说变作文学作品,白蛇故事首先以“异类幻化”的母题呈现在文学记载中。
这一母题一直维持至明末冯梦龙的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该文可以说是“白蛇”传说发展历程中的转折,也是民间传说“白蛇传”的基本定型。人与妖从对立开始变作爱情传奇,以故事角色为基础的“异类幻化”母题开始被涉及情节发展的“爱情悲剧”所取代。《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蛇女开始以白娘子的面目出现,而凡人也被冠以许宣之名,同时,青青(小青)和法海也一同登场,分别作为白娘子的帮手与对手。然而,不似现如今所接触的“白蛇传”为人与妖之恋所动容,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结尾,作者依旧喊出“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之音;但另一方面,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浮现的明朝,作者冯梦龙在捍卫宗教禁欲主义和儒家封建思想的同时,在文中也不自觉地体现出自身的人文主义思想。他并没有将白娘子写作令人恐惧的女妖,相反,白娘子即是从此时体现出了人情人性的一面,她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也得到了作者的肯定。
清代市民文艺得到长足的发展,口耳相传的民间神话“白蛇传”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陈嘉言父女所编写的梨园抄本《雷峰塔传奇》使白蛇故事步入成熟阶段,也是当今的艺术创作最为贴近的蓝本。故事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基础上加入许仙与白娘子的前世宿缘,从而让白娘子饮雄黄酒现身以及水漫金山的情节也设置得更为合理。作为民间文艺,白蛇故事也在不断注入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白娘子生子后被镇于塔下,结局也被丰富为其子衣锦还乡后救母的大团圆情节。这一时期白蛇故事的发展,完全遵从于人民的意愿,如果说蛇妖不似妖只是在形象和心理上贴近日常女性,那么“生子情节”的设置则就完全是“妖的人化”的完成;同时,衣锦还乡是儒学背景下人民群众对子女的殷切期盼,大团圆结局则完全迎合了清代市民的欣赏趣味。
白蛇故事的民间发展并不止于成熟,在梨园抄本以及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后亦有狗尾续貂之作产生。民国梦花馆主的《后白蛇传》虽然在人物上更加丰富,在白娘子之余也讲述了其子许梦蛟的故事,但其严重的封建思想表述、对于悲剧艺术的无视,使其只能成为不甚成功的民间自娱之作。
(二)白蛇母题的影视改编
改编是“以原著为基础,创作出具有表演性质的新作品”的艺术活动,其着重强调艺术体裁的变化。作为民间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蛇母题也不断实现着文学艺术向影视艺术的跨越。至2021年,以民间传说白蛇传为创作蓝本的影视剧作品已达30部,其中最早出现的电影作品是上海天一公司拍摄的《义妖白蛇传》(1926年)。这部作品的创作基本遵循了民间传说,同时结合民间野趣,增添了小青与许仙的情感细节,使得同身为“异类幻化”的小青与白娘子的“人间女子”形象形成了对比。而这种改编在日后亦有延续,1993年徐克导演的《青蛇》中则增加了青蛇与许仙、法海的情感纠缠。当然,相似的行为已有了不同的缘由,《义妖白蛇传》中对于小青形象的塑造是男性视角下对于女性以及男性自身欲望的想象,或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对民间传说的世俗化改写,而《青蛇》中对小青情感的塑造则可以看作是现代性话语下个性解放、多元主义的表达。
因此,虽然白娘子与小青是以“异类幻化”的创作母题呈现于作品之中,其创作内容实际上是不断在发生变化的。1939年上海华新电影公司出品的《白蛇传》(又名《荒塔沉渊》)可以说是最为大刀阔斧的现实主义改编,白素贞不再是蛇妖,而成为了蒙冤受屈的总兵之女,最后为了使儿子不遭受诽谤从塔顶直坠而下。影片将神话传说改编为封建礼教背景下女性的悲惨遭遇。在此之后的白蛇故事改编一方面是如《义妖白蛇传》,遵循民间传说或是在传说的人物情节架构上稍加增删,包括《夜祭雷峰塔》(1949,中国香港)、《白蛇传》(1952年、1955年、2006年各有一版,前二者为中国香港出品的电影作品,2006年版为中国大陆出品的电视剧作品)、《仕林祭塔》(1962,中国香港,戏曲电影)、《白蛇大闹天宫》(1975,中国台湾)、《真白蛇传》(1978,中国香港)、《新白娘子传奇》(1992,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于2019年进行同名翻拍)、《又见白娘子》(2010,中国大陆)、《小戏骨:白蛇传》(2016,中国大陆)、《白蛇传·情》(2019,中国大陆)。
另一方面则像《荒塔沉渊》一般进行大刀阔斧的创作,甚至只是借用原作人物或情节,最后则阐释完全不同的主题思想。如1956年中国香港与日本合拍的《白夫人の妖恋》,就在结尾之处加入了许仙幡然醒悟而自杀,最后与白蛇相遇于天界的情节,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融合了日本的物哀美学,强化了白蛇故事的悲剧色彩。在此之后还有将蛇妖与哪吒故事相结合的《白娘娘借尸还魂》(1959,中国香港);许仙为救白素贞身死,二人相聚有情天的《白蛇传》(1962,中国香港,戏曲电影);小青烧毁雷峰塔,救出白素贞的《白蛇传》(1980,中国大陆,戏曲电影);将人物完全改写的《奇幻人间世》(1990,中国香港);着力刻画小青、法海和许仙的人性情欲的《青蛇》(1993,中国香港);构想白素贞之子许仕林之俗世尘缘的《白蛇后传之人间有爱》(1994,新加坡);将许仙写作放浪形骸之人的《青蛇与白蛇》(2001,中国台湾、新加坡);深度开拓小青之爱情故事的《白蛇后传》(2010,中国大陆);复杂化白蛇的爱情悲剧,并吸收现代影视剧矛盾冲突手法的《白蛇传说》(2011,中国大陆);着眼于通过如何懂得爱而实现成长的动画片《水漫金山》(2012,中国大陆);讲述小白蛇白夭夭与药师宫宫上——许宣前世今生爱情故事的《天乩之白蛇传说》(2018,中国大陆),以及在白蛇传说的基础上再创作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2019,中国大陆)和《白蛇2:青蛇劫起》(2021,中国大陆)。
从文学到影视的跨越是白蛇故事在改编上的发展,而在影视作品内部,又有多种艺术体裁的划分,白蛇改编亦是如此。在粗略统计的30部白蛇改编作品中,电影占了18部之多,而20世纪的18部白蛇改编作品中,仅有3部以电视剧的形式出现。当然,这种情况与两种艺术形式的诞生先后及发展程度不无关联。21世纪肇始,白蛇故事便以其经典性和通俗性成为了电视剧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12部影视作品中,电视剧即占了7部。而数量甚微的电影作品也不再一板一眼地遵循原著,《白蛇传说》即将“白蛇”悲剧复杂化,并融入了现代影视的创作及技术手法,《白蛇:缘起》与《白蛇2:青蛇劫起》则是取“白蛇”人物的外壳,用原创性的故事表达了新的主题思想。
另一方面,如同于中国古代由唐传奇和话本小说发展为梨园抄本,内容丰富之余,白蛇故事的艺术形式也得到了更新。单在1962年,中国香港就出品了两部以白蛇传为蓝本的戏曲电影,分别为粤剧《仕林祭塔》和黄梅调《白蛇传》;在1980年,中国大陆亦出品了戏曲电影《白蛇传》,其中更有阶级斗争和革命伦理的显影;而最近一部出品的“白蛇传”戏剧电影,则是2019年由广东粤剧院打造的“国内首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
在戏曲艺术形式之外,动画也一直是“白蛇传”故事的又一发力点。最早以动画形式出现的“白蛇”故事,是1958年日本东映动画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动画片《白蛇传》。在2012年,中国大陆也借白蛇故事的文本出品了动画片《水漫金山》,其更注重于对于青少年的“爱的教育”,也深化了正邪对立的矛盾冲突。2019年和2021年,追光动画出品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和《白蛇2:青蛇劫起》则更多与当下的社会语境相结合,在思想价值的受众选择上也更多倾向于成年观众。
白蛇故事的影视改编在创作地域上也出现了集中的现象。建国后到21世纪之前,共有10部影视作品出自中国香港,足以看出“白蛇”故事具有极高的通俗性与商业性。21世纪后,除去2001年由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共同制作的电视剧《青蛇与白蛇》,剩余的11部“白蛇”改编作品全部出自中国大陆,一方面是以影视化的阐释方式不断更新经典传说,另一方面是将白蛇故事迁移至当下的社会语境,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叉点。
二、故事重心移置与现代意识的注入
不似20世纪的改编作品蜂拥至银幕,21世纪以来,白蛇故事在银幕上仅有《白蛇传说》一部作品出现。一方面是影视创作题材更为开阔,不再耽溺于从传统故事取材;另一方面是如何将传统与时代结合,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注入现代意识。电影改编之转向加上电视剧通俗艺术的迎击,使得白蛇故事的电影改编进入一段沉寂期。直至2019与2021年的《白蛇:缘起》和《白蛇2:青蛇劫起》,白蛇传说的故事层面才再度展现出现代意识的光辉。前者虽延续爱情母题,但着眼于二人的前世宿缘,在原作的基础上展开新的“爱情神话”;后者则更为标新立异,将故事主角由传统的白素贞置换为配角小青,讲述小青因为营救小白而执念过深、坠入修罗城的故事,着重展现小青与小白的姐妹情谊。大相径庭的故事书写和主题表达却同为白蛇故事的现代衍生,借经典之名关联时下之社会议题。
事实上,这种现实观照在20世纪亦有书写。譬如1939年版本的《荒塔沉渊》,即是在民国时空中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改编,凸显封建礼教下女性的悲惨境遇。而同样将故事主角进行置换的是1993年改编自李碧华同名小说的《青蛇》,可以说是现代化意识最为彰显的白蛇故事影视改编作品之一。故事一方面跳脱传统白蛇故事的窠臼,另辟蹊径以青蛇为主角,着重塑造小青对于人世情爱的好奇与尝试;另一方面,法海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得道高僧,而是健壮俊美的年轻僧人。纵欲与禁欲的两极化设置为小青和法海的矛盾碰撞创造了缘由与契机。“传统白蛇故事中每个人都是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但影片《青蛇》则在白蛇传说为母本的基础上,以人性欲念为依托,通过个性解放等现代意识的注入对影片的个中人物进行再度创作。
其后,白蛇故事的现代性思想于银幕消沉近30年,直至在《白蛇2:青蛇劫起》中才再度迸发。而与彼时《青蛇》所涉及的个性解放、多元主义不同的是,影片《白蛇2:青蛇劫起》更着重与时下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形成对话。影片肇始即展现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经典桥段,小青救姊亦是情理之中,而象征父权制的塔之意象,就此将故事人物分成泾渭分明的对立双方。如果说这一经典场景的动画化展现只是传统思想中男女二分的呈现,那么接下来小青坠入修罗城的一系列经历,则是女性主义话语的直接表达。首先,影片将其中的男性角色都化为反派,同时“还表现在对霸权男性气质的解构上,将之进行非人化想象”——影片的男性角色越想夺取修罗城的话语权,其形象离人之面目则愈远,所谓的男性气质就此与迷失心智的“非人类”产生交锋,小青与小白对于内心的坚持则更显得难能可贵。其次是小青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事实上,在影片肇始,小青只是厌恶像许宣般无法向女性施以帮助的男性,于是面对身体强健且头脑果决的司马,小青的内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依赖于男性的情感,这种依赖或是二人爱情可能性的起点,却亦成了刻板的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再现。而当司马临危弃小青而去,小青绝望之中说出“男人都是靠不住”之时,她内心被爱情迷惑的自我意识终于重现。观至此处女性观众或是戏谑或是共鸣,但问题在于,将个人的道德缺失推及至整个男性群体是否是女性主义表达的目的所在?编导将社会问题强行嫁接至影片文本的行径呼之欲出,女性主义的设置在影片中成为了男女对立的隐性表达。这种非此即彼的女性主义虽然以一种抵制霸权话语的方式达到了言说自身的目的,但过于极端的叙事,是否只是将女性主义推向了另一个霸权的陷阱。
在《白蛇2:青蛇劫起》中,小白与小青形成了一组镜像身份的设置,小白依旧寄托着传统社会对人间女子的想象,相夫教子、举案齐眉,而小青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呈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早期的白蛇文学故事中,小青仅仅作为若有似无的配角出现——因为白娘子才是社会正统所承认的对象。于是,小青与小白二者镜像身份的设立,不仅仅是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社会身份的一体两面,实际也形成了传统与现代跨越时空的碰撞对话。
故事内容的现代性演进不仅在主题表达中有所透露,在其叙事中也有所表征。冯梦龙在撰写白蛇故事时将其定名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永镇”即体现出白蛇故事的悲剧内核。习惯大团圆结局的观众在看到白娘子艳羡人间而作的多番努力后,便为其创造了一个“出塔”的美满结局,这一结局的动因也不断随着时代更迭而更新。在《白蛇2:青蛇劫起》中,小青对于小白的拯救出自其多年相伴的姐妹情谊,拯救过程则呈现出女性自我意识之觉醒。而追溯至清代,以乡民社会为代表的“小传统”在逐渐积累了其对于故事结局的不满后,创作者选取白娘子之子许仕林完成救母的任务,而这一行为的前提是建立在其衣锦还乡的基础上。至此呈现出以士绅阶层为支撑力量的“大传统”对乡民“小传统”的归化与改造——“仕林”之名即体现出传统社会之期许,入仕做官是彼时进入官方的单一渠道,虽然白娘子已借生子之由完成了从妖至人的身份跨越,但其子进入官方话语系统,使白娘子在民间伦理之外得到了主流话语之认定。而在“大传统”话语转型后,“出塔”之缘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写。“白蛇故事里儿子救母的家庭伦理路线违背了革命伦理,唯一的革命路线就是白娘子自救,即妇女解放路线,这符合反封建话语”,因此,小青则成为了白娘子妇女解放自救路上的帮手,“推塔”与“出塔”也成为了革命话语的变奏。
三、舞台艺术到银幕艺术的多元尝试
跳脱影片文本而从宏观角度考量白蛇母题的影视化改编,则发现其实际上所经历的是一个双重改编的过程——内容层面的现代意识注入与形式层面的多元尝试。“白蛇”系列动画选择以动画电影的方式呈现传统的白蛇母题,一方面出于口耳相传的白蛇故事有广大的基础受众;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动画电影尚处于发展阶段,撷取经典素材的方式亦为今后的原创文本打下基础。而在动画电影之外,中国独特的电影形式——戏曲电影也不断地从白蛇故事中汲取营养。事实上,白蛇故事的发展与戏曲有着先天的紧密关联。从唐朝《李黄》的发端到明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基本定型,白蛇故事不断丰盈但皆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发展至清代,与白蛇文本的成熟相对应的是在艺术形式上开始进行多元尝试,先后诞生了黄图珌、陈嘉言父女和方成培的戏曲版本,白蛇故事正式由文学艺术迈向舞台艺术。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艺术作品最早的改编尝试之一,因为改编“基本上是将以文字为媒介的仅供阅读的案头之作转变为了以人的表演为媒介的舞台艺术或影视艺术”,其首先涉及的就是艺术形式的转化问题。不同于文学的间接性,舞台艺术的可视性使得纸本中的人物以一种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于观众眼前,而其虚拟性的特点却又在具象化之外给观众留有足够的想象空间。
时至20世纪,电影的诞生为传统的文学内容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同时又为多元表达方式的结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1905年的《定军山》开始,戏曲电影即成为了中国电影艺术的独特形式。通过歌舞和唱腔表现故事情节的戏曲电影或与好莱坞的歌舞片形成巧妙的对位,但不似歌舞片在诞生之初便以类型电影的面目展现。戏曲电影的发展经历了颇为多舛的身份认定,究竟是以电影为主体还是以戏曲为主体一度成为了戏曲电影的体用之争,使其画面呈现方式在记录与展现中摇摆。另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艺术形式的时代碰撞,以现代技术发展为依托的电影艺术,其追求真实性的立场与传统戏曲的虚拟性似乎有着先天的矛盾。从受众出发,戏曲电影隐含读者的专业性、地域性、非传统性,以及审美期待中欣赏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缺乏,使这一电影形式一直处于银幕的边缘位置。直至2019年,传统故事与现代技术碰撞下诞生的《白蛇传·情》,才使戏曲电影再度展现出星星之火态势。
与《白蛇:缘起》同年诞生的《白蛇传·情》,不似前者大刀阔斧地对故事内容进行现代改写,其基本遵循民间传说的廓形,还原了许白二人桥上相遇、情愫暗生、昆仑盗草、水漫金山和永镇雷峰塔等经典情节。同时,从原作的传统视点出发,对“妖”的塑造予以弱化,通过保留生子环节,借用“孝”的核心价值使观众对白娘子的身份予以认同,最终确立白娘子的人间身份。
从艺术形式与故事主题出发,《白蛇传·情》是民间白蛇故事的严格承续。但改编之为改编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原作的删减摘录与形式转换,否则只会将艺术作品推向静态现象比较的泥淖之中。《白蛇传·情》或被学者称之为“青春版《白蛇传》”,许仙字斟句酌的情话“配合写意清雅的舞台,让人在视觉上感觉到了美的冲击,这些都很对年轻人的胃口。”因此,《白蛇传·情》实则是一次与现代语境结合的艺术形式尝试。对年轻人审美趣味的琢磨,使其在故事内容上放大爱情经典,艺术呈现上则更加注重意蕴和意境的塑造,与此同时,画面的宁静悠远与民间传统故事以及戏曲形式的选择一同形成了传统文化表现的互文,使其从内容到形式的创作层面都与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形成了紧密的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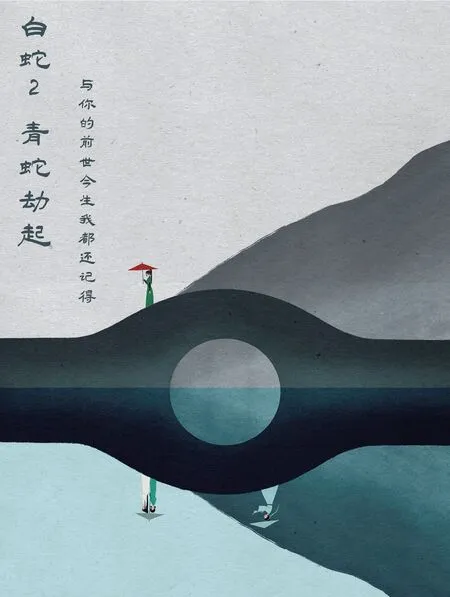
动画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海报
“以戏曲为主体而使用电影手段,必须是电影手段积极的、非纯粹舞台化的介入。如果仅仅是一种被动记录的话,那么就是舞台艺术纪录片而非戏曲电影了。”从此种定义出发回顾《白蛇传·情》,即可发现其艺术呈现上对于银幕视觉化呈现和舞台演出的平衡性把控。其保存了唱腔、唱词、亮相、动作、装扮及程式等戏曲的核心内容。同时,视听呈现上则以电影艺术形式表意,在白娘子营救许仙未果的一场戏中,大俯拍的使用强化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而全景、中景等景别的使用,让观众获得了有别于剧场观影的体验,同时也使演员的表演产生了相应的改变;剪辑的使用也是舞台塑造无法展现的效果,空镜头和景物特写的加入给予了观众情绪沉淀的空间,也使得剧情节奏张弛有度;而背景音乐也在戏曲的基础上融合了更多现代化的声音内容,与此对应的是唱词的“年轻化”修改,使之在节奏和语言上都更适宜当下在视觉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正如白蛇故事内容层面的开掘会引起多方讨论,对于艺术形式的尝试亦是褒贬不一。与年轻观众的褒扬相伴的是老戏迷们的诟病,而这种多集中于音乐使用和舞台效果的批评,一方面隐含的是故事内容呈现的成功;另一方面反映的则依旧是戏曲电影呈现中的尺度把控问题。戏曲以几招几式呈现千军万马的虚拟性,不仅是对戏曲演员精湛技巧的要求,也使观众形成了“调动想象”的欣赏经验。因此,当《白蛇传·情》真实地展现出许、白家中内景,同时动用大手笔以奇观化地呈现水漫金山等场景时,其恰恰是从电影真实性的角度出发,通过技术进步不断达成“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之核心目的。然而,对于以欣赏戏曲为目的的老戏迷,其观赏经验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挑战。两种艺术形式及其受众经验的博弈,使得《白蛇传·情》在艺术创作倒向电影一方的语境下,失去了传统戏迷的肯定。
作为国内首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是在借助白蛇故事这个集体共享型故事的基础上完成了戏曲电影的技术创新,再度讨论了戏曲电影中的体用之争。同时,新兴技术的尝试也帮助传统的白蛇故事开拓受众,使这一传统故事以形式层面的现代面貌深入人心。
结语
白蛇故事从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到借助受众想象力才得以完成的文学艺术作品,再到虚实相生的民间戏曲文艺和贴近日常生活的以真实为标准的影像艺术,不同形式的承载使白蛇故事的展现效果各有不同,受众层面亦有所开拓。“白蛇”作为一个集体共享型故事,在历代发展中承载着人们各个阶段的社会经验。从最初人类与异类相对抗的“异类幻化”母题发展成为社会“小传统”所热衷的爱情悲剧,而这种以民间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虽然形成了人们的精神抚慰,但其事实上也是在“大传统”的管控之中:白娘子对于爱情的追求可歌可泣,但其最终被镇于塔下再度证明了封建社会对情爱的压抑,而这种压抑的推翻却也仰赖于社会官方话语的认定。“大传统”和“小传统”就此缝合,白蛇母题成为了官方话语和民间情感共振的文化记忆。而随着现代意识的注入,白蛇故事开始承载起精英分子的时代关怀,从徐克的《青蛇》到黄家康的《白蛇2:青蛇劫起》,个人主义或女性主义的表达皆借白蛇故事之口得以传递。白蛇故事的重述性在于其中“人们的生命历程中较为普遍出现的生存困惑或逆境”——其爱情悲剧在一遍遍重演中得到人们跨越时代的共时性认同,但与此同时,正得益于其爱情悲剧的重述性基础,使得白蛇故事具备了不断更新主题思想以表达时代关怀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