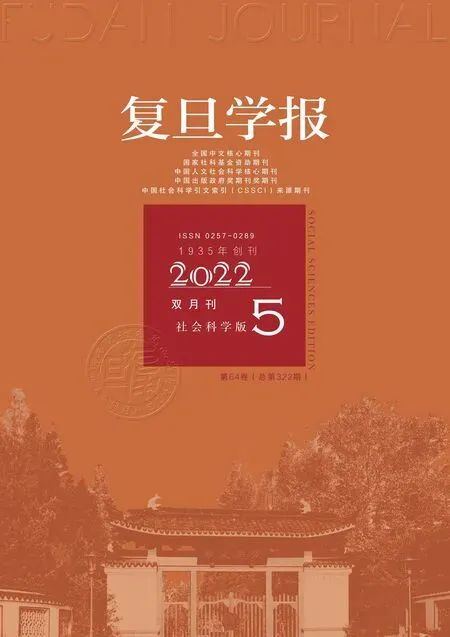费舍尔:一个人的东亚艺术博物馆
2022-09-29王维江
王维江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虽然大英博物馆早已收藏亚洲文物,但首先为亚洲文物独立建馆的是法国:1879年的吉美博物馆一骑绝尘,1898年的赛努奇博物馆则锦上添花。德国公共博物馆建设至少落后英法五十年,而个人出资建馆更属罕见。最具热心和实力赞助艺术品收藏的“棉纺大王”詹姆斯·西蒙(James Simon, 1851-1932)直到20世纪初对东亚艺术品仍无感。(1)Khanh Ngoc Trinh,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eds. Peter-Klaus Schuster, James Simon, Sammler und Mäzen für die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Berlin: SMPK, 2001) 38.自1872年起任职于国家博物馆的波德(Wilhelm von Bode, 1845-1929)乃倡导收藏东亚艺术品的先觉,(2)Julius von Schlosser, In Memoriam Wilhelm von Bode, in: Mitteilungen des Kunsthistorischen Institutes in Florenz, Vol.3, H.4, 1930, p.152.直到1906年,他甫任国家博物馆总馆长,仍感叹在募集东亚艺术品资金上“我们并没有一个‘西蒙’式的人物”!(3)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Briefwechsel aus 20 Jahren 1905-1925 (Norderstedt: Books on Demand GmbH, 2009) 21.
德国人中无“西蒙”,并不等于在德的外国人中也没有。彼时正有一位奥地利人在德国致力于东亚艺术品的收集和东亚艺术博物馆的创建,可惜此人未入波德法眼。这位舍弃父亲所指定的挣钱小目标、却实现了人生大目标的传奇人物就是费舍尔(Adolf Fischer, 1856-1914)。
一、 维也纳来的浪子
费舍尔出生于维也纳的“富足工业家家庭”,(4)D. H. Adolf Fischer (1856-1914),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H.1, 1914, p.104.其父为著名企业家,育有三子三女,他是次子。父母逝世后,费舍尔的“名字不再在企业中出现,或许是与其兄弟的关系紧张”;(5)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Die Gründung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in Köln (Köln: Gebrüder Kopp GmbH & Co., 2009) 10, 16.也可能是他主动退出,提早分得一份巨额遗产,否则无法解释他用于旅行和购买东亚艺术品的资金来源。
费舍尔热衷戏剧表演,先在维也纳拜名师,接着进军柏林舞台,最后转行剧院经理,皆未成功;他去非洲散心,又赴美国登台,再度铩羽而归;前往意大利研究艺术是其人生转折点,最终把他引向日本。他“一开始只是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后来才对日本和中国艺术产生兴趣。”(6)D. H. Adolf Fischer (1856-1914),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H.1, 1914, p.104.引发费舍尔对日本感兴趣的起点是1873年:
可以肯定的是,1873年世博会给费舍尔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日本时尚在维也纳狂热蔓延,日本服饰的化妆舞会、樱花节和其他日本节日及戏剧与歌剧节目纷至沓来,费舍尔不可能视而不见。(7)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12.
这一年,世博会首次在德语国家举办,维也纳世博会遂成为奥地利一代艺术家的共同记忆,“日本风”亦成为维也纳分离派画家的持续追求,浮世绘通过维也纳世博会进入欧洲,并在五年之后的巴黎世博会上再度登场,影响到法国印象派。1892年,首次访日的费舍尔便受分离派委托,大量购买浮世绘。(8)Monika Kopplin, Das Sammelwesen von Ostasiatika in Deutschland und Oesterreich, vorzugsweise verfolgt für die Zeit von 1860-1913, in: Goepper Roger eds., Zur Kunstgeschichte Asiens: 50 Jahre Lehre u.Forschung an der (Univ ersität. Köln,Wiesbaden: Steiner, 1977) 38.费舍尔同时邀请该派画家弗兰茨·高山(Franz Hohenberger, 1867-1941)全程陪同。1895年费舍尔第二次访日,高山再次同行。正是维也纳世博会和分离派画家的双重影响,让费舍尔取得先机,成为东亚艺术品收藏和研究的前驱。他比另一位重要的德国东亚艺术品收藏和研究前驱格罗塞(Ernst Grosse, 1862-1927)提早14年踏上日本国土。其两次日本之行的成果,除了购买艺术品,还有一本自撰日本游记,短短23行的前言主题鲜明:
因为我早已爱上日本,想以绘画形式令其永恒可观,所以来自维也纳的年轻朋友、画家高山再一次伴随我同行。我前往最古老的历史名城研究和洽购期间,他以水彩和油画形式,保留下来这里令人痴迷的独特风景、建筑和人民。(9)Adolf Fischer, Bilder aus Japan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Bondi, 1897) Vorwort.
与格罗塞相比,费舍尔确实更关注风土人情,入选游记82幅,超过一半是人物画——和尚、画家、稻农、黄包车夫、各阶层妇女、街头艺人、原住民爱奴人、能剧演员,另一小半多为风景,佛寺最多、其次村舍。
有学者判断,高山的“插图主题和构图受到日本木刻彩印和绘画的影响”,(10)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12.但未论证。或许证据隐藏在高山所绘作品中——其前期为西式素描,如图1的和尚,站在一幅佛教题材的立轴前。立轴反复在高山作品里出现,凸显他的偏爱;图2则以水彩笔法单独呈现了一幅佛像,标题是“古代日本立轴(菩萨)”,值得注意的是左下方的蝴蝶,构成典型的东亚绘画意趣。费舍尔欣赏葛饰北斋,其书中选登了北斋绘制的各种人物姿态,其中一构图依然是立轴(见图3)。费舍尔游记还选了一幅北斋的作品,向这位浮世绘巨子致敬。“日本艺术的重点在于其装饰绘画”(11)Adolf Fischer, Bilder aus Japan, p.80.——这是费舍尔由游历得出的经验和判断,也是促使他收藏东亚绘画的最早契机。对浮世绘的仰慕,表征着维也纳分离派和浮世绘两因素的持续影响,反映出费舍尔的研究侧重点最早放在日本绘画上,对日本绘画的喜爱引导他追根寻源,进而发现中国绘画并亲往中国。

图1 Bilder aus Japan, p.49

图2 Bilder aus Japan, p.61

图3 Bilder aus Japan, p.69
与格罗塞的另一不同之处在于,费舍尔不只对日本传统绘画有兴趣,他也乐于了解受西方影响下的当代日本绘画。他拜访铃木画派始祖铃木松年(Suzuki Shionen,1848-1918),大师告诉他提高技艺的奥秘——临摹中国古画。铃木还破例当场示范作画。高山临摹铃木的一幅作品也被收入费舍尔书中(见图4),这是维也纳分离派画家模仿和吸收日本画风的佐证。

图4 Bilder aus Japan, p.89
费舍尔还专程探访留法归来并引发争议的画家黑田清辉(Seiki Kuroda, 1866-1924),他于1896年成为日本首位油画教授。黑田派其得意弟子和田英作(Wada Eisaku, 1874-1959)充当费舍尔的向导兼翻译,费舍尔返德后即成为他留学法国的资助者,期望和田将来用现代欧洲绘画影响日本。
实地游历与出版相关书籍,费舍尔俨然已成为收藏东亚艺术品的先锋,但他的这番作为并未触动德国国家博物馆层面。总馆长波德晚年出版500余页的回忆录,列举的关键人物是格罗塞和屈曼尔(Otto Kümmel,1874-1952)师徒二人,只字不提费舍尔。当时欣赏费舍尔的大学教授则是东亚艺术的外行,他的名字出现在费舍尔日本游记的扉页上——“献给我敬仰的朋友、柏林的埃里希·施密特(Erich Schmidt)教授”。这位施密特少年得志,早在1880—1885年间已是维也纳大学教授,费舍尔应该在来德之前已结识施密特,两人年纪相当,谊兼师友。1887年施密特转任柏林大学,虽本业为德国文学,但兴趣广泛,也是最早建议费舍尔为东亚艺术品独立建馆之人。此外,他还是费舍尔婚姻的牵线人。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维也纳世博会和维也纳分离派的影响,费舍尔的东亚艺术品收藏方法和路径会与德国本土大相径庭;如果没有德国教授施密特的双重提携,费舍尔会成为德国人的女婿;如果没有成为德国人的女婿,是否还会有现在的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呢?
二、 两个人的志业
因为没有专门的博物馆,东亚艺术品只能入藏德国的民族学博物馆和工艺美术博物馆,而这种收藏并非建立在对东亚艺术的专业认知之上。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学术新星米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博士就是如此,他精通亚洲十余种语言,包括汉、日和朝鲜语,被视为德国“最为博学”的东方学家。(12)Friedrich Weller and Bruno Schindler, F. W. K. Müller, in: Asia Major, 1925, Vol.2, p. vii.; Ferdinand Lessing, F. W. K. Müller zum Gedächnis, i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3. u. 4. Heft, 1930, p.142.然而终其一生,他拒绝为东亚艺术品独立建馆,是波德的死对头,却是费舍尔的好友,因为两人见识接近,都把东亚艺术放在民族学的范畴内。1896年米勒履新馆长助理,同年费舍尔被聘为民族学私人讲师,或许就与米勒有关;费舍尔热衷于日文和中文学习,可能也是受到米勒的影响。
1896年圣诞节,费舍尔将自己的东亚艺术品在寓所展出,施密特携全家出席,并赋诗志庆:“那位风尘仆仆的旅人费舍尔/带着一千个箱子归来/……绘画青铜器漆器/拆开包装需三月/瓷器木刻加木雕/多得永远数不清”。(13)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Lehr-und Wanderjahre (München: F. Bruckmann Verlag, 1942) 9.诗句清晰点明费舍尔两次日本购藏之丰富,1899年到访的和田英作创作的一幅水彩画则直观展示出这些藏品(见图5)。(14)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12.

图5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15
施密特还将22岁的柏林工厂主之女费丽妲(Frieda Bartdorff,1874-1945)带来参观,她在日记中记下了展品种类:日本屏风、日本和中国佛像、绘画、铜器、漆器、瓷器、日本木刻彩印和剑镡、印度画像,织锦僧袍以及波斯、土耳其挂毯和地毯。(15)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10.展品迷住了费丽妲,费舍尔也被小自己18岁的费丽妲所迷住,他在首展日求婚,次日订婚,三个月后结婚:
1897年,我与富有魅力的费舍尔双手相叠,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舍弃自我,随他如影而行。带着热情和喜悦,我沉浸在他纯净的理想主义者的世界里。他为此踽踽前行,理解、亲历繁盛时期的人类最发达和最高贵的艺术,并最终为这一艺术服务。(16)Frieda Fischer, Japanisches Tagebuch (München: F.Bruckmann Verlag, 1938) 7.
有钱兼有理想,费舍尔同时收获事业和爱情。而凝结人生美好的媒介是一陌生领域,无论是大学者如米勒、大教授如施密特,至少在东亚艺术品鉴别上都不算是专家,纷至沓来的艺术家和作家,只是东亚艺术业余爱好者。波德、格罗塞未曾登门,无疑是不认可的明证。此刻费丽妲的坚定追随至关重要,为费舍尔的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新人婚后即启动第三次日本之行,旅行结束后的1900年,费舍尔的第二本书《日本艺术生活的变迁》面世,(17)Adolf Fischer, Wandlungen im Kunstleben Japans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0).扉页献辞为——“献给枢密大臣Woldemar von Seidlitz博士,致以真挚的敬意!”此人(1850-1922)是萨克森博物馆的主管,也是最早呼吁在德国建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有识之士,在萨克森的影响力相当于在柏林的波德。那么,这一献辞的背后是否暗含着费舍尔在向波德示威呢?他心目中的理想博物馆所在地是柏林!
本书的装帧充满东亚趣味,出自黑田清辉的学生和田英作之手,书页是手绘的亚洲植物——如竹子、银杏叶等(见图6),见证着费舍尔与黑田师徒的相互欣赏和长久情谊。在本书出版之前,费舍尔已在专业杂志上发表《“分离派”在日本》一文,标榜黑田为“日本分离派的创建者”。(18)Adolf Fischer, Die Secession“ in Japan, in: Die Kunst für alle: Malerei, Plastik, Graphik, Architektur, Heft 14 (15. April 1900) 322.费舍尔明知黑田是留法学生及印象派的信徒,却给他贴上分离派的标签,其用意,在于强调欧洲艺术对日本绘画的引导作用,所以他宣称以黑田为代表的日本分离派并非“要把日本艺术欧洲化,他们只是想教会其同胞正确地绘画”。(19)Adolf Fischer, Wandlungen im Kunstleben Japans, p.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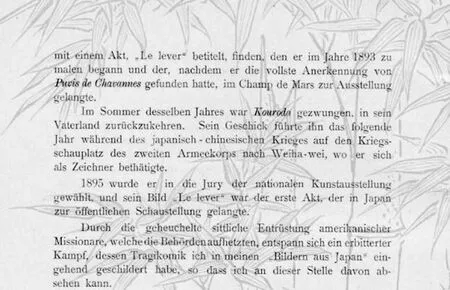
图6 Wandlungen im Kunsleben Japans, p.28
费舍尔与维也纳分离派的渊源及赞赏并不意味着他对日本传统绘画的轻视,恰恰相反,他借此表达的是对主动走向世界的日本传统画家的激赏。他所拜访的日本画坛巨擘,既有恪守传统的老画家,也有追求新潮的世博会弄潮儿:第一站在京都,他拜谒著名画家古濑素石(Kose Shoseki):“与现代的东京相反,他保存着古代传统的日本。”在画家竹内栖凤(Takeuchi Seiho)府宅午餐, “带着含蓄的自豪,他向我们展示画作,这些画作被选中在世博会上展出,有一幅参加了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画家望月玉船(Mochizuki Gyokusen)以水彩画的西式元素改造日本传统绘画,与弟子当场创作了一幅花鸟馈赠图,“主人带着我们参观他的书房,展示为1900年巴黎世博会准备的画作”。(20)以上三条引文均见Frieda Fischer, Japanisches Tagebuch, p.12, 16, 17.一方面是欧洲藏家对日本传统绘画的青睐,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画家求变求新,利用世博会的平台主动走向世界。这是费舍尔心中的日本画坛的理想状态。第二站在东京,费舍尔拜访了心仪已久的“最伟大的日本绘画专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称赞他是“发现日本绘画的第一人”。(21)以上两条引文均见Adolf Fischer, Wandlungen im Kunstleben Japans, p.88, 62.这位美国教授当然也是影响费舍尔收藏日本绘画的重要因素。此次赴日,费舍尔还受维也纳分离派的委托,买下1400幅木刻彩印,作为1900年第6届维也纳分离派展览的重要展品,“以实物展示日本木刻彩印各阶段的历史发展”。(22)费舍尔为第6届维也纳分离派画展所撰序言,转引自Monika Kopplin, Das Sammelwesen von Ostasiatika in Deutschland und Oesterreich, vorzugsweise verfolgt für die Zeit von 1860-1913, Goepper Roger, eds., Zur Kunstgeschichte Asiens: 50 Jahre Lehre und 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Köln (Wiesbaden: Steiner, 1977) 38.这是日、欧绘画方法和风格的互鉴,这一互鉴经验也影响到费舍尔对东亚艺术品的鉴别和评估:
东亚人的绘画从书法中发展而来,研究最佳途径乃古代的木刻印刷。对优美线条的欣赏深深植根于其文化之中,这是远古以来的传统,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种对线条的欣赏与其文化联系起来考量,我们可以理解,却无法感同身受。对这种优美线条的无端和过度推崇最近在我们这里变得流行起来,应该是出于一种寻找新鲜和独特的病态,以至于夸张盲目地复制。(23)Adolf Fischer, Wandlungen im Kunstleben Japans, p.101.
这是费舍尔一贯的看法,他热爱东亚绘画艺术,但排斥以此来变革欧洲艺术。鉴赏东亚绘画越来越自信,同时也意识到欧洲知识的不足。1899年回到柏林,他们一方面消化在日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参观维也纳、慕尼黑、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和古董店。两位未上过大学的老学生再作冯妇,在柏林大学旁听文学、哲学及欧洲艺术史课程。学习带来思想境界的提高,1901年,他们决定捐出自己的全部东亚收藏:
生活的一个重大转折:我们把自己的收藏转让给国家,国家将它们转让给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我们想走自由独立的生活道路,不只局限于个人爱好,而是朝着总体的文化目标迈进。(24)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14.
这一批艺术品有多少呢?“价值连城、独一无二的日本艺术珍宝和古物安置在14个房间里”,其中“包括维也纳分离派展会上的展品”。(25)当时一本杂志的报道。转引自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22.此时老友米勒已晋升为民族学博物馆馆长,费舍尔的捐赠顺理成章。他也想借此与米勒合作。正值八国联军战争期间,柏林方面视为抢购中国艺术品的良机,派米勒前往北京,费舍尔主动提出自费随米勒前往。(26)Ulrich Wiesner, Die Gründerjahre des Museums 1903-1913, p.6.
但米勒没有接受费舍尔的提议。尽管如此,费舍尔还是履行了捐赠允诺。德国政府以表彰其“对艺术和科学的赞助”之名,授予他教授头衔。这殊为罕见,波德和格罗塞一定不乐于看到这样的“交易”。
三、 费舍尔在中国
1895年第二次赴日的费舍尔已知晓中国是日本艺术的源头,为此返程他在港澳短暂逗留,但无暇前往内地。(27)Adolf Fischer, Bilder aus Japan, pp.59, 62, 106-107.真正引发他想法改变的是第三次日本之旅:
之前我对中国是东亚绘画最高成就的说法持有怀疑,此刻所有的怀疑都消失殆尽。毋庸置疑,日本画家将这些中国先贤视作不可企及的典范。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超过一千年的作品。(28)Adolf Fischer, Wandlungen im Kunstleben Japans, p.103.
随着此行与日本藏家之间的信任度不断加深,他在日本看到的中国古代文物也越来越稀见。1902年费舍尔夫妇再次赴日,已能看到唐代文物:“这只箱子来自空海,而且是从中国带回来的”、“空海为了僧侣所需从中国带回的书法卷轴上盖有九世纪唐代的中国印章。”日本博物馆收藏东亚古代文物之丰富,刺激费舍尔夫妇“逐渐有了一个计划,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不是民族学附庸的博物馆,只是献给东亚艺术的博物馆”。(29)以上引文均见Frieda Fischer, Japanisches Tagebuch, p.35, 36, 42.这是超越了单纯捐赠的思想飞跃,为此他们踏上了中国国土。
1902年10月17日,两人抵沪,雇佣一位叫大勇(Tayong)的中国人作为仆人、导游兼翻译,其实他只会一点洋泾浜英语。他们乘坐德国轮船“伊琳娜公主号”(Prinzess Irene)前往南京,船长将一顶绣有船名的女帽赠给费丽妲作为临别纪念品。大勇误以为她就是伊琳娜公主,四处炫耀,竟惊动官府,被一群官员迎入总督府,看到府内放置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的正是已故两江总督刘坤一。他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宴席,离开南京之际,又在码头邂逅继任总督张之洞。费丽妲写道:
第一次体验中国生活的氛围和中国人的特性,令我们发懵,尽管我们还没能闯入他们的生活。费舍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愿仔细认识和了解中国。”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庄严和世俗平衡相处。(30)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21. 引文中所称费舍尔日记乃未刊稿,现存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其馆员正在整理,无法查阅。
一场误会,却给费舍尔夫妇留下与日本不同的记忆,激发出他们了解中国的愿望,在华游历与他们返德后萌发创建独立博物馆的时间正相吻合。1903年2月,Seidlitz呼吁在柏林建立一座帝国级的“亚洲艺术的德国博物馆”,恰与费舍尔的想法暗合。这一提议也符合波德的心意,他在回忆录中称Seidlitz是“最为活跃的倡导在德国收藏东亚艺术品的代言人。”(31)Wilhelm Von Bode, Mein Leben, Vol.2, p.170.但柏林官方并未积极回应,只是承诺“扩大现有东亚艺术品收藏的可能性”。(32)其建议起初只是一份手稿,在小范围内传阅,两年后发表在《博物馆学》杂志上。参见Woldemar Von Seidlitz, Ein deutsches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in: Museumskunde, 1905, Vol.1, p.181。半年以后,从东亚回到柏林的费舍尔得到施密特教授的及时建议:
“你应该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像慈父一般的老友施密特这样建议费舍尔。其实我们早已无意识地做出选择,现在则是清醒无误的决定,我们将全心全意为艺术——而且只为东亚艺术——服务。欧洲尚未承认这一艺术是世界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愿将余生奉献于此。(33)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22.
在这样的微妙时刻——官方举棋不定,民间暗潮涌动——施密特的提醒弥足珍贵。1903年8月,独立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已在费舍尔心中诞生!他无疑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并在柏林民族学圈子里获得认可。1904年,他已担任民族学协会主席,并应理事会邀请,向会员展示自己的东亚艺术品收藏。会刊称费舍尔拥有“贵重的民族学展品”,(34)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H.5, 1904, p.698.虽属郢书燕说,却是当时民族学界、博物馆界对东亚艺术品的真实认识水准,反衬出费舍尔的学术水平。1904年11月,另一位研究中国地理的先行者、收藏中国青铜器的李希霍芬函告费舍尔:经他个人提议,政府已任命费舍尔担当首任驻华使馆科学专员,任期三年。这让费舍尔深感意外,因为这不只是对他收藏行为本身的肯定,更是对其专业能力的认可。由此也让他在与波德和格罗塞的竞争中胜出!1904年12月,费舍尔与基尔市签署了共建东亚艺术博物馆的协议。(35)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34.
1905年,费舍尔以外交官身份前往中国,途中先访日本,在德国驻日公使的引荐和陪同下,费舍尔得以走进日本大贵族井上(Inouye)、伊藤(Ito)、田中(Tanaka)的收藏;而在德国公使和上述顶级藏家的关照下,费舍尔夫妇竟然获准参观正仓院:
在日本追寻艺术品,随时会碰到中国艺术珍宝,它们自公元六世纪已随同佛教一起藏入寺院和庙宇的珍宝室。几百年以来,日本一直珍视和推崇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品。(36)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25.
费丽妲详细记录此行在日本所见的顶尖中国文物,正是为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做铺垫。1905年11月,甫抵北京的费舍尔夫妇立即聘请一位德国汉学家学中文;(37)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42.1906年1月,再聘一位中国人为汉语老师,每天学习长达五小时!这份努力很快得到奖赏:
两位皇家的汉族官员带着八名挑夫来到我们住处,递给我一张黄纸,上面写着中文“中国女皇奖赏大德国教授费舍尔太太四只花瓶”。他们把绘有彩色芍药花枝的四只巨型白色瓷瓶抬到我面前,我还未从不期而至的喜悦中反应过来,皇家使者再次降临,他们带给我的是四只红色圆形的大漆盒,上面绘有描金五爪皇家龙,里面装着中式点心。(38)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27.
慈禧的慷慨馈赠,当属庚子后对驻华西方外交官“夫人外交”的延续,也是对费舍尔夫妇倾慕华夏文化的赞赏和奖励。费舍尔深知,三年北京任期与自己的未来东亚艺术博物馆命运密切相关,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收藏圈子并从中学到鉴赏真本领:
庆宽先生是高级官员,是我们的好老师。他坐拥一座巨大的衙门,走过一进进的房子,穿过一个个的院落,再通过一座座的花园,……庆宽先生在其藏有瓷器的房间接待了我们,墙上的搁架上是一个个带盖的黑色木匣,盖子可从上端推开,他从一个个匣子里取出价值连城的瓷器,给我们讲解如何判定其真假和年代。(39)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p.35-36.
费舍尔得以登门拜访长期在内务府任职的庆宽,当然得益于其外交官身份的加持,这是他在华寻访和编织古玩人脉的优势;同时也有些失策,因为高官与外国人交往极为谨慎,未必讲真话,不会轻易出让所藏。费舍尔在华三载斩获有限,应与此策略有关。此刻他不问绘画问瓷器,或与庆宽的收藏专长有关,或与德国国内热衷收藏中国瓷器的风气有关。19世纪下半叶以降,德国拍卖行经营的绝大部分都是清初康雍乾瓷器,真假难辨;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京城外国人的瓷器收藏热:
尤其是美国人,目前正陷于瓷器热之中,竞相购买。一个牛血红瓶要价10000美金,一个苔绿色斑点的桃红小瓶2500美金,据说它们会增值。这样的判断我们无法认同,不为所动。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正面和负面的都有,我们孜孜不倦地向收藏家和交易商学习。(40)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38.
费丽妲没有记下中国收藏家和交易商的名字,这里也就无从进一步考索费舍尔的学习、交往圈子和收购路径。与此同时,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其中端方和戴鸿慈游历德国,可惜作为著名金石学家的端方未留下游记,但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仍再现了端方1906年5月在柏林访古的踪迹:
早十时,往观古器博物院。此院多存古物及各国器具,大抵十六、十七世纪之物为多,如牙器、骨器、漆器、木器、铜铁金石器、瓷器、钿器、药器,大都古制。中国瓷器,有十七世纪所造者,一则本国所购,一则得之波斯。自余中国铜器尊壶数事,古色斑斓,最为可宝。(41)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
两人的随行翻译只懂英文,所谓“古器博物馆”,乃随口一说,其确切名称是工艺美术博物馆(Kunstgewerbe-Museum),其中大部分中国藏品乃驻华公使巴兰德1879—1884年间所购,两人竟然对此一无所知。(42)Führer durch die Sammlung des Kunstgewerbe-Museums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907) 3-6, 11, 13. Führer durch da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Berlin: W. Spemann, 1898) 185-188.同日,端、戴还参观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即戴日记所称“人类博物馆”,并标出英文“Ethnographical museum”,说明他并非不在意原名与译名的一致,也隐约感到新奇。其馆藏除了绘画和铜器,其余并非都是艺术品。戴只以中国“风俗事物”一笔带过,未曾深究博物馆藏品与新学科之间的关联,也不曾询问这些中国文物入藏德国的来路。出使人员对外国博物馆和对流散国外的中国文物并不太在意。
端、戴在德一月有余,柏林逗留最久,“排日导观”的德方官员恰巧是民族学家出身的前驻沪总领事克纳贝(Wilhelm Knappe,1855-1910),之所以安排参观以上两个博物馆,因为他在华期间也是中国文物收藏家。回国后的端方奏陈自己在德忙于观摩“官署、学堂、工厂”,(43)端方:《端忠敏公奏稿》二,卷六,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668页。那是公务的需求,但忽略了博物馆,不只是辜负了克纳贝的好意,也错过了获得新学科和新知识的良机。中国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建设滞后日本至少五十年,很难说与这批使臣无关。而端方作为五大臣中通洋务的著名金石收藏家,至少可说是缺乏敏感和远见。
端、戴在德期间,费舍尔正在北京狂购,他不去琉璃厂,也不理会送上门来的古董商,“那些专门冲着外国人来的,并不中我们的意。”他自认为已寻获隐秘而可靠的进货渠道:
一个普通中国人把我们带到他家,院落空间已不足以将其珍宝完全展示。这是一件12扇的屏风,高2.85米,宽6.9米,折叠在一起,所以无法窥其全貌。但可见部分极为漂亮,我们买下。这位卖家保证,他从1900年起就拥有这件掠自皇宫的屏风,对此我们不甚在意。(44)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36.
此处所谓“不甚在意”,表明费舍尔不相信卖家讲述的故事,而坚信自己的判断。此屏风已入选1995年出版的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大师之作》(45)Adele Schlombs, Meisterwerke aus China, Korea und Japan (Müechen/New York: Prestel-Verlag, 1995) 121-123.一书,自然是费舍尔代表性藏品之一(见图7)。

图7 Meisterwerke aus China, Korea und Japan, p.123
费舍尔还前往文物大省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第一站太原,从英国人手里买下一件鹅造型的殉葬用青铜灯。第二站西安,他发现当地多有造假,称之为“天才般的赝品”。(46)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77.之前他在日本研究过古董造假业,并发表《日本和中国的文物造假业》一文,认为“日本在青铜器造假上已远超中国,中国在潍县一带和其他地方生产的赝品,无法与京都及周边地区一些造假者的一流赝品相比”。(47)Adolf Fischer, Fälscherwesen in Japan und China, Orientalisches Archiv, Leipzig: Verlag von Karl W. Hiersemann, Vol.3, 1912-1913, p.30.费舍尔在华轻易不染指青铜器,应与他洞悉造假内幕有关,而格罗塞收藏中国艺术品的首要成就是青铜器。第三站洛阳,“龙门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人物造像之美,“简直如同音乐”,“让人想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费舍尔以拓片和拍照的方式存真并带回德国:
从河南府带来的专业拓片师,为我们拓制礼佛浮雕,难度很大,极为吃力,因为浮雕很高,头部完全是立体的,纸张在加深敷涂时会撕裂。只要石窟里稀缺的光线允许,我们就拍照片。我们带着这些宝贝回家,它们为我们幻化出一个鲜活的龙门。(48)以上引文均见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94, 95, 97.
1906年9月,费舍尔再往山东,在嘉祥县武梁祠购入两块汉代石雕和一根汉代石柱,日后成为其馆藏珍宝。(49)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p.104-105, 112-113.1907年4月,他在南京拜访端方:
端方设盛宴招待,其间沉浸在对德国的回忆中,他给我们端上在德国亲自挑选的莱茵葡萄美酒以表欢迎之诚,他快乐地举杯致辞——“祝您健康”(Prosit)——这是他还记得的唯一德语单词。
贴心周到的款待,印证出端方热情好客的性格,给客人留下“睿智稳重”的印象。端方带着眼镜,身旁有英、法、德三位翻译,其中德语翻译是留德十年的海归,陪客中还有一位留德四年的青年军官。其名重一时的青铜器早已在客厅陈列就绪,供客人观赏,端方特意赠给费丽妲一张带有题字的“柉禁全图”照片,并钤“陶斋”印一枚。(50)以上三条引文均见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143, 142, 129.(见图8)最后,端方还给两人展示了一幅据说是顾恺之的画作。根据是费丽妲日记所载,这次拜访更具礼节性特征。

图8 Chinesisches Tagebuch, p.129
1908年2月,费舍尔结束三年任期荣归。3月,他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举办东亚宗教艺术品展,总馆长波德出席。此时费舍尔的学术名声已超出德国,被邀出席同年4月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第15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并发表演讲:
在担任德意志帝国三年任期的科学专员期间,我在东亚购买的艺术品主要是佛教木雕、早期绘画和前佛教时期的青铜器,除此之外,还有意义重大的汉代墓葬石雕以及山东省的浅浮雕装饰的石柱。(51)Adolf Fischer, Vertrag, gehalten auf dem 15th internationalen Oriendalisten-Kongress in Kopenhagen, in: T’oung Pao, Vol. 9, No. 4, 1908, p.577.
这里提到青铜器,但如今柏林和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里没有一件青铜器出自费舍尔名下的一流藏品,证明他确非这一领域有眼光的买手。借助于在学术界的名声,费舍尔开始走上坦途:1909年11月,科隆市出资赞助费舍尔前往东亚采购文物。在大阪,他特意拜会绘画和青铜器大藏家住友吉左卫门(Sumitomo Kichizaemon),求教鉴定方法(52)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40.——这是他在端方处未完成的任务。接着在沈阳大量收入康雍乾瓷器,检验自己在庆宽处学来的本领。翌年5月,再访龙门,购得一批河南新出土的陶俑。回到北京,他出手购买真假难辨的绘画:“我们一点也不恼火,即便北京的绘画市场总是令人失望。”(53)Frieda Fischer, Chinesisches Tagebuch, p.190.失望的原因在于看走眼。此次所购绘画质量仍不高,费舍尔夫妇赞美不已的明画《苏武》未在开馆导览册中出现,也未收入“二战”后馆长Werner Speiser(1908-1965)所著《东亚艺术史》,更不见于1995年出版的《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大师之作》,无疑是赝品。另一幅高其佩《少女》(Mädchen,见图9)虽被费丽妲激赏,但也未见于导览手册,这幅水墨作品脸部描绘可称拙劣。(54)Werner Speiser, Die Kunst Ostasiens (Berlin: Safari-Verlag) 299.这些误购说明费舍尔鉴定中国绘画的技能确未过关,亦反证格罗塞、屈曼尔师徒对费舍尔的指责并非都是门户之见。

图9 Die Kunst Ostasiens, p,299
1911年初,费舍尔再受科隆市委托,携重金前往东亚,屈曼尔向波德念叨:“费舍尔带着20万马克又去东亚,这位富有献身精神的科隆人令人既羡慕又嫉妒。”(55)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235.羡慕嫉妒之后,便难免生恨,费舍尔“请求文化部向外交部申请一封给德国驻东亚外交机构的推荐信,但在波德的干预下,文化部没有转这封信。”(56)Ulrich Wiesner, Die Gründerjahre des Museums 1903-1913, p.20.
费舍尔夫妇这次的幸运地是北京。7月,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处出购得10面汉唐铜镜。11月,从一韩姓古董商处购得“两块北齐时的石雕”(见图10),(57)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48, 52.其重要学术价值,已体现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中。(58)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7~43页。一河南古董商送上门来一件隋唐镀金铜质七菩萨祭坛用物:“其表面覆着一层厚厚的如同石头般的黏土,我把它浸在水里好几天,然后试着用小刀去掉黏土层,慢慢呈现出来菩萨及其带有光环的装饰物。”(59)1911年费舍尔未刊日记,转引自Adele Schlombs, 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52。费舍尔低价买入的这几件文物都入选1995年版《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大师之作》。一个国家动荡时期流散的往往是顶级文物,费舍尔能买到,不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图10 Meiserwerke aus China, Korea und Japan, p.59
作为费舍尔的后任,此时格罗塞任德国驻日使馆科学专员,恰好也在北京抢购文物,只是两人未曾谋面。如同格罗塞,费舍尔也是疯狂买家,他去世后的第三年,继任馆长费丽妲才把多余的698件藏品委托拍卖。(60)见Lepertz’sche Kunstversteigerung,第169号,Katalog Ostasiatische Kunstgegenstände aus dem Besitze des Museums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der Stadt Cöln, 1917.其中日本木雕木刻和绘画作品116件,中国绘画、青铜器、瓷器、漆器270件,另外还有朝鲜、印度和喀什米尔的文物。所不同的是,格罗塞的资金来自波德的筹集,其狂购行为屡遭波德抱怨。而费舍尔不仅有充足的私款,还得到科隆市的巨额资金。其竞购重点是中国绘画和佛教雕塑,1913年,他在导览手册前言中明确指出:“东亚艺术的伟大之处在于早期,最重要的便是绘画和雕塑。”(61)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der Stadt Köln, Vorwort zur 1. Auflage, 1927, p.7.尽管购入的古物并非一流,但他的确开风气之先。在购买和研究东亚绘画上,格罗塞和屈曼尔只能算是费舍尔的后继者。
四、 建馆之争
费舍尔就任驻华使馆科学专员之际,正是德国国内博物馆界风云突变之时:国家博物馆总馆长易帅,与前任相反,新上任的是从八十年代起致力于推动独立东亚艺术博物馆建设的波德博士。但波德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费舍尔的搜购行为和研究水平,也无法认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米勒的鉴赏能力,更与其建馆理念水火不容。波德坚定依赖的是格罗塞和屈曼尔师徒,在给屈曼尔的多封信函中,波德对在柏林的米勒和在北京的费舍尔冷嘲热讽:
费舍尔先生目前正在中国尽心尽责地狂购,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们这里的米勒教授也变身为中国和日本艺术品的热情收藏家,他从军官手里高价购买非常现代的玉器之类的物品。七号以后我要看看这些东西,有可能提出我的否决意见。(62)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21.
波德的道德文章和领导能力自不待言,他“属于极为罕见的一类人,信念坚定如铁”(63)Otto Kümmel, Wilhelm v. Bode,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H.2, 1929, p.45.——这是在职业生涯上得到波德坚定庇护的屈曼尔悼念恩主的用词,他才是波德眼中的理想的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人选:
议员Münsterberg成为东亚艺术博物馆的热情朋友——显然只是为了他哥哥的缘故。据我对此事的了解,他事先已对我们聘用您已有耳闻,所以抱怨我从一开始就把事情办坏:我把您当成了民族学家、把两件事混为一谈,等等,但我的“最大错误”他却避而不谈——即我没有请他(的哥哥)担任未来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64)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24.
“哥哥”指的是孟登堡(Oskar Münsterberg,1865-1920),德国研究东亚艺术史的先驱。蔡元培1911年在莱比锡曾助他“鉴别中国铜器”。(6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日记》第十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孟登堡博士从事印刷和出版行业,其专著尚未面世,故不是波德夹袋中人物。其弟乃帝国议会议员,试图助其兄登上尚在讨论中的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宝座,这使得国家博物馆内部之争更趋枝蔓,连远在北京的费舍尔也难以幸免。1906年10月,波德正式任命屈曼尔担任民族学博物馆新成立的东亚艺术部助理,用来制衡米勒。但老资格的米勒直到1928年退休,始终拒绝交出馆藏的东亚艺术品,导致东亚艺术部迟迟无法从民族学博物馆中分离,由此也把独立建馆的先机拱手让给了费舍尔。
1907年4月,费舍尔经朝鲜抵达东京,屈曼尔恰在同城。作为使馆科学随员的费舍尔有责任协助屈曼尔购买文物——如果他主动提出的话,孰料屈曼尔有意回避,费舍尔在给基尔市市长的信中抱怨:
我认识屈曼尔,他到了东京不见我,还是让我感到惊讶。随后我与他在东京博物馆邂逅,他未向我透露任何自己的此行使命,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惊慌,一种不信任的样子。他对我不友善,总是在隐瞒着什么。
几天以后,费舍尔又在横滨遇到前来协助屈曼尔的格罗塞:
在日本碰到我,他极为惊讶,他觉得我早已在北京。在我面前,他装模作样,好像来日本只是为了研究艺术。为了赢得我的信任,他信誓旦旦,来日本一样东西也不会购买,因为这里已无好物。他应自知,在日本他都还没摸着门呢!(66)以上两条引文均见Ulrich Wiesner, Die Gründerjahre des Museums 1903-1913, p.10.
格罗塞竭力隐瞒的是自己与屈曼尔此行的秘密使命——洽购林忠正的遗产,按理说,这事应该知会费舍尔。波德把本来属于费舍尔购买文物预算资金的一部分已悄悄拨付给屈曼尔。晚辈屈曼尔自然不买费舍尔的账,他函告波德:
像费舍尔和Migoen那样的参观当然获准,但其实只是日本式的欢迎姿态。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笑言,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只给他展示了两面镜子。(67)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176.
这样的议论属于道听途说,意气之争扑面而来。费丽妲日记可作为他们在日中两国研习和购买文物的可靠证据,其所见所闻也非屈曼尔所能想见:
就像朝圣者一样,我们从一个寺庙走向另一个寺庙。慈眉善目的僧侣尽可能地照顾我们,他们如画般的装扮及其尊贵的举止与周边的氛围极为和谐。我们的喜悦和对他们珍宝的理解,让他们深感欣慰。(68)Frieda Fischer, Japanisches Tagebuch, p.35.
年轻则不免气盛,屈曼尔或许还有说不出口的嫉妒——凭什么一个无学历的浪子轻而易举地拥有教授头衔和外交职位,还有花不完的家产和如影随行的娇妻?!其师格罗塞每次都是孑然一身前往日本,一次重感冒差点命丧异域。屈曼尔对老师格罗塞也有芥蒂,波德这样劝诫屈曼尔:
对于业已购买的格罗塞教授推荐的东西,还请你谨慎言之。……他是老一代的艺术学学者、是你的老师,你当然明了他的敏感。还有,你对米勒的直言不讳,结果很糟,他的藏品其实就是由费舍尔所买的东西组成,几件新购入的也还可用。(69)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39.
格罗塞所购文物,也不都是一流;米勒从北京购入的文物在德国国家博物馆线上展厅可查验,多属清代,不是精品,但也确实“可用”,如康雍乾名家丁观鹏的画作(见图11)。其实波德也是中日艺术品的藏家,尽管不懂中文,眼力并不差。

图11 http://www.smb-digital.de
1908年3月,任期已满的费舍尔荣归,声誉更隆:他撰写的《民族学博物馆东亚部的新购藏品》有关山东省嘉祥县汉代浮雕的内容被摘要刊登在国家博物馆刊物上。(70)Amtliche Berichte aus den Königlichen Kunstsammlungen, 29. Jahrg., Nr. 12 (Sep., 1908) 5-7.他在民族学博物馆举办的东亚宗教艺术品展,波德出席,正好在柏林的格罗塞也到场,赞扬汉代浮雕“确实不错”、浅石柱浮雕“是件好物”。(71)Hartmut Walravens, eds., Und der Sumeru meines Dankes würde wachs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 p.40.费舍尔公布了基尔建馆计划,1903年创刊于伦敦的《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也做了报道:“德国海军的家乡基尔将拥有一座崭新的亚洲艺术博物馆。”(72)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13, 1908, p.236.
1908年6月,如同打擂台,格罗塞和屈曼尔从日本采购的东亚艺术品在柏林工艺美术博物馆展出。格罗塞担心“孟登堡博士和一些人利用报刊对他所办的展览进行攻击,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未出现无理的取闹。”有人谣传波德宣称米勒的“藏品没有一件具有艺术价值”,波德不得不辩解,“我绝无可能说出这样的大话”。(73)以上两条引文均见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45, 189.
柏林的争斗扑朔迷离,基尔的建馆形势急转直下——1909年4月,财政困难的基尔市解除了与费舍尔的建馆合约,费舍尔则致函米勒:“现在我尚不知该怎么办,但我想,绝不会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珍贵藏品卖掉。”(74)Ulrich Wiesner, die Gründerjahre des Museums 1903-1913, p.15.而波德乐于看到这样的结果——“基尔官员似较其市长和费舍尔先生本人更聪明。”(75)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56.
尽管如此,还是有“更聪明”的官员认识到独立的东亚艺术博物馆对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价值。5月底,科隆市的官员专程前往基尔与费舍尔签约:
其藏品转让给科隆市,科隆市以退休金的形式每年向费舍尔支付6500马克,直到他本人或配偶逝世为止。费舍尔向科隆市支付10万马克,用于博物馆的建设,为此科隆市再向费舍尔每年支付5000马克的终身年金。科隆市承担博物馆的建设费用30万马克,……为了这些藏品能够在更大范围被利用,科隆市还计划在贸易学院设立一个相应的教授职位。(76)Orientalisches Archiv,1910-1911, Vol.1, pp.43-44.
科隆市的诚意体现在对费舍尔所提条件的充分满足,并极具远见地将博物馆的实践与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相结合,促成贸易学院的后身——科隆大学——艺术研究所的创设,东亚艺术史成为其重要学术研究分支,(77)Ulrich Wiesner, Die Geschichte der Abteilung Asien, p.4.影响至今。而首批三位犹太裔学者——Arthur Wachsberger(1819-1943)、Karl With(1891-1980)和Alfred Salmony(1890-1958)——由费舍尔从维也纳引入,在博物馆履行本职同时兼在科隆大学授课,形成德国东亚艺术史研究的“维也纳学派”,尤其是后两位在纳粹上台后逃往美国,又成为那里的东亚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学者。(78)Henry Trubner, Alfred Salmony; Karl With, Erinnerungen, in: Zur Kunstgeschichte Asiens, pp.17-31.费舍尔不仅是伯乐,而且为德国的东亚艺术史研究注入新的维也纳因素。
经历建馆挫折后的费舍尔首度亮相,是在1909年夏季的慕尼黑东亚艺术展上。在科隆市极力推动下,报名滞后的费舍尔竟然争取到展会的最佳位置,这再度引起同台竞技的屈曼尔的嫉妒:
经过约十四天的布展,费舍尔教授成功获得最大展厅并将获得观众的热情掌声。遗憾的是,我们怀疑这种掌声是否物有所值。尽管木雕在数量和尺寸上都足够应付,也无疑足够古老,但其质量极度令人怀疑。(79)Ulrich Wiesner, Die Gründerjahre des Museums 1903-1913, p.18.
屈曼尔向波德打小报告,称费舍尔“本来未被邀请,却在最后一刻以更好的东西迫使人家接受”,(80)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201.纯属猜测。费舍尔的烦恼还来自科隆市——在新馆建设期间,其藏品暂时栖身于科隆市工艺美术博物馆,这给人以误解,费舍尔绝不愿看到柏林一幕的重演,他迅速致函科隆市市长予以澄清:
尽管东亚艺术博物馆与工美博物馆共享同一堵墙,尽管吹过墙头的是同一股风,但丝毫不会改变的是我的独立性。它从来就不是工美馆的附属,而是一座自主运营的博物馆。(81)Ulrich Wiesner, Die Gründerjahre des Museums 1903-1913, p.18.
费舍尔从维也纳请来著名分离派建筑师霍夫曼(Joseph Hoffmann, 1870-1856)的门生、27岁的弗兰克(Joseph Franke, 1885-1967)博士担纲博物馆32个展厅的内部装饰设计和施工。从最初踏上东亚艺术品收藏之路,到最终安顿藏品的专门博物馆的建立,费舍尔与维也纳分离派未曾有过分离。
1913年10月26日,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在前一天为导览手册撰写的前言里,费舍尔宣告:“这里将是首次在欧洲以全面完整的方式,向观众展示整个东亚艺术的多姿多彩和繁茂鼎盛”。(82)Führer durch das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der Stadt Köln, 3. Auflage, Vorwort zur 1. Auflage, 1915, p.5.五十天之后,波德悄悄前往参观并致函屈曼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他的评论甚至有些孩子气:
本周一我在科隆逗留了几个小时,证实了您的看法:满眼都是寻常和差劣的东西,但富有技巧地摆放在明亮舒适的空间里,只是完全采用的是欧洲的方式。这样的藏品有什么用?为什么这些藏品收在科隆?(83)Wolfgang Klose, eds., Wilhelm von Bode-Otto Kümmel, p.115.
费舍尔笑在最后。但半年之后,即1914年4月,费舍尔突然病逝。波德没有任何表示,作为《东亚杂志》创刊主编之一的屈曼尔以笔名“D.H. ”(84)Adele Schlombs做出这一判断。参见Aufbruch in eine neue Zeit, p.42.撰写了一页纸的生平介绍,未见哀悼之词,却不吝“立言”和“立功”的评判:
尽管费舍尔的出版物数量很大,但基本无足轻重。一方面,其游记既无深度亦无特别的学术观察价值;另一方面,他所购买的出版物也多不具新见。当然,他并非真正的作家,也不是逐渐积累而成熟的科学工作者。
毋庸讳言的是,在一致的肯定声中,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质疑,尤其是对博物馆内容、对在科隆展示的文物、对年代确认以及命名的质疑。(85)D. H. Adolf Fischer (1856-1914),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H.1, p.104.
意气依然溢于纸面。与德国的冷淡相反,英、美行业内的反应及时而得体,且充满温情,《伯灵顿杂志》、《美国艺术新闻》(American Art News)、《大都会博物馆馆刊》(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报道及时,《伯灵顿杂志》的悼文声情并茂:
费舍尔的离去,是对他尚未了解的远东艺术学生及业余爱好者无可估量的损失。……他具有广泛影响力,是一位瞬间即可赢得本能和深情爱戴的人。亲密的朋友和仰慕的同事为失去他而哀伤,并为他的幸福生活感到欣慰。其生命的长度正好实现了自己的雄心壮志。(86)The Burlington Magazine, 25.134 (May, 1914): 128.
1937年,其遗孀、继任馆长费丽妲被纳粹扫地出门——因为其第二任丈夫是犹太人。1944年4月,博物馆被炸毁,所幸展品已提前转移。1945年12月,即纳粹倒台半年多之后,贫困交加的费丽妲离世。1977年,科隆市另行择址重建。旧址前的街道,以费舍尔的名字命名。生前,他建造了一座博物馆;死后,他赢得了一条街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