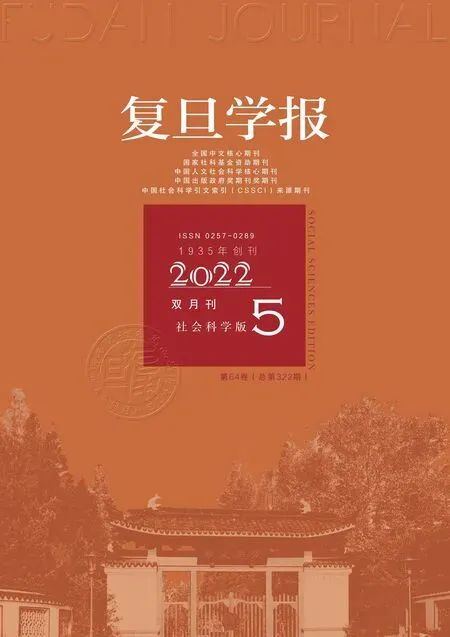自别于程朱:李塨对《大学》的诠释及其学术史意义
2022-11-27李敬峰
李敬峰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系,西安 710062)
梁启超说:“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命。”(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8页。此言可谓一语击中清代学术的优长。而在众多的经学文本中,《大学》一书“乃宋明理学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1页。更是朱熹、王阳明对垒的主要焦点。(3)钱穆说:“宋明儒学界朱、王之对垒,其主要论锋,乃集中于《大学》一书。”钱穆:《四书释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240页。聚焦到清初这一时期,尤以颜李学派中李塨的《大学》诠释(《大学辨业》、《大学传注》和《大学传注问》)较具典范性,呈现出内容丰富、视角独特、体裁多样、意义丰富的学术特质。然以往学界在“颜李”并称的框架下,过于强调颜元、李塨学术的同质、一体,从而将李塨作为颜元的附庸,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李塨学术的独特性以及在清初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中的地位,进而也难以整全地把握清初的学术面向。因此,本文以李塨的《大学》系列注本为对象,将其置于清初的学术思潮中给予详细的考察,以期从一个具体、鲜活的个案中来把握清初的学术格局和样态。
一、 《大学》文本及争议
在四书当中,唯有《大学》所关涉的争议最为繁复。尤其是“其(王阳明)与朱子抵牾处,总在《大学》一书”,(4)黄宗羲:《明儒学案》(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页。将《大学》的争议进一步凸显和放大,使得凡学者欲介入到《大学》的诠释中,首先面临和必须解决的就是《大学》文本及其争议,原因在于“文本与思想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即文本的改变会引发思想的变化,而思想的转变亦会影响文本的改变。”(5)陈群:《明清之际〈大学〉诠释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首先,就《大学》的版本来讲,李塨指出:
王草堂《二经汇刻》曰:“自程明道移易《大学》,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为然也。二程之学递传以至朱子,朱子已下递传以至鲁斋,一脉相承,源流可考。朱子再为移易增补,分别经传。鲁斋削去补传,以‘知止’、‘听讼’二段为释‘格物’、‘致知’,是徒不以师为然也。嗣后虚斋增‘所谓致知在格物者’一句,彭山削‘故治国在齐其家’七字。丰坊搀入《论语》,屺瞻定为七章,弇州、后渠另行移易,是后儒不以先儒为然也。何如恪尊原本?焉有异同?”(6)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李塨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34、934页。
(王草堂《二经汇刻》)曰: 何以朱子于《孝经》删削二百二十一字,于《大学》增补一百二十八言,以致后儒效尤,纷纷改窜,二经何辜,遭此割裂,至于此极耶?(7)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李塨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34、934页。
在《大学辨业》和《大学传注》中,李塨没有直接表露他的心迹,而是以借用与其学术旨趣高度趋同的好友王复礼(8)王复礼,字草堂,浙江钱塘人,是王阳明的后人,与李塨思想观点相近。之语来代己立意。在他看来,程颢、程颐、朱子、许衡、丰坊、崔铣等先后更定《大学》文本,尤其是朱子的改本影响最大,为后世学者开启改经移经之先路,透显的共同特质是后儒不尊先儒之说,导致言之不一,指归莫定。为了消弭这种纷争,李塨的方案是略过宋明诸儒,向前溯源,力主“《大学》用原本”,(9)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平书订》卷六,《李塨集》下,第1137页。认为应该以《礼记注疏》中所载的《大学》原本为据,也就是阳明所采之郑玄本来矫正诸种改本之误。这一“辨伪正经”举措隐含着李塨“凡古必真”的学术倾向,很大程度上着了乾嘉汉学的先鞭。尤其是他将朱子作为破坏《大学》文本的始作俑者来看待,给予严苛的批评,这就秉承了乃师颜元的“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10)颜元:《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8页。的排挤程朱理学的治经精神。
其次,在“大学”之“大”的读音上,李塨亦不惜笔墨,在《大学》经解三书中皆给予长篇辨析,因为在他看来,读音绝非只是训诂、考释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对《大学》一书的定性。李塨解释道:
大学“大”字,汉唐《注》、《疏》云:“旧音泰。”朱子《章句》云:“今读如字。”音代。夫古字通用者,时或通读,然大学称大(泰)学,犹大子称大(泰)子。古圣制度、定名,传至今犹然也,则不可臆改也矣。(11)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卷一,《李塨集》下,第932页。
这里,李塨并不尊奉朱子之意,而是依照汉唐注疏,将“大”读为“泰”。朱子之说于史无据,而汉唐注疏则是古已有之,有制度等的支撑。他在回答学人之问中将此观点进一步展开:
郑鱼门曰:“大学从古读泰学,不从《朱注》大人之学,何也?”曰:“经言大人小人,以位言,则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也,以德言,则从其大体为大人,小体为小人是也。薛方山曰‘经无以年长为大人、年少为小人者,有之,乃乡俗之谈。’用以注经,谓八岁以上曰‘小人’,十五曰‘大人’,恐不可矣。”(12)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传注问》,《李塨集》上,第708页。
李塨认为朱子是以“义理优先”为原则来释读“大”,唯有如此才符合其将“大学”定位为“大人之学”的思想主旨。但朱子这一说法是无根之谈,因为经书中只有从德和位两个角度来区分“小人”和“大人”,从来没有依照年龄来区分“小人”和“大人”。朱子将“大”释读为“泰”,并由此将“大学”定性为“大人之学”就缺乏合理性的依据,完全是朱子一家之言,不可信亦不可取。很明显,李塨遵从的是“文献优先”的原则,而朱子是“文本服从义理”的方式,两者观点出现差异自是情理之中。
最后,在《大学》文本结构的划分上,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朱子的“三纲八目”式的“经-传”结构。李塨主采古本,自然并不同意朱子这一划分,他给予自己独到的理解:
自“在明明德”至“虑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国治而后天下平”,言为其道则有事,而学其事则有物。(13)李塨:《大学辨业》卷二,《李塨集》上,第937页。
李塨用“道-事”的结构来划分《大学》,主张自篇首到“虑而后能得”主要是说“道”,而“物有本末”至“国治而后天下平”是言体现“道”的“事”,也就是说前者是体,后者是用。这种划分实际上亦是沿袭了朱子“三纲八目”所体现的“体用”之精神和旨趣。不同的是,他所划分之体和用与朱子大相径庭。在这种结构之下,李塨显然亦一并否决了朱子的格物缺传、补传之举。我们知道,自朱子提出“格物”缺传并补传之后,学者容或不赞同朱子“补传”之说,但却诱发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格物”确实有缺传,需要为“格物”寻找释文,差别在于是从文内还是文外寻找,这就是所谓的“朱熹的补注后人或有微词,但《大学》有阙文的意见却被多数学者接受”。(14)梁涛:《〈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载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新编》,《中国哲学》第23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4页。李塨的观点显然属于这一类,他是从文内为“格物”寻找释文,主张“格物”并不缺传。他指出:“诚意以至治平天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无者,以致知之功在于格物,而格物之事,即在《大学》作书者之时,大学教法尚在,不必言也。”(15)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卷二,《李塨集》上,第939页。这就是说,“格物致知”的意旨已经内在于《大学》的结构之中,根本不需要另作补传,那样反而属于画蛇添足,这就是所谓的“朱子补格致传固误”,(16)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卷三,《李塨集》上,第948页。因此“格物一传,可不必补”。(17)冯辰、刘调赞:《李塨传》,《李塨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5页。
要之,在《大学》文本及辐辏于其上的核心争议上,李塨的观点皆与朱子不类,刘师培的“国初治《学》、《庸》者,亦从朱子定本,自毛奇龄、李塨始排斥朱注”(18)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无疑是中肯的。当然,李塨虽然并未明确表示其遵从阳明,但其主张皆多与阳明一系暗合。
二、 格物所关非小
刘宗周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19)刘宗周:《大学杂言》,《刘宗周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57页。这就将“格物”释义的复杂性提揭出来,使得格物“向来是《大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思想史上很少有哪个概念能像格物这样,产生过这么多的分歧,这么多不同意见”。(20)梁涛:《〈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第80页。正是基于这一现状,李塨不无忧心地感叹到:“今格物不明,则学之正业失,正业失,则明亲之功不实,明亲之功不实,则往圣之道无以承,而斯世不获睹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关非小也”,(21)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序,《李塨集》上,第925、925页。李塨将“格物”地位上升至事关圣人之道的明晦、传衍的境地,这种拔擢不可谓不高。也正由于此,李塨对“格物”进行了毕生的思索和探究,思想几度发生变化。他说:
塨自幼从先孝悫受学,以躬行为主,迄弱冠,后往谒颜习斋先生,学六艺之学。先生言“《大学》‘格物’为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确,‘格 ’如《史记·殷本记》‘手格’之‘格’,身亲其事也。”已而出,阅当世讲学诸儒,则宗晦庵、阳明者,论格物各坚壁垒,贤达如汤潜庵、张武烈,齗齗弗相下,其他遂搆 讼,甚至操戈矛不解。私怪同尊圣道,苟有一人得其指归者,自当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乡,钱生为塨言:“《大学》起迄未载学习实功,其功具于‘有斐君子’节。”塨忽解《大学》一书,乃言学中之道在善、明、亲,而非言学习实事,如古人学礼学乐之类也。……丁丑,重入浙,戊寅端月至杭州,旅次晨兴,忽解“物”即《大学》中之“物”,“格”即可如程朱训为`“至”,即学也。“格物”、“致知”为学文诚意以至天下平为约礼。乃并解学与行是一是二,格物与诚意,以至天下平是一是二。返证之六经、《语》、《孟》,历历可据,而向未之见及也。(22)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序,《李塨集》上,第925、925页。
从这段引文中可见李塨对“格物”的理解的心路历程。首先是年二十五岁,尊父命,受业颜元闻听其“格物”为“身亲其事”之说,后又觉学者陷入非朱即王的两军对垒当中,莫衷一是,甚觉其非,颇为忧心。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李塨南游至浙江桐乡,受钱生启发,乃悟《大学》要旨在于“学中之道”,而非如乃师所言的学习实事。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南游至杭州,忽悟格物之“物”并不神秘,它就是《大学》文本中所言的“物”,而“格”就是朱子所言的“至”,是“学”的意思。这一说法受到王复礼、李甯一的肯定,并成为其思想定论。可见,李塨对“格物”的理解确实伴随着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历程,以此可见其对“格物”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乃师之说由早年的信奉到后期的背离。后在其撰写的《大学辨业》中对“格物”进一步展开论述:
格,《尔雅》曰“至也。”《虞书》“格于上下”是也。程子、朱子于格物“格”字皆训“至”。又《周书·君奭篇》“格于皇天”、“天寿平格”,蔡《注》训“通”。又孔从子《谏格虎赋》格义同“搏”。颜习斋谓“格物之格如之,谓亲手习其事也。”又《尔雅》:“格格,举也。”郭璞《注》曰:“举,持物也。”又《尔雅》“到”字、“极”字,皆同“格”,盖到其域,而通之、博之、举之、以至于极,皆格义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亲民也,即意、心、身、家、国、天下也。然而谓之物者,则以诚正修齐治平皆有其事,而学其事,皆有其物,《周礼》礼乐等皆谓之物是也。格物者,谓《大学》中之“物”,如学礼、学乐类,必举其事、造其极也。(23)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卷二,《李塨集》上,第938、939页。
李塨细数以往学者及经典关于“格”的解释,而在众多释义中,李塨最为钟情的就是朱子的“至”意。他进一步推衍其意道:“格者,于所学之物由浅及深,无所不到之谓也”,(24)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卷二,《李塨集》上,第938、939页。又说:“‘格’即可如程朱训为至,即学也。”(25)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序,《李塨集》上,第925页。可见,李塨以朱子之意为本,将“格”在“至”的基础上进行推阐,将“格”释为“学”,意在将所“学”对象由浅及深,无所不到。这就透显出李塨实际上只是与朱子名同而实不同。而对于“物”的解释,“其所争在以格物为《周礼》三物”,(26)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第233页。这就是说其所认为的“物”指向的是《周礼》所言的“三物”,他解释道:
方铁壶问:“格物必作三物,何也?”曰:“物者,学中之物,即明亲之事也。明亲之事有外于六德、六行、六艺者乎?盖六德即仁义礼智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艺即礼乐兵农也,此外无道矣。自朱子认为凡天下之物而草木并进,龙蛇杂陈,学入泛滥,茫无把持,矫而一变,遂为姚江,归于禅定,圣门之博文约礼者几亡矣。”(27)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传注问》,《李塨集》上,第709页。
在这段文字中,李塨通过层层推衍的方式阐述他何以将“物”解释为“六德”、“六艺”和“六行”。在他看来,与将“格”解释为“学”相适应,“物”也必须是“学”中之物,同时也是明亲之事,而明亲之事就是《周礼》所言的“六德”、“六艺”和“六行”。这“三物”既涵具内在的德性,亦指向外在的“礼乐兵农”等实事。李塨自认为这一解释不仅能够有效消解朱子将“物”泛化为天下万物所导致的无头脑之弊病,亦可以防止陷入阳明“格物”学说所诱发的禅定寂静之窠臼。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李塨对“物”的这一解读是否真的能够奏效呢?
可以说,李塨对朱、王“格物”学说不足和弊病的认识和把握是相当有见地的,一定程度上击中两者的要害。他的重新释义较之朱子,将“物”由原来的天下万物进一步压缩至具体的条目,限定了“物”的内容和范围;较之阳明,着意将阳明偏重于内在的正念头扩展至内外兼顾,将礼乐兵农之事纳入,体现了一贯的“征诸实用”的精神。这种调和,是否圆满无缺是需要打上问号的。这从学者对其的不同评议中可见一斑。毛奇龄则说:“李生受颜氏学,墨守六艺,谓古人只习六艺,《大学》只教六艺,已可笑矣。乃又不读书,不知六艺名目所始,反谓六经书册不是道艺,汉人以六艺名经即是贸乱,则自坐酒国安辨醒醉”,(28)毛奇龄:《逸讲笺》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7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9页。而朱一新则说:“以‘乡三物’解‘格物’,其说亦颇有根据。”(29)《朱一新全集》整理小组:《佩弦斋杂存》(上),《朱一新全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67页。从这一反一正的评价中可见,颜元、李塨师徒对“格物”的诠释乃是针对虚言格物与泛言格物者而发,颇具实学色彩。我们容或并不认同,但其从学理上纠治时弊之苦心是不容抹杀的,故清儒谭献所称的“李刚主实践朴学,折衷六艺,为命世之儒也”(30)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无疑是恰当的。
三、 诚意为明、亲之首
“诚意”不唯在《大学》八条目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承接、贯通八条目的枢纽,同样也是朱、王纷争的另一焦点。朱子强调“格物”在八条目中的第一义、优先性地位,但同时也在此框架下,将“诚意”作为“自修之首”(31)朱熹著,金良年译:《四书章句集注》(上),第10页。来看待。这里的“首”主要是针对“诚正修齐治平”而言的,与“格物”为第一序的工夫并不冲突。而阳明则反对朱子“格物”在“诚意”之前的主张,强调:“《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32)王阳明著,吴光等编:《大学古本序》,《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4页。主张以“诚意”来规范“格物”的内容和方向。虽然朱、王两者对“诚意”的定位有差别,但他们对“诚意”的重视是不容置疑的。在这样的语境下,李塨同样重视“诚意”,他反复强调“诚意为明、亲之首,故统《大学》之道”。(33)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卷四,《李塨集》上,第950页。这一定位就与阳明之旨较为接近,凸显“诚意”在《大学》中的首出地位。在对“诚意”的解释上,李塨对“诚”的理解与朱子并无不同,皆将其作为“实”来理解,但在对“意”的理解上,则多有不同。首先,他区分“心”与“意”:
冯枢天问心、意之分。曰:“心,统言之也。意,心所注之事也。心之物一,而心之境万,动静语默,常变生死,或念及,或意外,随其所值,而心即至焉。若意,则吾生欲为何人,何等事,而欲专赴之也。故心之所之曰意,意之所结曰志。志意一定,则终身之事决矣。终身诚此一意矣。盖君子庸人小人皆有心,而分正不正,意则至庸之人无之,君子意在为善,小人意在为恶,此其分也。”(34)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传注问》,《李塨集》上,第709,709页。
若《朱注》,以意为心之发,则心统动静,诚意即属正心功矣。何以经曰:“欲正其心,先诚其意”,分为二事也?况人心发念时多,未发时少,发念属诚意,则正心之功仅几希矣。若终日寂然惺然以为正心,则异端之玄牡白业,又非圣学矣。(35)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传注问》,《李塨集》上,第709,709页。
朱子、王阳明皆主张“意”为心中所显发的念虑。李塨则反对他们的“意为心之所发”的观点,主张“意为心所主之事也”,“心之所至曰意”。也就是说,“意”为心的目标和方向,是欲为圣人,而竭力达至的一种意向,是知修齐治平之善,而努力实行的一种志向。李塨的这一判定,实际上是对朱子“志者,心之所之也”的改造和发挥。他所谓的“意”是“心之所至”的定向之志,是一种好善恶恶的意向,不是朱熹、阳明所说的念虑。若依朱、王之说,一是将诚意等同于正心的工夫,与经文所言的“欲正其心,先诚其意”将两者视为两个工夫的主张相悖;二是将所有人都看作是有“意”之人,而实际上“庸人”是有“心”无“意”的,也就是无志向之人。同时,他对另一种解释亦表示反对:
先儒有以意为“主意”者,愚谓意不必训“主意”,而诚之则主意定矣。自此,心可正,身可修,而明亲之事在所必为矣。外此,又有为恶之意,在下文小人之意,非《大学》诚意之意也。盖君子诚意,诚于为善去恶之意也,故曰“不自欺”。小人亦诚意,诚于为恶去善之意也,故曰“诚于中”。唯庸人浮学,又一意曰:“姑勿为”,是之谓不诚。(36)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传注》,《李塨集》上,第724页。
这里的“先儒”主要指的是王栋。王栋是比刘宗周更早提出“意为心之所存”概念的学者。(37)黄宗羲说:“先儒曰:‘意者心之所发。’师以为心之所存……泰州王栋已言之矣……师未尝见泰州之书, 至理所在, 不谋而合也。”黄宗羲:《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南雷诗文集》上,《黄宗羲全集》第19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6页。他力主“所谓意也, 犹俗言主意之意, 盖意字从心、从立,中间象形太极圈中一点, 以主宰乎其间”,(3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33~734页。强调“意”是“心”的主宰,而非相反。李塨反对王栋这一解释,认为只要施加“诚”之工夫,主意自可定。否则,则会出现为恶之意。可见,李塨并不把为恶之意作为“诚意”之意,他所讲的“诚意”之“意”不是朱子所说的有善有恶之“意”,他说:
先儒谓诚意之意有善有恶,非也。既已入大学,而格物致知矣,尚意在为恶,亦鲜其人。即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诚意?岂教之以诚其恶意乎?(39)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卷四,《李塨集》上,第951页。
对于诚意之“意”的性质,朱子虽四次修改“诚意”注,但始终坚持“意”有善恶之分。而李塨却反对朱子的这一观点,他认为若意有恶意,那就会出现“诚”“恶意”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学》阶段,诚意是格物致知之后之事,也就是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学者已经明白为善去恶之意,已不可能落在为恶上。由此,李塨实际上主张“诚意”之“意”是好善恶恶的,不是善恶混杂的。这就与其好友胡渭之说极为相似,胡渭说:“不知所诚之意专在善一边,胡云峰曰:‘心发而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诚之之功。’盖因传有好恶二句,遂错认意有善有恶。”(40)胡渭:《大学翼真》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2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69页。李塨、胡渭之言实际上说的更多的是朱子所主张的应然层面的观点,而非实然层面的主张。也就是他着重强调的不是在善恶相杂的已发之念上用功,而是要在已发之前用功,意在矫正从已发维度理解“意”所导致的任心而行的思想流弊。要之,李塨对“诚意”的提揭和凸显与阳明相近,但在释义上却与朱子、阳明多有相异之处。
四、 李塨《大学》诠释的学术特质
作为清初《大学》诠释的典范,李塨的《大学》诠释呈现出如下明显的学术特质:
1. 汉宋兼采
李塨所处的时代,是学风“由蹈空而变为核实”(4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3页。的时代,但还不是后来以考据学著称的乾嘉汉学,而是“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42)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一集》卷二,《揅经室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6~37页。也就是皮锡瑞所谓的“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43)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第341页。这一“汉宋兼采”的学术特质在李塨的《大学》诠释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李塨的学术原本是一尊宋学,后在南游时,“始闻南方考订之学”,(4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29页。尤其是受毛奇龄影响最大。他自述“塨传注之文,实授于毛河右先生”,(45)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第166、56页。并对乃师颜元“勿染南方名士习”(46)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第166、56页。的告诫置之不理。在训释《大学》时,尤为注重名物制度、音读字义的考辨,力求通过扎实的考据训诂,为经书义理寻求扎实的依据,也就是他宣称的“不敢凭一己私意,遍考诸经以为准的”。(47)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序,《李塨集》上,第925页。但必须指出的是,李塨重视考据与清代中期的乾嘉汉学那种以考据学为务的学者有相当的距离,他说:“知训诂不足为儒,而内益之以心性,外辅之以躬行”,(48)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与方灵皐书》,《恕谷后集》卷四,《李塨集》下,第1401页。这就是强调不能单纯地以考据训诂为业,必须佐之以心性义理之学,方是儒者之道。由此可见,李塨确实还没有用汉学取代宋学的自觉和意图,可视为是清代学风由汉宋兼采到乾嘉汉学转变的过渡式人物,毕竟他的思想“终未全脱宋儒窠臼也”。(4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40页。
2. 自别于程朱
梁启超曾指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5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2页。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如何对待程朱、陆王是学者必须面对的学术议题。但与之相应的学术风气则是“世儒风气,敢于诬孔孟,不敢倍程朱。”(51)陈确:《与黄太冲书》,《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4页。李塨之师颜元则不惧世俗,对程朱之学批之甚严、驳之甚刻,主张“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52)颜元:《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颜元集》下,第 774 页。将程朱之学视为遮蔽孔孟之道的障碍而力求破除。尤其是他所主张的“汉儒见道,尤胜宋儒”对李塨影响最为深远。《清史列传》称:“塨之学出于元……于程朱讲习,陆王证悟,皆谓之空谈。……其解释经义,多与宋儒相反”,(53)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第233、246页。《大清畿辅先哲卷》更为准确地说:“塨解释经义,多与程朱不合。”(54)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第233、246页。这些论述可谓切中李塨的《大学》诠释特质。由前述可见,无论是从文本,还是义理,李塨皆对程朱之说难有认同,他“不附程朱陆王,直传孔孟”,(55)维坤:《题辞》,《李塨集》下,第930页。处处“自别于程朱”,(56)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第219页。尤其是在《大学》争议最多的格物、诚意上,皆对程朱之说给予苛责,既不认同程朱对“格物”的泛说,更不认同程朱对“意”的兼具善恶的定性。必须指出的是,李塨所批之程朱,只是他所理解的程朱,并不完全符合程朱思想的主旨。
3. 倡导实学
“虚实之辨”同样是清初的学术主题。李塨就说:“古之学实,今之学虚”,(57)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存学编》序,《李塨年谱》,第42页。《清史稿》亦称“塨学务以实用为主”。(58)冯辰、刘调赞:《李塨传》,《李塨年谱》,第56页。此言不虚。李塨在《大学》诠释中,反复强调“实学”的重要性。他在诠释“格物”时,着重凸显的就是格物的实学面向。首先,他将“物”解释为六艺、六德、六行,意在将原来或向内收缩的“格物”,或泛指的“格物”向有具体指谓的“格物”转进,使其落实到具体的实事上来。他说:
“程朱陆王何乃不言?”曰:“程朱固尝言之矣。”但圣人学习事物实学,后世渐湮,故辞或有游移耳。若认真实学,则诸儒之说皆可统摄。何者?穷理固亦学中之事也。格正事物,格去物欲,则皆学之诚意以后事也。(59)李塨著,陈山榜等点校:《大学辨业》卷三,《李塨集》,第949页。
李塨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格物”原本指向的就是实学,它是诸家“格物”学说的共同旨趣,只不过是后世学者淹没其旨,致使其不为世人所闻。正是基于李塨的实学面向,刘师培坚决反对那种将其看作为“经师”的观点,他说:“刚主继之,颜学益恢,乃后儒以经师拟之,呜呼,殆亦浅视乎刚主矣!”(60)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15页。
五、 结 语
“依经立说”(61)汪宇编:《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是中国哲学一贯的传统,而“《大学》是宋明理学最核心的经典,围绕着它的争论难计其数,而各家之差异,实牵涉到各种根本主张的不同”。(62)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页。作为受这一强势传统陶铸的学者,李塨通过对《大学》的系统性诠释,将其思想要旨呈现出来,并显豁出丰富的思想史意义。首先,迎合和助推清初的“回归原典”的学术思潮。林庆彰先生指出,清初“回归原典”运动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经学即理学、经学所以致用和说经应以孔、孟为正。(63)林庆彰:《明末清初经学研究的回归原典运动》,《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李塨显然属于第三类学者,他不仅受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助推这一思潮的壮大,成为清初“回归原典”运动中的佼佼者。其次,弥合颜元《大学》诠释的不足。颜元虽然“耻托空言,于道德则尚力行,于学术则崇实用”,(64)汪宇编:《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但却对考据训诂不屑一顾,并严令李塨远离这一学风。李塨受毛奇龄、万斯同等的影响,治经开始转向训诂考据,在汉宋兼采的视域下开展“欲反经,必自正经始”(65)钱谦益:《新刻十三经注疏序》,《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52页。的“正经”运动,意图改变宋明诸儒空言义理的解经方式,这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颜元诠释的不足。对此,姜广辉先生有着卓越的洞见:“颜元所标榜‘三事三物’只是他‘习行经济’思想的一层外衣,他经常在不经意中就将这层外衣脱去了,直言‘习行经济’,阐发其为学宗旨。而李塨却用更厚的外衣来裹挟颜学,这层外衣就是经传训诂。”(66)姜广辉:《颜李学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最后,丰富和拓展《大学》的诠释维度和思想世界。李塨的《大学》诠释在《大学》诠释史上是颇具特色的注本,原因在于他逆时代思潮而动,并没有随波逐流,淹没于清初尊奉朱子学的运动当中,而是操戈入室,从实学的角度“尽发程朱之所以失”,(67)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第220页。成为清初为数不多的批判程朱理学的注本。尤其是其独特的实学视角,进一步撑开《大学》诠释的维度,丰富《大学》的意义世界。要之,从李塨《大学》诠释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清初的学术面向是多维度的,不是单线的,这就印证了王国维“国初,学术大”(68)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3页。以及四库馆臣“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69)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页。观察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