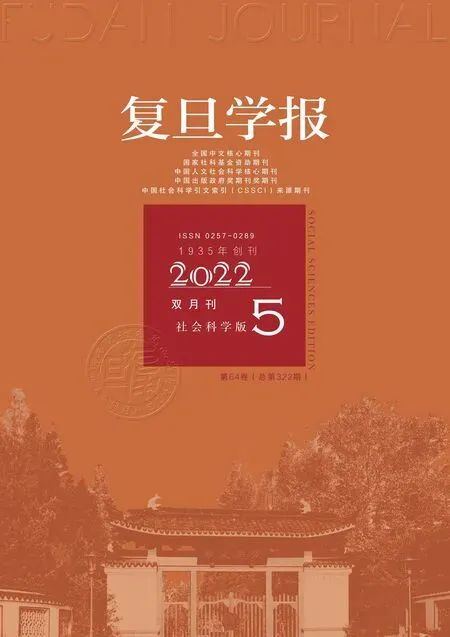贺知章生平再审视
——以历官与交游为中心
2022-11-27唐雯
唐 雯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贺知章作为唐代著名诗人,其生平、交游以及文学成就,学界很早便展开了充分的研究。(1)张仲清:《贺知章生平小考》(《绍兴文理学院》2002年第3期)、陈钧:《贺知章简谱》(《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综考其生平。辨析贺知章籍贯者有陈耀东:《贺知章籍贯里第的分歧和争议》(《宁波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张艮:《贺知章籍贯考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诸多文。钩沉其交游者则有胡可先:《贺知章交游考》(《徐州师范学院》1992年第4期)、张艮:《贺知章交游考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等文章。尤其是围绕着近几十年陆续出土的他所撰写的十方墓志,研究者或进行单篇考证,(2)如韦娜、赵振华:《贺知章撰许临墓志跋》,《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陶敏:《贺知章撰唐许临墓志考释》,《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毛阳光:《洛阳新出土贺知章撰〈姚异墓志〉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4期;王丽梅:《新出唐大理正陆景献墓志铭考略》,《唐史论丛》第十四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杨斌:《论唐〈杨执一墓志〉的文献价值》,《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牛红广:《贺知章撰张有德墓志述略》,《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韩达:《墓志、碑文与史传:多文本语境下的文学书写与史实考辨——以〈杨执一墓志〉、〈杨执一神道碑〉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李胜军:《唐裴子馀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炎黄地理》2021年第1期。或综合所有已知墓志讨论其史料价值及文学价值,(3)戴伟华:《贺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价值》,《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陈尚君:《贺知章的文学世界》,原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收入氏著《唐诗求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55~364页。虞越溪、胡可先:《新出资料与贺知章文学研究》,《国学》第七辑,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第1期。借以认识盛唐时代及贺知章本人的文学世界。不过有关贺知章生平与交游的研究,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考证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由于其人本身所留下的诗文较少,很难通过对诗文的解读来立体地还原其人生轨迹与其心路历程。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审视与他生平有关的一切信息的时候,也许会对其人生有一些不同的了解。本文即拟通过对传世文献中有关贺知章籍贯、历官等信息的解读,结合他所撰写的墓志中部分志主不平凡的生命历程,尝试重新勾勒其人生轨迹与交游,并解读他晚年脱略不羁的背后可能的原因。
(一)
传世文献中有关贺知章生平最详实的记载莫过于《旧唐书》本传,(4)刘昫:《旧唐书》卷一九○《贺知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3~5035、5033页。《新传》则仅仅增入了武后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这一有效信息,(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06页。余皆未出《旧传》范围。《旧传》中对于其“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的表达以及最终入道归乡,上自玄宗,下至百官皆作诗祖饯的宏大场面奠定了我们对他的基本认识。上推到唐代当时,无论是李白所谓一见如故、金龟换酒,还是疑似《实录》的文字中与张旭“游于人间,每见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索不如也”的记述,(6)《宋本册府元龟》卷八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889年,第3330页。都表明才高疏放的文士以及与世无争的隐士是时人乃至后世对他的一致认识与定位。不过重新审视其生平,却会发现贺知章的一生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平顺,而其看似通达的人生态度背后却有着不一般的经历。
贺知章生于高宗显庆四年(659),(7)《旧传》载贺知章天宝三年还乡时年八十六,不久即去世(第5034~5035页),逆推得生于高宗显庆四年,参前揭陈钧《贺知章简谱》。其籍贯,《旧唐书》记为会稽永兴,(8)刘昫:《旧唐书》卷一九○《贺知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3~5035、5033页。不过他本人却自号四明狂客。四明山在明州,即今宁波。另外贺知章晚年归乡时,相交甚深的卢象《送贺秘监归会稽歌》云:“山阴旧宅作仙坛,湖上闲田种芝草”,(9)孔延之编,邹志方点校:《会稽掇英总集》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页。则称其故乡为山阴。因此对于贺知章的籍贯,历来有永兴(萧山)、明州(宁波)、山阴的争论。(10)最早提出明州说是宋人莫将,其在绍兴十四年(1144)任明州太守时,建逸老堂,并作《逸老堂记》,后南宋时代人颇有主此说者,参前揭张艮《贺知章籍贯考辨》一文;山阴说代表论文见前揭张艮文。萧山说则见陈耀东《贺知章籍贯里第的分歧和争议》一文。亦有调和两者,谓绍兴、萧山皆属当日之会稽,即越州,参李珂:《贺知章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第11页。按,明州说现代学者多不取,今不论。永兴与山阴二说究竟哪个是对的呢?我们先来看两县的沿革。永兴原系南朝旧县,入唐后省废,至高宗仪凤二年(677),始分会稽、诸暨复置永兴县,至天宝元年,改为萧山。(11)《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第1590、1590页。山阴县,秦以来旧县,其县治“在州治,与会稽分理”,武德七年省。(12)《旧唐书》卷四○《地理志》三,第1590、1590页。至垂拱二年(686),“又割会稽西界别置山阴”。(1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18页。结合两县沿革,我们可知,在山阴县因为与会稽县分治越州州城,故始终处于尴尬的地位,因此唐代屡经废置,在武德七年(624),山阴便第一次被会稽所吞并,故仪凤二年分会稽、诸暨置永兴县的时候,实际上会稽分出的大部是西边的山阴故地,因此仪凤二年至垂拱二年这九年间,永兴县即包含了山阴。而贺知章的族祖贺德仁,《旧唐书》本传记其籍贯为越州山阴,(14)《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传》上,第4987页。《元和姓纂》亦云德仁、知章一族自“汉末徙会稽山阴”,(15)林宝:《元和姓纂》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313页。之后遂无迁徙,可知贺氏一族籍贯确为山阴。又贺氏此后世居镜湖侧,中唐施肩吾诗《遇越州贺仲宣》云:“君在镜湖西畔住。”(16)《全唐诗》卷四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607页。按,镜湖以稽山门驿路为界分东、西,在山阴者为西湖,在会稽者为东湖,(17)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三:“永和五年,太守马公臻始筑大堤,潴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镜湖,堤之在会稽者,自五云门东至于曹娥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阴者,自常喜门西至于西小江凡四十五里。故湖之形势亦分为二而隶两县,隶会稽曰东湖,隶山阴曰西湖,东西二湖由稽山门驿路为界。”《宋元方志丛刊》影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七册,第6943页。虽不知贺仲宣是否即是贺知章一族之后裔,仍可知其所居在湖西侧,属山阴无疑。
以上对于贺知章籍贯的考辨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山阴地划归永兴仅在仪凤二年至垂拱二年这九年之间,之后山阴县便恢复建制,终盛唐时代未再有变更。那么何以贺知章的籍贯被记作仅仅存在于这九年之间的永兴呢?可能的原因是,贺知章的籍贯最初被唐代官方文件系统记录的时间正在这九年之内,而此时贺知章正是19~28岁(本篇贺知章年龄皆取虚岁)的少年郎。一个南方的年青人之所以能进入官方的记录,参加科举是合理的解释。因为唐代前期的科举考试,举子必须在本贯(户籍所在地)投牒,通过县、州两级考试后才能获得本州推荐的“文解”,这才有资格去京城参加科举。到了京城以后,举子需把文解、家状等文件交给有司,家状则包括乡贯及三代名讳及本人体貌特征。(18)参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47页。贺知章进士出身,必然也经历过这样一系列流程。
由此,我们对于贺知章早年科第的情况可以有新的认识。此前研究者据《新传》所载贺知章“证圣初(695)擢进士、超拔群类科”这一信息认为贺知章在本年连中进士及超拔群类科,(19)前揭张仲清《贺知章生平小考》、陈钧《贺知章简谱》。然本年贺知章已37岁。如其在此年稍前赴京赶考,则与其“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自述不合。有的研究者认为他在少年时代已经离开家乡,寄居在贺德仁或族姑子陆象先家中,(20)张仲清:《贺知章生平小考》。但迟至三十七岁方中进士,显然有负《旧传》“少以文词知名”的评价,但如将其中进士的时间放到仪凤二年至稍后三五年间,一切就都能解释了。而《新唐书》所谓证圣初擢超拔群类科非源出《旧传》,而其有明确时间及科目,疑据唐代所存登科记一类材料补入。贺知章在证圣初参加制科考试,登超拔群类科应无问题,所谓“擢进士”应是连累而及,此时实际上距贺知章中进士第至少已在十年以上。
《旧传》载贺知章进士及第后即为四门博士,研究者多从其说,实际上目前见于文献的贺知章最早的官职是《嘉泰会稽志》所载其延和元年(712)八月加阶告,称其以四门助教拟宣义郎。(21)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六,《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第7019页。四门助教,为从八品上职事官,博士则是正七品上,助教升等后方可为博士。(22)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60页。宣义郎则是从七品下的散官,进士出身一般叙阶最低是从九品下的将仕郎,高不过从九品上的文林郎,(23)《唐六典》卷二,第31页。差宣义郎整整六阶。唐代官员散官品的升迁一是依据考课成绩,二是依据靠大赦等特诏赐予三品以下官员的泛阶。唐代前期官员四年任满,如果每年的考课等第都是中中的话,再次铨选授官的时候可以进一阶,如果比较优异则可加速升迁。(24)《唐六典》卷二:“内外六品已下,四考满,皆中中考者,因选,进一阶;每二中上考,又进两阶;每一上下考,进两阶。”第32页。不过不管以哪种算法,延和元年,53岁的贺知章所任的四门助教绝非其第一任官,在此之前他至少经过了一两次迁转,其起家官应该更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少年登第,然而贺知章的仕途并不顺利,渐入老境的他至此仍在担任较为基层的四门助教,其蹭蹬可知。
转折发生在不久之后。在短短的一年中,贺知章从四门助教升至四门博士,又至太常博士:
贺知章与族姑子陆象先特相友善,知章长于象先。景云二年,象先自中书侍郞加平章事,又加二品,知章始被引为四门博士及太常博士,身犹衣碧。后二十余年,象先为少保,知章授银靑光禄大夫。(25)《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一五,第3624页。
逮睿宗嗣历,复于北苑白莲华亭及大内甘露等殿别开会首,亦亲笔受,并沙门思忠及东印度大首领伊舍罗、直中书度颇具等译梵文,北印度沙门达摩、南印度沙门波若丘多等证梵义,沙门慧觉、宗一、普敬、履方等笔受,沙门胜庄、法藏、尘外、无着、深亮、怀迪等证义,沙门承礼、神暕、云观等次文,太子詹事东海郡公徐坚、邠王傅固安伯卢粲、尚书右丞东海男卢藏用、中书舍人野王男苏瑨、礼部郎中彭景直、左补阙祁县男王瑨、太府丞颜温之、太常博士贺知章等润色,中书侍郎平舆侯陆象先、侍中巨鹿公魏知古等监译,前太常卿薛崇胤、通事舍人弘农男杨仲嗣监护,缮写既了,将本进内,睿宗外总万方,内崇三宝,御笔制序,标于经首。前后总译五十三部,合一百一十一卷。(26)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66~567页。
陆象先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在景云二年(711)十月,(27)《旧唐书》卷七《睿宗纪》,第158页。次年,也就是延和元年的八月,贺知章尚是四门助教,而本年八月初三,睿宗即传位玄宗,改元先天,贺知章被引为四门博士显然已经到了先天年间。而《开元释教录》所载参与译经的一连串人物结衔透露了此段文字的写作时间:魏知古为侍中在先天元年八月庚戌(13日),而陆象先在次年七月三日玄宗发动政变后的庚辰(19日)便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故此番译经只能在此十一个月中。贺知章连续从四门助教升至博士,又转太常博士。四门助教到四门博士,虽然是学官系统中的正常升迁,职事品却遽然跃升为六阶。虽然唐代职事官的升迁并不完全取决于品级的高升,但在前期,品级仍旧是跃迁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姚崇武后时因应对契丹入侵得当,自夏官(兵部)郎中(从五品下)“超迁夏官侍郎”(正四品上),(28)《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1页。不过五阶。贺知章此次授官,尚非为皇帝亲所赏拔,故其超升速度实为惊人。《册府》引文有“身犹衣碧”一句,实际上是作者感叹其职事官升迁之快,(29)按《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文明元年七月诏……八品已下旧服者并改以碧。”(第1953页)据上文所考,延和元年八月以后,贺知章散官已升至从七品下,已可衣绿,《册府》记载稍误。因为散官品与职事官品阶差一般不会太过悬殊,散官品升迁需积劳考,而职事官的升沉陟降则取决于各种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如果从四门助教升至博士尚属学官内部升迁的话,转任太常博士则意味着贺知章由较为清冷的学官系统进入了九寺中最为重要的太常寺了。太常博士虽然品级不高,但却负责着各类皇家祭祀及礼典的引导、主持,所谓“其位虽卑,所任颇重……郊祀礼仪,朝廷典法,举措取则,职事实繁”,故而俸料“准六品已下常参官例处分”。(30)王溥:《唐会要》卷六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42页。更重要的是,官员去世以后的谥号也是先由太常博士拟定的,所谓“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如无异议的话便成为官员一生的定评,如有问题,太常博士则可以和三省官员一同集议,讨论其人一生的功过是非。(31)《唐六典》卷一四,第395页。因此,出任太常博士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朝中的核心官员。而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贺知章的表亲陆象先。
陆象先,苏州人,娶贺晦之女,贺晦另一女嫁萧嵩,(32)《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初,(嵩)娶会稽贺晦女,与吴郡陆象先为僚婿”,第3093页。今墓志已出土,记其祖为贺敱。(33)萧嵩妻贺睿墓志已出土,拓片刊《秦晋豫新出土墓志蒐佚续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502页。据《旧唐书·贺德仁传》,敱为贺德仁堂侄,(34)《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传》上《贺德仁传》,第4987页。则贺晦女为德仁曾孙辈,《姓纂》载贺知章为德仁族曾孙,(35)《元和姓纂》卷九,第1313页。则贺晦女与贺知章同辈,则陆象先所娶为贺知章族妹,而上引《册府》谓陆象先为贺知章族姑子,则其父陆元方亦娶于贺氏,则贺陆至少两代联姻。又萧嵩为昭明太子曾孙萧瑀之侄曾孙,系兰陵萧氏后裔。由此可勾勒出一个北迁南方士族的婚姻集团。
不过无论是贺德伦还是萧瑀都早早入北,(36)《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瑀九岁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闻,姊为隋晋王妃,从入长安。”《旧唐书》卷一九○上《贺德仁传》:“德仁事陈至吴兴王友,入隋,仆射杨素荐之,授豫章王府记室参军。”陆氏稍晚,元方“伯父柬之以工书知名,官至太子司议郎”。(37)《旧唐书》卷八八《陆元方传》,第2875、2875页。成长于会稽的贺知章与他们虽是亲戚,但实际上族属已远。而陆元方生性谨慎,《旧传》称其“在官清谨,再为宰相,则天将有迁除,每先以访之,必密封以进,未尝露其私恩,临终取前后草奏,悉命焚之……又有书一匣,常自缄封,家人莫有见者,及卒视之,乃前后敕书,其慎密如此。”即使在儿子陆象先的授官问题上,陆元方也极为克制:“象先……应制举拜扬州参军,秩满调选,时吉顼为吏部侍郎,擢授洛阳尉。元方时亦为吏部,固辞不敢当。顼……竟奏授之。”(38)《旧唐书》卷八八《陆元方传》,第2875、2875页。陆元方对儿子尚且如此,对于儿子的朋友显然更不会有特别的关照,因此贺知章五十岁之前的仕途与其早年的声名相比,实在是有些坎坷。
景云二年十月,在太平公主死党崔湜的强力推荐下,陆象先骤然拜相。(39)《旧唐书》卷八八《陆象先传》:“初,太平公主将引中书侍郞崔湜知政事,密以吿之,湜固让象先,主不许之,湜因亦请辞。主遽言于睿宗,乃并拜焉。”第2876页。虽然史称陆象先“清净寡欲,不以细务介意”,(40)《旧唐书》卷八八《陆象先传》,第2876页。但在他上任后极短的时间内贺知章便超迁四门博士和太常博士,而他的连襟萧嵩也两度被他汲引,以致本传称嵩“骤迁殿中侍御史”。(41)《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第3094页。虽然官方记载称陆象先在景云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了中立,(42)《旧唐书》卷八八《陆象先传》,第2876页。但是他本身由崔湜推荐拜相的立场,出任宰相后迅速提拔自己亲友的行为,以及玄宗政变成功后十多天便立刻将其罢相外放的结果,让人不免怀疑陆象先是否真如本传所称的那样清静寡欲、保持中立。
不过贺知章的确因此进入了政治核心圈。上揭《开元释教录》所载的译经活动应该是景云至先天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一系列借文化活动为名而进行的政治站队的一种。早在睿宗刚传位的先天元年八月至十二月间,玄宗便敕修了《一切道经音义》和《妙门由起》两部道经,其参与者的构成非常值得玩味——主持这两部书撰修的是后来在先天政变中被杀的高道史崇玄,而参与者包括了太平公主一党的昭文馆学士和政治立场偏向玄宗的崇文馆学士。两方人员之所以如此诡异地一同进行道书的编纂,雷闻认为系方便彼此之间的互相刺探。我们可以看到,在两部道经修撰的时候,无论是主持者还是实际参与者都以太平公主一方为多。(43)本文关于《一切道经音义》及《妙门缘起》之论述皆参考雷闻:《唐长安太清观与〈一切道经音义〉的编纂》,刊《唐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9~226页。据雷闻统计,参与人员中昭文馆学士13人,崇文馆学士9人。而在稍后所进行的译经活动中,(44)《一切道经音义》编纂之时,卢藏用结衔为工部侍郎,而至《开元释教录》所述,卢藏用已为尚书右丞,《旧唐书》卷九四本传称其“迁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工部侍郎、尚书右丞”(第3004页),显然译经在编纂《一切道经音义》之后。两方的力量对比有了微妙的变化。从上引《开元释教录》文字来看,参与的人员名单中,徐坚、陆象先、魏知古的政治立场都偏向于玄宗,薛崇胤为太平公主子,(45)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94页。卢藏用则又一次出现在名单中。不过这次属于玄宗一方的力量似乎更强一些,毕竟陆、魏两位史称颇具独立性的宰相都担任了此次译经活动的监修。而贺知章则以新任太常博士的身份参与到了此次译经活动中,不过从名单的排列来看,贺知章的资历显然是最浅的,即使是排在他前面一位的颜温之,其所担任的太府丞,品级也在从六品上,较太常博士还要高四阶。
此后贺知章的仕途不复五十岁之前的蹭蹬坎坷,几乎是一路坦途。他在太常博士任上至少待到了开元三年,(46)许临墓志作于开元三年,贺知章结衔尚为太常博士。此后的一年时间,贺知章连续转官,《嘉泰会稽志》记录了一方开元四年八月转为起居郎的告身。(47)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六,《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第7019页。原刻当然已经佚失,不过制书原文今天尚保存在《文苑英华》之中:
勅:朝议郎(正六品上)、前行户部员外郎贺知章,业优词学,时重才行,禀精微之髙妙,体仁恕以明达,必能书法不隐,立言可观,职于版图,伫擅声于铅笔。可行起居郎,散官如故。(48)《文苑英华》卷三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952页。
此时,贺知章的散官品已经连升七级,从四年前的宣义郎跃升为正六品上的朝议郎,职事官也从前一年七月的太常博士转为仕途八俊之一的户部员外郎。不过贺知章任户部员外郎的时间应该很短,至少到了四年的八月即已转为起居郎。起居郎和户部员外郎同为从六品上阶,不过从户部员外郎这一要职的位置转为专门负责起居注撰写的起居郎,却表明此时贺知章的仕途又一次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根据孙国栋对尚书诸司员外郎迁入迁出的统计,起居郎往往迁为尚书诸司员外,而员外迁出的正途当然是诸司郎中,其次则为士林华选的中书舍人。孙氏的统计中并没有尚书员外迁为起居郎的记录,(49)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4~58页。这可能是由于他漏计了贺知章的这次迁转。但可以看到,终唐之世,由尚书员外转起居郎,从现存的材料来看,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可说是一种“逆行”,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贬谪。此时贺知章显然从炙手可热的尚书郎官退回了学术官僚系统之中。之后,他又迁秘书少监,与起居郎一样,走的都是清而不要的知识官僚路线。开元十年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又奏请知章等入书院同撰《六典》等书,(50)《旧唐书》卷一九○中《贺知章传》,第5033页。从此开始了其文馆学士的生涯。之后不久贺知章又回到了太常寺,升任太常少卿。从秘书省迁至太常少卿,不仅在品级上跃升两阶,更使贺知章在这段时间内暂时离开了清而不要的学术机构,进入了九寺之首的太常寺,这无疑为他后续的升迁奠定了基础。果然在开元十三年的四月五日,贺知章自太常少卿迁至更为清要的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51)《唐会要》卷六四,第1322页。此后一直到其致仕的十八年间始终兼任集贤学士。对于此二职,当时的宰相源乾曜和张说有过这样一番议论:
乾曜问说曰:“贺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说对曰:“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52)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5页。
这是时人对于尚书省侍郎与集贤学士的认识。虽然张说对学士一职大加褒扬,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终究只是学术加衔,而侍郎却是真正的“具员之英”。在尚书各省责任尚重的开元时期,作为尚书省次官的侍郎显然是更为清要的职位。这大概是贺知章第二次有机会驶入唐人升迁的快车道。不过仅仅一年之后,岐王范去世,(53)《旧唐书》卷九五《惠文太子范传》,第3017页。作为礼部侍郎的贺知章非但无法弹压因为遴选挽郎不妥引起的门荫子弟的喧诉,更被子弟们逼迫到登梯翻墙逃离现场,一时间传为笑柄,(54)《旧唐书》卷一九○中《贺知章传》,第5034页。因此责授清冷的太子右庶子。(55)贺知章撰杨执一墓志,结衔为“右庶子、集贤学士”,杨执一墓志拓片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一册,1998年,第108页。录文刊《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36~1338页。虽然一度曾检校工部侍郎,不过从秘书监同正员的兼职和集贤院学士的馆职来看,(56)《法书要录》卷六窦臮《述书赋》下,第174页。他并未脱离学术官僚的轨道。此后贺知章又转秘书监,最终以太子宾客正授秘书监,始终未回到八俊的坦途上来。当时流传着有关他在秘书监久不升迁,朝中谓张九龄刻意压制,故贺知章因而借张罢相之机调笑以讽的轶事,(57)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卷一○,第92页。实际上反映了朝廷对他的最终定位。
从贺知章在开元年间的履历,我们可以看到,贺知章在任职户部员外郎后原本已经打开了仕宦的上升空间——事实上出任太常卿和礼部侍郎都显示了执政者在当时对其仍抱有学术官僚之外的期待,毕竟礼部和太常寺都有许多与祭祀、仪礼有关的日常工作需要处理。不过贺知章在礼部侍郎任上的表现和官方记载中留下的“晚年尤纵,无复规检”的印象可能最终导致其仍旧回到了学术官僚的轨道上来。(58)《旧唐书》卷一九○《贺知章传》,第5034页。为秘书监十八年,可能并不是张九龄对他的刻意压制,而是包括玄宗在内的高层对他的统一认识。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相对于他恣意潇洒的晚年而言,秘书监和集贤学士无疑是个相当适合他的位置。
(二)
如果贺知章的为官经历可以概括为几番触碰到权力核心之后归于闲散的话,他所交往的部分不太寻常的人物,或许对他晚年纵诞的形成有着些许意义。
我们对于贺知章交游,最有印象的几幕可能是初见李白时便呼之为谪仙人,便以金龟换酒;或是“与(张)旭游于人间,每见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59)《宋本册府元龟》卷八六一,第3330页。仿佛他所交往的人物,都是与他性情相投的潇洒纵诞之人。然而,这只是他交游的一个面向。事实上在他长达八十六年的一生中,有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物曾经深深地卷入到政治的漩涡之中,实际上此前所提到的陆象先本身便是景云年间政治漩涡中的人物,所幸陆氏未参与到此后的先天政变中去。而贺知章的其他一些亲友、相识却实实在在地卷入到唐前期历次政变之中,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是一些“危险人物”。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贺知章的另一位表亲,开元二年去世的曹州刺史许临。许临的墓志由贺知章所写,贺知章在墓志中交代了许临的家世历官之后,原原本本地记录了许临作为睿宗和太平公主的一方在先天政变中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家两代与睿宗的深厚渊源:
公讳临,字思顺,颖川人……南迁居于丹阳句容……曾祖胤,陈秘书监,隋蜀王师。祖叔牙,皇朝太子洗马,修文、崇贤两馆学士,太宗文武圣皇帝侍读。父子儒,皇朝吏部侍郎,赠秘书监,修文、崇文两馆学士,太上皇侍读,颍川县开国男。公……年廿三,以门资授殿中进马,转卫州司功,相府骑曹,稍迁录事,并参其军事,又除□□。时太上皇代邸潜龙,王门市骏,醴筵必备,同视申公之厚;琴瑟不拥,尝□史之入,故曳长裾者久之……神龙初,迁咨议……除虢州长史……岁余,授邠王府司马……除太子仆,擢为羽林将军,又徙为右武卫将军……夫典兵司禁,体国经埜,非征南之奉法,绛侯之必安,孰能□矣……公忠信兼之,足以干事。曩者常元楷等,窃发宫掖,秘为乱常。公以守道不如守官。太上皇楼居,繄公以义,夫劫之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挠。……天子休之,加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60)录文见前揭陶敏《贺知章撰唐许临墓志考释》及韦娜、赵振华《贺知章撰许临墓志跋》。
由此我们可知,许氏家族早迁南方,曾祖曾做过陈秘书监,不过与贺德仁、萧瑀家族一样,在隋代便已北迁。这里的太上皇指墓志写作当时尚在世的睿宗,可知其父曾为睿宗侍读,这便可以解释许临为何很快进入相王府担任骑曹参军,并任王府录事参军和咨议参军。墓志称其“曳长裾者久之”,用《汉书·邹阳传》之典,谓其久事王府,考墓志载许临开元二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则出生于龙朔二年(662);后文记其于神龙初(705)之后不久出为虢州长史,则此时他已44岁,距其23岁入王府已21年,的确久历年所,为睿宗亲信。
许临出任虢州长史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便出任邠王府司马。邠王是李贤子守礼,神龙中“遗诏进封邠王”,(61)《旧唐书》卷八六《邠王守礼传》,第2833页。这里的遗诏显然是武则天的遗诏。武则天于神龙元年十二月去世,守礼进封应在次年,与许临迁邠王府司马时间约略相值。邠王自武后时即与睿宗诸子同住,过往甚密,而王府司马在王府官中仅次于长史,因此许临此番出任邠府次官,可能也是睿宗为其悉心运作的结果。
许临此后的一任官是太子仆,考虑到神龙三年七月节愍太子乱后,中宗朝已无太子,这一任官所服务的对象可能即是玄宗。从许临父子与睿宗的渊源及其后来先天政变中的表现来看,许临并不是玄宗一党,而太子与睿宗及太平公主的明争暗斗在景云初年即已开始。(62)参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唐雯:《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如上文所述,在编纂道书和译制佛经的文化活动中,两方人物尚且在同一修书局中彼此渗透,睿宗派亲信出任太子仆亦属情理之中。
之后作为文官的许临仕宦走势显得更为诡异,他先是被擢为羽林将军。我们知道建制于武后时期的羽林卫是北门禁军中的一支部队,景云至先天年间,睿宗、太平公主与玄宗为控制北门禁军在羽林将军和大将军的人选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上文所提到的《一切道经音义》和《妙门由起》编纂人员中出现了三位羽林将军,他们分别是右散骑常侍权检校左羽林将军徐彦伯、右散骑常侍权检校右羽林将军贾膺福、主爵郎中权检校右羽林将军李猷。徐彦伯,“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63)刘:《隋唐嘉话》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页。贾膺福、李猷后来都在先天政变时被杀,显然这三位都是睿宗一党人物,而许临应该也在此时转任羽林将军。因为玄宗即位,太子暂缺,(64)玄宗的次子瑛至开元三年方被立为太子,见《旧唐书》卷一○七《废太子瑛传》,第3258页。一众东宫属官可能都有调整,故睿宗借此机会将其安排入北军。与许临、徐彦伯一样,贾膺福、李猷都是文官出身,这就导致这些睿宗一党的羽林军将领有其天然缺陷,也决定了之后政变的走向。(65)本段论述参上揭唐雯:《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在这批文士出任的羽林将军中,许临和徐彦伯都在先天政变前离开了羽林军,避免了贾膺福、李猷的悲惨命运。关于徐彦伯的转任,《隋唐嘉话》有这样一条记载:“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66)《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页。之后很快便告老辞官,并于开元二年去世。(67)《旧唐书》卷九四《徐彦伯传》,第3006~3007页。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徐彦伯的政治嗅觉,他完美地避开了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
许临似乎没有那么敏锐地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离开北军之后的下一个官职是右武卫将军。虽然北门禁军在唐代政变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日常的宫城守卫却是南衙十六卫的工作。右武卫的职责之一便是掌宫城之守卫,朝会的时候,将军需要带领门队驻守在正殿前或嘉德门内。(68)《唐六典》卷二四,第620页。宫城的正殿是太极殿,其外有太极门,往南则是嘉德门,再往南则是宫城正门承天门。(69)辛德勇、郎洁点校,[宋]宋敏求、[元]李好文撰:《长安志·长安志图》卷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32~233页。事变当天,睿宗闻乱北走至肃章门观变,又往南一路跑至承天门登楼召唤南衙卫士,当时承天门被关上,所以导致侍御史任知古组织的入宫勤王士兵被挡在了外面。(70)《旧唐书》卷一○六《王琚传》,第3250页。
作为右武卫将军的许临,按照职责范围可能在嘉德门北或太极殿驻守,也可能在皇城北部紧临承天门广场的右武卫驻所,参与了任知古组织的南衙卫士勤王行动。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许临最后被玄宗一方的兵士阻断了勤王的努力,并被控制了起来,方才有墓志“夫劫之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挠”的表述。显然许临在先天政变中坚定地站在睿宗一边,终不负两代辅佐相王的情谊。不过之后他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是被外放为曹州刺史。《旧唐书·陆象先传》云:“时穷讨至忠等枝党,连累稍众,象先密有申理,全济甚多。”(71)《旧唐书》卷八八《陆象先传》,第2876页。以许临睿宗死党的身份,能得到这样不错的结果,或许也是陆象先“全济”的结果。
作为不在现场的中层官僚,贺知章墓志中所提到的先天政变中的这些细节应该得自于许临本人,可见其与许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此外,这篇墓志写于开元三年七月稍前,距先天政变不过两年,贺知章却毫不避讳地写到了“太上皇楼居”这一细节。事实上,睿宗在登承天门楼上为的是组织南衙士兵对抗玄宗,在无法组织起抵抗的前提下,睿宗“闻东宫兵至,将欲投于楼下”,(72)《文苑英华》卷九七二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第5113页。欲以自杀来成玄宗之过。这一事件在当时是极为敏感的,但是贺知章仍将其写在了墓志中,并将许临的表现许之为“义”。至少在开元三年,贺知章还是敢于表达自己的立场的。
另一位同样卷入过政治风暴的人物是开元十四年去世的鄜州刺史杨执一,他的墓志也是由贺知章撰写的。同时,张说为他撰写的神道碑今亦保存了下来。在这两份材料中,我们惊异地发现他在武后末年曾经激烈地反对过张易之,之后又参与了神龙政变,并且怀疑与王同皎预谋刺杀韦后与武三思事件有关:
当天后朝,以献书讽谏,解褐特授左玉钤卫兵曹参军,盖贲贤也。常以攀槛抗词,削草论奏,遂为贼臣张易之所忌,黜授洛州伊川府左果毅都尉。长鸣必在于远途,左退适成其踠足。次当禁卫,复以封事上闻,天后深纳恳诚,亟蒙召见。趋奉轩戺,咫尺天威。载犯骊龙之鳞,爰□断马之剑,衷见于外,朝廷嘉焉。擢拜游击将军,迁右卫郎将。俄除左清道率,转右卫中郎将押千骑使。既而长乐弛政,辟阳僭权,压钮之兆未从,左袒之诚先发。安刘必勃,望古斯崇。中宗践祚,以佐命匡复,勋加云麾将军,迁右鹰扬卫将军……特赐铁券恕死者十,并厩马、金银、瑞锦之类。昔周武建邦,贤人所以表海;汉高创业,功臣所以誓河。魏绛锡重于和戎,甘宁宠加于克儁,无以尚也。府君秉心直道,奉上尽忠,虽穷鉴水之规,犹勖维尘之诫。初为武三思所愬,出为常州刺史,后转晋州。又谮与王同晈图废韦氏,复贬沁州。久之,三思以无礼自及,府君许归侍京第。(73)《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114页;《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336~1338页。
乃濯缨潢渚十,献策金门,干当代之圣君,论天下之成败。秦皇览奏,屏左右而与谋;汉帝闻言,膝前席而不觉。一见拔玉钤仓曹,再见取尚食直长,三见置典设郎。骤进直词,深触权嬖,为易之兄弟所嫉,左授伊川府果毅。又上封章,帝用嘉纳,加游击将军、右卫郎将。历左清道率,换右卫中郎、押千骑,使总统貔虎,便繁肘腋,故得协心五王,戡剿二竖,奋飞北洛,推戴中宗,嗣唐配天,不失旧物。……驸马都尉、琅琊王同皎,亲贤地切,休戚图深,安刘之策未遂,钟室之灾先及。吏扇纷狱,公陷关通,贬徙沁州刺史,不知事,仍长任。(74)《赠户部尚书河东公杨君神道碑》,收入熊明:《张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17页。
由此,我们可知杨执一的进身是由于献书武后,这在当时是比较常见的出身方式,陈子昂亦是因此得官。(75)《旧唐书》卷一九○中《陈子昂传》,第5018页。之后杨执一的历官走向有些离奇,据《神道碑》,他在献书求得左玉钤卫兵曹参军之后还屡次三番向武后奏事,并且因此迁尚食直长和典设郎。墓志所谓“常以攀槛抗词,削草论奏”并非只是虚词。不过最初只是一个正八品下的诸曹参军的杨执一,何以能屡次三番轻易上封事并获得武后召见,还能“深触权嬖,为易之兄弟所嫉”,这其中缘由颇难索解,不过《旧唐书》提到其兄杨执柔在“则天时为地官尚书,则天以外氏近属,甚优宠之。时武承嗣、攸宁相次知政事,则天尝曰:‘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由是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76)《旧唐书》卷六二《杨执柔传》,第2383页。杨执一的速度升迁未知是否与此有关。不过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武后对杨执一似乎颇为信任,竟然能由其“骤进直词,深触权嬖”,这当然会引起二张的猜忌,终于导致他的外贬。
而杨执一任伊川府左果毅都尉之时仍旧借着“次当禁卫”的番上机会再一次上了封事。这次所上封事的内容似乎比较重要,杨执一不但再次得到了武后的召见,并号称“犯骊龙之鳞”,并因此赐以断马之剑。断马之剑用的是汉代朱阳的典故,朱阳求赐以斩佞臣张禹。(77)《汉书》卷六七《朱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15页。这里剑指的对象应该就是跟杨有过矛盾的二张兄弟。如果墓志中的这句描写并非出于杨执一或者贺知章夸张虚构的话,那么墓志所显示的武后末年的政治走势则有一些超出我们的常识——武后信任杨似乎超过了二张,在杨那么明显地针对二张的情况下仍旧被任命为“右卫中郎、押千骑”。千骑是北门禁军中的主力之一,武后将与二张有过矛盾的杨执一放到这样关键的位置上,“使总统貔虎,便繁肘腋”,显然将北门的管钥交到了他的手中,这是否表明了她此时已经放弃了二张呢?杨执一最终果然参与了神龙政变,协助五王,拥立中宗复位,神道碑直接将他能“协心五王,戡剿二竖”归因于他总北门之兵的便利。
政变成功后的杨执一并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被武三思所忌,外放为刺史。不料很快在晋州担任刺史的杨执一被牵连到王同皎谋反案中,再一次卷入了政治漩涡。王同皎是中宗女儿定安郡主的丈夫,神龙政变中他“与右羽林将军李多祚迎太子于东宫”,因此立功。神龙二年,王同皎因不满武三思专权任势,便招集壮士,计划于武则天灵驾发引回长安时,劫杀三思,结果被同谋告发,被杀于都亭驿。(78)《旧唐书》卷一八七上《王同皎传》,第4878页。借着王同皎事件,武三思在朝中掀起大狱,包括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暐、张柬之等神龙功臣在内诸多大臣因此流贬。(79)《旧唐书》卷九一《桓彦范传》,第2930页。杨执一作为神龙政变的功臣之一,即使身在外州亦被牵连,直到武三思被杀,他才有机会回到京中。
这样一位深深卷入武后末期至中宗时代政治事件,可以说侥幸善终的人物,他的墓志由超脱世外的贺知章来撰写,似乎有些违和。墓志本身未曾交代贺知章与他的关系,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张说的神道碑记杨执一夫妇合葬时间在开元十五年六月,而墓志则记作九月,可能的解释是杨家因故推后了葬礼的时间。墓志既然能记录更改过的葬礼时间,其写作也应在神道碑之后,二者能看到些许的承袭关系,但后出的墓志仍在神道碑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内容。比如杨执一在开元年间出为许州刺史,神道碑未言其缘由,墓志则称其“府君怀柳惠之直,任汲黯之气,或忤时政,颇不见容,出许州刺史”,明言为宰相所出,不考虑其背后的政治因素,至少而言,贺知章对杨执一的人生际遇是比较熟悉的。同时墓志相较于神道碑,对于杨执一的人生际遇有着更多的同情。如在叙述其任朔方元帅整顿军吏之事,结果导致军情不稳,被迫离开朔方一事,墓志明显站在杨的立场对其被迫转官表达了愤怒和惋惜:
慰抚凋亡,纠绳滥窃。攘襁逾于巨万,盗骏轶于千蹄。而皆社鼠稷蜂,咸乃倾巢熏穴,竟以黄金见铄,白玉成磷。遂移疾朔方,来思右戟,复为右卫大将军,寻除右金吾大将军。
而神道碑则云:
公刚肠疾恶,擒奸摘罪,曩将之所弥缝,宿吏之所干没,匿赃散廪,一征百万;矫枉过正,众口嚣然。改右卫大将军,无何,复右金吾大将军。
显然张说的表达并未站在杨的立场,而是以“矫枉过正”隐隐表达了对他的不满。(80)杨执一墓志与神道碑的对比可参韩达:《墓志、碑文与史传:多文本语境下的文学书写与史实考辨——以〈杨执一墓志〉、〈杨执一神道碑〉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综上,贺知章与杨执一可能还是有一些私交的,墓志中才会流露出更偏向于志主本人的立场。而这是已知的第二方贺知章为曾经参加过政变的风云人物所写的墓志。
接下来的一方墓志,志主张有德本人早在贞观年间便很平顺地过完了一生,可是来延请贺知章撰写合祔迁葬墓志的家属却大有来头。墓志云:“嫡孙云麾将军、守左羽林军大将军、上柱国、邓国公暐等以为徽烈虽存,陵谷将贸,用题贞琰,以贲幽穸。”(81)《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沧州刺史始安郡开国公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录文见牛红广:《贺知章撰张有德墓志述略》,《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这位主持葬礼的张有德嫡孙张暐是玄宗为潞州别驾时的死党,玄宗的废太子瑛便是他进献的歌姬赵氏在他家中降生的。玄宗为太子后,他“与诸王、姜皎、崔涤、李令问、王守一、薛伯阳在太子左右以接欢”。在玄宗先天元年即位之初,他便被任命为右羽林将军,并主动提出要以羽林兵肃清太平公主一党。此事可以说是第二年先天政变的先声,当然最终因为张暐的行事不密,在事变之前就被揭发了出来,张暐因此流放岭南。玄宗消灭太平势力后,他也随即回到了京城,先后担任京兆尹、太子詹事、判尚书左右丞。(82)本段关于张暐之生平见《旧唐书》卷一○六《张暐传》,第3247~3248页,参前揭唐雯:《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请贺知章撰写墓志的开元九年,他正在左羽林大将军的任上,这意味着此时的张暐掌握着北门禁军,地位清贵而敏感。
以上几位可以说都曾经深深卷入过武后时代以来的政治风暴,并偶然幸存的下来的人物。虽然除了有着中表之亲的许临以外,我们很难衡量贺知章与杨执一、张暐的交往程度,但从他对于许、杨两篇墓志中相关段落的较其他墓志更为细致的表达中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对这些他虽然未曾参与,但实际上离他并不遥远的事变,他应该都是有所触动的,毕竟和他有过交集的这些人曾经距离被当时这一连串的政治漩涡吞噬只差了一点点而已。
让贺知章本身更为切近地感到政治险恶的应该是他任皇太子侍读的经历。《旧传》称其为皇太子侍读在开元十三年,这时候的皇太子是后来被废的李瑛。李瑛是玄宗次子,即是为潞州别驾时生在张暐家中的那个孩子,本名嗣谦,这一年他“改名鸿,纳妃薛氏,礼毕,曲赦京城之内,侍讲潘肃等并加级改职,中书令萧嵩亲迎”,(83)《旧唐书》卷一○七《庶人瑛传》,第3258~3259页。下文述太子瑛事如无特别注明,皆出《旧传》,下不一一出注。可以说是李瑛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贺知章可能因为潘肃的改职而成了他的新侍读。《旧唐书》对诸王侍读有这样一段记载:
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又引词学工书之人入敎,谓之侍读。……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亦分院而居。(84)《旧唐书》卷一○七《凉王璇传》,第3271页。
也就是说,侍读是需要去皇子或皇太子所居教授的。玄宗时的皇太子往往在帝所在的别院,因此作为皇太子侍读的贺知章虽然并无实权,但离权力中心是极为接近的。他的职事官也很快从礼部侍郎迁为太子右庶子,跟皇太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危机也在巅峰时刻埋下了种子。就在太子大婚的同年,原本养于宁王家的寿王回到了宫中,(85)《旧唐书》卷一○七《寿王瑁传》,第3266页。他的母亲是此时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因此寿王“钟爱非诸子所比”,太子瑛因此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旧传》称“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应该就是从寿王回宫开始的,而此时正是贺知章任太子庶子兼侍读的时候。到开元二十三年,随着武惠妃女儿咸宜公主下嫁杨洄,(86)《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记咸宜公主出降在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12页。事情进一步发酵了起来。杨洄希武惠妃旨,日求太子瑛的过错,上报给惠妃。惠妃则泣诉于玄宗,称“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因而震怒,意将废黜。我们不太清楚贺知章的侍读生涯持续了多久,但显然在开元十三年寿王回宫以后,太子瑛的处境逐渐变得尴尬,而贺知章作为侍读未必没有感受。开元二十五年,李瑛被废杀,天下以为冤。即使贺知章此时早已不再担任皇太子侍读,对于已经七十九岁的他来说,心灵所受到的冲击也一定是巨大的。
然而在此之后,贺知章的仕宦生涯仍旧与皇子们纠缠在一起。在《旧传》中,贺知章最后一任官是太子宾客兼秘书监,然而《述书赋》记录的是“秘书监、太子宾客、庆王侍读”。(87)《法书要录》卷六窦臮《述书赋》下,第174页。此时的太子便是肃宗,开元二十六年立。肃宗在玄宗时期的尴尬地位以及玄宗借李林甫之手试图铲除在肃宗周围形成的势力,学界论述已多。即使作为名义上的东宫僚属,贺知章不会感受不到压抑的政治气氛。更诡异的是,贺知章同时还兼任了庆王的侍读。庆王是玄宗的长子,(88)《旧唐书》卷一○七《靖德太子琮传》,第3258页。但是玄宗一开始便没有立他为太子,即使废了李瑛,也再次将他排除在外,其中缘由不得而知。但就和睿宗长子宋王成器一样,庆王的长子身份对于皇太子总归是一种尴尬的存在。而此时贺知章以太子宾客同时身兼庆王侍读,身份也同样尴尬。
当我们分析了以上这些曾与贺知章所交往的部分人物之后,再来看史书中对于贺知章性格的描写,或许会有别样的感受。“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的背后或许是游走在政治核心边缘的贺知章看过了交游们在政治风云中惊心动魄的浮沉,皇子们在皇帝父亲无常的喜怒之下无法把握的命运之后有意的选择。
天宝三年正月,八十六岁高龄的贺知章求为道士还乡,玄宗率领群臣作诗饯送。快要走到人生终点的贺知章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前半生的坎坷蹭蹬,晚年洒脱后的别有深意,都被这光环所笼罩,尚未盖棺,早已论定。然而看似毫无内容的历官信息、所撰墓志所勾勒的交游网络,却揭开这个看似潇洒的老人所经历过的起伏动荡,让我们窥见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