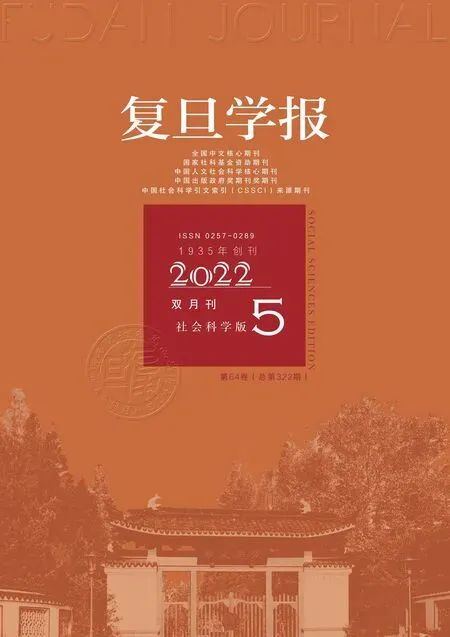即兴写作与空间意象:司汤达的叙事特点及其内在意蕴
——以《帕尔马修道院》为中心
2022-11-27杨亦雨
杨亦雨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一、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作为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中的著名作家,司汤达的小说不仅内容具有创造性,而且在写作与叙事方面也呈现独特的个性,这种独到的写作与叙事风格,又构成了他阐发文学理念的重要形式。在《帕尔马修道院》这部作品中,以上特点得到了经典的展现。
《帕尔马修道院》是司汤达继《红与黑》之后创作的又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该书的内在主题涉及自由、幸福等问题。自由、幸福本身是启蒙时代的重要观念,近代的思想家从不同的侧面对此作了阐释。以即兴写作和空间隐喻为叙事方式,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形象地表达了对以上问题的理解。注重细腻的心理描写,是司汤达创作的特点之一。他长期致力于情感研究。对他而言,理解情感、识别人性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也是走向自由与幸福的内在条件。以此为视域,司汤达十分认同爱尔维修关于人类有权享有幸福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自由和幸福的理解。从其个人经历看,司汤达不仅用科学的方法论证情感和幸福,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亲身践行,并由此追寻自由与幸福:对于玛蒂尔德的疯狂爱恋让他险些丧命,却成就了《论爱情》中对情感和幸福的独特定义与区分;他追随自己的精神领袖波拿巴远征沙场,虽未获胜,却感知到鲜活的情感和逐梦的自由与幸福。毋庸置疑,这种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不断折射在他的文学创作里。在司汤达的作品中,自由和幸福总能得到诗学的呈现,并成为他笔下主人公们争相追寻的终极目标:于连从一心一意向上爬到回归平凡幸福;米娜放弃优渥生活,冒险寻找真爱;富商之妻莱昂诺尔为了追求马戏团演员梅拉尔,不惜众叛亲离,艰难度日。在所有这些作品里,《帕尔马修道院》无疑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范本。该书出版于1839年,是司汤达创作晚期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不但展现人物追寻自由与幸福的曲折路径,也试图探讨幸福的真实内涵。在作者眼中,幸福在于自由行动与意志的自主选择,在于映现本真的自我形象。具体而言,自我既表现个体的自身认同,又以个体的自觉意识为其内容。作者运用即兴、空间意象等独特的写作方式,赋予人物自主行事和成就“英雄主义”的可能。
自由与“幸福”都是西方文学作品中常论不衰的主题,它涉及人类生存状况、精神追求、伦理判断等诸多深刻的论题,关于幸福内涵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幸福与德行关系紧密,幸福只有通过“德”和“善”才能实现。在谈到幸福与人的存在的关系时,康德曾指出:“尽管幸福使拥有幸福的人感到愉悦,但他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全面地善;相反,它总是以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前提条件。”(1)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93.对康德来说,合乎道德基于善良意志,后者又以实践理性的自由立法和选择为内容。在这里,人的自由与幸福的追求形成了某种关联。以梭伦为代表的思想家则认为,幸福是一种真实的生存经验。具体来说,幸福由五大基本要素组成,即中等财富、健康的身体、愉悦的心情、好的儿孙以及善终。这一看法已注意到了幸福的内涵既包含精神和意识层面的具体体验,也涉及人的多方面存在境遇。本文拟通过分析司汤达在《帕尔马修道院》中所运用的即兴创作和空间意象的写作方式,探讨其对自由和幸福的理解。
二、 即兴写作:叙事之外的意向
根据相关记载,司汤达仅用五十二天,便通过向速记员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这部巨著。可惜的是,专门收藏司汤达作品手稿的格勒诺布尔市立图书馆并未保留这部作品的原稿,后辈研究者也因此无从探寻该书的创作起源。然而,不难推测,极快的创作速度和口述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的书写方式:快速写作预示作者创作时的随意性和自由度,口授的方式则通过语言的连贯性,推动创作的进展。这一推断,也通过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之间往返的信件得到了证实:“我曾经在创作小说时,确实列过提纲,比如在写《法尼娜·法尼尼》的时候,可一列提纲我就会失去创作热情。我口述25~30页的内容,到了晚上,我需要好好消遣一下;第二天早上什么都忘记了,但只要看一眼前天写的最后三四页内容,便会确定今天要写些什么。”(2)Stendhal, Projet de réponse à Balzac, deuxième version uvres romanesqu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tome III, 2014) 663.从中可以看到,司汤达在创作《帕尔马修道院》时,并未制定周密的写作计划,对故事的发展也缺乏预先的设想。在他看来,过于精密的布局会阻断灵感的涌现。与之相对,他采取是一种全然相反的写作方式,比阿特丽斯·迪迪耶( Béatrice Didier)将这种随性而至的创作方式称为即兴写作(improvisation)。在《司汤达与幸福口述》中,迪迪耶把以上创作方式描述为一种“类似手工艺般的创作,与任何专业性写作无关”(3)Béatrice Didier, Stendhal ou la dictée du bonheur (Paris: Klincksieck, 2002) 59.,并认为其特点在《帕尔马修道院》中得到精妙的体现。众所周知,“手工艺”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不同于程序化的运作,也不受严格的规范约束。与之“类似”的写作方式,也相应地有别于专业化的模式,而是以灵活性和创造性为基本取向,后者同时构成了“即兴写作”的内在特征。
不难发现,即兴写作与作者的早年经历不无关系。司汤达的母亲博学开朗,但可惜在司汤达早年已逝,此后,其刻板保守的父亲和家庭教师拉亚尼神甫对小司汤达实行严苛的教育,抑制了他的自由天性和创造性。他每天必须严格遵行时刻表行事,定点完成读书、学习拉丁文、外出等活动。1800年,17岁的司汤达首次到达意大利,加入远征军,投身马伦哥战役。直到这时,司汤达才逐渐摆脱早年受到严格控制的生活方式,感受到自由的氛围和蓬勃的生命力量。司汤达在后来趋向于即兴随意的写作方式,既可以看作是对早年被“禁锢”的生活方式的反叛,也可以视为“释放”的军旅生活所留下的印记。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深切地感受到意大利特有的文化氛围。虽然深陷战乱,意大利人却依旧追寻共和、自由的梦想:他们充满激情,情感热烈,依照本能行事,极富创造力,将自由意志融入生活方式之中,总是试图成为一个一个不可复制的独特的“我”。在艺术方面,强调即兴创作的意大利谐歌剧(operabuffa)和即兴喜剧(commediadell’Arte)也让司汤达深受启发。在意大利的这两年,思想的解放、行为的自由和艺术的创造性让司汤达同时领略了真切的幸福:“我全然沉醉其中,感受到一种狂热的喜悦和幸福感。至此,一个充满激情与幸福的时代正式开启。”(4)Stendhal, Vie de Henri Brulard (Paris: Gallimard, 1973) 412.显然,司汤达将幸福的概念与自由思想、自主行事和尽情创造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可从自由的行为和追寻自我的过程中收获幸福。他将自己这种自由和幸福的理念,通过即兴写作的书写方式,融入到《帕尔马修道院》的文学创作中。事实上,即兴写作本身即包含自由行事、任其发展之意。作者既在书写的过程中获得自由和幸福感,也赋予笔下人物以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可能。
毋庸置疑,由于没有具体提纲,又付诸口述,即兴写作不同于基于严密构思的创作:虽然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却不免出现描述模糊和不断重复等现象。在人物描写时,年龄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指征,然而,作者对此往往只给出一些模糊的推断: “法布利斯是法国人来了以后生的,好像是1789年左右。”(5)Stendhal, La Chartreuse de Parme (Paris: LDP, 2018 ) 136.(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译文采用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郝运译本。)桑塞维利娜公爵夫人的年龄更是让人捉摸不定。在人物登场时(1796年)就给人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吉娜当时大约13岁,不过看起来却像十八岁。”(27页)在之后的情节中,类似情况也时有发生。按作者的描述,1814年,她看上去像31岁,到了1815年,莫斯卡伯爵以为她28岁左右。而1822年,本该39岁的公爵夫人,却被描述成36岁。类似含糊的书写还出现在对景物的描述中。在第15章中,法布利斯“正在登上那通往法尔耐斯塔的三百八十级的楼梯。”(353页)到了下一章,法布利斯又“爬上通往法尔耐斯塔的牢房的那三百九十级楼梯。”(366页)二者完全处于不同的空间,但却被作者杂糅在一起。这种写作方式固然体现了自由的运笔,但也往往使作品显得扑朔迷离。
即兴写作的另一局限在于同一情节的不断重复。例如,法布利斯在滑铁卢战场上的经历就经过多人之口被重复了数次。主人公先是在第一次入狱后向看守的妻子表明护国的决心。经她指点后,在向随军女商贩和奥布利伍张复述自己的冒险时,他掩饰了真实动机,将同一情节包装成了一个寻亲的故事。当法布利斯在一家客店养伤时,两位年轻姑娘又通过想象把他的冒险美化:“以为他是一个乔装改扮的王子。”(115页)然而到了法布利斯哥哥阿斯卡涅口中,同样的经历却转为一封告发信,信中,法布利斯成了庞大阴谋组织的成员。在后一情景中,为了解救他,姑妈桑塞维利娜公爵夫人又向宪兵、宾德尔男爵、译事司铎等将同一情节颠来倒去地绘制出不同的版本。
从表面上看,同一情节的重复难免显得单调、乏味。但如果仔细分辨,便不难发现,司汤达极力将同一情节以多样、丰富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就内容而言,同一段经历在作者笔下衍化出不同的内容,同一情节则被分解成多个版本,构成独立、全新的故事,拓宽了原始情节的叙事边界。从形式上看,司汤达在以上写作过程中运用多种叙事方式以展现同一个故事,包括第一人称讲述、第三人称转述、对话叙事、通过想象或回忆呈现事件与人物的变化等。情节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的叙事模式和话语结构,这些多样的叙事形式为文本增添了故事性和可读性。可以看到,即兴创作时的自由空间和自在想象为丰富单一情节和多样性叙事提供可能,而单一情节呈现出的多样性则可视为即兴写作的必然产物:只有在作者天马行空的自由灵感之下,才能实现多样化的文学效果。
以上两点当然不是即兴写作结出的唯一成果,在司汤达自由的创作空间中,还有许多其他即兴创作的特点,制造巧合便是其中之一。在《帕尔马修道院》中,充满了各种巧合,光是“巧合”(hasard)一词就出现了45次。举例来说,在兵荒马乱的滑铁卢战场上,法布利斯在与女商贩走散后,又能不断重逢;同样是在纷乱的沙场上,主人公遇到了自己的生父罗贝中尉;桑塞维利娜公爵夫人总能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法布利斯身旁:主人公先是在一家店铺里,与姑母府上的马车夫巧遇;此后又在一家酒馆中“看见他姑母的亲随头儿佩佩……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281页)毋庸置疑,巧合的发生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让故事变得更加曲折、紧凑。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巧合”一词与“自由”紧密相连:自由的即兴创作为巧合的产生提供前提条件,也让巧合的存在变得更具合理性。在巧合的运作下,书中人物的行动范围变得更为广阔,与外在行动相对应的内在精神领域也随之趋向自由。作者笔下的《帕尔马修道院》中的人物也与作者自身一样,总在“即兴行事”。法布利斯在听到密探的消息后,就决定抛下一切,投奔拿破仑;在一次打斗中,主人公激情所致,杀死了吉莱蒂,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法布利斯在每次危机中的种种说辞,也皆是即兴之作。可以看到,司汤达将即兴写作时的自由意志投射到了笔下人物身上,主人公们在自由精神的感召下,摆脱羁绊,探究自我的多个维度,追问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和司汤达一样,在自由中感受到精神独立和自主行事的幸福,也在自由中理解存在和幸福的涵义。借用斯宾诺莎的话来概括:“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6)斯宾诺莎著, 贺麟译:《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22页。这里,“生的沉思”指的就是对存在和幸福内涵的推敲和反思。
虽然即兴写作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但读者发现,司汤达似乎也在试图跳出即兴写作的摆布。一般来讲,即兴写作容易产生前后不一的疏漏(包括前文提到的信息不一致)。然而,我们却在文本中读到许多工整的前后呼应。这种呼应通常通过“征兆”的方式展现:在法布利斯得知拿破仑登陆儒昂湾的同一时刻,“看见在右边空中极高的地方飞着一只鹰,拿破仑的鸟。”(58页)这一情景与日后主人公征战沙场交相呼应;在战场上,法布利斯穿上死囚的衣服,感到“这一切都是不祥之兆,我命中注定要进监狱。”(103页)这为他后来被关入法尔耐斯塔的牢房埋下伏笔;在第一次遇见克莱莉娅时,法布利斯的直觉意识到:“这倒是个可爱的狱中伴侣。”(125页)这一假设也在日后成真。事实上,这些征兆与呼应暗含宿命论的观点。不难注意到,这里的宿命(必然)与上文的巧合(未知)相互对应,彼此渗透。从本质上来说,生命由必然和未知组成,未知往往与偶然相关,幸福则在必然的命运与未知的偶然的相互作用中。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曾在1968年的新年祝福中,鼓励大家对生活充满热情,追寻自我,因为幸福是人类真正的天命。司汤达的看法与之相近,二者都肯定:在自由中生发出的所有巧合(冒险、奋斗、创业)的原始动力主要来源于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幸福既是人类的理想,也是生活所追求的目标。
不难想见,以口述的方式完成的即兴创作充满口头用语的表达和口语性的效果,读者从文本中出现的大量对话中便可观察到这一特点。当然,司汤达并未囿于这样的设定之中,而是极力隐射“缄默”的重要性:书中人物的真实想法经常通过无声的心理独白展开;法布利斯和克莱莉娅总是通过非语言的手势传情;作品结尾处主人公在沉寂的修道院中归隐。作者似乎想透过这些细节向读者传递一种对自由和幸福的思考,即二者的不可表达性:人们难以完全达到自由之境,也无法确切描绘幸福的程度。即使在“奔放的热情中”,法布利斯和克莱莉娅也没有通过任何语言来表达“极度的幸福”(573页)。这里,司汤达再次跳出即兴写作的局限,赋予自由和幸福以缄默的色彩,暗示了其不可言说的特性,由此从一个方面进一步阐发了对二者内涵的理解。
三、 空间意象及其内蕴
在《帕尔马修道院》中,除了运用即兴创作的方式揭示幸福的内涵,司汤达还试图通过不同的空间意象来解读自由与幸福的意义。从宽泛的意义上看,“空间意象”隶属于空间叙事的范畴。在传统的叙事学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时间,因为叙事归根到底是一种语言行为,而语言表达又需要依照先后次序和时间辅助才能得以完成。然而,叙事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表述方式,存在于时空之中,而时间和空间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当然无法忽略空间的具体作用。正如让-伊夫·塔迪埃(Jean-Yves Tadié)所言:“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7)让-伊夫·塔迪埃著,桂裕芳、王森译:《普鲁斯特和小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事实上,空间在叙事文本中承担着双重角色。其一,故事情节总是在一个既定的空间场景中铺展开来,所以空间是情节构成的要素之一:它既可以成为整部作品创作的基准点,也能通过场景的变更,推动情节发展。米歇尔·克鲁泽(Michel Crouzet)甚至认为:“小说的生命动态来源于空间的位移,主人公的人格形态取决于他所到达的位置。”(8)Michel Crouzet, Le roman stendhalien: la Chartreuse de Parme (Orléans: Paradigme, 1996) 33.总的来说,通过这一功能,空间直接参与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其二,在叙事文本中,空间不仅是叙事进程下的简单布景,还常是贮存回忆、记录历史、发挥想象、抒发情感之地。这些回忆、历史、想象和情感赋予空间以更深沉的蕴意。此时,时间和空间彼此相融,因为这些元素的产生势必需要二者的共同介入与相互配合。在这样的“艺术时空体”中,空间成为展开多元社会关系、探索主体存在方式的场所,并展现了调动人物感官、引发内在情感的作用。在《帕尔马修道院》中,司汤达正是借用空间的以上功能并通过多样的空间意象,展现了笔下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内在的心理活动,而主人公在精神领域对幸福的追寻与解读也由此得到敞开。
在作品上卷中,科摩湖是一个频繁出现的空间意象。在第一章中,读者了解到科摩湖位于格里昂塔城堡附近,这是法布利斯成长的地方。作为自己故土的一部分,主人公对科摩湖倾注了极大的情感。他认为这是一片至美之地,以至于该湖周围连带的风景也变得无比动人,他被“科摩湖附近那些森林的庄严或者动人的景色迷住了……最能打动我们心灵的森林。”(236页)此外,童年的故土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它能触及人物的多重记忆。记忆作为人类存在的普遍精神体验是映射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表征之一,这些承载记忆的空间意象展现出有别于其他地理空间的独特性,具有见证人物心灵成长、引发真切情感的功能。在描述主人公的童年回忆时,作者写道:法布利斯望着两个湖汊,“美丽的景致使他很快就忘掉其他的一切,在他心里唤醒了最崇高的情感。童年的回忆不断涌上心头。……这一天,恐怕算得上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中的一个了。”(228页)这里,人物的童年的回忆通过遥望某个空间介质被彻底唤醒,并生发出一种由衷的幸福感。此刻,科摩湖不再是单一的物理空间,而成为迈克·克朗(Mike Crang)笔下富有深意的“文学地理景观”。由此,作者实质上“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9)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不难推断,主人公对童年的经历和故土的风景怀有真挚的情感和眷恋,如此,才会通过欣赏科摩湖这一空间意象,感受到幸福。同时,童年记忆所激发的幸福感,与前文提到的司汤达对幸福内涵的理解遥相呼应:通常来说,童年生活意味着无拘无束的行事态度和自由驰骋的思维方式,这与作者日后推崇以自由的方式处世不谋而合。事实上,此时的科摩湖不仅是可以承载记忆、呼应人物精神领域的空间意象,而且也类似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提出的“存在空间”,是人物隐藏在潜意识深处的私密领地;在意识之流的自由涌动中,它构成了判定“我”未来是否幸福的参照标的。
书中的另一主角桑塞维利娜公爵夫人也对科摩湖抱有深切情感。和法布利斯的感受相似,科摩湖让她“无限欣喜地重温着少女时代的旧梦”(52页);也使之认为:“平静的幸福生活终于在那美丽的湖边,我出生的地方,等着我啦。”(51页)然而,对于公爵夫人这一女性人物来说,科摩湖又是一个杂糅了现实与想象的空间载体:“她常在湖边去梦想重新再过那种豪华而奇妙的生活……她想象着自己在米兰的大街上,和在总督时代一样幸福快乐。”(154页)这里,科摩湖转化成了两层空间:第一空间是司汤达笔下的物质空间,第二空间则是公爵夫人用想象建构出的诗学世界。原本扁平的物理空间蜕变为立体的想象场所,科摩湖作为地理意象介入到女性的情感和欲望中来,成为女性精神领域的衍生与参照,这种特定的想象空间似乎更符合感情丰富、心思细腻的女性的审美经验和存在体验。这里,空间与人的主观感知相结合,成为内在于认识主体的感性直观形式。(10)郭辉:《文学空间论域下的文学理论之生成》, 《学术论坛》2012年第7期。
此外,想象的过程意味着碎片化的意识片段和多维的思考模式。这些片段常以交错、并置、互文、重叠、异位的空间模式层层展现。这些断裂的片段构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学场,并汇聚成一种“块茎”(Rhizome)式的意识空间模型。在这个巨大的观念化场中,公爵夫人将自己对于幸福的向往都投射到了科摩湖畔的想象空间里,渴望“与总督时代一样幸福快乐”。弗兰克曾在自己的空间学著作中引用埃兹拉·庞德的如下观点:“图像,是在瞬间中呈现出的智力和情感的复合体。”(11)Josef Frank, The Idea of Spatial For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这里的图像既是空间的所指,也蕴含着主体的能指。在这里,瞬时性所凝结的时间超越了特定的时域而同时呈现绵延性与广延性,意识空间即兼有以上特点。确实,小说中公爵夫人所内含的幸福渴望内在地展现出女主人公试图在幸福瞬间中达到时空中无限这一观念趋向。
在面对科摩湖时,无论法布利斯还是桑塞维利娜公爵夫人,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处所意识”(topophrenia)。科摩湖都能唤起“他们持续、强烈的意识和关切,这是主体与空间中的一种内在关系,也是主体存在的空间性特征”(12)方英:《空间转向之后的存在、写作与批评——评塔利的〈处所意识: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 《外国文学》2021年第3期。。在此,科摩湖既是文本叙事的空间意象,又是主人公追求幸福和展现自我的内视空间。
在作品下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空间意象无疑是法尔耐斯塔。这是一座高得惊人的监狱,法布利斯由于谋杀罪被投入监狱之中。在大众的认知中,监狱常常被等同于人间炼狱,意味着禁锢与困苦。可被囚禁的法布利斯不但“被这宏伟的美景感动了,迷住了”(406页),“并不感到自己不幸” (434页),而且甚至在监狱中发现“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刹那”,并认为“再没有能和它相比的了。”(422页)法布利斯之所以在监狱中依然感到幸福,是因为与克莱莉娅隔窗相望时,产生了爱情:“只要能看见她,我就幸福了。”(416页)此前,虽然主人公也有过一些情感经历,可那些爱情过于轻佻,转瞬即逝。未曾料想,他最终在限制自由的监狱中收获幸福。可以看到,对法布利斯而言,没有任何外部环境和条件可以限制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力和自主的选择。借用后来萨特的看法,可以说,“就连刽子手的屠刀也没有免除我们的自由”。(13)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48页。监狱本来是政治法律权力的一种象征,然而,司汤达笔下的监狱却呈现出一种“反权力”的空间倾向,并展现了另一种生存可能和形态:原本处于被监视和控制的个体,现在却成为观看他者的主体。由此,权力秩序开始出现某种转折,其中蕴含着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的更迭。在观看的过程中,个体同时保留了创作性与选择权利,构建了在监狱中特有的空间性单元。
在《帕尔马修道院》中,象征束缚和奴役的法尔耐斯塔成为映射自由和幸福的空间意象。相反,原本代表优渥自在生活的格里昂塔城堡却成了主人公眼中不可跨越的寒冬和牢笼:“我不能再在这座阴沉沉、冷冰冰的城堡里消沉下去。这些古老、发黑的围墙……,你不觉得它们正是阴郁的冬天的形象吗?”(59页)显然,在法布利斯看来,真正的不幸是麻木的肉身,而非被禁锢的自由心灵。换言之,在自由精神的驱使下,幸福在于激情和行动。事实上,在法尔耐斯塔中,法布利斯克确实既与莱莉娅产生了炽热的爱情(激情),又尽一切可能向莱莉娅表达自己的爱意(行动)。在这里,司汤达借用法尔耐斯塔这一空间意象,再一次表达了自己对于幸福内涵的理解。
此外,身处高耸的监狱中,主人公与外界隔离,有了更多思考与审视自我的契机。在《浪漫的监狱》中,维克多·布隆贝尔(Victor Brombert)认为监狱是个体实现自我成长、获取独立人格的场所之一。(14)Victor Brombert, La prison romantique, Essai sur l’imaginaire (Paris: José Corti, 1975) 71.和于连一样,法布利斯在狱中明白了幸福的真正含义:之前征战沙场的英雄主义梦想在此刻失去了意义,他的真正幸福在于留在爱人身旁:“我不原意逃走;我愿意死在这里!”(453页)此时,尽管主人公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他仍旧冒着巨大风险,甘愿放弃身体的自由,陪在克莱莉娅身边。在他看来,这种勇气和牺牲才是英雄主义的具体内容和真正意义,也是达到自由和实现幸福的方式和途径。确实,在追寻自由和幸福的艰难路途中,每个人都需要一些英雄主义的情怀和气魄。另外,法尔耐斯塔的惊人高度,既显现了主人公与世隔绝的生存境遇,也暗示了自由和幸福的另外两层内涵。第一,这里的高度不仅指涉物理高度,更象征着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的高度和灵魂的升华,这意味着自由和幸福是高尚灵魂才能获取的生存状态。第二,空灵的自由和崇高的幸福置身云端,与现实世界保持了某种距离。作品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需要攀登数百级台阶才能到达高塔,这一特质既隐喻了自由和幸福的难以企及性,也呼应了作品结尾“献给少数幸福的人”的题词。然而,正如上文所言,只要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彰显真正的自我,不放弃多方面的努力,人总是能够在不同意义上达到自由和幸福。
最后,回到作品的标题“帕尔马修道院”。司汤达对这一空间意象着墨不多,只在全文的最后一笔带过:法布利斯“隐退到离萨卡两法里,波河岸边树林中的帕尔马修道院去。”(645页)就外在形式而言,帕尔马修道院表现为一种相对确定的空间意象,隐退的选择则显示了某种自我沉淀。然而,它的背后,则是主人公通过动荡、曲折的人生冒险走向心灵自由和幸福理想的心路历程:在看似静态的空间意象中,蕴含和浓缩着动态的变迁过程。作为独立的个体,法布利斯在其存在过程中,总是难以仅仅停滞或凝固于某种形态。在司汤达之前,蒙田曾自称自己从不描绘状态,只描绘过程,司汤达的叙事也体现了相近的趋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法布利斯始终处于流变的过程,这一人物形象既暗示了精神的自由灵动,也隐喻了对幸福的不懈追求,这也许是司汤达所塑造的法布利斯这一角色具有恒久魅力的原因所在:不囿于单一的生活模式和人生理想,不断通过自身的多样行动与创造,以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概要而言,以即兴写作和空间意象的展现为叙事方式,司汤达在《帕尔马修道院》中展现了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和追求。这一进路首先折射了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之后,对世俗意义上美好生活的向往,就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趋向,在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以及后来席勒、歌德的作品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这种人生理想既体现了人的觉醒,也展现了肯定人的自由、关注人的存在意义的近代价值取向。即兴写作和空间意象等叙事方式以意识的灵动、空间的延展等形象方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代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以上书写方式也从文学的角度,表达了人类的普遍关切。如果说,启蒙时代的印记赋予这一作品以具体的历史形态,那么,普遍的人类关切则通过探寻文学的永恒主题而呈现了恒久的意义。正是以上双重品格,使这部小说成为十九世纪文学史中的不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