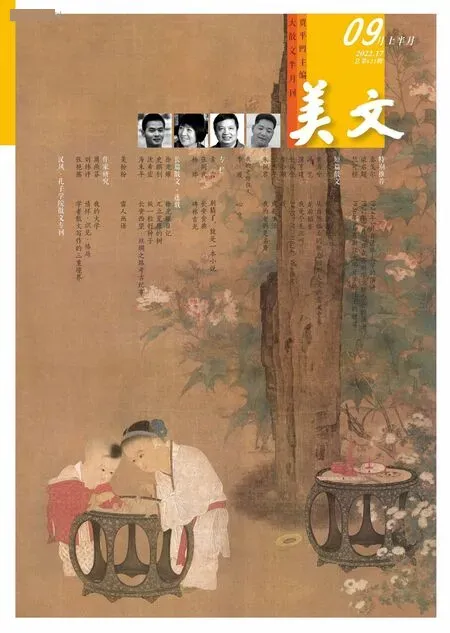我的大学
2022-09-17周燕芬
◎ 周燕芬
我的大学,叫“西北大学”,老校区坐落于古城西安西南城角,就是护城河由东到西再向北拐弯的地方。
我于1981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第五届大学生。经过了77级以来的几届高考招生,对于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来说,如何报考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按说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但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成绩这个决定因素外,好像并没有多少个人的未来规划参与其中。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陕北老家,父亲做主说,女娃娃家的,不要走太远,西安就最好。西北大学中文系在陕西是拔头筹的,我的成绩又刚好够上了分数线,很顺利就被录取了。从榆林到西安,长途客车摇晃了两天,晕得要死要活,迷迷瞪瞪地被高年级学长接进了西北大学的校门。
那是一个多雨的秋天,开学一个多月了,阴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加上极度地想家,给父亲写信说,西安哪有你说的那么好,连太阳都没有,写着写着禁不住要哭。太阳终究还是出来了,西北大学的新鲜姿容和迷人风物展露眼前,吸引我去亲近她融入她。大学生活日日变得紧张有序和丰富美好起来,唯一不同的是我离开了家,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掰着手指头期待着寒暑假。那时候不知道上大学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意识到,大学正在为我寻找一个新的家,一个独立自主的家,一个依托终生的家。
40多年过去了,我由一个西大的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到入职当老师,直至今天变成学生眼里的老教授,西北大学120年的历史,晚近的这40年,我也算是一个亲历者,西大是我的母校,而每每校友们弟子们归来,我又代表着他们的母校,以这样的身份来说西大,不可能不偏心不护短。记得2018年西北大学建校116周年庆典大会上,大学兄贾平凹有一段著名的发言,他说:“在我心中,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擀面擀得最好吃的,我的母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校。”这话说得很入心啊,不单因为是小说家会说话,更因为那是一种血缘亲情的触动,懂得感恩母爱的人一下子就意会和共鸣了这样的表达。无需过多解读,学子与母校之间,有这“一颗心”就足够。
西北大学校史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写起,光绪帝朱批开办陕西大学堂,成为西北大学创建的标志,也是高等教育在陕西乃至西北的发轫。其后几度沉寂,又几度兴起,终于在1939年以国立西北大学统冠陕、京两源,发展至今。中国高等教育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历史景深中走来,西北大学与百年社会动荡同波共振,有过领航西北的威名和荣耀,却也经历了更多的坎坷磨难。儿或不嫌母丑,却并不等于着我们会遮蔽历史的误区,掩饰时代的伤痕,高教历史恰是被身处高校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不断检视和省思着。我常想,西北大学正如一位饱经沧桑的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们来说,那久远的历史积淀和艰苦岁月中的人文坚守,或许还带着隐隐伤痛与悲情,却是一份更值得后代珍藏的宝贵财富。
因筹备120周年校庆的需要,我参与了文学院中文学科史的撰写工作,分给我执笔的历史时段是1949年至1977年,众所周知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实我自己也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段校史,但不能推辞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我已是目前在职教师中年龄离这段历史最近的人了。一切从头开始,翻阅资料,走访前辈老师,用了做学问的功夫。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学校颁发了《国立西北大学暂行组织规程草案》,重新规定校名为“国立西北大学”,1951年12月教育部通知,重新修正校名“西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自抗战时期高校西迁之后,新中国的西大又经历了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和1992年开始的高校合并,现代大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每一步,都在西北大学校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努力在1949至1977年的校史中寻找中文学科的发展脉络,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起步阶段应对高校各专业多次进行的分合拆制,愈来愈频繁的政治运动也在不断地干扰着高等教育的正常运转,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随着政策的起伏变化而呈现出时断时续的轨迹,尤其到1960年代中期以后,正常教学科研秩序遭到破坏,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这就更需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区间里寻幽探胜、披沙拣金。
所幸是金子总会发光。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侯外庐校长的感召下,西北大学一时间俊彦荟萃、名师云集。其中张西堂、傅庚生、郝御风、刘持生等教授,是西大乃至全国高校中文系名号颇响的人物,他们治学精湛、个性卓然,无论学术、师德还是文人风骨,都令后辈追慕不已,只可惜这样正常的学术岁月太短暂了。但即使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惨遭批判,先生们依然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坚守教育和学术阵地,据理自辩,不卑不亢,他们是校史中承载大学精神的典范,是最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标杆性学者。
翻阅史料的过程中,最令我无法释怀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67年。老教授傅庚生先生和老干部张宣先生被造反派批斗凌辱,“孟昭燕老师给学生们讲道理,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卧床数月”。孟昭燕是我的老师,我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后,她曾给我们上过中国现代戏剧文学专题课,记得她的讲义是一个发黄的小本子,不紧不慢地坐在讲桌前,标准的普通话里带着好听的京味。她讲《雷雨》中的人物,抑扬顿挫地念出台词时,一个美丽而幽怨的蘩漪形象就活在眼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孟老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经饰演过蘩漪一角,她是20世纪50年代北大毕业分配来西大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的夫人。于是,孟老师在同学们心中愈加神秘起来,回回上课都想抢坐在前排。我心中这样的孟老师,无法想象她当年竟遭如此厄运。一个年轻而文弱的女教师,能站出来保护老先生,在那样的严酷环境中是需要胆量的。我吃惊于孟老师竟然用“讲道理”来对待施暴者,静下来想,以孟老师的身份和性格,她会用那个时代流行的斗争方式来教育学生吗?当然不会。她只会用师者的苦口婆心,甚至是女性的温言软语,让孟老师挺身而出的或许不是我说的胆量,而是天性和教养。我看了中文系“新三届”为毕业30年编辑而成的纪念文集,加上我们自己的《八一集》,每一届回忆老师感念师恩的文章,都描述过孟老师当年的文学课堂,孟老师那咏诵话剧台词般的讲课声音,是如何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让他们几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我理解,这就是文学感性的力量,是艺术美感发生了作用,这美感在作品中,也在孟老师身上。孟老师2016年去世时,我正负责着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工作,记得是一大早坐校车赶去殡仪馆告别老师,站在孟老师灵前,脑子里盘旋的竟然还是老师上课的情景。斯人已去,声犹在耳,那一刻我悟到了,老师是以她独有的授课魅力,把她的文学教育雕刻在学生的心里了。
1981年我们这一级走进西北大学时,几位前辈大师如傅庚生、刘持生和单演义等先生年事已高,不再登台为本科生授课了。但我和我的同学依然非常幸运,遇上孟老师这样一批文学的启蒙老师。他们大都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学毕业,或留校或从外地分配来西大工作。在那个欢乐与痛苦交织的时代洪流中,他们经历了种种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革命的疾风暴雨确乎洗掉过知识分子曾经的傲岸和儒雅,而深藏于内心的,对知识的崇尚、对美的感应和对学问的敬畏,却如披在灵魂上的无形袈裟,未曾真的离去。一旦会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时,积压多年的学术热情喷薄而出,很快就迎来属于他们的学术黄金时代。我们八一级上大学时基本都是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前几级学长们相比,无论人生阅历、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都相差很远,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于是仰望讲台上的每一位老师,都有登堂入奥之感。给我们上过马列文论的刘秀兰老师每在校园和我见面聊天,总要提起我们八一级,说她最喜欢我们班了,上课时个个眼睛睁得圆溜溜的,求知欲特别强。这样的课堂想来特别能激发老师的授课激情,很自然地将正在进行中的学术研究,很鲜活地带到大学课堂上,不止于知识灌输,而是启发学生一起思考一起讨论。张华老师的“鲁迅思想研究”课第一次为我推开了鲁迅研究这扇厚重的大门,赵俊贤老师的“当代作家作品选讲”让我对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学现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我最早领受理论思辨的魅力,是在听了张孝评老师的“文学概论”之后。师生共处20世纪80年代文学复兴和学术回归的历史现场,当我们沉浸在获取知识和精神营养的巨大满足中,课余时间操场打球、宿舍弹唱、寒暑假游山玩水的时候,老师们正在废寝忘食点灯熬油,埋首于各自的学术研究。“科学的春天”来得有点晚,真正起步学术研究时已是人到中年,他们想抓住教学之外的一切时间,他们交出休闲,交出健康,甚至有老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有这一切,是当时年轻的我不曾意识的,其中的荣耀和牺牲、快乐和痛楚,更是我在经历多年求学,走上同样的工作岗位之后逐渐体味到的。后来我又反复阅读过老师们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术著作,看到“教与写”是如何互动生发,以及他们钻研学问的路径方法。想起鲁迅那句“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而我们是直接汲取了“牛奶”的精华成长起来的。对于这一代老师,他们的学术之路可谓悲壮,对于这一代学生,我们又是何其幸运和幸福。
学缘和血缘一样,讲究的是代际传递,学问更是世代积累方能大成。每一代人都会立足自身当下,回首“从哪里来”的历史,展望“到哪里去”的未来。西北大学走过120年而不衰,必有其薪火相传的“大学之魂”,或曰“西大精神”。通过校史的回顾不难发现,愈是处于民族危难社会动荡的关头,愈能看到西大人不畏艰辛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文化传承使命的秉力持守。1913年,为加强中日高等学校的交流,西北大学曾派学生赴日留学,当时“西北大学创始会”成员和第一任“文科学长”崔云松撰文送别,他回忆了西北大学建校经历的重重困难,特别慨叹学校“处于财政方面问题上的艰难缔造之历史”,而后告诫学生:“经此层层困难之阶段,始有此校之成立,始有诸君之就学,始有选派诸君出洋之盛举。然则吾陕之西北大学,苦学校也,经过之历史,苦历史也,诸君之入校肄业,苦学生也,此次之留学亦苦留学也。旅居之费,皆吾乡同胞之脂膏,不可以任意挥霍也。留学之目的为建设之预备,不可以畏难苟安也。”(崔云松《送西北大学学生留学东瀛序》)此后的西北大学似乎总是难逃“苦学校、苦历史、苦学生”的命运圈子,抗战期间西北联大在城固度过了八年艰苦岁月,1939年联大校长胡庶华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白开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西北联大校刊》第14期)即使是半饿着肚子,校舍极端简陋,老师讲课做学问依然兢兢业业,学生听课上自习一样刻苦用功。1949年天地翻覆,百废待兴,西北大学和共和国所有新生的高校一样,经历了国家经济从复苏到重整的艰难时日,1958年7月西北大学从“部属”变成“省属”,又极大地限制和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及至我们上学的1981年,第一次走进教室,那是什么样的大学教室,惊凉了所有同学的热切期待。班长刘卫平曾经在入校30年回忆文章中描写道:“它是三间毫无装饰的平房,屋顶苫着石棉瓦,外墙未涂白石灰,檐角甚多缝隙,屋内没有暖气设备。外面下大雨时,里墙也小有渗漏,外面下大雪时,里面也下小雪。”后来才得知,因为81级入学时,77级还有半年才毕业,五级同读,校舍根本不够用,只好临时增建和改建了一些简易教室,上课条件大概不比西北联大时期好多少。而且据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一级西大的所有专业都削减了招生人数,只招了计划中的一半新生,真是好险啊。同学聚会时常常说起这些,都感慨自己考入西大是多么幸运,而那间透风漏雨的“第六教室”,竟也成了大学美好记忆的一部分了。
时至今日,地处欠发达地区的西北大学,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学校整体上坚持保证教学科研的投入,我们的综合实力和很多方面还在领西北之风骚。所谓大学精神,具体在每个学人身上,就是具有不为外在环境所左右的文化定力,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还有自由包容的学术思想。回到20世纪80年代新思潮涌动的大学校园,西大经济系出了两个著名学生,一个是蔡大成,一个是张维迎。78级的蔡大成爱写小说,发表在中文系77级创办的《希望》杂志上。当时学生创办《希望》,西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郭琦先生给过很大的支持,不但拨发经费给他们,还放手让学生按自己的思路独立办刊。后来杂志出刊到第三期被有关部门强行叫停,蔡大成不服,竟主动提出退学以示抗议,又是郭校长再次出面力保学生,也使得当期刊物还能照常售卖。77级的张维迎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西大读研,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发热烈讨论,后来转化成带有政治意味的“批判”,在张维迎面临可能被中断学业的压力下,还是老校长郭琦力排众议,认为文章是“带学术性的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经过一番“检查”的周折后果断停止了这场讨论。最早听闻这两场“风波”的时候,低年级的我还懵懂无知,后来不断在各种史料和怀念文字中读到了郭琦校长,他在西北大学的开明作为和凌厉手段,对他治校能力、经验智慧和人格气度的口口传扬,渐渐在心中叠加成一座宏伟的人物雕像。大学校长通常是一个大学的对外形象,有校长的大气包容和临危担当,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触角才可能得到自由的伸展。北大蔡元培校长开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风气,中国一百多年来念兹在兹的大学精神,希望也能永远成为我们西北大学引以为傲的精神追求吧。
2000年以来,西北大学从桃园校区又扩展到西安南郊的长安校区,学校的建筑规模和校园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研究性大学的视野和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时光流转岁月更迭中,我的前辈师长也渐渐走入了生命的晚景,最近这两年,我们陆续失去了最亲近的几位业师,他们在告别校园时也告别了这个世界。我被悲伤刺痛着,反复醒觉生命的短促无常,不自觉中更多注目校园中的老先生们,用心捕捉他们身上的精神闪光,感受他们人格魅力。有一回在桃园校门外的理发店里,坐在我旁边椅子上的是90岁高龄的老校长张岂之先生,我听见他一直和年轻的理发师愉快地聊天,理发完毕后先走到收银台付了账,回头又拿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要给理发师,小伙子没想到还有小费,有点不知所措地推辞说不需要,先生说辛苦了坚持要给,我不由得也劝小伙子拿着拿着,理发师不好意思地收下了,张先生这才满意地又照照镜子里的发型,很精神地迈步出门了。我回家后把见到的情景讲给家人听,然后一整天沉浸在张先生带给我的特别温润的感动中。
另一位从桃园到长安校区经常见到的张先生是地质系的张国伟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我们西大的国宝级人物。张先生经常乘坐校门口的公交车出门办事,普通得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老头儿。搬到长安校区后,我和张先生住在了同一个单元门里,晚上散步经常遇到。今年年初西安遭遇疫情公寓楼被封,我被选举为本单元的单元长,负责疫情期间核酸人员统计和安排蔬菜食品发放,依然没有理由推脱,因为这回我好像是我们单元最年轻的在职教师。数学系的窦霁虹老师任楼长助理,我俩分工协作配合默契。老师们都非常体谅特殊时期的种种麻烦,特别是在逐户敲门调查人口的时候,都能在单元群里积极应答,协助我们很快完成了住户统计工作。重点要说的是张先生,因为年事已高不用微信,我就打印了纸质版让窦老师送上去,说好先填表格随后取回。大约半个小时候我们再去张先生家里取表格时,发现先生家的铁门虚掩着,先生一直等在家里,免了我们再次敲门。这看似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和窦老师还是被大大地感动了。名师大家中有风骨有个性者,多具备纯粹人格和高尚情操,既体现为他们一生做人的身正为范,也尽显于日常生活的小事细节中,这也未尝不是大学精神的另一种生动彰显。教育家们说得好,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常在校园看见老先生们的蹒跚背影,心里就觉得踏实,觉得有靠山,有和他们同在西北大学的那种自豪和骄傲。
记得前些年有一次也是校庆接待校友,当时的文学院院长、中文79级李浩学兄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当年毕业留校工作,慢慢就成了“看家护院”的人,我们在家就在,大家多回来。我也是学文学的,很容易就被感染到。一代又一代,我们也终于熬到了“看家护院”的辈分,而且随着年岁越大,爱家和护犊的情结就越发强烈起来。这一两年去长安校区上课时,过马路就看到停建很久的学术交流中心,还有几栋教学楼也都在等待经费,心中很不是滋味。知道西大依然是个穷学校,我们依然还在过苦日子,但作为一个西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同时还在西大教书育人的一名老师,至少我不能嫌她穷嫌她苦。况且,西大还是“公诚勤朴”的西大,是自由包容的西大,是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西大,是值得她的学子们为之守候和奋斗的西大。
西北大学即将迎来120周年华诞,时光不败,青春常在,祝母校120岁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