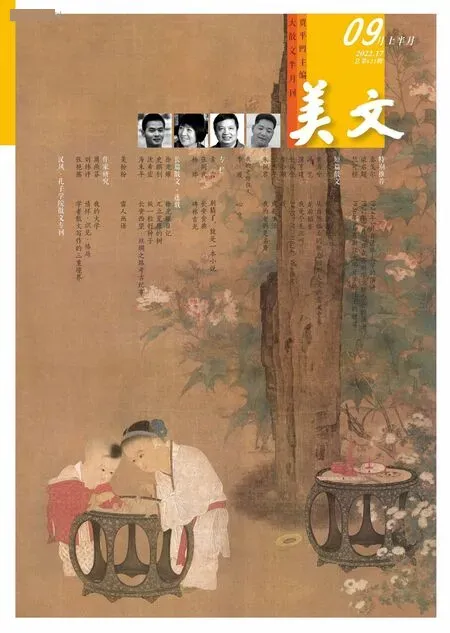34.15°N,118.14° W,往东
2022-10-20长从余
◎ 长从余
00:00
34.15°N,118.14°W
2:00 AM
已寄出
“夜里,浅梦,梦见一只白色长毛流浪猫。我在窄街上走,天空下着霏微的雨,它在后边儿尾随着。我把它抱起来,放到一处避雨的屋檐下。”
异乡的月亮正圆,低低地垂在晦黯的天幕上,纹理被雨水打得模糊了,像女人哭花了妆的面庞。冬日的鸣虫在叫,肝肠寸断地,想让十二月染上一丝四月的颜色。雨水会打穿它们的翅膀,令其飞不起来,孤零坠在泥土里。早生的虫子是一种悲哀——它们见不到春天。
Q很好奇加州冬夜的样子。于是,我在信中写了帕萨迪纳并不寒冷的气候。我还写了月亮下巨大的山脉、山脉上的雪、城市里的一场冰雹。
西海岸的一切都是大骨架的: 山、海、车子、房屋、公路,是与故乡相反的性格。我对它们的喜恨不相同:江南的雨是忧郁、西湖和红楼梦﹔ 而加州的阳光是一号公路和老鹰乐队。
Q是一个年龄同我相仿的姑娘。她在一座被群山环抱的盆地城市里上学。我在农历新年前的两三周收到她的信,彼时,她的寒假刚开始。
笔友是一种奇妙而纯粹的关系,通常来说,我们不会着急透露太多自己的故事。诸如住地、年龄一类具象的事物,在信纸上都是遮遮掩掩的,像是在打哑谜。Q比我更擅长隐藏这些讯息,她喜欢描摹一些生活里琐碎的事物——书封上的蛀痕,或是列车的窗户,以及不那么愉快的学校生活。
“一想到要开学,心里仿佛下了一场石头雨。”她在伊始的信中道,“兴许是初入大学还未适应,觉得身边的人优秀又努力,每日都在焦虑中度过。” Q是大一新生,对于陌生的环境,我俩有着相同的顾虑。
01:12
34.15°N,118.14°W
03:12 AM
“往家走了一段路,回头瞥了一眼猫儿。它踮着足跑过来,跳到我怀里。寅时,梦醒,冷风从窗格吹进来。”
白猫正站在窗台上。
“睡不着吗?”它开口道。
我点点头。
“随我走吧。”
“往哪儿去?”我问它。
“不晓得。” 它回道。缄默了一会儿,转过头去,“故乡。”
“独在异乡的孤独与乐趣还没有体味过,大抵与我的孤独不是来自一处。”Q在信中这样告诉我,“我所熟知的孤独,只是在一方小天地里与自身对话。如若揭开独处的壁障, 热闹喧哗中,不知道还能否守住本心。”
我不清楚该怎样宽慰她,这半年来,人在异域文化的洪流里多少是有些迷惘的。
我生命中的前十八年都是在象牙塔中度过,是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的。人到加州后,猝然间与社会有了交集。除开学业,生活上的琐事也需独自照料,租房、交水电费、银行开户、置办家具、保险、网络,着实令人应接不暇。这一年里,算是真正体味到维系一个小“家”的难处,方才明白父母的不容易。成年离家,少年时代何等向往过,可只有在某个陌生的十字路口找不到去向时,才晓得所谓自由,不过是自以为逃离长辈的束缚,殊不知社会已绕身绑上一捆枷锁。
02:00
33.23° N,118. 25° W
04:04 AM
“人是害怕黑夜的动物,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与猫正相反。人是害怕落单的动物,也是刻在骨子里的,与猫正相反。”
失眠的时候,脑内的事情辗转往复。愈想入睡,愈是不能够。唯有在无事可做的夜里,我会写信给B。
B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早婚生子,事业上不大顺利。学文科的人,早晚要面对理想与生活间的落差,满腔热血撞上现实,一桶水淋下来,只剩一地柴灰。幸运而有才华的成了作家学者,余下的人没有几条出路——教育行业,或者公务员。B 同我讲,公务员考试并不容易,今年考不上,便挣扎着过活一年。日复一日,何其的恼苦。
B想过靠文字维生。如今读书的人少,报亭关了,图书馆成了咖啡店。“文学在这片土地上眼见的荒芜了,有点像你笔下加州的山脉,广博、耸峙,却长不出几棵草。”
“古怪的故事、陌生的城市你还同我讲吗?”B有时会催促我回信。
“书信就如一片被秋风捋下的叶子,落到哪片泥土上都是我的幸运。你莫要担心,秋风起的时间不定,我不会无故断却音讯。”
03:16
33.23°N,118. 25°W
05:16 AM
“在洛杉矶城市的边缘,是林地与荒丘的起始点。猫在这些微妙的边界留下标志物——通常是一块光滑的、会在风中发出哨声的石头,或一条异色的小溪,淡淡的血红色,像一根脐带,拴着土地和她的孩童。”
“过来吗?”猫问我。
“有什么分别?” 我望着浅洼的溪水,挽起裤脚,双手提着鞋子。
“没区别。”猫道,“我们又不会在地界上树一堵墙,你进来便是进来了,不用担心被赶出去。”
“猫总是能找出两个地点间最隐秘的一条路。猫的路与人的路不是一种概念,它们的小径是排布于空间之外的精巧构造,像一条条蚁穴,构成一张庞大的网络。人若是不巧闯入这种结构,会很快发觉自己迷失了方向;跟着猫走,则会有意外收获。运气好的话,两个相距数千公里的城市,仅用几分钟就到达了。有时,则正相反。换句话讲,人的旅程是有目的性的,缩短与终点的距离是唯一的目标。而猫的旅程则是出发点的逃离,旅程的时间取决于一座城市逃跑的速度,因而,不能够用距离来衡量。”
过了河,我们往密林中走。
“现在,你是‘客人’了。”猫道。
“我本就是异乡人。”我笑道。
Q会同我聊一些国内的消息。在外地不到一年,我与故里的脉搏有了脱节,中秋不食月饼,春节未听见鞭炮声,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潜移默化地起了改变。
“你的城市下雪吗?” 我在信中问她。我喜欢脚踩在雪地里的触感,年初一场雪后,世界仿佛清静了许多。帕萨迪纳和上海的冬日皆是半调子的脾性,唯有回到外婆的住地方能常看见白色。
“成都是冬天下雨的城市。”Q回道,“昨夜,听见雪落屋脊的声音,早上起来,却只寻到一地潮湿。”她笔下的成都总是让我想起上海。同样的湿热的夏天。玻璃幕墙覆盖的高楼耸立在平原上,雾气从柏油路的裂隙蒸腾起来,慢悠悠地往天上飘,遮住了云彩。
成都和上海的市中心是一座迷雾中的森林,进去了,很难再出来。云层顶上的景致只要看见一次,就绝不会想落下去。从小地方去往大城市的年轻人很多,这在何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成都、上海,或是洛杉矶。求学、工作、毕业、结婚,到头来,大多数人只是用十年的生命,换城市骨架里的一根钢筋。
南方的平原城市多少有些相仿的眉目……像嘴碎的女人,总有着纤细的情绪。当然,对于那些只去过一两次的城市,认知是有偏差的。就像我对上海的记忆或许是武康路弄里的某一间咖啡馆,而游人却只记住了黄浦江和陆家嘴的水泥丛林。
04:09
31.23° N,121.47° E
10:09 PM
“走了许久,树木褪去,显露出一片开阔地。砂质的土壤在鞋底下发出细碎的摩擦声。平地上,长着一片片的荆芥草,月光散下来,反出浅淡幽蓝的光。风一吹动,高低起伏,好似静谧的海浪。荆芥海里总有星星点点的地方凹下去,走近看,发觉是一群猫儿慵懒地躺着。我从一旁经过,它们只是半睁开眼睛,头也不抬地一瞥,又转过身子睡去了,颇有点学生上课睡昏沉的样子。”
有一只猫生着棕墨相间的虎皮花纹,我认出那是只狸花,于是蹲下身子,想摸摸它的皮毛。
“躺着的猫都是白天活动的,莫要打搅它们。”白猫道。
“走慢点儿。”我说,“头有些昏。”
“是荆芥草的作用,走出去就不困了。”猫道。
“听你意思,这草药能够助眠?”我问道,“能否容我采些回去?“
“随意摘。不过,荆芥草并不安神,而是消磨记忆之物。过往的事情忘却了,也就不再辗转难眠。”
“那还是算了。”我回道。
“猫儿不怜惜过往吗?” 我问。
“猫与人这点很相像,太阳下待久了,容易忘记月色。”
B在疾驰的高铁上同我写信。过年她回趟老家,母亲再婚了。“这问题曾想过许多次,但事到临头,还是难以接受,甚至生出飘零之感,觉得此处再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无论生在何处,心安即是归处吧。” B在信末道。
“拍张合影吗?” 离开上海那日,母亲问我。
站在机场安检入口,手里提着大包小包。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映出三个人:我、母亲、父亲。父母早年离乡到上海打拼,我们在这里没什么亲戚。父亲讲,至今仍不喜欢上海,即使他大半辈子都给了这里。“无论到何时,这座海边的迷宫,都难称作家乡。”他叹道。
母亲这几年变了许多,长裙换成了羽绒夹克;卷曲的栗色长发,扎成了黑色杂霜的发髻。男人的老去并不是那么令人烦忧的,女人的衰老则要可怕许多。男人是树,即使黄了叶子,依旧枝干挺拔;女人是玉兰花,倘若提早绽放,香黯后少有人在意了。
脑海里曾预演过许多次离别的情形,我害怕母亲会哭,她若泫然地看着,我的步伐会变得沉重。真实的道别没有眼泪——比想象平静良多——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短暂的拥抱。父亲一直驻足望着我,远了,看不清,就扒着楼梯的扶手踮脚眺望。楼梯上还有许多与他年龄相仿的中年男人。行李沉重,我不愿回头太多次,不晓得他在那里站了多久。
05:20
29.99° N,120.59° E
11:20 PM
“我们从一条破落的小巷穿过去,昏黄的路灯闪个不停,把盘绕的蛾子隔成了画片,一帧一帧,忽暗忽明。周遭传来细碎的声响,似笔尖在信纸上摩挲。”
“那是夜晚的动物。”猫道。
一只野兽趴在老式公房的屋顶上,它紧随着我们,瓦片刷拉刷拉地震着,落下尘埃来。我有些畏惧,不由得加快脚步。
“慢点。” 猫在身后懒懒地叫道,“怕什么,你仔细瞧瞧。”
聚睛一瞧,才发觉那屋檐上的并非野兽,而是许多双豆大的瞳仁,颤抖地盯着我。
“莫非,它们惧怕我?”
“是的。” 猫道,“你非夜里常见的生物,体格又不小,它们瞧你陌生,难免提高防备。”
与笔友往来久了,会不禁通过文字揣测她们的样貌。这是一种自恋的行为。主观意识构建出的玫瑰,仅对自己芬芳,他者只能够触到刺。
Q和B都喜欢看汪曾祺的作品。我与她们在读书的喜好上不大契合,有时,我会自顾自地花上半封信的篇幅聊诗歌。Q和B总会尝试做出些回复,这是我的至幸。能够长久往来的笔友终究是少数,很蓦然的,某封信寄出后,就成了断线的风筝。
信写多了,大抵能分辨一时兴起的句子。写出满篇烦忧的人,等烦忧散了,便再没有下笔的理由。即使知晓难有音讯,我依旧会回复每一封信。人于低谷时,最想听的莫过一句陌生人的安慰话。
06:12
30.66° N,04.08° E
12:12 PM
“猫在一处学校的山墙停了下来。我们在此歇息片刻,天正要亮了。”
墙顶系了很多琉璃烧制的风铃。猫不语。我无事做,从墙头走到墙尾,手拂过铃铛。一个姑娘从院落深处的楼里探出身子道:“我还以为是起风了哩。”
“这些风铃很是可爱。”我同她讲。
“谢谢,这是我和朋友系上的。”
成都的疫情有反复,Q的大学封闭管理,不让随意出校门。人终日在三点一线中往复:宿舍、食堂、教学楼。女人的心思比男人来的细密,Q很是怜悯在疫情中受苦的人。“新闻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别人的父母或孩子。”她道。
最近总有想法:世上有人是不幸福的,身在苦难之外的人就更应当好好活着;苦中作乐也好,潜心读书也罢,绝不能辜负自己,亦不可辜负在意自己的人。人是很难共情的动物,糟心的事情离得再近,只要没有切身体会,难真正晓得其中苦痛。心里屡屡替别人惋惜了,可轮到自己做些小牺牲,嘴上又难免抱怨。
偶尔在新闻里瞧见受难的孩子 ,反观自己的幸运,油然生出负罪感来。
Q询问我加州疫情的状况。我告诉她,这边疫情自来时就已平缓。加州太阳狠毒,口罩戴久了,会在脸颊上留下一道分界线,往上的肤色会明显比鼻尖下的部分深一个色号。不少南方人来这儿后都落得一半奔放紫铜皮色,一半江南柔弱造作。远看去,好似宫崎骏电影里的狸猫。
“解封后你一定要去吃顿好的。”我同Q 说,“学业对身心是一种考验,可千万别亏待了胃。”
07:23
30.66° N,104.08° E
01:23 AM +1 DAY
姑娘戴着一顶宽檐的帽子。
“墙角那只白猫是你养的吗?”她问。
“不,猫没有主人。”我道。
“猫和人互相拥有彼此。”她说,“就像笔友一样。”
“我不在乎什么彼此。”猫道,“形单影只是猫的乐趣。”
“所以人不能够是猫。”我说。
Q喜欢在每封信的末尾附上一首曲子。她喜欢日语歌,有些年代的,平成初年的歌姬,是柔和且妩媚的调子。我也喜欢老歌,但说实在,对赏析毫无天赋。音乐唯一的作用只是陪伴我熬夜,是一个情人,我只在乎能从她那里得到什么,不大关心她的内在。
08:06
30.97° N,103.52° E
02:06 AM+1 DAY
“楼宇中传来一声鸟啼,而后,高处的群鸟逐渐骚动,扑羽鸣叫,盖过了姑娘说话的声音。猫正坐在地上舔舐毛发,闻此状,呲牙吼了一声。鸟群受惊,四散而去。”
猫道:“鸟是白天的动物,不怕人。”
远处的云层见亮。三月,桃花浸雨,压低了枝杈,伴着古祠堂的琉璃瓦,烧透了半边天。
“我要回房了。”姑娘道。
“不再留一会儿吗?”我问。
“太阳出来了就要看清你的脸哩。”姑娘回道,“祝你安好。”
“祝好。”
猫喵呜叫了一声。
“成都的早春是应当万分珍惜的,还来不及细细感受,她便溜掉了。”
Q在最近的一封信中告诉我,我才知晓成都已是入春。同大多数姑娘一样,Q喜欢赏花;见晴的日子,她会借口离开学校往郁金香田去。川蜀的城市与加州相比少了一丝造作,细密的古巷如毛细血管般在沉重的混凝土里延伸着,滋养了许多无心生出的地界: 一株古木、一片花田,一个弹琴的流浪人。她们是属于一个城市性格的烙印,悲悯的、模糊的过往记忆。成都古老的脉络里,如此规划之外的存在良多。人在其中,能够明晰地感知到时节之变化。
09:17
30.97° N,103.52° E
03:17 AM+1 DAY
“夜晚的猫群从夜色里跑出来,逆着黎明橘红色的云,往有树林的方向去,生怕灰白的毛发染上一丝色彩。锦色的毛团子从荆芥海里走出来,顺着阳光的方向,散开,渗透到城市的血管里。白天的猫接管了这座城。”
“你准备往哪儿去?”
“看心情。”白猫道,“我不同它们任何一群有交集。独来独往,很浪漫,不是吗?”
B准备考公务员。她讲,断断续续地考了近十年,人前已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内心却总犹犹豫豫地放不下,多少是有些不甘。人慢慢成熟了,会变得安于现状,往日的冲劲早已淡漠。
“你在异国求学,虽饱受议论,但选择了理想的专业,是一种幸运和勇气。”B同我说道,“我在十八线小城市工作,按部就班地过日子,消磨兴趣与欲望。也曾想过逃离,但回头看看房子孩子,顿时没了勇气。”
我在回信中同她讲了一个关于白色流浪猫的故事。
“故事里的白猫是你吗?”B问我,“兴许,也是我自己。”
10:31
30.99° N,104.20° E
04:31 AM+1 DAY
“我要回去了。”我说。
“不再坐一会儿吗?”猫问,“看完日出。”
“早上还有课,等太阳全出来,就该迟到了。”
“你可认识回去的路?”
“怎么不认得。”
猫很高兴,它从石凳上跳下来,翘着尾巴。
“你会再来找我的,是吗?”我问道。
“兴许吧。” 猫回道,“等你睡不着的时候。”
学期过半,Q逐渐适应了节奏。封校顶是无聊,烦闷时,她便循着小径跑步。“成都来了暖风,校园里一夜间开了许多花,乍暖还寒,还未来得及留下照片,便又都谢了。”Q抱怨道,“瞧着一地的残粉,稍有一丝感同,它们这般零落于泥土中,无人欣赏。这些天我罕有地体会到孤独,但并不自哀,反倒是学会了独处。我顶为自己骄傲的。”
成都周围的山脉,景致秀丽,草木葱郁。Q喜动,独爱从山顶上往下跑的一段路,风拂在脸颊上,大口呼吸林间的湿润,人存在于世的认知变得更加清晰了。同她相反,我的性格有些闷,并不常出门。听闻我饱受失眠的困扰,Q鼓动我抽空出去踏春。
“看春景一定是明智的选择,春日溜得快,莫要让她逃走了。”
11:45
30.99° N,104.20° E
05:45 AM +1 DAY
“猫向我道别,往山上走去。朝霞照向它的身子,毛色白得发亮。长毛猫是现实留不住的动物,它是属于未来的。”
12:00
30.57° N,104.07° E
06:00 AM+1 DAY
已送达
尾 声
车子驶上高速公路,风从半掩着的窗户吹了进来,夹杂着海、泥土和野鹿的气味。晌午的阳光很刺眼,照在远处San Gabriel山脉残存的雪上,反出银色的光晕。裸露的山脊上,有星星点点的绿。这里是常有山火的气候,故植被长不茂盛。我不觉得远处的山和近处的平原荒凉,它们像长滩上沐浴阳光的肌肤——是一种浅褐的、健康的颜色。
记得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有这样一段话: “不快乐的城市在每一秒钟都包藏着一个快乐的城市,只是它自己并不知道罢了。”
周日往南边的平原跑了一趟,是去交停车罚单。在这里缴交通罚款不是件容易事,人口稀疏,交管所离住处有近两个小时车程。我本是很抵触出这趟远门的,因为花费的时间都要从晚上的睡眠里抽﹔ 到头来却有些感激这张罚单,将我从繁重的学业里抽出来,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稍稍加深了油门,引擎的轰鸣盖过电台里的西语歌。人行得快,周遭的风景慢下来,身上沉重的东西仿佛被八十迈的车速甩掉了。
B公务员考罢,正忐忑地等着结果。清明,她回到乡下。“油菜花已然凋谢,长成一汪翠绿菜籽地。叫不出名字的鸟儿落在田埂上,一蹦一跳,消失在庄稼里。” 兴许是年龄之间的隔阂,我与她的交集愈发淡漠,信件往来的频率渐疏。
临近期末Q有些忙碌,许久没有回信了。她同我寄了一首木心的诗歌:
……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
昨夜突降细雨,淋淋漓漓落个不停,打在窗台上。恍惚间有了回到江南的错觉。在潮湿的梦里,又一次触到故乡。白猫在雨中静静地蹲着,水丝落在它细密毛发上,消瘦了轮廓。雨里,凉亭的瓦响得清脆,街角咖啡馆昏沉地晃着灯。雨顺着我的头顶滚下来,迷离了眼睛,恍惚中仿佛瞧见猫儿褪去皮毛,露出了人的模样。
早晨起来,雨已是落尽,出了太阳,云雾还暧昧着不肯消散。窗台上有一团白色的毛发,比指甲盖稍大些,像蒲公英的种子。
这些天我睡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