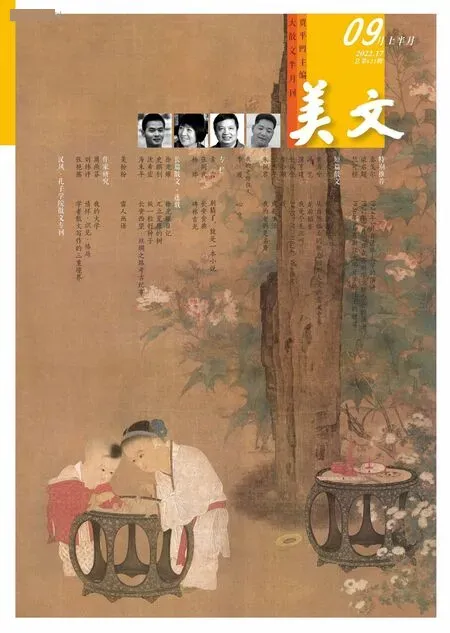我是个毛三叫
2022-10-20蒲亨建
◎ 蒲亨建
我是个毛三叫
毛三叫,重庆话,即毛手毛脚的意思。
我这辈子没有出过大事故,但小事故不断。要么砍骨头手一滑把手指头切破;要么干列检员(拿着榔头检查到站列车的走行部分)时爬列车上偷水果,被一声吼吓得掉在铁轨上,担伤了勒巴骨,一瘸一拐到公安处挨批,或从行进的列车上跳下来摔个狗啃泥(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都晓得,有一定技术难度,必须面向列车行进方向后仰着身体跳下来,顺着惯性小跑);要么干车工时被飞转的机头扬起的铁屑划伤……
幸好我通过七年的不懈挣扎,终于跳出“虎口”,干了最安全的工作——教书。之所以叫“虎口”,只是对我这个毛三叫而言。因为如果我不改行,大概率早已下岗或已经残废,我现在还经常从噩梦中惊醒。教书虽然也有“教学事故”,但这种事故伤的是心而不是身。比如我就被学生告过状,说我不会教乐理,原因是没按李重光的顺序来。院长找我谈话,问我为啥子这样教,把我搞得鬼火冒:说那你让告我的学生来教我吧,或者你来教我怎么教。当然院长不可能教我,就算是李重光,也只可能我教他,不可能他教我也。
今天到万家买肉,伸手去拿排骨,毛手毛脚地碰在了一把尖刀刃上,顿时鲜血淋漓,店员赶紧带我去服务台处理,双氧水、云南白药外加三块创可贴才把血止住。
根据我的观察经验,我发现一个真理:毛三叫不适合当工人,但适合干学术。
为啥子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干学术不会受伤,可以由着性子来。而由着性子来是毛三叫的强项。
反过来说,当工人必须小心翼翼,“安全第一”。但如果把这条规矩用在干学术上,就基本上可以肯定不会有啥出息。
所以我建议搞“名人访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您是个毛三叫吗?或者客气点儿问:你年轻的时候是个毛三叫吗?
如果名人的回答是:我不是,我这个人做事情非常小心,非常细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其他问题都不需要问了。
为啥子呢?
因为只凭他不是毛三叫这一点,就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没啥出息。
我干了最适合我的行当
这个世上的行当有万万千,我发现上帝对我特别、非常、尤其好,让我万里挑一,干了音乐研究这个行当。
我把音乐的后面加了研究二字,就是说光说音乐二字还不确切。为啥子呢?因为光说音乐二字,郎朗、朱践耳、宋祖英、帕瓦罗蒂都适合学音乐,不能说明我的独一无二之处。要说独一无二之处,叫郎朗适合学音乐中的钢琴,朱践耳适合学音乐中的作曲,宋祖英适合学音乐中的民族唱法,帕瓦罗蒂适合学音乐中的美声唱法。所以精确定位的话,我适合学音乐中的研究。
按这种横向的精确比较,我觉得只有老帕可以跟我相提并论。为啥子呢?因为只有老帕是公认的世界第一男高音,也只有我是公认的世界第一男音乐研究家(具体表现形式是默认)。而钢琴的郎朗水平、作曲的朱践耳水平、民族唱法的宋祖英水平,则可以抓出一大把,所以他们都不敢称第一。
我为啥子最适合干音乐研究这个行当呢?
首先,我有三项特别厉害的能力:一个是音乐感知力,这是学音乐这门大行当中的任何小行当都必须具备的能力;一个是想象力,这个能力在音乐这门大行当中的演奏、演唱小行当中的要求不太高,但在作曲与研究行当中,则要求特别高。作曲自不待言,没有想象力就根本不适合搞作曲,搞研究也一样,没有想象力,就没法产生厉害的观点。再一个是逻辑思维能力或理性分析能力,这项能力就基本上是搞音乐研究所需独具的能力了。
这三种力之合力的唯一指向,就是音乐研究。
为啥子呢?
因为学任何其他行当,都顶多只需要上面之一或之二力,或者外加什么其他力。
当然,音乐研究中也有不需要以上三种力的研究,比如某些“跨学科”研究就不需要音乐感知力;某些音乐史学研究就没有想象力;更多乱七八糟的研究就缺乏理性分析力。
至于某些在其他行当吃不开混进来冒充的音乐研究大咖,则更是三不沾,一项力都没有。
干大事儿要粗糙点儿
在淘宝买了个迷你小冰箱,328元。结果里面的灯不亮,联系客服,说是可以申请退货,但不上门取件,心想这么重的东西,我蒲大爷的人工费都不止买冰箱的钱,说那就算了,你退我点儿钱就行,客服说没这种退法,要么找个师傅上门儿看看。如果还是不亮恐怕也只有算了,只要能制冷就将就用。
老婆说叫你不用淘宝你不听,拼多多便宜得多,而且还上门取件。
在淘宝还买了个阳台塑料收纳柜,只看了宽与高的尺寸,结果深度不够,放不进去晾衣架,只能退货。好在那东西质量稀烂,既薄且软又轻,可以自己扛去菜鸟驿站。
上次说过,我干事儿一向粗心大意,菜刀割破切破手指头的事儿都发生过好几次,其他丢三落四的事情更是不计其数,旅游的时候还至少两次丢过老婆。
但我发现一个现象:粗枝大叶的人不一定能干大事,但能干大事的人一定是粗枝大叶的人。
我说的干大事的人,不是国内顶级科学研究大咖施一公之类的人。为啥子呢?因为我不认为在《自然》《细胞》等国际顶级刊物发文章的人就叫干大事的人。又为啥子呢?因为在这种刊物发文章的人都很细心,数据一个都不能错。而数据一个都不能错的人往往干不成大事。
真正能干大事的人,是老牛、老爱、老杨和我老蒲这号人。
这种人很少,几百年才出一个;而在《自然》《细胞》发文章的人每年都有很多个。干大事的人不能多,粗略算来至少一百年才出一个。
还有一种现象是:真正干大事的人,一辈子就干几件事,其他很多事都不愿意干。
比如我蒲大爷,现在就觉得没啥事情值得我干的了,具体表现为没啥论文可写了。
如果拿我跟老爱相比较,他的论文的数量比我少,所以他干的事情比我大。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我比他还厉害,厉害在哪里呢?他直到翘辫子都还有个“引力来源”的大问题没有解决,说明他还有事情要干;我呢?已经干到没有问题可解决了,因为关于音乐的大问题,我已经解决到底了。
我现在的烦恼是:我的智商还没有用完,就把音乐的大问题都解决了,剩余的智商不知道用来干啥。这说明音乐的大问题没有老爱的物理学问题大。
没有办法,我剩下的顶级智商只能用来写些文章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的全国倒数第一纪录
今天我的学术交流群有人夸我:大家只看到了蒲老师的成就,根本无法想象蒲老师背后没日没夜的付出。
我道:那倒没有没日没夜,我喜欢在电脑上打QQ游戏,拖拉机负分七十八万多,军棋负分六万多,排名全国倒数第一。
为啥子我的负分是全国倒数第一呢?因为我不止一次看见对手说:这种分数简直绝了,第一次见这么高的负分。
我有一个个人经验:如果一个人要在某个方面获得全国或世界第一,那么他就得在另一个方面获得全国或世界倒数第一。
大家晓得老牛与老爱是不同时期的世界第一,那么他俩有没有世界倒数第一的纪录呢?我想只有他俩自己知道。我跟他俩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我敢把自己的屁股亮给大家看。
我为啥子会有这么高的游戏负分呢?
这取决于两点:
一是我搞科研并非死磕,会找点儿爱好来调剂心情,其中一大爱好就是打游戏,而且花的时间还不少,一般都是睡前整上两小时,有时候白天也整(原来没有电脑的时候是打麻将)。
二是我很少下象棋,因为那玩意儿太费脑壳,一般只整上一两盘儿就转到拖拉机或者军棋,后者主要靠手气或运气。我通常见势不妙就逃跑,所以负分上升较快、越攒越多。
为啥子我要这么搞呢?这不叫耍赖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打牌下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获得愉快的心情,所以我充分领会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为啥子呢?因为明知打不赢还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了避免痛苦,就干脆跑掉,所以我从来没真正输过,几乎全都是赢,因而获得了美好的心情。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这既叫耍赖也不叫耍赖。又为啥子呢?因为我每跑一次,就会直接被扣十多分,对手也会涨十多分。根据游戏奖惩规则,我是有所付出的,对手也是有所回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不叫耍赖,对不?
我的明智之处在于:我跟绝大多数玩友的想法不同,他们为了那点游戏分死磕苦熬;我呢?觉得扣分再多也不是真金白银,咋扣都不心痛,换来的却是美丽的心情。甚至看到我的纪录,心情更是十分酸爽。
我的科研之所以能搞到全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经验之谈,兹隆重地把它推荐给大家。
学术文章中的外行写法
现在的学术文章中,有很多外行写法,不仅大量愣头青,甚至一些已经混成大腕儿的家伙也用这些外行写法来写文章,并发表在大刊物上。至于一般刊物,更是屡见不鲜,有些还用编辑部公众号隆重推出,让人产生各种不良反应:肉麻、喷饭;甩脑壳、拍桌子;笑掉大牙、昏昏欲睡……想不出词儿来了,学张振涛来点儿排比句(比他高明一点儿,不但是排比句,而且是等差数列结构)。
有哪些外行写法呢?
据我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如下几类。
一、狐假虎威的写法
这种外行写法就是用名人的观点来作为自己的观点的证据。这种写法的最大痛点或尿点就是没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要证明的就是名人已经说过的观点。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呢?就是用名人的观点本身来作出证明。这个证明的逻辑程序是: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所以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是一,所以是一。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一段式,比规定动作的逻辑三段式整整少了两段。比如某某大咖就说过这档子事儿啊,发表在啥子大刊物上啊,而且还写成了书,甚至还写进了工具书……可谓铁证如山,毋庸置喙。这种“证明”亦称“循环论证”的“自证”,即论证的前提就是论证的结论,因此又称为“先定结论”。
二、人多势众的写法
这种外行写法就是要证明一个观点,拉上一大帮子人抬轿子就行了。比如大名鼎鼎的某学者就用了这种写法,按他的说法是:支持他某一论述的大多数人的评价都很中肯,而反对他的人只有那么两三个,而且这两三个人的说法都很扯淡。
这种写法在不懂学术的人看来是很有效的,为啥子呢?因为不懂学术的人通常都占了大多数。但真正懂学术的人都懂得一个基本道理:学术研究跟打群架不是一码事。为啥子呢?因为打群架肯定是人多的一方赢,人少的一方输。但学术这玩意儿不是打群架,情况往往是反过来的:人多的一方往往是外行,真正的内行是很少的。
三、“政治”正确的写法
有些人写文章,喜欢套用高大上的东西来代替学术研究,一看标题就知是正确的废话。这种文章你千万别跟他商榷,一商榷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了。当然,这种文章中本就没有什么学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商榷。
四、热血沸腾的写法
这种写法是以情感代替理智,一上来就拍桌子打巴掌,或声泪俱下,或义愤填膺;要么喊口号,要么吟诗赋词;用语夸张溢美,无所不用其极。绝大多数傻里吧唧的读者往往会被他们的捶胸顿足、哭天喊地所打动,殊不知这种人纯属入错了行。为啥子呢?因为他们最适合的行当是去搞传销而非学术。
再写四种,合起来刚好凑够“八仙”。
五、行行都懂的写法
这种写法就是在文章中吹嘘其行行都懂,甚至行行都通。说起来写的是音乐学文章,里面社会学知识、人类学知识、民俗学知识、历史学知识等各种其他学科知识(一般来说没有理科知识)啥都有,就是没有音乐学知识。美其名曰:“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这种写法在当下的音乐学界尤其时髦、特别吃香。就我所见,搞这种写法的人大都(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音乐学知识的半瓶子醋,甚至根本就不懂音乐。为啥子呢?正因为他们肚子里的音乐知识空空,只能四处去讨饭来填肚子,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把文章写成了四不像。结果搞得不仅别的学科没入门儿,最后连自己的家门儿都找不着了。
当然其中也有个别懂点儿音乐的,比如某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就懂点儿音乐,还能搞点儿音乐的技术分析。但他觉得光搞音乐的单一分析法搞不深音乐,要用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法”才搞得深。其实他犯了个基本认识上的低级错误。一来他以为音乐的技术分析就是高级分析,不晓得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原理分析。比如物理学界的牛大爷与爱大爷、音乐学界的童大爷与蒲大爷,搞的就是单一分析而非综合分析,搞出来的东西可以惊掉于老爷的下巴。二来他不懂得一般来说,综合分析方法与单一分析方法之间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之所以叫“一般来说”,是我蒲大爷还有一种特殊认识:综合分析比单一分析臭得多,因为事实上所谓的综合分析都搞得很臭,他稍好而已;而童大爷与蒲大爷搞出来的东西,比他高了岂止几篾片。有兴趣可以参阅蒲大爷的《音乐的社会—历史、文化学分析深度观质疑——兼及对音乐本体分析深度观的重新认知》第二章。
六、一团糨糊的写法
刚才说了搞跨学科研究的人一般不会跨理科知识,实际上搞音乐学的人基本上都不懂理科知识。而缺乏理科知识的人写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脑壳不清醒,缺乏逻辑思维,把文章写成了一团糨糊。
我之所以不喜欢看音乐学的文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难看出其中的理路,东拉西扯不晓得在说啥。我即使要看,也只是偶尔瞅瞅大腕儿的文章,说明这个毛病是大腕级别的通病。
有些大家大夸特夸的人,写的文章就看得我打脑壳,眉毛胡子一把抓,让人脑壳发晕,不忍卒读。所以后来我只要一见是他们的名字,就直接略过,免得看出脑血栓。
七、跟风炒作的写法
这种写法通常是没有脑壳或马屁精的写法,比如香港的某位,脑袋一拍搞出来了个“音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都一片“音声”蛙鸣。为啥子呢?一来国内一大帮腕儿都到那里去混了个博士,回来一炒,必然产生蝴蝶效应。直到蒲大爷发表《“音声”之疑》后,才算暂时安静了一会儿。再如上音某个腕儿挖空心思搞出来了个“临响”,只见他的博士硕士个个都“临响”。至于外国佬搞出来的东西,啥子“隐喻”啊、“互文”啊都成了抢手货。我院某博导的硕士博士几乎届届都把鼻子凑在一块“互闻”。
八、和尚念经的写法
这也是音乐学界某些大腕儿的搞法。咋个搞的呢?就是把一个臭不可闻的“观点”或搞法没完没了地不断反刍,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重复发表。为啥子我称之为和尚念经呢?因为和尚每天都要做早晚功课,这个早晚功课就是念经,这个念的经每天都一样,永远不变。
我就在想了,为啥子这些大腕儿不能学学我蒲大爷,搞出点儿新玩意儿来呢?
我蒲大爷虽然也念经,比如关于商音、关于同均三宫等等等等,就念了多次,但每一次都能念出新东西,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每念的一次经,都能让人百看不厌。
这才是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