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文化交流视野下唐帝陵吐蕃石像生研究
2022-09-02万宇涵西藏民族大学
万宇涵 西藏民族大学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唐朝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唐王朝中原政权和周边多数少数民族政权均有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交往。而吐蕃王朝作为当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最为强盛者和唐政权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并且当时所留下的实物材料更是反映这段历史的直接载体。现将目光落在“吐蕃石像生”的身上,试图从唐蕃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研究关中地区的吐蕃石像生。
唐蕃之间文化交流
据史籍统计,从吐蕃首次派遣使者来到长安到两个王朝覆灭的前后二百多年里,双方往来使者的互动达到两百余次,唐与吐蕃之间的文化交往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最初,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在官方的推动下进行的,从松赞干布开始,吐蕃就派遣豪门贵族子弟前往长安学习诗书礼仪,在这一时期,不少吐蕃人不仅精通汉族诗书,还懂得汉族法律、国之朝纲,正所谓“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吐蕃人来到长安学习汉学的同时也将吐蕃文化带入了中原,如唐朝宫廷所喜好的马球活动,耳朵上佩戴“耳坠”以及西北一带汉人居住的平顶房屋,均是受吐蕃文化影响的结果。
不仅有吐蕃人来到长安,唐朝也派去吐蕃一批能工巧匠。吐蕃的手工业很大一部分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唐派往吐蕃的工匠教授给藏族人民“酿酒、制纸、冶金、建筑、制陶、缫丝”等相关技术,并培养出一批批吐蕃工匠,使得这些手工业得以在吐蕃发展起来。
同时,吐蕃王朝曾三次派遣使者来唐,请求在唐与吐蕃接壤之地互设市场。这些经济物资之间的交流活动对唐蕃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些交流交往促进了唐蕃之间的文化交融,并遗留下一批实物材料,其中吐蕃石像生较为特殊。吐蕃石像生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唐和吐蕃交流的史实,同时还能反映出唐蕃之间的相处模式、吐蕃来使的次数及人数、唐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态度等。笔者将在后文展开对吐蕃石像生身份探究、设立意义等方面内容的介绍。
唐帝陵吐蕃石像生
唐帝陵的吐蕃石像生是以吐蕃一族首领为题材的写实性石刻艺术。目前已经被确定身份的吐蕃石像生共有三座,分别是位于昭陵的吐蕃赞府松赞干布、位于乾陵的吐蕃大酋长赞婆和吐蕃使大论悉曩热,其他唐帝陵中的蕃酋像因未见衔名且保存较差还没能对其族属问题做出判断,故其是否存在吐蕃石像生尚未可知。以下介绍的三座吐蕃石像生的身份已经得到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的双重认证。
昭陵吐蕃赞府松赞干布
最早对昭陵设立蕃酋像进行记载的是唐代史学家封演,其在《封氏闻见记》“羊虎”条中写道:“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宋人所编《唐会要》中亦说:“山陵毕。上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
《旧唐书·吐蕃传》中明确记载将吐蕃赞府形象刻立于昭陵:“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册府元龟》中还说明了刻立吐蕃赞府像的原因:“高宗以贞观二十三年即位,拜吐蕃赞府(普)弄赞为驸马都尉,封海西郡王,弄赞因致书长孙无忌云:‘上初即位,若臣下有不臧之心者,请勒兵以赴之。’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以表其诚。于是进封宾王,赐杂彩三千段,乃刻其形象,列于昭陵玄阙之下”。后来宋元祐年间,游师雄曾对昭陵诸蕃酋像当时可见衔名进行了记录,整理成《昭陵六骏碑》,其后又被元代李好文收录到《长安志图》中,得以传世,这其中的记录亦有“吐蕃赞府”之名。此外,清人林侗所著《唐昭陵石迹考略》一书中对各个蕃酋像的位置都有所记录,还将吐蕃赞府记录为西侧第三人。然而,《唐昭陵石迹考略》所记石像位置未得到考古调查的证实。后来的考古调查结果表明,书中包括吐蕃赞府在内的多座蕃酋像在位置记录上存在谬误。
早在196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文教局组成的昭陵碑石调查组在昭陵进行调研时,就在昭陵祭坛发现了包括“吐蕃赞府”在内的四座蕃酋像座(如图)及部分石像的残躯和头块。1982年,昭陵博物馆在整理祭坛遗址时新发现三座蕃酋像座。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和清理工作,带铭刻的像座残块有20余块,连同以前所发现的铭刻石座已有13件,在本次发掘中还发现有蕃酋像的残头和残躯干,其服饰、佩饰、发型各不相同,面相亦各异:或高眉骨、深眼窝,或疏眉细眼、广额宽颊,还有的在背后拖有5根或7根发辫。这也证实了文献中所描述的:系“肖其形”而刻,与晚唐时期帝陵石人普遍采用模式化的造型具有明显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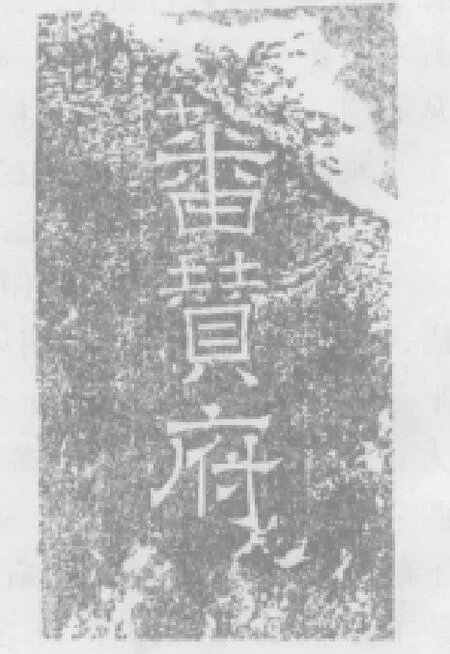
图 吐蕃赞府衔名拓本(作者自绘)
由于这些残块被发现时已不在原位,且破碎得较为严重,所以还不能根据这些石像残块判断出其身份,也不能得知昭陵吐蕃赞府石像的具体形象。但可以根据历次发掘结果获得的信息知晓包括吐蕃赞府在内的昭陵蕃酋像安置的具体形制。这些蕃酋像由人像和石座两部分组成,石座形制相同:近似正方体,长87—90厘米,宽85—90厘米,高50—57厘米,石座上部有一方形槽,人像双足下连接的小立方体能正好卡入石座方槽内,石刻的人像名刻于石座的正面,铭刻全部竖行排列,多为三四字一行。
乾陵吐蕃大酋长赞婆
最早对乾陵蕃酋像进行记录的是宋元祐年间游师雄,他曾命人将乾陵蕃酋像背刻衔名转刻在四座石碑上,并矗立于这些蕃酋像前,后经元李好文整理收录进《长安志图》中,其中便有“吐蕃大酋长赞婆”之名。清人叶奕苞在《金石录补》中称曾在友人处亲眼见过此衔名的原刻拓片:长二尺许,字阔二寸。
赞婆是吐蕃相禄东赞的第三子,和他的兄长钦陵共同治理吐蕃多年。《册府元龟》记载:“钦陵每多居中,诸弟分提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余年,尝为边患。其兄弟皆有才略,诸蕃惮之。”对于赞婆能够出现在乾陵蕃酋像之列的原因并没有文献直接说明,但在文献材料中有多处关于赞婆为唐蕃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的记载,例如《新唐书》中“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诛钦陵,而其弟赞婆等来降,因诏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往迎。授主客郎中”,在吐蕃政权内部拨乱动荡、互相猜忌之时,赞婆主动向唐表明归顺之意,促使唐和吐蕃实现和平,避免了战乱,为吐蕃人民带来了安定的生活,相信也正是赞婆在唐蕃关系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得其形象被刻立在了乾陵。
对乾陵蕃酋像的调查工作开展得较昭陵更多,且通过陕西省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乾陵残缺损毁的蕃酋像进行了修复,现将保存下来的六十一座蕃酋像重新竖立在乾陵。宋代游师雄所刻石人衔名辗转至今仅能得见三十六人之名,吐蕃大酋长赞婆之名出现在右二碑第十一人的位置,刘庆柱、李毓芳两位先生在对唐帝陵进行调查时曾对乾陵六十一蕃酋像的大小、保存情况进行了记录,但其编号与《长安志图》中的顺序不同,所以还不能将其确认为吐蕃大酋长赞婆像。
乾陵吐蕃使大论悉曩热
吐蕃使大论悉曩热在文献中亦被写作“悉薰然”“悉熏热”或“悉董热”,陈国灿先生认为,吐蕃官员中用“悉曩”为名者颇多,且“悉曩”的对音为“phyinan”,所以应该以此为正。
文献中关于悉曩热的内容较少,没有关于其具体事件的记载,多是在来唐使臣的名单中有所提及。例如,《旧唐书·吐蕃传》中有“俄而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曩热(悉薰然)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又如在《册府元龟》中,“吐蕃赞普遣其大臣悉曩热(悉董热)献方物”。由此可见,悉曩热是这一时期吐蕃来唐较为频繁且较为重要的使臣之一,并且在金城公主和亲这一事件上,使臣悉曩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知,对唐蕃之间友好交往关系的促进应是悉曩热形象被刻立在乾陵的原因。
吐蕃使大论悉曩热之衔名在游刻碑中位于右二碑第六位,同样的,由于不能确定游师雄所刻衔名是按照何种顺序排列,所以还不能与今天对乾陵蕃酋像的调查结果相结合,对于具体哪座蕃酋像为悉曩热还未可知。
此外,悉曩热这一人物的发现与研究为乾陵蕃酋像的设立时间及设立原因的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设立时间方面,随着唐乾陵蕃酋像衔名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现已将唐乾陵蕃酋像的设立时间界定在神龙元年(705)之后。现在的主要争议点就在于乾陵蕃酋像的设立时间是否晚于神龙三年(707),根据文献记载,悉曩热最早来到长安的时间是神龙三年(707),所以有学者据此推断乾陵蕃酋像的设立时间应是在神龙三年(707)之后;然而,问题在于此时距离武则天去世已经过去九个月,且其早已入葬于乾陵,不可能将她死后才来到长安的使臣像竖立于乾陵,所以另有学者认为悉曩热应早于神龙三年(707)就来过长安,只是缺失了文献记载。目前对于乾陵蕃酋像的具体设立时间还未达成共识,但晚于神龙元年(705)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在设立原因方面,在先前对乾陵蕃酋像设立原因的看法中,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被刻像于乾陵的蕃酋是前来参加高宗葬礼的吊唁者,或是和昭陵蕃酋像的刻立原因一样——曾侍轩禁者,然而包括乾陵吐蕃使大论悉曩热在内的三座乾陵蕃酋像衔名中带有“使”字,表明了其使臣的身份,促进了对乾陵蕃酋像设立原因准确性的认识。
唐帝陵吐蕃石像生的意义
唐帝陵中所放置的吐蕃石像生作为唐帝陵地面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石刻的艺术价值,同时,其也是唐与包括吐蕃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交往互通的真实写照。在昭陵和乾陵所设立的吐蕃石像生是当时吐蕃来唐使臣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而吐蕃来唐担任官职或与唐政权产生交集的吐蕃族人则更多,他们参与了唐朝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唐朝时期,吐蕃和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
吐蕃石像生的发现首先证实了吐蕃与唐交往紧密的真实性。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均能见到唐帝陵这三座蕃酋像人物原型的名字,他们都是和唐交往交流较为密切的吐蕃使臣,而且以汉族为中心的文献记载中也有他们的事迹。吐蕃石像生的发现证明在唐朝时期吐蕃和唐来往紧密确有其事,也证实了文献中所记录的吐蕃来唐使臣确有其人。这份实物材料也使得这段历史更加鲜活且真实。
其次,反映出周边少数民族和唐朝交流交往时的关系。在当时,虽然唐朝仍是汉族占据主要地位的统治政权,但是其疆域的管理是由多个民族共同参与的,唐王朝政权对周边各族统治者施行册封授爵、质子宿卫等政策,并且在边疆地区设立都督府和州交由少数民族官员来管理。然而,通过蕃酋像的设立及其衔名可知,让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管理并不是出于民族平等的理念,其依然是封建统治集团下的一种隶属关系,唐王朝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理,而蕃酋像就是这段历史的实物证据。此外,这三座被刻立在乾陵的吐蕃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为唐蕃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乾陵设蕃酋像的用意,即赞扬为唐蕃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作出贡献的人,表达了唐希望和吐蕃建立和平关系的愿望。
唐朝石刻艺术的一种形式。虽然根据今天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分辨出这些蕃酋像的族属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唐朝工匠对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的雕刻技术,卷曲的头发、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以及面部褶皱等各处细节都能够通过雕刻手法刻画出来。同时笔者也希望通过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能够将唐昭、乾二陵所发现的蕃酋像实物材料和其身份相互对应,以此对当时各个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特征形成更全面且真实的认识。
总之,吐蕃石像生是反映唐蕃交流历史的实物材料,它的发现将唐与吐蕃在历史中的这段关系真实化。此外,唐帝陵前属于吐蕃一族的三座蕃酋像在历史文献中均能得到考证。然而关于唐帝陵中的部分蕃酋像,我们并未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他们的生活痕迹。所以就目前而言,最终被刻立成像竖立在唐帝陵前成为这些蕃臣曾经生活在这段历史中所留下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