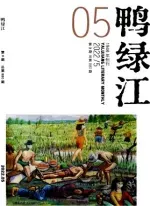吾师在民盟
2022-08-15张洪
张 洪
梨园行讲究多,有法无法,程式为法,“要投明师”的箴言,大家手摩心画。出身科班,传人纷纭,师承有序,林立的门派渊源有自,唱念做打,名不苟得,风头自然强劲。现如今高校归属和排名的浪头夺人眼球,亦步亦趋,争上游创一流,你方唱罢我登场,院系专业、教师弟子无不裹挟其中,名校名师名专业,求知报考升学,学生都晓得看大势论座次,以占先手并寄寓未来。
1983年高考成绩公布后,填报志愿只写了三所学校,想以财经、师范类学院打发了事,压根儿没瞄本省省城。彼一时,慨然称大的高校还未遍地开花。发榜结果出乎意料,没申请竟录取,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里把授课教师分成四级,藐予小子觉得新鲜。系内在职三位教授、二十几名副教授,私下议论时,闻所未闻“民主教授”一词,我得知教授高擎洲、副教授张毓茂先生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同一教研室共事。七年中,从本科时必修、选修课到研究生的专题班答辩会,聆听请益于两位前辈。教庭之外,他们作为东北地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五位理事之一,承担学术角色;又先后被选为民盟辽宁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由亲身所见所知发声行事,书生意气,义以为上。两位老师最称莫逆,经常互相打趣逗乐,开些善意的玩笑,抖抖包袱。高老师得知自己一位学生教授过毓茂师中学语文,笑呵呵不紧不慢地说,不小心你又小了一辈。张老师多年后告诉我,无论什么场合的会议,高师坐定后掏出烟卷儿,磕磕弹弹,淡定环顾,即知道上首诸位需要听什么,这发言该怎么开口收尾。孔子所谓侍于君子之三愆,陪同德位在上者坐谈,你这位导师从来不犯急躁、隐匿、盲目的毛病。反感徒具形式的慰老礼仪,不愿庙堂酬酢,不追时风荣光,高师志虑修己育人,不诽不谤,从无机心,不争不求不虑不思子女工作安排、家庭住房等琐事,个人档案、工资关系一直放在学校,将教书思考的乐趣保持了终生,心心所在,笃行不倦。执弟子礼的自己毕业走出校园,仍喜欢回师门求教,也呼朋唤友、携妻带子向老师表敬。更其经常的,是交流见闻,评说谈天,祝寿拜年,住院陪护,二十年里可谓师生一家,亲如父子了。
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名家,现代文学课堂内外的精彩片段,互为映照,我大学二年级上学期时即笃定了考研目标和方向。帝制结束到新中国成立间的三十多年文学,那阵儿全国专职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总共四千人。张老师为我们讲授百余人的年级大课,也指点三两弟子具体讨论,还邀请昔日师长、室友同窗出关来沈做讲座,使边疆学子有机会领略王瑶、费振刚、张炯、孙绍振等名师风采。王瑶先生所操山西平遥普通话难懂之极,印象深刻倒是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自得其乐的呵呵笑声,手托烟斗,一面讲一面笑,高频率“似喘似咳的笑”(女弟子赵园语),智者面目和气。孙绍振围绕其春风版《文学创作论》大谈陈陈相因之弊,批评界从南到北流行的名词犹如家家户户推门即见的大立柜。散文圈盛行的杨朔模式,他不愿附和,不敢苟同,不屑合流。出版社组稿人邓荫柯是作者当年的北大诗友,评价此书乃自成体系的一家之言。孙老师度量自己毫不留情,读了舒婷诗歌,再反观自身,中学时即萌发的作诗雅兴当即罢手,就此搁笔。孤傲的才气,谦退的智慧,当场闻见。理论与创作脱节,只说不练,传授写作课的人,哪怕写上一首儿歌让大家欣赏也行啊,毓茂师调侃起来与知交老友遥相呼应。王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学生们单一的思维,颇为怀疑其受教能力,“青年人在评论作品时有三多,一是爱国主义,二是人民性,三是局限性。”“反正学生总是对的,你只有检讨权,没有解释权,而且是越解释越糟糕。”僵化呆板的学习,缺陷畸形的传授,可想而知。知止知不足知束缚,高山前修吾不如,乃三省吾身之果。剖析自我,自欺自叛常常相伴,虚荣懒惰时时缠绕,尤其不能迷信自己,看来究竟我是谁,抛开自恋自怨何其难也。品评当年昵称“孙猴子”的大学同伴,谢冕称孙绍振是“一道奇美的风景”,张炯夸赞其为“绝顶聪明的才子”。毓茂师喜欢援引绍振好友对他的揶揄,“害怕别人咬了你的××”,嘻嘻哈哈的自嘲间,貌似刻薄的质问中,说难道易,刀刃向内,行己有耻,反躬自笑。绍振老师慧眼,东北挚友身上的幽默是草根式的,笑谈里有真言,笑谈间见至理。戏说中点拨着文学和人生的本来。
四十多年前,巴金主席屡次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沪上王晓明等学者呼吁重写文学史,高老师私下说道年轻时喜欢的芦焚等作家在出版物中难觅踪影,辽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开始了《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的酝酿与写作。课本里没写的,教材中回避的,讲坛上不宜深说、语焉不详的,在师生辩难发问间切榷往来。当时通行的三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分别由王瑶、李何林、唐弢三位前辈撰写主编。王先生由清华到北大,李先生先后在京津学府和北京鲁迅博物馆主持相关教研。唐先生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孤岛”创作时颇有“鲁迅风”,20世纪30年代末曾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文章修养》一书,八万多字十几个篇章,讲解文章妙处何在,援引古今域外作品,言约意丰。该书时文部分引录鲁迅著作十几处,名列亚军季军的同时代作家分别为巴金、芦焚。几十年来,现代与当代文学彼此张望逐渐合流。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明清、近现代和当代连贯一体,从17世纪一直写到21世纪初,溪流成了长河。现代现代,真是个妙语好词。
研究图书文献学的白化文先生尤为赞赏老师课堂内外一阵阵“神哨”,神聊海侃,看似野马脱缰,那才是别处听不来的思想火花的迸发呢,学养襟怀,听闲扯漫谈最为受益。语气神态、表情动作,敏感话题点到为止,兴会神交,教外别传,成为师生间最深层的默契记忆。遥想林风眠指导畏手畏脚的学生时笑眯眯地说“乱画嘛”,宗白华身体力行提醒弟子“放开胆子写,不要怕”,平视眼光,平常心态,平和面对消长进退,逐渐成为母校中国现代文学史区域“小气候”。海峡两岸对话中,一方不知张爱玲、林语堂,对方回避茅盾、郭沫若。我从1988年开始准备以张爱玲创作为题的硕士论文,由此系统浏览港台参考资料,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叩问于吴福辉、陈子善老师。宽容开放的高先生勇于讲解尚处禁区的作家作品,“俾作文立说者知所矜式”,章法在前,应知虚怀谦卑,南宋史学家洪迈所言极是。弟子们明白了真正的教育过程始终充满各种差异,理性追寻真谛真性,而真知总是碎片,不确定不完整的碎片往往折射着机制灵光。碎片不可化约,它们同样是经验是记忆是个性化的生存,容纳见证者参与者各种各样的人,允其发声,方能了然了悟。鼓励同事选题撰写评价胡风文艺思想的论文,为文化报事件中含冤饮恨的萧军大声疾呼,主编洋洋大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东北现代文学史论》,在文化土层稀薄的边疆大地深耕细耘,堪称毓茂师一行精彩得意之笔,黄钟大吕之声。张师1956年念北大中文系二年级时即登门拜访结识了作家萧军,进入新时期以来密切交往友谊弥深,拟编全集未成,为萧公撰写了几十万字的长篇传记。高师抗战期间辗转流亡,由鲁入川投考东北大学时,第一次读到《八月的乡村》,慷慨悲壮的内容使他警醒,摄人心魄的艺术令他振奋。两人同一年当选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可惜萧军因病未能赴会。1983年9月,高师张师作为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在辽西萧军家乡举办了200余人参加的庆祝萧军同志创作生涯五十年学术讨论会,高老师致开幕词并作大会总结,马加主席、毓茂老师等十几位代表大会发言,四五天的密集交流成为关外文坛盛事。八年后萧军去世,“学院派”两位代表又参与运筹主编了《萧军纪念集》。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捧读这本厚厚的大书,感慨“在延安出过事,后来在东北又闹过事”的老友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追怀文章也成了一本很有分量的书。贾先生弟子,同样执教复旦的郜元宝教授意味深长地道出了大家心声:中国现代是有那么一点儿文艺复兴和文化自由的气象,也确实出了不少人才。通人硕德成群结队而来,蔚为大观。
民盟中贤长云集,我是从高擎洲和张毓茂两位业师那里渐次了解的。高老师多次陪同费孝通主席来辽宁访问调研,“南有黄山,北有千山”,社会学家对北国景色大加褒扬。张老师后来兼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界别宿儒长者故事,经他绘声绘色转述给身边人。他称呼年长自己近十岁的丁石孙为校长而不是主席、副委员长,丁先生1984至1989年间出任北大校长,此前先后在清北二校讲授数学三十多年。在几次民盟高等教育研讨会和倡言科教兴国时,丁老反思过去缺点,教学计划订得太死。统一的教学计划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更不利于创新精神培养。强求统一并提出过高的标准,往往会把事情搞糟。我们要培养学生自己拿出主意来。晚年活动不便“不良于行”,自觉“有话可说”的丁校长,在学生辈部下京城就医时,坐着轮椅前往探望,执弟子礼的毓茂师感愧交加。知识分子是站立起来独立思考的人,季羡林引用德国哲人之言回首自身扭曲的经历。1944年由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秘书长介绍入盟的经济学家千家驹,从来言简意赅,不遮不掩,没有废话。天文学家叶叔华一片赤诚,高声激浊,直言疾呼。西南联大时由闻一多介绍入盟,王瑶与学生个别接触时愈加心存戒备,夸赞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导师桃李满天下,愧称自己只是一个“毛桃”。同门师兄孙毅、编辑前贤俞晓群介绍引见民盟中央宣传部笔锋劲健之士,吴志实、张冠生,亦师亦友、著述颇丰的大手笔让北疆出版获益良多,我又向费老侄子费皖、女婿张荣华组稿成书了《我的叔叔费孝通》《人文类型·乡土中国》两三部作品。
言传身教,亲炙私淑,不敢谬妄自许。其实,恭敬阅读应是最好的拜师与致谢。年轻时购买巴金《随想录》、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多年后再观费孝通对其评价,感触颇深。“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里,肯说真话,而且敢于把真话,怕口说无凭,用黑字印在纸上的实在不多。”“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我认识到他(梁先生)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费老85岁在南京师范大学座谈时即席发言,自问自答: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教育就是讲做人的道理,教人怎么做人。如何做先生?“修德而后可讲学”,身体力行恪尽厥责,笃学重教自为良师。为师、为学,大道何在?钱伟长撰文检点,切中流弊要害。
中国民主同盟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成立第一个省域地方组织,创办的《民主周刊》上刊载了众位先哲的扪心诘问和睿智作答,云南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推出合刊本,方便了集中浏览,撷其精华。盟中央委员兼省支部主委,云南大学教授、文史系主任楚图南1945年畅想战后教育,“教育是传递人类的生活经济,和寻求正确的知识,发现真理机关。而世界上的真理,只是一个。”李公朴读史有得,“吾辈追求真理,认识真理,抱着真理,为民族、人类服务,有什么疑惑呢?”“要使每个同学能做到自动、自学、自问的境界,我们以为要自动,学习兴趣才能持久而坚强,要自学才能学到踏实而需要的学问,要自问才能真正考试出学习的进展。”闻一多任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1946年发表《民盟的性质与作风》袒露心声,“这双拿了一辈子粉笔的手,是可以随时张开给你看的。你瞧,这雪白的一把粉笔灰,正是它的象征色……许许多多这样的手团结起来,它可以团结更多更多的手。”“平生最怕唁电稿,年来唁电偏不少。”东北民主爱国先驱高崇民,新中国成立后荣任民盟中央和全国政协副主席,1946年相继失去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位民主运动战友,悼诗中他声求气应,“李闻而后又一陶,青年学习失启导”“知君弥留有遗憾,前仆后继在我曹”。二十多年不写新诗的朱自清,奋笔疾书《挽一多先生》:“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他是一个斗士,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朱自清联合叶圣陶、吴晗等人共同编纂《闻一多全集》,“反动派消灭了他的肉体,咱们就得拥护他的精神永生”。同窗时从清华学校到异邦美国,再到国立青岛大学共执教鞭,老朋友梁实秋晚年满贮感情追忆闻一多,说道老同学留学时就执意不肯“向学术纪律低头”,宁可不获正式毕业资格,不听劝,不补修。虽然自称对他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一概不知”。闻一多的莫逆之交,一辈子“志于教读并将老于教读”的潘光旦,感喟“百事模糊松懈”的传统,培养完整的人饱满的人始终是其不坠之志,“教育一个人就得把人性的经纬诸端都教育到了,否则,结果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师从潘光旦近四十年的费孝通,感慨于良师的锦心绣口、高声疾呼,其通才教育主张厚重丰满,尽管与流行的专业受训、思想钳制背离相左,尽管为此受到排挤批判,仍初衷不改。
中国民主同盟先驱张澜先生1942年撰《四勉·一戒》之文自警自励,“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知恶去恶,好善行善,行与知,不可相违也。向真弃伪,告别造作炫耀虚夸,智者仁心,“无妄之谓诚”“人须是一个真”,如此境界与品格实在是教育的当行本色当务之急。“真,有它的本色,不用彩饰。”“美如果有真来添加光辉,它就会显得更美,更美多少倍。”莎士比亚的诗咏,中西契合。“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认可陶行知的箴言不难,付诸实施绝非易事。不然何有鲁迅对年轻人的呐喊:“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希圣希贤是好事,凡人真人更应然,时事维艰,教育尤难,千家驹1949年3月写就大作《假如陶行知还活着》,眺望新中国,“新中国是多么需要像行知先生这样一位人民教育家啊!”“行知先生将在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永远地活着。”真相真情,真实无妄,真学问,大见识,民盟先辈的理念与作为,值得我们永远对其报以全部的敬意。
吾生有幸,在向学心切的80年代,曾蒙贤长教泽,及门受业于尊师。“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荀子《劝学》,吾辈领教。“师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无功。”离开校门三十多年,白发门徒文字劳动接近尾声,回向先师嘉懿言行,追慕无已。懵懂茫然间,学,有所得知不足无所缺,近是疑非,寻思渐悟,学似春冰积不高。鲁钝愚顽后学如我也者,难窥夫子之墙,不能成其万一,景师德,报师恩,只有恒久感念师表前贤。道不远人,唯愿踏实地,勤补拙,言意合,言实契,躬身前行走出榛莽蛮荒,沿路掬心香一瓣,不忘救赎,不敢自满,为信为当,学而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