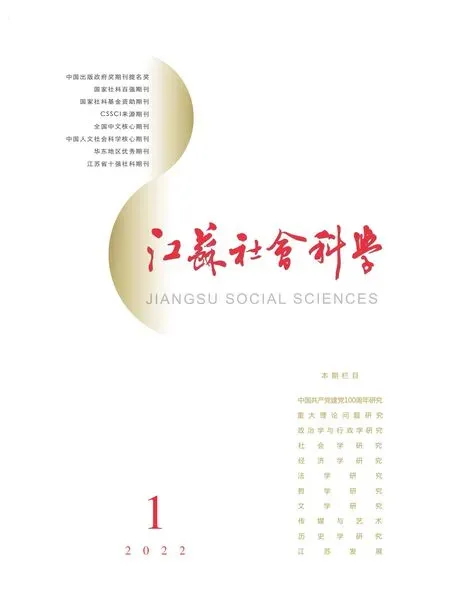被动担责与集体共谋: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的类型学考察
2022-08-05赵聚军张昊辰
赵聚军 张昊辰
内容提要 十八大以来掀起的问责风暴,已经由最初的党风廉政建设利器演变为政策执行的重要助推器。相应地,问责事件实际演化为个人和工作两种主要类型,前者主要契合党风廉政建设的初衷,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推动政策执行。基于对X县部分官员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问责事件的类型为依据,将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归纳为两类四种:针对个人问题的被动担责;针对工作问题的结构避责、私下合谋与理性避责。研究发现:针对个人问题的问责,通常只能被动担责;针对工作问题的问责,基层官员则会综合考虑问责主体和政治场域、问责事项与责任大小,以及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理性选择应对策略,集体共谋色彩浓厚。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续的高压问责直接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胜利,但作为政策执行工具,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职责同构和压力型体制所诱发的基层权责失衡,以及县域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构成了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生成的体制和社会根源。论文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基于扎实的田野证据,对常见的分析范式进行了证伪,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一、问题的提出
从古至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中国的基层官员在面临上级压力时的惯常选择,学术界则用“政策变通”描述这一行为[1]张翔:《基层政策执行的“共识式变通”:一个组织学解释——基于市场监管系统上下级互动过程的观察》,《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问责新政,不仅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利器,也在实践中逐步演变为政策执行的重要推动工具。面对汹涌澎湃的问责风暴,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也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变通”,乃至组织化倾向。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晋升锦标赛”“一票否决”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地方官员激励(约束)机制,均属于压力型体制的外在反映[1]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其中,“晋升锦标赛”作为正向激励手段,直接指向官员的晋升[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一票否决”则带有较强的负激励色彩,但也主要指向官员的晋升与评优[3]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随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全面发展观的强调,针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又开始表现出一定的“达标赛”和“末位淘汰赛”特点[4]袁方成、姜煜威:《“晋升锦标赛”依然有效?——以生态环境治理为讨论场域》,《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年第3期。,负向激励的色彩更加浓厚。然而,对于基层官员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上述范式似乎都难以对其行为特点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一方面,由于晋升“天花板”的存在,大多数基层官员无论工作多努力,实际的晋升空间都比较有限,这使得“晋升锦标赛”和“一票否决”难以适用于这一群体[5]王亚华:《中国用水户协会改革:政策执行视角的审视》,《管理世界》2013年第6期。;另一方面,“无过便是功”和事实上的终身任职,又使得当下流行的“达标赛”和“淘汰赛”范式也难以圆满地解释其行为特点。此外,现实中,基层官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仅仅因为一些“小事儿”就被严厉问责,但有些较大的责任却可以规避。那么,随着十八大以来的问责常态化和严厉化,基层官员是如何应对的?具体的应对策略存在哪些类型?影响因素有哪些?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从学理上更好地归纳现阶段官员激励机制的变化,也有利于理解当下政策执行机制的新变化。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1.文献回顾
问责制度与官员的避责行为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早期西方学界关于问责制度的研究多是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认知前设,集中于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和责任制政府等相对宏观的课题,希冀通过制度完善强化“政治”对“行政”的控制[6]Rod Hague and Martin Harop,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2004,p.160.。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关研究开始变得更加具体和细化。一方面,针对制度本身的研究依然受到关注,强调各级官僚要对作为委托人的民选政治家和全体公民负责[7]Neil McGrvey,“Accountabili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A Multi-Perspective Framework of Analysis”,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01,16(2),pp.17-29.。另一方面,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问责的重心也由政治责任层面转向绩效层面,代理人的身份从政府公共管理者转变为了“企业家”,传统的大众也被视为“顾客”或“消费者”[8]Anwar Shah,Performance Accountability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Washington D.C.: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7,p.21.。但是,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在理论上存在的缺陷和在实际改革中遇到的困境,相关研究随之进入后新公共管理阶段[9]Charles Conteh,“Transcending New Public Management: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ector Reforms”,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0,12(5),pp.751-754.,问责理论也随之更新,产生了“共享问责”“网络化问责”等新型问责模式[10]Carol Harlow and Richard Rawlings,“Promoting Accountability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A Network Approach”,European Law Journal,2007,13(4),pp.542-562.。
另一方面,随着问责制度与手段的不断革新,官员的避责策略也在不断变化,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概括而言,避责行为泛指官员为了逃避责任而采取的所有行动[1]Markus Hinterleitner and Fritz Sager,“Avoiding Blame—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and the Australian Home Insulation Program Fiasco”,Policy Studies Journal,2015,43(1),pp.139-161.。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避责行为属于正常的行为模式,其产生与科层制下的理性官僚人格密切相关[2]Barry Bozeman and Hal Griffin Rainey,“Organizational Rules and the‘Bureaucratic Personalit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8,42(1),pp.163-189.。关于避责策略,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其归纳为组织层面的“寻找替罪羊”、行为层面的“旋转摆脱困境”、政策层面的“不做争议判断”[3]Arjen Boin,et al,“Leadership Style,Crisis Response and Blame Management:The Case of Hurricane Katrina”,Public Administration,2010,88(3),pp.706-723,pp.706-723.。具体的避责行为则反映为限制议程、重新定义问题、互相推诿、随大流、顽抗到底、“帮我悬崖勒马”等[4]R.Kent Weaver,“The Politics of Blame Avoidance”,Journal of Public Policy,1986,6(4),pp.371-398.。而官员采用何种避责策略,则受到个人、制度、文化、情境等因素的交互影响[5]Raanan Sulitzeanu-Kenan,“If They Get It Right: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Effects of the Appointment and Reports of UK Public Inquiries”,Public Administration,2006,84(3),pp.623-653.。显然,普遍存在的官员避责行为会对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重大威胁[6]Donald P.Moynihan,“Extra-Network Organizational Reputation and Blame Avoidance in Networks:The Hurricane Katrina Example”,Governance,2012,25(4),pp.567-588.,弱化官员之间的相互信任[7]《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第85页。。
相比于国外关于避责政治的研究,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也形成了丰富的论述,研究者结合本土实践,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地方官员的行动趋向由邀功到避责的明显变化[8]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相关研究开始变得更为丰富。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官员避责行为的产生归纳出了三种常见的解释:一是环境论,认为社会、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共同塑造了官员的避责行为[9]谷志军:《问责政治的逻辑:在问责与避责之间》,《思想战线》2018年第6期。;二是理性选择论,认为避责行为是官员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10]陶鹏:《迟滞、分化及泛化:避责政治与风险规制体制形塑》,《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而十八大以来负向激励的强化则在客观上推动了理性避责行为的泛滥[11]郑永君:《属地责任制下的谋利型上访:生成机制与治理逻辑》,《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2期。;三是组织行为论,认为不同层级政府和官员之间的权责失衡状态,客观上重塑和放大了各类风险,并诱发避责行为[12]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将基层官员的避责策略归纳为机构性策略、表象性策略与政策性策略[13]谷志军、陈科霖:《责任政治中的问责与避责互动逻辑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6期。,具体手段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方式[14]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甚至连下级政府所立下的责任状[15]颜昌武、赖柳媚:《基层治理中的责任状:“督责令”还是“免责单”?》,《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2期。,乃至于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成为避责的方式[16]刘然:《政策失灵与避责机制——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责任悖论》,《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此外,在不同的政治场景中,还出现了府际联合避责[17]李晓飞:《行政发包制下的府际联合避责:生成、类型与防治》,《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0期。、下级向上级反向避责[18]邓大才:《反向避责:上位转嫁与逐层移责——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过程为分析对象》,《理论探讨》2020年第2期。等新型避责手段。当然,针对避责行为的治理,学界也提出了多种建设性对策:比如,注重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外部化,问责行为和问责过程的法律化和制度化[19]施雪华:《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效果乏力的病理分析与改革措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8期。;理顺权力关系、明确责任划分[20]张贤明:《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的问题与对策》,《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1期。;重塑问责文化、健全和强化异体问责机制[21]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中国监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等等。此外,有学者认为我国以执政党自身的变革推动责任政府建设,构建出了一套有助于发挥制度优势的问责体制[1]杨雪冬:《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府责任体制变革:一个总体性评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
综上,国内外学界关于问责制度和避责行为的研究已经颇为丰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国内研究而言,研究者多是在借鉴国外成熟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哪些因素会促进或者抑制避责行为的发生,本土化程度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问责事件本身的敏感性,使得已有研究普遍缺乏深入的田野调查,一手经验证据对研究的支撑稍显不足,并进一步导致对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的呈现不够全面和生动,“黑匣子”依然没有被完全打开。
2.研究设计
不同于官员完全因个人事项而引发的问责,因政策执行而产生的问责本质上属于一种集体行动,很多情况下存在上下级之间的互动和“默契”行为。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例如,有学者发现,在美国数任总统的任期内,都存在联邦内阁成员代替总统承受问责的现象[2]Richard J.Ellis,Presidential Lightning Rods:The Politics of Blame Avoidance,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4,p.88.。但需要明确的是,与西方情景不同,在压力型体制下,中国的每一级地方政府都与上级政府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基层官员不仅要承受公共舆论的压力,更要面对上级的考核与监督压力,此外还会受到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问责应对策略更为复杂、多变。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政策变通”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3]张翔:《基层政策执行的“共识式变通”:一个组织学解释——基于市场监管系统上下级互动过程的观察》,《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但并未将其拓展到官员面临问责压力时的应对策略的层面。鉴于此,以已有研究为起点,本文将从基层官员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本土化个案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尝试归纳和解释在当前问责常态化和严厉化的背景下,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之所以选取一个县作为案例,主要是考虑到县作为中国距离基层最近的完整建制单位,处于与基层官员接触的第一线:既不同于省级、地市级政府由于层级较多而隔断了与基层的直接联系,也区别于由于缺乏问责权力而无法全面呈现当下问责新常态的乡镇政府。
当然,不能否认,因为案例研究的样本数量通常较少,很难完全避免第三变量的可能影响。就本文而言,考虑所选案例仅为A省中部的一个县,很难做到理论抽样饱和。此外,我们作为外部观察者也很难做到全链条的追踪,因此只能尝试通过选择自变量极值的方式,尽可能克服第三变量的影响。具体来看,综合所掌握的一手资料以及问责风暴本身已经由最初的着眼于党风廉政建设演变为兼顾党风廉政建设与政策执行这一重要变化,我们发现针对基层官员的问责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即因个人问题产生的问责和因工作问题产生的问责:前者比较契合通过强化问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初衷;后者则更加契合当前问责主要被作为政策执行工具的现实。相应地,基层官员针对上述两类问责事件会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1:完全由于官员个人问题产生的问责,避责空间较小。这里所说的个人问题主要是指官员因个人的廉政、生活作风等问题,违反了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在当前的政治情景下,因个人问题产生的问责,一般很难避责,也很难产生集体行动。
假设2:在面对因工作问题产生的问责时,官员内部可能会出现集体行动,避责空间较大。由于政策执行通常由多个主体共同推动,面临问责压力时,相关主体有可能集体应对,减轻乃至抵制问责。
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通过半结构性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搜集一手经验证据。一方面,本文的两位作者曾于2019年7月—2020年5月,多次赴X县进行田野调查,先后深度访谈了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县委办、部分乡镇政府负责人及驻村干部等,共18人(包括曾经被问责的基层官员7人),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文中所列访谈记录的具编码规则为:工作单位+行政级别+访谈日期。官员行政级别的具体编码规则为:1为科员,2为股级干部,3为副科级干部,4为正科级干部,5为副处级干部。如果同一个单位有多位同级官员接受访谈,也会以数字加以区分。例如,X县纪委的股级干部为XJW-2,但如果有两位县纪委股级干部接受了访谈,为了区分,相应的编码就会变为XJW-21和XJW-22。。另一方面,本文的作者之一曾经于2019年7—8月,在X县行政执法局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工作实习。其间,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了解了该县实施问责的工作机制,成为访谈所获一手资料的有力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本文的访谈对象虽然不是很多,但基本涉及了X县与问责相关的县乡两级官员,既包括了多个被问责对象、多名纪委官员,也包括了诸如环保等问责高风险领域的官员;其次,本文所涉及的问责案例虽然不多,但却覆盖了“八项规定”实施以来X县出现的问责类型,代表性较强;最后,根据在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八项规定”实施以来X县出现的问责案例数量本身也不足以支撑起“大样本”的案例研究。

表1 访谈对象简况
三、X县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的类型学呈现
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制度供给与治理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都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推进模式,也决定着行政主体的行为选择。相较而言,X县基层官员面临的问责压力实际上是远超平均水平的。一方面,近年来中央对环境治理高度重视,在京津冀地区掀起了多轮次的环保风暴,给A省的各级政府造成了极大的问责压力。X县的支柱产业集中于高污染的羽绒业、制鞋业,这使得其各级官员在环保工作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近年来X县开始积极推动新区建设,虽然征迁任务沉重且极容易引起矛盾冲突,但由于上级制定了明确的征迁时间表,由此衍生出新的问责压力。在此背景下,X县的各级官员,尤其是一线基层官员,为了应对巨大的问责压力,逐渐衍生出多种类型的应对策略。联系本文的研究假设,本节内容将以引发问责的事件为官员的个人问题还是工作问题为基本依据,尝试将X县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划分为两类四种。
1.因个人问题引发的问责:被动担责
这里所说的被动担责是与主动担当相对而言的,具体是指在当前问责严厉化和常态化的宏观政策背景下,被问责的基层官员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从综合调研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在主要由官员个人问题被问责而引发的被动担责现象中,大致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责任较重且由上级纪检部门直接办理;二是因个人问题被现场发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问责的方式、体系与深度均通过新体制、新机制的形式被全面强化,典型如“巡视制度”“督查责任制”等手段的广泛使用,使得自上而下的渗透能力得以全面提升,而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也拓展了上级的信息汲取渠道。面对新形势,A省积极响应中央要求,全面加强了对地方干部的巡视督察,严查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并通过无人机巡视等高科技手段加强对干部日常行为的监察。
在此形势下,X县一名官员因在朋友家中聚餐被省委巡视组发现,县纪委当即对其进行了约谈,并迅速做出了处理意见并上报。最终,省委巡视组将此行为定性为“一桌餐”并给予这名官员党内警告处分。显然,这种被上级巡视组直接在现场发现并迅速查办的案例,由于证据确凿处理迅速,很难有机会进行协调或运作,只能被动担责。
这种直接被纪委部门抓在别人家中,也就只能认了。省委的巡视干部与我们并不熟悉,这种被抓在现场也没有别的办法,当天晚上就定性了,而且这也不是工作上的错误,是自己违反了党规党纪,也就只能接受上级的处分了,组织上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接受组织的决定。(访谈记录:XZF-520190928)
当然,上述案例也与当时正处于全国整治政治生态的风口浪尖有较大的关系。在这样的特殊政治场域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完成重要政治任务,这限制了地方在问责标准上的调适空间。而该官员被严厉问责的时间段,正处于A省全面贯彻“八项规定”精神,展开政治生态治理的关键时期。与上述案例的情景十分类似,X县另有一名官员在巡视期间被直接问责。
省委巡视期间发现一位干部违规为女儿操办婚宴,超出了申报的标准,并且违规收取同事和下属的礼金,被定性为严重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最终被党内严重警告。为自己女儿操办婚宴属于个人问题且较为严重,没有理由也很难把责任推脱出去,也不会有下属主动为他担责。(访谈记录:XZW-420200528)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上级直接实施的问责,在目标管理制下,上级对纪委处理违规违纪案件数目也有一定的要求。为了完成目标,纪委也需要尽职尽责,对每个问题严加落实。
我们也不想问责这么多人,看起来像是没事找事,但每年的问责数目都有一定的要求。很难想到这种(到)朋友家一起吃顿饭都能够被定性为“一桌餐”……不过这也只能认倒霉,谁叫现在需要抓几个典型呢?上级纪委也要完成任务。(访谈记录:XJW-2120191209)
此外,除了处理迅速、问责主体层级高,没有人情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也是导致上述两个官员被动担责的原因。由于问责由省委巡视组直接经办,巡视组与基层官员的联系较少,被问责官员很难施加影响,这与县级对下级的问责是存在明显不同的。
2.因工作问题引发的问责:结构避责、私下合谋与理性避责
(1)结构避责
这里所说的结构避责,是指地方领导干部时常会利用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在被问责时避免承担主要责任。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巡视督察,在常规治理情境下,问责的主体、方式与规模通常都是可控、可调适的。反映在实际案例中,除非发生社会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或者纯粹的个人违纪违法问题,一般很难对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直接问责。对于因工作问题引发的问责,主要领导干部通常最多承担轻微的领导责任,问责的主要对象往往是负责具体执行的基层官员。
在X县,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在推动某些工作时大都会采取“只能做不能说,更不能形成文件”的做法。在领导干部看来,这种做法已经是一种支持下级工作的态度,是在姿态上的默认或支持。但“态度”却是易变的,其最终解释权掌握在表态的领导干部手中;一旦发生“意外”,领导干部能够从容做出解释:“谁叫你们这样做的?我们下了这样的文件吗?”在此情境下,一旦政策执行中发生了“意外”或者未取得良好的效果,通常主要由一线的执行者担责。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旦态度形成了文件,就成为有字可证、有据可查的公开允许和支持,就可以对出现的“意外”进行定性——这是违规和非法的[1]欧阳静:《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以桔镇为研究对象》,《社会》2009年第5期。。总之,由于缺乏必要的文件和书面证明,在进行问责和考评时,虽然有时明知一项决策没有相关领导的默许是无法推行的,但由于没有直接和有力的证据,下级政府和一线干部很容易成为上级的替罪羊。
说到问责,我就拿环保领域举个例子吧。环保是目前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问责的压力也是经常有的,但是一般不会问责到主要领导。目前,环保局把乡镇划片,一个股级干部负责几个乡镇,但是一些不是很大的污染,他们也不会去查,根本查不过来。而当巡视组去巡视的时候,发现污染没有治理好,会直接找第一负责人也就是管片干部,出现问题了都是他们自己处理。而且由于不会出现很大的污染,那些股级干部最多会背一个党内警告。股级干部被党内警告,那领导的责任肯定不会大吧,最多有一个诫勉谈话。(访谈记录:XST-320191008)
另一方面,在严厉的问责态势下,县纪委为了完成目标任务,通常会关注扶贫、环保、征迁等容易出现“意外”的领域。但由于是县纪委主导问责,一旦涉及行政级别较高或实际权力较大的官员,问责往往难以有效实施,最后大多只能指向具体的基层执行人员,尤其是“没关系”的官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变相保护领导干部。
由于上面每年都有任务和政策,我们也必须要执行对吧。总不能说咱们县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怎么可能?上级也不会相信哪。虽然我们有时候知道这个是主要领导的问题,但也不可能去问责他们吧?这不是得罪人吗?而且有时候那些领导的级别比我都高,我们也就是发现问题后对主要执行人问责就可以了,尽量不把事态扩大化。(访谈记录:XJW-420191209)
综上,在责任相对较轻且由县级纪委主导调查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问责地方主要领导干部,比如科局、乡镇的一把手。这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要领导干部在事前已经做好了布局,将责任分散化;二是由于责任较轻微,一般干部也愿意替领导分担部分责任;三是此类问责主要是由县纪委实施,通常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
(2)私下合谋
这里说的私下合谋,是指部分基层官员在面临问责风险时,通过轮流担责的形式,将问责的风险分散,减小对被问责官员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基层官员尤其是负责具体执行的一线非领导干部,在日益强化的问责压力下已成为被问责的主要目标群体,他们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具体来看,除了对上级政策进行变通执行,他们也会在出现问责风险后相互沟通,避免出现被严重问责乃至撤职的情况。
从X县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基层官员因为工作原因被问责时,除非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通常只会被处以党内或政务警告等较为轻微的处分。和全国很多地方类似,在X县,基层乡镇干部的待遇较低且晋升空间有限,所以很多年轻干部都会积极寻求通过内部考调等方式离开乡镇。最后,无法离开乡镇的干部多是那些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老同志”。对于这些晋升空间十分有限的“老同志”而言,警告等轻微处分尚属可承受的范围。但在当下较强的问责压力下,有些基层官员甚至会在短期内面临多次被问责的风险。如果在警告期内再次被问责,相应的处分就可能升格为党内严重警告,乃至于撤职等严厉处分,这是基层官员难以承受的。也正是考虑到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在X县的问责案例中,除非是在特殊的政治场域,例如上级巡视组直接查办的案件,当县纪委作为问责主体时,轻易不会直接做出党内严重警告等可以深刻影响甚至摧毁官员职业生涯的处分。对于县纪委而言,既不能直接做出严厉的处分,又须有人担责,于是很多时候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私下合谋行为的发生。通常,作为问责事件第一责任人的基层官员如果处于处分期内,就会寻求其他没有背负处分的干部帮忙承担,领导干部也会居中协调。这种情况下,在县域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中,社会关系网络就会发挥“串联”和“润滑”作用。
虽然社会关系网络在合谋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如何运用关系,如何寻找“替代者”,也有一定的规律。首先,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一定会对直接负责的股级干部问责。但如果该股级干部已经背负了处分,就需要本人去寻找平常与其交好的相关工作人员作为“替代者”。甚至,为了方便责任的替换,在一些文件上,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相关官员不会直接被点名。其次,面临问责风险的干部无法找到熟人帮忙担责时,通常就会把目光投向一些关系相对较远的同事,这种情况有时需要领导居中协调。最后,如果被问责的官员是外乡人或在本地没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即使可能面对撤职等严重的处分,通常也只能自己去承担。这既是在县域社会中人情因素重要性的直接反映,也是对外乡人进行社会排斥的间接体现。
在环保、扶贫领域,这种帮忙顶替的事情是比较多的。那上面下来查一个项目,总不能说没有问题吧,只能说责任的大或小,以及相关负责人是否把这个事情把握得很好。比如说我现在包的一个村又出现了问题,而我已经被处分过了,再给处分就要被免职(撤职)了。但是(我)和领导还有纪委的关系都不错,纪委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就只能换另一个人帮我承担。首先,我会找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帮忙顶一下,我们又不是年轻人,都没有什么再往上爬的欲望了。如果实在不行呢,就再找领导帮忙协调一下。当然一般大家都会帮忙的,毕竟你帮了我,那下次我还会帮你嘛,而且关系也还不错。(访谈记录:XHB-2220191209)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很少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出现问责风险后总是会有人主动帮忙承担。比如,为了不耽误背景深厚的年轻人晋升,或者是卖上级领导一个人情,就出现了主动帮助某些基层官员承担责任的情况。例如,在X县的定点扶贫工作中,碰巧某位年轻官员在纪委检查时无故离岗。这种情况一定是要处理的,但也不能让一位有一定社会背景、职业发展前景良好的年轻人背负处分,于是相关领导就会私下协调,希望有年纪较大、晋升空间不大的官员帮忙承担一些责任,事后再给予顶替者一些其他方面的补偿。
我也帮某个领导的孩子担过一个处分呢。有一回他在驻村的时候迟到了,那孩子年轻,才刚参加工作,这样弄一个处分那以后就很难再升上去了。那我正好卖领导一个面子,反正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有太大的晋升空间了,耽误一两年影响也不是很大。后来年末评比,我们组得了一个优秀,我这个处分也正好就消除了。(访谈记录:XZFJ-320200106)
(3)理性避责
理性避责在这里是指官员通过提前布局,逃离问责的重灾区,避免被问责。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一些年纪较大、晋升希望渺茫的基层官员身上。一方面,对于这些沉积在乡镇基层的“老同志”而言,即使工作十分努力,但受自身年龄和学历、基层晋升“天花板”等内外部条件的制约,绝大多数也都很难进一步晋升。另一方面,基层官员只要不背负严厉的处分,基本不会被撤职或开除。这就导致通过逃避工作责任避免被问责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尤其是在当下问责常态化和严厉化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在部分基层“老同志”眼中,主动“做事儿”,通常只不过有可能获得领导的口头表扬等非实质性回报,但却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势必增加被问责的风险。在此情境下,一些身在乡镇基层的“老同志”就会通过逃避“风险较大”的工作任务,或是逃离问责的重灾区,甚至主动请求到“清水衙门”工作等形式,降低问责风险,上级领导通常也会予以理解和配合。比如X县一名在乡镇工作的科级干部,因为所负责的村庄出现了工作失误而被问责,事后很快就主动申请调动,最终平级调动到了工作任务较轻、工作难度较小的乡镇。
我这么大年纪了,再想升也不可能了,而且我这个副的又不是一把手,别人能给我什么好处?还要担那么大的责任。万一哪天出现事情了,我不是又要被问责、追责?我现在挣这点工资也就够了,也不想做出成绩了,就老老实实等退休就好了。我要是没有这么多年的党性修养,我也早想辞职不干了,或者去个政协人大。(访谈记录:XQT-320200106)
总结来看,就X县的整体情况而言,理性避责源于相当部分年龄较大的基层官员的普遍境遇:基层权力小而责任大,即使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受年龄、学历等因素的制约,通常也很难获得晋升。在此情境下,他们会从自身的利弊得失出发,做出理性的选择——逃避。具体的做法主要有两类:一是不负责某项具体的工作或区域,由于不是直接责任人,就无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主动申请调离问责风险较大的区域,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已经被问责后。而上级领导的配合,则反映出理性避责也是一种变相的集体共谋行为。
综合对两类四种问责应对策略的梳理,本文以问责事项(个人问题或工作问题)作为主要变量关系,以问责主体、责任大小、政治场域,以及官员的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发展前景等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大体上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即由廉政、个人作风等个人问题引发的问责,缺乏集体合谋的空间,很难避责。这也说明,十八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政治生态得以明显好转。
同时,论文同样也证明:由工作问题产生的问责有可能导致集体共谋行为,避责空间较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持续的高压问责推动政策执行,并未完全取得预期效果。当然,上述判断也非绝对:从X县的实际情况来看,问责主体、责任大小等外部因素,以及被问责人员的行政级别、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发展前景等内部因素,都会对避责空间的大小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在外部诸因素中,当问责主体为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时,避责空间相对较小,如果是县级纪检机关负责实施,相应的避责空间则会扩大;责任大小则可以被视为问责主体因素的调节变量。内部诸因素中,在控制了外部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常被问责官员的行政级别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越发达、职业发展前景越光明,相应的避责空间就越大。
此外,也不能忽视政治场域的影响。通常,在常规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官员灵活应对的空间相对较大,更有可能出现上下、左右“勾兑”等集体合谋现象。但在一些特殊的政治场域,尤其是为了完成某项重要政治任务而展开的运动式治理中,由于问责的主体判定、标准适用、具体手段等均遵循高效率、严把关等基本原则,地方的调适空间就会被大大压缩,应对灵活性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更有可能出现被动担责现象。
四、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生成的结构逻辑
参照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基层官员的问责应对策略大体上可以归到行动者逻辑的分析范畴。从结构逻辑与行动者逻辑的交互影响来看,结构逻辑不仅对行动者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因此,通过进一步梳理问责主体与政治场域,问责事项与责任大小,问责对象的行政级别、社会关系网络与职业发展前景等较为表层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可以发现在行动者逻辑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结构逻辑。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基层官员相对“灵活”的应对策略主要存在于由工作问题产生的问责事件,实际聚焦于政策执行问题,因此本节的分析也主要围绕因工作问题产生的问责展开。
1.职责同构与压力型体制夹缝下的基层权责失衡
职责同构模式作为解释当代中国纵向府际关系的一个代表性分析框架,基本内涵是指各级政府在职责配置和机构设置方面的高度相似,即所谓“上下对口,左右对齐”[1]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通常认为,职责同构模式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纵向府际权责配置难以被清晰地界定,以至于被认为是当下上级政府不断“甩锅”、基层权责严重失衡的重要体制性根源之一。例如在X县的环境治理中,由于局面错综复杂,项目审批权事关重大,但上级政府却把大量的相关审批权划拨给了X县政府,这就使得X县既面临着上级的问责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块块”部门简政放权、加快审批的压力,最终导致了“上级动动嘴,下级跑断腿”的格局。
我们县的私营企业比较多,经济相对发达。但是在之前,什么比较重要的项目,都轮不到咱们去审批。现在简政放权了,(上边就把)很多难以审核、检测的(项目)都分给了咱们,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但是,现在这些项目容易出事啊,那出事了就找第一责任人,也就是审批人。那上级不批,推给咱们,咱们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被问责就认倒霉了。(访谈记录:XZF-320200212)
当然,基层权责失衡问题的不断积累,也离不开另一个体制性现象的“助攻”:如果说职责同构为自上而下的“甩锅”行为创造了可能,那么长期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以及与之相伴而行的目标责任制[2]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则成为向下输出问责事项和压力的主要载体。在职责同构和压力型体制的夹缝下,除了基层,各级政府实际都已经蜕变为“管政府的政府”,待层层加码后的工作指标最终下达到基层时,往往已经是令人难以承受。另外,在近年来的改革实践中,一些地方虽然打着“做实基层”的旗号,但往往仅仅是输出工作任务,相应的执行资源和执法权力却不会同步下放。面对很多工作有责无权的现实格局,基层官员很难做到万无一失;但上级督导组却常会对基层的工作进行面面俱到的检查,只要发现工作出现一点疏漏就会立即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表面上看起来是上级的管理更加严格了,但更多时候实际上只是增加了基层的压力。但不推动工作又会被扣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作为的帽子。
你看看这个局里上上下下哪个没有担过责任?只要干事情就一定要做好被问责的准备。很多事情不是不想查得严,有的是根本查不过来,有的富一些的乡镇上百家企业,划给一个股几个人和环保所包片,(他们)根本是能力不够啊;而且再加上企业的排污方法、手段,层出不穷,不断更新,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力不从心啊。(访谈记录:XHB-220200106)
2.县域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
地域空间有限的县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在一个县的权力架构之中,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其他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本地人。而在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中工作生活的官员由于共同的交际圈、共同的经历和生活模式,且相互之间常常通过血缘、地缘、联姻等方式加深联系,从而在县域的官场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资本、较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以及附着在其上的非正式规则。在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下,县域几乎的每一位官员都处于人情网之中,从而为多样化问责应对策略的生成提供了土壤。而且,受制于人情、关系等非正式规则,如果被帮助的一方不做出相应的回应,就会遭受道德上的谴责,承受人力资本的损耗,这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中是十分致命的。
在一个县城,一个单位生活、工作了这么多年,谁也得有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吧?大家平时关系都不错,等到了(问责的)事情上,大家都会帮个忙的,毕竟事情并不是很大,而且我们对于晋升也没有那么多的渴望了。(访谈记录:XDW-3120191116)
另外,县域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也给县纪委的正常履职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由于包括纪委干部在内的每一个官员都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人情、关系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此情境下,在县纪委主导的案件中,一般不会对相关的责任人查处得太过严厉,否则就可能违背了整个县域社会的潜规则,办案人员将面临极大的社会压力,甚至受到其他成员的排挤。而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县乡领导干部共同的习性和团体精神比内部冲突和狭隘观念要重要得多,制度环境使得县乡领导必须进行战略性合作或合谋”[1]〔德〕托马斯·海贝勒、舒耕德、刘承礼:《作为战略性群体的县乡干部(上)——透视中国地方政府战略能动性的一种新方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综合前文的分析过程,以X县为案例,本文尝试归纳出了在问责日趋常态化和严厉化的背景下,基层官员应对策略的生成逻辑(见图1)。

图1 基层官员问责应对策略的生成逻辑
五、结论与讨论
联系前文的分析,国内学界目前主要是在借鉴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环境论、理性选择论、组织行为论三个层面分析官员避责行为的产生,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大致印证了上述理论范式。首先,十八大以来问责的常态化与严厉化显然是催生“被动担当”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而县域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和特殊的官场文化亦是滋生“集体合谋”行为的温床;其次,官员通过逃离问责重灾区等形式,避免被问责,显然是理性选择论的生动写照;最后,职责同构与压力型体制夹缝下的基层权责失衡成为基层被问责泛滥的体制原因,说明组织行为论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由于很多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某个特定的范式对避责行为展开单向度的分析,且缺乏深入的田野调查,实际上都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提出的相应治理策略普遍也不够周全。本文的研究工作,显然有助于推动上述分析范式的本土化进程,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目前学界普遍将“问责-避责”视为一种理性的应激反应[2]Gao Jie,"Pernicious Manipulation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China's Cadre Evaluation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2015,223,pp.618-637.,但本文的研究却发现:基层官员的问责应对策略,既有可能是个体行为,也有可能是集体行为。其中,针对因个人问题产生的问责,在汹涌澎湃的问责风暴之下,多数基层官员只能被动担责,很难“理性避责”。通常,应对因工作问题产生的问责时,会有一定的避责空间:避责行为既可能是被动担责等个体行为,更可能是结构避责、私下合谋等典型的集体共谋行为,以及带有一定集体共谋色彩的理性避责。
第二,部分研究者认为自上而下不断增加的问责压力,客观上有利于强化政策执行效果,约束官员行为[1]陈家喜:《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然而,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基层官员应对问责压力的集体共谋行为主要围绕因工作问题而产生的问责事件展开,表明单方面提升问责力度无益于问题的长效解决。职责同构模式和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权责配置的严重失衡,才是诱发基层官员多样化应对策略,进而导致问责有效性被不断消解的主要体制根源。
第三,进一步来看,如果明确界定了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是否就可以有效避免避责行为的蔓延?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已有研究对中国职责体系的考察,多是从科层制合理化的视角切入的[2]周振超:《打破职责同构:条块关系变革的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9期。,较少考虑责任配置的问题。因为在科层制下,权责是统一的,但中国政府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科层制政府,纵向“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和新近的强化,使得权责始终存在严重的分离[3]张翔:《“行政共同体”:对城市政府结构化过程的一种解释》,《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这就要求充分考虑权责匹配,既要“下责”也要“放权”,追求确权与确责的平衡[4]赵聚军、王智睿:《职责同构视角下运动式环境治理常规化的形成与转型——以S市大气污染防治为案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1期。。
虽然体制和社会文化层面的革新艰巨而复杂,但这并不妨碍运用必要的机制手段来缓解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蔓延。首先,可以通过平衡问责与容错,允许干部在适当的范围内犯错,以激发其活力和积极性[5]宁烨、霍日雯、邰慧宇:《跨文化情境下组织“试错学习”对组织结构变革的影响研究》,《公司治理评论》2012年第2期。。这就要求科学设计容错机制,明确免责条款的适用对象和行为。目前来看,科学设计容错机制一方面需着力扭转以结果论英雄的问责导向,提倡“决策—过程—结果”式的三方检验。另一方面,应逐步扭转过度依赖负向激励的考核机制。关于此,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央已经开始高度重视:2019年颁布实施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都强调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这对于健全激励机制,拓宽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干部的职业发展空间,调动其工作积极性,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部分地方在保持高压问责的同时,加强破格提拔等正面激励手段的运用,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成为推动抗疫走向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其次,除了职务和职级双梯制晋升带来的正向激励效应,基于科学绩效考核的物质激励,也有助于对冲当前对于负向激励的过度依赖。最后,对于在县域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场域下衍生的特殊官场文化,其重塑过程甚至要比体制的革新更为复杂和漫长。当然,也应看到,包括X县在内,随着大量非本地大学生不断加入干部队伍,实际上也在逐步冲击着县域特殊的官场文化。
总之,只有通过追求确权与确责的平衡、扭转以结果论英雄和过度依赖负向激励的考核机制,并逐步冲击县域特殊的官场文化,才有可能真正走出“上级严厉问责-下级花式避责”的窠臼。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通过选择自变量极值的方式,尽可能地克服了第三变量的影响,但考虑到单案例研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可能依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一些在现实中可能会出现的问责案例,如因工作问题引发调查进而发现个人问题,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田野证据,就无法进行梳理和归纳,这显然是一个遗憾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