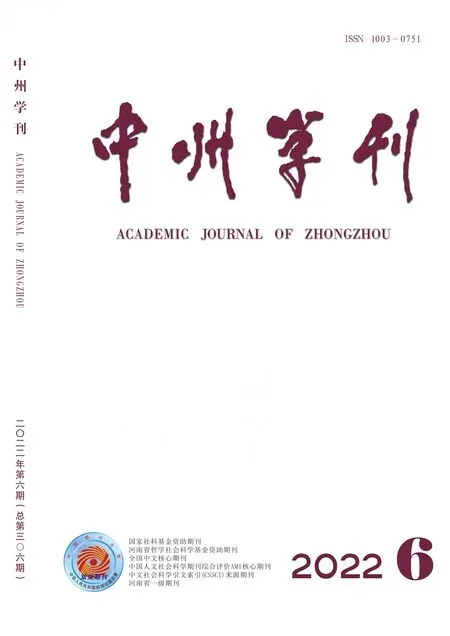《老子》“自然观”探微
2022-07-22顺真汤伟
顺 真 汤 伟
一、基于古文字向度对“自”“然”的再探讨
从过往的相关研究来看,论者大多集中探讨“自然”作为合成词的概念意义,而进一步深细的梳理乃是试着换一个视角,即先将“自然”分解开来,分别研究“自”“然”的各自语义,明确其多重意蕴,由此进行语义取舍,进而梳理出老子从“自”到“然”,最后确立“自然”这一哲学表达的逻辑与认知的甚深意趣。不言而喻,唯后一种方法才能够更深层次地对老子“自然观”做出既合乎古典文献诠释通则又不违普遍逻辑理性的深度诠释,因此,其为一条更加具有确实性的研究路径当属无疑。就直接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刘笑敢先生的大作《老子古今》两册,不仅集近代以来老子义理研究诸多论域之大成,而且其五种老子版本的对勘以及单字索引,已经成为今天研究《老子》最为便利的基底性文献,故相关的字词索引研究以该书为主要参考。
1.关于“自”
依据《老子古今》给出的索引,“自”字皆以在字句串中的形式出现,去除其完全相同的使用,单次出现累积共29次,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类,“自”作为介词,其义为从,如“自今”“自古”;第二类,“自”作为代名词,其义为自己,此类用例最多,如“自生”“自遗”“自示”“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自宾”“自均”“自知”“自胜”“自为”“自大”“自化”“自正”“自定”“自谓”“自称”“自名”“自富”“自檏(朴)”“自清”“自爱”“自贵”“自来”“自伤”,其在语句中作为独立语义皆是主语;第三类,“自”作为内动词,其义为由、因,如“自然”,其在语句中乃是作为谓语“然”之状语构成的来源(详见下)。就中,第二、第三关乎“自”的本义,尤其是第三项词义涉及“自然”概念的全新阐释,故有必要从古文字的角度对其作一精要的梳理。

如在某自我与某他者的对话中,某他者对某自我说“谁”,某自我以食指回指自身,其食指所指之方向,最自然的情形下,莫过于鼻子的位置。以指指鼻,则鼻即自,即被约定俗成为对反身之我的唯一指示,亦即通过以指指鼻的行为连接方式,“鼻”即“自”字便从“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独体象形字被引申为第一人称指示代词。深层而言,“自”这个第一人称指示代词,乃是指特殊具体情形中独一性的自我,就其为独一性的自我而言,其非指任何存在,唯是指谓当下独一的生命个体,这种言语命名所确定的“自”字之义,是非常精确明晰的。进而,我们才可以把“自”引申为对人人的指称与指谓,但当它一旦进入具体存在情境中时,其被指谓者必是一一独一的个体存在。是故,这个“自”就是独一之我、独一自我之义,亦即唯活生生的独一“自”,才能是确实性的自我。由此表明,“自”字在一般训诂解释的层面是第一人称指示代词,但在哲学上的解释,乃是人人当中的这个人或物物当中的这个物,亦即人人当中独一性的这个人而非他人,物物当中独一性的这个物而非他物。亦即,自乃是基于真实存在对人或物的确实性指称与指谓。
2.关于“然”
在《老子》一书中,“然”字亦以多种构词形态出现,去除其完全相同的使用,单次出现累计共10次,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第一类,“然”作为指示代词,其义为如是、如此,如“众父之然”“天下之然”“天下其然”“知其然也”“人之道则不然”之然;第二类为语末助词,如“超然”“合然”“默然”“繟然”之然,其义乃助形容词为其语尾;第三类为动词,如“自然”之“然”,其义为呈现(详见下)。



图1 两犬相争相卿图


二、《庄子》对“肰”(然)的深入讨论



三、从“自肰”到“自然”
这个问题关乎两个方面,一是如前所述关于《老子》早期写本“肰”字的字形考察,二是“自然”作为哲学范畴在哲学史上主要阐释内容的巨大变化。毋庸置疑,前者是后者的根基,即若对前者内在构成的义理基底不能真正明了,则对后者的理解难免处于一种外在性的梳理状态。
在《老子》一书中,“自肰”一词共出现五次:
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肰也。(竹简本,17章)
希言,自肰。(帛书本等,23章)
道法自肰。(竹简本等,25章)
夫莫之爵也,而恒自肰也。(帛书本,51章)



进而,以前文的考察为基准,可对上述五处“自肰”的用法作具体的分析。第一,从基础语义的理解来看,其每句都可以省略“自”但不能省略“肰”,则可知如“道法自肰”可省略为“道法肰”,但若省略“肰”而为“道法自”,则作为语句就难以理解。第二,若是则老子“道法自肰”的深刻意蕴乃为道取法于以一一“自”为因而呈现出的存在结果层面的“肰”,亦即老子创立“道论”,绝非超越于经验进而截断众流,唯在单一理性向度空悬出一个所谓理性概念的“道”去指谓一切存在的根基与本源,其乃为通过对一一之“自”依“自”而“肰”地呈现过程与结果,进而通过归纳逻辑的路径而提出“道”这一范畴,亦即深刻考察一切存在从因到果的经验过程而创立自家的学说,也可以说是老子依据老子本人这个生命个体之“自”所亲历内证的“因自而肰”的生命体验、历史考察进而在紫气东来、过关随缘的情境中,为后人留下五千言之绝妙好辞。太史公《老子传》曰:

所说“道德之意”的“意”,若从老子其人来看,似可以说就是老子本人内在生命“微妙玄通”所亲历体验的“因自而肰”,亦即老聃作为生命个体之内丹修行历程并最终证得如《庄子·天下》所说“博大真人”的“自→肰”。



在前文主要阐释“肰”的基础上,进而详细分析“自”的道学意趣。从“自肰”即“因自而肰”的阐释来看,自是肰的因,肰是自的果,而自作为存在结果之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因呢?
一方面,从经验的立场看,自是存在,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类自身之一一独一个体的存在。正如世界是有的存在,因此一一之自也是有的存在,而且这一一有的存在虽然在结果而言是一一独立个体,但其存在皆为相昫相待的存在,亦即作为独立个体之自我,必须直面亦作为独立个体之他者。因此作为经验存在的本质乃是自我之他者、他者之自我,唯自则不能不预设了他者,唯他则不能不预设了自我。套用《老子》第二章的说法即是:“天下皆知自之为自,他矣;天下皆知他之为他,自矣!”故就人类作为“群”之存在而言,其存在的表层只是角色转化下的“自我—他者”“他者—自我”。由此而言,自我非自、他者非他,互为因果、共损共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已。亦即经验之自,以其有形有质故必有生有灭、方生方死,如是则必为有限的存在而非无限的存在。《老子》帛书本第23章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熟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即是此义。天有天之自、地有地之自、人有人之自、飘风骤雨有飘风骤雨之自,但唯就此自而言,大到天地、中到人类、小到风雨,皆不能长久,其忽来忽去乃亦乍生乍灭而已。
另一方面,虽然如是,或即使许多智者也都认为如此,但那也只是自之存在的经验性而已,若从其来源来看,老子坚定认为一一经验之自,自有其无限永恒的超验性来源。《老子》帛书本第6章曰:“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之根。绵绵呵其若存,用之不勤。”同时,作为超验永恒的玄牝之门即道,其虽必然性地由朴而之散,但其核心在于,作为已然孕育万物子的万物母,其于一一独立个体之中到底是存在呢,还是到底不再存在呢?《老子》第21章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第25章又曰:“有物昆成,先天地生。寂呵廖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可知,道不仅是天地万物的因由,而且就遍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对此庄子有相当生动明了的说法:

“道在屎尿”,一语道尽!


因此,所说“由自而肰”的“自肰”实质即是“自”→“肰”,其有两个向度:一是由道生物,故《老子》第42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竹简本第40章又曰:“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亡。”二是从物返道,故《老子》竹简本第40章曰:“返也者,道动也。”竹简本第16章又曰:“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万物旁作,居以须復也。天道員員,各復其根。”若精要地概括,即是从超验到经验、从经验到超验;而若从存在结果来看,超验即经验、经验即超验。故若要人为地将道之自离于物之自,或将物之自离于道之自,即使虽可成一家之言,不仅其在逻辑上尚待推敲,究实而言,其离《老子》之“义”、老聃之“意”已相远甚。于此,其在后世相关的哲学阐释中尤以郭象的“自然观”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