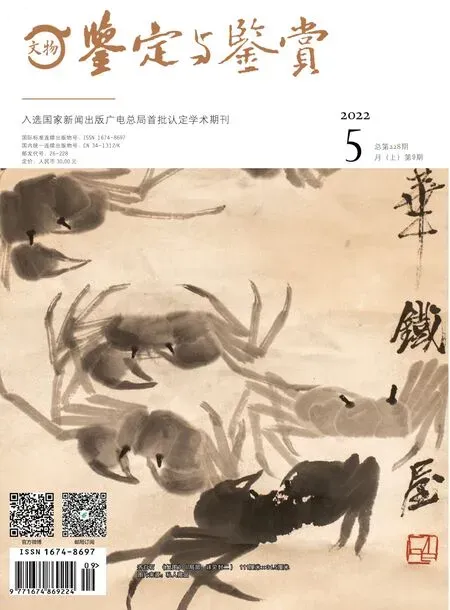从一件王懿荣手札谈民间文献类文物的收集
2022-07-22范琪
范琪
(沂南县博物馆,山东 沂南 276300)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收藏了一封王懿荣写给清代登州收藏大家张允勷的草书信札。这封信札是王懿荣收藏过程的见证,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1 王懿荣信札研究
1.1 信札内容
信札全文如下:
允勷姻世,讲足下去年匆匆一谭,又荷雅贶多珍,感谢无似。弟今年不及再请郡城话别,月底即北上再西行也。埙拓本一卣,埙拓本一历代年表一本籍已寄赠。外弟所著南北朝存石目二册寄来请略资繙览,览毕仍封交来人带回。此书大旨具在后序,尚未脱稿,行走皆以自随,到川刻成即以寄呈也。此后来往信件均请封固,幸勿致外人拆阅也。登州金石志之议当与足下共成之,幸勿怠忽,登州桑梓之遗一说亦然。外有单一纸开书画人名遇优请为弟购存也。
即请春安,弟懿荣顿首。
翻译为白话文,大意如下:
允勷世兄(姻世,未查找到确切含义,但从书信大意,笔者认为应当是王懿荣称张允勷为“兄”,清代和民国诗词中多见“姻世兄”称呼,如陈望曾的《叔臧姻世兄四十双寿倩吴江周维屏画松石图寄祝》、方仁渊的《戏简周子标姻世兄六十寿辰》等,均是平辈间的称呼),去年你我匆匆见过一面,你慷慨地赠送给我许多古玩,实在是不知道怎样感谢才好。我今年来不及再去找你见面了,月底我就要北上然后西行。我做的一本陶埙拓本、一本年表已经寄送给你。另外,我所著的《南北朝存石目》也已经寄给你,请翻阅指正,然后交给送书的人带回来。这本书主要的含义都在后序中,尚未脱稿,我现在随身带着以便随时修改,等我到四川刻版印刷后马上寄给你。今后,你我往来的信件一定要密封好,不要让外人拆开偷看。我们在登州讨论的金石志一事应当共同完成,千万不能懈怠,《桑梓之遗》也是一样(《桑梓之遗》作者是康熙、乾隆年间山东莱州府胶州书画篆刻家、收藏家高凤翰。高凤翰生前欲收集宋至清的百余位山东著名书画家的作品集,称《桑梓之遗》,但辑成三册后去世,其后《桑梓之遗》书稿辗转经过郭廷翕、郭季子、陈子懿、陈介锡等人之手,增至百册,由孙毓汶收藏。孙毓汶之后,《桑梓之遗》竟不知所终,现仅存有潍坊博物馆收藏一册)。另外,遇到单一纸开的书画,如果有比较好的,请先帮我购买保存。在这里我给你请安了,兄弟王懿荣敬上。
手札通篇为草书,书于暗黄色有鱼纹的宣纸上,颇为精美(图1、图2)。

图1 王懿荣手札全貌

图2 王懿荣手札局部
1.2 王懿荣其人及《南北朝存石目》
王懿荣,生于1845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投井自尽,字廉生、正儒,清代福山县(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清代山东收藏大家,因发现甲骨文而著称。王懿荣酷爱文物古籍,尤其潜心于金石之学。为搜求文物,他走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四川等地,收集种类涵盖书籍、字画、铜器、印章、钱币、石刻、瓦当等。
信中提及的《南北朝存石目》,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着手,到光绪七年(1881)成书,耗时长达19年时间,成书过程中,匡源、潘祖荫、缪荃孙等17位名流、学者曾给予帮助。《南北朝存石目》收录内容时间涵盖南北朝至隋代,分为碑、志、记、梵典四类,按拓本年月著录,年代不确者分类附后。《南北朝存石目》被《山东通志·艺文志》收录,称为《六朝石刻存目》,但未能刊行,仅存稿本。《南北朝存石目》之后,王懿荣又作《汉石存目》上、下二卷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刊行,王懿荣自识:“近世所存汉石已尽于此。”此外,王懿荣还著有《王文敏公遗集》八卷、《天壤阁丛书》(与其父王祖源共同编辑刊行)、《翠墨园语》、神州国光社(1954年并入新知识出版社)版《古泉精选》一卷等。《汉石存目》与《南北朝存石目》是王懿荣除发现甲骨文外,在金石学方面的最大成就。这两部存石目录在当时看来,分类准确、收录内容丰富、体例守备,堪称清代石刻目录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1.3 允勷其人
允勷,当是张允勷,是清末山东登州(今蓬莱)收藏大家,涉猎甚广,包括汉画像石、书画、砖瓦、古钱币等。王廉生云:“近年蓬黄福三县所出之古砖,大约西归黄县王穆庵、丁彝斋,北归蓬莱张允勷,东南则为烟台之官商取去。……允勷砖以‘日主五官之堂’及‘上大夫’为最精。”陈介祺62岁那年还派胥伦到蓬莱张允勷处拓图,其中有“长安乐”砖拓和“节墨小刀化”,并把这些拓片寄给王懿荣鉴赏。
张允勷藏石,以汉琴亭国李夫人墓门画像石最著名。汉琴亭国李夫人石门画像石俗称“汉鹿”。据《蓬莱县地理志》记载,此画像石“清同治壬申出于第六区河北乡余家村(沈余村)”,现由蓬莱县文物管理所珍藏。碑长105厘米,宽46厘米,厚30厘米,一端空白,一端刻隶书“汉廿八将佐命功苗东藩琴亭国李□夫人灵第之门”21字,中部浮雕卧鹿,鹿角冲出边栏,极为生动。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杨守敬《寰宇贞石图》及香港梁披云所编《中国书法大辞典》等均予著录。
关于张允勷发现此画像石的过程,《语石·卷五·私家藏画像石条》描述为:“同治中,蓬莱张允勷处士,笃贤好古之士也。以事之东乡饮马于井,见井阑之石甚古,以手拊石下,觉有字迹,因经乡人购归。辨其字画,中间一鹿隐起,左方题字为汉琴亭国李夫人灵第之门,远近传为异品。陶斋曾以五千金相易,张君坚拒之,益自珍秘。此石以翻刻一本,以应索拓者。陶斋之力犹且不能致,名遂大著,今尚在张氏也。”光绪重修《登州府志·金石志》亦云:“同治壬申(1872),村人甃古井得此石,蓬莱张氏得之,因摹以传。”从清代诗人王鹄的题跋来看,汉琴亭国李夫人墓门画像石最早拓片拓印于同治癸酉(1873),即此画像石出土后次年,该拓片最初赠送给潘祖荫,又历经十余位收藏名家题跋、钤印,显得弥足珍贵。
汉琴亭国李夫人墓门画像石拓片传世甚多,2006年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12年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等曾拍卖过其拓片。其中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拓片钤印有十余个,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图3)。天津市同方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曾在2012年拍卖张允勷藏金石砖拓本,无论拓器、题跋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审美价值。

图3 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所拍卖李夫人墓门画像石拓片
1.4 信札书写时间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中进士后归里省亲之际,腊月二十三农历小年后,王懿荣冒雪赶到登州府城,并在蓬莱逗留两天。虽然他是第一次到蓬莱,但他没有去蓬莱阁等名胜,而是去拜访张允勷,观看蓬莱县东边郭村出土的张允勷收藏的文物,发现这批文物多而且精,“不及细数”,可惜却无一本旧书。这次见面,应当是手札中提及的“去年匆匆一谭”,因此可断定这封信札写于次年,即1881年。
从信札内容来看,王懿荣和张允勷虽只有一面之缘,但交情颇为深厚,互有往来,可谓君子之交,称得上是清末金石界的一段佳话。
张允勷涉猎甚广,藏品颇丰,但有关他的史料却极其稀少,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1.5 王懿荣书法造诣及信札价值
王懿荣最大的成就是发现甲骨文,其书法造诣常被人们忽略。王懿荣家族世代显赫,在明清两代先后出六名翰林、二十四名进士、五十八名举人。乾隆皇帝曾称赞王家“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王懿荣自幼年起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后受业于外叔祖谢学庵、母舅谢琴南、谢价人、表伯张墨林、翰林编修崔清如、礼部主事周孟伯等。
王懿荣出身书香官宦之家,他个人必然把通过科举入仕作为目标。科举考试仅凭一张考卷断定优劣,因此考试中书法字迹工整、秀美显得尤为重要,每名学子从幼年时即把书法作为学习的重中之重。王懿荣家族世代为官,书法功底必定深厚,写字功课自然是王懿荣幼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伴随其终生,这也奠定了他深厚的书法功底。
道光年间,社会动荡不安,大批碑帖、书画、文玩在社会流散,金石学家、收藏家有了更多搜购机遇。王懿荣所著《天壤阁杂记》中记载,临淄到青州,河南、陕西至汉中一带,到处是古董坑,每次去都流连忘返,不舍地离开。在此期间,他利用省亲和游历在鲁、陕、川诸省搜购大量金石,其中不乏《道因碑》《智永千字文》《岳麓寺》《圣教序》《九成宫》《曹全碑》《乙瑛碑》等大宗珍贵拓本。
王懿荣在青年时代即注意交游,与当时的礼部尚书匡鹤泉,工部尚书、经学大师潘祖荫,翰林编修缪荃孙,收藏大家陈介祺、吴大澂,书画家赵之谦等均交往甚密。授庶吉士后,有了更多的切磋艺事的朋友和机会。这些人或是文人雅士,或是朝中高官,更是当时知识界的精英,对王懿荣收藏和书法帮助极大。
王懿荣在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光绪九年(1883)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在光绪二十年(1894)升迁侍读,入直南书房,任职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国子监祭酒达三次之多。光绪二十年又擢升一级,成为三品衔国子监祭酒。仕途顺畅,让王懿荣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研究金石书画,曾多次被召“鉴别书画”或“恭代御笔”。
良好的教育、丰富的阅历、广泛的交游以及身居高位,促成了王懿荣深厚的书法造诣。清人曾评价王懿荣的书法“刚健清华,无美不备”。清末,有“翁(同酥)、王(懿荣)、何(绍基)、戴(彬元)书法四家”之称。王懿荣书法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很广,曾为四川的雪堂书写《大朗和尚封号碑》、为孙诒让题“百晋精庐”和“百晋陶斋”、为丁培绅(山东大收藏家丁榦圃之父)书写墓志。
王懿荣楷、行、隶、篆各种字体皆通,尤其擅长行书和楷书,书法风格深受唐代书法家李邕(史称“李北海”)的影响,他对自己的行书、楷书也较为自信。现存王懿荣书法作品中行楷对联最多,牌匾、手卷次之,而信札甚少,并且这封信札通篇为草书,运笔流畅,用纸考究,是研究王懿荣书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2 民间文献类文物收集相关问题思考
王懿荣信札收藏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1992年由临沂市文物店移交。移交后,这件信札一直用宣纸包裹,很少有人知晓其内容,直到2014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才由普查人员采集数据,并发现其文献价值。由此,笔者联想到,在我国民间存在大量私人文献类文物,如敕封、考卷、地契等,这些文献类文物湮没于民间,难以发挥其价值。如能通过妥善方法将其收集,无疑会对研究古代和近代社会各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例如,青州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魏振圣在筹建青州市博物馆过程中,为了征集一件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往青州城东20千米的郑母村跑了24趟,最终打动赵秉忠13代嫡孙赵焕斌,使大家有机会看到这件国内外唯一的明代殿试状元卷真迹。
再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馆藏清乾隆四十五年封诰,与王懿荣信札经历相同,也是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才引起关注。这件“敕封”内容褒扬父母对子女的教导及妇女的相夫教子、贤淑等,引导子女答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以父母为榜样,以对长辈的孝顺作为对皇帝(国家)的忠诚,是对“孝”和“忠”的一种宣扬,在今天无疑具有正面教育意义。而这件“敕封”是从惠民县流传而来,至于被文物点收集的过程无从考证。
在收集文献类文物过程中,整体感觉是当前工作偏重于地契、宣传材料、文件等革命文物,对书信、文书等私人文献则重视不足,而这类文献中,往往包含有大量信息。同时,随着民间收藏越来越受到社会追捧,很多市民受到误导,认为家中的文献资料都是“古物”“国宝级”,过多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加上博物馆大多经费紧张,造成这些资料难见天日。在文献类文物收集方面,笔者认为要在几个方面努力:一是政府重视,私人文献与其他文物同收集、同研究、同保护;二是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引导市民正确看待家中的文献类文物,在必要时候以合适价格转让给博物馆,甚至无偿捐献,使更多人有机会看到这些文物;三是加大博物馆文物征集经费扶持;四是经常性开展民间文献类文物信息采集工作,对无法征集的民间文献类文物进行信息采集,在不发生权属变更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历史价值。
①叶昌炽,柯昌泗.语石:语石异同评: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4:339.
②龙震.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馆藏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勅封[J].写真地理,2018(1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