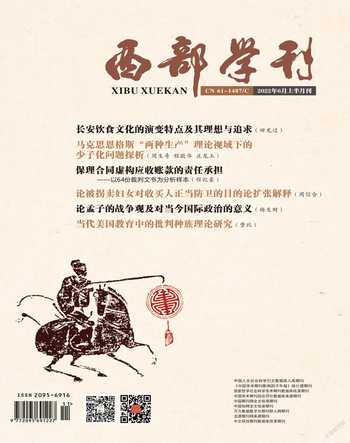精神分析与话语实践:克里斯蒂娃眼中的女性主体
2022-07-10陈思旭
摘要:作为二十世纪末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克里斯蒂娃沿承了拉康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将女性命运与境遇放置在“符号态”与“象征态”的对照中予以论证。在个体微观学的透视之下,克里斯蒂娃看到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表象之下的话语危机,并将解放之可能性诉诸于“司各特主义”,主张在无意识挖掘和诗性语言的创造中实现“符号态”与“象征态”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精神分析;符号态;女性主体
中图分类号:C913.68;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1-0173-04
作为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吸收了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多元领域的知识养分,在性别理论、精神分析和文学创作等方面上颇有建树,撰有《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国妇女》《恐怖的权力——论卑贱》等著作。克里斯蒂娃与西苏(HLNE CIXOUS)、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共同占据了法国后现代主义性别理论的主流地位,她借助精神分析和符号学对女性主体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代女性运动有着独特见解。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逐渐走进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她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一、“符号态”与“象征态”:精神分析中的女性境遇
延续着精神分析的脉络,克里斯蒂娃探索了女性生命经验中所遭受的时空压制,揭露了欲望生产机制中的女性被动。在弗洛伊德看来,女童走向成年必须经历从内在生产的性冲动转向由接受男性性征的外在吸引而产生的欲望机制。拉康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延伸:个体从儿童期过渡到成年期往往需要脱离“母性空间”跨越到“语言主体”的象征秩序之中。在此基础上,对于性别差异抱有矛盾态度的克里斯蒂娃一方面想要摆脱西方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框架,另一方面她又借助精神分析法,在母子关系的纠缠和分离中找寻这种差异的存在。
想要理解这种差异,需要把握克里斯蒂娃所一直强调的两个相对的概念:符号态和象征态。两者均作为主体意指过程的两种模态,在克里斯蒂娃的文本中,符号态被表达为“母性空间”,或被称为“穹若”,它是个体未经驯化与规训的生命原点和无秩序空间,标记着个体被去除了同一性和统一性的还未开始的状态。符号态是母亲神圣而混沌的身体,它孕育着无意识,安放着驱力与冲动,也牵绊着女性踏入象征态的脚步。象征态支撑着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主宰,包含了一切象征秩序与结构性束缚,“这些束缚通常源于物的差异和具体的、历史的家庭结构。”[1]
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配下,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以男性统治为根基,又通过制造二元對立的概念体系来强化男性统治。西苏曾提到,这些概念的对立正是源于男性与女性的对立。阳与阴、秩序与混乱、理性与感性、明与暗、灵魂与肉体,前者在男性中心主义的象征界呈现出来,后者则在母体原始混沌的符号态中涌动着。
在拉康的理论表达中,这种二元对立的阴影在主体生成的过程中完整地表现出来。儿童需经由与母亲的分离才能迈入象征界的意义联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克里斯蒂娃延续着拉康的道路,认为女性想要进入到象征界,就必然要加入纵欲享乐的母性身体与基督教禁欲的象征秩序的斗争之中,后者压抑着前者,而前者又会在不经意间从秩序的裂缝中涌现出来[2]。在亲属关系法则和言语的交流系统中,父亲的象征秩序不断生成并强化,前者规定了对父姓的传承和对乱伦的禁忌,构建了以父亲为核心的稳定的关系纽带;后者代表了一种高度逻辑化的、科学化的语言[3]。这种语言从属于象征态,象征秩序皆借助语言实现生成、传递和强化的任务。语言建构了秩序:象征态隔离了充满韵律的、节奏感强的“诗意”话语,并冠以其无意义的标记,放逐在符号态的母性空间中,从而建构起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象征秩序。在此,母亲的身体是无法被语言言说的,她是如此的隐晦,被压抑在男性话语的同一性表象之下,而作为母性产物的无意识也被排斥在象征秩序的主流话语范畴之外。
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支配下,象征态和符号态的分裂既体现在空间上,更在时间维度中划定出男性的范畴。近代以来的时间特质是典型的属于“父亲”的、“男性”的时间,它是线性的、直指未来的,以进步为前提的历史时间。在此,男性作为历史的主宰,并未给女性留下书写与创造的时间[4]。女性被围困在无意义的反复之中,身处生活空间的被规定之处,扮演着被支配者的角色。其生命的周期性和韵律感与宇宙万物循环反复的生物学规律重叠,显现出圆环的形态。然而,无限反复的日常生活与奔赴历史的终点并无关联。在此,女性表达总是持续缺场,其表达自身的方式只能是沉默着成为女性。
然而,想要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统治,却要先接受象征秩序的洗礼与同化。拉康曾尖锐地提出“女人是不存在的”,女性只是男性爱欲的外在投射对象。克里斯蒂娃则说“古希腊城邦作为一个完美的、超越家庭的政治共同体,是经由反俄狄浦斯的机制建立起来的,没有厄勒克特拉对父亲的固恋,就不会有城邦的历史”。如此,为了与“他者”建立契约的女性进入父亲的时间里,参与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共同体实践。在此,超我伴随着本我与自我的崩塌与消解逐渐建立起来,意识随着无意识的暗淡而逐渐明亮。这一背离母体而与父亲的“同一化”过程,使女性有望突破性别差异的压制而进入象征态,即使这种行动本身就建构出巨大顽固的差异。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提到的“规范的性欲强化了规范的性别”。如此一来,女性“一部分在男性统治的空间中扮演着官僚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一部分则成为愤懑不平的左派分子”[5]。
二、个体微观学:透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话语陷阱
与父亲积极的“同一化”过程固然使得女性主体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放大,但克里斯蒂娃却认为这种并未脱离男性话语秩序的集体行动未能使个体生成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
在与他者的权力争夺与话语较量中,女性主体缓慢而艰难地拼凑生成。在三个阶段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克里斯蒂娃发现了根植于其中的“去差异化”和“排他性”倾向。第一阶段的女性解放运动围绕男女平等的价值理念展开了一系列争取女性参政权、财产继承权、受教育权的运动;第二阶段的女性解放则在波伏娃《第二性》的巨大影响下掀起波澜,此阶段的女性运动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在自由主义思潮下的女性运动开始关注性别平等,激进女性主义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框架下分析女性受到的父权与资本的双重剥削,反抗与此相关的性别分工和家庭关系。第三阶段的女性解放则受到“五月风暴”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致力于挖掘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性体现在性经验、文学创作、政治行动等多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集体主义的“否定性”实践,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并未有助于女性思考其独特的生命经验和生存境况。其根源首先在于它忽视了个体生命特质的独特性,对个体进行了“去差异化”处理。在此过程中,女性以整体行动单位出现,那些附着在个体身上千差万别的社会性因素被通通抹平,女性成为一个空洞抽象的简单概念。此种未经主体性思想过滤的集体行动已经退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反常活动,不仅未将女性从生存境遇中拯救出来,反而存在沦落为极权主义的危险。
其次,克里斯蒂娃意识到妇女解放依赖于一种身份政治,其实质是建立起基于身份认同的排他性防线,在基于性别差异的阵营划分中,同质性社群成员对异己者采取了驱逐排斥的策略。此外,克里斯蒂娃批判了当下西方女权运动正在强化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秩序。那些声称“我是女性”,以便改变女性在生育代价、职业机会、教育公平等方面的不公待遇的口号,并没有真正将女性带离生存困境和思想压迫。以此对照,我国女权主义运动借助网络与舆论推动现实社会中结构性不公的显现与批判,在整体上呈现出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张力,建构对立的话语斗争始终先于权利平等的制度化保障,形塑出网络文化的“后现代状态”与现实文化“前现代”状态之间的分裂局面。两种社会情境下的女性主义运动皆反对作为一种消极实践,吞噬了女性对同一性的反思和审视,使其将解放的希望寄予“他者”,从而成为隐藏在言说与表达之下的危险陷阱。
克里斯蒂娃意识到,女性在物种繁衍上的特殊性使其更多受到道德伦理教化和父女、夫妻关系等结构性的外在责任束缚,相比于生物性征和机体属性带来的规定,前者更为明显,所以女性更倾向于对外在的否定而非内在的尼采式的狂怒。即使她肯定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进步意义,但她依旧认为身为女性的困难和压力,并非仅存在于那些外在的,主体可以轻易表达的那一部分,而更是潜在着的,无法被言说却决定着女性命运的那一部分。因此,克里斯蒂娃强调了对“女性”的去命名化,她提倡将“女性”从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抽离出来,否定了那些从形而上学层面上定义女性的理论。相比于积极热烈的“为权力而战”的女权主义运动,她希望这种行动策略应该是的“消极”的,甚至直接提出“对抗女性”的主张,其意图则在于摧毁那些固着在女性身上,使其成为女性的标签与符号。
在1974年的中国之行中,克里斯蒂娃更为警醒地认识到社会变迁与历史沉浮中女性命运的跌宕起伏。在中国,性与政治的紧密联结使得妇女解放道路与政治变革的轨迹重叠交叉,女性的身体既消化吸收着儒家伦理教化,又孕育着革命的火种和解放的生机。借助对文本与史料的考究,克里斯蒂娃在宋朝文人李清照的词韵参差中看到了对秩序的超越,又在向警予、蔡畅、邓颖超等人身上看到女性炽热的革命激情以及企图冲破封建枷锁的魄力和坚毅。
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中,克里斯蒂娃则关注到阿伦特、克莱因和柯莱特潜在的女性特质,她们对主体间性的深沉关怀、思想与生命的高度融合和不断新生的执着观念,使其摆脱了两态对立,完美地呈现出“游离”的生命状态。阿伦特对极权政治和平庸之恶的反抗与对政治体制凝滞状态的拒斥;克莱因借助“反移情机制”探索分析师如何在回溯童年经历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和对象的双向治愈;柯莱特则敏锐地捕捉到母亲茜多专注于事物新生的热情而不选择身陷关系的囹圄。
可见,她们都以积极的意志围绕自我的生命经历和情绪体验重新塑造着独特的思维观念,这无疑为迷航中的女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不必偏執于对象征秩序的追求,亦无需在符号空间的荫蔽中畏缩不前。生活,就是“思想、升华、书写”。
因此,克里斯蒂娃认定真正的女性解放应朝向“司各特主义”(Duns Scot),实现个体的特殊性。她希望女性立足于自身生命的独特性,借助精神分析挖掘那些神秘强大而充满魅力的品质,在某一历史的关键时刻将此种品质完美呈现出来。需强调的是,克里斯蒂娃对个体微观学的聚焦并非意味着她放弃了对广泛意义上女性解放的价值追求,她坚信个体对自我的认同、对生命的欣赏和热爱,是女性改变自身境遇的关键一步。因此,她更崇尚“个人的政治”而非“集体的政治”,注重“个体特殊性的意义挖掘”而非“群体普遍性的价值狂热”。
三、符号的生命感:个体解放是否可能
克里斯蒂娃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强调了符号的生命感,她看到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已经无法对时代出现的新状况进行完全的说明,她呼吁人们应以全新面貌积极改变那些可以称之为符号的事物。因此,克里斯蒂娃希望女性能够掌握语言表达和文本创造的自由和自主,在无意识的挖掘中赋予符号生命感,通过激发女性对自身生命的诗意创造来撼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秩序。作为揭露无意识机制的重要工具,精神分析能够帮助个体把握行为表象背后的无意识冲动和本能驱力,挖掘蕴含在母性空间中的隐秘能量,从而激活个人语言系统中的诗性创造。
在语言的范畴内,诗性语言作为符号的生成系统,孕育了主体及其主体性。正如德·塞图所提及的“一部书写的文本,亦即一个由符号系统生成的地点”[6]。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文学创作是无意识涌动和诗性语言的书写相互结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符号态与象征态相互融合,在动态的辩证过程中促进了意义的生成,并肯定了主体在语言表达中享乐特权的正当性。在克里斯蒂娃眼中,这种诗意的表达方式是对自由人性的释放,是潜在的、隐秘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但克里斯蒂娃并未放弃对社会结构的现实考量和对集体价值的实践追求,她重新厘清了语言实践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辩证关系,并强调了语言实践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经由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过滤,克里斯蒂娃十分清醒结构与能动之间的紧密关联,无论是文学创作中主体无意识的涌动还是语言文本的书写表达,都是铺垫在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背景中。教条主义和美学神秘主义曾挖空文学实践的政治性根基,但克里斯蒂娃将极具个人主义色彩的话语表述放置在主体间性的意义脉络中,赋予主体无意识以强大能动性,她将文学创作重新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土壤中,从而使文学与文本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暴力。
当然,这种旨在构造符号生命感的无意识活动并非仅仅停留在语言范畴内,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超语言领域,克里斯蒂娃也提倡个体要基于人的特殊性积极敏锐地在周遭世界的经验中探寻潜隐的无意识活动。
克里斯蒂娃认为,男性居于象征界的主体地位,女性则游离于象征界的边缘地带,此种游离状态并非将女性置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而是赋予了女性更大的创造性和破坏力。在代表着规训与权力话语的象征态和孕育着混沌与冲动的符号态穹若之间,她可以以周期性的、充满韵律感的生命特质书写、表达,生成具有颠覆作用的诗性的意义。在父亲迷恋线性的、进化的时间范畴和母体生命特质的规律性循环之间,她可以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中不断新生。作为女性,她们并不拘泥于象征界的僵死和固化,并不偏执于制造无趣的统一性话语秩序,而总在无意识之中创造出一种飘浮着的、不断变化和流动的开放式语言。
四、结语
克里斯蒂娃的性别理论为我们构建日常生活的“微型实践”并激发个体“诗意”创造的抵抗之路提供了启发思路。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最有利于女性的表达与创造,而不使语言的浪漫与诗意被扼杀在他者眼光的审视之下。此外,应意识到克里斯蒂娃对女性主体的探讨的局限所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合理的劳动分工和经济剥削依然使女性面临巨大压力、父权主导的家庭模式中母职捆绑的社会事实依然存在。因此,在社会结构、制度规范和道德文化的多重领域为女性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开放平等的公共空间依然是我们当代社會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M].张颖,王小姣,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16.
[2]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M].赵靓,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20-24.
[3]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M].王青,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8.
[4]JULIA KRISTEVA.Women’s Tim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20.
[5]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M].宋素凤,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17.
[6]米歇尔·德·塞图.日常生活实践[M].方琳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2.
作者简介:陈思旭(1997—),女,汉族,山东淄博人,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文化社会学。
(责任编辑:朱希良)